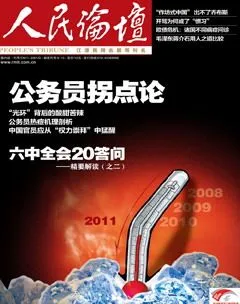透视溺水事件中的法律纠葛
2011-12-29梁志波范秀娜
人民论坛 2011年21期
编者的话
目前,依照现有法律,消防队是国家救援工作的主力,民间救援队只能是补充力量;而且针对民间救援行动,我国尚未颁布任何法律法规,这也意味着大多数民间救援队还没有合法的身份。
民间救援力量依然还在夹缝中生存。我们经常会看到民间救援受阻的情形。据新京报10月9日报道,一名天津驴友在长白山穿越时不慎坠入山崖,全身受伤。蓝天救援队迅速赶到,却被拒绝入内。景区相关负责人的解释是,森林防火期外人禁止入内。而一名警官认为“怕人太多导致现场混乱。”
当然,国家针对民间救援组织的政策正在不断完善中。撇开民间救援自身的不足不谈,合法的身份和认同是民间救援崛起的先决条件。否则,不光救援受阻,救援行为也容易陷入法律纠葛中。
某市一名市民溺水于某湖中,该市冬泳协会成立的一个民间公益性组织“水上义务搜救队”,接到河道管理方的求救电话后,带志愿者迅即赶赴现场欲施救,却遭到了在场巡防队员的阻止。巡防队员同意溺水者家属下水救人,但要求志愿者必须出示“打捞许可证”方可下水救人。然而,溺水者家属不习水性、无法下水,因此,志愿者强烈要求并与巡防队交涉一个小时后,方得准许下水,6分钟即将溺水者打捞上岸,但已是尸体一具。
悲剧是令人痛心的。然而,公众的狂欢无助于司法权的公正实现,公众的狂怒也无助于行政权的正当行使。认清事件背后的法律纠葛,才能正视听、鉴往来。其中,特别需要明确的是救人是否属于行政机关许可的事项范围呢?
湖泊“打捞许可证”是否有依据
目前,关于内水打捞作业方面的管理法规,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于1999年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潜水员管理办法》,2002年由国务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另外还有2010年交通部救捞局制定的《专业打捞船舶调度指挥管理办法》和《专业救助船舶调度指挥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潜水员管理办法》第二条规定,本办法适用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水域,从事产业潜水作业的潜水员,不适用于从事军事、科研、娱乐和运动的潜水员。下水救人有可能需要潜入水下寻人,但并不属于第二条规定的产业潜水作业,因为志愿者完全是见义勇为,不收取任何报酬。下水救人也不属于第二条列举排除的军事、科研、娱乐和运动,但列举排除的四种潜水都具有非盈利性,该水上义务搜救队的宗旨是明确的,明显具有非盈利性,因此,排除《中华人民共和国潜水员管理办法》的适用,亦即,见义勇为者无须获得该办法要求的潜水员证书方得下水。
《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第九十一条专门就条例用语的含义进行解释,内河通航水域是指由海事管理机构认定的可供船舶航行的江、河、湖泊、水库、运河等水域。船舶,是指各类排水或者非排水的船、艇、筏、水上飞行器、潜水器、移动式平台以及其他水上移动装置。因此,该条例适用于湖泊是不存在问题的,但该条例规制的对象限于船舶和船员,针对的事项是交通安全,下水救人事项不在其列。至于《专业打捞船舶调度指挥管理办法》和《专业救助船舶调度指挥管理办法》所规制的对象亦为船舶,亦不适用于下水救人。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下属的内设司局单位搜救中心于2009年发布的《关于加强非水网地区水上搜救工作的指导意见》可以针对下水救人事项,但搜救中心作为一个部委内设机构,所制定的文件仅具有内部效力,不具有普遍约束力。另外,该指导意见在第三条第三项就加强水上搜救队伍建设中明确提出,要按照“专群结合、军地结合”的模式,充分发挥军队及社会力量在搜救中的作用,并要求鼓励和招募志愿者参与搜救,并辅以适当的培训。该指导意见的导向是明确的,即搜救和安全为第一要务,对社会力量参与搜救是鼓励的,对志愿者是明确欢迎的。
从以上文件可以得知:其一,内水中的个体搜救作业并非行政许可事项,巡防员要求出示打捞许可证毫无依据;其二,对于非水网地区水上搜救工作,政府鼓励志愿者参与,搜救并非为公权力所专有,私力救济、民间力量皆可介入。
“打捞许可”反映了行政权的扩张性
行政权力的存在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维护社会秩序之需,公权力的唯一来源是个人权利的让渡,社会个体将自身部分权利集体让渡给公权组织的根本目的在于期望通过这种让渡,给自身利益的实现创造一种社会秩序,这种社会秩序包括了和平、安全的公共秩序;社会资源的合理开发、分配和利用;主体利益的有效保障;符合主体间共同意志的道德的维护等。行政权的支配对象是或直接或间接的个人权利让渡的产物,由此决定了行政权与个人权利的根本冲突。行政权本身具有扩张的内在冲动,同时由于人性自利的天性使然,行政权具有异化的趋势。
因此,对于行政权的控制与驯服成为现代行政法的基础。法定性是行政权的特征之一,它意味着任何一个组织的行政职权都是法定的,而不是自我设定的。换言之,行政主体拥有或行使行政职权必须通过合法途径,否则便不能成立。公民行使权利时,法无禁止即为许可,这与专制时代的法无许可即为禁止相反。而巡防队要求志愿者出示尚未存在的“打捞许可证”,且不说巡防队是否为本文情形中的适格执法主体,即便其拥有湖面作业的执法权,这种超越权限的行为也是对行政权法定的违背,这种要求主观上源于法无许可即为禁止的思想,志愿者不能出具这些巡防队员头脑中臆想的“打捞许可证”,便被禁止下水,是行政权的恶性膨胀对个人合法权利的漠视和挤压。本质上则是行政权与个人权利的冲突,行政执法者过于陶醉于其强势地位,而忘记了其权力来自于人民的赋予。未经依法赋权,虽一湖之狭促,打捞之稀有,尚欲一展权力之长翼,视为禁鸾,虽牺牲无辜生命而不惜,置中央倡导并力行的服务型政府于何地?置人民的生命健康于何地?
巡防队员在阻止志愿者下水的过程中,保持着与上级的联系,因此,这些行为属于职务行为,是违法行政;职务行为导致公民因搜救不及时而溺死,属于《国家赔偿法》第三条第五款规定的侵犯人身权的情形,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
是否有人应为死亡结果负刑事责任
因为溺水者被志愿者打捞上来时已经死亡,而志愿者们也并非在溺水者入水的当时即在现场,可于落水瞬间便展开搜救,所以不能得知,若不存在巡防队员的阻拦干扰,志愿者赶来进行施救,溺水者是否一定能够生还,如果此时溺水者必能救活,则阻拦者的行为则与死亡结果存在因果关系,亦即,阻拦是溺死的原因。若即使无人阻拦,志愿者到现场进行施救,而溺水者仍然无法生还,此时巡防队员的阻拦行为与溺水者的死亡之间就不存在因果关系,阻拦行为没有对死亡结果进行加功,巡防队员所阻拦的无非是志愿者打捞尸体,而非挽救生命,自无刑事责任存在。在无人阻拦的情况下,志愿者马上展开施救,溺水者可被顺利救出得以生还,那么,巡防队员明知其阻拦行为将导致溺水人的死亡结果发生,仍断然阻止搜救者下水施救,将搜救行动延迟一个小时,以社会一般人的观念来判断,溺水一个小时后,断无生还之理,因此,巡防队员对溺水人的死亡结果持放任态度,而且溺水人死亡的结果果然出现。这符合刑法中不作为犯以间接故意实施故意杀人罪,不能排除巡防队员的刑事责任。
(作者单位分别为北京市延庆人民检察院,河南省人民检察院)
责编/张晓 美编/石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