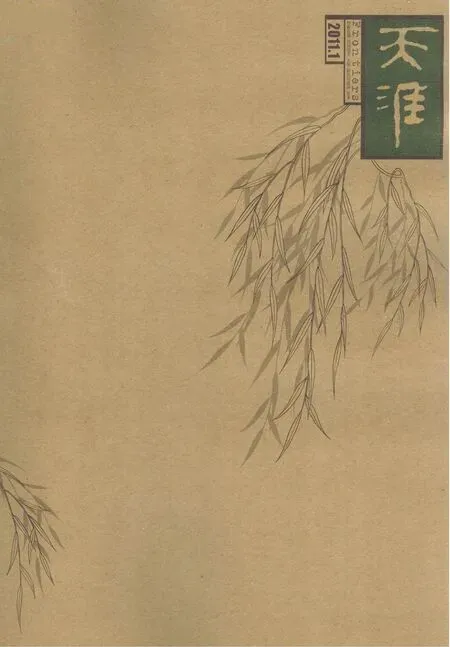教堂
2011-12-25徐则臣
徐则臣
在美国我拍得最多的建筑是教堂,远远看见它们举上天空的十字架,我就把相机打开,一个都不放过。整理照片时发现,拍下的各类教堂数十座,如果不惮于摄影技术的简陋,可以考虑办一个教堂摄影展。我是无神论者,可我喜欢教堂,喜欢它们的高瘦挺拔和清冷庄严,在我所见的美国建筑里,它们比芝加哥的西尔斯大厦与天空靠得更近。当西尔斯大厦的顶端在高处的某一点停住时,所有教堂的十字架继续上升,不论它们有多矮,垂直于天的那一端像一根根执拗的手指,一直指上去。
——我是无神论者,喜欢教堂。作为一种建筑,教堂最大限度地体现了民间纷繁复杂的建筑智慧,你很难看见两座长相雷同的教堂,一座一个样,它们极大地满足了我这个形式主义者的癖好;同时作为某种让我着迷的精神象征,它所负载的信仰的力量让我震惊。一座教堂也许只是一个美的形式,无数座教堂一起,就从形式变成了内容,既抽象又实在,就像看见千万人一起弯腰、祷告,向一个共同敬畏的神灵说,我将与人为善,我渴望安宁的来生。我一座接一座地看,源源不断,这是个充满了基督教的国家,永远有你看不完的教堂。
在奥马哈,我拍下了五座教堂。但据说这个不到四十万人的城市里,教堂百座有余,可惜我不能总是把相机像钱包一样随身携带,所以对一闪而过的很多教堂只能扭回头狠狠地再看一眼。在奥马哈,有两座教堂每天必看。一个月里我从不同的角度给它们俩拍了无数张照片。
一座在我住的J教授和Y教授家的旁边,出门就能看见并列耸向天空的教堂双塔。这是座古老的教堂,高大雄浑,听说内部装饰极为华丽,必须借用“金碧辉煌”这样的汉语成语才能解释清楚。在J教授的介绍里,我总是想到凡尔赛宫和克林姆林宫,因为只有欧洲的宫殿才会有巨大的穹顶,有哥特式的窄门和坚韧的立柱。在故宫还叫紫禁城的时候,在皇帝和嫔妃们还活着的时候,奢华则奢华矣,那个空间却是平面的、向下的,别人指向天,我们指向地,我们要牢牢抓紧大地得到现世的权势和荣华才能放心。我一直想进教堂里看看,又怯于一个人进去,我总是看见它大门紧闭,而板着脸的巨大的门让我本能地感到神秘和恐惧。——这有道理又没道理,因为教堂本质在于宽容、接纳和施与,天国之门欢迎万方来朝。
也许正是源于这个神秘和恐惧,我总会想象如果我推门而入,那会是一个经典的电影镜头,一个忐忑的小偷进来了。无神论者也可以有恐惧,所以我宁愿不进去。我只把它放进镜头里,啪嗒一张,啪嗒又一张。
如果去克瑞顿大学,必定要经过大学的教堂。教堂始建于1878年,根据这个古老的年头就可以想象它的雄伟和庄严。受一些三流影视剧的影响,我总有一个固执的错觉,就是这教堂依山面海,山在高山之巅,背后是万丈悬崖,中世纪的风擦着后脑勺呼啸而过。事实当然并非如此,这大学教堂只是处在一个高地上,两个塔尖直插云霄,因为高大,每次拍它我不得不仰拍,这更助长了它的傲岸,简直成了连接天地的唯一的路。这教堂必须要建得伟大,因为克瑞顿大学是教会大学,教堂是中心,所有的建筑和活动要围绕它展开,就像斯蒂文斯的那只著名的田纳西罐子,这是世界的原点。
克瑞顿的教堂门楣宽大,周围装饰浮雕,有天使在墙壁上飞。它是大学的中心,门前是学校的主干道,所有学校重大的事情多半要发生在这里。比如募捐、会餐,比如裸奔。
有几天我总能在教堂前面的喷泉旁边看见一顶帐篷,帐篷里坐着几个学生。今天坐这两个,明天又换成另外两个。我终于忍不住想问问他们为什么要把小帐篷搭到这个地方来,当时我和Y教授在一起,就请Y教授问一下。帐篷里的一个女孩说,他们在募捐帐篷,现在经济危机了,奥马哈一定有破了产的无家可归者,为了他们不至于露宿街头,所以同学们决定募捐帐篷。他们把帐篷搭在最显眼的位置上,募捐效果就会好一点。原来如此。
有个下午我从办公室出来,看见教堂附近挤满了人,人人拿着一个碟子。我弄不明白什么样的集体活动需要大家都端着饭碗边吃边干,问了才知道,这学期课程在今天结束了,明天就要复习迎考了,庆祝一下,所以食堂干脆把餐车推到室外,天大地大让同学们吃一顿自由餐。旁边的草坪上有乐队在演奏,黑人小伙子激情澎湃地敲着爵士鼓,一个男生在唱歌。他们的狂欢想来是为了庆祝学期结束,要是为了庆祝可以考试,那境界实在是太高了。
大概也是为了庆祝,有人第二天从教堂门前裸奔而过。
那会儿接近中午,我和J教授、Y教授开车到学校,他们俩去学生活动中心参加个聚会,我一个人去亚洲世界中心的办公室。过马路的时候还在想是不是要把相机拿出来,过了马路我要去拍一尊圣母雕像,犹豫一下决定还是到了雕像前才拿相机。刚过马路,听见旁边嗷嗷怪叫,扭头看见两个白白胖胖的光身子从身后跑过来。两个小伙子头上裹着白T恤,只露出两只眼,张牙舞爪地裸奔,嘴里兴奋地直叫唤。白人的确是白,小鸡鸡都白,在身体前面甩来甩去。他们沿着教堂前面的大道一路跑下去,当时路上行人不少,很多女生哈哈大笑。我看到了西洋景,想必这裸奔对她们来说也是个西洋景。等我反应过来要去拿相机,裸奔英雄们已经跑到教堂前面了,而过了教堂地势开始降低,就只能看见他们裹得严严实实的脑袋了,然后脑袋也消失了,只有喊叫声经久不息。我沿着大道望过去,几乎所有人都原地不动,要么瞠目结舌,要么觉得好玩,像过节一样开心。可见即便在裸奔无罪的美国校园里,它也不会频繁到成为日常现象。
J教授和Y教授说,他们在克瑞顿这么多年了,也没撞上这种事。我开玩笑说,那是我运气好。裸奔经过教堂,这在道德家看来,完全可以上升为一个复杂的象征,没准最后可以证明出:世界已经完全乱了。但在克瑞顿的主干道上,等裸奔者消失,等瞠目结舌者五官归位,等过节一样开心者敛住笑容,他们继续走路、聊天、思考,没有人觉得有必要去看见比裸奔的过程更多的东西,裸奔事件到此结束,日常生活重新开始。教堂是教堂,裸奔是裸奔,裸奔经过教堂不过是裸奔经过教堂,而不会是其他什么更为严重的东西,不必要求他们写检讨或者留校察看。
每次驱车购物的路上都要经过一座教堂,很可能是奥马哈最大的一座。在一个小坡顶上。奥马哈没有山,但地势起伏,你从最低处往上看那教堂,它就在山上,规模极其巨大。出门即见的双塔教堂和克瑞顿教堂只是座教堂,进去就是那种不需要解释的厅堂,而这座教堂却是一大片建筑群,做礼拜的、办公的、后勤的、钟楼,各有其宽大的场所,周围是一大片树木、草坪和停车场。如果你不看它突出的尖顶和十字架,你会以为这是座巨大的庄园;如果枝叶再繁盛一点你看不见房屋,你会以为正经过一个路边公园。一点没有意外,这座教堂建筑华美,好像是出自某著名建筑设计师之手。
事实上,很多教堂都是著名建筑师设计出来的。在任何一个居住区里,教堂都毫无疑问是最重要的公共场所,房屋居所是自己的,你可以随便怎么整都行,教堂的建造却必须群策群力,所以经过一个个美国小镇时,我看见镇上的教堂几乎都是最好的建筑,材料是,造型也是,一个小镇的智慧都集中在这同一座建筑上。甚至地理位置也是最好的。对一个新兴的小镇,最先出现的建筑通常就是教堂,身体可以露宿野地,灵魂不行,他们必须先把主供奉在一个安全、舒适、正大的所在。他们在最具天时地利人和之处择定方位,所有人都把木头运过来,商讨,设计,叮叮当当一阵猛干,他们的耶稣基督在此落户了,然后他们以此为中心,紧密地团结在十字架周围。
Y教授有个精妙的比喻,对美国小镇来说,教堂有点像中国的居委会。的确如此,这是小镇最大的公共空间,大家来礼拜祈祷,开始前和结束后可以展开社交,大大小小的事情在出门之前就已经解决了。而政府的职能单位市政厅、镇政厅,往往小得可怜,我见过的很多小镇上很多管理部门只有一间小房子,要不是门前挂着“CITYHALL”的小牌子,你会以为这地方无为而治。当然它的确也不需要骇人听闻地巨大,它是个服务部门,市长镇长有的连工资都不拿,它不需要通过豪华巍峨的政府大楼来体现自己的权威。在这一点上,也许小镇上的居民相信神来管理众生,比挺着大肚子的官员来管理更可靠一些。
我是个无神论者,不能切身地体会他们对主的虔诚和敬畏,但那虔诚和敬畏本身是我所喜欢的。我总以为,有虔诚和理想总比没有虔诚和理想要好,有敬畏总比没有敬畏要好。因为我们无所敬畏,所以肆无忌惮,要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且其乐无穷,天和地和人有时候的确需要去斗一斗,但斗多了斗过头了,其结果证明的恰恰不是人的伟大,而是人的不堪和毁灭性。虔诚和敬畏不在一定要皈依某种宗教,它只是个信仰问题,比如,你也可以信仰最基本的善,由此你有了基本的善恶判断,也就有了必要的规矩和准则。有规矩乃成方圆,这个世界在这个意义上才可能会更好。
在所有见过的教堂里,能拍下来的我尽量拍下来,如果相机打开得迟了,车行疾速一闪而过,那就只好遗憾了。最遗憾的是错过了南达科他州的一座小教堂,非常小,小得都算不上一间小房子,小得都容不下三个人同时站进去。在南达科他州印第安人保留区里的一片旷野上,在路边,一个陡峭的急转弯从教堂前面经过,等我看见它时,车子已经开始拐弯,当时天不好,风和雨和黑云朵压在头顶,我不好意思让车停下来,只能最大限度地扭转脖子去多看几眼。实话实说,当时我感到震撼,不是因为它的小,而是因为它的存在。
自从白人带着枪炮和现代文明来到北美大陆,印第安人的生活就被迫越来越狭窄。他们遭到屠杀和驱赶,最后被从马上赶下来,他们当年纵横的整个北美大陆辽阔的疆域萎缩成了现在的印第安人保留区。他们不得不把坐惯了马背的屁股移到汽车上,他们很不开心。为了保留草原、山林、野牛、游牧、自由和自己的文化,印第安人与白人争斗了几百年之后,人口和土地同时急剧减少,现在他们像蒲公英一样分散在保留区的一个个角落里。我看见的就是其中一朵或者两朵小蒲公英。离教堂不远有几间很小的旧房子,甚至还有一间学校,小得如同模型。
——我想说的是,即便如此,他们依然需要一个教堂,不管它有多小,但必须有。有和没有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可以被驱赶,可以贫困,可以偏安一隅乃至与世隔绝,但精神依然要寻求安放,他们要保留住敬畏和通往天堂的路径。有希望和寄托才可以继续活下去。我想象如果小房子里的人同时出来做礼拜,不管几个人,也只能一个一个来。一个人进去,祈祷,完毕,出来后另一个再进去。如是,一个接着一个,仿佛轮回,在这片可以忽略时代的旷野上,岁月悠长,十字架永远垂直着问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