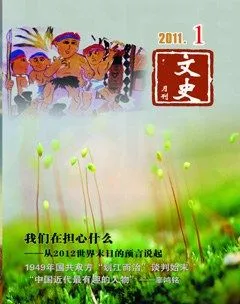春联
2011-12-24樊宝珠
文史月刊 2011年1期
去年初三,一位老朋友光临寒舍,我俩拱手相互贺年。落座后,我说:“咱俩都是一大把年纪的人了,不是早就相约逢年过节打电话道贺吗,怎么还……”他打断我的话,说:“我是走街串巷挨家逐户看春联,看着看着不知不觉就到了你这儿。”我不解:“看春联?”他说:“是呀,看春联。”接着,他劝我:“你不要老钻在埚舍看书,也到街上看看,那些高楼大厦、单门独院,甚至临时搭建的工棚,大门小扇上到处贴着鲜红的春联,琳琅满目,争奇斗艳,堪称一道亮丽的风景。”
话题由春联自然地转移到从腊月二十三过小年起直到过大年的忙碌而欢悦的情景。我俩顽童似的你一句我一句念叨起我国北方一些地区几乎人人耳熟能详的一段谚语:
二十三糖瓜粘,
二十四扫房子,
二十五磨麦子,
二十六去割肉,
二十七写对子,
二十八贴窗花,
二十九蒸馒头,
三十夜齐守岁,
年初一祭祖先,
初五前忙拜年。
说完,两人不禁哈哈大笑了。
我说:“过春节的讲究真多,除刚才说到的外,还有挂红灯、放爆竹、发红包、闹红火等等,春节是我国最重要的传统节日。那么,你说什么又是这个节日里展示中华传统文化的最重要的传统节目呢?”他脱口而出:“春联,贴春联。”我想了想,说:“对、对,有道理。”
一
春联也叫门对、春贴、对联、对子等,它以工整、对偶、简洁、精巧的文字,描绘时代背景,抒发美好愿望。古有灯谜一则:
姐妹一般长,打扮各梳妆;
满面放红光,年年报吉祥。
谜底即为春联。春联给春节增添了绚丽的色彩和喜庆的气氛。
春联历史悠久,桃符是其起源之一。按古时习俗,鬼怕桃树,元旦之日,在桃木板上写上或画上主管万鬼的两兄弟神荼和郁垒之名或像,尊号“门神”,挂在大门两旁,用来驱鬼辟邪,保佑平安。所以,后人亦以桃符作为春联的别称。
据《辞海》(1979年版)“桃符”条载:“五代时后蜀的宫廷里开始在桃符上题联语。”《宋史·西蜀孟氏》:“每岁除,命学士为词,题桃符,置寝门左右。末年,学士幸寅逊撰词,昶以其非工,自命笔题云:‘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清人梁章钜也在《楹联丛话·自序》中认为:“楹联之兴,肇于五代之桃符。孟蜀‘余庆’、‘长春’十字,其最古也。”
然而,我曾经看到一篇文章,却否定了这种说法。那篇文章可以概括为一个字:最。文中略述了最早的春联、寿联、喜联,最早和最长的挽联,最长的楹联,最短的联,最早亲手写对联言志抒怀的帝王,字迹最大的摩崖石刻联和字迹最小的分别刻在黑、白两根头发上的对联等。文章不长,却很有趣,正如它的题目《对联趣谈》。在谈到最早的春联时,此文明确指出,最早的春联见之于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敦煌遗书目上,该遗书记录了12副春联,排列序位中的第一副为“三阳始布;四序初开。”撰联人为唐人刘丘子,作于开元十一年,较后蜀主孟昶的题门联早240年。
尽管说法不一,但源远无疑,而且流长。千余年来,每逢岁末年初,冬去春来,除旧布新,一元复始的时候,诗人们的脑海里总会自然地涌动起诗意,甚至诗兴大发,写上几首欢庆春节的诗篇,而其中又有不少会写到春联。以宋代为例,陆游的“半盏屠苏犹未举,灯前小草写桃符”(《除夜雪》)、“桃符呵笔写,椒酒过花斜”(《己酉元旦》)和宋伯仁的“桃板随人换,梅花隔岁香”(《岁旦》)等诗句,都很好地写出了书写、张贴春联的喜庆气氛。当然,公认的魁首之作还是王安石的《元日》:
爆竹声中一岁除,
春风送暖入屠苏。
千门万户日,
总把新桃换旧符。
王安安石这首即景之作,表达了迎接新春的欢悦,也说明春节在桃木板上写春联已具有相当的广泛性。
郭沫若先生曾说过“自古神州原尚赤。”这不单因为红色象征着吉祥喜庆,热烈欢快,还在于古时传说春节出来伤人的猛兽“年”惧怕红色,故明代开始用红纸写春联。明太祖朱元璋定都金陵后,除夕传旨“公卿士庶门上,须加春联一副”。他还给文臣武将赐赠春联。一年除夕夜,朱元璋微服出巡,见一户人家门上未贴春联,经查得知为阉猪户,只善动刀,不会动笔。朱元璋灵机一动,便亲自写了一副春联送给这家,联曰:“双手劈开生死路,一刀割断是非根。”该联贴切生动不泛幽默,成为史料之美谈。由于明太祖的提倡,此后,每逢春节,无论达官贵人还是黎民百姓,无论巨擘名流抑或潦倒穷汉,莫不贴春联。春节贴春联成为一种普遍习俗。
清代以降,春联艺术达到了炉火纯青、日臻完美的程度。名人写春联成为时尚,对汉文化有较深素养的康熙、乾隆于春联更是情有独钟,紫禁城的春联,不少出自圣手。有趣的是,民间还流传着一则乾隆皇帝像明太祖那样给一户人家写春联的故事。不过,他不是写给阉猪户,而是写给一间修鞋铺。那故事说,一年春节前,乾隆皇帝下江南,途经一个地方,见街上有间破旧的修鞋铺,里面坐着个愁眉苦脸的修鞋匠,他问:“怎么没有生意呢?”鞋匠唉声叹气地说:“没人来修鞋,有啥办法!”他看了看修鞋铺旁的财神庙,沉思了一会,便给鞋匠写了一副春联:“拉拉拉拉来五路财神,锥锥锥锥走四方穷鬼。”从此修鞋匠的生意就日渐好了起来。这虽是一则传说故事,但从其联语来看,却写得颇为工整对仗,很有意思。
如果说前述的唐人刘丘子作于开元十一年的那副春联是我国最早的春联的话,那么,它距今已有1286年了。在如此漫长的岁月里,朝代屡有更迭,春联则传承不绝。只是在“史无前例”的年代,推行“过革命化春节”,贴春联等春节必不可少的节目被列入“四旧”而横遭扫除。然而,以人民愿望为“根”的富有生命力的民俗,是“扫”而难“除”的。高喊“革命”的“四人帮”倒台后,春联这一独特的传统艺术,又焕发出它的青春。特别是在改革开放的春风淋浴下,神州处处万象更新,春联更是得到人们的青睐。
二
尽人皆知,在印刷体春联出现之前,春联都是人们用毛笔书写的。我国的书法和春联一样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传统艺术。书法曾经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的重要载体,春联是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载体样式,二者相溶相依,密不可分。有这样一首诗:
草体的鸟儿,隶体的鸟儿,
在一片红光中拍动着翅膀,
把瑞气和欢喜荡满屋梁,
把庭院领往春天的深处,
……
是啊,请书法家用篆、隶、草、楷、行书等任何一种字体写上副春联,那令人赏心悦目的精美的书法,真像是能把我们领往春天的灵动的鸟儿。然而,对众多普通人来说,请书法家写春联,谈何容易!
东晋书法家王羲之,“其书备精诸体,尤善正、行,字势雄强多变化,为历代学书者所宗尚,影响极大”,世称书圣。相传,有一年春节前夕,他三次贴出春联,因人们爱其书法,全被揭走,只得重新再写一副。写好后,唯恐再被人揭走,他把上半截剪下来先贴出去,上联是“福无双至”,下联是“祸不单行”,因内容不吉利,这一次无人再揭。到了大年清晨,王羲之贴出了下半截,整副春联变成了“福无双至今日至;祸不单行昨夜行”。路人莫不击掌叫绝。试想,像这等大书法家能有几人,能请得动他写春联吗?即使个别与其熟稔者有幸求得了,贴出去能保留住吗?
元代赵孟頫,书画家,尤精正、行书和小楷。扬州明月楼主请其书联,一副七言联,酬谢金壶一把。我不知此金壶多么大。不过,既然请书联者是扬州明月楼主,被请者是大书法家,而且据说赵书联后,明月楼的身价顿时倍增,想来那把金壶也不会太小。普通人有此等财力吗?
清人郑燮(板桥),书画家、文学家。清·宣鼎《夜雨秋灯录》记,郑在扬州时,某年春节前,有富商求他给东汉时创立道派的张道陵、后被道教徒尊为“天师”的道观书一副对联。郑故意向其索要千金,富商只给了五百。郑挥毫写下“龙虎山中真宰相”一句,掷笔欲走,富商问:“何只有上联?”郑答:“言明一千金,尔只与五百,我亦仅与其半。”富商无奈,又付五百,郑乃书下联:“麒麟阁上活神仙”。从郑燮早年家贫、做知县后以助农民胜讼及办理赈济得罪豪绅而罢官、做官前后居扬州卖书画等情况来看,普通人请其写对联,可以想象他一定会欣然命笔,而且绝不会像对富商那样故意索要高价,但他是以卖书画为生的,总应该付其润笔吧。
当然,书法家是有层次的,上述几位只是古代书法家中的佼佼者,著名者,何况古代书法是以一种极其广阔的社会必需性为背景的。所以,从整体上说,称得上是书法家的人可能会很多。但是,他们是散居于全国各地的,其中不少人又处于上层,这样一来,在民间,特别在农村,书法家就成了凤毛麟角。而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钢笔代替了毛笔,以毛笔为工具的书法家自然越来越少了。所以,在旧社会,特别在教育滞后的广大农村,即使你付得起润笔,请书法家写春联,实在是一种奢望。
那么,怎么办?过春节总不能不贴春联吧。据上世纪40年代的陕西《宜川县志》载,春节写春联,“人们会写吉祥语句,不识字的乡民则写‘十’字”。可能是盼望日子过得十全十美。我猜测,这里所说的“不识字的乡民”,极有可能是居住在没有识字人的山庄窝铺,而年前又不知什么原因没法出村,否则,他们会外出求人写春联的。
我曾听说过类似的做法。我外祖父家居住的地方,是个只有几户人家的山庄,没有学校,没人读书,自然也没人会写字。每年春节前,农民们总要外出求人写春联。有一年,天公不作美,下了场鹅毛大雪,本来就崎岖难行的羊肠小道,此时更无法行走了。他们便以锅底黑调水当墨汁,用碗底蘸之,在裁好的红纸条上,印上数量相等的圆圈,作为春联,象征着团团圆圆、欢欢乐乐。
比较起来,我家乡的情况要好得多。虽地处黄土丘陵区,然系县境集镇之一,历来有学校,读书人较多,春节写春联,人们的办法是“筷子里拔旗杆”,即从镇里识文断字的人中选自己认为毛笔字写得好的人书写。我父亲就是这样拔出的“旗杆”,虽然不是镇里最高的“旗杆”,但起码比筷子高。他生于1901年,清末民初读过私塾,爱好书法,临池不辍,毛笔字写得委实不错。从我上学起,每岁过了小年以后,淳朴善良的乡亲们,耳边夹支纸烟,手拿一张或几张红纸,纷至沓来,请写春联。父亲总是笑脸相迎,乐此不疲,倒不是为那支作为酬劳的纸烟(他吸旱烟),而是为乡亲们看重他写的字。我则自然成了“墨童”,帮着化笔、磨墨、裁纸。其时家贫,没有书桌,父亲只得把笔墨摆放在吃饭时放咸盐、辣椒钵子和苦菜盘子的小炕桌上,盘腿而坐,拿起那支不知用了多少年的秃笔,凑着小小的炕桌,委婉转折地写了起来。坐久了,腿麻了,他就干脆站在地下,让我和请他写春联的人把裁好的红纸轻轻拉直,自己立于一侧,饱蘸浓墨,悬腕挥毫,一气呵成。然后,坐在炕边,吸袋烟,歇会儿,再继续写。
其实,此时此刻,我家乡的那些“旗杆”们又何尝不都是在如此这般地忙碌着呢!
诚然,他们的毛笔字,与王羲之的妍美流便、欧阳询的险峻高远、颜真卿的雄深宽厚、柳公权的骨力洞达相比,有天壤之别,但在我的家乡,除夕贴出来,不失为一年一度的书法艺术展览。
三
去年春节前后,不经意间,从报纸上看到有关春联的一篇文章和一则消息。文章的作者说,年前的一天,他和书画界的朋友参加市里组织的“三下乡”活动,为农民写春联直到中午才作罢。一位没有得到春联的大爷不满地唠叨着,他问这位大爷:“现在不是有很多印刷精美的印刷体春联吗?您不喜欢?谁知他说了一句:‘没有味道!’”消息是新华社记者就春节张贴春联一事访问天津社科院教授王来华后发出的。王教授介绍了春联的悠久历史、种类和文化内涵,最后建议:“春联一年就贴这一次,公众最好亲自手写或者找别人代写,让春联‘活’起来。”乡下大爷想要的春联正是王教授所说手写的“活”的春联,王教授的建议反映了乡下大爷的要求。乡下大爷和王教授对春联的看法何以如此一致呢?消息中转述的王教授的话,明白无误地回答了这个回题:“现在的春联都是机器流水作业的产物,缺乏文化内涵。”
春联,作为中国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烘托着节日浓厚的文化氛围,而且反映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底蕴和书法艺术的博大精深。关于书法艺术,从曾被毕加索认为是一幅现代抽象画,近被联合国批准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名录”,即可见其博大精深,见其具有当代社会艺术审美时尚的元素。这里要着重说的是春联的文化底蕴,简言之,春联要以诗的格律、词的长短、曲的俚白、文的哲理、史的典故,或歌时颂春,或贺岁祈福,或言志抒怀,或荡浊扬清……给人力量、信心和勇气。
记得,我父亲写春联的时候,正值抗战之初。他写的春联的内容,基本上是当时响彻全国、声震神州、正在或已经变成广大军民实际行动的口号,诸如“抗日救国,人人有责”、“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寸寸山河寸寸金,人人奋起打东洋”等,连大门和住室对面墙上往年贴的“出门见喜”、“抬头见喜”的春条,当时也写成“打倒日寇”、“铲除汉奸”。此外,还有我后来渐渐懂了的古人爱国、报国的诗句,诸如陈子昂的“感时思报国,拔剑起蒿莱”、韦应物的“丈夫当为国,破敌如摧山”、陆游的“平生铁石心,忘家思报国”、于谦的“富贵傥来君莫问,丹心报国是男儿”等。无论是当时的口号还是古人的诗句都反映了全国军民抗战到底、牺牲救国的决心。
德业闻望的名人,其撰写的春联,也能从侧面看出他的德行情操、人生见解。据报载,新中国成立后,老舍先生几乎年年写新春联,讴歌新社会、新风尚。如“酒热诗歌壮;梅红天地新”、“吟诗辞旧岁;举杯贺新年”、“勤俭持家,有备无恙;热诚报国,发奋图强”。1962年作的春联是“除夕立春同日双节;随时进步一刻千金”。可惜,这样一位热诚报国、随时进步的著名作家,也逃不过“文革”劫难,被迫害致死。
改革开放以来,春联的内容焕发一新。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台湾师范大学教授陈大络刊之于大陆报刊的联作:“两岸春风化雨;一统大地笙歌”、“耳餐和平调;心醉统一音”、“春景春辉,春风春雨,接福迎春,两岸春光闹;新事新业,新人新貌,革故鼎新,万民新机多”。陈教授热诚期望两岸统一、祖国昌盛的拳拳之心,令人感动,令人敬重。
我离休后,每年春节前,单位总要赠送印刷体春联一副。这无疑是单位对老干部的关爱,我铭感不忘。但,恕我不知好歹,容我实话实说,我连一副都没有贴,原因无他,在于春联的内容不宜我用。以去年赠送的春联为例,丝绒质地,金边金字,装饰精美,估计价格不菲。但看联语,可谓集浅俗之大成:“福到华堂添富贵;财临吉宅永平安”,横批“吉星高照”。我想,这副春联送给那些精神世界远远跟不上财富积聚的“暴发户”倒比较适宜。而于我,“惟是风马牛不相及也”。我受党的教育60多年,生活待遇由当初的供给制到现在的工薪阶层中的一员,常感自己为革命付出的太少,人民给予自己的太多,从未想过“华堂”呀“富贵”呀“财临吉宅”呀什么的。我这个人,论性格(不是说“性格决定命运”吗?),耿直较真,好提意见,庸官讨厌(贪官尤甚),小人暗算(污吏更恨);论年龄和身体,年届八旬,垂垂老矣,双手颤抖,生活难理。过去没有,现在更不可能奢望什么“吉星高照”了。如能假以时日,迟些付火,多活几年,多看看国家强盛、人民幸福的美好景象,那就谢天谢地了。
哦!扯远了,还是说春联吧。既然赠送得不适宜,那就另想一副与自己情况相吻合的。我用新兴的心理学分支积极心理学,发现自己居住条件具有优势的一面。家住底楼二十多年,开始还没感觉什么,后来南面又有一幢高楼拔地而起,且楼距很窄。这样一来,我家基本上就成了太阳照射不到的地方,常年阴暗潮湿,心情自然不好。但门在北边,抬脚就到了与北楼距离较宽的楼间,这里有几个水泥墩儿,更有几株粗壮高大的梧桐树,几株在我国被列为第四香花的丁香花,几株开花较早、名符其实的迎春花……每当供暖气前、停暖气后,家里比院里阴冷的时候,我就到楼间追太阳,坐在水泥墩上,背负阳光,或看看书,或与邻居们聊聊天,怡然自得。由此,我忽然想起清代篆刻家、书法家邓石如先生的一副联作:“石畔坐消无事福,花间补读未观书。”我不禁欣喜放声:好!就借它一用了。我还自撰了横批“乐在其中”。并求我昔日的同事,写得一手漂亮毛笔字的宿旺同志书写。
大年初二,省委党史办公室主任张铁锁同志来看望我。他是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我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进门前,自然要品读门上贴的春联。所以,一进门,他不是说过年的话,而是连声称赞春联:“联、书俱佳!”
当代著名诗人、曾任中国楹联学会顾问的臧克家先生说过:“希望做到风格别具,联内有我。”诚哉斯言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