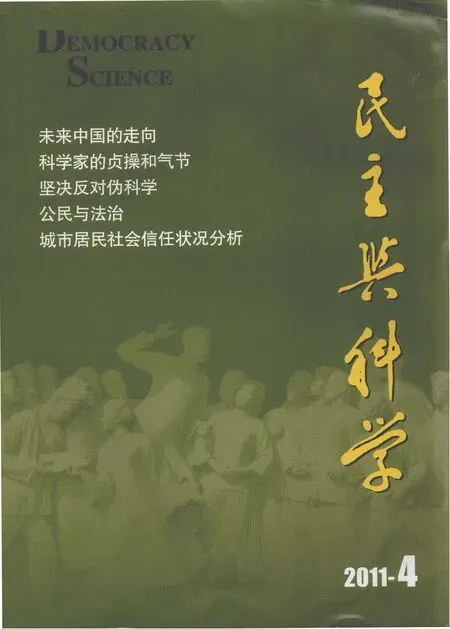有所作为是人生的最高境界
——记于光远先生
2011-12-24孙慕天
■孙慕天
有所作为是人生的最高境界
——记于光远先生
■孙慕天
在我大学本科老师中,从专业角度说,与我一生事业关系最密切的是于光远先生,因为他是中国自然辩证法公认的“祖师爷”。我在哲学的诸多分支中,选择了自然辩证法作为专业方向,当然有诸多理由,这里不去说它;吊诡的是,光远师虽是我的授业师,但我搞科学哲学却并不是受他的影响。我在本科时,自然科学哲学的相关课程并不是光远师开的,主要的一位老师是林万和先生,这位老师在中国自然辩证法史上,本应占有重要位置,却几乎被完全遗忘了,这事以后再说罢。
我在中学时就知道光远先生的大名,不仅因为他是《学习》杂志主编,我喜欢看那上面的一些文章,而且因为他和胡绳、王惠德主编的《政治常识读本》是我们中学政治课的教科书。
我真正成为于光远先生的学生,是因为1961年听了他的辩证逻辑课。我们那时人大哲学系的课程设置,出自何思敬先生的手笔,他设重课,聘名师,在当时的语境下,硬是在中国大学中打造出一个亮点,在某些方面,突破了时代的限制。光远先生和萧前先生等为我们开出的辩证逻辑课,就是中国哲学专业的一个首创。那天,光远先生的打扮颇另类,戴着一副墨镜,穿着淡黄色麻纱料的中山装,用一个精致草编扁筐装着讲稿,精神抖擞,腰板挺直,那派头很有点像高级将领。他分担的是第六、七章,讲辩证逻辑的方法,主要是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和分析与综合的方法。想来光远先生是专业经济学家,而这两种方法都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特别采用的方法,由光远先生来讲自然是再合适不过了。从这时起,于光远先生真正成了我的老师。
于师讲课的最大特点是独创性。他认为,从具体到抽象和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所涉及的关键问题是“认识从哪里开始”?是从感性开始,还是从理论开始?于师明确指出,现实的认识从感性经验入手,但理论的分析必须从概念入手。认为科学研究从现实的前提出发,是常识的认识,但这种看法是错误的;理论认识要把握的是事物的本质,这就要求研究蕴含事物内在矛盾的概念细胞,而不能着眼于混沌的直观表象。大约同时,亦即1960年8月和1961年1月,在地球的另一端,波普尔在斯坦福国际科学哲学会议和英国科学哲学学会上,分别做了演讲,提出“科学开始于问题,而不是开始于观察”的著名命题,对于“先有H(假说),还是先有O(观察)”的问题给出了与常识实在论相反的回答。他的这些观点收在1968年出版的《猜想与反驳》(Conjectures and Refutations)中,当时的中国当然没有人知道这些观点。到上世纪80年代,波普尔的思想传入中国后,我想起于师的这些观点,不禁想到一句英国成语:great minds think alike——英雄所见略同。
于师讲的第二个题目是分析和综合。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于师好像是最早从辩证逻辑视域上论述这一问题的中国学者。他把分析和综合视为解决个别和一般辩证关系的关键,分析是把握个别,综合是把握一般,而这个问题的解决是认识一切矛盾的根本途径。他还认为,虽然没有分析就没有综合,但分析必须以对事物的整体把握为前提,这种理论上的整体性认识,指导着分析活动。掌握了分析与综合的辩证法,就找到了解开一般和个别之谜的钥匙,也就真正走进了本质性的认识,这是科学认识的真正秘密。辩证法就是认识论,不能离开认识去寻求虚无缥缈的自在的辩证理念,那是柏拉图。我一直咀嚼着于师的这些深刻的看法,后来,通过学习列宁的《哲学笔记》和毛泽东的《矛盾论》,终于弄明白了,为什么分析和综合是辩证法三要素之一,而且是辩证法的精髓。这使我意识到,学马克思主义还有另一种视角,后来在苏联读了伊里因科夫和所谓认识论派的论著,又反复比较西方后逻辑实证主义走下“冰峰”的哲学,愈发钦佩叹服于师的超前性。哲学是人的哲学,是从人观物,物物而不物于物。
我入学正值反右那一年,“左”的思潮主宰一切,马克思主义的词句被当作一切认识和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但是,于师使我看到另一种马克思主义。那时,我对马克思早期思想产生了浓厚兴趣,不仅读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神圣家族》,还从俄文版读到马克思22岁时写的《伊壁鸠鲁、斯多噶和怀疑派哲学笔记》,那是一个充满人性关怀的马克思,一个不受任何陈腐教条束缚的马克思。而于师正是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由于参加了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的工作,使我得以走近于师,并有了直接接触。1979年,在成都锦江宾馆自然辩证法会议上,劫后重逢,再次见到于师,他已是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的首届理事长了。自那以后,一直到2002年,每年总要在各种会议上聆听他大开大阖的放言高论。恩格斯在形容思想丰富时有一个词叫“盈盈欲滴”,而于师的思想不仅盈盈欲滴,而且不拘一格,总是出人意表,显示出学术大师的强烈自我意识。他曾说人要有十二“开”:开拓的精神,开通的思想,开放的路子,开动的脑筋,开明的态度,开发的干劲,开阔的眼界,开朗的性格,开导的方法,开诚的友谊,开创的局面,开心的情绪。我常想,能做到这十二“开”的,世界上能有几人?于师正是兼具十二“开”的超人。文化大革命中,于师被下放到宁夏五七干校,被戴上三顶帽子: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动学术权威,属于“专政”对象。当时能读的书,只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于师却为后来写作经典作家《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论自然辩证法和自然科学工作》积累了大量资料;同时,他竟然还编了一本《马克思恩格斯论喝酒》,介绍马克思因病戒酒的前夕特地大喝一通等趣事。记得上世纪90年代有一次在农科院开会,于师在开幕式上讲话,劈头就说:“我最近要出一本书,跟出版社提出,我的书文责自负,要么照样发排,要么我把稿子抽回。事情是,我的文章中既有阿拉伯数字,又有汉字大写的数字,他们要求都改成阿拉伯数字,我坚决表示反对。但是他们根据国家出版局等七单位颁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却硬是要我把所使用的数字一律改为阿拉伯数码。”我本来想听于师讲学科的前沿问题,而他竟讲起这样一件琐事,心想老师是不是年事已高,思维有点混乱了。没想到,接下去他却由此从两个方面讲出了深刻的道理。从科学上说,数字既表示大小,又表示准确程度。个十百千万作为位数,必须是可靠的,如 23576 中,2、3、5、7 作为万千百十必须是准确的,如果位数不准确,后面的数都没有意义。所以,写成10000,前面的1和后面的0,都必须是可靠的。但写成汉字一万,其意义是表示一种数量估计,即量的大致程度,大致在九千到一万一千之间都可以;说“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就是这种模糊说法;如果改成“不怕10000,就怕1/10000”,岂不成笑话了。一些词组,如二倍体、三叶虫、十滴水、二氧化碳等等,当然也不能用阿拉伯数码表示。这说明,坚持科学的态度,对任何事情作科学分析,是何等重要;而我们常常忘记了科学态度。从政治上说,江泽民在党的第十四届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大量使用了汉字表示的数字,出版社并没有要求党中央把这篇重要文献中的数字一律改成阿拉伯数码。为什么中央领导可以不改,普通老百姓就必须改呢?这样的双重标准表明,政治对科学的干预仍然存在于我国社会生活的内在结构之中。于师话锋一转,尖锐地指出,自然辩证法的工作中心,仍然是倡导科学精神,在这方面,我们研究会任重而道远。于师这种独树一帜、挥洒自如的学术风格,总是使我有醍醐灌顶之感。有一次在饭桌上闲谈,他说:“我提倡开创国土经济学这门学科,有人说,国外没有;我说,他们没有我们就不能独创?学科名称干脆就从中文音译成英文,叫Guotuology!”
有些人认为于师的言论和行为背弃了马克思主义,至少是与主流观点相悖的。说这话的人要不是有意曲解于师的言行,就是根本不了解于师。于师是自然科学专业出身,1934年到清华物理系师从大物理学家周培源教授,毕业论文题目是《坐标系在引力场中的运动》,这使他接受了严格的实证科学训练。后来,于师投身革命,参加民族解放先锋队,是“一二·九”运动的骨干;“七七”事变后,他在北京郊区从日寇坦克履带下侥幸逃生,后来到了延安,一直站在革命的最前线,并成为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我几次亲耳听于师说:“我是一个不悔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我觉得他是一个特别的马克思主义者——不知道这样说是否合适——他的马克思主义渗透着深刻的科学精神。1979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过不久,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在成都锦江宾馆开工作会议。大会发言由于师主持,当时“人体特异功能”闹得正欢,四川又刚刚出了个唐雨“耳朵认字”,轰动全国。会上北大一位姓叶的中年教师,登台介绍他们对“人体特异功能”的实验。不料,他刚刚讲了几句,于师就厉声说:“你不要讲了。”这位叶先生反问:“为什么?”于师说:“我们这个会不容许宣传伪科学!”叶大声说:“您没有参与科学实验,怎么能说是伪科学呢?”于师说:“我不用看,搞自然辩证法的不知道什么是经验论?”会场下面秩序大乱,有人大喊:“光远同志,百家争鸣嘛,让人家说话!”于师也提高声音说:“你下去,要不你就出去,我这里就是不给你发言权!”接着于师就推荐大家重读恩格斯的《神灵世界的自然科学》,说识别伪科学只能靠科学理性,不能靠经验,这是自然辩证法的ABC。忘记了这一点,就不配当自然辩证法工作者。后来许多年间,于师坚持反对伪科学,甚至与某著名科学家发生龃龉,并被某些科学骗子称作“四大恶人”之首。我有一位教授老友,是自然辩证法的资深学者,文革前就与于师多有交往;后来一度热心参加人体特异功能的研究,于师得知后,几次在会上点名批评,措辞严厉,见面也不打招呼,一点不留情面。这就是于师的原则性,他捍卫学术民主,鼓吹思想自由,但对反科学和反马克思主义的行径嫉恶如仇,绝不妥协。
于师是著名经济学家,又是哲学大家,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院士)中,唯一在世的。这样的大师,竟是我的老师,只能说是我年轻时的一种机缘。作为一种因缘,我竟和于师发生了极其亲密的交往关系。我不但参与了于师主编的《自然辩证法百科全书》的工作,为此书撰写了七个条目,而且和于师有了直接的接触。1996年11月3日,我收到了于师亲笔签赠的书《碎思录》,这是本颇特别的书,全书由100篇超短文组成,每篇不超过200字;各篇标题由著名科学史家戈革治印附在篇后;全书仿线装,在香港出版,是精美的艺术品。开卷后,第一篇就是“无时不思,无日不写”,这是于师的座右铭,这样的馈赠,使我心灵受到强烈的震撼。1997年8月19日,于师来到哈尔滨,省委杨光洪书记出面在和平邨设宴接待,于师提出要见经济学家熊映梧先生和我。我赶到宾馆时,于师的秘书胡冀燕女士在电梯里对我说:“于老到了就对杨书记说要见见你和熊先生。”来到餐厅,我向老师鞠躬致敬,于师说的第一句话是:“但愿寿长八十万小时!”见我愕然,于师解释说:“就是活到九十一岁又九十五天。现代生活节奏加快,以年月计算失之过粗,以分秒计之,失之过细;以小时计,恰到好处。”于师能饮一点红酒,但谈兴甚浓。他说自己八十二岁,年纪尚轻;不久前成立太平洋学会,请他出任会长。“我告诉他们,”于师说,“我年轻不够资格,我给你们请一位会长,陈翰笙,今年正好100岁,生于1897年,是一位有望跨三个世纪的人物。”我知道这位陈翰老是哈佛博士,在欧美和苏联都声名赫赫的大学者,是蔡元培20年代聘请的北大教授。但使我震撼的是于师的精神境界,他告诉我们,活着要“言道,言志,言望”,就是道理、志趣、希望,有了这三条,就能有真正的人生,因为“人的寿命应当以有充实内容的生存时间来衡量”。那天晚上我失眠了,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想:我才57岁,我的道在哪里,志坚与否,期望又是什么?
于师生于1915年,是我在《亲炙拾零》中提到的八位男老师中唯一健在的。于师曾引用恩格斯的一句话:“有所作为是人生的最高境界。”这话我也引用过,但始终没有查到出处,所以只能说是从于师那里转引的。于师在最高境界中度过了自己的一生,他还在继续发出灿烂的光焰照耀着我们;在他的思想和人格的光芒下走向人生的最高境界,是我余生的愿望和幸福。
(作者单位:哈尔滨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