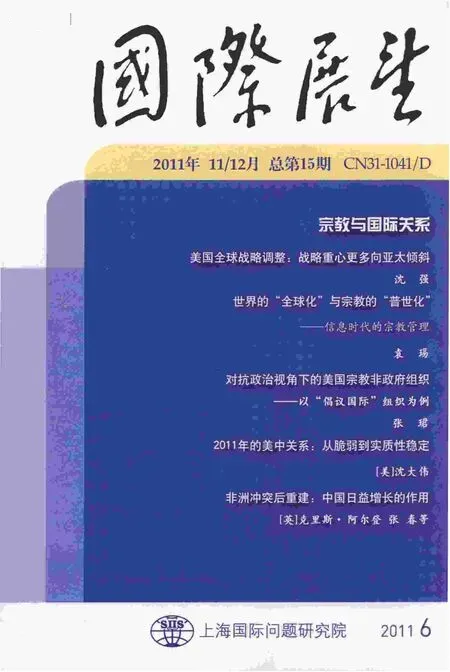对抗政治视角下的美国宗教非政府组织——以“倡议国际”组织为例
2011-12-24张珺
张 珺
对抗政治视角下的美国宗教非政府组织
——以“倡议国际”组织为例
张 珺
在跨国对抗研究中,宗教一直是一个被“边缘化”的因素,然而宗教非政府组织的跨国集体行动使得它们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力日益显著,形成了“宗教性跨国对抗”。本文从宗教非政府组织所关注的主要议题之一“宗教人权”领域,以个案“倡议国际”组织为例,结合政治社会学、国际关系的相关理论分析这一类型组织的国际政治参与。
对抗政治 宗教非政府组织 美国外交
在“全球宗教复兴”①Scott M. Thomas, The Global Resurgence of Religio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truggle for the Soul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 2005.背景下,形形色色的宗教非政府组织及宗教人权倡议网络纷纷对国际关系产生日益显著的影响,它们通常不具有暴力性,但其影响范围更大或具有广泛的群众性,②徐以骅:“全球化时代的宗教与国际关系”,《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年第9期,第17页。尤其是一些宗教和人权团体发起的集体行动可以被视为“对抗政治”的一种形式。从对抗政治的视角来探究宗教非政府组织的政治参与是一个不同于以往的分析架构,本文选取美国宗教人权这一议题领域的典型案例“倡议国际”,从“宗教性跨国对抗”的视角来解释这一类型的组织如何在国际关系中发挥影响。
一、何为“宗教性跨国对抗”
随着20世纪60年代西方社会运动的兴起,西方国家的国内政治由此发展出有别于常规制度、正式政治的独特政治形态——对抗政治。①Contentious politics在国内学术界有多种译法,“争议政治”、“斗争政治”、“抗争政治”以及“对抗政治”,等等,虽然在英语学界早已不是一个新词,但国内目前并无统一的术语。梯利和塔罗等学者在提出“对抗政治”这一概念后受到一些批评时回应到,从“抗议”(protest)、“社会运动”(social movement)、“集体行动”(collective action)到“对抗政治”(contentious politics)等不同的术语(term)都表明了研究者不同的方法、材料、解释和对依据的使用。他们使用“对抗政治”一词意在超越西方学界研究了几十年的社会运动理论和近十多年来广泛运用的倡议网络理论,同时弥合欧洲学派和美国学派对于社会“集体行动”研究的分歧。参见Sidney Tarrow, “Transnational Politics: Contention and Institution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No.4, 2001, pp.1-20. Charles Tilly, “Contentious Choices,” Theory and Society, Vol.33, No. 3/4, (Jun. - Aug., 2004), pp. 473-481。“对抗政治”在政治社会学领域并不是一个新鲜的术语,无论是集体行动、社会运动、还是倡议网络等,都被作为对抗政治的一种加以研究,且已具有大量的研究成果。诸多的理论认为,这一政治形态对其国内政治的民主和治理都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而在国际政治领域,尽管有许多课题涉及此类形式的国际政治行为,但由于在术语上的宽泛选择以及分析层次上的不同,“对抗政治”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特别是理论层面尚未得到充分的研究。许多国际关系研究者从全球治理的角度来看待跨国倡议网络和跨国社会运动,而政治社会学者更为关心的主题是“民主化”、“民族主义浪潮”等一些带有明显政治学色彩的命题。这类有意无意忽视宗教因素的研究是社会科学理论的“通病”。事实上宗教从来没有在对抗政治中缺席,无论是宗教性还是非宗教性,诸如波兰的“团结工会”是以波兰最具合法性且最为强有力的机构——天主教会——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又成功地利用了天主教会这一巨大的文化势力进行其声势浩大的社会运动。①[美]查尔斯·蒂利、西德尼·塔罗著,李义中译:《抗争政治》,译林出版社,2010年,第145-147页。随着宗教在国际关系中的“回归”,“宗教性跨国对抗”也成为有待从新的视角加以研究的议题。
目前学界对于国际非政府组织的研究主要有三大范式:多元主义、跨国主义和集体行动。需要说明的是,三大研究范式都来源于西方学者,因此难免有“西方中心主义”的色彩,尤其在集体行动范式中,往往以社会运动推动“民主化”为最主流的研究议题,研究范围涉及各个国家和地区,被冠以“对抗政治”的集体行动就是其最新的研究成果。②参见李峰:“刍议国际非政府组织国际政治参与的研究范式”,《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第103-106页;谢岳、曹开雄:“集体行动理论化系谱:从社会运动理论到抗争政治理论”,《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第13-20页。本文认为,塔罗和蒂利在使用“对抗政治”(contentious politics)一词时,是针对定义较为宽泛的社会集体行动,就这类行动的基本性质即“对抗性”来进行政治社会学的阐释。一方面,它超越了社会运动和倡议网络理论,换了一个视角对集体行动进行新的归类和理论整合;另一方面,它也继承了相当多的以往研究成果、观点。鉴于西方学者无论是从国际非政府组织研究的哪个范式入手,所选取的案例多半具有明显的政治倾向性,往往给予较为正面的评价,而“抗争”或是“斗争”这一译法在汉语语境中又具有偏褒义的含义,从而使得学术研究的客观性和中立性有所欠缺。因此,本文使用“对抗政治”主要出于对这类集体行动的客观描述性,并不认为发起“对抗”的一方必定代表着公正或是道德上的优势。
美国皮尤宗教与公共生活论坛2009年12月16日发布了对198个国家和地区在2006年到2008年间的情况所作的研究报告。该研究报告把对宗教的限制分为政府限制(横轴)和社会限制(纵轴)两大类,在限制程度上又分为高度(严重)、非常高度(严重)、温和、低度等级别,就某些国家的宗教受限度而言,可以出现政府较高度限制、社会较低度限制或社会较高度限制、政府较低度限制等多种情形。2011年该论坛再度发布关于国际宗教自由状况的报告,指出和两年前相比,全球约有三分之一的人生活在政府对宗教限制或社会敌意正在增加的国家,约有百分之一的人生活在政府限制或社会敌意有所下降的国家和地区。并且,前者是限制和敌意指数很高的国家,而后者则是限制和敌意指数很低的国家。换句话说,在皮尤论坛的调查报告看来,宗教自由状况的两极分化趋势愈加显著。①皮尤宗教与公共生活论坛关于“国际宗教自由”2009年的报告“Global Restrictions on Religion”见:http://pewforum.org/Government/Global-Restrictions-on-Religion.aspx;2011年的报告“Rising Restrictions on Religion”见:http://pewforum.org/Government/R ising-Restrictions-on-Religion-GRI.aspx 。当然,西方国家对于所谓“宗教自由”问题的关注由来已久,冷战期间,宗教一直在幕后起着隐性的推动作用。②Dianne Kirby ed. Religion and the Cold War,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2.冷战结束后,世界范围内的宗教复兴表象之一就是宗教非政府组织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在人权运动中,逐渐衍生出以宗教人权为议题的宗教或世俗非政府组织,它们往往充当了西方外交政策的非正式执行者,成为在西方国家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国际宗教自由运动即新人权运动的主要领导者和组织者,并推动了跨国宗教倡议网络和国际宗教人权机制的形成。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与主权国家、政府间国际组织以及其他非政府之间的互动,已成为全球和国际政治现实的重要因素。这种互动过程就是“宗教性跨国对抗”,它包含了至少三方行为体,即作为提出要求者的(非政府)宗教和人权组织、作为对抗对象的政府以及第三方的支持者。跨国对抗是因为发起者认为他们政治表达的常规性制度渠道不能使他们的要求得到相应的回复。由于宗教非政府组织和它们所对抗的政府或国际组织并不对等,尤其是对抗他国政府时,现有国际体系并没有常规性制度渠道,因此它们寻求在此之外用跨国对抗的形式提出要求。此外,本文将引发对抗的原因作为类别区分的界限,因而在分析概念上,既保持“对抗政治”中的一般概念,也使用“宗教性跨国对抗”这样的分类,以突出“宗教”因素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
从社会运动的角度来看,宗教人权运动接近于“新社会运动”。首先,人们加入传统社会运动一般是因为某种物质需求,但新社会运动的主要动机往往是为了实现一些非物质性的价值,而不是因为经济和物质上的受剥削和受压迫。第二,传统社会运动的背后往往有一个宏大的意识形态,而新社会运动想要改变的仅仅是社会上的某一种主流价值观和行事方式,(所以新社会运动又被称为“单议题运动”),其成员之间的凝聚基础往往是对一种共同身份的认同。因此新社会运动有时候又被称为认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第三,传统社会运动的对象一般是统治阶级以及使社会运动参与者处于被剥削被压迫地位的经济和政治结构,但新社会运动并不追求打破国家机器和建立新政权,其对象往往是公民社会本身。第四,传统社会运动的组织形态是分层的,而许多新社会运动采用了一种大民主性的、平等的组织形态。在有些场合下,新社会运动的核心是少数专业人才。在更多的场合,其核心成员是一个个小规模的朋友圈子和社会运动网络,通过现代通讯手段迅速联络,达致协调行动。在目前西方,伴随各式新社会运动的是大量右翼社会运动的兴起和教会实力的增长。而且,西方社会已经进入了所谓“社会运动社会”,首先是保守派、精英层开始参与社会运动,一改以往社会运动特有的左派和草根性质,其次是一些对抗政治的形式经过多年发展被逐渐纳入到常规政治中并加以制度化。
现代通讯手段和社会网络的重新组合连接使得社会运动形成了一种外在式的动员结构。在这种结构模式下,我们见到的不是数个等级分明的社会运动组织,而是众多小型的、互相没有隶属关系的社会运动组织和网络。这些组织和网络的核心成员人数不多,有些人是一些社会运动组织的专职人员。它们在平时仅仅有着松散的联系,一旦出现某些问题,有着相似利益的组织和网络就成了一种社会运动过渡性团队(transitory team)。每个团队都通过自己的网络来动员运动参加者,不同团队之间又通过现代通讯手段迅速进行联系和协调。一个具有一定规模的社会运动在很短时间内就能发动起来,但运动过后这些组织又各自归位,并不会形成一个内部结构和等级森严的社会运动组织。大量过渡性团队的存在以及它们有效的组织和通讯能力,也是社会运动得以产生的一个原因。显然,宗教人权运动具有这些新社会运动的特征。①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290-293页。
二、宗教人权组织与宗教性跨国对抗
宗教人权组织的一般目标是通过改善“国际宗教自由状况”间接促进传教。由诸多宗教人权组织构建起来的国际倡议网络也是继承了其“历史先驱”——19世纪西方传教士在反缠足、反妇女割礼等跨国运动的运动方式,②[美]玛格丽特·E. 凯克、凯瑟琳·辛金克著,韩召颖、孙英丽译:《超越国界的活动家——国际政治中的倡议网络》,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并且在现代社会中运用新的信息手段以实现其多重目的。艾伦·D.赫兹克对于美国基督教在所谓国际宗教自由问题的研究已为这一议题领域的政治社会学分析打下一个基础,他从历史的、社会的、宗教—神学的、政治的等各个方面来描述美国基督教组织及个人是如何介入国际事务的,对其动因、过程及结果作出了一些颇有启发性的研究。③参见赫兹克的一系列相关论著,如 Freeing God’s Children, The Influence of Faith,Representing God in Washington等。
(一)美国宗教人权组织
1.分类
美国的宗教人权组织在所谓国际宗教自由领域的活动从目标对象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专门针对国内,另一类是针对海外。大多数较有影响的宗教人权组织主要是针对海外,也就是着眼于所谓“国际宗教自由”问题。从神学背景的属性来分,保守基督教福音派是所谓国际宗教自由运动的主要发起者,他们大张旗鼓地为“反宗教迫害”造势,危言耸听地把基督徒说成是世界范围宗教迫害的最大受害者。此种言论极具煽动性,足以触动本国教内外人士的神经。①徐以骅:“宗教与冷战后美国外交政策”,《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 5期,第 201页。福音派中也有左、右翼之分。另外,从自身定位上来分,一类是接近于宗教—传教组织,另一类则基本是关乎宗教的组织,更接近于一般的非赢利组织。美国的宗教非政府组织采用了非常广泛的行动形式,这种灵活性使得它们能适应环境的变化,既将不同的行为者组织起来,又迫使政治领袖处理新的问题。
2.组织架构和行为理念
宗教人权组织的组织形式通常有平行组织或是具有科层制的等级关系两类,其总部一般设在美国,同时在其他西方“中等国家”设有分支机构。西方“中等国家”即指那些推崇全球社会民主价值观和政策的所谓“好撒马利亚人之国”,一般指挪威、瑞士、丹麦、荷兰、加拿大诸国。②参见 Steven L. Lami, “The Role of Religious NGOs in Shaping Foreign Policy: Western Middle Powers and Reform Internationalism,” in Patrick James, ed., Religion, Identity, and Global Governance: Ideas, Evidence, and Practice,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2011, pp.244-254。转引自徐以骅:“全球化时代的宗教与国际关系”,《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年第9期,第10页。宗教人权组织活跃在这些西方国家中。从组织特性上来看,“倡议国际”是具有职业性的基督教组织,与一般基于教会的宗教非政府组织不同,世俗化倾向更为明显,职业特征突出。在该组织罗列出的六大行动领域中,宗教自由在其行动数量上占了将近一半,无疑这与其基督教背景有关,但同时该组织的其他一大半活动是致力于和平、人权、家庭、社区的社会服务类事业,这又与其他世俗的援助类组织类似。因此,从这点来看,“倡议国际”的世俗化倾向较为明显,保证“宗教自由”虽然是其“重要利益”但绝非唯一的“核心利益”。
从行为理念来看,“倡议国际”是一个带有较少“冷战思维”的宗教人权组织。它于1991年成立,彼时距离冷战结束已有时日,在2000年以后尤其是“9·11”事件之后趋于活跃,这与国际社会、国际政治学界开始重视宗教因素不无关联。①关于宗教“回归”国际关系的著作与论文的梳理和总结参见徐以骅:“全球化时代的宗教与国际关系”,《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年第9期。它基本不具有冷战的连续性,其政治参与的理念缘起也是冷战后。多数学者也认为,20世纪下半叶以来的全球宗教版图变迁在使宗教问题国际化、造成基督教会与民族国家和其他不同宗教/民族之间以及基督教内部的紧张关系甚至冲突对抗等方面有直接作用,并且成为影响西方国家安全战略制定的因素。②涂怡超:“基督教福音派海外传教运动与当代国际关系”,徐以骅等主编:《宗教与美国社会——当代传教运动》(第六辑),时事出版社,2009年,第16-53页。事实上,宗教组织作为跨国对抗互相联系的基础已经为 19世纪以来的诸多跨国社会运动提供了强有力的联系渠道。而且,尽管许多运动的最初动力来源于跨国倡议的扩散,它们却常常依赖世界霸权国家的力量,并在不同的国家以不同的方式生根。③[美]西德尼·塔罗著,吴庆宏译:《运动中的力量——社会运动与斗争政治》,译林出版社,2005年,第246页。“倡议国际”这一组织的创始直接来自于美国颇具影响力的基督徒法律协会(Christian Legal Society)的先后两位领导人,因而在组织上、理念上与后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倡议国际不是传教组织转型而来的宗教人权组织,是“后冷战时代”的产物,基本不具有厚重的“冷战遗产”。在该组织看来,冷战结束后重建一些国家的社会和法律体系是首要的,基督徒律师想要有所作为,希望“用关爱维护正义”。④http://www.advocatesinternational.org/content/chronology-advocacy-mentoring-1991-201 0.
(二)宗教人权组织在宗教性跨国对抗中的作用
作为宗教性跨国对抗的行动者,形形色色的宗教人权组织都是提出要求方,即对抗主体。在诸多对抗主体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有些组织诸如“倡议国际”发挥了“中间人”(broker)的作用。关于社会运动中“中间人”的研究是非常令人感兴趣的。在20世纪80年代关于社会运动中“招募”、“动员”、“领导”等研究中,“中间人”是研究重点。近年来,“中间人”角色研究作为解释对抗政治的机制和过程部分再次得到关注。①Marisa von Bülow, “Brokers in Action: Transnational Coalitions and Trade Agreem ents in the Americas,” Mobilization: An International Quarterly, June 2011, Vol.16,No.2, pp.165 – 180, http://lasa.international.pitt.edu/members/congress-papers/lasa2010/files/1515.pdf.作为中间人,必须在关系网络中具备较悠久历史、较高声誉、较熟练的政治技巧等要素,才能在网络中担负起具有影响力的“领导”角色,他们并不是普通的行动者,而是具有权势者。特别是对于分散的个人和规模较小的组织来说,中间人的作用不可忽视,正是他们将所有这些组织联结到一起,推动了运动的形成和进展。玛丽莎·冯·布罗将对抗政治、政治居间和社会网络分析相结合,来分析美洲贸易协定谈判过程中代理人扮演什么角色,采用什么策略。她认为中间人能够积聚更多的社会资本,从而促进信息和各类资源的流通。他们还能吸引新的集体行动参与者。布罗借用“参与阶梯”的比喻,将中间人按照由易到难的次序排列分成四种角色,即传送者(translators)、协调者(coordinators)、联结者(articulators)、代表者(representatives)。②Ibid, p. 170.本文认为,在这一纵向的“阶梯”中,一项运动中作为“中间人”的组织处于阶梯的不同“台阶”上,一方面是因为地位不同,另一方面也是取向的不同。单从这四级角色阶梯来看,并无特别地表现出中间人的积极面和消极面作用,此处所谓的积极和消极是针对有效结束、化解“对抗”而言,并不是完全从某一方的立场出发。一类更愿意作为中间人在一定程度上化解“对抗”,他们不仅仅作为提出要求者一方的联络人,同时也可能成为对抗双方的联络人;而另一类则较为坚持其位于自身这一方的网络中,即使与对抗客体有所接触,也带有明显“对抗性”。
作为对于宗教和人权问题的“法律援助”组织,“倡议国际”在跨国倡议网络中是作为“中间人”角色出现的。可以看到,“倡议国际”与法律界的联系非常紧密,比如与基督教法律协会等组织定期的会议、集会等,另外该组织的国际顾问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法律界人士,诸如律师、法学教授等,因此相比之下,“倡议国际”与宗教人权组织联系是不定期且不紧密的。“宗教自由”是该组织为其亚洲分部定下的核心任务。因此,它们为“受限者”,诸如传教士、教会传递信息,提供签证、法律和其他方面的援助,并为一些国家关于宗教的法律条文提出建议,相对来说用较为温和的方式来处理其他国家内部的对抗政治,以这样的行为参与到福音派推进国际宗教自由的跨国运动中。例如2009年“倡议国际”的主席山姆·埃里克森(Sam Ericsson)和世界福音联盟的其他福音派领袖一起到访中国,与中国教会领袖和政府官员会面。在一些学者看来,埃里克森本人代表着能够与中国政府官员保持较良好关系的部分宗教人权活动者。①Allen D. Hertzke, Freeing God’s Children: The Unlikely Alliance for Global Human Rights, Lanham, Marylan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2004, p.87.
对于宗教人权组织来说,爬上中间人阶梯本身已是不易,要在阶梯中占据高位更需要持久和战略运作。跨国网络是多层次的,在一个网络中作为中间人,意味着有更多社会资本,具有更高地位、声誉,而在另一个层次的网络中可能就是普通的行动参与者。中间人本身也是行为体,只是分工不同,因此,其活动空间比一般行动者大。对于中间人来说,一旦在网络中确立了一定的地位资格,占据了一定的台阶之后,就意味着更多的责任,其行为反而易受到约束。一个社会运动要取得成效,有力的领导者是必须的。在宗教人权组织的网络中,宗教性更强的组织往往获得更高的声誉,具有更广泛和持久的影响力。
(三) 宗教人权运动的机制—过程分析
对于宗教人权组织的诸多机制—过程来说,最重要的莫过于传播、协同行动、界限激活和合法性确认。按照蒂利和塔罗的定义,传播是指对抗表演、对抗所针对的问题以及有关的解释性框架从一个地点向另一地点扩散。协同行动是指两个或更多的政治行动者针对同一对象而共同发出信号或共同提出要求。界限激活是指将两个政治行动者彼此区分的“我们—他们之别”明显增加。合法性确认则指某个外部权利当局发出信号,表示打算承认并支持某一政治行动者的存在及其所提要求。①[美]查尔斯·蒂利、西德尼·塔罗著,李义中译:《抗争政治》,译林出版社,2010年,第266—267页。
从宗教性跨国对抗的行为体来说,宗教人权组织扮演了发起者和中间人的角色。有些组织善于进行政治表演,比如“殉道者之声”在“国际宗教自由祈祷日”召集海外及国内的教会领袖和宗教人权问题方面的活跃个人或组织,讲述所谓的“受害经历”,或是在2008年奥运会前夕发放所谓“中国奥运祈祷箍带”,并将箍带送到了白宫;有些组织具有广泛的信息来源和经常性的网络更新,作为中间人担负起传播所谓“宗教受限”信息的任务,如大多数宗教人权组织都会定期或不定期发布“新闻简报”,将关于一些传教士、牧师等个人的故事汇总,或是以年度报告的形式将所谓“国际宗教自由状况”作“权威性”的解读;有些组织则善于利用政治机遇发出活动倡议,协同其他组织共同行动。而扮演“支持者”角色的则非美国之类的所谓“人权卫士”莫属,“宗教人权问题”已然进入美国外交政策的中心议程。②徐以骅:“宗教与冷战后美国外交政策——以美国宗教团体的‘苏丹运动’为例”,《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第199-200页。
此外,从技术方面来说,互联网对于大众对抗的推动力具有影响。政治抗议传统上主要依靠要求提出者(抗争主体)在街头集会,对权力拥有者进行抗议。互联网改变了这一行动方式,虚拟且有效地在网络上推进抗议理念和策略的扩散,并迅速传遍全球。由于较少受制于时间和地理空间,互联网使决策者面对其公共接触的便捷和影响的立竿见影感到措手不及。这一虚拟扩散,亦存在需要警惕的一面,因为互联网具有力量将不可靠的、未经证实的信息转化为全球的虚拟暴力/对抗。①Jeffrey M. Ayres, “From the Streets to the Internet: The Cyber-Diffusion of Contention,”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Vol.566,No.1,pp.132-143.需要指出的是,宗教人权运动的对抗形式事实上主要发生在虚拟的网络空间,它们重视互联网的作用,因而有些组织根据形势的变化和需要将网站内容改版,以增加关注度。
在这一跨国对抗过程中,宗教非政府组织提出并建构议题,通过互联网、基于教会的社会网络从草根到精英传播相关信息。具有专业背景的组织如“倡议国际”则从法律上对该问题进行拓展,使其不至于停留在与老传教运动类似的“宗教援助”方式上,同时其他规模不一的类似组织各显神通地与媒体建立联系,扩大影响,从而可以获得更多的公众支持,而与美国政府的互动通常能够赢得宗教人权运动的“合法性确认”。因此,在“1998年国际宗教自由法”即将到期的情况下,一些宗教人权组织诸如“门户开放”便急切动员民众写信给国会议员要求修改这一法案,并且要求提升“国际宗教自由大使”在国务院中的地位,以建立美国外交政策建制中和其他驻外大使同等的直接向国务卿报告的制度。②http://www.opendoorsusa.org/advocacy/amend-the-international-religious-freedom-act.“殉道者之声”也是这一活动的积极参与者。
三、宗教人权运动的争议和效果
当今世界,宗教—种族冲突并不少见,从波黑战争中的穆斯林、天主教徒和东正教徒之间的矛盾,到苏丹国内伊斯兰教法和基督徒、非洲传统信仰之间的分歧,宗教都是显而易见的冲突变量。对多数美国人来说,“宗教”和“人权”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同时也认为许多人权倡导者是宗教团体的杰出成员这一现象是自然而然的。①Johan D. van der Vyver & John Witte, Jr. eds., Religious Human Rights in Global Perspective: Legal Perspectives,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Preface, p.6.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人权问题的争论是北方国家和南方国家之间关系持久的一个分歧。②Johan D. van der Vyver & John Witte, Jr. eds., Religious Human Rights in Global Perspective: Legal Perspectives,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Introduction, p.13.在这场跨国抗争中,利益受损方是南方国家的政府,主要损失的是国家主权和安全,获益方是其余三者,但实际获益最大的却是北方/西方国家的政府。因为它们利用外交政策工具,以宗教人权议题施加国际压力,换取在其他方面的利益。宗教人权组织开展一些运动诸如反诽谤决议、苏丹运动等都涉及其他国家和非政府行为体、个人的利益,因而引起很大的争议。比如对于苏丹内部的宗教争斗,美国的一些宗教人权组织就扮演了中间人及行动者的角色,区别是各种组织分别扮演两种角色。如“倡议国际”和“门户开放”组织都对联合国的人权委员会/理事会的权威性表示一定程度的尊重,希望这一最大的国际组织能够在保护宗教人权方面使用其权威并给予他们行动的合法性确认,以表示明确的支持。而另一些组织诸如“殉道者之声”则转向寻求美国政府的支持。
在本文所研究的跨国对抗政治的四个行为方当中,对抗的发起者、对抗的对象、对抗的支持者都受到相当的限制,作为民族国家,无论是国内政治还是对外政策,能够调整和转寰的余地都相当小,而作为非政府组织的代理人/中间人是最具灵活性的,活动空间也较充分。从积极的角度来看,这类组织能够随局势变化及时调整策略,但是从消极面来看,这种灵活性亦有可能使得这类组织变得“不负责任”。尽管它们常常以“监督者”的形象出现,声称自己代表了“公平和正义”,国际社会却没有对这些所谓“监督者”进行监督的机制。此外,“监督”也往往意味着对他国内政的关注、介入甚至强硬的干涉,因此也对一些国家安全、主权造成损害。这也是“不负责任”的表现之一。另外一种不负责任是有选择性的传递信息,甚至误导。
塔罗等学者曾用“全球性社会运动”来描述全球化背景下的跨国集体行动。但是全球性社会运动并不见得是新社会运动,也不见得是单议题运动,且不一定是左派运动。而全球性社会运动也不一定是跨国对抗的一种。虽然所谓“国际宗教人权运动”并非全球性社会运动,但它作为跨国对抗的一种,可以被视为类似跨国的“新社会运动”,它和全球性社会运动有类似之处,比如它针对的不是本国政府,该运动组织与其所在国的互动形式以及该运动的发展仍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所在国的国家—社会关系的制约。①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290-297页。本文之所以不采用“全球化”这一术语是因为,宗教人权运动的核心命题并不是全球化带来的,全球化也未曾带来一个强势的全球性认同,跨国的宗教人权运动本身是一个较为弱势的社会运动。一方面其草根性是根深蒂固的,部分法律精英的参与并不能使整个运动带有更多的精英色彩,精英还是局限于自己的网络中;另一方面,对于宗教人权组织所在的民族国家来说(本文主要指总部设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组织),虽然也意图利用这一运动来干涉其他国家的政治,但是在自身的国家利益(主要是政治、经济、安全)面前,宗教和人权往往是撬动其他利益的杠杆。
四、小 结
正如塔罗所声称的,“关心别人的事”正逐渐成为今日世界社会和政治变化的一个重要助推力。②[美]西德尼·塔罗著,吴庆宏译:《运动中的力量》,译林出版社,2005年,第 254页。跨国对抗还体现出这样一个事实,即在多元化的社会中,对美国的基督徒特别是保守的福音派来说,强烈的跨国宗教认同是唤起他们“远距受难心态”③此处“远距离受难心态”是受到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远距离民族主义”(long-distance的最主要因素。除了个别宗教人权组织的领袖,诸如“殉道者之声”的创始人温布兰牧师夫妇等是真正经历冷战中两大阵营的对垒或是所谓“宗教迫害”之外,其他组织成员以及被动员起来的信徒,都只是“远距离受难者”。他们既不是亲历者,甚至也不是所谓“受难”信息的直接来源,他们也以“受难的基督徒”这一话语来界定自身。正是宗教这一“强跨国纽带”使跨国对抗成为事实。通过富有浓郁福音派气氛的集会、具有煽动性的“受难”信息,宗教人权组织把对“海外受迫基督徒”关注的潜在政治力转变为协同一致的运动,从而影响美国的外交政策。
赫茨克认为,美国福音派对“国际宗教自由”的倡议以复杂的方式与并行的人权运动交叉,在宗教自由方面给予以信仰为基础的联盟互相补充,有时则互相关系紧张。福音派的国际参与意味着它们对公民社会的影响力增强,而且,鉴于福音派人口的数量,这种国际参与可能作为全体公民孤立主义倾向的平衡力量,提高美国对外政策对各种人权提案的支持。①艾伦·赫茨克:“福音派及其国际参与”,《宗教与美国社会——当代传教运动》(第六辑),时事出版社,2009年,第250页。甚至像“倡议国际”这样的组织,在反对“迫害”的立法努力中汲取、积累了经验,还卷入人权倡议的其他领域。在美国福音派与海外基督教团体打交道的过程中,他们日益发现自己与其说是派遣传教士到海外的领导者,不如说是为英勇的本土信徒提供支持的“仆从”。
最后需要注意的是,“跨国对抗”本身不是一个完备的、包罗万象的理论体系,而是从新的视角来解释跨国政治行为的一个“工具箱”。提出并丰富这一视角的学者都是政治社会学领域颇有建树者,其学科背景和大量的国内社会政治的实证研究是发展出这一视角的基础。本文对参与宗教性跨国对抗的宗教非政府组织所作的初步研究是一个跨学科的尝试,以期从个案研究的基础上解释国际关系中的这一现象。
The RNGOs in Transnational Contention: A Case Study on“Advocates International”
ZHANG Jun (32)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美洲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Religion has been “neglected” in the studies of transnational contentions.However, with their increasing activism and involvement in transnational collective actions, the RNGOs (Religious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became a key actor in “religious transnational contention”. This paper seeks to explore the role of RNGOs which focuses on “religious human rights” in the transnational contention through a case study on “Advocates International”.
nationalism)的启发,这一概念指在西方移民社会,一部分人选择以民族国家的话语来界定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