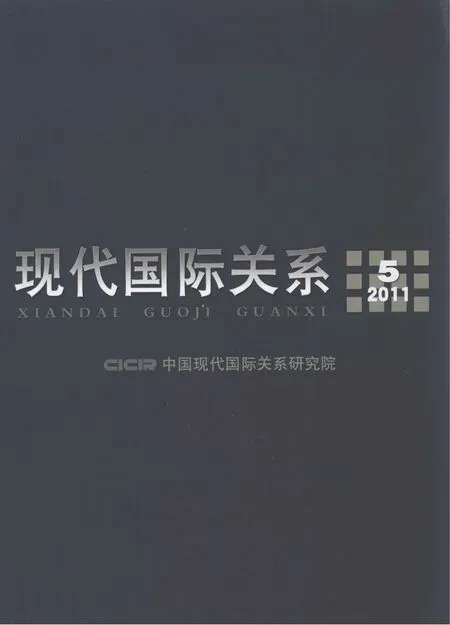中美关系的八大迷思
2011-12-23牛新春
牛新春
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其对国际经济趋势和国际政治格局的影响独一无二;同时,中美关系也是世界上最复杂的双边关系。冷战后,中美两国学者曾屡次试图找到一个言简意赅的词汇或词组来定位中美关系,先后提出过“战略伙伴”、“战略竞争对手”、“竞合”、“两国集团”等,但很快都归于沉寂。时至今日,对中美关系性质的概括最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还是小布什常用的“复杂”二字。正因为中美关系的复杂性,任何一种单一的逻辑、理论和视角在解释和预测中美关系时,都显得力不从心。对中美关系性质、问题和走向的研究,在过于简单或者不对逻辑前提进行批评性检验的情况下,存在着诸多似是而非、极具迷惑性的论述。下面是关于中美关系的八大迷思,作者将一一对之进行辨析。
第一个迷思:崛起大国与现存大国之间存在结构性矛盾,决定了中美关系的根本性质是竞争、矛盾和冲突。
这个判断基本上是错误的。“中美结构性矛盾”论是影响最大、最深的一种观点,在中美两国都有相当多的信众。一些国际问题学者相信“中美结构性矛盾”论,是掌握了以现实主义为基础的系统理论和严密逻辑;大部分公众则仅仅基于朴素的人际关系逻辑,从一把手与二把手、老大和老二的角度看中美关系而在潜意识里支持这种观点。米尔斯海默2001年出版的《大国政治的悲剧》是这种观点的代表。
米尔斯海默认为,目前世界上只有一个地区霸权,那就是美国在美洲的霸权。美国是那里唯一的大国,没有邻国与其展开安全竞争。例如,加拿大和墨西哥都未对美国构成任何军事威胁。①John J.Mearsheimer,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W.W.Norton&Company,2001,p.380.可见,成为某个地区的唯一大国,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能力与其展开安全竞争,就是所谓的地区霸权。他还预测,一个富裕的中国不是一个维持现状的国家,而必然是一个进攻性的国家,注定要谋求地区霸权。这不是因为富裕的中国就有险恶的意图,而是任何国家都想把生存机遇最大化,最好的途径就是建立地区霸权。如果中国经济持续发展,中国必然要采取进攻性对外政策,寻求成为东北亚地区的霸权,这将会引起中美之间的冲突。
“结构性矛盾”论的基本假设是,国际无政府状态是霍布斯式的,安全是稀缺的,国家的首要目标是确保生存和安全。除了地区霸权国外,所有国家都面临生存危机,追求地区霸权是每个大国的目标。大国为了追求最大程度的安全,必然要排他性地控制其所在地区。这种逻辑对冷战时期的国际政治有非常强大的解释能力,那时美苏争夺的就是对全球各个地区排他性的影响力和控制力,大体上把全球划分为两大阵营。但是,冷战结束已经二十多年了,全球化、信息化使国际政治性质发生了很大变化,美国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排他性地控制任何一个地区,而是追求“门户开放”政策,防止其他任何大国排他性地控制任何一个地区,特别是具有重要战略位置或战略资源丰富的地区,如中东、东南亚和中亚等。中美作为两个全球性大国,对国际影响力的竞争当然是存在的,均担心被对方排挤出某一地区,但是没有任何一方试图独自控制一个地区。
一方面,中美之间并没有像米尔斯海默预测的那样在东北亚地区发生全面的安全竞争。过去十年是中国崛起速度最快的时期,理论上,中国应当追求在东北亚的地区霸权,美国应当加大投入遏制中国的霸权冲动,而事实上,中国既没有在该地区寻求排他性的影响力,美国也没有加大对中国的战略遏制。相反,中国越来越认识到美国在东北亚的存在可能成为一种稳定的、积极的力量。中国在2009年的《中美联合声明》中指出,“欢迎美国作为一个亚太国家为本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作出努力”。①“中美联合声明”,人民网,2009年11月17日,http://world.people.com.cn/GB/10394969.html.(上网时间:2010年2月10日)这是中国首次正面评价美国在亚太的存在和影响。在米尔斯海默看来,中国一定是在长期执行错误的对外战略,因为这与他10年前所预测的“强大范式中国”的对外战略不一致。
另一方面,按米尔斯海默的观点,美国在美洲的霸权也丧失了,因为它并没有尽全力遏制中国在南美洲的影响力。中国与拉美的贸易额从十年前的120亿美元增加到目前的1400亿美元,而美国与南美洲的年贸易额约为2000亿美元。显然用不了多久,中国对拉美的经济重要性就会超过美国。奇怪的是,面对全球唯一地区霸权地位的丧失,美国并没有反扑,也没有采取相应措施,似乎听之任之。
如果说结构性矛盾是主导中美关系的最关键因素,那么就没有办法合理解释过去30年中美关系的发展过程。在中美关系中,安全主导一切的时代已经结束,相互依赖的重要性超过了安全竞争的重要性,“复合相互依赖”是中美关系的本质特征。在中美关系中,没有一个因素能够主导全局,经济、军事、政治关系都在各自的轨道上发展,都按各自的规模运行。“在这种概念下,利益冲突被分门别类地通过正常渠道解决,而不再动辄触及整个关系的根基。”②[美]江忆恩:“中国参与国际体制的若干思考”,《世界经济与政治》,1999年,第7期,第10页。中美两国依然存在“结构性矛盾”论所指的安全竞争,中国在南美洲的影响扩大,自然会引起美国的警觉,同样,美国重返东南亚也令中国担忧。但是,这种安全竞争仅仅是中美关系中的一项内容,并不能主导和统领其他领域的双边关系。
第二个迷思:追求全球霸权或领导地位是美国全球战略的本质和核心目标,从美国全球战略角度看,美国必然要尽可能迟滞中国崛起,至少不希望中国崛起。
这个判断只对了一半。前半句是对的,后半句是错的。前提是正确的,推论是有问题的。此一时,彼一时也。现在美国很少提“霸权”,而更多地使用“全球领导地位”了。原因很简单,正如米尔斯海默所定义的,霸权是对一个地区排他性的控制,现在美国在全球的政策显然不是这样。但是,历届美国政府都在努力维护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却是不争的事实。国务卿克林顿2010年9月8日在演说中称,“美国能够、必须而且将会领导新世纪”,③Hillary Rodham Clinton,Remarkson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at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Washington,DC,September 8,2010.其言辞之确凿、态度之坚定,似乎没有任何商量余地。
问题是,什么是美国所追求的领导权呢?或者美国追求什么样的领导地位呢?这关系到对美国这个国家性质的判断,关系到对美国全球战略的定位,当然也直接关系到美国对华政策的性质。克林顿国务卿指出,全球领导地位就是构建一种全球体系,包括盟国和伙伴网络、地区组织和全球性机构,以便把各个国家组织起来,解决共同问题。确立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包括以下六个步骤:第一,依靠最亲密的盟国,这些盟国同美国享有共同的价值观和利益,愿意一道解决问题;第二,对于正在成为美国伙伴的国家,美国要帮助提升它们的能力,让它们有能力解决自己的问题;第三,深化与新兴力量的接触,使其能发挥建设性的、地区的和全球的作用;第四,振兴美国跨大西洋、跨太平洋和全球的领导地位;第五,重新参与和改造现存国际机制,以适应新的挑战;第六,支持和保卫普世价值观。①Hillary Rodham Clinton,Remarkson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at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Washington,DC,September 8,2010.显然,今天美国想要的领导地位是对全球机制的主导能力,通过各种机制把全球重要国家吸收进去,而不是编织遏制中国的网络。如果美国想组织遏制中国的联盟,恐怕世界上没有多少国家愿意跟随。约瑟夫·奈就指出,“呼吁遏制中国的鹰派将无法打着这个旗号聚集起其他国家”。②[美]约瑟夫·奈:“中美关系的未来”,《美国研究》,2009年,第1期,第8页。只要中国愿意接受美国主导下的全球体系,美国宁愿在现存国际体制内与中国竞争,而不愿意遏制或围堵中国,因为那样做的成本更高、风险更大。
中国会不会拒绝加入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对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形成挑战呢?冷战结束之初,美国曾经非常担心出现这样的前景,制定了对华“接触”政策,试图把中国“融入”国际体系。但现在美国的这种担心已经基本消除了,转而担心中国能否在现存国际体系中承担应有义务。2005年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正式宣布,中国加入了大多数国际机制,中国已经是国际体系的一员了,并且中国是现存国际体系的受益者。③RobertB.Zoellick,Deputy Secretary of State,“Whither China:From Membership to Responsibility?”Remarks to National Committee on U.S.-China Relations,New York City,September 21,2005,http://www.state.gov/s/d/rem/53682.htm.(上网时间:2005年9月28日)现在中美之间斗争的不是中国是否加入国际体系问题,而是谁在体系中承担多少责任、享受多大利益问题。显然,通过遏制和妨碍中国崛起解决不了这个问题,而且会削弱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因为遏制中国经济发展,只能让美国的经济状况恶化;遏制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只能让美国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2009年11月14日,奥巴马在东京就美国的亚洲政策发表演说指出,在21世纪,一个国家的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不再以另一个国家的利益为代价,权力之间不再是零和游戏,国家之间不再需要担心对方的成功。他强调美国欢迎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大的作用,美国不会寻求遏制中国。④Remarks by President Barack Obama at Suntory Hall,November 14,2009,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remarks-president-barack-obama-suntory-hall.(上网时间:2011年4月20日)事实上,没有中国的参与,美国不可能独自解决任何全球重大问题。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怎么可能遏制中国呢?!
当然,美国认为中国的未来具有不确定性,担心中国在韬光养晦后突然挑战美国。但是这种担心并不足以让美国目前就放弃合作带来的巨大利益,转而采取以遏制为主的政策。至少到目前为止,美国对华政策中合作、协调是第一位的,防范、遏制是第二位的。
第三个迷思:2001年至2009年中美关系长期保持稳定是因为美国受制于反恐战争,无暇顾及应对中国崛起。因此,2011年美国再次陷入中东乱局,中美关系又一次迎来了机遇期。
这个判断有一定道理,但并非决定性因果关系。这个判断关系到21世纪头十年中美关系的改善是内因主导型的,还是外因影响型的。如果是内因主导,就标志着中美关系的性质发生了一定的变化,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反之则不然。回顾过去十年中美两国的内外政策变化,至少有两大动向值得关注。其一,中美关系最稳定的十年,是美国专注于反恐的十年。其二,中美关系最稳定的十年,也是中国崛起最快的十年,中国参与国际事务最广泛的十年。比较而言,中国自身变化的因素应当更重要。一个强大、自信、国际化的中国,是中美关系保持长期稳定的重要前提之一。
一方面,中国越强大,对美国的利害关系越大,合作就越是美国的最优选择。经济上,经过十年发展,中美两国谁都离不开谁,都希望对方经济繁荣。目前,中美两国互为对方第二大贸易伙伴,依赖性不言而喻。中国是美国第一大债权国,美国持续不断的财政赤字离不开中国的投资,中国居高不下的外汇储备也需要美国的投资市场。中美之间的经济对抗能力被称为“经济恐怖平衡”,正如当年美苏之间“相互确保摧毁”战略一样,“经济恐怖平衡”能保证中美之间稳定的经贸关系,任何一方都不能承受大规模经济制裁的损失。①Jim Hoagland,“The Lukewarm WarW ith China”,TheW ashington Post,April 16,2006,p.B07.在经济相互依赖程度加深的同时,在全球事务中美国也日益离不开中国的支持。在亚太,朝鲜半岛问题、南海安全、巴基斯坦问题、缅甸问题等,均不可能在中国缺席的情况下解决;在全球,伊朗问题、气候变化、核不扩散、苏丹问题等,中国均能发挥重要作用。在中美传统问题没有任何一个得到解决的情况下,中美相互复合依赖程度的提高,是中美关系拓宽和加深的基础。
另一方面,一个自信、国际化的中国更有可能与美国建立良好的关系。改革开放三十年,是中国不断探索参与国际社会的三十年。事实证明,当中国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状况良好,中国的自信心比较强时,中国就乐于广泛参与国际机制、愿意参加国际合作。在朝核问题上,中美共同创建了六方会谈机制,合作通过了联合国安理会的三个制裁法案。在苏丹达尔富尔问题上,2006年中美共同支持三阶段和平协议,2007年中国派出300名工程兵,成为达尔富尔首批非洲国家以外的维和人员。在缅甸问题上,2007年6月在中国的斡旋下,美国与缅甸在北京举行了助理国务卿帮办级磋商。2008年5月在中国的帮助之下,美国军用飞机把国际援助源源不断地运入缅甸。在伊朗核问题上,中国先后支持联合国安理会关于伊朗核问题的三个决议,要求德黑兰完全停止与铀浓缩有关的活动和核废料再处理活动。在利比亚问题上,中国在授权设立禁飞区问题上没有投反对票。过去十年是中美两国在联合国安理会合作最好的十年。
美国因专注反恐而无暇顾及中国,意味着美国没有精力给中国崛起制造麻烦,中美关系可以免于倒退,但是无法解释中美关系的基础在拓宽,中美国际合作在增加。实际上,小布什政府是冷战后美国四届政府中在全球战略上最具有进攻性的一届政府,打了两场地区战争,组织了制裁伊朗、朝鲜的国际联盟,搞“大中东民主化”计划,驻兵中亚,加强同印度的合作,其进攻性的对外战略让美欧关系、美俄关系等陷入了危机。在这种背景下,唯独中美关系一枝独秀,除了中美关系内生性主导因素外,用其他外部因素很难解释。
第四个迷思:2010年中国采取进攻性的、扩张性的对外政策,是中国国力和自信心增强的体现,是中美关系动荡的主要原因。
这是部分美国人对2010年中美关系动荡原因的解释,显露出他们对中国内政的不熟悉。持这一观点的人只看到了两个表面现象——中美实力对比的变化和中国对美的一些强硬态度,并且自然而然地把这两个现象看作因果关系,把先后逻辑当成了因果逻辑。
中国崛起是一个长期趋势,但2007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国一枝独秀的表现尤其让美国人印象深刻。当美国等西方国家经济出现负增长的时候,中国经济增长仍然维持在8%左右的高位;当美国等西方国家出现超负荷财政赤字时,中国却出现了大量财政盈余;当美国国内因为高铁、清洁能源等问题争得你死我活的时候,中国已经开始大规模建设了;当美国之音、BBC因预算问题计划停止对华广播的时候,中国政府却投资数百亿美元扩展国际媒体。正所谓不患富,而患独富,强烈的对比让美国人心里失衡、恐惧。与此同时,美国人似乎看到了他们预期中的事情。2009年年中在南海发生了“无瑕”号事件,年底中国在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上强硬回应美国的要求,2010年初中国强势批评美国对台军售、奥巴马会见达赖,年中中国外交部激烈谴责美国干涉中国南海事务,坚决反对美国航母进入黄海演习,稍后中国又坚持要求日本就钓鱼岛撞船事件道歉。许多美国人解读,这一系列事件表明中国正在远离“韬光养晦”的传统外交思想,而采取诸多进攻性、过分自信的政策。
美国人自然而然地把上述两个现象以因果逻辑联系起来,认为强大后的中国必然采取进攻性的对外政策。然而,美国人没有足够重视中国出现的另外两个现象。一方面,通过奥运会、世博会和亚运会的成功举办,以及“神六”升空和金融危机时期中国经济的良好表现,中国普通民众的民族自豪感和国际自信心已被充分调动起来,要求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有更亮丽的表现;另一方面,西方国家一些人以人权为理由抵制奥运开幕式,境内外各种势力勾结给奥运火炬的境外传递制造种种麻烦,并且给奥运安保制造了非常大的难题;同时,中国又发生了举国震惊的西藏“3·14”和新疆“7·5”事件。正如中国一位著名学者指出的,“通过对中国历史的独特解读,中国领导人长期以来对外部威胁引发的国内动乱非常敏感”。①Wang Jisi,“China’s Search for a Grand Strategy”,Foreign Affairs,March/April 2011,p.69.民族自信心增强和政治脆弱性凸显,使中国在处理对外关系时压力陡然增加,操作空间缩小。仔细分析美国所列举的案例,所谓中国外交的转变,均是言辞和态度上的变化,而非实质性行动。
美国误读中国的外交行为,源于将中美关系当作双边博弈,认为中国的行为就是针对美国的。然而,中美博弈是多方博弈,中国的外交行为要同时向美国、中国国内和周边国家传达信息,甚至有的时候美国并不是主要考虑对象。
第五个迷思:2009年奥巴马的积极对华政策未取得预期成效,2010年其对华政策转趋强硬,奥巴马应对当年中美关系恶化负责。
这是部分中国人对2010年中美关系动荡原因的解释,反映出他们对美国内政不甚了了。2009年奥巴马政府的积极对华政策是存在的,2010年奥巴马调整对华政策也是确实的,对中美关系恶化负责也是应当的,但是这之间并不必然存在因果关系。其关键在于奥巴马政府的政策优先目标发生了变化,引起对华决策模式和对华政策的变化,由此造成中美关系的不正常起落。
2009年上台后,奥巴马把执政重点放在了稳定金融秩序、推动新能源法案上,中国对其而言至关重要。在金融方面,中国手中持有近万亿美元美国国债,确保中国不抛售美国国债是美国金融稳定的头等大事。在新能源法案问题上,能否就气候变化问题与中国达成一致,直接关系到国会是否会通过新能源法案。因此,在美国最关注的两件大事上,中国都有很大的发言权。在这种情况下,中美关系中一切不和谐因素都被美国“和谐”掉了。这一时期,白宫亲自掌握对华决策权,主导和调度对华政策的方方面面,其他政府部门必须跟着白宫的主旋律起舞。2009年美国内阁官员纷纷访华,都在讨论金融合作和气候变化问题,人权不谈了,对台军售推迟了,达赖访美被劝阻了,就连“无瑕”号事件都被“低调”了。进入2010年后,美国稳定金融体系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增加就业、创造出口成为奥巴马政府的首要目标。为此,奥巴马推出“国家出口战略”,提出了“出口倍增计划”,规定未来5年增加200万个就业机会。在增加就业阶段,作为“世界工厂”,中国是美国重要的竞争对手。因此,从2010年开始,中美两国在经济领域的斗争日趋激烈,从汇率问题到不公平贸易问题,此起彼伏。更重要的是,由于奥巴马的新能源法案在国会受阻,气候变化议题从美国的重要议事日程上消失,中国对美国的重要性急剧下降。尽管中美两国之间有许多共同利益,但是2009年主导中美关系的两大议题消失后,没有任何一个新的议题足以让白宫专注于中美关系。于是,中美关系的决策模式从“白宫主导时期”进入“自由漂流时期”。在“白宫主导”的外交中,以国家安全委员会为中心,由总统直接控制。而在“自由漂流时期”,决策模式是“内阁主导”,由国防部、国务院和财政部等各部门各行其事。这时,被白宫“和谐”掉的问题都浮出水面了,对台军售、会见达赖、人权和海上安全等问题接踵而来。
可见,中美关系从2009年一路高歌状态转向2010年一路颠簸,可以说是从“非正常”转向了“正常”。由于中美两国之间的实力差距依然显著,美国在中美关系中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中国还在担当反应和应对角色。未来中美关系的走向,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的政策需求。
第六个迷思:美国重返东南亚是冲着中国来的,中美在亚太地区全面安全竞争的时代来临。
这个论断说对了一部分。美国重返东南亚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不仅美国政府自己高调宣布,而且近两年也确实做了一些事。美国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和东亚峰会,任命驻东盟大使;2010年在纽约主办了美国-东盟峰会,2011年将在檀香山主办APEC峰会;克林顿国务卿公开在多边场合宣布,南中国海涉及美国利益,提出“航行自由、和平解决”的原则。但是,就此认为美国重返东南亚就是针对中国的,却有失偏颇。
首先,美国重返东南亚有平衡中国影响力的意图。自从越南战争结束后,美国对东南亚的接触一直是试探性的。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美国反应迟缓,中国则快速、大规模介入,国家形象在东南亚地区迅速上升。从小布什政府开始,美国已经在修正自己的东南亚政策,在2004年的大海啸中,美国救灾反应非常及时,形象得以改善。但是,由于美国专注于伊拉克、阿富汗战争,错过几次东南亚地区的峰会,给人造成了美国忽视东南亚的印象。与此同时,中国在东南亚的影响力快速上升,美国的影响则在下降,这引起了美国担忧。作为一个全球性大国,美国要确保在世界上任何一个重点地区的影响力,防止其他大国排他性的影响力,这是美国全球领导地位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中美之间的这种影响力竞争不同于遏制或围堵。
其次,美国有意缓解亚太国家对美国战略收缩的担忧。同小布什时期的扩张性全球战略相比,奥巴马政府明显采取收缩性全球战略,希望把国家战略的重心转向国内。2010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指出,美国要追求一个民族复兴和全球领导地位的战略,即重塑美国实力和影响力的基础,而第一步必须从国内开始。①“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The White House,May 2010,http://www.whitehouse.gov/sites/default/files/rss_viewer/national_security_strategy.pdf.(上网时间2011年5月3日)显而易见,对于美国这样一个全球性大国而言,这是一个非常“内向型”的全球战略。亚太国家普遍意识到美国的战略收缩态势,担心在金融危机冲击下,美国会减少对亚太的安全投入。为增强亚洲盟国对美国的信心,也为了增强自信心,美国开始了重返亚洲的步伐。越是在影响力下降的时刻,美国越要显示自己是负责任的。
一方面,应当看到,美国平衡中国影响力的企图将增加中美在亚太的摩擦和冲突。随着中国海军现代化的推进,以及中国在东南亚和整个亚太地区影响力的扩展,中美在军事、政治和经济领域的纠纷将不可避免增多。但是影响力竞争同经济竞争一样,并非零和游戏。东南亚国家在欢迎美国重返的同时,没有一个国家希望中国撤出。尽管解决和缓解两国地区影响力竞争的挑战非常大,但是并非不可为,双方和平共处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另一方面,更应当认识到,美国有可能成为东南亚地区和平稳定的一支积极力量。美国加大对东南亚的关注力度,并没有推翻此前的东南亚政策,依然谋求当离岸平衡手。也就是说,美国不可能公开在站在哪一边,而是基本保持中立立场,做东南亚地区权力平衡的保护者。由于中国实力上升快,理论上美国将站在东南亚国家一边,帮助它们平衡中国。从1980年代以来,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国力虽越来越强大,却一直坚持以和平手段解决领土争端。但是随着中国实力增强,同中国有领海争端的国家不可避免地产生恐慌感。新加坡《联合早报》2011年4月18日社论指出,与中国有争端的国家或地区应尽早与中国谈判解决纠纷,才能最大限度争取利益。②“尽早与中国和平解决争端”,新加坡《联合早报》,2011年4月18日。与此同时,肯定也有一些国家相信,晚挑衅不如早挑衅。在此情况下,美国虽意在平衡中国的影响力,实际上能帮助中国安抚东南亚国家,让它们感到放心和安心,不要急于挑衅。
第七个迷思:人权价值观外交是虚伪的,是美国打压中国的一个借口和幌子,是美国对华大战略的组成部分。
这个论断对错参半。美国对华政策中始终存在人权外交,未来也将继续存在,有时是真实的,有时则是伪善的;有时是对华战略的有机组成,有时则同美国整体对华战略背道而驰。
美国生来就是一个重视普世价值观的国家,一位美国驻华外交官称这是美国的基因。有学者指出,“美国是一个具有教会灵魂的国家”,“你看到的美国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个庞大的教会”。①G.K.Chesterton,W hat I saw in America,New York:Dodd,Mead,1923,pp.11-12.这个国家关注普世价值观在全球的传播不是虚伪的,而是真实的,并且是离不开的,这是美国之所以成为“美国”的根源之一。当美国言行一致帮助别人改善人权时,它的人权外交是真实的;当美国口惠而实不至、不愿意为改善别国人权牺牲自己的利益时,它的人权外交就是伪善的。
人权外交有时同美国的大战略是一致的,但更多时候是相冲突的。这种情况下,美国常常会牺牲所谓的价值观目标,服务于国家利益。美国无数次不顾价值观冲突,与自己所认定的独裁政权结成联盟。即使这样,美国也并非完全放弃人权价值观外交。例如在中东地区,美国同一些独裁政权结成盟友,却同时支持这些国家内部的反政府运动。在中美关系中,人权外交同美国“亡我之心不死”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不能简单地将美对人权、西藏、新疆和台湾政策等同于美国就是要分裂中国、推翻中国政府,并非美国在所有这些事件上采取的行动都是“亡我”大战略的一个组件。正如美国中国问题专家傅立民指出的,中美关系一直是并仍然是利益来驱动,而不是以价值观为基础。②[美]傅立民:“对中美关系变化的展望”,《美国研究》,2009年,第1期,第8页。依据价值观采取的上述一些对华政策往往不符合美国利益。
当美国想破坏中美关系时,人权价值观就是一个很好的工具和手段,但是当美国想推动中美关系时,人权价值观就是一个障碍。就当前中美关系而言,人权价值观日益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牵制因素。在中国方面看来,人权外交是美国政府手中的一个便利工具,想用的时候就拿来敲打一下中国,不想用的时候就弃之一边。在美国政府看来,人权外交不是一个想用就用想丢就丢的工具,而是一个必须供奉起来的牌位,任何时候都不能丢,已经成为一个烫手山药。在人权和利益之间选择时,美国政府往往很纠结。例如,美国国务院最近给一个反对中国政府的技术公司拨款150万美元,“尽管奥巴马和克林顿支持互联网自由,但这个决定在政府内部非常有争议”。一部分人担心,这样的举动将激怒中国政府,影响中美之间的广泛合作。③John Pomfret,“U.S.risks China’s ire with decision to fund software maker tied to Falun Gong”,W ashington Post,May 12,2010,p.A01.
第八个迷思:台湾是中美关系发展的最主要障碍,美国应当“弃台”来发展中美关系。
这个想法是好的,但是严重脱离实际,反而会损害中美关系。台湾问题始终是影响中美关系发展的一个障碍,过去三十多年中美两国主要依靠有效管控其负面影响来追求双方共同利益。当然,如果美国真能彻底弃台,一次性割除中美关系中的这个毒瘤,对中美双方都是好事。正因为这事太好了,所以不可能是真实的。
最近,美国前参谋长会议副主席比尔·欧文、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查尔斯·格拉泽、美国前驻华大使普里赫都认为,美国应检讨《与台湾关系法》,解除中美关系中最难办的对台军售问题,甚至放弃对台湾的安全承诺。④Charles Glaser,“W illChina’sRiseLead toWar?”Foreign Affairs,March/April 2001,pp.80-91.“弃台”论并不新鲜,从1949年至今不断有人提出,但从未被美国政府认真考虑过。原因在于,台湾问题不仅仅是台湾问题,而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问题。
摩根索把国家之间的争端分成三类,一是“单纯争端”,是两个没有任何紧张关系的国家之间存在的争端,或者两个国家之间虽然存在紧张关系,但是这个争端与紧张关系没有关联;二是“作为整体紧张关系一部分的争端”,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就像一座冰山,这个争端是露出水面的一角;三是“作为紧张关系代表或象征的争端”,看起来像一个“单纯争端”,实际上代表着两国的整体紧张关系。⑤Hans J.Morgenthau,Politics among Nations: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New York:Alfred A.Knopf,1948,pp.344-346.
台湾问题是第二类和第三类争端的结合体,既是中美斗争中的一个实质性问题,又是中美对立的象征和代表,这类争端最难解。中美之间有诸多争端,从贸易、货币到人权、安全议题,台湾问题只是其中之一。固然,台湾问题是迄今为止中国政府界定为“核心国家利益”的唯一的单一外交议题。⑥Wang Jisi,“China’s Search for a Grand Strategy”,Foreign Affairs,March/April 2011,p.71.但是,在复杂的中美关系中台湾问题不是唯一的争端,而是中美紧张关系这座冰山的一块,它直接关系到中美之间的安全竞争、影响力竞争。
更重要的是,台湾问题在中美斗争中具有很强的象征性意义和代表性。对中国而言,完成台湾统一,不仅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个重要象征,也是中国成为世界一流强国的标志。对美国而言,维护对台湾的安全承诺事关美国的全球信誉和全球领导地位。一位美国学者指出,台湾使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与美国强烈的荣誉感产生了碰撞。①[美]傅立民:“对中美关系变化的展望”,《美国研究》,2009年,第1期,第8页。台湾问题陷在如此复杂的背景之中,中美任何一方都不可能轻易退让。过去三十年,中美关系在其他方面发生了重大变化,但在台湾问题上的态度基本未变。“弃台”论者错把台湾问题当作摩根索所指的第一类冲突和第二类冲突的结合,而不是当作第二类和第三类的结合。
就其复杂性和立体性而言,可以将中美关系视为一个“综合性难题”。在判断中美关系的性质和趋势时,既不可能有一个单一的简洁而完美的论断,也不可能一掌毙命式地击垮一个假说。尽可能多地提供事实判断,尽可能多地提出假设,尽可能多地寻找因果机制,让不同的事实、逻辑和假设之间互相验证、否定和补充,才能逐渐产生更深刻、更有说服力、更接近事实的判断。否则,一些简单、粗糙的判断就会落地生根,久而久之成为集体思维定势,禁锢深入的研究和深刻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