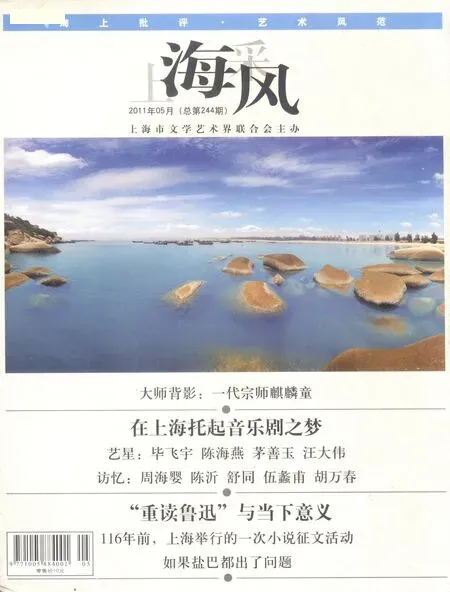追忆家父周海婴先生
2011-11-21周令飞
周令飞
追忆家父周海婴先生
周令飞
2011年4月7日凌晨5点36分,家父周海婴先生在北京医院病逝,享年81岁。父亲自去年5月开始入院治疗,近一年的时间里一直在与病魔进行抗争,弥留之际依然念念不忘弘扬鲁迅文化的事业。在离世前二十多年,父亲一直在为鲁迅奔忙着。
很多人认为在祖父鲁迅的盛名之下,父亲的一生承载着“不能承受之重”。父亲确实也曾说过:“我是在一个‘人场’的环境下长大的,就像磁场,我被这个‘人场’控制着。”然而,父亲又说,鲁迅在给他压力的同时又一直在鞭策着他,父亲延承了祖父的坚韧执着以及对社会的强烈使命感。或许父亲海婴先生的一生过于沉重了一些,但是这对他来讲也是一种历练的过程,他的一生是成长的一生,不停地在成长,在最后一刻还在健全他的整个人格。如果回顾他成长的过程,我认为可以归纳为三个阶段。
北大物理系读书时,同学们在打桥牌、跳交谊舞,父亲出于好奇,偶尔走去观看,马上有人在背后指指点点,说“鲁迅的儿子不好好读书,只知道打牌跳舞。”父亲只能选择沉默,黯然离开。父亲大学学习的是无线电,工作始终是行政管理,父亲是记住了鲁迅临终那句针对他的遗言的:“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然而,周围人还是拿着不同的尺子来丈量他,对他提出一些苛刻的要求。所以最初,在一个绑手绑脚的、不平等的环境中,那时候的他是想要远离的,这是父亲的第一阶段。
但是,上世纪80年代以后,市场经济让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有很多个人打着集体甚至政府的旗号在侵权,其中,对鲁迅的知识产权的侵权行为也越来越严重。对于这些事情父亲是很看不惯的,他觉得,过去,我们把鲁迅的一切几乎都交给国家了,是为了纪念,是为了研究和宣传,是为了公益事业,怎么会有个别人拿鲁迅去赚钱呢?从我父亲的思维角度想,你私人拿去赚钱的话,那我是继承者,你当然要征求我的意见了,我同意也好不同意也好,都是我的权力。实际上我父亲并不懂法,他只是从一个“人”的角度考虑,我是他儿子,你都不理我,就躺在别人身上去赚钱,这道理上说不过去呀。而且父亲发现,不仅是鲁迅的权益被公然侵犯,几乎所有现代文化名人的、尤其是一些左翼作家的后裔的权益也被冠冕堂皇地剥夺。他感到了必须进行维权活动的重要性。由此父亲开始了第二个成长阶段,他不再逃离祖父的光环,而是选择拿起法律的武器,无所畏惧地站出来。耿直的他无法忍受“背负着鲁迅儿子的重负却几乎不能直率地表白,当把所有鲁迅遗物捐出去以后,从此就开始被当成了花瓶”。
直至2000年,父亲已经在维护鲁迅权利的路上很辛苦地走了十几年。但他尚未彻底赢得一场官司,却已经收获了许多白眼和骂名,比如说:鲁迅的儿子不孝;周海婴真让他的父亲丢脸,竟为了钱对簿公堂;周海婴死要钱贪得无厌,要了还想要,他还算是个共产党员、全国人大代表吗?父亲曾告诉我:“不仅仅是朋友,甚至于有一些有权力的知识界人士、领导干部也这么认为。他们也爱护鲁迅,但是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他们对我说,鲁迅这么伟大,那么你这个鲁迅的后代,就绝对不能提权或者钱。这些都不能提。提了好像就丢了脸。甚至有一位领导来找我,很亲切地跟我说,海婴啊,你是鲁迅的儿子,你要爱惜你父亲在社会上的影响啊!”
各种不理解、责备甚至辱骂扑面而来,父亲顶着“鲁迅不孝子”的恶名以及极大的委屈坚持了下来。他的内心是非常坚强的,他有着科技行业人士的思维,一是一、二是二,只要他认为是对的,就非得坚持。而且我父亲是不轻易下决心的,一旦认准了道路,就会一直走到底。当别人对他冷嘲热讽时,他嘴上不讲,只是淡淡的一笑,但是心里很清楚,这个事情是对还是错。当谈论某事时,他会当面锣对面鼓地把意见提出来,把自己的观点亮出来,有时会让人觉得他不够圆滑,有时还会得罪人。但是我觉得现在社会上像他这样敢讲真话的人太少了。
1999年,我正在上海,看到父亲维权辛苦,又经常被人家骂,觉得不应该让他一个人去承受这些,太难为他了,我就开始帮他。帮着帮着我们就觉得家属应该成立一个机构出面维权,来做一些事情。2002年3月我们成立了上海鲁迅文化发展中心,将父亲个人的维权活动,提升为一个机构、一种事业来开展,以机构对应机构,以集体方式开展活动,以规模化经营推进文化事业。而以后许多与鲁迅有关的活动都得以迅速启动,获得广泛支持。
经过多年不懈的努力,我们已经促成北京、上海两个鲁迅博物馆纪念馆整理出鲁迅捐赠物品清单;维护鲁迅权益,由单纯的稿酬案、著作权官司,延伸到肖像权系列诉讼案、名人姓名权案、商标注册权案、冠名权案、网络域名抢注案等等,为这十年里中国的法制建设、尤其是知识产权法律法规的健全和完善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用著名律师朱妙春先生的话说:通过鲁迅系列法律官司,我们为当代法律建设开创了许多先河。特别是2008年3月直接在全国政协会议上提出《关于〈从鲁迅纪念馆看健全文博工作〉的提案》《关于〈健全名人姓名注册中文域名〉的提案》,更是法制建设里的重要举措。
同时,在为维权奔忙的过程中,我们又发现一个问题:在已经存在的对鲁迅的认识和理解中,鲁迅的真实形象显得遥远而模糊,这不是我们家属认识的鲁迅。父亲开始感觉到维权是一部分,更重要的是要弘扬鲁迅精神,还原鲁迅的本来面目。为此,2001年父亲完成并出版了《鲁迅与我七十年》,第一次从他个人的角度,讲述鲁迅作为一个父亲的具体形象和精神品质,还原一个慈爱、温暖的人间鲁迅,彻底把“思想家、革命家”意识形态虚构的鲁迅释放出来。而且,这本书的出版,以其真实、勇敢的回忆和敏锐的话题,激起非常强烈的社会反响。之后,父亲与我又整理出版一系列鲁迅有关著作,如《鲁迅家庭大相簿》、《两地书原信》、《鲁迅回忆录》手稿本、《鲁迅大全集》等等正本清源的鲁迅还原工作。
在出版还原鲁迅本来面貌的图书同时,父亲与我还开展了一系列鲁迅宣传、普及活动,如2006年为纪念鲁迅逝世70周年,在上海、广州、深圳、香港、澳门等地举办“鲁迅是谁?”系列图片展,以及相应的专题讲座;又如自2005年以来,逐年举办的“鲁迅论坛”活动;2009年以来每年一度的“鲁迅青少年文学奖”评选等。
我以为,在这个时刻,父亲已经成长到第三个阶段了,他在为纷纭混乱的社会文化乱相担忧:鲁迅精神与鲁迅思想,是二十世纪以来代表着中华民族先进文化方向的文化遗产,而如今,从商业上的无序滥用盗用,到中小学教育有意淡化鲁迅精神教育,再到儒家文化无限复苏、封建专制思想死灰复燃……这些都表现为鲁迅精神的丧失。他希望能通过重新梳理、弘扬鲁迅思想精神来推动文化的开拓创新、民族的复兴。为推动鲁迅研究走向一个更深更新的研究空间,2009年我们在同济大学成立了鲁迅研究中心,组织海内外数十位专家学者开展《鲁迅思想系统研究》和《鲁迅社会影响的调查报告》的专题研究(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并在每年举办学术会议,邀请国际国内知名学者探讨鲁迅思想传播问题。
在这些工作中,父亲受着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的推动,不顾年迈,越做越起劲。父亲与我也相互鼓励,碰到困难会相互商量。在工作中,虽然他是我的领导,但是很民主,会听取我的意见、想法;在生活上他是我的父亲,他的言行举止让我感到他的执着、韧性与我的祖父很像。在家庭里父亲的凝聚力也非常强,我们做的所有的事情,都得到了我的兄弟和妹妹的理解与支持。当然这有一个过程,一开始,他们认为不要自找麻烦,因为维权过程中也听到了一些批评的声音,辱骂的声音。大家就觉得何必呢?尤其是我母亲,觉得父亲年纪大了,别再管这些事情了,也没什么好处啊。确实,我们所做的很多事跟利益是没有关系的。
但是我父亲为什么这样做呢?因为他觉得总要有人出头做这些事情,作为鲁迅的家属,更应有大是大非的观念,在很多事情上要讲原则。他认为如果大家都不关心,都不去做的话,这个国家这个时代这个民族是没法一直往前发展的。也许这样说显得在讲大道理,但是父亲确实感受到肩头的沉甸甸的责任,作为名人后代的责任感。现在有很多人都事不关己,不愿意受名人之累,只想过平淡的生活,这也可以,但是不要忘了身上的责任啊,既然继承了某某名人后代这样一个名号,应该切切实实做点传承的事情。就是抱着这样的观念,即便在最后的时间里,只要父亲能动,就一直在做还原鲁迅、弘扬鲁迅的事情。父亲和我都认为,如果革命干部、革命烈士、各个领域的名人后代,都有传承革命的先进优良传统的使命感和责任感的话,相信我们的国家会更好。
如今,上海鲁迅文化发展中心已经成立9年了,做了一系列的工作,有了一定的成效。但是依然困难重重,第一我们没有经费来源,第二家族成立的组织还是有很大的局限。父亲认为鲁迅的事情,我们家族要参与,但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参与进来,所以他希望能成立基金会,用基金会的力量争取到更多的支持和赞助,维护公益的文化事业,这也是这几年他和我商量思考过的必须要采取的途径。去年5月份父亲有过一次病危,他写了一份求助书,求助大家一定要把鲁迅基金会成立起来。后来他的病情慢慢好起来了,这封信也没有寄出。近一年时间里,他的病情反复了好几次,我一次一次赶去北京,他把我赶回上海。他对我说,北京有子女可以照顾他,而上海鲁迅文化发展中心这边有很多事情需要我去做。父亲一直记挂着今年鲁迅诞辰130年的纪念活动,他把这件事情看得非常重,他觉得如果这一年的事情没有好好做的话,对纪念、延续鲁迅文化的传统会有很大的影响,会成为一个断档。
我觉得父亲真的很不简单,他的意志非常坚定,他不像一般老人那样考虑的是如何安享晚年,考虑的是小家庭里的一些琐碎事。在今年的一月份,他就做了一个托付,和我谈了一天关于身后的安排,我按照他的意思写好了,之后又稍作修改,他就签名了,以后再也没有提过,他是很干脆的。父亲最后的日子里,主要关心的、谈论的始终是,今年鲁迅诞辰130周年的纪念活动怎么办啊,进行得顺利不顺利啊,进度是否来不及啊。那时父亲只能带着呼吸机面罩听我汇报工作,表情非常痛苦。因为带着呼吸机,不方便讲完整的话,我就和父亲商定,由我来讲,他认同就点头,不认同就摇头,父亲临终前的那段日子,我们经常是这样来沟通的。父亲当时的意识还是非常清楚的,比如提到文化复辟的事情,提到天安门广场上的孔子像,他就一直在摇头。即便身体非常虚弱,父亲依然坚持颤抖着手签上自己的名字。父亲在其生命的最后一刻,可以把所有事情都放在一边,只关心鲁迅文化的弘扬,让我非常感动。
目前,父亲还有三件待实现的心愿,一是出版首部1500万字36卷的《鲁迅大全集》,二是成立全国性的鲁迅基金会。这两件事都已经进行了五年有余,预定在今年9月25日鲁迅诞辰130周年纪念日前完成。三是把鲁迅诞辰130周年纪念活动办好,而且他认为今年比往年尤为重要(详情可参考父亲的政协提案)。我们会帮他完成。几十年来,父亲遇到了很多的困难,家里人也曾劝他知难而退,但是父亲坚持了下来。父亲认定了方向就义无反顾往前走的执着,是对我们后代的极大教育和鞭策。现在父亲不在了,但我们会继承他的遗志,继续奋斗。
2011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