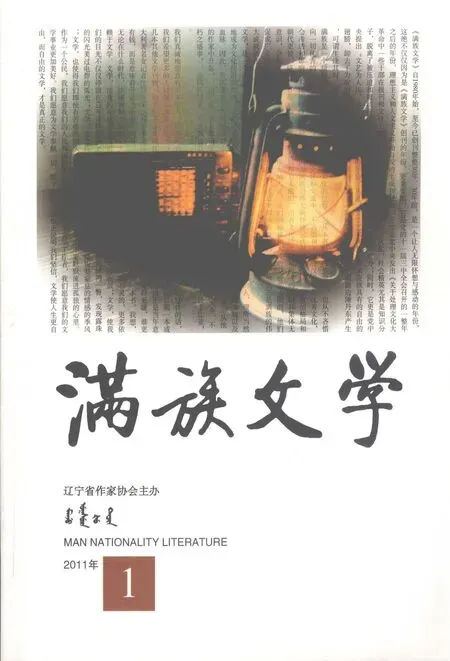和鼠曲草一起飞
2011-11-21石岸
石岸
和鼠曲草一起飞
石岸
那天黄昏时,他们在泗水河边散步。空气是那样的清新。若是平时,乔茹总是一副小鸟依人的模样挽着他的胳膊。但是今天,他们只是在一起走着,俩人保持着一米多远的距离。这种距离算不上多么遥远,但极易模糊他们之间的关系。其实,那会儿他打电话给她,她就有些迟疑了。她“嗯”了一声。在这个字眼的后面,出现了也许只有一两秒钟的停顿。他仅仅只是隐隐地有了某种感觉,他几乎都没来得及把这种感觉说出来,乔茹就已经答应了他。乔茹说,你在那儿等着我,别走啊。最后的卷舌音,儿化。让人有着缠绵不尽的联想。
刚见面时,乔茹一如既往地给他一个灿烂的微笑。这样的微笑,总会让他平静的心脏突然加快跳动。今天她穿的是件浅蓝色牛仔套装,显得简洁而又有几分洒脱。他们拉了拉手,然后又拥抱了一下。因为是在大街上,这种亲昵,当然更带有象征性的意味。当走进空旷的河滩时,他们反而不同寻常地拉开了一定的距离。在这期间,他曾主动地挽住了对方的胳膊。作为男人,这样做多少有些不伦不类。好在乔茹没有任何反感。
前些日子,他和乔茹约好到公园里去打羽毛球。他是一个不太喜欢球类运动的男人。乔茹整天忙于生计,极少运动,人免不了要发胖。她打羽毛球当然主要是为了减肥。一时间他对这项运动也产生了一种奇妙的亲切感。他老早就跃跃欲试地说要和她打一场球了。他还用很煽情的语言去说这件事,乔茹果然反应热烈。这一次他很正经地把这件事提出来,乔茹说,行啊,那咱们明天早上六点半准时见面。
为了这次打球,他翻箱倒柜,把他多年前穿过的一套蓝色运动服又给找了出来。穿在身上虽说有些皱皱巴巴,显得很别扭,但他还是以一身这样的行头出了门。他准时来到了公园里。那时虽说有些薄雾,但他还是一眼就把乔茹给认出来了。和她搭档的是一个很高大的中年男人。应该说,乔茹的球技不错。平时在他看来略显臃肿的乔茹,此时却是身轻如燕。相反,那个中年男人的动作却有些生硬,一看就知道是一个很少运动的人。他有些迟疑,他只是在相距十几米远的地方观看着。他相信这样的距离乔茹会看到他,会向他招手,然后他很从容地走过去。他甚至想到,因为他的到来,那个男人会很知趣地退场。乔茹太投入了。她不时地纵身跃起,挥动球拍的动作干脆利落,并发出一声声快乐的喊叫。他立刻被她的喊叫所感染,心里莫名地生出一种自豪感。但乔茹并没有看见他。他沿着栅栏向南绕过去,这样他就直接面对着她了。果然,乔茹在捡球时发现了他。他看到乔茹脸色绯红,脑门上的汗珠亮闪闪的。她十分开心地笑着,并举起球拍向他示意。她好像还向他说了一些什么,因为相距较远,他没有听清。他本来是想紧绷着面孔的,但还是勉强地笑了笑。他突然感到自已的内心十分的酸涩。
说起来,他们走到一起已经将近一个月了。二十多天前,他们在“牵手缘”超市门前偶然相遇。俩人当时都是格外的惊喜。只见乔茹拨开人群,快步向他走来。她披散的长发都在空中飘了起来。他当时也是激动得两手直搓。别人可能是日久生情,可是他们却在极短的时间里擦出火花了。十多年前,他们曾经恋爱过。但是那场恋爱却是无果而终。十多年后的今天,他们人到中年,而那场无果而终的爱情,相信只要有合适的土壤,就会重新发芽。那天晚上,他们只能用身体来补偿过去的缺憾了。现在,他自已也觉得很奇怪。这二十多天里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他都能够记得清清楚楚。看来突然降临的爱情,已经使他完全的改变。他早就觉察到他身体上的每一个器官,好像都被一种神奇的东西给激活了。要知道,他过去可不是这样的。不能说他整天浑浑噩噩,但是说他对周围的人和事变得麻木和淡漠,却是一点也不为过。有一天,他对乔茹说,咱们自相遇到今天,已经整整二十天了。乔茹很惊讶:哦,是吗?你怎么记得这样清楚?他睃她一眼:你真没记性!咱们相遇那天是十一月二十二号,到了今天不正好是二十天吗?乔茹更惊讶了,语气中都充满了钦佩:李晔,我真的没有想到呢,你的记忆力这么好呀!
他注意到了,乔茹这些日子以来应该说是第一次对他直呼其名。他并不感到突兀。这说明对方的心更向他靠近了。这微小的变化使他喜不自禁。他当然不在乎对方对他如何称呼。他记得乔茹过去都是这样和他说话的。哎,把拖把递过来好吗?或者说,哎,帮我剥一棵葱吧。要不就是,哎,快去把洗衣机里的水放掉吧。他那时一点也不反感乔茹把他叫成“哎”。他乐意在她的呼唤声中帮她做事。他其实做得并不好,有些笨手笨脚。比如拖地。他就有些不得要领。本来还算干净的地板,反而被他弄成了纵横交错的地图。乔茹并不责怪他,而是用手掩着嘴唇儿笑。最后,她接过拖把,说,还是我来吧。
那时候,他还沉缅在那一声声“哎”之中。他后来想,这可能是她还不习惯叫他的名字,这里头也许就隐含着一种羞涩或敬重吧。在这些日子里,他们每天都保持着电话联系,都要相互问候一声。虽然同居一城,但并不是每时每刻都能待在一起的。情人之间,其实并没有多少话要说的。该做的事做了,该说的话也说了。爱是什么?爱有时就是那种重复多遍的一声问候呢。有一天早上,他突发奇想地在电话里对乔茹说,喂,乔茹,你好吗?你知道你现在在我心目中是什么吗?我告诉你吧。咱们现在已经超越了一般情人的关系。你现在就是我的妻子。我绝对是拿你当作妻子看待的。请你相信我。对,我现在就是你的丈夫了。后来见面时,他们就老婆老公地相互叫了起来。这样的话好像是脱口而出,有一种水到渠成的意思。他原先以为乔茹会有些不好意思的,会像小姑娘那样脸色绯红,或者害羞似的扭过身子。没想到,那“老公”两个字,会大大方方地从她的嘴里蹦出来。她说,哎,老公啊,快过来瞧瞧我烧的牛肉吧,尝尝味道怎么样呢。这时候,他的眼睛里流光溢彩,恰似一江春水,觉得当年放弃她,实在是一个不可原谅的错误。
星期六早上七点多钟,乔茹突然打来电话。她说,李晔,咱们今天请许梅吃饭吧。许梅?他迟疑了一下,脑子一时似乎没有反应过来,或者许梅这个名字在他脑子里根本就没存在过。怎么,我的好朋友你都忘了?电话里传来了乔茹粗重的喘息声。
说起来,他和许梅已经有了两次接触。那是他和乔茹刚相遇不久。那天乔茹在家里给她儿子过十六岁生日。她儿子初中毕业后,学了一门理发手艺。平时吃住都在店里,极少回家。乔茹是一个聪明的女人,她可能是想借此机会,让她的儿子默认自已和他的关系。除了他,许梅也被她邀请来了。在此之前,她当然要把她的好朋友许梅的情况跟他介绍。在乔茹的描述中,许梅是一个比她还要漂亮的少妇。他说,嗬!她能比你还要漂亮?乔茹说,谁骗你呀!那就把她也喊来吧,让你们见见面。那天许梅和他一样,手里也拎着一个大蛋糕。她进门时风风火火的。也不打招呼,“咣当”一下,就把门给撞开了。不用说,许梅给他第一印象就很糟。他觉得乔茹对许梅的评价太夸大其词了。在他看来,许梅并没多少出色之处。和乔茹相比,许梅只是在身材上略占优势。其实,她们是两个完全不同类型的女人。乔茹高大、结实,许梅则显得纤弱、瘦小。他喜欢高大丰满的女性。他倾向于乔茹是不言而喻的。
那天以许梅大醉而收场。为此事,他还抱怨过乔茹呢。
过了几天,许梅让乔茹给他捎话,说要请他吃饭。他当时在鼻子里就哼了哼。他面带愠怒地说,这种女人,我不想再见到她了!乔茹笑笑,和颜悦色地望着他。怎么,大美女你都不想见了?其实,乔茹对他“苦口婆心”时间并不长,他就不再坚持了。他想,不看僧面看佛面,既是乔茹的朋友,他怎么能不给人家面子呢?
那天许梅还带了一个男人来。姓王,叫王一亮。是某房地产公司的总经理。乔茹看来和这个姓王的很熟,她拍拍王一亮的肩对他说,李晔,你别看王经理人长的不怎样的,他可是咱青城第一款爷呢。他觉得此人很面熟。乔茹立刻说,对啦,你们见过面的。然后她俯身对他耳语:上次我和他打球,你还吃醋呢。王一亮挺着很有风度的啤酒肚,走过来主动和他握手。他的手很有力。李老兄,幸会,幸会啊。上卫生间时,王一亮很坦然地对他说,我和许梅的关系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倒是你和乔茹今后还会有戏呢。他很吃惊。他没想到王一亮会谈及这样敏感的话题,一时觉得很窘。他支吾着说,我也不知道今后会怎么发展呢。
他决定回请许梅。他想,秤砣打大锣,就这一次吧。
他从家里带了两瓶“双沟青瓷”。四个人能把两瓶酒喝完绝对是可以了。今天是他做东,他以为他能够左右局面,见好就收的。可是一开始他就有些被动了,而许梅和王一亮却喝得很轻松。是那种绵里藏针的轻松。他记得上次许梅请客,他们并没有用碗端,而是用那种很常见的小酒杯。大家都是彬彬有礼的,都是你谦我让的。许梅和王一亮今天的配合,是相当的默契。他们一上来就端起了碗,说这样喝酒爽快。那种兵临城下、咄咄逼人的态势再明显不过了。而他和乔茹呢?一上来就有些怯了,就有些不知所措了,这从他俩慌乱的眼神中可以看得出来。王一亮到底是见过世面的。他轻咳一声说,你们要是不行呢,那就不要勉强了,大家随意喝吧。王一亮这种柔中有刚的话,让他和乔茹更加吃不住了。这样一来,人家是反客为主,你怎么好意思“随意”呢?他睃了乔茹一眼。这一眼暗含着商讨对策和“救驾”的意思,而乔茹此时只是矜持地微笑着。她的眼眸亮亮的,水汪汪的。后来,她的目光开始闪烁起来。一会儿落在他身上,一会儿又落在王一亮身上。就像一只小鸟在两个枝头上跳来跳去的。他还在无意中发现王一亮和乔茹悄悄交换了一下眼神。
王一亮先把碗端起来,高过额头,然后再缓缓地往下降(有点儿像演戏),接着贴住自已的嘴唇,只是稍稍倾斜,也没听见什么响声,那酒就下去了一大半。他抬起头来,目光富有深意地盯着他。他当然明白对方的潜台词:怎么样?下面就看你的了。他稳了稳神,心想,不就是喝酒吗?想当初咱号称“李八两”呢。他倏地站了起来,甩了一下肩,把羽绒服脱了,搭在身后的椅背上。他还用力地拍了拍椅背,明显是应战的意思。他端起酒碗,一扬脖子,碗到酒尽。当地叫做“一口闷”。然后他把碗倾斜过来面对众人,有一种广而告之的意思。王一亮似乎不吃他这一套,只是很有城府地点点头,送给他一个赞许的眼神,随后也把碗里剩下的酒给干了。许梅起哄似的叫了一声好,然后也是一饮而尽。一直含笑不语的乔茹,此时终于沉不住气了。我的乖乖,你们都玩命了,我也不能装孬呀!说着她也是碗到酒尽。王一亮对乔茹竖起姆指:对,就这样好,咱要向女侠们学习!四个人开始你来我往,很快,两瓶酒就见了底。如果这时候结束,他也不会醉到哪去的。但是,许梅和王一亮都没有要结束的意思。王一亮还假惺惺地对他说,李兄,我看就到此为止了吧。他明白对方的弦外之音。他用餐巾纸擦了一下手,很用力地抛了出去,叫道:服务员,上酒!
醉是不可避免的。
他记得在大街上他和他们分手了。他开始感到自已两腿发软,走路发飘。他极力稳住自已。他和他们分别时,他的头脑是清醒的。王一亮提议他到乔茹家坐坐,听听歌,喝喝茶什么的。他摇头拒绝了。这时候他看到乔茹走路也是摇摇晃晃的。王一亮见他不同意,马上说,我到东苑小区打牌去。他看到他们三个人同时钻进了一辆出租车。然而,他只是走到了步行街广场上,他的手机就响了。乔茹在电话里说,你快来吧。他们都在我家坐呢。他可怜巴巴地说,我快要不行了,想吐酒……我要回家睡觉。乔茹说,哎呀,有那么严重吗?是王经理再三要我喊你来的。他说咱们四家正好打牌呢。
于是,他掉转头向乔茹家走去。
乔茹家在东苑小区,某幢五楼。他在楼下门洞里看到许梅站在那儿,就问她,你在等谁?许梅用下巴向上示意说,他们都在楼上呢,你先上去吧。他跌跌撞撞地走到了五楼,他看到乔茹的家门大开着,就径直走了进去。客厅里的灯开着,但没人。茶几上摆着两只玻璃茶杯,茶杯旁还有剥下的桔子皮。他摇晃着走进乔茹的卧室,看到乔茹头发纷乱地倚靠在床上。她穿着一件红色毛衣,脸色也是通红的。乔茹看到他进来,突然格格地笑起来。他觉得乔茹今晚上的笑,一点也不灿烂。哎,亲爱的……你……快上来吧。说着还对他招了招手。他摇晃了一下身子,又站住了。那床好像突然有了吸力,或者是一阵风在吹拂着他,他已经很难稳住自已了。他的右手按在了乔茹的肩膀上,左手则在空中划来划去。乔茹说,你这是干什么?他说,这是飞机在飞哩……接着,他感觉到整个人都像一架飞机了,或者更像是一枚树叶了,他眼睁睁地看着自已飘落在了床上。他咕哝了一声:我是在飞吗?
以后发生的事情,他什么也不知道了。
天亮了,他和乔茹几乎是同时醒来的。他是被渴醒的,他做梦都在找水喝。他在梦中看到自已行走在一片沼泽中。大片的青苔覆盖着水面,使他无从下手。醒来时他发现自已和乔茹是相拥着的。乔茹的脑袋枕在他的胳膊上,她的身体蜷曲着,依偎在他的胸前,就像一只受惊吓的小鸟。她对他莞尔一笑,又更紧地把自已的胸贴过去,并同时伸出手臂把对方箍住。他舔了一下自已干燥的嘴唇说,水……
也许是室内过份的安静首先让他意识到了什么,或者根本就是他无意中往外一瞥,使他看到了卧室的门是敞开着的。门怎么没有关上?乔茹说,这怎么可能啊?我昨晚明明看见是你把门关上的。是的,他想,他隐约记得是自已进来之后把门关上的。直到这时,他们才意识到问题严重了。他第一个走到客厅里,一眼就看见通往楼梯的防盗门也是敞开的。乔茹衣裳都没来得及穿,匆匆来到客厅里。她好像突然醒悟似的,直奔他儿子的卧室。她果然发现了新的情况。她说她儿子不在家睡觉时,都是她把被子叠得整整齐齐的。现在被子却凌乱地堆放在床上,说明他儿子昨天夜里已经回来过了。他们几乎同时想到,这孩子显然已经目睹了他和乔茹同床同枕的情景。他们继而又想到了另外的情景,许梅和王一亮说不定也目睹了这样的场面。
乔茹顿时面无血色,声音都变了。这下完了!
他们在泗水河岸边已经走了很久。夜色早已笼罩了大地。有一艘机帆船从水面上突突地驶过。他们嗅到了空气中淡淡的柴油味。泗水东岸是一片最近几年开发的新城区。色彩斑斓的霓虹灯倒映在水面上,更使得夜色缤纷迷人。这些日子以来,他的心情渐渐地好了起来。那件事并没有给他带来多大的影响。他有什么好担心的呢?许梅和王一亮都不在他的社交圈之内。但是乔茹就不是这样的了。她整天心事重重,担心事态会进一步扩大,甚至到最后变得不可收拾。乔茹的儿子已经好几天没有回家了。许梅和王一亮自此再也没有露面。事情越来越得到了“证实”。乔茹似乎也越来越没有自已的主见了。她不时问他:李晔,你说咱们应该怎么办呢?除了叹气,他只能用沉默来回答她。
涌动的波浪使霓虹灯的倒影在水面上变得支离破碎了。好像冥冥之中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在撕扯着那片倒影。他们默默地离开河岸往回走。到了路灯下,他们都站住了。乔茹用复杂的眼神望着他,他知道对方还要向他说些什么。乔茹终于这样说道:李晔,我不想做你的情人了。我要嫁给你!你愿意吗?他神情定定地望着她,然后非常庄重地点了点头,他非常冲动地抱住了她。只听乔茹柔声地对他说,到我家去吧……
他们相隔着一定的距离,像做贼似的,一前一后上了楼。乔茹拧亮了紧挨着床头的壁灯。灯光是粉红色的,此时乔茹的情绪不错。她的目光晶莹闪亮,透出一丝脉脉温情。他们无言相对了许久。乔茹突然风情万种地说,李晔,你把我的衣裳脱掉吧。他惊住了,好像不认识似地看着她。他的嘴巴张得很大,这样的口形好像已被定格了。快呀,你愣什么呀!乔茹催促他。乔茹还很矫情地把身体扭动了一下。在过去的做爱中,乔茹总是自已动手的。此时,他愣愣地看着她,然后又是突然醒悟似地动作起来。他手忙脚乱的,就像做着一件完全生疏的、不得要领的事情。他浑身哆嗦着,当他看到最后那件蛋青色带有蕾丝镶边的乳罩时,他的手指就突然地僵住了。乔茹扭过身子,催促他:快把我身后的扣子解开呀!他好像没有听到她的话,整个人像似一只泥俑。就是他自已也没有弄清楚,他体内那股刚刚升起的激情,为什么突然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乔茹裸露着上身,一动不动地坐在床上。她好像已经明白了什么。她的目光凝固了。
这一夜,他们什么事也没有做。他只是紧紧地拥着乔茹。乔茹的身体水一样的冰凉。后半夜,他被乔茹猛烈的咳嗽声给惊醒了。他欠起身子问,你是不是生病了?咱们去医院吧。乔茹摇摇头:没事的,这是我从小就落下的病根。可能是昨晚在河边散步时着凉了。他听了这话非常感动。他没有想到乔茹这么善解人意,分明是那会儿他替她脱衣裳造成的,她却避而不说。他再次拥紧了她。他说,我现在就到医院去给你抓药!乔茹在他的肩上按了按说,我这病吃任何药都没用,过些天自然就会好的。她接着告诉他:小时候她母亲从野地里挖回来一些野草给她熬汤喝,就居然把她的病给治好了。那是什么草药?他问。乔茹想了一下说,可能叫清明菜吧。清明菜?他自语着。他极力在脑海中搜寻着这种植物的形状,可是他一片模糊。他想起少年时自已也在农村生活过的,他差不多认识各类植物。比如灯笼草、荠荠菜、菖薄……可是他对清明菜为什么一点印象都没有呢?
他暗暗发誓:我一定要找到它!
这一年年底,乔茹去了南方。
有一天,许梅突然神情激动地打来电话告诉他,说乔茹和王一亮私奔了!她说她有绝对的证据,乔茹就在王一亮的公司里当售楼部副总监。许梅补充说,王一亮最近在南方某城市开发中购得一宗土地,已经在那里投资兴建一座大型公寓。他半晌无语。他曾经有过这样的预感,但他坚信乔茹是不会背叛他的。“李晔,我不想做你的情人,我要嫁给你……”这样的话似乎言犹在耳。许梅说,李哥,我早看出来了,你是个书呆子。现在的人,怎么能像你这样单纯呢?许梅又说,李哥,你怎么不说话啦?他们私奔了,咱们该怎么办呀?他从懵懂中醒悟过来,他似乎听出来了对方的弦外之音。他笑了笑,什么也没说,只是默默地关了手机。
一天晚上,他接到许梅发来的短信。他打开手机屏,上面写着:“天气变得好快,暖风渐渐吹来,因为你的可爱,所以给你关怀,没事啃啃骨头,那样可以补钙,不要再说我坏,祝你今夜愉快”。自他获知那个惊人的消息后,许梅总是不断地给他打电话。他有些烦不胜烦。他已经多次警告过她了,她也表示今后“再不会自作多情”。可是过了没几天,许梅又不断地给他发来短信。类似上面的这样短信,他已经收到十几条了。鬼知道许梅是从哪里捣腾来的?他接到许梅的短信从不回复,而且立即删除。每次删除后,他都要冷笑一下。
清明节那天,他和朋友们到城外郊游。他好久没有这样心情舒畅地到外面走走了。刚刚下过雨,地面上湿湿的,空气中飘浮着一缕野草的清香。他下意识地东张西望着,好像在寻找着什么。突然,他奔跑起来。众人愕然。后来有人回忆那一幕说,他奔跑的身影非常轻盈,就像一只飞行的鸟。他在一条小河前停下来,河滩上搁浅着一条破损的小船。远处,有一群鸽子在水边觅食。他出神地看着那株植物,并围绕着它转了两圈。好像这种相遇,就是冥冥中注定的事情。那植物开着灿烂的黄花,条形的叶片互生着,并且紧紧地缠绕在一起。四周是灰黄色的泥土,而它们花团锦簇,因此它们在阳光下是那样的醒目。一个朋友告诉他,这种植物叫清明菜,学名叫鼠曲草……他心中蓦然一惊,突然就想起了乔茹。有人看到他眼睛里已是泪光闪闪。他缓缓地蹲下来,小心翼翼地把它连根拨起,然后用纸包裹,装入衣兜中。到了家里,他一遍又一遍地把它清洗着,然后放在阳台上晾晒。
有一天,他妻子问他,你在阳台上晒的是什么?他转过身来望着妻子,他的眼神很陌生。这些年来,他们一直分居着,俩人几乎无话可说。他本来是不想搭理她的,但又觉得不妥,于是他敷衍她说,是野生绞股蓝,能减肥的。又有一天,他妻子对他说,外面起风了。你还不赶快把阳台上的绞股蓝收进来?他急忙奔向阳台。可是他晚了一步。那根早已干透的鼠曲草,已经被风旋起,在空中慢悠悠地旋转着。一圈,又一圈……它离阳台时远时近,有时只有一米多远。他极力伸出手臂去抓,可是只差那么一点点。那鼠曲草在空中飘荡着,好像故意在撩拨着他,引诱着他。他再次掂起脚尖,伸手去抓。那鼠曲草又慢悠悠地飘回来了。他把早已悬空的身体再次向阳台外伸去……他恍然看到自已的手指尖终于触及到那株鼠曲草了,同时,他感到自已在空中飞了起来。
〔责任编辑 宋长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