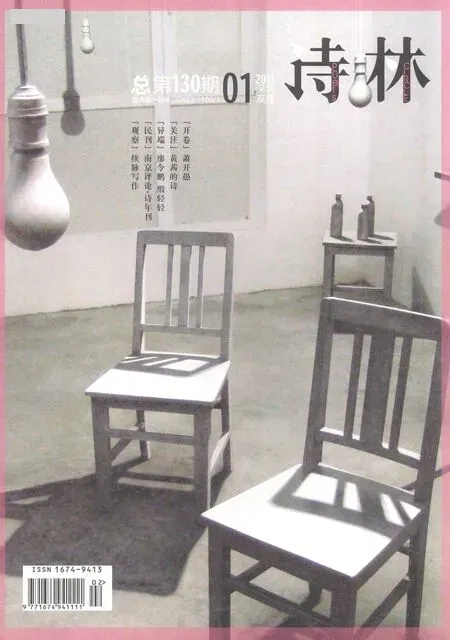穿过植物茎管催动诗歌的力
2011-11-21刘化童
刘化童
菁 菁
穿过植物茎管催动诗歌的力
刘化童
写作是为了再现我们所生活的世界,这种老生常谈的论调似乎从未过时,进一步的要求则鞭策着写作者从现实世界里遴选出一些闪光的碎片,用来重新拼装出一个更为真实的世界。何谓写作?不妨来看罗兰·巴特的见解,某一时代一切作家共同遵从的一套语言结构犹如“自然”一般,贯穿于作家的言语表达之中,写作者游荡在语言的丛林里捕猎到自己的言语,在词语的物种里搜寻到自己的语词。这个言语与语词的古老任务向每一个好的猎手发起挑战,他必须找到那个最为闪光的猎物,并且成功捕获到它,以此奠定自己的英雄地位。现代主义诗歌史上,那些语词能手们纷纷斩获了自己的诗歌图腾——里尔克的豹、布莱克的老虎、波德莱尔的天鹅、爱伦坡的乌鸦、史蒂文斯的乌鸫等等。就如同原始社会的图腾多以凶猛的动物担任而极少采用植物,将征服语言的疆域视为己任的诗人更像是荒野上奔波的猎人,努力追逐着难以驯服的野兽,真正隐居在植物园里与草木打交道的并不多,严格来说,似乎只有特拉克尔与他的接骨木。
维特根斯坦声称,“我的语言的边界就是我的世界的边界”。谁的语词的核心就是他的言语的核心,继而标识出他的世界的核心。原始图腾往往承载着使用者自我标识的核心价值,通过标记性(相同血缘的采用相同图腾)与象征性(认同野兽的某种属性来象征自我拥有与之相关的某种品德)将它像语言一般传播而出。诗歌图腾也颇为相似——你选择相同的图腾,即是延续着某些诗人的精神血脉;反之,则说明在精神向度上的差异性。当某个图腾作为诗人的核心意象频繁出现时,也就表明你与它具有隐秘的关联,分享着隐喻意义上的文化气质。换言之,诗眼是认知全诗的密匙,对于诗歌图腾了如指掌就能够认清相关诗人那张模糊的脸。
简单而言,西方文化是肉食性的,中国文化具有食草特征。西方诗人喜欢留恋于动物庄园里认领他们的关键词,中国诗人则更倾向于在植物园里完成自我的形象塑造,将诗意嫁接在植物之上。同样的道理还在唐代诗坛上得到印证,具有豪放旨趣的边塞诗人大多选取牛羊或战马作为意象,田园诗人则采撷植物意象来满足隐逸的诗趣。总体来说,较之动物,植物更符合中国传统诗教里的温柔敦厚。在这个历时久远的农业帝国里,诗歌文本被用来当做普及农业的启蒙读物,孔子在细数读《诗》的好处时,就将“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列入其中。虽有评论家指出,1989年天才诗人海子卧轨自杀宣告了农业抒情时代的终结,但是,即便到了本世纪依然不乏诗歌必须重视自然的呼声。十八年之后,它再度枯木逢春,在芒克、宋琳等诗人起草的《天问诗歌公约》里,最末一条就提出“诗人是自然之子。一个诗人必须认识二十四种以上的植物。我们反对转基因”。至少在他们看来,所知植物种类的多寡直接影响着一个汉语诗人合格与否。潜台词则在暗示,植物是汉语诗歌的图腾,并且它从古至今从未中断。
茱萸,这个以植物为名的汉语诗人,注定了要人如其名地成为用植物之名来重组世界的园艺师。用他的一首诗名来说,他的诗篇就是“卉木志”。或者,用他自己的诗来说,他写诗的历程及其归宿无非是:
盛夏盘踞在途中,终结了花粉的暮年,
余下的葳蕤,却教人袭用草木柔弱的名字
以驱赶初踏陌生之地的隐秘惊惶。
——《分湖午梦:叶小鸾》
植物位居食物链的低端部分,其上还有食草类动物、食肉类动物以及两者兼而有之的人类,在弱肉强食的生物界,它非但没有濒临绝迹反而郁郁葱葱,凭借的正是它优良的生长性。当隐秘的惊惶环伺四周时,那些袭用了草木性质的人类同样柔弱,却也依靠生长性繁衍着后代。在历史的艰难行进中,人类从植物上看到了示范作用,它犹如节拍器与指南针,“有些生动的植物以及/值得道说的枯燥细节仍在左右着我们的步子”(《风雪与远游》)。至于诗歌,那更是如此,它的柔弱看似难以抵挡任何强权,正如谢默斯·希尼的名言——“从来没有一首诗歌阻止过一辆坦克”。但是,也从来没有一辆坦克能够扼杀所有的诗歌,它植根于语言的土壤自然而生。植物与诗歌,这对亲缘关系共享着柔弱性与生长性,而在后者这对彼此内耗的关系中,人们获得了本体论意义上的抚慰。热爱植物学的诗人米沃什,曾经声言,“我觉得自己如果在社会学中受到了伤害,那么可能从生物学中得到安慰。”
这种安慰并不应对于所有的状况,米沃什似乎忽略了天文与地理的作用。首先是气候,“不生长植物的季节,是干枯的”(《风雪与远游》),或者“南方的三月细腻到了极点,她随时可以/制造新的腐烂,天气的变化更令人无从谈起”(《池上饮》),过涝过旱的天气都在抑制植物的生命。其次是土壤,它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一如当年种入土壤的先人骨殖。它们是否完好已然不重要了,/劫后余生的枝蔓,终于长成”(《白蔓郎》)。然而并非所有土壤都利于植物长成,倘若没有提供作物养分的腐殖质(如氮、磷、钾、硫、钙等元素),或者土地本身不适合种植(如盐碱地等),植物自然难以生长。恶劣的气候与土壤共谋般地营造了荒原,它宣告着生长性的缺席状态——绝非没有生长性,这是植物的本质,而是生长性被判定为不可能。在此意义上,艾略特也是一位植物诗人。略有不同的是,在他那长着丁香的四月残忍的荒地上,不再有意义产生。他以植物的空集来表明植物的集合,仿佛没有花语的花朵,进而暗示着意义才是生长性的核心问题。
在环保人士眼中,植物的意义就在于光合作用,它利用太阳光能将所吸收的二氧化碳和水合成有机物,转换为氧气再将之释放。意义生成于二氧化碳与氧气的对话之中,而植物提供了交换性的场所。语言本身恰如绿色植物,在语言的介质中,对话使得编码与解码交替重叠出现,能指与所指完成着相互的转换,由此释放出经过提炼与纯化而成的意义。“我们湿漉漉的对话,要保持恒温且鲜绿,/如刚刚过去的春昼般冗长,却并不乏味”(《池上饮》),诗歌是终极意义上的语言对话,诗人们向来把语言视为诗歌的本体,而把诗歌视为开拓语言边界的驱动力,仿佛语言的神秘就来源于“穿过绿色茎管催动花朵的力”(狄兰·托马斯语)。
推动诗歌的神秘力量,时而来源于缪斯女神的眷顾,时而是现代语言学的基本观念——不是我在说话,而是话在说我。古罗马著名的“哲人王”马可·奥勒留曾说,植物中叶子的本性由于有知觉或理性而成为阻碍我们本性的一部分。它同样适用于语言,由于它自身的知觉(能指与所指的任意性)和理性(约定俗成的话语习惯或语法规范),阻碍着言说的绝对自由与掌控语言的绝对权威。诗歌,或者更大意义上的语言,并非总如写作者预期的那样,它总是自然生长,甚至从写下某个诗句的那一刻起,它就挣脱了写作者的意志。
汉语内部的知觉与理性经历了多重劫难(白话文运动、简体字运动)后,出现了语言学的地质层断裂,古代汉语(文言文)与现代汉语(白话文)犹如耸峙的峡谷两岸,难以实现两者在表达规范与意义上的交换性。茱萸的写作旨在制造出“两种汉语表达形态的诗歌翻译器”(参见拙文《“在南方”诗歌群像》),或者说,演绎出两株不同植物如何有效嫁接的园艺技术。但是,它们自身的知觉与理性阻碍着茱萸企图续接传统与现代这两重诗意的雄心。甚至,在不少人眼中——其中不乏相当数量的专业读者——茱萸的诗歌被语言自身的分裂之力撕扯着,既非文言,也非白话,在语言结构上颇为古怪,在语感上略显拗口。总之,就是读来太过佶屈聱牙,而这足以摧毁观赏者的耐心。
该承认的是,我向来缺乏言说的耐心。
我不清楚每一株植物、每个细节的名字,
却偏要用形容词堆积出大量的烟幕。
——《池上饮》
就如同观察一株长时间里毫无动静的植物一样,不论是言说,还是倾听,耐心总是至关重要的。观赏植物、谛听诗句,必须首先要具备如诗如植物一般的耐心,就如巴列霍所说——“我的耐性是木质的,又聋又像植物”。作为静态的艺术,唯有耐心才能够探取到植物与诗歌观赏价值,亦即它在预期中将要呈现出来的美学效果。平心静气地在细微变化处发现诗意,这种向耐心发起挑战的难度不亚于一口气阅读完《追忆似水年华》之类的煌煌巨著。不必苛求读者,哪怕是写作者本人要完成它,也需要相当的毅力。然而,现代文学史中并不缺以观察入微著称的作家。父母均为植物学家的卡尔维诺即是此中的好手,他的《帕洛马尔》是用小说写就的现象学著作,堪称如何观察世界的宝典。美国作家厄普代克在评价他时说,“他对嵌埋在动物、植物、历史和宇宙脉络中的人性真理最感好奇;他的一切探究全都围绕着‘我们将如何生活’的核心问题在打转”。
茱萸的问题不在于此,这位声称“向来缺乏言说的耐心”的年轻诗人,并不对植物本身缺乏耐心。那么,他所谓的“不清楚每一株植物、每个细节的名字”只能出于一个原因——他对植物分类学缺乏必要的耐心。从中,也不难窥测出立志成为植物诗人的茱萸,所感兴趣的只是作为全集的那个统称,而没有分门别类地筛选出某种特别钟情的植物,并将它纳为自己的核心意象与诗歌图腾。在他的组诗《群芳谱》里,混杂栖息着香菖兰、石榴花、白玉兰、樱花等多种花卉,就如宋儒周敦颐所谓“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繁”,他却不曾有“余独爱”之物。在茱萸的诗歌里,植物总是混杂而居,没有主角与配角的分别,各种花卉也没有明确的指称对象与象征含义,隐约透露出《离骚》里“香草美人”对他的影响,却没有革命年代里“恶草毒花”对他的毒副作用。没有独爱,与其说是博爱,毋宁说是对于分类的重要性的疏忽。唯有善于分类,才能善于挑选,继而能够作为标记用以自我定位。
然而,茱萸不这么认为。无论是李时珍《本草纲目》把植物分为草部、谷部、菜部、果部、本部五部,抑或植物分类学专家林奈创立的“双名命名法”对植物进行统一命名与分类,这些似乎都与茱萸无关。甚至,在极端的意义上,作为一个诗人的自我定位、以此证明的诗歌图腾也无法令他提起兴趣。他声称:
这是场盛大的悲剧,我注定要退居幕后。
相对于韶光里湮没不闻的秘密而言,
“白蔓郎”,作为某种植物的别称,
只是多此一举的命名和安慰。
——《白蔓郎》
在语言的盛大悲剧里——我被言说,而非我是言说者——他自认为要宿命般地退居到语言帷幕之后。在此过程中,植物作为这个世界中人与事的别称(隐喻或者象征)才被提出。纵然这是多此一举的,但也无妨,茱萸似乎在表明着诗人的自我定位还有另一条途径,即便不靠核心意象、诗歌图腾或者出类拔萃而流传广泛的标志性诗句,诗人也可以获得安慰。毕竟,诗人就是在“上帝死了”之后,担负起用语词来为世界命名这一职责的人,而他从现实世界采撷到一些植物,用来重新拼装出一个他的世界。以植物为己命名,以植物为世界命名,茱萸能为诗歌阅读者所知恰恰就是因为这广泛而博爱的植物命名权,他由此习得了穿过植物茎管催动诗歌的力。
菁 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