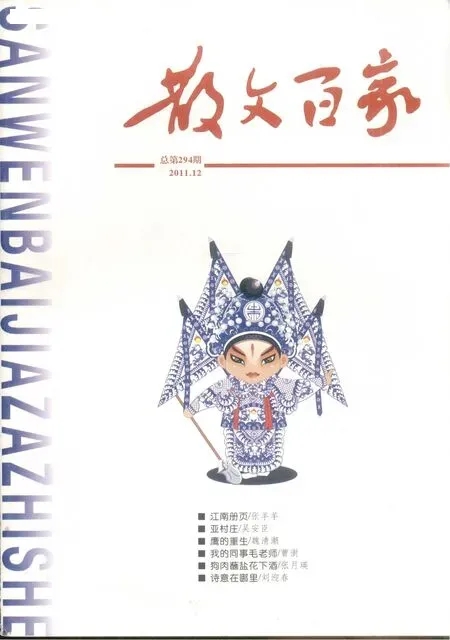花非花(外一篇)
2011-11-21杨宏玲
● 杨宏玲
又一个天女木兰花开的季节,面对山野间鲜活、柔美的生命,我无比欣喜,然后暗自许下一个心愿:岁月静好、心灵安宁。归来后我将它留在我的个性签名里,有友回:岁月几日静好?心灵何时平宁?我答:朴素的思想来自山野纯白的花朵,静默有时比奔跑更有力量。愿每朵花都纯净而缤纷。
多年以前,喜欢席慕容的诗,渴望在美好的青春年华,在开满栀子花的山口,有一个美丽而真纯的相遇。多年以后,无数个靠近花朵的瞬间,我已经忽略了曾经的梦,懂得了相遇并不容易。只是喜欢听,花开的声音。
花开的声音很动人,但只有用心才能听到,并且恰好那声音不被喧嚣所覆盖。更多的时候,世间纷攘,流年日深,喧嚣来自内心,在行走中发现,自己多么浮躁而孤单。
曾有那样的时刻,对人生剧目里自己的角色充满疑惑与厌倦,对身体莫名的疼痛更加深恶痛绝,因此怀念年少无知的岁月。那时虽然会为一朵花的枯萎而忧伤,但也会将蜻蜓拴住尾巴拎着在田野上奔跑。那时的忧郁很浅,快乐很多。
海拔千米以上的高原,夏天似乎总是比他处来得晚一些。那些翠绿的颜色——树的叶子,花的叶子,草的叶子,自谷底蔓延,然后爬满山坡,并以一种眺望与拥抱的姿态爬上高原。其间有一种力量,像女人望向爱人的目光,像母亲怀中沉睡的婴孩。这力量来自自然,来自高贵的花朵与卑微的草芥,来自悄然而至的日光,来自静谧的风,来自宁静的心灵。
伍尔夫说:每个女人都要有一间自己的房间。我认为除了房子,每个女人都应该懂得寻找自己的山野,那里有花草、牛羊,有奔跑的牧人,有小溪,有虫儿鸣唱。那里的蝴蝶是一种独特的语言,它与花朵交谈,与石头说悄悄话儿,与翠绿的蚂蚱共同停留在一片草叶上。这样的山野比房子开阔,也更自由,更容易接纳,也更容易让人遗忘。
读书也是一种让生活开阔的方式。在那些具有穿透力、并给人予提示和力量的句子中,可以找到被滋养和丰富的感觉。而有些书,你完全可以不读,就放在那儿,像一段珍贵的情感,不去碰触,拥有就足够了。而写作,也可以帮助我们安静下来,内心向隅,用以安慰自己或者警醒他人。相比于喧嚷的聚会,或者随着热烈的乐曲舞动,读书与写作自然显得清冷和素淡了些,但作为女人,浮华的东西早早晚晚都要散了去,而最终必将望向自己的内心,必须努力成为自己暗夜的灯盏。
很多人也许并不会想到,高原的木兰花开,绝非偶然,遇见也需要太多的机缘。它在适当的气温下、时节里开花,可能早些,也可能迟些,酝酿的时间很长,花期很短。你恰在这样的时节有这样的闲暇与心情,到山间来,然后与它们相遇。似是不期,实是相约太久。这真的是需要缘分的,就像一段人生际遇,你期待或者恐惧,它依然会来。也许欣喜地遇见,就像曾经约好了一起上路。进入静穆地对峙,或者选择在一张画片上永存,都是幸福的,如同置身清澈的境界。在俗常的生活中,女人常常看到自己慌乱或者形容枯槁的样子,或者镜中设计过的笑容和形象。而此刻,全然是另外的模样与心情。
杜拉斯在《物质生活》里记叙,卡堡,有风的黄昏。那个小孩在那个地方一动不动,那是一个两腿瘫痪的孩子。别的小孩都已经走了,只有那个孩子在那儿玩风筝。杜拉斯相信天黑之前肯定有人跑去把孩子带回,天空上飘扬的风筝指明他所在的地点,那是不会错的。其实,每个人的心里都应该有坚持的方向,如果不,不能行走的孩子如何回家,寻找孩子的妈妈又如何找到他。如果不,女人像花一样绽放的时刻多欣喜,零落成泥的时刻又该如何的自苦。脆弱永远是女人最致命的伤。奥地利诗人里尔克,因指尖被蔷薇花的刺扎伤得了破伤风,两个月后死去,为此,蔷薇花成为热爱里尔克诗歌的我心头的一根刺。它与席慕容笔下充满期待的栀子花多么不同。但是今日我释然了。人事纷扰,每一株草木、每一片花瓣来到世间,都有其深刻的寄寓,并不仅仅是与绿叶聚首。流光易老,有足够的力量抵御万千风尘的,唯有花朵。
花非花。这样的词汇似有着无尽的禅的意味,这让我一再想起史铁生,这个自称职业是生病、业余写一点东西的作家,一生都在与疾病抗争,用以支撑残破肉身的是强大的精神力量,它来自于深刻的体验与坚持不懈的写作。它让脆弱的生命延续,让破碎飘摇的生活变得缤纷而有味道。写作于他而言,实在是生命的需要。而我们,选择行走在这样的路上,必定也是因了某种需要,才一直向前。
我自静默向纷华,是一本书的名字,作者是英国的莎拉·梅特兰。她在书的结尾处写到:恐惧、冒险与美是并肩而行的。但有恐惧,便有美丽,别无其他。其余的,我希望,是静默。
背负翅膀的鸟儿
我常常梦见自己,在天空飞。
不知道为什么或是预示着什么。我并没有高远的理想,只想守着温暖的巢,如其他平凡的鸟雀一样,安稳地生活,存在,做一个平凡但幸福的小鸟。但这两年来我总是做这样的梦,梦见黝黑的林子。壁上的山崖以及怪异的楼群,都在我的俯视之下掠过,我看得见自己浅灰色的翅膀,巨大、沉重,压得我没有力量。
我是从飘着槐花香气的小城飞向城市深灰的天空的。其间的路程并不遥远,但我却觉得异常艰难。我曾经在那个小城亲眼目睹了许多个春天的来临,空旷洁净的沙滩成了我内心的眷恋。我企图超越记忆在心底留住些什么,但我不能。在最后停留的日子,我是徘徊的。不是留或走的权衡,我是没有能力顾及太多的。徘徊是因为我想记住那里的一草一木以及一些人。没有人知道我在风雨中的挣扎以及不可言说的寂寞。
梦里的那扇门是黑褐色的,条状的栏杆可以将天空或者风景分割成若干块。但那是破碎的,并不完整。如果心可以是平宁的,我便可以选择不离开。我一直希望有人能为我阻挡住什么,为我,路或者其他。一些夜晚我守着澄明的月光,在烁亮的灯影里坐到天明。忧郁是不存在的,心里却有着千万只蝼蚁在啃啮我的肠胃和肌肤。那种感觉是飘忽和隐忍的,如果我不说,他人永远不会明了。就像我飞翔的梦境。其实我飞翔的梦并不如我内心期待与描绘的那般让人向往。你可以想象吗?飞临的地方是万丈悬崖,我以为可以游刃有余地从此峰穿越彼峰,但那种切近的碰撞的危险与坠落的恐惧时时笼罩着我。我时刻在怀疑自己,这是最可怕的,我想我怎么就可以飞呢?梦里我便这样虚弱地一遍遍问自己,然后我看见我臂膀后巨大的翅膀垂在脊背上。飞翔的过程也是背负的过程,我的怀疑让我心神不宁。然后脚下突然蹬空,失重的感觉只是一瞬,醒来,午夜的黑像一块脏的布。我不能用它来擦拭什么,蒙蔽也不能。不能拒绝的还有回想。
我不知道我是怎样坠落的,我是一只背负翅膀的鸟儿。
于是我惧怕睡眠,没有睡眠的人是痛苦的,鸟儿也一样。就是那时开始我开始喜欢上听虫鸣的,青蝗、蝼蚁、蟋蟀……我能分辨出它们各自的声音与心情,沉溺其间,我将其视为我熟稔的邻居。它们搭筑大厦、玩乐或者开音乐会,窃窃地交谈。有时也争吵,僵持,然后和好。它们和好的速度是和我那一刻的心情相关的,如果有时还愉悦,它们在半秒内就卿卿我我,甜甜蜜蜜。如果不,它们便用巨大的沉默来抗争,对峙,直至让一切都变得没有耐心甚至绝望。我曾经在我展开的书页上看到两只疯狂奔走的红蚂蚁,它们先前似乎以为这黑色蝇头小字是其同类,发现错误时它们却被围困了,左奔右突,找不到一条可以突出重围的路,然后它们用半个晚上的时间挣扎,歇息,放弃,然后开始重新寻找。
更多的时候,虫的生命里只剩下简单的快乐,它们用鸣叫呼唤同伴,警醒自己,或用这短促急迫的歌声填满每一个在夜晚醒着的人的心灵。它们让我感到羞愧,因为我在世上生存的时日将长达几十个春秋,我拥有许多可以与虫儿抗衡的时光,当然还有比时光更值得关注与期待的东西。
我试图改变自己,或者内心可以更坦然一些。但城市是喧嚣和琐碎的,它没有更多的空间让我寄托。空洞的梦照常来袭,我还做不到摆脱,心境竟有些苍老了。听虫鸣的事变得依稀,孤独的种子在内心从未停止过成长,而所有的快乐与温情都是不确定的,在那些个以为很长的时光之中,红了樱桃,绿了芭蕉,我却依然是背负翅膀的鸟儿。
我知道我不可以做出选择,如同爱与被爱。岁末的时候,我依然在每个清寒的早晨醒来,满室的阳光。这是片刻最切近的温暖,仿佛昨日的好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