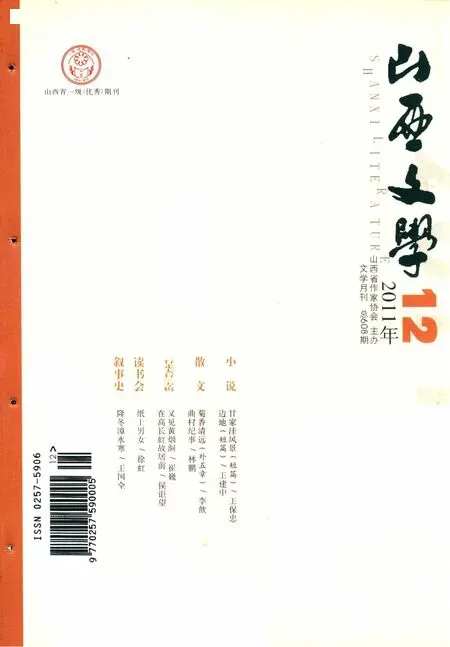始终站在乡村的这边——作家王保忠访谈
2011-11-21王保忠刘秀娟
王保忠 刘秀娟
刘秀娟(《文艺报》编辑、记者,以下简称刘):在一个雷声爆裂的雨天读完了《甘家洼风景》的最后一篇《香火》——我心里也炸开了一声惊雷。我相信,这也是甘家洼这块土地上空响彻的惊雷。磨粉的毁灭和村长老甘、葵爷对甘家洼香火永续的期望,形成了强烈的讽刺、悖谬和悲剧感,当然还有希望——可是希望寄托在了一个娶不上媳妇的哑巴身上,这种复杂的情绪是否寄予了你对乡村社会现状与未来的困惑、担忧以及看不到方向的微弱希望?
王保忠(以下简称王):《香火》是这部小说的收束篇,但画的不是句号,而是问号——我觉得我是在问自己,也是试图和读者讨论一个问题——甘家洼的“香火”能不能延续下去?这个追问还有一层意思,即乡村式微了,那种与乡土共生共长的善良、宽厚、仁爱、真诚等美德能否得以传承下去?你知道,一个传统村庄的形成至少需要二三百年的时间,这么久可以积累起多少东西,但现在,不少这样一些有历史感的“甘家洼”却逐渐萎缩、凋敝并空心化了。青壮年劳力涌入城市打工,还有一些青年人则通过考学迫不及待地离开了乡村,精华和希望走了,缺少了智力和文化支持的村庄焉能不枯败、不消失?《甘家洼风景》写的就是在现代化过程中正在式微的乡村风景,呈现的是农耕文明在当代社会生活中尴尬、落寞的处境。马克思曾经说过:“现代的历史是乡村城市化,而不像在古代那样,是城市乡村化。”虽然我知道城市化是乡村的未来走向,乡村的消逝也是必然的,但我心里还是很矛盾、很纠结,我不知道自己在这部小说里有没有写出变革过程中乡村社会的现状,以及人们内心无所依附的焦灼感。刚才你提到村长老甘、葵爷把甘家洼香火永续的期望寄托在一个哑巴身上,写完后我也觉得有点震惊,把这么大的事交待给一个哑巴,这靠得住吗?作为“失语者”的哑巴,他很难向别人表达自己的内心;作为同样弱势的这部分乡村,他也无法向公众表达自己的愿望,那么,我是在为他们代言吗?其实我能做到的也仅此而已,小说里的许多问题都不是我能解决的,我只能把这些困惑摆出来,和大家一起探讨。所以,就某种程度而言,这部小说就是写困惑的,甘家洼的困惑,我的困惑。
刘:这的确很让人无奈。我们的乡土文学作家,甚至所有的作家,在将近一个世纪里,都不得不面对一个乡土中国渐渐转向的事实,也力图表达在各种巨变或微澜中的乡村处境,直到今天,你这一代的作家又接了过来……我注意到,你用了“代言”这个词。这是中国乡土文学中意味复杂的一个语汇:有时候我们用它来称赞一个作家,有时候我们又用它来否定某种写作,核心的问题是——写作者与农民和乡村之间的关系,以及他所表现出的立场和姿态。
王:我曾写过一篇《十问乡土小说》的小文章,其中的一个问题是,乡土小说的写作者有没有假想的倾诉对象?如果要我回答这个问题,我得说,我的倾诉对象是“小说世界”以外的人,他应该具备相当的阅读能力。或者说,我是在向乡村世界以外的人诉说着什么,我诉说什么呢?自然是“甘家洼”,我想把这个村庄和这个村庄人们的处境告诉城市里的“你们”,在你们的想象之外有一些人这样卑微地艰难地活着。我为什么要把这些告诉你们?因为这个世界是我的出发地,这里有打动我的地方,我和他们的情感有许多相通之处,所以我觉得我和甘家洼的人们是“我们”,我在叙述的时候,说的就是“我们”的事。可能你也注意到了,在《空城计》、《酒国》等篇什里,我直接摹拟的是老甘的语调,他在滔滔不绝地向你们言说他的遭遇,他内心遇到的困难。在《雪国》里,我摹拟的是“小皮”的语调,通过乡村里的一只狗,告诉你这里生态的东西正在遭到破坏,“我”和“老甘”都被伤害了。在这种“代言”里,我和老甘他们的界线彻底混淆了,所以,我既是在“代言”,也是在表达我自己。
刘:阅读整个小说过程中的同情、悲愤、压抑在心里像一直在远处滚动的轰隆隆的闷雷,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来,没有流泪的感动,也没有撕心裂肺的痛,有一种慢慢消磨、钝刀割肉的感觉,一种哭也哭不出来的半死不活的状态,似乎有一点点希望(比如在《向日葵》、《普通话》里),但更多的还是找不到出路的绝望感——村长老甘越营造热闹(比如《空城计》、《酒国》),我的绝望和凄凉越强烈。曾经茂盛的乡村正在慢慢枯败。你以“甘家洼”为整部小说所有故事的背景,是否也有“取样”的意思——甘家洼并不仅仅是一个西北乡村,而是中国大部分乡村(某些东部乡村除外)的缩影?
刘:你的这种努力流贯在你近期的大多数作品中,《文艺报》近来也编发了你的一些纪实性文章,比如《立春》、《远村》,我能感觉到,你最近似乎把观察和思考的重心放在了“甘家洼”这样一些村庄中。在现实中的这些村子里,你看到了什么样的“风景”?
王:应该说进入我视野的村庄,还是比较平静、温和的,它们的消逝有一个缓慢的过程,这有利于我的观察,也正是我选择书写它们的原因。而城郊结合处的一些乡村,可能就没这么幸运了,也许一夜之间,就面临被整体拆除的命运。刚才你说读这些小说有一种钝刀割肉的感觉,可能与我的这种选择有关。我小说里的“甘家洼”,其实有一个真实的地理模拟,它的模样要比甘家洼憔悴得多,沧桑得多。有一天,我无意中闯入了这个没几个人的村子,迎接我的是一条大黑狗和跛着腿的村长。我和那个村长谈了很久,说实话当时心里很受震动。后来,我开始有意识地观察这类村庄,看到曾经红火热闹的学校、村委会或医疗所败落得那么彻底,你不能不心疼。前些天,我回老家参加一个长辈的葬礼,因为同族的青壮年劳力也都走了,想找几个人抬棺材都难,这处境也实在太尴尬了。
刘:这种“尴尬的处境”正是当下乡土文学所要面对的现实。随着乡村现实境地的变化,现当代文学的乡土书写一直在“跟踪”,乡土文学所取得的成就也成为你这样的年轻作家的参照和试图跨越的标高,无论是“底层文学”还是“新乡土文学”的概念,虽然存在争议,但都表达了年轻作家希望能把住当下乡村的脉搏、寻求新的文学表达的愿望。这些小说明显带着一点“野心”,你如何看待我们文学中的乡村经验?希望为它增添怎样的新元素?
王:现代文学有两种经典的乡土书写方式,一种是鲁迅的启蒙主义思想主导下的书写方式,一种是沈从文式的浪漫主义的书写方式,这两种书写方式下的乡村,一种是落后、麻木、愚昧和封闭的,另一种虽然也苦难重重、危机四伏,但并不仅仅是一个落后的想象,相反,它是一个理想的、或者想象的精神家园。如果要问,这两种乡村哪一种更真实?这自然很难回答,就如一首歌所唱到的:天上有个月亮,水中有个月亮,我不知道哪一个更圆,哪一个更亮?我这样说,是觉得对乡村的书写,从来都是和作家所处的时代背景、思想文化构成和现实焦虑有关的,这决定了他们的笔下呈现出怎样的乡村。尽管如此,如你所言,一代又一代的乡村书写者,还是会尽可能地去“跟踪”乡村,去把握乡村的脉搏,至于在何种程度上逼近了乡村,很难有一个判断的标准。因为文学的乡村并不等同于现实的乡村。再看赵树理笔下的乡村,我将它称为第三种书写方式,他书写的乡村基本没有变形,没有矮化,也没有理想化,呈现出来的是复杂的具有多种精神况味的乡村。赵树理对乡村是很有感情的,但这不妨碍他触及乡村的矛盾和问题,所以他的书写更真诚、更独特、也更值得借鉴。但是在鲜活的乡村现实面前,经典的书写方式并不能包办一切,甚至常常会成为一种限制。突破这种限制便是每一个乡村书写者所必须面对的。就我而言,我所面对的“甘家洼”,是日渐凋敝的养育过我的这一类乡村的典型,它既不是一种落后的想象,也并不是我理想中的“精神家园”,但我和它之间却连接着一种割不断的脐带,我需要和它一起经历凋敝的疼痛、一起往前走的困惑。我得承认,我内心的力量还没有强大到可以超乎乡村之上,所以,它的困惑就是我的困惑,它的疼痛又是我的疼痛,这种伴着我的疼痛、困惑的乡村,就是我要书写的乡村。有时,我甚至觉得我就是小说里的那些人,是甘家洼的老甘。
刘:说到“老甘”,我认为这个人物是当代文学中一个新形象。新的乡村现实催生了这个人物,我有时候甚至想,这个人是有“前世”的,或者说他的前半生我们可以想象,可能是淳朴中带点狡黠,对乡村权力有点渴望但也有为民之心,这样的形象作为一个乡村符号,在当代文学中有很多类似的表达——但是,因为乡村的衰败,他变得复杂,他从今以后的生活是我们文学中其他的“村长”所未曾面对的。在《夜活儿》里,有这么几句:“这村子多空啊,空得老甘心里发虚……要是老甘走了,这个村庄还会存在吗?”你对老甘这个人物的塑造特别有意思,复杂难言。老甘眼下的处境、老甘的心情、老甘对于一个村庄的意义,却是你新的思考。甚至可以说,你的重点已经不在老甘的人物特点和性格,而在他和自己村庄的关系。你似乎对这个人物寄予很多的心思?
王:城市化或现代化过程中村庄和农民的命运,这是《甘家洼风景》的基本主题。我写老甘,更着眼于他在村庄凋敝过程中无所依托、漂泊不安的状态和灵魂的失落感、焦灼感。老甘这个人,基本上贯穿这个系列的始终,他的一些类似于堂吉诃德的想法、举动,是我特别感兴趣的。城市化、现代化是一种潮流,作为“甘家洼”的村长,老甘肯定也意识到了这种潮流的势不可挡,但他还是倔强地守护着什么。为了找回村庄昔日的“繁荣”,他时常做出一些可笑的举动,比如,在小年这一天他自己掏钱雇戏班子唱戏,再比如,在醉酒之后,他坐到大戏台上给想象中的村民开会,等等,明明知道大势已去,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这就有些荒唐,可笑,但是我们却笑不出声来,甚至有一种想哭的感觉。老甘的失败,可能就是甘家洼的失败,就是农耕文明的失败,但是老甘真的失败了吗?至少他自己没这样认为,他不甘“失败”,他的“野心”还在蓬蓬勃勃地生长着,无论是《空城计》里的老甘,还是《酒国》里的老甘,都希望明年再唱一回戏,明天再开一次会。所以有时候我想,只要有老甘这样的人在,有他的那些逆潮流的不合时宜的想法在,村庄就不会消失。
刘:我能感觉到,你也努力在小说形式上和乡村的现实以及你的内心情绪形成呼应。在《甘家洼风景》里,小皮(老甘的狗)、麻雀、蚂蚁、死去的人在需要的时候都开口说话,而且你完全没有特别的交代,就自然而然地与人交谈了,并非志怪小说的写法。怎么想到用这种处理方式?
蛋白质是饲料中成本最高,决定鱼类最佳生长的关键营养物质[12]。若饲料中蛋白质含量不足,将导致鱼类生长速度和饲料转化率降低,但过量饲料蛋白质摄入不仅增加饲料成本,同时会加重鱼体代谢负担并增加氮排放,严重影响水质。因此研究饲料中适宜的蛋白质含量对成本优化、保持鱼类健康快速生长具有实际意义。大黄鱼[13]、鲈鱼[14]、卵形鲳鲹[15]、乌鳢[16]等主要养殖经济鱼类已有较多研究,但对大刺鳅适宜蛋白质需求的相关报道较少。本试验采用饲料蛋白质梯度法,考察饲料蛋白水平对大刺鳅幼鱼生长性能、消化酶及肝功能的影响,旨在为大刺鳅饲料配方设计提供理论依据。
王:小说的形式创造最终还是为了最好地表达你的想法,而不是为了创造而创造,从来就没有离开内容的形式。如果我没去过甘家洼,没有体验过那种生活,没有表达这种经验的欲望,我想我不会找到这种形式的。只要你去过甘家洼,你就会觉得我找到了最恰当的小说形式。一个人处在那样一个死寂的村庄,但是你还活着,你有驱遣这种寂寞的欲望,渴望和别人交流,但找到交流的对象又是件多么奢侈的事,于是自说自话就成了一种自然而然的言说方式,和狗啊麻雀啊死去的人等等交流也是一件正常的事。
刘:《甘家洼风景》的结构也很有意思。每一篇都是独立的,读起来没有任何障碍,但放在一起读,就看出了内在的联系,这些篇章是相互牵连的,一个人物看似不经意的一句话,恰恰引出了下一篇的故事或者人物,设置得很巧妙。相互勾连在一起,就形成了一幅甘家洼的众生相以及生活形态。我觉得这肯定不是一个短篇小说的合集,也不同于我们通常所看到的“系列小说”,那么,按照你的想法,你要把它做成一种什么样的小说文体?
王:最初,我打算把它做成“系列小说”或类似的样子,一篇一个故事或人物,通过好多个短篇表达一个大的想法,但写作过程中又有了变化,我发现我不是每一篇写一个人,比如我用八个短篇写村长老甘这个人,大约有八九万字吧,通过多个篇章的强调,我觉得这个人的性格基本出来了。小说里的其他主要人物,比如月桂、天成等,也是通过好几个故事完成的,他们的性格也有一个大致的发展过程。小说的整体情节也有一个时间顺序,大致发生在两年这个时间段内。所以,我觉得我其实是在写一部自己心目中的“长篇小说”。其实任何一种小说结构,都是在表达时代和现实经验中形成的,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永远没有一种现成的结构。
刘:我很赞成你的这个观点。我们经常把内容和形式作为两个体系去言说,很多时候我们感觉创新很难,小说的各种形式似乎都被尝试过了,但实际上,出问题的不是“形式”,而是整个写作本身,或者说对小说的理解、对生活的理解都过于狭窄、肤浅。我能感觉到你在这部作品中表现出了非常强的探索意识,虽然我现在还说不清这个方向是什么,它的特质和个性是什么,但是,感觉到这些小说有了合适自己的表达方式。
王:但是探索其实是难乎其难的,有时候我们在某个地方着力求新,可折腾了半天,突然有一刻我们发现这些形式早有人尝试过了。艺术是一条河流,属于乡土中国的乡土文学更是一条长河,有时候我发现我们连一朵泡沫都不是,想到这一点真的很悲观。比如说我的这部书,我不敢说整体上有多高明,我只能在某一个很小很小的点上写出新意,写出一点属于我自己的东西。所以,就这一点而言,作为一个乡土写作者,可能要面对两种尴尬,一种是乡村的尴尬处境,一种是叙事者的尴尬处境。我只能困兽般的左冲右突,以突破某种限制。
刘:你说的叙事者的尴尬指的是什么?
王:乡土小说反映是的乡村的人和事,按理说它的读者首先应该是农民,但是我发现大多数农民并不去读乡土小说。这让我有时候很怀念赵树理和赵树理时代的农民读者。你说这不是我们这个时代乡土作家的尴尬吗?
刘:这可能与作家的写作意图有关,也与你的语言操作有关。我注意到,你的这个系列的语言呈现出一种非常驳杂的面貌,文雅的、诗性的,不属于乡村的语言与晋北方言有机地交糅在一起,达到了一种特殊的叙事效果。你是经过反复调整,才找到这种叙述腔调的,还是自然而然的选择?
王:我写小说,必须找到整个小说的叙事基调,否则就写不下去。我觉得每个小说都有它自己的调子,旋律,它应该从开头响彻到结尾,并回旋在作者的脑海。有时我写一个小说的开头,需要几个半天,不是我没想好故事和人物,是没想好小说的调子,调子想好了,形成了,那么小说差不多就完成了一半。小说的调子、语言,我觉得有时甚至超过了故事本身。具体到这部书,我前面说过,我假想的倾诉对象是“城市”,是城市里的“你们”,我要把甘家洼的事讲给你们听,而不是反过来说给甘家洼的人们听,所以,我必须找到一种你们能够接受的叙事腔调,这个叙事腔调又必须带上我的“口音”,也就是说,我是在给你们讲故事。我不能用农民的腔调给你们讲故事,因为我首先不是农民,我有我的言说方式,但是我有时候会摹仿老甘的语调,不过细读后你就觉得那并不纯粹是老甘的语调,那里面还夹杂着我的语调。
刘:我发现你这部作品的观察视角在不断变换,比如,在《空城计》里,你是通过“我”(老甘)观察别人,而在《雪国》里,你则通过“小皮”观察老甘和这个世界。我觉得视角的变换,使你的这种“摹仿”有了更多的机会。但我宁愿相信这是一种叙事策略,是为了更好的表现你的想法。
王:这比较复杂。有时候我管不住小说里的人物,一个人物一旦在小说里活了起来,那么他就会按照自己的方式言说,比如在《闹喜》里,老张头是民间说“四六句”的高手,他在小说里说的全部是“串串话”,而我只能隐藏在一个“小孩”的声音里。在《酒国》里,我也只能隐藏在老甘的声音里,根本无法制止他醉酒后的胡言乱语,一任他那么说下去。也有时候,我一开始就能控制住小说人物,比如在《鸳鸯枕》里,我摹拟了天成的鬼魂讲故事,这种叙述语言根本不是天成的口语,因为我总觉得作为民工的天成,在他死去后,他的魂灵应该变得温文尔雅,脱离他过去的那个话语系统。
刘:说到天成,我想到你的这些小说基本是两条线,一是像老甘、月桂、婆婆、老富、老葵这些留守在甘家洼的人,二是像天成、二旺、甘小雪、北大这些外出打工或求学的人,那些发生在各个城市里的故事,其根基还在甘家洼,所以“甘家洼风景”并非只发生在甘家洼村,也延伸到了中国的各个城市。这实际上连接了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两端,把乡村放置到现代性的维度上思考和呈现。
王:小说虽然叫《甘家洼风景》,但我没打算把它做成一部简单的地域小说,没有局限于乡村的经验世界,它并不封闭,是开放的,以甘家洼为中心,以甘家洼的人为线,辐射出一定的社会面和时代面。因为以甘家洼为中心或根基,我首先得把村庄的环境夯实,又因为我想反映甘家洼人的时代际遇,所以我势必要写到城市,城市也成了我反观乡村的一个坐标,如果我不这样写,甘家洼就是不完整的,小说也是不完整的。
刘:没错,这也是今天的乡土小说和之前的不同——甚至,我有时候觉得,在今天,我们对乡村所有的言说,其话语的背后都矗立着一个城市。这些小说中的人,几乎都在默默地、或者自言自语地跟一个不在身边而在城市的亲人对话,他们的问题都已经不是在乡村的内部能够解决的了。
王:说到这里,我想到了“呈现”这个词,我觉得“呈现”与“表现”最大的不同是,一个偏重于你要叙述的世界,一个偏向叙述者的内心或观念。我要呈现一个完整的乡村,那么我所言说的对象就不能仅仅是一个孤立的乡村,也包括它周围的环境比如城市,把周围的环境交待清楚了,这有利于对乡村的叙事。而假如我的叙述重在“表现”,那么我肯定要用我的观念放大或缩小这个村庄,这样经过处理的村庄肯定就变形了,离它本身已经相去甚远了。
刘:作为相对的结构单元,我特别欣赏《普通话》、《看西湖去》、《知己》、《回家》等,在担任小说的整体叙事功能之余,单独拿出来,又都是非常出彩的短篇小说。比如《看西湖去》,非常讲究,铺垫得非常充足,展开得非常有耐心,结尾非常有爆发力却又很自然;《向日葵》让我欣赏的是这个比喻的恰切,尤其是天霞和男人教孩子一起念“向——日——葵”时,那种和甘家洼的向日葵联系在一起的希望,让人心酸而感动。从这个角度讲,这部小说又具备了长篇和短篇的双重叙事难度。就是说,你既精心打磨每一个结构单元,又注重它们整体产生的复调效果。这些尝试和探索对你自己来说,也是一个挑战。从你个人的角度而言,这些小说和你之前的创作有什么不同?
王:我做小说有十几年了吧,又因为我的出身和经历,这十几年又做的多是乡土小说。我不知道别的从乡村出来的作家他们最早师从的是谁,我在刚写小说时对鲁迅很着迷,这不仅仅因为他是大师,实在是他那种激情的批判很适合我当时的年龄、立场,但鲁迅是思想巨人,他的批判是站在一个时代的峰巅之上,而我不是,我只是因为看到了乡村的一些缺点,回过头来,反“咬”一口。这个阶段,我写过《柳叶飞刀》、《张树的最后生活》、《愤怒的电影》等小说,前一篇小说里的“来宝”,有人评价说几乎是当代版的阿Q。到了2005年,随着对城市认识的深入,我对乡村的态度随之有了转变,过去在我小说里显得有些阴暗的乡村开始像田野里的向日葵渐渐高过我的头顶,而我却变得很低,很低。这个时期我一些小说,如《前夫》、《奶香》、《长城别》、《教育诗》等,写得都很温暖,抒情。我给一个刊物写过一篇创作谈,叫“文学应当温暖世界”,大致能代表我当时的想法。我得承认,我需要这样的小说借以“取暖”,需要从小说里质朴善良的人物身上汲取某种力量。当然,我也希望这些文字能够温暖别人。我觉得我这个阶段小说里的乡村是温暖的、高大的,几乎成了我的一种“信仰”。最近这两三年,也就是从2009年起,我主要致力于《甘家洼风景》的写作,我希望写出当下农村的真实风貌,它的矛盾,它的困惑,用文字挽留住一些东西。对小说的形式,刚才我也说了,我希望能够找到一种表达新的经验的形式。不过说到底,我还是喜欢中国化的民族化的小说,虽然这个阶段我看西方小说多些,但我看这些文字,只是希望不致于成为它们的样子。
刘:从你的言语中,我能感觉到你对这本书的看重。这的确是一个非常丰盈的小说世界。不止是物质的生存,它更注重从精神、伦理的角度去看乡村结构的变化和危机。老甘的倔强、执著,月桂在欲望、爱情和道德、亲情上的博弈,我觉得你是很动感情却又很客观地呈现出了乡村的图景。
王:我写《甘家洼风景》,主要不是写它经济上的落后贫困,更注重的是在城市化过程中甘家洼人们内心的风景或风暴。这样的风景有宁静的一面也有动荡的一面,有阳光的一面也有阴暗的一面,就是说它是一个复杂的不安的世界。我希望写出甘家洼人向上、向善、蓬蓬勃勃的一面,也希望写出他们阴冷、灰暗的一面。也许,再过二十年、五十年,甘家洼这样的村庄就消失了,到那时候,当有人指着村庄的废墟问我们这些作家为它们都做过些什么时,我不会太愧疚。我也希望,当现实的甘家洼消失了,作为文学地理的甘家洼会被永远留住。
刘:能看得出来,无论小说的基调、风格、立场如何变化,但有一点是没有变的——你始终在描绘、思考你的乡村经验(你自身的经历以及种种的观察),留下一代人对自己时代乡村的记录。那么,这个系列对你来说是一个逗号还是句号?你会把它继续下去吗?
王:就像小说里的老甘倔强地守护着他的甘家洼,我也会将我的乡土写作进行到底。当然我不可能局限于目前这种形式,我总觉得有一种新的东西等待着我用一种新的形式去完成。比如对于甘家洼,我呈现的只是它的现在时、进行时,但是我们知道,叙述一个事物既不能与它的周围割裂,更不能无视它的过去,在这个系列里因为我书写的主要是甘家洼的“现在时”,对它的过去或历史还着力不够,下一步我或许就要搞清它的来龙去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