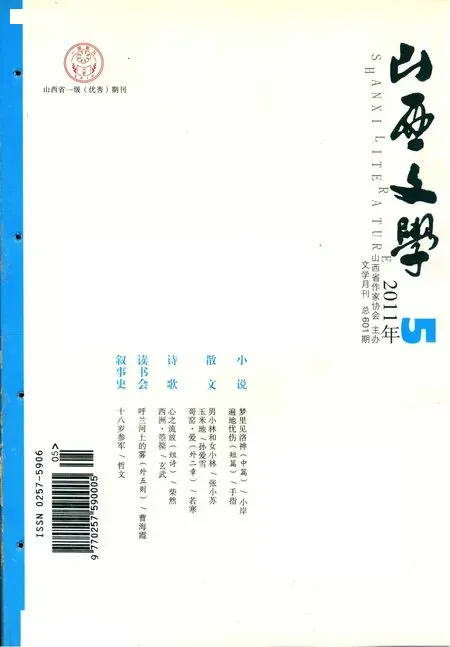呼兰河上的雾(外五则)
2011-11-21曹海霞
曹海霞
呼兰河上的雾(外五则)
曹海霞
萧红的《呼兰河传》中写到爷爷把泥水中淹死的小猪剥刮干净,烤得吱吱冒油,撒上盐巴和菜花递给她吃,满嘴是油,肚子老大。一直惦念着烤小猪的味道是怎么样,从我阅读过这一幕之后。我想每个人在阅读中都会获得关于不同方面的独特情结,除了自己的因素,还有就是作者文字美。就好比美食,有专门写美食的,有文中捎带着描绘的,就那么寥寥几笔,啪地一下,好像铅块断裂一样,击中读者的心。比如周作人、梁实秋、汪曾祺、陆文夫、蔡澜、叶广苓等,能把美食的生命端上来,达到艺术境界,实在是互不辜负这一场邂逅和钟情。当然这里面包含了极为细致的观察和敏锐的感受力,或者一些天生的说不明的东西。我吃过的东西特少,又蠢,更不用提什么鉴赏品味,满是木炭味的烤焦的鸡,长胡子的大鲶鱼,平凡的蔬菜,大米,面食,我吃来都是美味的,而烤猪,大雁肉,青蛙肉,都不曾吃过,对“肥美”二字毫无抵抗力。
萧红的书里有一个很大的菜园子,就是一架豆荚,一丛黄瓜,也写得声色动人,透过纸面可以听到枝梗嘎嘣折掉的脆响,从一个声音可以捕捉到一种敏感、孤独和纯粹,从一个味道可以接触到一个灵魂核心。《呼兰河传》是一部萧红的孤独史,一个女人在回顾多年前的黄昏,火烧云,后院的雨,还有她的哀愁。《呼兰河传》是一部长篇小说,更像是一首叙事诗,一系列散文,朴实自然,平静动人。萧红笔下的生死,悲欢,在呼兰河上空迷离如雾地蔓延。这里的人注定要湮没,却渴求着一点暖。远天的一轮月亮仿佛是一盏白灯笼,又像是招魂的幡。
寻找
作家梭罗(HenryDavidThoreau)寻找一种在夜间和白昼一样歌唱的“夜啼鸟”,寻找了十二年,他说:“你耗尽半生一直寻觅不到的东西,有一天却在饭桌上和它不期而遇,你寻找它像寻找一个梦,而找到它,你就成了它的俘虏。”梭罗或许无意使他的表达费解,但他的文字始终像是简朴的谜语,你瞧,他的描述轻易就使“寻找”这一命题增添了深刻的神秘色彩和透彻的美学理想。梭罗在《瓦尔登湖》中有一段谜样的叙述:“很久以前我丢失了一条猎犬、一匹枣红马和一只斑鸠,至今仍在寻找。我曾对许多旅行者说起过它们,描述它们的踪迹,以及它们对什么样的呼唤会有回应。我遇见过一两个人曾经听到猎犬的吠声和奔马的蹄声,甚至还见到斑鸠飞入云层后面。他们也急于要找回它们,就像是自己失去的一样。”无论作家在此所指的事物是什么,我想他似乎也在传递这样的信息,那就是失落的人是很多的,他们也在寻找,而这寻找已和他们的吃饭,睡眠,生活起居一样必要且重要了。而长期以来,我对我所寻找的事物却并没有掌握确切的数据和特征,它们有的是一种声音,一种力量,一种丢失的过去,还有崭新的未来,甚或只是一些具体的男人,女人。在冥冥之中我知道那就是我想要的,虽然我不知道那确切是什么,或者那是谁,似乎每次都像中魔那样不可思议,比如说我曾寻找
到过一个女人,她像一个母亲,又像一个少女,没有姓名,面目模糊,倏忽去来,极为陌生;还有一个男人,我长期依靠着他的脖颈,肩背,我爱着他,却不知道他的脸长什么样子,也从未想过扳过他的身体一睹究竟,真的从来没有,而且我发现我的旅途距离之远与我的寻找收获并不成正比,在人群集中的地方,我并不能多得到些什么,在雨湿花成团的城市街头,我反而遗忘得更多,我的身体也比平常时候更加迅速地消瘦。我觉得没有什么比一个群体充斥着遗忘,麻木与阿司匹林更糟糕的了,因为他们已不知道失望的滋味,痛苦的刻度,或是垂垂欲落的喜悦了。在这样的时候,当然也是在所有的时候,对于那些寻找者来说,应该要始终记得,不要忘记,我们的寻找初衷,寻找目的,以及寻找这一行动本身的意义。
提奥,我的头上长着耳朵
1881年12月,身居海牙,时年28岁的荷兰印象派画家文森特·梵高在给弟弟的信中写道:提奥,我的头上长着耳朵。如果有人说“你的性格坏透了”,这时候我该怎么办呢?这句话很惊艳。其实在由梵高遗留下来的书信集结而成的美术理论传记《亲爱的提奥》这本书中,其对画作技法,自然风景,贫民生活有大量阐述,新鲜的句子不计其数,但是仍然没能禁住我在读到这段言语时那一见倾心,刻骨绵柔的疼痛感。
读这本书的具体环境,是在开往W城的火车上,我倚靠窗外的风景,枕着咣当的节奏,难免会疲惫,幸好不时会有一些有机的,脆生生的话语,呼吸着,从百年前的老式信纸上融化开来,让我的眼睛闪闪发亮。而且这本书挺厚的,将近500页,49.1万字,很耐读,文字内容也很适宜旅行途中阅读。
梵高对美术的贡献是举世瞩目的,虽然被肯定是在他离开后,着实惋惜。他早期大量进行素描训练,他认为素描画给人风雪呼啸中散步之感,凌乱萧条,有脊椎,他创作水彩画,油画,似乎把生命透析而入,萃在色彩里,让他笔下的画灿烂燃烧。他在其中一封信中曾如此写道:当我画一个太阳,我希望人们感觉它在以惊人的速度旋转,正在发出骇人的光热巨浪。当我画一片麦田,我希望人们感觉到原子正朝着它们最后的成熟和绽放努力。当我画一棵苹果树,我希望人们能感觉到苹果里面的果汁正把苹果皮撑开,果核中的种子正在为结出果实奋进。当我画一个男人,我就要画出他滔滔的一生。如果生活中不再有某种无限的、深刻的、真实的东西,我不再眷恋人间……读到这样的文字,仿佛作者不是画家,而是作家,有着卓越敏感的感受和表达能力。
同时,文森特·梵高也在该自传中连贯显示了他作为天才和平凡人双重身份矛盾挣扎,短暂悲惨的一生,他对穷人有着天生的悲悯和热爱。他把自己的饭每天分给不相识的怀孕的贫苦妇女,为他的穷苦模特免费送来的一筐土豆而感动,他孜孜不倦地描绘着广袤土地上的朴素而光辉的农民、煤矿工人,还有乡村自然风景,他笔下的花朵烂漫成河,间或出现扶疏的人影,细细的头发可以窥到风的方向。他爱过很多女人,虽然那些女人总是让他难受;他被画家毛威表示断交后,什么也没说,只是在信中告诉提奥:“我一个人转身回去了。”他还提到他的叔叔、婶婶,两位老人在很晚的时候,迷雾泥泞的街道上为其指引适宜的旅馆,他能感受到他所获不多的每一分微弱的爱。
所以说,梵高在《亲爱的提奥》里提了那么多的事,很细腻,很唯美,很坚持,但是这些都只给他,提奥,他忠诚的弟弟,亲爱的提奥,在哥哥去世之后半年也离世了。
待我读到150页,已经晚上7点了,抬头看窗外,风景已经看不见了,只看到玻璃上映出的乘客们的群像,尤其鲜明的是一张张都颇具特色的脸。另外,以前几乎在火车上从不吃东西的我这次倒是买了份便宜的打折盒饭,里面是笋片和发乌的米,可能因为天气太冷的关系,很愉快地将它吃掉。
到达W城的时候,时间显示凌晨1:23,此时,W城的每一条街道都在下雪。新雪踩下去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而随着我的脚步声,还是那一句话不停地在我心中回荡:提奥,我的头上长着耳朵。如果有人说“你的性格坏透了”,这时候我该怎么办呢?是的,我无比确定,这句话触及到了一些我内心一直存在但未曾察觉过的部分,软弱的部分。但是,是不是有些令人意味深长呢,写过这句话的七年后,1888年,画家梵高的一只耳朵割掉了,有说是梵高自己把它割掉的,有说是高更割掉的,说法不一。后期的梵高丢失了一只耳朵,但也许,他从不希望自己有耳朵。
斯嘉丽
或是战争中留下的习惯,不论发生多大的事,斯嘉丽都会强迫自己明天再去想,然后借用烈酒辅助睡眠。斯嘉丽热爱土地,棉作物,玉米浓汤,黑面包,以及沐浴阳光。亚历山德拉里普利的《斯嘉丽》完整而澎湃地续出一段美国往事,据说《飘》的很多读者不喜欢它,故事不再辛辣、苦涩,倒是不错的优美感人的篇章。我,始终愿意将两本书一起阅读,乐此不疲,不纯粹是作为一个读者,倒似乎是作为一个会为模糊的遗憾而痛到穿心的女人。随着时间逝去,再清楚不过的是,斯嘉丽的模样在我心中愈见清晰,越来越重。有时候,我能听见,我的泪滴在她的耳上。
秋天的耳朵
孤独的人群多半热爱阅读《麦田里的守望者》,这部诞生于1951年的长篇小说,作家唯一的一部长篇。我读的版本是纯绿色纸张的封面,手感柔软而结实,纸面上涌出只黑色的小鹿,泼开细致的印象和干净的轮廓。
作家塞林格在一个人言语,以一个少年的口气,讲述着你愿意或不愿意听的事情和心情,可是,他讲得很迷人。不出意外的话,每个音节都落在你的心坎,你为他难过。这种难过的情绪是浓的,就像一团工笔花卉,红的要化成灰,触手却凉,凉得就像,秋天的耳朵。
另外,写出这部16万字朴实而有力量的作品的杰罗姆·大卫·塞林格,美国人,出生于1919年,当过兵,写作,隐居,活到91岁,经历传奇,性格古怪。可是,说实在的,能够任性地让自己古怪的人,很了不起,不是这样吗?
绿梦未曾醒
台湾女作家罗兰,在内地风靡一时的是她的散文集《罗兰小语》,但她有一部很好的作品却不太为人所知,就是一部10万字左右的中篇小说《绿色小屋》。全书以旁观者的身份讲述民国时期天津一外交官家的公子的爱情故事,散发出作者对人间情谊和人生的不自由的悲观,冷静而坦诚,结局出人意料,文字清新出奇。
“我”的表哥纪宪纲清俊潇洒,为人善良热情、自然随性,却是其父即已退休的外交官纪维群口中的不孝子,不成器的烂铁,被认定是不务正业,挥霍钱财的纨绔子弟。听继母说,表哥曾经戴着手铐脚镣,从二楼跳上黄包车逃脱禁闭,游荡在外,成日不归,而他家里那个高贵端凝的妻子出身名门。表嫂知书达理,无可指摘,这更是加重了表哥的罪孽。纪宪纲外面有个女人,这件事大家都知道了,只有父亲纪维群不知道,这也是全书的伏笔。
孩子们跟着表哥穿过一地刨花和木头,到达木厂深处一简陋的小屋。纪宪纲以自己的风格随性地介绍:这是表妹表弟,这是陈绿芬。陈绿芬,清高磊落的气质,平静的语气,不落俗套的个性,头巾和长裙随意搭配得恰到好处。书中有一段写道“我”第一次见到的陈绿芬,“穿着一件花繁叶茂的印度绸衬衫,下面是一条白卡其布的裙子,只有一边开衩,显得她摇曳生姿”。表嫂邵佩玉也是美的,书里这么说,“灯下的邵佩玉,好像一朵粉红色的盛开的康乃馨,细致而娇柔”。邵佩玉的美好似混着香水和胭脂气息,吞了冷香丸的宝钗般。两相比较,陈绿芬则像野生植物,很怪,又说不出哪里怪,因为她不像人们传说中的“妖精”。表弟表妹们瞅着陈绿芬做饭,就只是炒个茄子,在她手底下也好像精细的艺术,很好看。纪宪纲说,不要看她。她是个怪物。表哥是有趣的。他总说各种各样的俏皮话,陈绿芬从来不打击他。在这里,他那么精神,眉毛格外浓,眼珠格外黑,唇红齿白的。
他们把房子刷成绿色,信手涂鸦,他们搭积木,呈现出各式各样的建筑风格,他们查很多很多资料。陈绿芬懂外文,家世也很好,据说几年前从东北来到天津,供职于一家书店,而纪宪纲经常跑书店看书找资料。宪纲表哥说,后来去书店就是看陈绿芬了。陈绿芬就只是笑,嘴唇亮晶晶的。似乎,这样的人才是适合纪宪纲的。他们是一路人。虽然也吵过,还动过手,可是他们一直在一起。他们在一起的时候,纪宪纲才是纪宪纲,是他自己。陈绿芬在附近种满了牵牛花,烂漫美丽。这种生长周期短的植物似乎也预示了这份情感也会恍如一梦。
纪维群的寿宴,表哥回家被父亲赶出家门。他把精心准备的古董笔洗托“我”转交,知父莫若子,他一直都是爱亲人的。相爱却不能理解,这个家庭的痛苦。
纸包不住火,早晚而已。纪维群知道了纪宪纲外面有人的事情,大发雷霆,刚烈的老人承受不了这等有辱家门的丑事,双手颤抖地写声明要登报断绝父子关系。报纸终究没有登,因为纪宪纲回来了,而陈绿芬,走了。纪宪纲曾说过,陈绿芬是他的知己。陈绿芬了解他,纪宪纲做不了大恶人。她也做不了。善良的人很难成为一个彻底的反叛者。他们平静地分开了。时光如水。
纪维群新买了一套房子,位于英租界35号路。这套房子的设计非常清雅,所有的材料都是用最好的,纪维群赞不绝口,唯一遗憾的是交货时未完工,纪维群询问儿子的看法时,纪宪纲不做声。纪维群不满地斥责,你懂什么,你什么时候才能有些真才实学。纪宪纲望着院子里的水池对“我”说,里面那块石头,现在布满了苔藓,还看不见,其实上面刻着两字:绿梦。
表哥开始做外交官,和妻子相敬如宾,他说,想做一个好男人或者好丈夫或者好儿子,是很容易的事情。纪宪纲成为了一个好父亲,好儿子,好丈夫,他却不是他自己。这样的表哥让人想要哭了。
陈绿芬依然是美丽独立的陈绿芬,再见面还是亲切地称“我”表妹。她说,爱过那样一个人,以后不会再嫁了。只是这次回来想回去看看表哥设计的那栋房子。“什么房子?”“宪纲在英租界有设计一套房子,可惜没有完工。”“英租界35号路?”“你怎么知道?”原来他父亲买的那个房子是他一手设计的,那块石头是他们一起埋的。陈绿芬愕然,睫毛上蒙了泪雾,“这也许就是天意吧。”陈绿芬一身白衣从林荫大道隐去。
一段宛如天堂、于世不容的恋情,就像一个梦。大家一起埋掉它。世人都说我们错了。虽然我们已经平静,但是有些人,有些事,在心底,陈年的念想,百折千回的往昔。就像有人说的,过去的岁月有它的意义。
责任编辑/鲁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