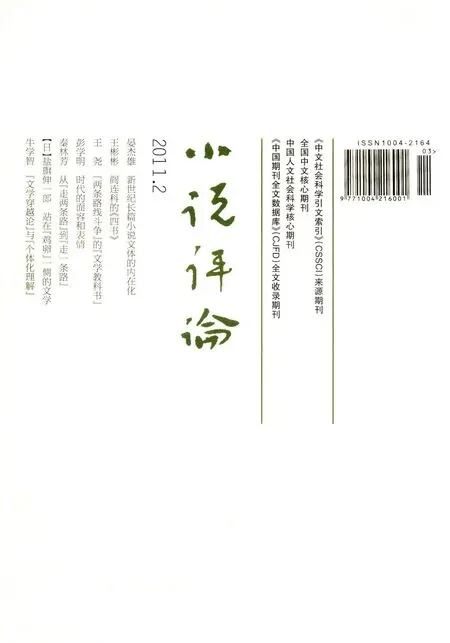《所以》:“革命城市”的世俗叙事
2011-11-19张新珍
张新珍
《所以》:“革命城市”的世俗叙事
张新珍
以《烦恼人生》、《太阳出世》等作品蜚声文坛的新写实小说家池莉历时三年,三易其稿,于2007年隆重推出长篇力作《所以》。这部小说延续了她擅长的爱情婚姻题材,讲述了一个现代都市知识女性的三段情感纠葛。小说推出后,有评论家讶然地质疑池莉创作能力的蜕变。但是当我们以艺术创新的眼光仔细打量时,不难发现作家出于强烈的文体意识,在小说中大胆冒险地进行着艺术探索之旅,试图超越自我凝固的僵硬模式。
一、女性叙述者的“革命城市”构形
五十年代出生的池莉,将主人公叶紫的成长叙事时间起点设置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在近四十年的社会时代风雨变迁中,第一人称叙述者叶紫不断寻求着对当代城市生活以及女性生存困境的理解和挖掘。小说一开头,作家并没有按照时间脉络交代一座城市的“革命传奇”背景。辛亥革命作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动力源和加速器,成就了武汉“革命历史”重镇的威名。在作家笔下,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过程变形为幼年叶紫们热衷的儿童游戏。儿童游戏营造出来繁杂喧嚣的图景,凸显出历史事件的重大价值和理性因素当下存在的荒谬感。儿童们不能完全理解历史的本真含义,他们通过语言建立起同历史文化体系的联系。叙述者还特别提到游戏中有的孩子喊出“打鬼子!除汉奸!”、“蒋匪帮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等时空错位的口号,折射出当时主流话语对民间日常生活的强力撞击。儿童们一方面在角色扮演游戏中初始体验到语言暴力所带来的宣泄快感,另一方面对儿童来说,游戏的语言、仪式、情节,具有某种懵懂无知的神圣性。这一开篇,将以往单质的武汉“世俗叙事”糅合起厚重的革命和历史传统,充分表明池莉努力在根源性上完成对武汉这座城市文学叙事的探索与实践。
第一人称叙述者叶紫在游戏中完成了女身的“易性想象”。在游戏的角色分配及扮演过程里,叶紫潜意识中受男权文化的支配,强烈地拒绝认同女性自我身份,不由自主地认同于男性的高贵和男性的社会性优势。这也表明,当女性想跻身社会历史主流阶层时,必须以放逐自身性别特质为代价。但是女性面对自我性别意识时总是充满了矛盾,无论叶紫怎样“易性”,她始终摆脱不掉先天的女性特质。在表演性的历史大情境里,叶紫仍然本能地关注女性个人情感空间。蛇山追逐“湖广总督瑞瀓的家眷”时,她捕捉到“一群娇滴滴的女孩子,一边逃命,一边回头讨饶”的镜头,这个寓意深长的画面,预示着无论是在历史大主题的公共领域还是在日常生活的私人空间里,女性的命运和遭际殊途同归:男权控制的社会秩序中,摆在女人面前的出路只有屈服与逃离。叙述者有机地将重大历史情境叙述与女性个人主体性的身份叙事相碰撞、融合,在宏大的历史情怀叙述中夹杂感伤、琐碎的女性细腻感情。这种异质性的画面和声音,反而形成强烈的冲击力。其意义不光是从女性的目光来注视、演绎出的历史本相,同时也为女性意识争取了与主流意识对话的权利。
想象和书写一座城市,需要完成空间的建构。除了对叶紫有着“双重家园”意义的彭刘杨路外,叙述者叶紫主要在情感行进中完成对武汉的城市空间构形。东湖、珞珈山是叶紫最初的“浪漫之地”,在那里她抗拒着“爱情”带来的幻觉和眩晕感;解放公园先后见证了叶紫的两段情感纠葛,及至后来商业大潮席卷下解放公园又成为叶祖辉、王汉仙们锻炼、跳舞的集散地。这些积淀着革命历史光辉荣耀的地名,承载着现实生活内容在文本中构建着武汉的地理空间。跟华林结婚后,叶紫热衷于到武汉商场门口、汉正街里淘便宜货,生活重心从浪漫的山光水色辗转至小商品堆积地。作为传统文化诗意象征的黄鹤楼,并没有在小说中作为空间地标式建筑加以展现,它只是主人公叶紫在背诵传统文化文本唐诗时得以重建。日常生活的细微末节消解着传统文化的价值,使其沦为商业社会的消费品。
叙述者叶紫还细腻入微地道出了中国人面对城市化进程时错综复杂的心态。在现代文学里,城市素来是作家批判的对象,一直作为与农村朴素生活相反的道德叙述层面来展现。可是女性作家不同,女人天生是城市文明的尤物。虽然叶紫当初以大义凛然的姿态无奈离开武汉奔向孝感,可是叙述者眼里的乡村却没有呈现出理想化、诗化的田园旖旎风光,相反物质文化生活的贫穷愚昧一览无余。叶紫的城市生活经验所带来的优越感不时作祟,促使她迫切地想离开孝感。可吊诡的是,这段不算长的乡村生活经历,却使叶紫罹患上了都市怀乡病。再次返回武汉这个大都市后,她一面力求在经济生活层面与城市节奏趋同,一面带着农耕文明色彩的道德模式对武汉人做道义上的批判:“只有乡下老人(我们孝感乡下那种没有文化的、淳朴老实的、纯粹为子女而活着的老人),才是世界上最可贵的人!”
二、迷思:世俗武汉的成长叙事
单纯从空间上构形一座城市,无法使读者整体感知到城市的风貌。城市是人的聚居地,人特有的行为方式、生活态度和价值取向,组成了城市居民的生存状态。作家往往通过人物的思想观念、语言行为、情绪态度、理想信仰去表达城市的整体文化品格。乍看上去,池莉选择老套的恋爱婚姻来构塑“世俗”武汉的情感模式。实际上,叶紫的爱情故事被作家有策略地压缩、延迟、变异之后传输出来,隐藏在文本深处暗流涌动的线索仍然是母女之间缠绕了几十年的复杂的爱恨情绪,富有中国传统色彩的家族血缘叙事实质上占据着小说的主导。在小说里,叶紫这对母女经历了“渴望分离——决裂——聚合”三个阶段,完成了叶紫的成长叙事。
叙述者叶紫花了不少篇幅追溯自我成长的艰难历程。童年的叶紫从未出生起就注定了不受欢迎的命运,尚在妈妈的子宫里就险被母体分离出去,以“非人类动物”的异类形象首次亮相人世受到冷落,这种由父母造就的“疏离感”,折射出现代都市人普遍感受到的个体的孤独。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被践踏者、被轻视者往往具有坚韧的生命力,叶紫“自己长大了”。而这样的成长环境,注定了她长期处于被温暖幸福疏远、驱逐的威胁之中,严重缺乏安全感。
叶紫一改传统女性长期处于“被看”、“被赏识”的命运,对他人、世界施以主动“凝视”的方式。如在母权专制的家庭,发现失语的父亲的场景:“意外地看了看父亲,清晰地看见了他的脸。这是父亲给我的第一深刻印象,此前我叫他爸爸,……”从“爸爸”到“父亲”这一语言的亲属称谓系统内部看似微小的变化,代表着叶紫从心底对父亲身份真正的确认。“爸爸”一词据《唐书》记载:“德宗以怀光外孙燕八八为后八八。盖语称老成者曰八八或巴巴。今回回教以老成者呼八八。”①明朝的《正字通·父部》更明确指称“爸爸”一词是对老者的尊称。随着时间的推移,“爸爸”被约定俗成地用于“口语”对“父亲”的称呼,但书面上更喜用“父亲”一词表达父亲在培养儿女成长中的特殊力量。这种“父女”的血缘性关系的一旦确认,绵延深远,以致叶紫此后常常会发出类似“到底是我的父亲!”的感叹。
叶紫不光窥视父母,暗地里也不停地窥探着兄长叶祖辉的成长和变化。叶祖辉刻在梧桐树上、女厕所里的名字、符号或图案,隐晦地道出有关“暴力”、“性”等的青春期多重焦虑症。叶紫无法直接获知哥哥的成长奥秘,她借助于“直视”梧桐树,发现、保守着哥哥成长的秘密,也从梧桐鲜活的生命力中获得父亲般的力量支持:“这种一定,极大地安抚了一个小女孩的恓惶,就像我清晰看见父亲面容那样,……”。
兄长叶祖辉在叶紫的成长过程中行使着“代父”的职责。当叶紫为家庭出身问题惶悸时,叶祖辉仿效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的劝导,使叶紫重振对自家政治身份的信心。有意味的是,当政治身份无虞后,父亲试图接管教育叶紫生存法则的任务。但由于长期浸染在国家历史政治的宏大叙述话语里,他报告似的长篇大论,显示出他早已丧失了世俗性的多元化表达能力。哥哥和父亲对叶紫的言语教导虽有所不同,但无论他们的观点是否有价值,男性作为革命历史的代言人,维护社会、政治、文化等秩序时的强硬姿态还是给叶紫留下了深刻印象。一如拉康所说的那样,叶紫对“代父”和父亲身份的确认,表明自我主体完成社会化的确认。作为“代父”的兄长叶祖辉在叶紫遇到人生“瓶颈”的关键时刻,如返汉、与禹宏宽决裂、与华林发生龌龊等,都给予叶紫莫大的支持和鼓舞。
跟母亲决裂后,青春期的叶紫开始了实现自我的重构和定位的历程。一开头,叶紫追求的不是带有西方文明色彩的“浪漫爱情”,她的爱情理想,不是来自于先天对神圣情感的渴求,而是由底层生活经验造就的:对不安全世界中一处温暖安全的避难所的寻求。这种对房间的向往有着浓厚的传统中国乡村封闭式的经验。叶紫赋予了彭刘杨路居民尤其是民警小何夫妻城市文化中的重情尚义、热心快肠的秉性,而将感情纠葛里的三个男人描述成代表着武汉城市文化积弊的三种世俗人生形态走向。关淳跟他的家庭一样,徒有光鲜令人艳羡的外表,但实里却是市侩主义的:自私精明,有着功利性婚姻的目标。禹宏宽带有一丝农民式的狡黠,以传统的道德准作为爱情认知的基础,追求满足个人幸福,向往相对稳定的传统自然经济状态的家庭模式。而华林带有典型的“码头文化”的痞子习气,缺乏羞耻与歉疚之心。叶紫的婚恋,充分表明“婚姻却是女人的一种社会遭遇,一条狭隘的命运小路。”②
生活呈现螺旋式上升的往复循环,母亲最终又回到了叶紫的生活里。母亲和女儿的身份却发生了“置换”,母亲成为需要照顾保护的对象。象征着母女间的较量与碰撞的景德镇瓷器,被母亲暂时搁置起来。在小说的末尾,叶紫通过镜子将自我人生的过去与现在同时并构,完成了对自我的审视和衡量,也陷入了更远的迷思。镜里是年少美貌的青春时期,镜外是衰老烦躁的中年叶紫,叶紫越是想用自我的眼光去完成对自我、对世界的认知,越是清晰地认识到女性自我受制于男权社会的评判标准、价值尺度,女性往往只有陶醉于想象和幻觉之中,才能得到自欺欺人的幸福。
正如《文子·自然》所言:“天下有始主莫知其理,唯圣人能知所以。”通过叶紫的情感叙事,池莉揭示出含蕴复杂的表达:“所以是一种结果,也是一种态度,也是一种立场,也是一种无奈”③。
三、背离与破坏:语言的实验场
在这部“革命城市”的世俗故事里,池莉把小说语言当作复写当代武汉现实生活的实验场。新写实小说家一出道就摒弃了传统知识分子的英雄立场和精英情怀,《所以》更是刻意保持着对诗学品性和宏大叙事的疏离。池莉努力将小说从诗性、散文化语言中剥离出来,背离了传统作品中优雅的修辞、富有韵律和节奏感的语言,用一种非诗性的语言破坏着五四以来形成的规范性的句法。她较少使用表达繁琐的长句。长句往往带有过多的限定语或者修饰语,词语之间的纠缠不休使人迷惑,词语自身所弥散的魔力也会产生夸张和欺骗的效用,反而遮蔽了生活的真相。而“短句的阅读更有弹性,更加机警,内涵更加个人,也更加辽阔”④,池莉在《所以》里尽量减少定语、状语等对句子的填充,采用短句直接表现庸常的世俗生活,甚至短到词语的排列。如:“树影。草丛。刺溜蹿过小路的黄鼠狼。机警的猫。偶然遇到的同学。断断续续的语言。突兀。简短,无聊,出口而随风而逝,淡而无味。”名词化或者形容词的排列,产生蒙太奇的效果剪辑出叶紫初恋生活的茫然与无趣。
“旧历的年底毕竟还是最像年底。”小说在最后部分不露声色地引用了鲁迅《祝福》中富有启蒙色彩的话语,一下子就将小说的触角从现实层面延伸到了五四新文化传统,潜伏于武汉日常语言下的正统性文化语言不经意地浮出水面。同时也传递出植根于普通百姓日常生活的社会民俗大传统具有强大韧性:“节日习俗所带给人们的情感的、伦理的、审美的乃至信仰的价值都是无可估量的”⑤这种无意识的引用,意在说明我们付出人生或者社会不安定的代价追求新价值、新事物,然而民间社会有着自身的内在秩序,它会带着巨大的惯性维持其系统的稳定性。
池莉对于小说艺术理解显然带有自己生命体验的理解,她讲述的“武汉故事”里充满了对女性生命的反思和认知,她在小说语言上的创新实验纵然存在着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但仍不失为一种开拓性的尝试。
张新珍 华中科技大学中文系
注释:
①方以智:方以智全书·通雅·卷十九[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660页。
②③④郑媛、池莉:太多因为于是《所以》。半月选读[J]。2007年第6期:48页、48页、49页。
⑤王桂妹:启蒙之剑与习俗之饼,文艺争鸣[J],2010年第9期:63页。
猜你喜欢
杂志排行
小说评论的其它文章
- 揭示灵魂隐秘与生命迷津
——评胡学文《从下午开始的黄昏》 - ">"文学穿越论"与“个体化理解”————吴炫文学批评理论
- 祛积极赞同之魅
——重评《艳阳天》 - 玫瑰底色是真诚,洗尽铅华识不俗
——读叶兆言新作《玫瑰的岁月》 - 站在“鸡卵”一侧的文学
——今读《白鹿原》 - 延异的创伤与断裂的诗学
——重读废名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