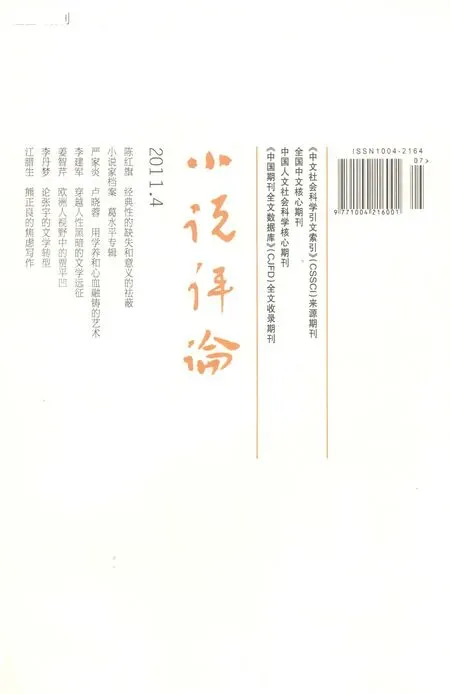日常叙事中的母性观照
2011-11-19余竹平
余竹平
新写实作家的写作源于作家对市民日常生活的反观和对启蒙叙事虚伪性的洞察,作家以更加理性的目光审视母性,使母性由圣坛走向了日常。以池莉论,她的母性书写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对传统家庭伦理的回归和当下母性的实存为标举。代表作有《烦恼人生》;第二阶段是90年代中后期,具有女性意识的小说,以对母性历史的沉入为特征的母性书写,主要作品是《你是一条河》。
一、世俗的承担
池莉的小说贯穿着对母性精神缺失的遗憾,她的成名作《烦恼人生》﹙《上海文学》1987年08期﹚,主要体现了母性在现实的艰难处境中,作为生活支撑和依靠的作用。其中,虽有对母亲坚韧精神的赞颂,但总有一种不圆满感。《烦恼人生》通过对现实生存环境诸如:住房、吃饭、挤车、奖金分配、小孩入托等等日常生活琐事的描写,凸现出生存的艰难。然而,在诸多的人生烦恼、精神颓败的情形中,对于家庭来讲,母性却是一脉支撑和依靠的力量。而爱情、理想、情人则在现实的生存环境中被挤兑了:“雅丽怎么能够懂得他和老婆是分不开的呢?普通人家的老婆就得粗粗糙糙,没有半点身份架子,尽管做丈夫的不无遗憾,可那又怎么样呢?”、“你遗憾老婆为什么不鲜亮一点呢?然而这世界就只有她一个人送你和等你回来”,“他的家,他的老婆!尽管是憔悴、爱和他扯横皮的老婆。此刻,花前月下的爱情,精神上微妙的沟通,等于远离这个饥饿困顿的人”。①这其中虽有对生活的无奈和妥协,然而更多的是对母性力量的肯定。呈现出的是,男人被环境挤压之后的最后依托和无奈的选择。人在其中已丧失了作为人选择的主体性。虽然印家厚有杀死妻子的一脉寒意,然而其精神的超越性却被生存之烦掩盖了,母性最终成了世俗中的拯救力量。
二、养与教的尴尬
《你是一条河》﹙1995年﹚是池莉的“沔水镇”故事之一,这是一部力赞母性伟大的作品。然而她讲述的却不是一位母亲如何拉扯大八个孩子的故事,而是在养与教、文明与愚昧的辨别中,消解了已成范式的传统作家关于圣母的心理反应。在这部作品中,池莉在对母性历史的追溯和对母性生存坚韧性的描写中抽象出了母性的本质,表现出偏离传统规范更关注女性生命体验的走向。
《你是一条河》中浸洇着明显的女性意识,在历史的追溯中创造了典型化的母性形象。从而背离了80年代中后期“生活流”描写的初衷,其情境的设置已表现出回归传统现实主义典型的趋向:地点是商业古镇“沔水镇”,时段是文革期间、丈夫死后、自然灾害、政治灾害并发时期,人是底层母亲辣辣和八个孩子组成的家庭及小叔子、老朱等人。突出了环境上的艰难,抽掉了所谓传统文化以及政治等因素(某种程度上,辣辣是与文化、政治环境隔绝的)的影响。在这里母性成了生存的本源性力量。在丈夫去世之后,面对八张嗷嗷待哺的小口,辣辣试图通过自杀来逃避责任的承担。然而母性本能的觉醒,使她放弃了这种选择,承担起为母的职责。这也是萨特人道主义的基本内涵:即自由选择中的责任和义务向度。在那样的年代里生存成了她生命的全部内容,首先,她必须承担起八个孩子的生计问题:“活下去”是她具体而坚实的母爱。如戴锦华所言:“文革对于三十岁突然守寡,必须将八个孩子拉扯大的辣辣来说,那不是机遇,也不是灾难,只是她必须去应付的变故”。②辣辣凭借着自己的艰辛和身体换取一家八口的生存,在辣辣那里性成了谋生的一种手段,而不是爱情的自然表达,所以她拒绝了酸腐的、手不能拿、肩不能挑的小叔子,而选择了粮店老李的“米袋子”。这不仅使人想起柔石的小说《被奴隶的母亲》,性之于她们具有同等的意义。然而,辣辣的这种交换,却换来了女儿冬儿的鄙视,这也是造成她们母女嫌恶的主要原因。在传统文化中,母亲是圣洁的,母亲的性爱只限于父亲,父亲之外的性是不道德的。但是,冬儿永远也无法理解一个母亲的辛酸,正如方方所言:“我的小说,主要反映了生存环境对人的命运的塑造。”推之于池莉的创作也成立,生存处境的制约决定了辣辣只能成为这样的母亲。所以在辣辣身上侧重体现的是一个母亲养的困难。池莉正是把生存困境推到了极致,从而显示出母性力量的本源性和坚韧性,表现出典型环境对母性人格的塑造和精神状态的影响。
三、母性批判的动因
池莉塑造辣辣这一母亲形象,是为了进行母性批判,是为了对母亲角色重新思考。进而去反思社会、反思文化、反省女性生命自身。
其一,在现实生活中,池莉就是一位另类的母亲和家长。在养育女儿的过程中,她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育女经”。她对女儿的教育重在精神的引导,推崇“快乐教育法”。她认为每个孩子都是唯一的,要保留她的个性。而家长能够做的就是建立良好的生存环境、生存方式和生命态度。对此她曾经说过一句感人至深的话:“如果她盛开需要肥沃的土壤,那么我情愿腐朽在她根下。”这就表明她是一位非常重视女儿精神成长的母亲。在《来吧,孩子》中她写道:“衣食是一种大事,勤俭是一种美德,心静是一种大气,宽容是一种真爱,知晓是一种美好。”③那么,辣辣身上缺少的正是对子女的宽容和知晓,她并不真正把子女当作一个人来看待,她也不了解每个孩子的个性和生命欲求,对待子女只有打骂,她不了解冬儿对书的热爱,而在她最心爱的书上吐痰。为了生存,她纵容社员偷盗,最终把儿子送上了刑场。由于她的愚昧,致使福子夭折,贵子自闭,怀孕后远嫁他乡。所以,在这里既有对母亲生存艰难的同情,同时更多的是一种母性批判。是对母性精神的深层反思。这其中有辣辣的自审,也有同为母亲的池莉的自我审视。
其二,这种批判还在于民族集体无意识之中对地母原型的构想之于个人心理结构的影响:“原型不仅是一种动力,一种如在宗教中,那样的影响人类心理的直接力量,而且与一种无意识观念相一致,在象征即原型意象中,它所传达的意义,只能被高度发展了的意识作出概念性的理解,而且还得付出巨大的努力……她是以神话的方式、以原始意象、以象征来经验世界。”④如同冬儿对母亲的观照源于父权视野下的圣母想象而忽视了自己母亲的处境。作为父权文化的拥护者,再加上母亲精神引导的缺失,使冬儿并不能真正理解母亲,即便她也作了母亲,也不能真正与母亲在精神上沟通。就作者自己的价值立场来看她的态度仍然是矛盾的,虽然她竭力凸显母亲的生存之苦,但对辣辣的精神贫瘠同情而无法认同。作者也让辣辣为此付出了代价:福子的死,贵子的远嫁,冬儿的诀别,得屋的发疯,社员被枪毙,四清出走,这些无疑是对她所有付出的否定。
其三,这种批判的心理动因还来自父权文化立场。如张德祥在《新写实的艺术精神》中所言:“文化场中,场是一种环境、是一种无所不在的存在,场中之物,不无场性,反过来,非有场性便不能在场中生存。”⑤90年代,虽然父权文化已失去了统摄作用,但它对人类心理的影响仍然存在,母性的生命、心理需要在这样的境遇中受到了压抑,这恰恰证明了这种文化境遇的不合理面,那么,冬儿再以父权的道德标准去评判母性时,其行为就显得乖谬:肉体的出卖显然有悖于圣母的规范;以及偏爱体贴自己的社员,对社员偷盗行为的默许;与朱老头心灵相恤的私情;这些都不符合父权社会对母性的要求。由此可见,父权文化删减了母性丰富的人性内涵,这其中潜含着对文化的叩问和批判,谢有顺在论述个人与文化环境的关系时说:“每个人所生活的文化境遇,仿佛都是一个巨大的茧,把自我囚禁在里面,这个茧导致人不但不能顺畅地与他人交流,甚至与自我的交流都疏离了。”⑥作为被囚于文化之茧中的冬儿只看到父权文化对母性的正面要求,而忽略了处境对母性生存的抑制性和遮蔽性,同时,母亲的不公正待遇又使她不能谨慎地对父权文化反思,而由道德标准而不是内在自然力量决定的传统文化品格,必然导致其在世俗化、日常化情境中显示出衰弱的生命力,因此,从文化世俗化的意义上来看,新写实对父权文化的批判是极有深度的。
总观新写实小说的母性书写,作家从处境与母性的关系入手,在对现实与历史的钩沉中,抽象出母性作为生存支撑和依靠的积极意义,以及作为母亲的生养功能这一最本质的母性内涵,作家对父权文化的批判是极其深刻的。这印证了西蒙娜·德·波伏娃在《第二性》中的阐述:“母爱不是‘直觉的’,‘天生的’,在任何情况下,‘天生’这两个字均不适于人类,母亲对小孩的态度完全决定于母亲的处境以及对此处境的反应。”⑦
四、拯救还在路上
在80年代中后期,新写实作家以其平民意识、日常化意识对启蒙文化进行挑战,从而显现出群众生活的神圣性方面。然而,这一代作家并没有真正完成自我撕裂,而是处于启蒙意识向平民意识过渡阶段。表征有二:一是文本中对冬儿、来双瑗等启蒙者的执着迷恋;二是对男性的态度。
一方面,在新写实作家笔下,冬儿、来双瑗等作为启蒙者、道德评判者浮现于文本之中,在某种程度上也折射出作者的情感取向,虽然对她们不无反讽的嘲弄。零度叙述是新写实作家的叙事格调。然而,海德格尔认为,人在面对事物时,事物不可能被置于“观看”的视野之外,而在“看”中必须有一种在先的领会,称为“先行具有的意图和信念”。⑧日常化写作者“看”出来的,与其说是日常生活的原生态,不如说是一种日常生活观,本质上也是一种价值观和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冬儿、来双瑗以隐含作者的身份潜入文本,她们对母性的态度也反映了作者本人的困惑,即这种与母性的认同只是表面上的,而不能获得真正的精神沟通,但在叙述中,母性的生存逻辑常使启蒙者的理性说教显得苍白。如来双瑗靠来双扬交付原单位的管理费等,但是母亲对这些启蒙者的迷恋以及她们最终所作出的选择,也间接地表明了作者对冬儿、来双瑗价值取向的认同。在文本中显现出价值判断的两难,而态度的游移表现的恰是精神的虚弱和苍白,从而也削弱其文化的批判力度。所以,深入新写实精神的内核,我们可以看出,新写实作家缺少的正是这种母性基本原则和范式的建立,和对母性生命的追问。在对父权文化和母性的批判与认同中,其目标是空无的,因此,在虚构的批判之后又回归到了她们所批判的父权文化本身。
另一方面,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文本《烦恼人生》、《太阳出世》中作者以平民意识观照文本中的男女,给予他们的生活以客观的呈现。9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女性意识的加入,作者则让母性以俯瞰的姿态充当了父权家庭的拯救者。对母性形象注入了极大的同情与理解,主要体现在男性形象的塑造上。《生活秀》中长兄来双元靠妹妹养活全家,弟弟来双久靠姐姐吸毒,唯一的成功男士卓雄洲在性较量中也成了卑琐的存在。《你是一条河》中男性形象更是无一可观:且不说被枪毙的社员,出走的四清,更有抓住历史机遇的王氏叔侄,然而一残一疯证明了历史非理性对庸众的戏弄,从而反证了母性原始文化的实在性及其拯救意义。然而,这并不是作者理智的归处,母性对物质性的片面执著仍被视作文明的对立面,从而失去了拯救的可能。因此,从母性角度来看,她们也违背了创作的初衷,并没有真正完成对启蒙理性的撕裂与超越,对真理的寻找与归向的悖反,再次证明了拯救的虚幻。
因此,综观新写实作家的母性书写,虽能在生存本体意义上表现母性的生存艰难,但对其精神缺失不无遗憾。在对母亲生养功能的肯定中,试图完成对这种生存状态的超越,然而不论是启蒙者还是母性自身,其最终的精神指向仍是父权文化,而不是一种新的文化形态作为拯救与回归之路。
注释:
①池莉著,《池莉文集:细腰》,江苏文艺出版社,2002年。
②戴锦华著,《神圣的烦恼人生》,《文学评论》,1999年第6期。
③池莉著,《来吧,孩子》,作家出版社,2008年版。
④埃利希·诺伊曼著,《大母神—原形批评》,李以洪泽,东方出版社,1998年。
⑤张德详著,《新写实的艺术精神》,《文学评论》,1998年6月。
⑥谢有顺著,《我们时代的恐惧与慰藉》,http://www.sina.com.cn.2002/07/17。
⑦【法】西蒙娜·德·波伏娃著,陶铁柱译,《第二性》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
⑧陈家琪著,《话语的真相》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