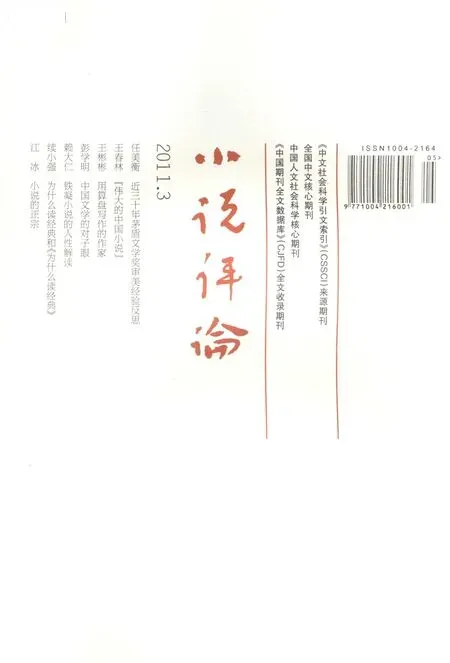《闪闪的红星》:电影对小说的修改
2011-11-19王尧
王尧
《闪闪的红星》:电影对小说的修改
王尧
电影《闪闪的红星》,是那个年代留给我们这一代最深刻的记忆之一。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这部电影,1974年3月完成文学剧本,同年上映。《闪闪的红星》无疑是当年少数几部能够让观众兴奋的电影,即便“文革”之后对“文革”文学艺术的批判,也很少涉及《闪闪的红星》这部电影。
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前些年,《闪闪的红星》也被所谓“恶搞”,出了一部短片《闪闪的红星之潘冬子参赛记》,其中有一段对白是:
潘冬子:你看,青年歌手大赛开始报名了,我们也去报名吧。
春伢子:对,闲着也是闲着。你说,咱们报哪一种唱法好呢?我想报美声,谁让咱长得像帕瓦罗蒂呢。
潘冬子:不,我爸说,民族唱法容易上春节晚会。对,我们唱民族吧。听说刀郎一场演唱能赚100万,那得多少钱呢。我们就唱民族吧。
春伢子:好,民族就民族。我们一起走穴,那得赚多少钱呢。
潘冬子:对,去年超女那么火,今年也轮到我们了。
为此,八一电影制品厂发表的声明称:“这样去篡改一部红色经典影片,如此戏谑地调侃一个备受迫害奋起反抗的小英雄形象,已经伤害到影片《闪闪的红星》相关创作人员,更伤害了对《闪闪的红星》有着深厚情感的中国观众,同时也会误导青少年观众,使他们漠视中国革命历史,甚至会引发许多人以恶搞红色经典影片为乐趣。”
对潘冬子这样一个少年英雄形象的捍卫,涉及到“红色经典”与当下精神生活的关系。这不是一个纯粹的文学史问题。从更为年轻的一代对电影《闪闪的红星》的反应来看,“革命”作为一种精神,依然具有某种激励作用。我在网上读到一些中学生写的观后感,基本都是表达了一种用革命精神来激励自己的想法。有一个学生写道:“这部电影使我受益匪浅,它让我知道了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它让我了解到红军战士们为了使人们得到解放,不畏艰辛,不惧困难,不惜生命与不怕牺牲的崇高品质;也让我们学习潘冬子机智,勇敢与顽强的奋斗精神。”“这部电影像导航的灯塔,照亮我前进的道路,它又像战士的号角,时时催促我奋发向上。它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一个时代的回忆,而是一种精神的延续,它所代表的是在困苦环境下不屈不挠和对真理的执著追求。”这样一种表达的方式和内容,和我们这一代人在当年的观后感几乎没有二致,也与当下的“主旋律”合拍。无论这样的表达是否为内心真实,但都透露出当代中国精神生活的复杂性。
《闪闪的红星》是一部“成长小说”。“一九三四年,我七岁。”小说以第一人称这样开头。到小说的结尾时,“我”——潘冬子,已经成为解放军战士潘震山。潘冬子在小说中回顾说,“从一九三四年到一九四九年,这十五年不算长,也不算短,我已经从一个七岁的儿童,成长为一个青年,当了一年解放军战士了。这十五年,敌人的魔爪捕捉过我多少次呀,可是,他们没有害倒我,却使我经历着一场又一场的风雨,迎接着一个又一个的战斗。”“是党和毛主席给战斗的力量,是革命的人民哺育我成长。”小说的立意也在此。
“红星”在小说中的象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如果比较理性地解释,大概可以用小说的“内容说明”中的文字:“本书写的是红军长征北上抗日、离开江西革命根据地以后,留在当地的一个红军战士的孩子潘震山在党组织和革命群众的关怀教育下、在阶级斗争的风雨中锻炼成长的历程,表现了老区人民对阶级敌人的强烈仇恨,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对党和革命军队的深厚阶级感情。”这样一个成长的历程,始终有一颗红星在闪耀,在引导。已经成为解放军战士的潘冬子在写给父亲的信中,对“红星”的意义有一番抒情性的文字:“爹,你给我的那颗红五星,我还一直保留着,我千遍万遍地看过它,每次看到它,都像看到了你。我曾经带着它,黑夜中迎着北斗去找延安,我曾经带着它,在大风大浪里横渡长江,去找解放军。十五年来,我把这颗红五星紧紧地带在身边,是它,给我信心,给我希望,更给了我勇敢;是它,鼓舞和鞭策着我紧跟你们的脚印,顽强地生活和战斗。心中,我已经成为革命队伍中的一个战士了。我们的革命正在节节胜利,我的亲人也找到了,今天再看看这颗红五星,我满怀胜利的喜悦和自豪。爹,我心中把这颗红五星再寄给你,看到它,也就想着见到了我。虽然已经十五年了,爹,你看这颗红星,还是那样红艳艳的。”
这样一种叙述语言以及蕴藉其中的政治文化含义,散发的是五六十年代文学的气息。作者李心田是在1961-1966年间创作《闪闪的红星》的,1971年修改后于次年5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我们现在无法明确从60年代的初稿到70年代的修订稿究竟有多大的变化,根据李心田自己的叙述,修订稿删除的是初稿中关于人性、人情的一些内容。一篇短文对此有所披露:“李心田说,当时的这部初稿跟后来大家看到的那部书有很多东西不同,因为初稿里他是从人性写起的,写了一个孩子跟亲人的生离死别,是一种自然感情的描写,看了让人比较感动。因为那时,他受张天翼所讲的文学要表现人性的影响,所以整个故事看上去要比现在真实感人。”和“文革”时期假大空的作品相比,《闪闪的红星》无疑是一个具有一定艺术性的作品,但“文革”对小说文本的影响也留下的这样的印记。小说仍然写到了亲情、乡情,但阶级感情是主要的。李心田的成功在于他在人性、亲情与阶级感情之间大致达成了某种平衡。这也是这部作品在“文革”结束以后仍然为一些读者认可的一个主要原因。
但是,电影则在“文革”语境中,从“现实斗争”的需要出发,重构了小说。小说的原主题是“闪闪的红星”如何照耀潘冬子在群众斗争中成长,强调的是阶级斗争。而从剧本到电影则进行了“再创作”,突出了“路线斗争”,影片的主题成为“一曲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赞歌,一曲在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中茁壮成长的‘儿童团’的赞歌。”由小说到电影,主题变化的原因,是改编者“认真学习了革命样板戏的创作经验,根据小说所反映的时代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结合当前的现实斗争的需要,紧紧抓住革命成果的‘得而复失,失而复得’,即两条不同路线产生两种不同结果的问题进行再创作。”在这里,我们可以通过分析《闪闪的红星》由小说改变为电影文学剧本的过程,探析“样板戏”的话语霸权是如何实施的。
“样板戏”在文化生活中的作用也被推至高无上的地位。初澜在《中国革命历史的壮丽画卷》中说:“如果把革命样板戏比作傲霜雪、斗严寒的红梅,那么红梅的绽开必然会引出一个万紫千红、百花盛开的春天。”北大、清华两校写作组的文章则进一步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革命样板戏普及全国,深入人心;新的革命样板作品不断产生;在它的带动下,以工农兵为主力军的群众创作和演出活动蓬勃开展;好的和比较好的文学、戏剧、电影、音乐、美术、舞蹈、摄影、曲艺作品,如雨后春笋,大量涌现。文艺战线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欣欣向荣,生气勃勃。”“样板戏”的话语霸权体现在文艺创作的方方面面。
我们知道有些“样板戏”并非“原创”,而是脱胎于某些剧作。将这些剧作改编为“样板戏”的过程,深刻反映了“样板戏”话语的霸权特征。在重新阅读关于“样板戏”剧组的体会文章或相关的评论文章时发现,改编的过程往往被看作“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过程,我们可以《红灯记》的改编为例。中国京剧团《红灯记》剧组在谈塑造李玉和形象的体会时,认为“《红灯记》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激烈搏斗的产物”。“在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关怀、支持下,我们彻底批判了他们炮制的原改编本,彻底批判了刘少奇、周扬反革命的修正主义文艺黑线形形色色的谬论,对原改编本进行了脱胎换骨的改造,终于使《红灯记》成为无产阶级文艺的样板,李玉和成为无产阶级英雄的艺术形象,成为‘帮助群众推动历史前进’的巨大精神力量。”文章对“原改编本”提出的批评有:“不仅只字不提伟大领袖毛主席,还拒绝在戏中安排游击队与敌人‘开打’的场面,孤立地表现地下工作,又一再让李玉和违反党的秘密工作原则。”“从根本上歪曲了无产阶级对敌人的阶级斗争。在他们的笔下,日寇是凶焰万丈,温文尔雅;李玉和却是罗锅背,既不敢斗争,又不善于斗争,处处被动。”“不仅不根本表现李玉和与群众血肉相联的阶级关系,还竭力宣扬说明‘家庭气氛’、‘骨肉情况’,贩卖反动的人性论。”“大肆渲染‘苦难’和‘恐怖’,罪行累累。”“把第五场无产阶级的壮别歪曲为泣别”,“剧的结尾一片灰暗”。等等。
以普及“样板戏”来推行其话语霸权,从而带动各种文艺形式的“革命”,这是“文革”时期文艺创作的一个普遍现象。在八个“样板戏”之后,又有了钢琴协奏曲《黄河》、钢琴伴唱《红灯记》、交响乐《智取威虎山》,现代京剧《龙江颂》《红色娘子军》《平原作战》《杜鹃山》以及现代舞剧《草原儿女》《沂蒙颂》等等。至于如何普及“样板戏”,主流文艺批评总结的主要“经验”是“必须坚持文艺战线上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在斗争中认真地学习毛主席的文艺思想。只有这样,才能充分认识普及革命样板戏的深远意义,真正理解革命样板戏的革命精神,学好演好革命样板戏。”
移植“样板戏”被视为普及“样板戏”的一个重要措施,是推动地方戏曲和其他文艺形式革命的重要途径。“各种文艺形式,通过移植,可以直接学习革命样板戏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典型的经验和其他重要经验,从而为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发展各种文艺形式的创作,打下牢固的基础。”在当时受到肯定的移植有:河北梆子《红灯记》、维吾尔语歌剧《红灯记》、评剧《智取威虎山》、河南花鼓戏《沙家浜》、粤剧《沙家浜》、淮剧《海港》,晋剧《龙江颂》以及快板书《奇袭白虎团》等等。
电影《闪闪的红星》编剧之一王愿坚在谈改编体会时突出了“如何运用三突出、两结合方法创作的问题”,并把改编《闪闪的红星》的过程,看成是“思想改造,世界观、艺术观的改造过程”:“回顾这一段,我们等于进了一次学校,学习样板戏的艺术学校和思想学校。我们组过去程度不同地受文艺黑线影响,特别是我们两个执笔者,在实践中,也写过有倾向性错误的东西,给党带来损失,经过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所认识,对旧的文艺思想所有洗刷,但我们的创作实践还不够,还会有些旧的东西反映到创作中来。因此,在实践中,有个如何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以及和文艺黑线回潮作斗争的问题。”王愿坚曾经创作过《普通劳动者》等有艺术品位的作品,在这里的自我否定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文革”改造作家的成效。
在“样板戏创作经验”的影响下,改编的出发点是以“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任务”即“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典型”依据。为此剧本对小说作了几个方面的修改。突出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来设置英雄人物潘冬子活动的典型环境。恩格斯所讲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典型性”被改编者和主流文学批评理解为阶级本质。当时曾有人著文阐释电影在这方面的成功:“影片正是选定了这样一个激烈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背景,去塑造潘冬子的英雄典型性格和揭示深刻的主题思想。‘疾风知劲草,岁寒见松柏’。在激烈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锻炼出成千上万个可歌可泣的无产阶级英雄典型人物,潘冬子就是这个‘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之一。”为了突出“路线斗争”,小说反映的时间1934-1949年在剧本中改为1931-1937年。
电影从两个大的方面,对小说进行了“再创作”。一是从“路线的高度”,为潘冬子的成长确定“历史的依据”;二是要表现“儿童团斗垮还乡团”。而这两个方面的“再认识”都是和“现实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联系起来”的。如此,潘冬子的成长也就有了“高起点”。一个少年,被填充了“路线斗争”的内容,文本的叙事话语也就成了象征话语。在电影中,潘冬子的其他自然属性差不多都被删除了,他在一个既定的“政治秩序”中长大:潘冬子生长在一个世世代代受地主压迫、剥削的贫苦农民家庭里。地主胡汉山逼死他的爷爷,他与地主老财有世代怨仇。残酷的阶级压迫,决定了潘冬子从小就有反抗阶级压迫的可贵本质。同时,潘冬子又是生长在一个革命的家庭里,从小就受到父母革命英雄主义的熏陶,有一棵强烈向往革命的心。激烈曲折的斗争道路,磨炼了潘冬子的勇敢、灵活,不怕苦、不怕死的顽强革命意志。正反两条路线所带来的不同结果,使潘冬子无比地热爱毛主席。党的无微不至的关怀和辛勤的培育,指引着潘冬子在革命的不平坦的道路上勇敢战斗,从来没有后退一步……
为了能够突出潘冬子与胡汉三的矛盾斗争,剧本对小说中的情节作了重新设计。譬如关于打土豪分田地,在小说中是发生在潘冬子5岁时,剧本则将其挪后二年,让潘亲眼见到,亲身参加,亲手牵着胡游街。胡汉三逃走的细节也改为潘冬子在做“打土豪”游戏时发现的,并设计了投枪刺敌、拳打逃敌、口咬敌人等面对面的斗争。其中一个比较大的改动是胡汉三的死。小说中关于胡汉三的死是这样描写的:
公审大会整整开了一上午,最后判处胡汉三死刑,就地执行枪决。
“砰!砰!”两声,胡汉三像一只死狗一样躺下了。大场上响起了人们轰天动地的口号声:
“打倒国民党反动派!”
“解放全中国!”
“中国共产党万岁!”
“毛主席万岁!”
电影则将这个公审的场面改为小冬子用柴刀砍死胡汉三:
深夜,小冬子背插柴刀,手提一把煤油壶,蹑手蹑脚来到胡汉三睡觉的房门口。房门虚掩,门上挂着一把铜锁。
屋里传出胡汉三的鼾声。
小冬子止步,想了想,轻轻把门推开,走进。
桌上,一盏带罩子的半明半暗的煤油灯。
小冬子毅然提起油壶,把煤油全部浇在胡汉三的床上。然后,拿过油灯,拨下灯罩。
被子点燃了,帐子烧着了,满床腾起了熊熊烈焰。
火光映着小冬子充满愤怒和仇恨的脸。他从容地拨出柴刀,提在手里,大步向房门走去。
就在这是,被烧得焦头烂额的胡汉三,连滚带爬地滚到床下,又挣扎着向门边爬了几步。
小冬子回转身来。他威严地站着,鄙夷地盯着脚下的胡汉三。
胡汉三仰脸向上一望,惊惧地:“是你?……”
小冬子厉声地:“是我!红军战士潘冬子!”
雪亮的柴刀,迎着火光,高高地举起,又凌空劈下。
这一改写,自然突出了“儿童团斗垮还乡团”的改编理念。
小说中一些体现民间日常生活的情节也被重新设计,如潘冬子在茂源米号的斗争,小说描写的是潘冬子学徒受欺凌和揭露米号老板囤积居奇、牟取暴利。这样的描写在改编中被认为游离于潘与胡斗争这条主线之外,影响了潘冬子英雄形象的塑造和主题的挖掘。修改后的茂源米号既囤积居奇、牟取暴利,而且还是一个专为胡汉三搜山筹办军粮的罪恶地方。处于激烈的矛盾冲突中的潘冬子当然不会自发地成长,因此剧本比小说更突出、强化了一个“他者”,即红军吴大叔。潘冬子父亲受伤取子弹的情节,在小说里是由父亲对潘冬子讲述,要潘冬子记住这子弹和子弹上的血,剧本改为由吴大叔对潘冬子讲述,对他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帮助潘摆脱狭隘的个人复仇观念让潘明白要白狗子流血与保卫红色政权、解放全人类之间的关系。
《闪闪的红星》的改编被主流文艺评论给予了高度评价,并把它的改编视为坚持“三突出”创作原则的胜利:“电影《闪闪的红星》对小说的改编所取得的这些成就决不是偶然的。它是在江青同志领导的无产阶级文艺革命进行了十个年头的必然产物,是革命的电影工作者努力实践革命样板戏的‘三突出’创作经验的可喜成果。电影《闪闪的红星》改编成功,再一次宣告那些攻击革命样板戏的‘三突出’创作原则不适用于电影艺术的谬论的破产。事实再一次证明,不是革命样板戏‘三突出’的创作原则不适用于电影艺术,相反,凡是离开了这个原则,必然要滑到修正主义的歪路上去,必然会犯‘写真实论’‘中间人物论’‘无冲突论’即政治上的阶级斗争熄灭论等错误。这就是被近几年来电影和其他的艺术创作中行动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教训所证明了的一条真理。”
很多年以后,小说作者李心田仍然认为电影的改编是成功的,这让我诧异。如果要进行革命传统教育,我以为还是读小说《闪闪的红星》。
王尧 苏州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