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话与知识建构
——以汉代墓室中的天文图为例
2011-10-30刘惠萍
刘惠萍
(台湾“国立”东华大学中国语文学系,台湾花莲,97441)
神话与知识建构
——以汉代墓室中的天文图为例
刘惠萍
(台湾“国立”东华大学中国语文学系,台湾花莲,97441)
汉代是中国天文学发展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同样地,在许多汉代的墓室顶部,也经常配置有刻绘日、月、星辰等表现“天文”的图像,并经常可见如二十八宿、北斗与帝车、东宫苍龙、西宫白虎、牛郎与女宿、彗星等各式象征“天文”的星斗,以及象征日、月食等特殊天文现象的图像。这些刻绘于墓室中的天文图,除了具有象征墓室小宇宙的天空或天界之功能外,更充分地反映了两汉时期人们对于天文的理解与想象。
然而,较特别的是,这些汉画像中的天文图,大多并非是真实、客观准确地再现天空的科学性描绘,反而较多地是一种以古典神话内容结合人文想象的表现。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现象,则可能与神话传说在当时所能提供的对天文的理解,较之深奥难懂的天文哲理,将更浅显易懂,是表现意象、传播天文知识最好的手段。而这一类被当成“知识”的神话传说,它们的社会功能便在于以人们熟悉且相信的“真实”,来合理化一些本土知识。
汉画像 天文图 神话 知识建构
前 言
冯时在《中国天文考古学》一书中论及中国古代的天文学与丧葬制度之联系时曾指出:
中国古代的埋葬制度孕育著这样一种传统,死者再现生者世界的做法在墓葬中得到了特别的运用,其中最显著的就是使墓穴呈现出宇宙的模样,他们或以半球形的封冢及穹窿形墓顶象征天穹,甚至在象征的天穹上布列星象,同时又以方形的墓室象征大地……[1]
而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秦始皇马骊山陵玄宫:“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可知秦始皇的墓室中可能已出现有代表天文的图像。另从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于墓室中绘制天象图,亦有其悠久的历史[2]。
到了汉代,在许多汉代的墓室顶部,更经常出现配置有刻绘日、月、星辰等表现“天文”[3]的图像,且似成为两汉时期一种普遍的葬俗。这些与天文星象相关的画像,有的是汉代天象观测的真实记录;有的是以结合丰富想象力的神话传说来象征汉代人对“天”哲学理解的艺术品。
历来学者多认为这些融科学、现实、想象为一体的汉代墓室天文图像,除能反映出两汉时期人们对于固有神话的继承外,更为我们研究汉代天文学提供了形象而直观的文物资料,具有很高的天文学价值[4]。 然从相关的研究中发现,许多画像石的工匠可能并不识字[5],故这些刻画的工匠常常只依据口耳相传的故事或作坊粉本来从事制作[6]。另一方面,巫鸿和包华石(Martins Powers,1949— )在研究中也指出,汉代画像石墓的建造,有墓主、丧家与工匠沟通的过程[7]。而以墓主可考者多是二千石以下的地方官员的身份来看,这些墓葬中所刻画的故事,除了必须是工匠所熟知的题材外,更是墓主及其家属所爱好的题材。是故汉画像中的题材,虽难免与文献所载有出入,但却往往更能反映当时流传于民间的知识与观念。
因此,本文拟透过对各与“天文”相关主题汉画像内容与特征的整理与分析,以了解相关图像在当时的流行情况,以及它们在汉代社会中的作用,并探讨作为“大传统”的汉代天文学与民间神话传说“小传统”[8]之间互相依存、互相交流的关系。
汉代墓室中的“天文图”
自汉代始,由于受到当时社会风气、宗教信仰以及墓室建筑形制的演化等因素之影响,以各种图案随葬或装饰墓室的风气大为盛行,使得墓葬艺术有了空前的发展。而在这些墓葬艺术中,又经常可见以神话式的构图来表现各种天文及星宿的形象。如在许多墓室的顶部便经常可见到如四宫、二十八宿、北斗与帝车、东宫苍龙、西宫白虎、牛郎与女宿、彗星等各式以神话式构图象征天文的图像,以及以神话式情节表现的日食、月食、日晕等特殊天象图像的画像主题。
就目前考古出土的材料来看,在流行时间上,至晚从西汉初期开始,到东汉晚期;在地域的分布上,则两汉时期的各大墓区都有出现相关的天文画像。其中,尤其是南阳地区,更出土了大量的相关画像。兹就今所知见汉代墓室中发现与“天文”相关的画像概述如下:
(一)日、月
在许多汉代墓葬出土的文物中,最常见与天文相关的画像便是日、月的图像。如在年代属于西汉早期的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帛画[9]、三号墓帛画[10]及山东临沂金雀山九号墓帛画[11]中都已明确出现中有乌鸟的“日”及有蟾蜍、兔子的“月”形象。同样地,在四川以及河南、江苏、山东等地出土的许多墓室壁画或画像砖、石上,也常常可以看到借金乌或三足乌,以及蟾蜍、兔子、桂树等形象,表现人们对日、月之理解与想象的图像。例如在属西汉中期的河南洛阳卜千秋壁画墓中,在以描绘天界景象为主的墓室顶脊西端,便绘有伏羲胸前有日轮,而日中有飞翔金乌;女娲胸前有圆月,而月中有蟾蜍和桂的形象(图1)[12]。

图1 河南洛阳卜千秋汉墓主室顶壁画·日中金乌、月中蟾蜍与桂树
这些日、月的形象,除了多具有象征墓室“小宇宙”的日、月之功能外,据韩连武《南阳汉画像石上星图研究》一文的考察,以为在南阳地区多幅日月星象汉画像中呈现的日、月运行及其位置,可能亦具有表现地球自转和公转及特定时序天象的意义[13]。
(二)四宫
关于四宫星座的图像,就目前出土的汉画像来看,则可于河南南阳阮堂出土画像石(图2)[14]、南阳蒲山1号汉墓画像石(图3)[15]、陇西寨亦祠画像石发现有“苍龙”星座的图像。其中如南阳卧龙区阮堂出土画像石,画面的上方为一月轮,内有玉兔、蟾蜍。下刻苍龙星座,从头到尾以十九颗星组成的生动龙形象来表示,画像中虽明确刻有角、亢、氐、房、心、尾、箕七个主要星宿,然整个画面仍以物象的苍龙为主,星象七宿为辅。而在南阳蒲山1号汉墓画像石中,虽刻有五颗星,然中央仍以一苍龙的形象为主体,龙的前面再配以可能是苍龙星座中的角宿的两颗星;而龙的身下则有大概是心宿的相连三颗星。

图2 南阳卧龙区阮堂画像

图3 南阳蒲山1号汉墓画像石·苍龙星座
除了苍龙星座外,同样在南阳蒲山1号汉墓画像石[16],以及1935年在南阳市采集的画像石(图4)、南阳白滩出土的画像石(图8)[17],也发现有“白虎”星座的形象。按白虎星包括奎、娄、胃、昴、毕、嘴、参七宿,然据《史记·天官书》所云:“参为白虎,小三星隅置曰嘴觿,为虎首,主葆旅事。”孟康注以为:“参三星者,白虎宿中,东西直,似称衡。”[18]又《汉书·天文志》有:“参为白虎,三星直者,是为衡石。……其外四星,左右肩股也。小三星隅置,曰嘴觿,为虎首。”[19]故在南阳市采集的画像石,正中便刻一只张口翘尾的猛虎,虎前有六星,横直三星连线在上面;竖直三星连线在下面。其横三星为“参宿”中的“衡石”,竖三星为它的辅星伐。虎腹下排列三颗大星。画像石上的白虎星座虽未刻全七宿,但借着白虎的形象,使人看去一目了然。

图4 南阳市采集画像石
此外,如河南南阳市西麒麟岗汉墓画像石(图5)[20],在画面中刻一中央天神正襟危坐、头戴山形冠,可能为西王母。其四周由以龙、鸟、虎、龟蛇交体四种动物形表现的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环绕。虽无星点的形象,但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以神话象征手法表现的天文知识。

图5 河南南阳麒麟岗画像石
(三)星象
除了四宫等较显著的星座外,如在1987年4月于西安交大附小发现的西安交通大学西汉壁画墓的券顶,也有一幅外径达2.7公尺的古代彩色天象图(图6)[21]。此图南北分列日、月,日中有金乌,月中有蟾蜍、兔子,日、月之外绘有由两个巨大的同心圆组成的环带,环带内布列二十八宿星象。而二十八宿的每个星座,几乎都配着一个人物或动物。
另在汉代墓室中也发现了几幅属于玄武星座区域里的主要星宿——“牛郎”星和“织女”星的形象。如在属东汉早期的山东孝堂山石祠隔梁底画像的南段刻一日轮,日旁有一坐在织机上操作女子的头上画了三星的形象,即是以神话人物形象结合星宿表现织女星(图7)[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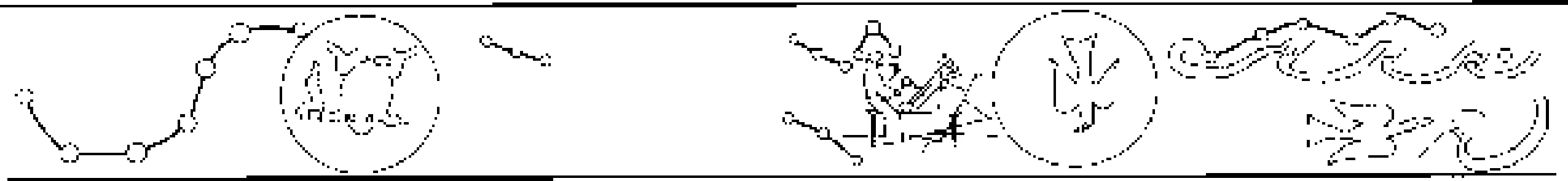
图7 山东孝堂山石祠画像
另如在南阳白滩画像石(图8)上,除了西宫白虎外,还有一幅被称为“牛郎织女”的画像石。画面的左下方有四星相连成梯形,内有一高髻女子拱手跽坐,应是织女星[23];而右上有三星相连,下刻牛郎牵牛图,故此三星应为“河鼓二”,即所谓的“牵牛星”。也是以具象的神话人物象征牛郎、织女星。

图8 南阳白滩画像石
此外,在汉画像中还有一些以人物及情节的方式表现牛郎织女形象者,如四川郫县2号石棺的棺盖(图9)[24]上,便刻有一牛郎牵牛、织女执梭的画面,由其与四象中的青龙、白虎相配,且从绘于棺盖的位置来看,应亦为天文的象征。然其画面中完全没有出现星斗的形象,更突出地表现了运用神话情节表现天文的特征。

图9 四川郫县2号石棺棺盖
(四)特殊天象
除了日月及星宿的刻绘外,汉画像充分展现了两汉时期人们对天文的观察与知识,故亦出现一些表现有特殊天象题材的画像。
如在南阳宛城区出土的画像石(图10)[25],画面主要由前所提及的苍龙星座及毕宿组成,上方中间则刻一巨大的阳乌背负日轮而行﹔其后亦刻一阳乌背负日轮,日轮内却刻一象征月亮的蟾蜍,表示日月重叠发生了日食。故学者多称此图为“日月交蚀图”[26],而日月交会,在汉代又被称为“日月合璧”,是祥瑞的象征。

图10 南阳宛城·日月交蚀
中国关于日食的最早记录见于甲骨文,汉代人不仅对日、月食作了记录[27],且对它们的成因也有所认识[28]。而此一以神话情节表现的日、月交叠画像的出土,更充分显示了汉代天文学发展的水准。
至于在表现特异星象的部分,汉画像中最常出现的则为彗星的形象。如东汉早期的南阳王寨汉墓前室过梁下方画像石[29],向西刻有负日的阳乌,东边刻一满月,内刻蟾蜍。日月之间有六星连线呈ㄩ形[30],月亮右边又有六星连线状似北斗的星座,其上下各刻一彗头向东、彗尾向西直尾,人称“蚩尤旗”的特殊形状彗星。然而,像彗星这样的特殊天象,汉画像中也出现了以具象人物情节表现的画面,如新莽时期的江苏盱眙汉1号墓棺盖顶板(图11)的最右侧,有三颗无连线星点、三颗连线星点,若仅由其形象,实无法判断其星名。但由其右下角出现一骑着扫帚、状似彗星的人形,而左上角却有个呼号疾走的小人,殆是以张皇失措的样子来表现人们对彗星出现的恐惧。

图11 江苏盱眙1号墓棺盖顶板
综上可知,汉代墓室中经常可见以神话或人物的形象来作为表现天文现象的方式之一。
汉代墓室天文图与汉代天文学
汉代墓室之所以大量出现这些表现“天文”的图像,一方面固然与中国自古即有于墓室顶绘天文图的传统有关。尤其,我们从许多汉代墓室的建筑及画像的内容配置可以发现,这些墓室实具有“象天法地”的设计意图。然而,从我们对相关图像中大量出现具象且有时近乎科学的天文图像内容来看,这些汉代墓室中的天文图,除了是一种汉代人们企求借由这些“象天”的图像达到与天沟通愿望的具体表现外,可能更反映了两汉时期人们对于天文的认识和理解。故相关图像的形成,或亦与汉代天文学的高度发展有关。
首先,中国是世界上天文学发展最早的国家之一,甲骨文中即已有六十干支表,并有日蚀、月蚀、新星、恒星、“鸟星”、“大岁”等名的记录。而在传世文献中,如《尚书·尧典》中即已有年、月、日、旬、四季、闰月的概念,并有以星象定季节的描述。《诗经》中更有不少关于天象的记载,如“东有启明,西有长庚”、“定之方中,作于楚宫”、“七月流火,九月授衣”等,都是观察天象的经验之谈。另《诗经》中还记有如火、箕、定、昴、毕、参等二十八宿的星宿名。此外,还记载着与观象授时有密切联系的天汉、北斗、牵牛、织女等星象。又相传《大载礼记·夏小正》记载了夏朝的历法,其中更有按月记载中星、斗柄指向、气候变化的记录。因而在三代以前,中国人在天象的观测等方面,已具有颇高的成就。
而汉代则可说是中国古代天文学的黄金时期,除了在历法、仪象等方面有显著的成绩外,汉代人在天文的观测及理论建构方面,也都有极大的贡献。从相关的记载可知,汉代人已认识形成日食、月食和太阳黑子等现象的原因,且已懂得观测日食、月食[31]。更有不少学者认为,日中有乌之说是因为上古人民以肉眼观察的方式,偶然地发现了太阳上有黑点,也就是现今所谓的“太阳黑子”,于是就用全身乌黑的乌鸦来象征太阳中的黑斑,乌鸦也就变成了太阳鸟[32]。
此外,假若南阳宛城画像石上所见人称“日月交蚀图”的画像,确实是反映日、月食的天象,那么亦正与汉代史籍中多次对日、月食的记录若合符节。其中如《汉书·五行志》中便对公元89年5月29日的一次日食有这样的记载:“征和四年八月辛酉晦,日月食之,不尽如钩,在亢二度,哺时食从西北,日下哺时复。”又《西汉会要》亦载有:“凡汉著纪十二世、百一十二年,日食五十三起。”汉代人不仅对日、月食作了记录,而且对它们的成因也有所认识。据张衡《灵宪》载:“月光生于日所照,魄生于日之所蔽。当之则光盈,就日则光尽也……当日之冲,光常不合者,蔽于地也,是谓‘虚’。在星则星微,遇月则月食。”[33]故这幅日月交蚀图,则可能是研究中国古代天文科学的珍贵资料。
此外,汉代在星象的观测和认识上也取得了重大成就,除已掌握了五大行星的运动规律[34],对于恒星的观测,亦称完备。按张衡《灵宪》载:“中外之官,常。明者百有二十四,可名者三百二十,为星二千五百,微星之数,盖万有一千五百二十。”并称“海人之占,尚不与也”。可见,汉代在对星象的观察上已有极高的成就。同时,到了汉代可能即已有科学性星图的绘制,因此,反映在汉代墓室的画像中,自然便出现了丰富而多样的星宿形象。如前所举南阳麒麟岗的四神画像石,在画面左端便刻有女娲及南斗六星;画面的右端则是伏羲及北斗星(图5)。另如南阳唐河针织厂画像石[35]、南阳丁凤店出土画像石(图12)[36]、南阳溧河乡十里铺画像石墓后室画像石[37]、南阳王寨汉墓画像石[38]等,也都出现有北斗七宿的图像。而到了东汉中、晚期,南阳地区更出现了不少表现具象星宿的画像。如南阳丁凤店出土画像石(图12)[39],画面即为一星象图:左为背负日轮之金乌,金乌左一星为“太白”,乌尾三星连者为“河鼓二”。连成菱形的四星似为“女宿”,连成杓形的为北斗七星。北斗柄下星为“相”,而柄上的三星,按《晋书·天文志》载:“天枪三星,在北斗杓东,一曰天钺。”故此三星应为“天枪”。至于像南阳草店北梁画像石则出现有阳乌、月及“勾陈”星。[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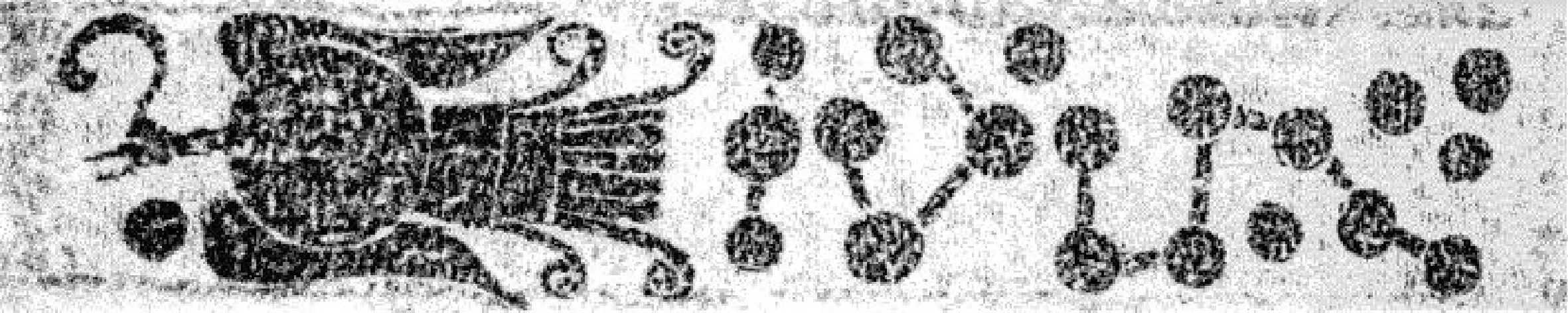
图12 南阳丁凤店出土画像石
至于“二十八宿”之名,虽然在《诗经》、《夏小正》、《尚书》等典籍中已有其中部分星名的出现,然其名称的真正确立,则要到《吕氏春秋》、《淮南子》等书。据此可知,西安交通大学墓室顶壁画天文图中对于二十八宿细致且科学的描绘,则更是一种汉代天文学发展的体现。
另,汉代墓室中还有一些表现彗星形象的图像,中国古代对彗星的观测,虽于春秋时期即已有所谓“孛”之名,然“彗”之名则最早见于《史记》,并有“客星”之说[41]。据《汉书·天文志》载:武帝“元光元年六月,客星见于房”[42]。这可能即现今所说的彗星。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73年在湖南长沙马王堆3号墓中出土了一幅描绘了二十九幅彗星的帛画(图13)[43],各彗星图像下还附有命名,并记载了星占家的种种预言。这幅彗星图可能成书于公元前4世纪而经后人传抄,它更标示了至晚在汉代以前,中国古代天文学家对彗星多种多样形态的观测记录与分类研究。

图13 长沙马王堆3号墓出土彗星图
由以上的脉络来看,除了有继承自汉以前于墓葬中绘制天文图的传统外,汉代墓室中之所以大量出现与“天文”相关的画像,其或更源自汉代天文学的高度发展,因而更扩充了汉代人对天文的知识/思想视野,于是两汉时期的人们便可以从这些相关的天文学知识中汲取相关的“思想资源”,而成为汉代墓室天象图中所表现内容与题材的参考或依据。
神话与天文知识建构
虽然,汉代天文知识的发展提供了两汉时期人们在绘制墓室天文图的思想资源,而促成汉代墓室中出现了不少具象、甚或科学性的星图。然而,较为特别的是,由以上的整理可知,这些墓室中表现日、月、星辰及特殊天象的画像,往往并非是真实、客观、准确地再现天空的科学性描绘,反而较多地是一种以古典神话内容结合人文想象的表现。
如在大多的汉代墓葬艺术中,日中有时绘有金乌;月中有时绘有蟾蜍、玉兔或桂树。而各星宿也经常以神话式的构图来表示。以西安交通大学壁画墓墓顶的天象图为例,除了在分列南北的日、月轮中出现有金乌、蟾蜍、作奔跑状的兔子外,月之外所绘由两个巨大的同心圆组成的环带内所布列的二十八宿,每个星座几乎都配着一个人物或动物。星图作者将天文知识与神话传说作巧妙地结合,将各个星宿融于相关的人物、动物之中,如跽坐人持箕、人牵牛、豺啄、双角猫头鹰、猎人网兔、须女等[44]。

此外,关于“奎”宿,西安交通大学汉墓顶壁画中的奎宿则绘一奔跑的猪。按《史记·天官书》载:“奎曰封豕,为沟渎。”而同时与正义中所云的“奎,天之府库,一曰天豕,亦曰封豕”[45]相印证,可知奎是天上的府库,府库中所贮为天豕。由此图的奎宿,更可理解《史记·天官书》之意,以及汉代流行的相关说法。至于“鬼”宿,按《史记·天官书》载:“舆鬼,鬼祠事;中白者为质。”[46]同样,在曾侯乙墓漆箱盖上亦有“舆鬼”之星名。然何谓舆鬼?过去不知所以。而西安交通大学汉墓的天象图却可以提供我们理解的讯息,壁画中鬼宿绘着两人抬着一个板形舆,舆中有一个似人而非人的鬼,这可能是因为以肉眼观测时,鬼宿星团类似星云状的天体[47],故古代中国人认为似“鬼气”。这幅天象图可说是舆鬼的最佳解释。
除了西安交通大学的墓顶天象图外,在山东嘉祥武开明墓石祠画像中,也出现了以驾着由七星组成的魁状车出行的北斗;及以六童子拽鼓车,车上坐一执槌击鼓状神人的雷神出行图。形象的风吹动神人象征风伯,执鞭及斧者象征雷神,抱瓿倒水象征雨师,与作钻下击披发跪伏者象征电母……这类以神话形象表现天文现象的画像[48]。
由此可知,汉代画像的创作者经常以神话或人物形象来表现日、月、星辰及天文的现象。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现象,或与两汉时期一般俗民大众对天文认识的局限有关。固然,天文的知识增进了两汉时期人们对天文的理解,并提供了更多对于构拟“天文”图像的素材,然科学性的星图可能未必为一般俗民大众所理解与认知,因而出现了神话式的天空。
但若从王充于《论衡》中对儒者以为日中有乌、月中有蟾兔说法的批驳,以及如洛阳烧沟61号墓顶壁画(图14)[49]等西汉至新莽时期的壁画墓中,已出现大量具科学性星图的画像来看,或正如夏鼐所言:“我们这些星图的描绘者,不会自己便是一个天文学者,他大概是根据一个蓝本,‘依样画葫芦’。因此,在描摹时,可能在某些方面走了样……”[50]而这些“蓝本”的创制者,必然对天文的观测已有一定的水准。若果如是,则可进一步推论,天文知识的不足,可能并非两汉时期墓室画像习以神话表现天文形象的主要原因。

图14 洛阳烧沟61号墓顶壁画·日月星象线描图
由前面的讨论可知汉代天文学的高度发展,因而更扩充了汉代人对天文的知识∕思想视野,然而,对一般非天文学的研究者来说,天文的内容是充满着熟悉而又陌生的文化认知。因此,如何去表现这些新的知识与观念则将是一大挑战。
黄敏兰在探讨中国古代史时,发现有所谓的“故事现象”:
即在皇帝、官僚的政治、行政、法律以及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大至改朝换代,或决定政事、职官、礼仪等诸种事务,常常要引用故事作为其行为的依据,而使之具合法性。我们称这种现象为“故事现象”。所谓故事,是指曾经发生过的事情或曾经实行过的制度。故事一经后世人模仿、实行,就成为一种合法的规范和制度[51]。黄敏兰并指出:“故事制度由于具有判例法和习惯法的特征和作用,可以起到补充成文法的作用,所以当人们的某些行动明显地缺乏成文法或法定制度的依据时,他往往就寻找故事作为合法依据。”[52]
自古以来,尤其在文字尚未发明或普及以前,人类的历史与知识本即多源自“口传”。虽然,在两汉时期已发展出一定的文明,然而,当面对不可确知或不甚熟悉的事物时,人们或仍多取法于一些传闻、旧说。而邢义田从许多汉代的典籍史中发现,汉代人在日常行政时,常有以所谓“如故事”、“自有故事”的“故事”来决断事宜。而在汉人的措辞中,故事又可称为“旧事”、“旧制”、“旧典”、“旧章”、“旧仪”、“典故”、“古典”、“典常”、“前制”、“汉典旧事”、“先祖法度”、“祖宗典故”、“祖宗故事”、“国家故事”,或仅称之为“旧”。即凡经典与汉制皆可称为“故事”[53]。
因此,或正如汉代的“故事现象”,两汉时期的人们在无法为天文特征找到为人们所理解的说解依据时,这些形象化的人、物或神话情节,可以作为人们“巧譬善喻”的工具,而其所具有的特征和习惯性思考作用,也可以提供人们在寻找合法依据时的某些资源。因此,两汉时期的人们多以传统神话或传说来作为表现“天文”的一种方式,其主要的原因可能是为大家所熟知的神话故事,即人们所熟悉的“日中有乌”、“月中有蟾、兔、桂树”,以及牛郎织女等神话故事的内容,可能更是表现意象、传播天文知识最好的手段。其在当时所能提供的理解,较之深奥难懂的天文哲理,将更浅显易懂,更能散布广远。故这一类被当成“知识”的神话传说,它们的社会功能便在于以人们熟悉且相信的“真实”,来合理化一些本土知识。
结 语
综上可知,汉代墓室中这些融科学、现实、想象为一体的天文图像,除了有受到汉代天文学知识的启发外,其内容或亦有受到当时人们对相关天文现象的理解、想象,甚或口头传说的影响,而出现了与相关载籍不同的表现。故早在1983年谢柏轲便曾指出:
我们真能相信如此精工细作、天衣无缝的画面是以如此散漫不一的文献材料为背景创作的吗——一个形象来自这个文献,另一个形象来自那个文献?难道它的来源必然是文献或仅仅只是文献,而没有口头传统和非文字性行为、艺术行为和灵感的作用?[54]
在现代性的语境或科学语境的话语中,“科学”与“神话传说”之间的区别似乎就是“真理”与“虚构”之间的差别。长久以来,人们大多把神话传说视为荒谬、杜撰以及不可信的同义语,并把它与科学对立起来。然事实上,世界上许多民族的早期天文科学的发展,原本源自早期人们以物候变化定季节、因“观象授时”的需求,而有的想象与理解。只是到了后来,天文知识或成为皇权的象征,为统治阶级所垄断,因而渐成为专门的知识。故在探讨相关知识的来源时,实不可忽略如神话、传说这类源自民间的知识系统。
注释:
[1] 冯时:《中国天文考古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343页。
[2] 如在1978年于湖北省随县擂鼓墩发掘的战国早期(约公元前433年)曾侯乙墓一漆箱盖上,便出现了中央绘有篆文粗体的“斗”字,以表示北斗,而周围环书二十八宿和四象绘的星象图。湖北省博物馆:《曾侯乙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年;湖北省博物馆等:《湖北随州擂鼓墩二号墓发掘简报》,《文物》1979年第7期,第1~14页。同样,在1987年和1988年于河南濮阳西水坡仰韶文化遗址所发掘、距今6500年前左右的45号墓,墓中墓主人遗骸的两侧,除有白色蚌壳精心摆饰与人身约同等大小的龙与虎外,墓主头顶上方还有用蚌壳摆塑成的北斗七星。而这样的结构,似又与曾侯乙墓漆箱盖的星象图相似,故相关的研究者认为这样的安排,并非古人随意为之,可能是一种具观象授时作用的星象图。此墓据考古和碳14测定墓葬的年代在距今6500年前左右。参濮阳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濮阳市博物馆、濮阳市文物工作队:《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3期,第1~6页;濮阳西水坡遗址考古队:《1988年濮阳西水坡遗址发掘报告》,《考古》1989年第12期,第1057~1066页。
[3] 考中国古籍中最早使用“天文”一词者,似为《易·彖传·贲》的“观乎天文,以察时变”。于此,“天文”一词实指天之文理。又据《淮南子·天文训》称:“文者,象也。”故在两汉时期,“天文”一词,殆指“天象”或“天空的现象”,而并非现代自然科学中以研究天体的分布、运动、位置、状态、结构、组成、性质及起源和演化的学问。
[4] 如周到:《南阳汉画像石中的几幅天文图》,《考古》1975年第1期;吴曾德、周到:《南阳汉画像石的神话与天文》,《郑州大学学报》1978年第4期;长山等:《汉墓中的珍贵彗星图》,《解放日报》1982年1月5日等。
[5] 据王思礼的研究,今天山东金乡的老石工并不识字,须等待别人写好字后再刻,否则榜题也是空着。见王氏著:《从莒县东莞画像石中的七女图释武氏祠“水陆攻战图”》,《莒县文史》1999年第10期,第214页。
[6] 邢义田:《格套、榜题、文献与画像解读——以一个失传的“七女为父报仇”汉画故事为例》,邢义田主编:《第三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中世纪以前的地域文化、宗教与艺术》,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02年,第218页。
[7] Wu Hung,MonumentalityinEarlyChineseArtandArchitecture,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189-250; Martins J. Powers,ArtandPoliticalExpressioninEarlyChina,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1,pp.1-30.
[8] 大传统与小传统(Great Tradition and Little Tradition)是美国人类学家罗伯特·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在1956年出版的《乡民社会与文化:一位人类学家对文明之研究》(Peasant Society and Culture: an Anthropological Approach to Civilization)一书中提出的概念,借以说明乡民社会中存在的两种不同文化传统。雷德菲尔德研究拉丁美洲的乡民社会时,认为乡民社会中存在两种不同的文化传统:一种是由国家与住在城镇的士绅与市民们所掌握、书写的文化传统;另一种存在于乡村之中,乡民借由口传等方式流传的大众文化传统。他主张,由于乡民具有两种性质:对于土地的热爱与追求(不只是利益,还包含熟悉度、亲切感与价值判断等)促使他们愿意以祖先的方式依附土地度过一生,但另一方面,他们却不同于与世隔绝的部落社会,必须与邻近城镇的居民打交道,接受外在社会的新事物的引入或影响。因此,大传统与小传统间借由士绅与乡民这两者相互依赖,构成整个乡民社会的文化传统。
[9] 湖南省博物馆等:《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73年,第6页。关于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帛画的图像结构方面,有两种看法:多数学者认为画面分为三个部分,但也有学者认为应可分为四个部分。然而基本上各家学者皆以为华盖以上代表“天界”,有日、月、升龙及天门。而代表天界的最上层部分,右上方绘一太阳,日中有阳乌;左上方则是一弯镰刀形的白色月亮,月上绘有一只大蟾蜍和一只体积较小的兔子,两旁缭绕着云气。
[10] 湖南省博物馆:《长沙马王堆二、三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4年第7期,第40、44页;彩色图版、黑白图版4。
[11] 临沂博物馆:《山东临沂金雀山九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7年第11期,第25~26页。
[12] 洛阳博物馆:《洛阳西汉卜千秋壁画墓发掘简报》,《文物》1977年第6期,第25~26页。
[13] 韩连武:《南阳汉画像石星图研究》,《南阳师专学报》1982年3期,第105~112页。
[14] 中国画像石全集编辑委员会主编:《中国画像石全集6·河南汉画像石》,郑州:河南美术出版社,2006年,图一一O,第85页。
[15] 韩玉祥、李陈广主编;南阳汉画馆编:《南阳汉代画像石墓》,郑州:河南美术出版社,1998年,图10,第128~130页。
[16] 韩玉祥、李陈广主编;南阳汉画馆编:《南阳汉代画像石墓》,郑州:河南美术出版社,1998年,图9,第130页。
[17] 中国画像石全集编辑委员会主编:《中国画像石全集6·河南汉画像石》,郑州:河南美术出版社,2006年,图一一六,第91页。
[18] (汉)司马迁撰;(刘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杨家骆主编:《新校本史记》,卷二十七,《天官书第五》,第1306页。
[19] (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杨家骆主编:《新校本汉书》,卷二十六,《天官书第六》,第1278页。
[20] 中国画像石全集编辑委员会主编:《中国画像石全集6·河南汉画像石》,郑州:河南美术出版社,2006年,图一二八,第192页。
[21] 经文献考证,此为西汉御史大夫、太子太傅萧望之墓。墓中天象图是迄今为止所知的中国最早的二十八宿古天象图。如此完整又比较科学的天象图在我国尚属首次发现,这一发现为研究中国古代天文史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实物资料,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其绘画的运笔、色彩均具特色,艺术手法高超,形态变化万千,也为研究汉代绘画提供了新的具体资料。陕西考古研究所、西安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西汉壁画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90年第4期,第57~63页。陕西考古研究所、西安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西汉壁画墓》,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1991年。
[22] 罗哲文:《孝堂山郭氏墓祠堂》,《文物》1961年第4、5期合刊。图版采自中国画像石全集编辑委员会主编:《中国画像石全集1·山东汉画像石》,济南、郑州:山东美术出版社、河南美术出版社,2000年,图四七,第27页。
[23] 《中国画像石全集》作者以为是为“织女”。但周到等先生认为应是北宫玄武中的“女宿”。吴曾德、周到:《南阳汉画像石中的神话与天文》,《郑州大学学报》1978年第4期,第86~87页。
[24] 中国画像石全集编辑委员会主编:《中国画像石全集6·河南汉画像石》,郑州:河南美术出版社,2006年,图一一O说明,第85页。
[25] 中国画像石全集编辑委员会主编:《中国画像石全集6·河南汉画像石》,郑州:河南美术出版社,2006年,图一六O,第131页。
[26] 吴曾德:《汉代画像石》,台北市:丹青图书,1986年,第67~68页。
[27] 汉代史籍对日月食有多次记录,且较详细。如《汉书·五行志》中记载了发生在汉武帝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的一次日食:“征和四年八月辛酉晦,日月食之,不尽如钩,在亢二度,哺时食从西北,日下哺时复。”又《西汉会要》载:“凡汉著纪十二世、百一十二年,日食五十三起”。
[28] 张衡《灵宪》曰:“月光生于日所照,魄生于日之所蔽。当之则光盈,就日则光尽也……当日之冲,光常不合者,蔽于地也,是谓‘虚’。在星则星微,遇月则月食。”对月食的成因作了正确的解释。
[29] 《中国画像石全集·河南汉画像石》作者认为,ㄩ形星座为简化的“天庙”星座。中国画像石全集编辑委员会主编:《中国画像石全集6·河南汉画像石》,郑州:河南美术出版社,2006年,图一四八,第120页。
[30] 中国画像石全集编辑委员会主编:《中国画像石全集·河南汉画像石》,郑州:河南美术出版社,2006年,图一四八说明,第120页。
[31] 其中如《汉书·五行志》中便对公元89年5月29日的一次日食有这样的记载:“征和四年八月辛酉晦,日月食之,不尽如钩,在亢二度,哺时食从西北,日下哺时复。”又《西汉会要》亦载有:“凡汉著纪十二世、百一十二年,日食五十三起。”汉代人不仅对日、月食作了记录,而且对它们的成因也有所认识。据张衡《灵宪》载:“月光生于日所照,魄生于日之所蔽。当之则光盈,就日则光尽也……当日之冲,光常不合者,蔽于地也,是谓‘虚’。在星则星微,遇月则月食。”
[32] 此说最早为日人山本清一所主张,转引自〔日〕出石诚彥:《上代中國の日と月との說話について》,收入出氏著:《中國神話傳說の研究》,中央公论社,昭和十八年,第76~77页。后来受到许多近世学者的认同,如刘城淮也颇赞同此一说法,并以甘肃临洮村辛店文化遗址中出土的一只彩陶罐为证,认为罐上太阳纹中的一黑点,正是代表着太阳黑子。参刘城淮:《中国上古神话》,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第163页。此外,如何新、萧兵、何星亮、鲁惟一(Michael Loewe, 1922— )也认为这是古人观测到“太阳黑子”的现象。参何新:《诸神的起源:中国远古神话与历史》,台北:木铎出版社,1987年,第97~98页。萧兵:《楚辞与神话》,江苏: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4月,第54页。何星亮:《中国自然神与自然崇拜》,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第169~170页。Michael Loewe,WaystoParadise:TheChineseQuestImmortality,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1979, p.128.
[33] (清)严可均校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后汉文》,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卷五十五,《张衡四·灵宪》。
[34] 汉代对五星的观测非常精密,无论三统历、四分历、乾象历等所测的五星行度和会合周期,都与今日所测之值相差不远,而四分历所测水星的会合周期为115.87日,几乎和今日之值完全一致。
[35] 《南阳汉代画像石》,唐河针织厂014。
[36] 中国画像石全集编辑委员会主编:《中国画像石全集6·河南汉画像石》,郑州:河南美术出版社,2006年,图一一二,第87页。
[37] 南阳地区文物工作队、南阳县文化馆:《河南南阳县十里铺画像石墓》,《文物》1986年第4期,第48~63页。
[38] 中国画像石全集编辑委员会主编:《中国画像石全集6·河南汉画像石》,郑州:河南美术出版社,2006年,图一四八,第120页。
[39] 中国画像石全集编辑委员会主编:《中国画像石全集6·河南汉画像石》,郑州:河南美术出版社,2006年,图一一二,第87页。
[40] 韩玉祥、李陈广主编;南阳汉画像馆编:《南阳汉代画像石墓》,郑州:河南美术出版社,1998年,第85页。
[41] 《史记·天官书》中有多处对“客星出”、“客星入”、“客星守之”的记载。参(汉)司马迁撰;(刘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杨家骆主编:《新校本史记》,卷二十七,《天官书第五》,第1295~1351页。
[42] (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新校本汉书》,卷二十六,《天文志第六》,第1305页。
[43] 这幅图席宗泽、顾铁符称为〈天文气象杂占〉,参顾铁符:《马王堆帛书〈天文气象杂占〉内容简述》,《文物》1978年第2期,第1~4页。顾铁符:《马王堆帛书〈天文气象杂占〉》,收入顾铁符:《夕阳刍稿》,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88年,第202~231页。
[44] 陕西考古研究所、西安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西汉壁画墓》,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1991年。
[45] (汉)司马迁撰;(刘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引;(唐)张守节正义;杨家骆主编:《新校本史记》,卷二十七,《天官书第五》,第1305页。
[46] (汉)司马迁撰;(刘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引;(唐)张守节正义;杨家骆主编:《新校本史记》,卷二十七,《天官书第五》,第1302页。
[47] 由于鬼宿外观类似蜂巢,故在西方也被称为“蜂巢星团”,是一个位于巨蟹座的疏散星团。
[48]中国画像石全集编辑委员会主编:《中国画像石全集1·山东汉画像石一》,济南:山东美术出版社,2000年,图七三,第49页。
[49] 1957年在河南洛阳市西北角城外的洛阳烧沟61号墓,在墓室顶的壁画中便发现了一幅日月星象图。这幅日月星象图以彩色描绘在12块长方砖上,由东而西的第1块是太阳,中有金乌;第7块是月亮兼星象,月中有蟾蜍及一只奔跑的兔子,其余10幅都是星象图。这些星象图都是用白粉涂地,然后用朱、墨二色绘有流云,用朱色圆点绘出星辰(图14)。夏鼐、李发林等学者曾为此图的各星点、星宿之可能名称作过相关的讨论。洛阳区考古发掘队:《洛阳烧沟汉墓》,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年,第40页。夏鼐以为这些星点分别代表“中宫”的北斗及与其有关的“五车”和“贯索”;然后是二十八宿中东方的心、房;西方的毕、卯、参;北方的虚、危;南方的柳、鬼(或轸)等九宿,并插入了河鼓及与其有关的旗星和织女。因此,这可能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幅星象图。夏鼐:《洛阳西汉壁画墓中的星象图》,《考古》1965年第2期,第80~90页;李发林:《洛阳西汉壁画墓星象图新探》,《中原文物》1987年特刊《洛阳古墓博物馆》创刊号,第153~162页。
[50] 夏鼐:《洛阳西汉壁画墓中的星象图》,《考古》1965年第2期,第81页。
[51] 黄敏兰:《论中国古代故事现象的产生》,《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1期,第73页。
[52] 黄敏兰:《论中国古代故事现象的产生》,《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1期,第73~74页。
[53] 邢义田:《汉代“故事”考述》,收入许倬云等著:《劳贞一先生八秩荣庆论文集》,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371~423页。
[54] J. Silbergeld, “Mawangdui, Excavated Materials and Transmitted Texts: A Cautionary Note,”EarlyChina8(1982-83),p.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