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梦学习
2011-10-16刘亮程
刘亮程
向梦学习
刘亮程
谁教会了我做梦。
据说孩子一出生就会做梦,甚至在母腹中便做了无数的梦。在我不会说话走路的幼年,一个一个的梦,在小小的头脑里发生。我最早开始做的一件事情,应该是做梦。不知道那些梦从哪来,谁给了我。我的头脑在白天黑夜的睡梦中,生长。大人知道我做梦,我睡着时突然地笑、哭。我笑时大人也笑,但不出声。知道我做好梦了。做不好的梦时,我会惊恐,大人看见了就叫醒我。
很难知道一个婴儿梦中的情景,他还没学会说话,却已经在做梦了。梦中是否说了话,那些梦话又是一种什么语言。
据说平常人能记住7岁时的梦。作家可记住3到5岁时的梦。有天赋的作家能记得自己出生时的经历。极具天赋的作家甚至能记住在母腹中的情景。那像梦一样的胎儿生活,如果真记住的了,该多有意思。漫漫的十个月,独自蜷缩在小小孕室,外面是一个声音的世界。眼睛闭住,耳朵张开,小拳头攥紧。独自倾听冥想的姿势。他听到的声音有颜色吗,能构成一个怎样的人世。
有一点我还不太清楚,在母腹中胎儿时睡时醒呢,还是一直在睡梦中。一个长梦做到出生。
梦是一种学习。很早的时候,我一定通过梦熟悉了生活。或者,梦给我做出了一种生活。后来,真正的生活开始了。我出生,成长。梦渐渐隐退到背后。早年的梦多被忘记。
还是有人记住一种叫梦的生活。他们成了作家。
作家是在暗夜里独自长成的一种人,接受夜和梦的教育。梦是一所学校。夜夜必修的功课是做梦。
我早期的诗和散文,一直在努力地写出梦景。作文如做梦。在犹如做梦的写作状态中,文字的意味向虚幻、恍惚和不可捉摸的真实飘移,我时而入梦,时而醒来说梦。梦和黑夜的氛围缠绕不散。我沉迷于这样的幻想。写作亦如暗夜中打捞,沉入遗忘的事物被唤醒。
梦是我的启蒙老师。我早年的写作一定向梦学习了许多,我却浑然不知。
早年经常做的一个梦:我走进一间挨一间的房子,那些房子破旧、空荡、布满灰尘,每一间我都熟悉,仿佛在里面居住过,我从一扇门走进另一扇门,一夜都走不出去。
另一个梦里我在钻洞,一个曲折漫长的洞,我熟悉里面的每个拐弯和岔道,我从没走错却从没走出过。
有一段时间我梦见自己在爬一个高塔,仿佛已经爬过无数次,每次快爬到顶了,醒过来。多年后我带母亲回甘肃老家,在金塔县城,突然看见我梦中爬过无数次的高塔,我在塔下愣愣地站了好久,第一次清醒地看见一个早年的梦景。那是母亲逃荒到新疆40年后第一次回老家,当年她在甘肃金塔县怀孕,在腹中把我带到遥远的新疆,后来,我在新疆沙湾县出生。我有两个故乡。那个夜夜梦见的高塔是父母早年的念叨被我记住了呢,还是,我在孕育中早早看见了它。
另一个梦中我长途跋涉去一座城市,城市北边有一个破煤矿,路拐弯处是一片楼房,每次我都回到一幢未完工楼房的5楼,不知道那是谁的家,我在那里寂静地住下来。也是好多年后,我在乌鲁木齐南湖小区5层的住宅里,突然想起早年在乡下的梦。离这不远是已经废弃的六道湾煤矿,梦中的场景和现实惊人相似。似乎我的一部分生活,突然地掉进早年做好的一个梦里。
更多的梦中我跑着跑着飞起来。就在昨晚的梦中,我又一次飞了起来,脚下是大片的夏天的绿色玉米地。
不知道那些反反复复的梦,要告诉我什么。我因为不理解也许早已错过了什么。做梦似乎是天生的,不需要向谁学习。我的写作,却一直在向梦学习。
我不知道自己一直向梦学习。我很早就懂得隐喻、夸张、跳跃、倒叙、插叙、独白这些作文手法。后来,我写作了多年,才意识到,这些在文学写作中常用的手法,在梦中随处使用。做梦用的手法跟作文一模一样。
隐喻作为一种文学手法,很可能是作家从梦中学来的。所有的梦都有隐喻性、多解性。早晨醒来回想梦,一如阅读深奥晦涩的文学。梦充满隐喻,令人费解。人相信梦的暗示,千方求解,并大致找到了梦隐喻的规律。比如梦见小孩是遇到小人,梦见火要发财,梦见飞是长个子等等。一些复杂的梦需要专门的人解读,回想梦的过程是文学欣赏的过程。破译梦便上升到文学研究了。
梦的多义性是文学的重要特征。我写一个句子时,希望语言的意义朝无数个方向延伸,在它的主指之外有无限的旁指,延伸向远方。这也是梦的特征。
梦呓、梦话也叫胡话。说胡话。一个已经睡着不该说话的人说的话。突兀的一两句。没前没后。自言自语。他对着梦说话,我们看不见他的梦。
最好的文学语言是梦语言。
梦呓被多少文学家借鉴发展为超现实的语言叙述方式。
梦是夸张的。梦的夸张体现在敏感。一只蚊子飞过耳旁,梦会夸张成一架飞机。一个关于飞机的梦,就这样从一只蚊子飞过耳旁开始了。许多宏大的文学作品可能起源于一个小小的诱因。
梦中的故事常常跳跃,一念间从一个场景跳到另一场景。有时似乎跳跃得跑题了,醒来一想,此梦的主题恰好在离题万里的细节上。
有些梦是倒叙,先有果,后有因,故事逆着时间朝前发生。我突然回到了童年。回到童年的梦都是倒叙。梦应用倒叙非常顺便。因为梦里的时间是一种可以悬置、翻转、倒退、仰俯、伸缩自如的文学时间。
插叙是梦中惯用的手法,一个平铺直叙的梦,常有莫名其妙的故事插入。有时中途插入的故事成了梦的主题,旁枝长成主干。好像也没什么不合理。梦自有合理性。
伏笔更是被梦用到极致。经常在一个新梦里感觉到熟悉的气息,仿佛先前经历,或许这事在旧时的梦里开了头,略微显露了一下,此梦牵出彼梦的头绪来,甚至几十年前埋的伏笔,都牵连出来。
不知道人一生的梦是否在完成着一个巨大的梦。就像作家耗尽毕生写一部巨著。如果是的话,胎儿时的梦,童年的梦,中年老年的梦,便都连接起来了。那将是一个多么大的梦巨作。梦有压缩性,几十年的时间,可以压缩到瞬间。据说生命终结时,人一生的故事在脑海中梦一般回放。这是生命程序中最美妙的一瞬,一部人生巨作已然结尾,前呼后应地做一次回味。
这个始于梦终于梦的做梦动物,中间那一阵子时梦时醒的人世生活,是多么地令自己回味。那压缩在短短时空里的整个此生,将带往彼世。
作家干的是装订梦境的活。在梦中学会各种各样的文学表达,把各种各样的梦变成文字。许多作家天生会写作,几乎不怎么经过向别的作家学习的过程,梦早已教会他所有的文学写作方法。进入写作时,真实世界隐退了。虚构世界梦一般浮现。文字活跃起来。文字在捕捉。在塑造编造这个世界。唯一存在的是文字。一个文字中的世界,和现实的关系,就是一场梦的关系。也是此生彼世的关系。
文学是梦学。
《一个人的村庄》是一个人的无边白日梦,那个无所事事游逛在乡村的闲人,是我在梦里找到的一个人物。我很早注意到,在梦里我比梦外悠闲,我背着手,看着一些事情发生,我像个局外人。我塑造了一个自己,照着他的样子生活,想事情。我将他带到童年,让他从我的小时候开始,看见我的童年梦。写作之初,我并不完全知道这场写作的意义。我只清楚,回忆和做梦一样,纯属虚构。
写作就是对生活中那些根本没有过的事情的真切回忆。
我无知地知道这些写作规则。不然我不会从童年写起。我的童年遇到了不幸。父亲在我8岁时死去,那是“文革”后期,母亲带着5个孩子艰苦度日,我是家里的老二,我大哥那时12岁,最小的妹妹不满1岁。这样的童年谁愿意回忆。可是,《一个人的村庄》里看不到这些苦难,《虚土》中也看不到。当我在写作中回到小时候的村庄,这些苦难被我忘记了,我写了这个村庄的草木和动物,写了风、夜晚、月光和梦,写我一个人的孤独和快乐、希望和失望,还有无边无际的冥想,当那本书完成时,我发现我的童年被成功地修改了,我把那个8岁丧父的自己从童年的苦海中救了出来,我给自己创造了一个童年。我感谢我的文字,它拯救了我。
写作是一个创造自己的过程。我塑造了一个主人公。他却改变了我。
《虚土》是我的另一场梦。在那个叫虚土庄的地方,梦把天空顶高,把大地变得更加辽阔。每个人都活在别人不知道的梦里。梦是我不知道的另一种生活。梦乡是我遗忘的故乡。照耀着梦的是无边的星光月光。
《虚土》里那个5岁孩子,一直在一个未醒来的梦里,怀疑自己是否出生,或者已经出生却从未长大。长大的全是别人。我的生活早已被别人过掉,废墟一样弃在荒野。我又在过着谁的生活。在那个漫长的梦里,一个人的百年岁月开花了。
到《凿空》时,我被一个地方的现实撞醒,写了这本书。好在这里的生活,本来就有一种不用刻意营造的魔幻味道。一个地方的真实生活,也许在别处的人看来,就是荒诞的梦。《凿空》是一部醒来的书,写一个聋子耳朵里的声音世界。全是过去的声音。那个孤独的倾听者,耳朵闭住,眼睛张开,清醒地看着这个在母腹中曾经听到的外面世界。
梦启迪了文学,文学又教会更多的人做梦。优秀的文学都是一场梦。人们遗忘的梦,习以为常却从未说出的梦,未做过的梦,呈现在文学中。文学艺术是造梦术。写作是一件繁复却有意思的修梦工程。用现实材料,修复破损的梦。又用梦中材料,修复破损的现实。不厌其烦地把现实带进梦境,又把梦带回现实。
那个在母腹中偷听人世做了无数梦的未来人,是一个作家原型。作家孤独如母腹中的孩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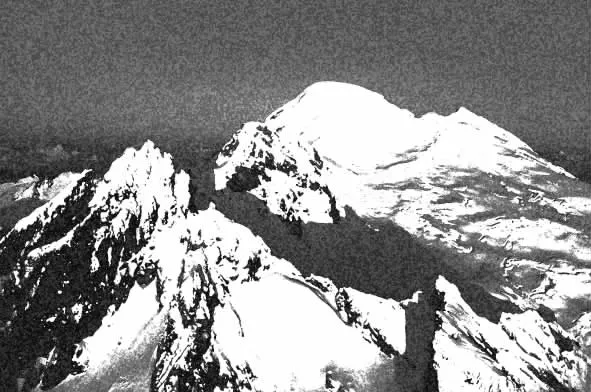

刘亮程
刘亮程,新疆沙湾县人。著有诗集《晒晒黄沙梁的太阳》,散文集《一个人的村庄》、《库车行》、《刘亮程散文》,及长篇小说《虚土》、《凿空》等。
曾获“冯牧文学奖”。
《寒风吹彻》、《今生今世的证据》等多篇散文选人全国中学及大学语文课本。《寒风吹彻》同时选人香港大学语文教材。
《凿空》入选《亚洲周刊》“2010十大长篇小说”。
现任职于新疆作家协会。

┝著名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