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多美,罗斯,我亲爱的罗斯:俄国风景画家列维坦素描
2011-10-13山西
/[山西]李 亮
1899年12月25日,伊萨克·伊里奇·列维坦来到其时俄罗斯南方滨海城市雅尔塔,探望正在那里疗养的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久别重逢,多年的友谊使他们自有说不完的话题。
一天傍晚,列维坦坐在壁炉对面的安乐椅上,而契诃夫则像往常那样,在书房里来回踱步。他说,看不到北方俄罗斯的大自然,让他很是寂寞。列维坦听了,对作家的妹妹玛丽亚·巴甫洛夫娜说:“玛莎,请您给我一块纸板。”她拿来一块硬纸板。列维坦把纸板裁成了需要的形状,按在壁炉上,只用一个半小时就完成了一幅油画,这就是著名的《黄昏中的草垛》。时逢“中国国际美术年”的1998年4月,这幅作品竟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美术馆,它就陈列在中厅。画幅不大,只有7.5cm×23cm,却为宽大的银灰色画框包围,在众多展品中极为夺目。画面上夕光隐去,黄昏来临,几垛干草似沉沉睡去,初月笼罩在升起的薄雾之中,一片昏暗里,透出宁静和感伤。它显示出画家成熟期作品的高度单纯,尤其是对总体氛围的把握表现了与契诃夫小说单纯、简洁与节制之审美取向的同一性。然而,与契诃夫不同,就其作品的精神内涵而言,列维坦通过对俄罗斯自然的广泛描绘,以风景画的形式,深刻地传达出19世纪后期的时代氛围,且以无言的忧伤、宁静的沉思呈现出对古罗斯土地淳朴、深挚的情怀,以及那种俄罗斯特有的深重的宗教式悲剧精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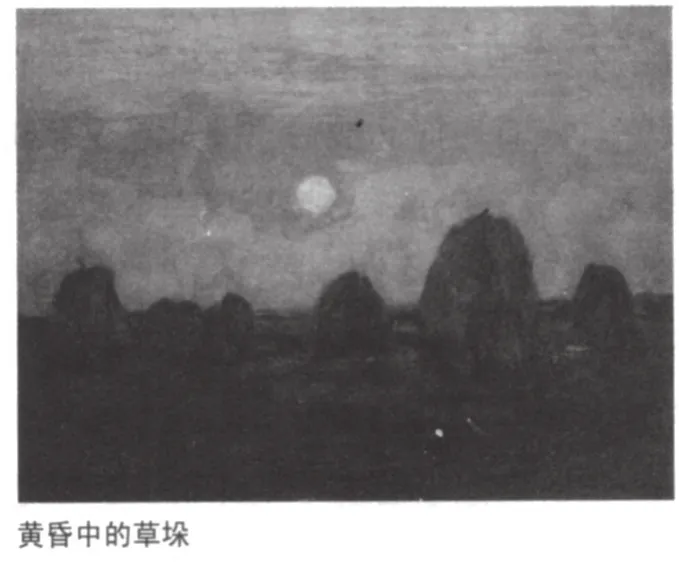
他有一副基督的形容
青瘦,黑色须发,脸形美丽而高贵,列维坦是犹太人,却具有西班牙——阿拉伯人最优雅的外表,相当忧郁的神色中似乎深藏着俄罗斯心灵中最隐秘的东西,当他用那双富于表情的黑眼睛瞧着你,特别是当他讲话的时候,就会流露出内心的温和、真挚和诚恳。在聆听女友库符申尼科娃为他弹奏贝多芬《月光奏鸣曲》的时候,列维坦常常会习惯地唉声叹气。
有一次和几位朋友旅行,他突然在田庄停了下来,像等待什么。这时莫斯科大剧院男高音歌手顿斯科依问道:“您在想什么?”“您看到了这块云吗?”列维坦指着天空,“它马上就要把太阳遮住,那时四周就要笼罩在半明半暗中,我就是等着看这个。”契诃夫在1896年12月21日的日记里写道:“列维坦患了主动脉扩张,胸上敷了黏土。绝妙的习作和燃烧般的生之欲望。”
有一年,画家波梁诺夫准备创作圣经题材的作品《基督与罪女》,正苦于找不到模特儿,忽然想到一个朋友,便找上门去,正是列维坦为他扮相画中基督的脸容。1893年冬,画家谢洛夫为列维坦画像。画中列维坦左臂横卧椅背,绝妙的手绻曲下垂,光亮突出的前额,黑色须发,些许倦容正衬出一双深沉忧伤的眼。其时列维坦三十三岁,正值创作的巅峰期。列维坦对自己的画像相当满意,他说:“谢洛夫是位了不起的画家,我相信,他画的这幅肖像,将来一定会挂在特列嘉柯夫绘画陈列馆里的。”他的话应验了。当后人在这一绘画馆参观时,惊奇地发现,谢洛夫的列维坦肖像,竟与伊万诺夫1835年的《基督显圣》、克拉姆斯科依1872年的《沙漠中的基督》两画中的基督,其形容颇有几分相似。这是俄罗斯宗教文化中的基督,深沉、凝重而忧伤,有别于西方那般惨烈。
俄罗斯的苦行僧
学生时代的列维坦,在给一位亲戚的信中说:“真对不起,我好久没有还你的钱。原因是我现在囊空如洗,穷到曾经一连三天没有午餐,我想不久就可以有钱了,那时必定奉还。”
1873年9月,十三岁的列维坦进入莫斯科绘画雕塑建筑专科学校之后,贫穷、饥饿、侮辱和委屈阴霾般无所不至地笼罩了他生活的一切角落。起初是因为缴不起学费遭到退学的威胁。继之是居无定所:只要方便,就在熟人或陌生人家里过夜;学校的更夫出于怜悯,让这个无家可归的孩子在自己的小屋旁过夜,用马车夫的坐垫给他当床铺;有时竟至钻进教室窗下的大木柜里,还顺便盖上几块木板,以免被人发觉,在那里度过漫长的冬夜。他每天只吃三戈比的伙食,或仅以一块小小的黑面包充饥……
1879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在索罗维耶夫遇刺,时风严酷,开始要犹太人迁出莫斯科。双亲早逝的列维坦兄弟姐妹四人,只得迁至莫城十五俄里以外的下新城附近,陷入极度贫困的境地。已经十九岁的列维坦竟没有一件体面的衣服,身着一件旧红色衬衫,破裤子,光脚穿一双破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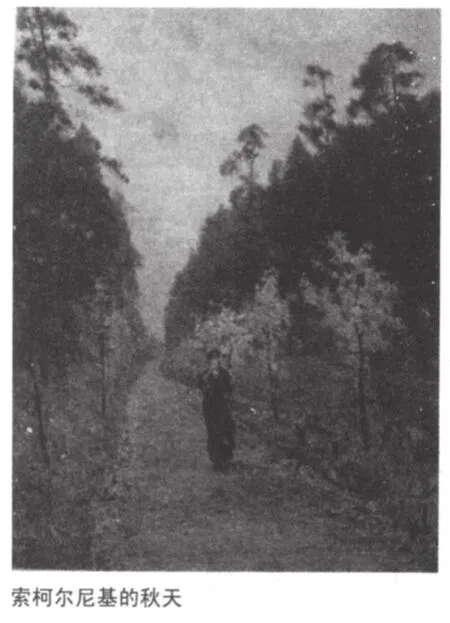
其实,同情和怜悯从来就是这个民族的良知。就在列维坦遭到退学威胁时,曾有人代他缴付学费,但画家始终不知道是谁。1879年,画家的勤奋和天资引起道尔果鲁科夫公爵的注意,终于将其列入奖学金名单。也就在这一年,他进入风景画家萨甫拉索夫的画室,名作《索柯尔尼基的秋天》正是在萨氏指导下完成。当初,列维坦因贫困几近绝望的时候,画家的姐姐曾去找特列嘉柯夫帮助,却遭到拒绝。这位收藏家说:“当列维坦画出一幅好画,我将同意购买,并会出一个好价钱。”这道理很简单:天才只需激励,而庸才则无须一顾。1880年1月,《索柯尔尼基的秋天》成为特列嘉柯夫购藏的列维坦第一幅作品。
贫穷是伟大天才的伴侣。“对于青年时期来说,唯有贫穷才算得上体面。”哲学家洛扎诺夫如是说。然而,贫穷终究给心灵蒙上了忧郁凄凉的阴影,以致成为一种情结。1885年4月,应契诃夫邀请,画家来到其所在附近的一个小村度假。有一次突然为忧郁侵袭,列维坦竟然在麦秸堆上开枪自杀,幸而没有击中。大约十年后,在写给他的医生蓝果沃依的信中,曾有如下陈述:“您是我的医生和好友,我可以向您吐露全部真情。忧郁症逼得我到了用枪自杀的地步。我还活着……这就是您的忠诚的仆人自我作践的结果。”看来他做这种蠢事已非一次。画家的好友契诃夫认为,这种情绪是某种病症,某种不是由外界引起的,而是人体内在的病症。据画家利普金回忆,列维坦有一次说:“在我们俄罗斯,绘画买不了房子,也许还会挨饿。”他去过列维坦的居室和卧房,“那种简朴到几乎像苦行僧般的陈设,使我感到惊异”。正是痛苦的生活,使列维坦画中充满如此的忧伤。尽管后来他成了教授,被授予院士,却仍不止一次地为救助饥饿的农民义卖画作,为救助穷困的学生慷慨解囊,并力所能及地帮助那些急需帮助的人。
1896年7月,列维坦在一封信中曾说:“我们是陷在绝望里,我们是堂·吉诃德,但还要比他不幸百倍。因为我们知道自己在跟风车作战,而他则不知道。”这位天才在其创作的盛期,面对俄罗斯的无边暗夜,在与命运的抗争中,呈现出一种可谓悲剧性的生命痉挛。1900年7月22日,列维坦终于大限来临,他死于严重的心脏病,只活了不到四十个年头。重病中,契诃夫等众多友人曾关怀备至。这一年,在巴黎的世界博览会俄罗斯艺术馆,列维坦的最后作品围上了黑纱。
深情的“农舍”系列
19世纪的俄罗斯是一个巨大的庄稼汉的王国,深为农奴制束缚,尽管1861年颁布了解放农奴的法令,但庄稼汉的苦难并无根本性的改变。敏感而多情的俄罗斯知识分子无不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为什么”、“怎么办”成为响彻整个19世纪俄罗斯文学艺术的主旋律。先是文学中的普希金、果戈理、车尔尼雪夫斯基,继之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列夫·托尔斯泰和契诃夫;在绘画领域,先有瓦西里·佩罗夫的《送葬》《三套马》,继之有巡回展览派发起人克拉姆斯科依,他曾以《沙漠中的基督》表现当时知识分子对时代的沉思,而列宾的《伏尔加河上的纤夫》和苏里科夫的《近卫军临刑的早晨》等作品,表现的也都是一些悲剧性的主题。其中深刻反映苦难题材的瓦西里·佩罗夫,乃是列维坦的校友。俄罗斯文化是苦难的文化,为真理而牺牲的文化。早在1842年,普希金在阅读《死魂灵》时就感叹道:“上帝就像我们俄罗斯一样忧伤。”哲学家别尔嘉耶夫认为:“这是整个19世纪所有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叹息。”

这就是画家列维坦置身其中的文化语境。
在风景画家列维坦的作品中,毕其一生是画之不尽的路、黄昏、夕晖、月夜,忧伤的树、沉凝的云、静静的河湾,以及五光十色的湖面。特别是那一幅又一幅寂静的农舍,空寂无人而又引人沉思,仿佛能听到充满忧伤的心灵诉说。据艺术史家格涅季奇回忆,有一次契诃夫曾说:“要是我有钱,我一定向列维坦买一幅‘农舍’,他那灰色的、可怜相的、孤单的、难看的,但却流露着难以言喻的和无以抗拒的魔力的,人们朝它看了又看的‘农舍’。”其实,“农舍”的创作,早在1877年,十七岁的列维坦已经有《黄昏》问世。画中一条泥泞坎坷的路,弯曲地通向远处晦暗的农舍,阴空重压下,只有低沉的为夕阳反照的云层。1883年又有《耕地上的黄昏》,那是一位俄罗斯老农,在辽阔的土地上,时至黄昏仍耕作不辍,人与马在夕照中犹如剪影。直到1900年画家去逝前的《月色黄昏》,沿围栏而上,仍是薄暮月色中沉睡的农舍。在俄语中,农民(Крестьянин)与基督徒(Хрестьянин)本为谐音。在列维坦画中反复出现的农舍,莫非是敏感的画家对农民无尽苦难的一种表达符号、一种良知的献祭、一种深情的倾诉,抑或把这种淳朴的美当做上帝来祈祷?俄罗斯哲学先驱恰达耶夫有一段“箴言”说得好:“自然界每一个对象的背后,都有着我们用智慧或想象放置进去的某种东西,这也就是艺术家应该在作品中再现的无形之物,因此,使我们感动、使我们激动的正是这种东西,而绝非我们所见的对象。”正如人的个体一样,俄罗斯民族的每一个个体,可以是一块泥土,可以是一片树叶,也可以是一缕阳光,或拂过白桦林树梢的一阵轻风,都是这民族的一个微粒,那是人在画中的无形存在。
淳朴的农舍毕生激动着画家的心灵,淳朴无华的风景只属于大画家,何况列维坦从来就无视所谓“美丽”的风景。
悲怆与辉煌之美的丰碑

19世纪90年代,是列维坦创作的高峰期,大型纪念碑式的作品相继涌现。1892年有《深渊旁》(150cm×209cm),其习作最初完成于一位男爵夫人领地的磨房附近。这是一个“祸地”:传说从前一位磨房主的女儿爱上一位马夫,但她父亲极力反对,竟然买通当局将马夫征去终身当兵,致使姑娘痛苦绝望,最终投渊自尽。在最后完成的作品中,这个民间传说促成了作品叙事的传奇色彩。画面中的板材和圆木表现出画家惊人的写实功力,幽深的树丛和投射于水中的暗影,显然酿造出某种神秘气氛,而画风的淳朴和总体氛围的把握,也充分传达出俄罗斯大自然的诗情之美。真正令人震惊的是同年完成的《弗拉基米尔公路》(79cm×123cm),这是一幅真正地老天荒而令人顿生绝望之感的作品。在铺天盖地的云空下,众多歧生的小路归于一条砾石错杂、行进艰难的大路,并最终消失在无尽的天边……据库符申尼科娃回忆:“我和列维坦走在旧的弗拉基米尔大道上,道路像一条白色长带;在远处可以看到两个女巡礼者的身影,一根倾斜的墓标带着被风雨侵蚀的圣像。这是古老时代的遗迹。”这就是从莫斯科经过弗拉基米尔城去西伯利亚的一条大道,帝俄时代流放犯人的必经之路。而“路”是俄罗斯文学艺术中被反复表现的重大主题,它与这片广大辽阔的土地和这个民族的苦难密切相关。列维坦说:“从前,沿着这条道路,有多少不幸的人,在镣铐声里走向西伯利亚……”一种深藏心底的哀伤使画面表达的寂静变得忧郁起来,灰色的天空也显出了愁惨,仿佛受难的、忍辱负重的俄罗斯灵魂布散在广袤无垠的大地上。列维坦研究专家费多罗夫-达维多夫甚至认为,画家在这里依据的是当时的现实和成为先进知识分子特征的那种国民感情,用纯风景画表达了丰富的社会思想,是一类历史风景画。同年,列维坦还作有《晚钟》(87cm×107.6cm),那是听到傍晚钟声的召唤,乘小船赶去河对岸的教堂做晚祷的信众,在夕阳的笼罩下,远处教堂的尖顶金光闪耀,宁静的自然在晚霞里弥漫着天国的声响。与此相关,此前还有《黄昏·金色的普寥斯》《雨后的普寥斯》《静静的修道院》《教堂秋色》,以及最后的《湖》等,概可视为“教堂系列”。那就是画中或远或近反复出现的东正教的教堂圆顶,不论晴天的灰蓝还是晚照中的金黄,那指向苍穹的十字架都是圣灵的召唤。作为自然的奥秘和画家的心灵,它所呈现的乃是与土地相联系的宗教意识。土地是俄罗斯民族最终的庇护者,土地就是人民。“谁喜欢俄罗斯人民,谁就不能不喜欢教堂;因为人民及其教堂是二者合一。而且只有在俄罗斯人那里,才是二者的合一。”洛扎诺夫的这些话,实在是道出了俄罗斯文化的精髓。


就此而言,画家1894年完成的《墓地上空》(150cm×206cm),又译《在永恒的寂静之上》,是画家终其一生,献给俄罗斯民族的一曲深沉宏伟的挽歌。画面下方是一个隆起的丘岗,若隐若现的小路通向一座简陋而饱历岁月风雨的小教堂,窗口一粒烛光依稀可见,倾圮散乱的墓石或十字架尽显人世的变易沧桑;而在教堂和墓地之间,是仍富生命的小小树丛,晚风拂过树梢,恍有亡灵飘动……这一切尽在高远的俯视之下。在浩大湖面之上的广阔天空,有巨大运行的云团,呈现一派奇幻、凝重甚至诡谲而变动不居的悲壮意味;一线负载夕照的云束如箭一般穿过巨大的云团,尽显生命的顽强、力度和迅疾的流逝,使原本虚幻的天空透出强劲的生命感;而人世生存的大地丘岗之一角却散发着浓重的死亡气息,消逝的生命已进入寂静中的永恒。人生是何等的短暂而无常!人生有限而宇宙无穷——这就是这支庄严宏伟的悲怆交响曲的主旨。它仿佛把《深渊旁》《弗拉基米尔公路》《晚钟》以至“农舍”系列中种种使画家心灵激动的情感聚拢起来融而为一,使民间传奇意义的、历史社会意义的和宗教意义的众多内涵集于一体。关于这幅作品,1894年5月18日,画家在给特列嘉柯夫信中有言:“整个的我,我的全部精神,我的全部内涵,都在这一幅当中了。”据画家女友回忆,此画的创作是在一个夏季的湖畔,全部画材均在一次溯流而上的旅行中得来,而教堂则在另一处;在作画的过程中,列维坦坚持女友为他弹奏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特别是其中的第二乐章“葬礼进行曲”。其实,就在画家创作此画的前一年,柴可夫斯基刚好完成其最后的作品第六交响曲《悲怆》。那第一乐章中铜管乐吹奏出的,旧时俄罗斯教堂为死者举行葬礼的挽歌《与圣者共安息》的旋律,自当更加切近《墓地上空》的悲剧性主旨。这幅画作创作于1893年至1894年,先有两幅素描稿《雷雨前》和《墓地》,后有一幅《墓地上空》的“习作”。在“习作”中,画面下方左侧有教堂的丘岗向右回旋而上,与湖中远处的一抹湖滩相连,形成一个不小的回形湖湾。这个湖湾定稿时被切掉,使湖面更为开阔;教堂前的十字架被后移,教堂与树丛的位置也有变动;云空中那一线为夕晖反照的云束则被延伸而更加突出。事实上,画家的许多作品几乎都经过速写、习作到定稿几个阶段,他始终以宗教般的敬业精神对待自己的作品。他的信条是:按照你所看到的自然,用心灵去过滤,把握总的色调氛围,捕捉对象的特征加以提炼,不迷恋细枝末节,尤其反对细描,力求简洁明快地去表现大自然的淳朴本色。画家一以贯之的这个创作纲领,在《墓地上空》中再一次得到完全的实现。
《湖·俄罗斯》(149cm×208cm)是可与《墓地上空》媲美的又一大型作品,创作于1899年至1900年。这时,留给画家的时间已经不多。如果后者是一曲挽歌,那么前者则是一首颂歌。它凝聚了画家一生全部的欢乐和期望——无论是《五月新绿》(1883)条栅后枝叶扶疏掩映的板屋,还是《三月》(1895)白雪消融中的春讯,抑或作于同年,让中国人永远记住了这位画家的《金色的秋天》(1895),以及意境清幽、绿荫如盖的《白桦林》(1885—1889),都洋溢着作者的欢欣、激动和心灵透出的亮色;而《林边草地》(1898),则更有浓荫绿树下的野花纷呈,使人如嗅其香,优美如一首抒情小诗;直到画家生命最后仍未完成的《收割干草》(1900),那在广阔秋田远处,布散的是众多男女农人欢快劳作的点点红白身影——成为画家对俄罗斯民族的最后牵挂。《湖·俄罗斯》从习作到完成有三幅(其中一幅习作1998年4月曾来中国展出,且被放大为“标牌”立于中国美术馆入口右侧)。据列维坦的学生利普金后来回忆:“他给我看了自己的一幅大草图《湖》说,‘这就是根据我在年初时给你们出的那个题目来画的,“暴风雨后残留的一片乌云”……为什么要用普希金的诗句来画呢,这是因为许多人,其中有比我们高明的人,都在学习普希金、莱蒙托夫,不过,有时候最好不要强使观众接受任何东西,而让他们自己去想。这个题目我画了很久,想把这幅画称为“罗斯”,不过这有一点儿妄自尊大了。无论如何还是谦虚一点的好。’”“罗斯”乃俄罗斯的古称,这确是一个宏大而严肃的主题。“画了很久,想称为‘罗斯’”,我们仿佛看到了画家那契诃夫般的谦逊而羞赧的面容,其情其意真有些语焉不详而言近旨远。在这最后完成的画面上真可谓一片璀璨:天空的云朵被强调,湖对岸远处的村庄、收割完毕的田畴、村庄里的教堂都一同映入大片湖水,得到精湛处理的倒影色彩错落,在晚霞明媚的秋日傍晚,呈现一派少有的灿烂辉煌,俄罗斯真正的高雅和华美。在这里,忧郁消失了,死亡更是绝无踪影;明朗的晚照中,天空和大地是一片宁静中节日般的欢快和幸福。这是理想的俄罗斯,俄罗斯的理想,古老罗斯的真正浪漫:“你多美,罗斯,我亲爱的罗斯……”这是其民族天才诗人叶赛宁,在十四年后的1914年,对这幅画作内涵的一个深情回应。在这幅画中,画家把他柔肠百结的全部情思都献给了祖国,献给了曾经忧郁、历经苦难、付出牺牲的俄罗斯大地。它无愧一首感人肺腑的华彩乐章,回肠荡气的节日颂歌。俄罗斯祖国在画家最后的一瞥中,呈现为节日般的辉煌,绽放出幸福的微笑。

人类困境中的审美精神
这是一位虔诚的巡礼者,在广阔无垠的大地上,向着远方,向着大自然之美,向着真和善,在历经风雨的精神磨难之后,终至于重睹圣迹。
1900年,在巴黎世界博览会的俄国艺术馆里,一位勤务兵默默地把黑纱围在列维坦最后的作品上,作为哀悼的标志。
当年,列维坦对他的学生利普金说过:“还是要更专心地坚持风景画,否则就只能仿照巴洛克,仿照文艺复兴时期给商人的家屋作画,迎合他们的兴趣。除非您为了赚钱,那就是又一回事了。”在人生的历程中,不仅有对一己利害的关顾,也有对自我生命体验的感受;为了摆脱有限自我的阴影,审美需要便成为沟通现实生命与自我超越之间的桥梁。这是人的一种发自内心的精神需求,它直接通向人类困境中的审美精神。读者诸君,如果认为列维坦不合时宜,观念陈旧,请不妨找来果戈理当年的一个短篇小说《肖像》一读。
“人们对列维坦的作品太不重视,太不珍惜了,这简直是耻辱。列维坦是一个伟大的、独树一帜的奇特的天才,他的作品多么清新而有力,本该引起一个变革的。是的,列维坦死得太早了,太早了。”这是大作家、画家的好友契诃夫对列维坦的最后评价。他们生于同年,毕生相知,死后墓穴同列,小说家也不过只比画家多活了四个年头。
当年,特列嘉柯夫每年都要为自己的陈列馆购买几幅列维坦的新作,现今俄罗斯国立特列嘉柯夫绘画陈列馆拥有最多最好的列维坦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