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苏小说四题
2011-10-08■严苏
■严 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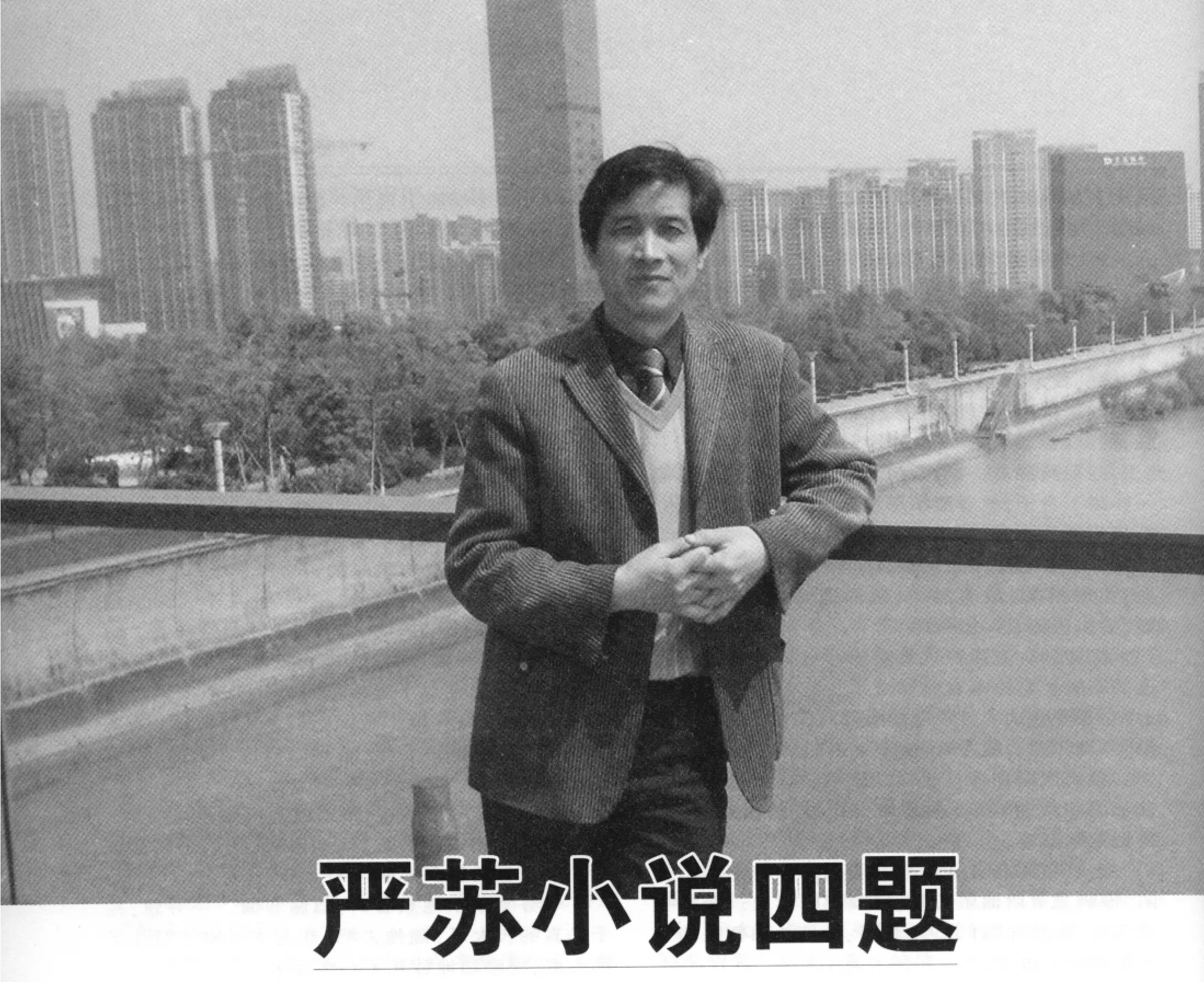
一字惹祸
今天与往日一样,太阳从东方冉冉升起,毋庸说,傍晚时分又将从西天徐徐落下——一天天,一月月,时光凝聚成岁月,人也就在这岁月中一天天长大,又一天天老去。
任老师55岁了,满打满算,还有五年就告老还乡,和妻儿团聚。任老师盼着这一天快点到来,又害怕这一天真的到来。盼,是因为他厌倦了这种走钢丝般的生活;怕,是因为他喜爱孩子,留恋校园,他不知他一旦离开校园,离开孩子,还能做些什么,活着是否还有意义。
在教工食堂吃过早饭,别的老师都回宿舍去,等待预备铃声响起再去上班。任老师没有回去,他穿过两排教工宿舍,直接到办公室去,他要把昨晚备好的课再温习一遍。任老师从教三十年,教的又是低年级,可以骄傲地说一句,他不用准备,闭着眼睛都能上课,而且一定上得很好。但是任老师不那样做,也不会那样做,他三十年如一日,把每一节课都当成新课,精心准备,认真备课,把他讲了无数遍的课讲得新意盎然,趣味横生。
任老师热爱他的工作,他的学生也热爱他。
任老师是学校的骨干教师,他供职的学校是淮县中心小学。
从事教育工作的人都知道,淮县师范学校和淮县中心小学是挂钩单位,每学期都派数名学生到中心小学实习。名师出高徒。跟谁实习,首推任老师,学生也以能跟任老师学习为荣。任老师既要教学,又要带实习生,每天忙得跟陀螺似的,少有闲暇时间。而同年级或是其他年级的老师,除了上课没别的事,倒也落得清闲自在。
任老师也想过一过悠闲的日子,就像其他老师那样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但是这个念头刚出现,就被任老师连根掐掉。
老师的职责就是授业、解惑,不该有其他杂念。
任老师今天上午有两节课,一节语文,另一节是作文。
今天的课,上的是《太阳》。听课者除了五十名学生,还有二十名实习生。实习生分坐在两边的过道里,把教室挤得满满的。今天的课气氛很活跃,因为孩子们都熟悉太阳,熟悉到像门前的枣树、院内的水缸,菜田里的南瓜……可以说已熟到熟视无睹的程度,但学了课文,特别是听了任老师的讲授,才知道太阳对地球、对人类是如此重要,重要到须臾不可分离。任老师说,没有太阳,世界将一片黑暗,永远没有光明!听听,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啊。任老师还讲了风和雨形成的过程,学生们听了,一个个惊得张大嘴巴,异口同声说,太阳是个神奇的魔术师啊!一节课不知不觉过去了,学生们撒着欢往外跑,实习生簇拥着任老师走出教室。
课间10分钟倏忽过去。
下一节是作文课。
作文是新课,三年级学生还是孩子,需要引导,提示,甚至还要写出范文,让他们照葫芦画瓢,他们才会挤牙膏似的写出一二百字的小文章。可别小看这些学生,更不能小看他们这一篇篇稚气得如同嫩芽似的小文章,要知道参天大树是由幼苗长成的,大作家也有童年。
上课铃声响起,学生们踩着铃声往回跑,实习生也鱼贯进入教室。任老师最后一个进来,他走上讲台,扫一眼台下,转过身在黑板上写下作文题:《池塘》。上一课学的是《太阳》,结合课文,任老师给孩子们一些提示,说水是生命之源——人离开水将无法生存,农作物离开水也无法生长。孩子们听了,一个个埋头写起来。
人如果有未卜先知的本领,那他就可以避开临近的灾祸,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永远过着幸福安宁的生活。
世界上没有如果——其实灾祸已悄然逼近任老师,任老师还浑然不觉,他像一棵大树站在讲台前,准备回答学生提出的各种问题。
作文课能有什么问题呢?也就是文章写到某处卡住了,他给点拨一下,那个学生便茅塞顿开,拿起笔继续往下写;或者写着写着,被一个字难住了,举手问一下,说得清的字任老师就说出来,说不清的就写到黑板上。三年级的孩子,写不出的字多着呢。
刚说曹操,曹操就到了。
一个学生举起手说:“任老师,‘哄’字我不会写。”
任老师说:“这个字是左右结构——左边一个‘口’字,右边一个共产党的‘共’字,合起来就是‘哄’。会写吗?”
那个问话的学生响亮地回答:“老师,我会写啦!”
也该任老师倒霉,他说这话时,恰逢县革委会主任来学校视察工作,正巧又路过任老师的班级,任老师的话一字不漏全被他听到了。主任生气道:“这还了得,我们共产党是哄人的吗!这是反革命言论啊!这样的坏人怎么能教书育人,培养好革命的下一代呢?你们说是不是?”
陪同视察的教育局长听完革委会主任一席话,脸都吓白了,点头如鸡啄米,诺诺连声:“是!是!”
革委会主任对教育局长下指示,说:“特事特办,你派人抓紧整理这个人的材料,明天上报革委会!”
局长一边点头,一边擦汗。
任老师仍站在讲台前,两眼看着这一群可爱的孩子,准备解答他们提出的各种问题,对即将降临的灾祸一无所知——等待他的是一顶“现行反革命”的帽子,还有开除工职、回家劳动改造的处理决定。
处理意见下来那天,任老师像头暴怒的雄狮,大吼一声,抬手狠狠地甩给自己两记响亮的耳光。在场所有人都看到,任老师的嘴流血了,两条红蚯蚓钻出来,在他的脖颈上一拱一拱地向下爬行……
欲加之罪
任老师的事,让淮县中心小学的全体老师如惊弓之鸟,惶惶不可终日。
教师的职责是授业、解惑。授业、解惑要动口,还要动手。前车之鉴,老师们怕祸从口出,重蹈任老师覆辙,上课照本宣科,下课闭口不语,同事见面,说说天气,最多问一声:吃了吗?除此不多一言。
郝云老师毕业于地区师范专科学校美术系,淮县中心小学,数他学历最高。
读书时,郝云因一幅水彩画在全省大学生绘画比赛中摘得头奖,被省美术家协会吸收为会员。那时入会的人少,能加入省美术家协会的更是凤毛麟角,全地区仅有二人,称他为画家也不为过。按郝云的才华和影响,分到地区中学任教是板上钉钉子——铁定的。淮县中心小学缺美术老师,武厉校长跑到地区教育局,找到分管人事的副局长,硬把郝云要了回来,理由是郝云是淮县人士,回县反哺乡人。
武厉校长如愿,郝云却受了委屈。
武厉是暗中操作,郝云被蒙在鼓里,所以对能分到淮县中心小学工作,心里还挺满意。毕竟是农村孩子,要求不高,能分进县城,而且在重点学校工作,是祖宗积德,老天保佑啊。
郝云教高年级美术,武厉重用他,委以美术组长——这在淮县中心小学校史上,是史无前例的。分析人士判断,不要几年,郝云即可跻身领导岗位,具体说就是升任教务副主任。分析人士的话有一定道理,因为老主任年龄大,过几年退位,副主任前进一步,留下一个窝,非郝云莫属。从校方看,形势也是朝着这个方向发展的。
郝云工作第二年开始恋爱,是学生家长牵线搭桥的。女孩身材窈窕,皮肤细白,瓜子脸双眼皮,是个大美人。大美人在县百货公司做营业员。营业员是公众人物,更是炙手可热、令人羡慕的好职业。老师们闻说后,课余时间纷纷去百货公司饱眼福。看后都说,美人嫁才子,天下绝配!才子是烈火,美人是干柴,两者相见便燃起熊熊烈火,没多久,美人就显山露水,没奈何,只得匆忙成婚。半年后美人生下一子,一家人和美生活。
孩子学步时,郝云稳步前进,果如分析人士说的那样荣升教务副主任。
这一年,“文化大革命”正向深处发展,形势如火如荼,一片大好。
郝云是领导,也是画家,他每天除了行政与教学工作,还要为学校墙报的批判专栏画插图。插图大多是漫画,批判谁了,就画谁。郝云的画讽刺性强,看他的画比读批判文章痛快。一天,县教育局长来中心小学视察运动进展情况,他看标语、读墙报,最后被墙报的插图吸引住。局长把校园里的墙报看完后,问武厉是谁画的画。武厉说是郝云,前几年从地区挖过来的。局长听明白事情的来龙去脉,大夸武厉,说他是伯乐,慧眼识英才。武厉听了,嘴上谦虚,心里偷乐。局长回去后,组织机关里的人来中心小学参观,其他学校也闻风而动,纷纷过来学习取经。郝云名气大增,淮县教育界无人不知他;武厉赚面子,全局召开批判经验交流会,他走上主席台,做了半小时典型发言。
凡事都有两面性,就在武厉绞尽脑汁,想让学校工作再出新亮点,教育局来了调令,调郝云去局里工作。武厉找局长,想把郝云留下来,继续为学校服务。局长要武厉识大体顾大局。武厉说他当年就是顾大局想长远,才到地区挖人的。听他这么说,局长“喷”地笑了,说:“你能到地区挖人,我就不能从下面调人吗?”听话听音,武厉知道他说了也是口抹石灰——白说,胳膊永远扭不过大腿,阻拦下去也是螳螂挡车。不过武厉还想争取一下,郝云来中心小学这几年,武厉对他不薄,年纪轻轻就让他走上领导岗位。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如果征求一下郝云意见,他若不愿走,事情还有转机。想到这里,武厉说:“局长,我们应该听听郝云的意见,是留是走由他定。”局长闻后,把握十足地说:“好啊,我们应该尊重他本人意见!”武厉错了。人是往高处走的,水是往大海流的,郝云对来征求意见的人说了一句很上水平的话:“听党话跟党走,服从组织安排。”武厉暗想,换上他,也会这么说的。
郝云调到局里,安排在办公室,工作就是为局里的两块板报出批判专栏。在中心学校,郝云既搞行政又忙教学,还要忙里偷闲出墙报,整天忙忙碌碌,常感时间不够用。调进局里,工作单一,他成了时间富翁。郝云闲不住,于是自作主张,将一周一换的板报改成一周两换。如此一来,他的工作量加大一倍。
有事做好啊,忙了生活才充实。
前面说了,郝云是画家,他的画讽刺性强。郝云画人,排斥共性,捕捉个性,寥寥几笔就能把一个人的特征勾画出来。郝云画反面人物,也画正面人物和伟人。郝云作画,板报前常有人驻足观赏,看了或捧腹大笑,或点头称赞。教育局的板报成为全县机关的一道亮丽风景,县革委会主任一天出来看板报,当他来到教育局的板报前,脚下像生了根。在场的人看到,主任看报时脸上挂满笑容,还不时点一点头。
局长也因此走上主席台,面对全县机关干部,做了40分钟典型发言。
因为板报,局长给主任留下极好印象。有官场经验的人预测,局长仕途看好,年内有望升迁。
局长在等着这一天,他盼望时间像白驹过隙,跑得快一些,再快一些。
时间好像有意与局长作对,走得慢慢吞吞,像老牛爬坡。局长头上已急出几丝白发。
终于到了动人的时候,出乎意料,局长没有升迁,郝云却调动了。县革委会没有征求教育局意见,就开出调令,就像数月前教育局从中心小学调人一样,不同的是调令上的那个戳子。
这一天是周三,教育局换板报的日子。按说郝云已接到调令,他应该忙自己的事,调动了,有好多事等着办,换不换板报已与他无关。但是郝云没有那么做。郝云是个完美主义者,他想站好最后一班岗,给自己交一份满意的答卷。
恰好这天夜里伟人向全国人民下达最新指示。在构思板报内容时,郝云把最新指示用在报头上,还配以伟人的侧面头像。
出好一块板报,还剩一块没出。为使两块板报对称呼应,郝云选了伟人的一段语录,用在这一块板报的报头上,插图时也配上伟人的侧面头像。
两块板报花时一天,而以往只需半天,可见郝云是下了工夫的。
真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郝云因画而名,画让他平步青云,一脚登天。郝云还不到30岁,脚下的路很长,前途不可限量啊。
郝云有所不知,这一天,他已走到人生的顶点。顶点即高峰,高峰的任何一方都是坡面。
下班了,郝云回办公室收拾东西,他要把自己的东西全部拿走。
这一天,县革委会主任难得没有应酬,他拎起公文包,关上门就走了。秘书听到碰锁“哒”的一声响,急步出来,把主任的包拎到自己手里。主任大步流星,军大衣被迎面风吹得一飘一飘的,走到教育局那两块板报前,主任停下脚步。有人在看那两块新出的板报。主任也看,刚看一眼,眉头皱起;看第二眼,感觉出报人有点居心叵测。伟人怎么全是侧面像呢?一只耳朵,这是含沙射影,影射伟人偏听偏信啊!
“这是反革命行为!”主任义愤填膺地说:“谁这么大胆,简直是狗胆包天!”
革委会主任是全县几十万人的最高长官,他的话就是圣旨。秘书领命而去,须臾返回来,汇报说:“是郝云!”
主任反问一句:“郝云……就是我要用的那个人?”
秘书说:“正是,今天刚开出调令。”
主任的大手用力一劈,说:“他是潜藏在革命队伍里的反革命,我们不能姑息养奸,应该打倒他,再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
秘书又一次跑开去。
此时,郝云已整理好东西,他把办公室的钥匙从钥匙扣上解下来,刚走出门,就被几个年轻人团团围住,只听“咔嚓”一声,郝云那双画画的手就被铐了起来……
催 眠
文华学的是化学,却迷恋文学,得空就往中文系跑,要么一头扎进图书馆,找一些中外名著看。同学见他厚彼薄此,都摇头咂嘴,说文华这样做,是耕了别人的田,荒了自家的地。与他同组的一位女同学说:“文华是鬼迷心窍,他这么做,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到头来吃苦的是他自己。”没想到女同学一语成谶,这是后话。
爱学习的人都知道,一个人如果读书多了,他的内心就很辽阔,思想也比常人深刻,看事物既看正面,也看反面。哲学用语,叫做事物的两面性,或多样性。文华就是这样的人。
文华是真爱文学,爱到骨子里。学习很苦,创作更苦。文华不像同学说的那样,他非但没有荒废自家的地,别人的田也长得青翠欲滴,五谷丰登。说明白一点,就是文华本专业学的很好,文学方面也是硕果累累。他是双丰收啊,在校几年,文华不但写诗,也写小说。他写的小说,手稿被同学传着看,一传十、十传百,后来竟然出现手抄本。
大学毕业,文华被分配到县中学任教。文华白天教学,晚上创作。一份耕耘,一份收获。不久,文华的小说就在《人民文学》杂志上发表了。文华刚分来学校时,有人说文华是大才子,在大学就写诗写小说,好多人读过他的手抄本。听的人不相信,说会写小说的人是作家。作家是什么?是人类灵魂工程师啊!意思不言自明。没几个月,从北京寄来的一封信证实那人所言不谬。那是一封奇大的信,信封上清清楚楚地写着文华的名字。传达室的魏师傅神情肃然地从邮递员手中接过来,感觉沉甸甸的——这是他干传达以来见到的最大最沉的一封信。此刻,魏师傅把大信封端端正正地摆放在桌子上,等着文华下课来取。那个曾经不相信文华会写小说的人路过传达室,一眼看到大封信,张开嘴巴“啊”了一声,当即返回办公室,比比画画,夸张地对同事说了一番,没课的老师都跑来传达室看稀罕。我的妈呀!这么大的信封,跟档案袋一般大小。寄信人的地址和邮戳都来自北京。信,在几个人手中传递着。
下课铃声响起。性急者走出传达室,想把这个消息告诉文华。有眼尖的老师高声叫道:“看,文华来啦!”大伙把目光齐刷刷地投向远处,果然是文华!他下课没回办公室,而是直接来传达室取他的信,看来有人把消息传过去了。文华愈走愈近,已经能看清他脸上的笑容了。大伙往两边退,中间留下一条通道给文华走,有点夹道欢迎的意思。文华大步流星,走路带风。大伙的目光如同剧场里的追光,紧紧地跟着文华。文华走进传达室,拿起信封,“嚓”地撕开封口,取出杂志,先看目录,再翻内容。靠近的人,如同一群伸长脖子的鹅,嘴里念着:“《讲台》,文华!”这是一篇反映教师生活的小说,据后来看过小说的人说,小说取材他们学校,人物有老师,也有学生,都是一些司空见惯的事,但经过文华描写,就变得不一样了。同为老师,文华把生活变成小说,而他们连想都不曾想过,真是人比人死,货比货扔啊。
从此,老师们对文华都高看一眼。
文华一如既往,白天上课,晚上挑灯夜战,常常忘了时间,直到公鸡打鸣才上床小睡。文华把时间看得比金子贵重,年近30岁也不恋爱。学校有一名年轻女教师,相貌出众,人品极佳,不乏追求者,均遭拒绝。男子钟情,女子怀春,世间常情也——女教师也不例外,她的情早有所属,心亦有所系,心中的那扇小门是专为文华留着的,只等他有朝一日来叩响,再轻轻地推开。年级组长也是女性,姓吴,已婚。结过婚的人眼睛带着“毒”,女教师的心思早被她洞穿。她见文华迟迟没有行动,很是担心《梁山伯与祝英台》在她身边上演,于是甘愿当红娘,为他俩牵线搭桥,完成人间一桩美满姻缘。吴组长性急,这一天见文华一个人在办公室,不加铺垫,就把这事说了。文华正在批改作业(抑或在构思某篇小说,入得太深?),大脑一时没转过弯来。吴组长见他懵懂如梁山伯,吃吃一笑,遂又复述一遍。说完了,吴组长在文华对面坐下来。文华如果抬头,就会看到,吴组长的嘴角弯弯如上弦月,眼睛眯眯如睡美人——此时此刻,吴组长正等着文华谢她呢。前面说过,吴组长是结过婚的。已婚女人做事是穿钉鞋拄拐杖,步步求稳实——女教师是佳人,文华是才子。佳人配才子,古今传佳话……文华继续批改作业,头还是不抬。吴组长想他这是害羞呢,别看他是作家,情场却是新手……就这时文华有了动作,他换一个坐姿,继而摇一摇头。
吴组长有点不相信,失声变调地问:“怎么?你……你看不上她?”
文华又摇一摇头。
吴组长糊涂了,她闹不清文华第二次摇头是何意思。吴组长想打破沙锅问到底,就这时下课铃响了,别的老师回来了。吴组长把滚到嘴边的话咽回肚子里。
吴组长很无趣,地下有缝她能一头扎进去!回到位置上,吴组长鼻息粗重,胸膛一起一伏的。吴组长在心里骂自己贱,说自己是狗逮耗子多管闲事。下次嘴痒,就到砖墙上蹭去!
吴组长最后发狠道:“哼!不就是作家吗?有什么了不起!”
从此,吴组长对文华有了看法。
一天课间休息,办公室有一女老师向同事诉苦,说她睡眠不好,过了12点就睡不着,睁着眼睛盼天明。
有同事支招,说数数呀,数累了保管你就睡着了;还有说吃安眠药啊,那东西管用,一粒就见效。
文华听了,对女老师说:“我教你个法子,保你睡得香!”
女老师问:“啥法?快教说!”
文华小声说:“看‘毛选’啊(《毛泽东选集》),一看就困,我屡试不爽!”
女老师信心不足,半晌才说:“我试试看吧。”
这话被吴组长听到了。听到就听到,当时也没当回事。
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学校停课闹革命,每天开会,高举拳头,狂呼革命口号,会场乱哄哄,仿佛一锅粥。县革委会派出工作组进驻学校,老师们人人自危,担心自己成为革命对象。工作组是带着任务下来的:他们要在学校挖出一颗 “定时炸弹”,这颗“炸弹”就是反革命!谁是反革命?老师们迷惘、彷徨、恐惧。工作组几个人分头找老师谈话。谈话采用的是启发式和诱导式。工作组的人个个都像嗅觉灵敏的警犬,他们能从老师们的谈话中寻找出蛛丝马迹,然后顺藤摸瓜,最后揪出坏人。
这天,吴组长被找来谈话。经过启发和诱导,吴组长突然想起文华那天说过的话,于是一字不漏地对工作组的人说了。工作组的人一听,眼睛立马亮了,“砰”地拍了一下桌子,骂道:“妈的!好一条大鱼,好险让他漏网脱逃!”
有了人证,文华就成了彻头彻尾的反革命!
那时的政策是从快从重,文华先被判处死刑,后改判无期,险些丢了脑袋。
审 片
老黄供职于地委宣传部,任副部长,副处级。在地区,这个级别算是高干。
老黄53岁,离退休还有几年,日子长着呢。在部里,老黄分管新闻和文化。众所周知,新闻指的是报社、电台和电视台;文化就是文化局。文化局是个大单位,属下有几家剧团,还有电影公司、博物馆、群艺馆、图书馆、书画院、戏剧学校等等。在宣传部,数老黄手里的事多,忙起来别说部里人见不到他,连他的老伴一周也见不上他几次,老黄忙起来就像古代的大禹,路过家门而不入。一次,老黄的老伴亲眼看到老黄拎着人造革皮包,在马路的那一头一摇一摆地往这边来,老伴就站在门前等,哪知他走着走着却拐了道,向另一个方向去了。老伴把手卷成喇叭筒,跟在后面“喂”“喂”大叫,老黄耳朵里像塞一团驴毛,愣是没听见(老黄老伴的口头禅)。老黄两天没回家了,家里有急事要和他商量,不见面咋行呢。老伴回家把门锁起,骑上车子追赶,马路上连老黄的影子也没有。人找人,如同大海捞针。老伴想走捷径,先把他的去向摸准确,然后来个瓮中捉鳖。这样一想,于是掉转车头,到宣传部去。宣传部在地委大院内,老伴有幸跟老黄去过一次,道路是记熟的,骑车一二十分钟就到了。宣传部办公室的人告诉她,说老黄到京剧团调研去了。老伴走出来,骑上车子就往京剧团赶,那个扮演李铁梅的女演员说,你找黄部长啊?他刚走不久,到淮剧团调研去了。又是调研,这狗撵兔子,何时才能逮个正着呀(又是口头禅)。老伴脚下用力,心急火燎地往前骑,赶到淮剧团,抬头一看,剧团的门上挂着一把大铁锁。老伴走进传达室,看门老头耷拉着眼皮说,下班了,要找人下午过来。老伴没有多话,更没有耽搁,骑上车火烧屁股似的往家跑——两孩子这会正在下班路上,她要赶回家给他们做饭。老伴本来没有气,这会有气了。老伴嘀咕道:“老黄啊老黄,你心里还有这个家吗?等你晚上回来,我一定要你说个清楚明白!”
当晚老黄没有回来,第二天也没回,直到星期天中午,老黄才拎着那个皮包回家来。老伴有一肚子话要说,此刻那些话像一团乱麻在她肚子里乱拱,老伴想把话理顺畅,然后再一句一句说出来(老黄教导她,说话要条理分明)。哪知她还没开口,老黄就扔给她一包脏衣服,命令说:“赶紧洗去,我明天要带走。”
听话听音,看来老黄下周又要有几天不归家。老伴心里气啊,肚子一起一伏的,里面的话更乱了。老伴不管不顾了,脱口道:“地球离开你怕是不转了,看你忙的,连家都不要了!”
老黄是烧鸡蛋炸瞎眼没瞅出火候,他真是忙昏了头,到这时竟然还说:“我真是忙啊,下午还要加班,在家里审片子,没有政治问题、生活问题,电影公司才能卖票放映。”
老伴阴阳怪气地问:“你的权好大呀,管天管地,快赶上任部长了。”
任部长是常委,地委主要领导。老黄当老伴不懂,轻言好语对她说:“不懂不要瞎说。任部长是地委常委,省管干部,我比他差一大截子。”
老伴心想,我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当我啥也不知呢,真是!她将错就错,接着刚才的话说:“你管那么多事,又是剧团,又是电影公司,还有别的单位,人口合到一块成百上千,全归你领导,谦虚啥呀!”
老黄一听跳起来:“别说剧团,说了我来气!”
老伴装着关心的样子,问:“气啥呢,谁得罪你啦?”
老黄气呼呼地说:“不是得罪,是捅娄子!”
“这不是太岁头上动土吗?”老伴幸灾乐祸地说。
老黄叹息一声说:“有几个女演员,仗着自己长着漂亮脸蛋,趁着地委书记接见时告团里的状。”
“告剧团又不是告你,你操啥心?”老伴追问。
老黄说:“我是分管领导,不操心行吗?这几天,忙的都是这事!”
说着话,家里的电话响了。老黄抓起话筒一听,是电影公司吴经理打来的。吴经理告诉黄部长,放映员午饭后来他家,放香港内部影片 《铁牛》,请黄部长审查。吴经理还告诉黄部长,其他几位审查员都看过了,就等黄部长看后拍板拿意见,如果没问题,他们下午就把海报贴出去。老黄一边听电话,一边点头,嘴里还不停地说好,好。老黄这几天在两个剧团跑来跑去,把审查影片之事放到一边,误了人家时间。老黄本想说几句歉意话的,一想他是领导,领导做什么由自己做主,于是没多说话,就把电话挂了。
老伴听了电话,知道老黄一会还有事,是电影公司的人来家里放电影,就不和老黄戗戗了。老伴想,既然电影公司的人来家里放电影,她大概也能跟着沾一点光的。想到这里,闷在心里的气一下子烟消云散,于是高高兴兴地做饭去了。
电影公司的人说来就来,到时老黄刚丢下饭碗。
放映员来了就开始忙碌,他把放映机架在客厅里,在电视机前扯上一块幕布,拿出拷贝就准备放映。老黄有些激动,心怦怦狂跳,两颊一阵一阵蹿火。老黄听人说过这部影片。这是一部动作片,在香港很火,入座率极高,场场爆满。爆满的原因,是因为片中有打斗,人人功夫了得;还有谈情说爱的镜头,男女搂搂抱抱,嘴巴对着嘴巴接吻,时间在5秒钟以上。老黄听别人议论,当时不太相信,但听人家说得有鼻子有眼,又不得不信。影片马上就要放映,如果传说是真的,不用多说,肯定通不过。他是宣传部长,又是审片组长,他不能让黄色影片公开上映,毒害人民,污染社会。
放映开始,老黄将老伴和两个孩子轰出去。孩子不乐意,但不敢反对。老伴就不同了,在家她也是主人,和老黄平起平坐,老黄不分青红皂白,把她和孩子混为一谈,一道往外轰,说明她在老黄心里没有位置。老伴虽然有气,但当着放映员的面,还是给老黄留了面子,离开时她给放映员倒了一杯水。
老黄坐在沙发上,跷起二郎腿,一摇一晃的。客厅里就他和放映员,一个人放,一个人看,真惬意啊,比在小会堂审片舒服多了。
电影很热闹,情节一步一步向前发展,看趋势,男女主人公真的要恋爱了。老黄心跳加快了,他希望传说是真的,因为他也想看一看别的人拥抱和接吻是啥样子;同时又担心传说是真的,如果那些传说中的镜头真的出现在银幕上,这部电影就死定了。
老黄每年要审查几部电影,《铁牛》给他有一种别样的感觉。老黄目不转睛,紧紧盯着银幕瞅。男女主人公说说笑笑,眉目传情,他们愈走愈近,果真拥抱了,又接吻了……老黄坐不住了,身上像着了火,他把衣扣全部解开,感觉还是热;喉咙很干,仿佛龟裂的土地。老黄起身倒水,他想把喉咙滋润一下。就这时响起敲门声。老黄当是两孩子,他把门打开一条缝,伸出头刚要轰他们,不想门口站着几名公安。不等老黄说话,几名公安已冲进室内,其中一人说,他们接到群众举报,说有人在家看黄色电影。接报后他们迅速出警,果然人赃俱获!老黄镇定下来,说: “你们搞错没有?我是审查影片,不是看黄色电影。”那人冷笑一声说:“不要狡辩,死到临头,有话到公安局说去!”话音刚落,几名公安就把老黄和放映员押走了。放映机、拷贝,还有幕布也被一道带走,这是赃物,更是铁证。
老黄和放映员被关了一夜,说破嘴人家也不放他。第二天,经部领导斡旋,另几名审查员出面作证,老黄和放映员才被释放回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