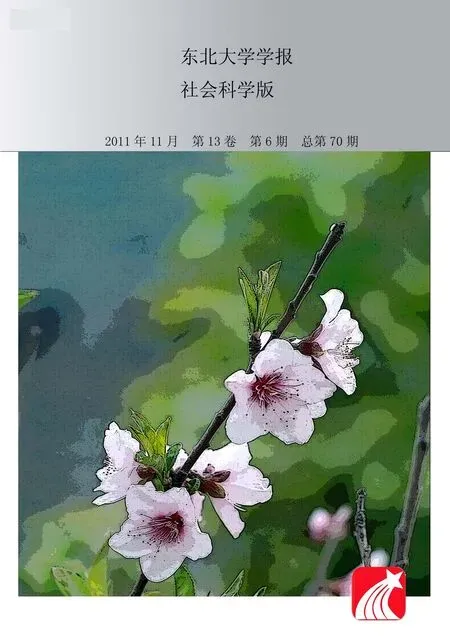语用视角下意义的复杂性回归
----语言顺应论之“意义观”阐释
2011-09-25毛延生
毛延生
(1.黑龙江大学俄语学院,黑龙江哈尔滨 150080;2.哈尔滨工程大学外语系,黑龙江哈尔滨 150001)
奥格登与理查兹在以“意义”本身为研究对象的《意义的意义》一书中,将意义视为“语言的中心问题”[1]。自此以后,意义的研究重要性在语言研究当中得以很好地继承,这体现在语义学和语用学两大阵营学者对于意义研究均赋予了严肃的学术尊重与海量的研究投入,尽管彼此在研究视角以及外延划定上存在些微差别。随着20世纪学术研究的“语用学转向”,意义的语用学研究变得炙手可热[2]13,其被赋予更为丰实的本体论、价值论和认识论洞见可谓与时俱进的感召。对于意义的态度可以十分清楚地表明任何一个学术研究范式的严肃程度及其发展潜质。无论是格莱斯主义,还是新格莱斯主义均因其对“意义”的“原子主义”关注而得到学术界的认可,这与其逻辑实证主义的研究传统一脉相传[3]。与之相比,欧洲大陆语用学派则似乎并没有受到这样的厚待,相反这一研究范式往往被驳难以过于宽泛或宏观的缺陷,这直接导致该学派在研究理念和研究方法上的亮点未能得到充分的显现。仅以顺应论为例,学界尽管已然认识到它无论在理论层面还是在应用方面都能给人带来诸多启示(例如,其多元的研究方法、动态的意义处理[4]、元语用意识的突显[5]等等颇为新颖的理论见解让人耳目一新),但在语用学界顺应论实际上得到的学术关注却是严重不足。
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很多[6],但我们认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学界对于顺应论的意义观把握不够准确。具体来说,有关顺应论如何看待“意义”这一颇具本源性的问题,当下语用学界似乎缺乏深入的思辨性考察,尽管Verschueren在《语用学新解》一书当中已经作了详细的说明----语用视角下的意义需要回归复杂性[7]48。这一研究盲点一方面使得顺应论似乎深陷于研究范式“假、大、空”的藩篱之内,原本强调意义研究的顺应论似乎却背离了意义这一语言研究的中心;另一方面使得顺应论给人以离群寡居的印象,似乎它割裂了自身与意义研究的关联而成为多个学科的临时保护伞[8]。由此可见,及时梳理与阐释顺应论的“意义观”就显得格外紧迫,这不但可以从微观上厘清顺应论在意义研究传统中的历时占位、澄清顺应论所负载的一些莫名诘难,而且还可以从宏观上为欧洲大陆语用学派研究取向的价值正名。有鉴于此,本文基于顺应论的主体文献,尝试对于顺应论的“意义观”予以文献式深度阐释。我们认为,顺应论视阈中的意义观体现了语言价值的人性回归----交待“在使用语言的时候,语言人做了什么”[7]48。这一意义观不但反映了顺应论对于“意义是什么”这一传统意义内涵的关注,而且还涵盖了“意义意味着什么”以及“意义应当成为什么”两层“人性化”的语用追问与认识指向。借此,这一独特的“意义观”突显了顺应论视角下“意义”研究的符号价值、深刻内涵以及它对于符号与符号使用者之间的主体间性的理性规定。下面我们就分别从意义的语用内涵描述、语用价值判断与语用期望指向三个方面阐释顺应论的“意义观”。
一、意义之语用内涵描述:从分析性到复杂性
在语用视角下要回答“意义是什么”这一语用内涵问题,首先得知道什么是内涵。“内涵是指反映在概念中的对象的特有属性。”[9]29因此,意义的语用内涵描述就应该揭示意义所具有的语用属性。鉴于“内涵实质上是反映概念所反映的对象是什么,内涵属于主观范畴”[9]29,我们可以说内涵是认识概念所反映的对象的一个主观视角。据此,从语用学来看待意义的内涵就可以理解为认识意义的一种语用视角。鉴于语用视角下的意义并非一个单一概念,涉及语言形式和语用人以及主体间性,因此意义的内涵必然具有一定的复杂性。诚如Davidson所言,意义研究必然由分析性走入复杂性----“是一种整体的信念在支配人们对他人的表达式的理解,而不是逐个对照式的证实真假”[10]。与英美语用学研究“重分析性,轻复杂性”不同,顺应论认为意义研究应该转向复杂性,而不应过分地关注分析性。语言顺应论的产生首先源自对于当时意义研究方法的不满:或者是单一语言学的研究视野----只从语言本体展开研究意义;或者是文化主义的研究框定----只从社会文化方面研究意义;或者是生物学主义的研究范式----只从自然生物方面研究意义。在Verschueren看来[7]42,这些“单打独斗”的研究范式违反了Morris对于语用学界定的初衷[11]。因此,这些研究对意义的认识都只得到片面的结果,毕竟意义是语言人与社会心理互动的触媒与载体。再如温奇[12]所言:“解释一个词语的意义就是描述它如何被使用;而描述它如何被使用也就是描述它所进入的社会交往。”在这方面,顺应论表现出整合性的特点,因为它强调意义与多维度整合论。相应地,顺应论希望在方法论上引入多视角、多原理和多观点,以求弥补顺应论给人造成“旨在建构普适理论”的错误印象[7]63-64。
顺应论视角下意义的内涵研究对于复杂性的重视集中体现在顺应论对于语用学的重新界定之上。在《语用学新解》一书中,Verschueren开宗明义地说明了顺应论将语用学界定为“关于语言和交际的认知、社会、文化的研究”,并以“语用视角”为题,将语用学描述为关于语言(任何方面)的全面的、功能性的视角”[7]69。依据这一定义,语用研究必须整合认知、社会和文化三个维度。对于语用视角下的意义内涵来说,认知、社会与文化三个维度所涉及的复杂性必须予以兼容考虑。唯有如此,意义内涵才能名副其实地完成其在“语用学转向”中的核心地位----语言人与符号之间的复杂性关系决定了语用视角下意义研究必须跳出分析性而走向复杂性。基于这一定义可知,顺应论对于意义内涵复杂性的看重是为了满足理论描述的充分性考虑,而这又是理论效度得以保证的重要前提。通过引入认知、文化和社会等维度而由分析性让渡到复杂性,顺应论是在确定自己的一个主要任务----要全面地说明语言使用中所涉及的语言人的主体性和自主性。被称为主体的语言人是交际当中具有自主性的社会人,这首先与其具有保持和发展自身存在的目的有关。语言人不是被动地遵从外界环境因素的作用发生变化的单一生物体,他们的行为都是根据把有关环境因素的意义和有关自身目的的意义结合起来进行加工得出的指令信息进行的,因此离不开认知、文化和社会三个核心维度。
试想,如果意义内涵忽略了上述三个维度所建构的复杂性,语言人的“人性”本质将会被抽离出去,这势必导致意义研究重回“语言学转向”的老路----非但不能摆脱形而上的幻相,反而使自己陷入语法的幻相[2]2,使我们的理智入魔[2]109,而这正是意义研究的语用学转向力求避除之处。值得一提的是,顺应论视角下的意义研究需要回归复杂性并不是意味着该理论的意义内涵完全排斥分析性。具体来说,顺应论将Grice所完全承认的那些“非语言因素”或“语境”因素在意义建构与解读中所起的作用又进一步予以推进与澄清,这足以说明顺应论对于分析性的珍视。实际上,在处理意义问题时,顺应论对分析性与复杂性的“双义性”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可以说,分析性和复杂性占有同样根本的本体论地位,它们在具体语境下捕捉意义的动态运作过程中都发挥着“双义性”的作用。确切地说,复杂性的积极作用是保持意义相关维度介入意义运作的持续性与完整性,而其消极作用则是它的模糊性抑制明晰性单元的切分与划定;分析性的积极作用是它能够突破意义的复杂性而提纯出意义的动态生成秩序,进而交代意义新陈代谢的产生条件,而其消极作用在于它的保守性抑制我们对于意义研究的全面认识,同时导致意义研究的全息维度彼此走向解体。通过主张意义研究走出分析性,进入复杂性,顺应论视角下意义的内涵回归力求整合“一元”与“多元”的对立,这正是顺应论的古典实用主义哲学基础的张力所在。
鉴于顺应论对于意义内涵复杂性的重视,因此“顺应”不能被概括为一个主导词,不能被化归为一个简单的概念,否则,顺应论对于意义的内涵处理终将陷入传统语用研究所难以摆脱的“化简”与“割裂”疲敝,而这彻头彻尾地违反了顺应论的初衷。通过强调意义内涵走出分析性,进而回归复杂性,顺应论不但赋予具体语境下意义发生变异的可能性,而且还因为语境的介入而多了一个保证意义稳定性的可靠参数。这样,顺应论一方面将意义的分析性研究视角囊括在内,另一方面可以摆脱以分析性视角研究“意义是什么”的学者对于语境介入意义研究所导致的过泛与失控的诸多担心。语言顺应论走出分析性而进入复杂性就是在倡导意义内涵的语用回归必然体现在意义研究对于自然性的尊重。顺应论强调意义内涵的复杂性回归正是这一关照的充分体现。
二、意义之语用价值判断:从语义三角到语用三角
意义的语用价值判断将解释这一复杂性范畴在确定二者之间概念关系时到底是如何运作的。换言之,“意义意味着什么”这一价值判断则更多地涉及评价活动,它具体指向意义生成当中复杂性所具有的价值以及价值判定的阶乘分布。毫无疑问,“意义是什么”的研究首先关联着的是意义内涵的认知观问题,这与传统的语义三角颇为相似。一般而言,具体意义的生成往往以语言人的语用思维为参照,因为“一切理论界不仅必然携带着不可消除的理解者的主观性,而且以这种主观性作为理解的前提”[13]。换言之,在理论上存在依靠话语选择而呈现为有意义的各种语言资源,因为任何通过语言来表达的理论,它们作为知识都存在着通过语言而对语言进行诠释与理解的问题[13]。从语言人的话语选择来看,首先就要追问语言选择所显现的意义首先与“意义是什么”如何相互关联。但是,同时我们会发现单单知道“意义是什么”还远远不够,何况作为人适应世界的语言结构,它无疑更多地表现为在不同视阈下不同语言人的主体性之间关系的探寻,从而也更直接地对应于“意义意味着什么”的问题。相应地,这个问题进一步将概念化的意义引入意义的语用价值判断领域。因此,意义的语用价值判断所体现的事物与人的关系必须在意义的语用学视角当中通过评价而得到具体的判定和确认。这样看来,剥离了“人的原则、策略或目的”的传统语义三角无法就意义的上述维度给出让人满意的解释。相对而言,顺应论通过给予“人的因素”充分关照而十分巧妙地做到了这一点。这一点在顺应论中体现为三个核心概念之间的复杂性构建所衍生出来的顺应三角关系。
首先,变异性表征了商讨性,商讨性则指向顺应性,由此变异性可以实现顺应性。对于三者之间的关系,参考语义三角模型(图1),这里尝试将其表述为图2。尽管变异性、商讨性和顺应性[7]69这三个概念表面上关注的是语言或语言使用的属性,但实质上关注的却是语用人眼中交际“意向”的价值判断:变异性是这一意向的表征手段,商讨性则是这一意向得以充实的指南,而顺应性则是该意向的最终旨归。通过赋予意义价值判断充分的“人性”内涵,顺应论视阈中的意义研究才能表现出复杂性研究所看重的相对完备性,而这是意义的语用价值判断得以实施的根本前提[7]68。

图1 语义三角

图2 顺应三角
其次,顺应论中的顺应三角实际上隐含了语义三角图式,但又有所超越,从而形成一个带有“双层性”特点的表意评价空间。依据定义,变异性圈定了意义表征的基本范围,因为变异性主要划定的就是语言使用各个层面所存在的变异性选择。与语义三角当中的语码或者符号一极相比,二者的相同点在于其载体均是具体的语言符号本体层面,但变异性的优点在于通过引入符号本体变异性与复杂性而突显了语用人的自主性以及语言的全息性。商讨性通过赋予语用原则或策略充分的尊重而为意义的价值判断提供语用指南,即意义的语用价值所在必须参考语用原则或策略等思想性与概念性的抽象实体。与语义三角当中的概念一极不同,商讨性的关注点超越了语义三角中的单一概念表征维度,通过引入了策略性与原则性元素从而使得意义的价值判断更具有“语用学转向”所看重的“非形而上”特征。就顺应性而言,它不但关注交际所指概念的现实性,更为强调其交际价值的挖掘与阐述,因为它所涉及的交际需要满足程度直接决定了意义价值的饱和度。据此,顺应性可被看做是意义价值判断的硬性指标。综合以上分析,顺应论中的顺应三角思想可以进一步丰实为图3。

图3 语用三角
从语义三角到语用三角让我们看到了意义研究如何跨越“意义是什么”而进入“意义意味着什么”的具体进路。这在根本上源自于语言使用者的“人性”介入,在顺应论中具体表现为嵌合着语义三角的顺应三角当中。从语义三角到语用三角的升华有效地区分了顺应论的意义观和传统意义观,这使得语用视角下的意义研究突破了分析主义范式中意义研究的封闭性观点,进入到人类生活实践中来,而这正是Morris和Pierce所推崇的“语用关怀”所在。比较而言,顺应论视阈中的意义被放置于价值判断之后,就可以通过“对语境开放”来组织自身的封闭性,从而突显意义的社会性功能与语用价值,这在语用三角中体现为商讨性所隐含的策略性以及顺应性所蕴涵的目的性。从这样一个带有“意义价值判断”色彩的语用三角中,我们可以推导出顺应论中两个十分重要的动态意义观点:第一,在具体交际语境当中,意义生成与理解所遵循的法则不是关于平衡态的,而是关于不断被补偿的非平衡态的,关于被稳定的运动态的,这也就是顺应论所看重的意义的动态生成;第二,更为重要的是,意义的可理解性应该不仅在于语言系统本身,而且存在它与环境的关系中;这种关系不只是一种简单的对外在非语言因素的依赖性,而是意义本身的构成因素。这样来看,意义在本质上既存在于自身与其开放语境的联系中,又存在于其间的区别中。在逻辑上,意义就不再囿于只能把语境包含于其本身的情况下加以理解,这个语境对于它既是内在的又是外在的,在构成它本身的一部分之时又处于它的外部。在方法论上,顺应论借助语用三角摆脱了传统语用视角下意义研究的诟病----把开放语境作为根本上可隔离的实体来研究变得困难。在理论上和经验上,意义价值判断的语境介入使得意义研究具备了“进化”的特点----意义进化只能源自意义和语境的相互作用,而且最可注意的组织性质变可以被视为超越系统而进入元系统,而这些显然是单纯关注“意义是什么”所不能企及的。
三、意义之语用期望指向:从最优解到优化解
如果说“意义是什么”指向内涵层面的深层规定,“意义意味着什么”以价值关系为基本内容,那么“意义应当成为什么”则更多地呈现出对于实用性意义的深度关注。换言之,第一点意味着通过人的实践活动使意义打上了人的印记,并体现人的价值理想;第二点不仅表现为被认知或被理解的存在,而且通过评价而被赋予价值的内涵并具化于不同形式的语境当中;第三点则表明意义往往因为人性因素的介入而使得意义表现出深切的“期望(或目的)”特征。上述三个方面充分表明“以人的存在与世界之在为本源,意义既内在并展现于人化的实在,也取得观念的形式”[14]。顺应论对此持认同的观点,但更为直接地将“期望”背后的人性因素缩限到人的“有限理性”之上,具体表现为语用视角下的意义研究不是对于“最优解”的探索,而是对于“优化解”的寻求。最优解与优化解之间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以无限理性为基础,后者以有限理性为前提;前者以绝对有效为目的,后者以相对满意为皈依。顺应论对意义研究所提出的“语用期望”实际上希望意义研究回归到原点,从语用人和生存需要的满足度上寻找意义研究的实用指向,而这也是“语用学”一词在词源学上的本义缘起。
顺应论所认同的优化并非以人的完全理性为基础,而是以有限理性作为选择的基本出发点。语言人的有限理性思想可以说贯穿顺应论的始终。例如,在交代语言选择以及交际需要时,顺应论明确说明如下几点:第一,语言使用者受交际时间和可利用资源的限制,在意向表达时的语言选择具有相对性;第二,为了避除交际中无谓的风险,语言使用者往往尽量避免不快,倾向于选择风险较小的语言选择项;第三,语言使用者在交际中往往只寻求相对满意的结果,即交际需要得以满足即可。因此,顺应论视阈中的交际需要存在度的变化。可见,顺应论对于“意义”的“期望”着眼于有限理性。这充分表明顺应论在意义表征与阐释上放弃了传统意义研究中的最优解而转向优化解。这完全符合当下“语用学转向”的要义----我们对于语言的把握由思维的抽象走向交际中的具体需要;由片面的分析走向新的综合[2]8。
顺应论针对意义的语用期望所进行的有限理性缩限其实不无根据,因为顺应论对于优化解的求解策略具备夯实的理据。对此,我们再次回到顺应论对语用学的内涵界定当中所看重的“社会心理(mind in society)”[7]173之上,这一概念也是符号学中语用维度的原初关注,它在本质上反映了语用视角下“意义”研究必然走向基于有限理性的优化解路径。从认知的角度来看,人类神经系统在智能活动中显现出两个值得注意的特征:输入信息的模糊性和输出结果的满意性。基于这些模糊信息,交际者的脑神经认知系统开始信息处理后,所给出的决策性输出答案或者顺应性反应大都不是最优解而是属于能够解决问题的优化解。以交际中的信息采集为例,我们只是观察周围自己感兴趣的事物(选择性注意),听别人讲话时,只抓住对方通过语言表达的主要意思(选择性理解)。每天从各个方面获得众多信息,但保存在记忆中的只是极少部分重要的事项或数据(选择性遗忘)。如果交际处处为了寻求最优解,那么“眉头一皱,计上心来”的决策就成为梦幻泡影,因为它很可能只是找出一条能解决当前面临问题的有效方法,显然,各个方面都最佳的方案不可能在“眉头一皱”的瞬间得以完成。
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大多数人进行话语选择的时候依靠的是感性选择。其特点是:在不完全信息条件下选择话语,善于依靠直觉来减少话语选择成本。这里的直觉体现了交际语境感知的有限性,这同样也十分契合顺应论对于语境激活中“视线”的重视----并不是世界中的一切事物都会介入话语选择当中,只有那些被视线激活的有限的事物成为话语选择的参考[7]77。从语言选择者的角度来讲,这就是一种感性选择带有直觉性特征,特别是社会交际过程中社会关系以及个体心理纷繁复杂,加之注意力存在限制,所以不可能一下子注意到一切。如果交际以寻求最优解为目的,那么它就以效用最大化为目标。此时,它就无法直接解决话语产出的意义问题;同时,它也隐含了反信息化的假设----完全信息假设。相比较而言,如果交际以寻求优化解为目的,它就是价值最大化为目标,满意就是对价值的满足。有限理性指导下的顺应论在探究意义的优化解时,正是采取了以满意为导向的弹性策略,从而实现了意义理解与生成的实用性原点回归。
顺应论要求意义的语用期望指向优化解而非最优解,意义有三。第一,正因为意识到语用人的有限理性特点,顺应论采取跨学科视角来弥补这一不足,从而真正地回归具有现实意义而不是实验室意义的“模范交际人”[15]。第二,对于意义这个不能化归抑或化简的概念,不能仅以本体论和价值论的方法来使它单元化,而且是要认识它的根本所在和多元特点。第三,有限理性思想的介入让我们看到意义的两重性逻辑如何整合于语言人的认识当中----语言人一方面依靠意义的本体稳定性来传承可以“传承”的信息,从而保留传统与历史;语言人另一方面依靠意义的价值变异性来创造可以“重建”的信息,从而实现创新与进步。换言之,意义的本体发出的信息不断地与语境联系,使得语言人的表现性存在成为可能,而另一种稳定的逻辑保证了语言人的创新与情趣。两重性逻辑的原则使我们能够在统一性的内部保持二元性,它连接了两个既对立又互补的项目,而这正是顺应论强调意义研究中的优化解而非最优解的又一重要启示。
四、 结 语
有关语言的功能性发挥,意义研究首当其冲[7]68。顺应论发轫之初就赋予意义极大的关注,并要求意义回归复杂性。唯有在复杂性内考察意义,才能涵盖语言产出与理解中的诸多互动元素,才能客观公正地描摹意义在人类现实中的核心地位。我们结合顺应论的一手文献,细致地讨论了顺应论所倡导的“语用视角下的意义研究需要回归复杂性”这一基本命题。我们认为,顺应论对于意义复杂性的强调是它的重要区别性特征。如果说顺应论第一次为语用学系统地构建了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那么顺应论呼吁意义回归复杂性这一观点不容小觑。随着语言人在宇观语境(生存世界或者社会心理语境)和微观语境(语言语境)愈益前进,“分相”研究将会显得陈旧而又虚幻,否则语用研究的基本问题(即人的问题)将逐渐被流放到天上,似乎变成了与语用学毫不相干的游荡幽灵。正当语用学对于意义的研究似乎变得越加贫血的时候,顺应论带来了新的希望,尽管它作为一个视角所取得的成功往往被它的方法瑕疵所掩盖。显然,这个走出了意义研究“偏食症”的新视角值得学界深思,至少其包容性折射出意义如何在语言共同体内演绎本体论、价值论和认识论的多重变奏。
参考文献:
[1] Ogden C K, Richards I A. The Meaning of Meaning: A Study of the Influence of Language upon Thought and of the Science of Symbolism[M]. London: Routledge, 1952.
[2] 盛晓明. 话语规则与知识基础:语用学维度[M]. 上海:学林出版社, 2004.
[3] Marmaridou S. Pragmatic Meaning and Cognition[M].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00.
[4] 钱冠连. 语用学:统一连贯的理论框架----Verschueren J《如何理解语用学》述评[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0(3):230-232.
[5] Jaffe A. Review of Jef Verschueren's Understanding Pragmatics[J]. Language in Society, 2001(30):104-106.
[6] 谢朝群,陈新仁. 语用学三论:关联论·顺应论·模因论[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7.
[7] Verschueren J. Understanding Pragmatics[M]. London: Edward Arnold (Publishers ) Limited, 1999.
[8] Levinson S C. Minimization and Conversational Inference[M]∥Verschueren J, Bertuccelli-Papi M. The Pragmatic Perspective.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1987:61-129.
[9] 杜雄柏. 逻辑学教程[M]. 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 2001.
[10] Davidson D. Radical Interpretation in Inquires into Truth and Interpretation[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5:113.
[11] Morris C. Foundations of the Theory of Signs[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38:30.
[12] 温奇. 社会科学观念及其与哲学的关系[M]. 张庆熊,张缨,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
[13] 潘德荣. 认知与诠释[J]. 中国社会科学, 2010(3):63-73.
[14] 杨国荣. 论意义世界[J]. 中国社会科学, 2009(4):15-27.
[15] Levinson S. Pragmatic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