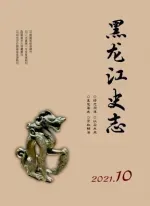晚清协饷与票号
2011-08-15郭芳芳
郭芳芳
(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00)
协饷是清政府一项重要的财政制度,它是指国家为调剂地区贫富和以应急需在省区之间进行的财政调拨方式。协饷的协济原则是先近后远,此外,各省若别有急需,应协济者,随时于邻近省分通融拨解,如果藩库银不敷用,可以动盐课或请内帑。协饷的运行基础是各省的财政经常费用支出稳定,收支平衡,并由中央政府控制。
票号产生于道光初年,主要的业务内容是商业汇兑,为日趋发展的埠际贸易服务,也为清政府收解捐纳银两。
但太平天国运动兴起后,清政府出现了财政危机,中央府库财政短缺,地方为解决财政危机想出了各种方法,最后,地方财政权增长,中央无力实行调剂,协饷制度无法正常运行。这为票号的发展提供了机会。
一、协饷解运方式的变化
协饷在清初的解运方式是官运官解,装鞘运现,不准商人参与其事。以现银方式解送饷银,清廷制定了一整套的防护措施:起解州县须饬令委解官员从通途大路行走,丢失饷银只赔一半,如果委解官员走小路,而且不请护送,导致失事的,起解州县独赔;饷银解送途中,经过州县须核对饷银的鞘数及委解官员的兵牌,以防“虚报失鞘情弊”;经过州县须派兵保护;经过州县若保护不力,以致饷银劫失,地方官须革职留任,超过一年仍未拿获盗首者,即革任,且需议赔一半饷银;委解官员须清点护解兵役的人数,将饷鞘及兵役自一至百分别排号,一一对应,“傥有疏虞,照号查究”(1)等等。这种解运方式在承平时期是非常有用的,但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南方各省、关解运饷银的道路被堵,各省不得不另想办法解运饷银。
在运饷道路的选择上,不是经由大路。如,咸丰八年(1858)各省协济安徽的军饷,清政府“以捻氛日炽,饷道不通”,谕令“此后解饷务由秦安、沂州一带行走,河南省亦由东路绕越”(2)。
委解官员是饷银运送的实施者,饷银因无法及时运送时,加强催解成了受协省份对承协省份委解官员的习惯性要求。如,咸丰十年(1860),安徽军情紧急,张芾奏催江西协饷,户部令所有江西省应解安徽的饷银,迅速筹拨,源源接济。
此为还有加强运送途中的安全工作,即增加保护饷银的人数和及时通知有关方面做好接银的准备。
尽管清政府采取了这些措施,但还是不能解决饷银运现中的问题,于是各省、关为解决协饷运解过程中的困难,开始将协饷交由票号汇解。票号汇兑官饷是从京饷开始的,最初是福建通过票号汇兑京饷的。咸丰十年(1861),时任福建布政使的张集馨写道:“浙省告警,奉拨十万两,不拘何款赶紧批解,已经解过八万矣。前奉提关税二十万,已解过十五万,并部饭三千两,交陈同恩汇兑解京矣”(3)。于是,协饷也继京饷之后由票号汇解。
同治八年(1869),山东为筹解协济贵州的饷银,仿照广东、福建拨解京饷汇兑之法,在山东事先找好信誉好的银号,然后将协饷汇兑至四川、重庆。同治四年(1865),山西河东道应解甘肃兰州协饷三次,共计银八万两,均交由平遥票商汇兑。同年,四川奉拨甘饷二万两,交票号元丰玖等字号,汇解陕西藩库。同治七年(1868),闽海关四成洋税项下,按月各拨银一万两,作为陕西协饷,交由福州阜康银号汇解。浙江协济陕甘军饷,自同治八年(1869)正月至同治十二年(1873)七月,共计四百二十八万两,均交由阜康银号汇解。到光绪六年、七年(1880、1881),又续由阜康银号汇解一百九十二万两。到光绪十九年(1893),据不完全统计,各省交由票号汇兑陕、甘、新协饷达四百六十余万两。(4)
在票号汇兑官款中,京饷占很大一部分,其次是协饷。同治元年(1862)到同治十三年(1874),票号汇兑官款共一千八百余万两,其中协饷占1.8%;光绪元年(1875)到光绪十九年(1893),共汇兑官款六千二百余万两,协饷占18.73%。
除了汇兑,票号还垫汇、垫借协饷。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各省、关财政逐步恶化,无力如期如数进行协济饷银,但受协省份和户部一直在催促,为了完成协饷任务,只好向票号借垫。时任两广总督的瑞麟说:“奉拨京饷及广储司公用定限綦严,协济各省军饷亦属急需,筹解均不容缓。而关税入不敷支,惟赖与银号商借,缓急通融”(5)。光绪四年(1878),广东省为拨解京、协各饷,已借票号之款达五十余万。
二十世纪初,广西军饷缺乏十分严重,广东财政也陷入危机,只得向票号挪借。“窃照广西师旅饥馑,相逼迭乘,军饷赈款,所需甚巨。广西既库空如洗,广东亦筹拨有限。……臣春煊焦急迫切,于前次濒往洵州时,曾商于臣常恩。臣常恩身居粤地,备悉艰难,不兹将伯之呼,忍作膜外之视。第粤海关近年应解京饷协饷及归还洋款期限甚严,周转不及,恒先从西商挪借,续由税收归还,时形断绌,积欠难清。今粤西事急,唯有仍向西商挪借洋银十二万两协济军赈,交臣春煊饬发广东藩库撙节动支”。(6)
随着清政府财政权力的下移及中央与地方财政的困难,票号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增强,不仅汇兑协饷,还开垫借政府用以协济军事。
二、票号与西征协饷
左宗棠西征,军费开支庞大,而甘肃、新疆历来是受协省份,甘肃协饷是清政府财政支出中的很大一笔。道光年间,甘肃协饷每年达404万两或415万两,除留抵外,每年实拨银达300余万两。但咸丰年间,由于财政危机,甘肃协饷屡屡欠解,每年实拨银减至302万两,同治初年,每年实拨到新疆的仅44万两,而且常年拖欠。(7)统计每年归左宗棠支配的饷银应有700余万两,但实际收到的仅500万两。尽管左宗棠屡次催解,但拖欠仍然存在。在左宗棠催饷无着的情况下,只好举借内外债。甘肃“用兵既久,官私耗竭,有时需用孔亟,储积已空,则于富室大商挪移借贷,随时归款。甘肃本地无可筹商,如协款不到,惟有借用洋商巨款及饬各台、局向附近殷实商人议息筹借,洋款则必指省、关还款,以印票为凭,借华款则必饬台、局于附近商贾会萃之区筹办,以信约为凭”(8)。
左宗棠西征借款就达11,653,730两,其中不少是向票号举借的。光绪元年(1875)到三年(1877),借款340万两,四年(1878)到六年(1880)406万两,七年(1881)到八年(1882)100万两,总计达 846万两。(9)如,光绪三年(1877),由于饷源中断,左宗棠在洋款没有借成之前,向华商借银一百一十万两。光绪四年(1878),“刘典向兰州票号借银四万两,又饬后路粮台道员王加敏息借汉商银四十万两,驻陕军需局陕安道沈应奎息借票号银二十万两,暂应急需”(10)。光绪四年(1878),第五次西征借款,胡光墉招集了沪杭苏一带的商人组织乾泰公司募股认购债票,但仅募得半数,共175万两。票号借款利息,一般低于外商借款利息率,月息为一分二厘或一分。票号借款是一种短期信用借款,一般不限银数,不拘年数,不拘期次,归还本息。
票号能够汇兑官款,除了在战乱时期它具有运解方面的方便外,还由于它的诚信。左宗棠西征虽然向票号贷款,但总是做到有借有还,极力保持信用。他曾在上海采运局向华商筹借银六十万两,但都在各省协饷到上海时分期扣还。他明确表示,他之所以“不肯爽约失信于华商票号者,正欲留此生路,为将来商借地步耳”(11)。因此,同治十二年(1873),在他攻下肃州时,清政府“拨库款一百万两,户部续拨各省、关有著之款又一百万两,内除收到七十余万两,划还各台、局代借商款,尚不敷银二十余万两”(12)。光绪元年(1875),左宗棠在他所借洋款三百万元中,又陆续划还沪、鄂、陕省先后筹借商款本利银一百二十余万两。这些事例表明,左宗棠非常重视票号在调度金融上对他军事行动的支持,票号被左宗棠视为缓急之间的生路,足以说明票号在左宗棠西北军事活动中的重要作用。
三、甲午战争后票号与协饷的关系
甲午战争后,清政府的财政收支出现了巨额亏空,原来中央指定解拨的各项的款被移作他用,京协饷制度陷于瓦解状态。由于甲午战费及赔款而举借的各项外债,除汇丰银款、汇丰镑款、俄法借款、英德借款用关税担保之外,瑞记借款、克萨镑款和续英德借款用盐厘、盐课、厘金作为担保。但因外债而挪移的地方财源必须另行解决,才能使京协饷制度运行起来,但清政府对此一筹莫展,因此也瓦解了京协饷制度,造成了中央财政调度失灵、地方财政互相割据的严重局面,各省之间的协拨实际处于瘫痪状态。而此时由于银根奇紧,票号也不敢承汇公款,“兹据署督粮道张瑄详称:查江西应解前项勇饷,先系发交商号汇兑,兹据商号以东北军务,银根奇紧,不敢承汇,自应委员起解,以济急需。”(13)
庚子事变后,各省协款的情况更糟。江苏“自盐货厘金抵换洋债以后,指拨各省协补款项欠解累累”(14)。拨补浙东厘金的“协济各饷,半存虚数”,“截至宣统元年已达七百万之多”(15)。截至光绪三十二年(1906),各省历年欠解东三省俸饷银已达389.5万两。协饷制度已处于崩溃边缘。
甲午、庚子战争后,清政府为了支付巨额赔款,大量举借外债,而这些外债大部分是通过票号汇兑的。同治元年(1862)到光绪十九年(1893),票号汇兑公款八千一百余万两,汇往各省的协饷约占14.2%,汇往上海的借款只占1.57%。而光绪十九年(1893)到宣统三年(1911),票号共汇兑公款一亿四千一百余万两,汇往上海的借款占66.25%,而汇往各省的协饷只占9.9%。因此,这一时期票号主要汇兑的是汇往上海的偿还赔款的官款。
因战争赔款的增加,各省财政入不敷出,由票号垫汇的款项,多数不能如期偿还,为了保证票号的正常运转,票庄指定用协饷做抵押。如:甘肃练兵经费每年由票号汇解,但“因举办新政,用款繁多,司道各库入不敷出,不能依期归还,票庄不肯垫解,必指定某省协饷作抵,始得勉强敷衍”(16)。
由于协饷制度的基本瓦解,各省关解往受协地区的协饷越来越少。云南是受协省份,但从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到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八月,各省欠解就近200万两,欠解贵州的协饷达500余万两。甲午战争后,票号汇兑协饷的数目自然也就减少,宣统三年,随着协饷制度的彻底瓦解,票号与协饷也就断了关系。
晚清,由于中央财力的下移,协饷制度受到影响,协饷的解运方式不再是官运官解,而且由于承协省份财力的困窘,对受协省份饷银的解送也不及时足额。作为金融机构的票号,在此时发挥了它的作用,票号开始承汇、汇兑协饷,并逐步垫汇、垫借协饷。票号汇兑、垫汇协饷,对清政府军事活动的支持,无疑使处境险恶的清政府中央财政获得了一个喘息的机会,同时也为票号赢得了利润和声誉。
注释:
(1)光绪朝《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一百六十九。
(2)《清实录》,卷 273,中华书局出版,1987年版,4页。
(3)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中华书局,1981年版,196页。
(4)张国辉:《晚清钱庄和票号研究》,中华书局,1989年版,84页。
(5)《两广总督瑞麟片》同治八年,《军机处录副奏折》。
(6)黄鉴晖:《山西票号史料》增订本,山西经济出版社,2002年版,101页。
(7)陈策:《西征协饷与晚清财政运行》,《兰州教育学院学报》,2003年第2期。
(8)《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 47,上海书店,1986年版,32—33页。
(9)周育民:《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266页。
(10)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册,662页。
(11)《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6,上海书店,1986年版,54页。
(12)《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45,上海书店,1986年版,69页。
(13)黄鉴晖:《山西票号史料》增订本,山西经济出版社,2002年版,219页。
(14)《刘坤一遗集》,第3册,中华书局,1959年版,1312页。
(15)《浙江财政说明书》,第1册,协款。
(16)傅秉鉴:《甘肃清理财政说明书》三编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