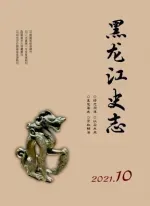战 栗——《哈尔滨档案》读后
2011-08-15钟楠
钟 楠
《哈尔滨档案》(Secrets and Spies: The H arbin Files)是一部家族寻根史类著作,讲述了一个哈尔滨的俄侨家族在上世纪30年代回到祖国后的悲惨命运。在大清洗运动中,家族五名成员悉数被捕,两人被“镇压”,一人死于集中营,两人被判刑。罪名都是莫须有的日本间谍。本书作者是家族的后裔,出生在哈尔滨的玛拉·穆斯塔芬女士,50年代她随父母移居澳大利亚。
本书英文版2002年在澳大利亚出版后,广受好评并屡屡获奖。2008年中文版由中华书局出版后也备受瞩目,一度登上畅销书排行榜。著名作家王蒙的评语是:“《哈尔滨档案》给人以大震动、大悲怆,正视历史也如正视现实,要能战栗,能不战栗。至少不能转过脸去。正视至少能让人记住哪怕是前进一小步。遗忘与躲避只能是无可救药地走向死亡。”
一、回家
1935 年,苏联政府单方将中东铁路转手给伪满政府后,陆续从哈尔滨等铁路沿线城市撤回苏籍员工。之前为生计不得不领取苏联护照的“红萝卜”白俄,再次面临抉择,或是去红色苏联,或是滞留在原居住地。他们很清楚,如果要留下来,就必须忍受日本人,那个“从树上下来得太早”的族群的欺压和凌辱。当然,也有第三条路可走,移居天津、上海的租界区或是去第三国。但是对普通苏侨或俄侨家庭而言,这个按钮呈现为灰色的锁死状,只有极少数富裕家庭才能点击进入。如此状况下,返回苏联就成了大多数人的选项。
据不完全统计,中东铁路转让后,大约有三万名哈尔滨俄罗斯人返回了前苏联,其中包括数千名临时办理苏联护照的无国籍白俄。在浩荡的返乡人流中就包括《哈尔滨档案》一书中的主人公一家五口人。
我相信这些人在做出回国的决定以前,一定充分考虑到了回国后的种种可能。白眼、训斥和政治审查之类的待遇不难预料。从政治立场上说,他们起码属于帮扶对象,动摇分子。即便如此,也好过日本刺刀的威胁。这样的结果大约是人们想象的底线了。何况此前回国的亲友们的反馈光明而美好。全苏正在掀起建设社会主义高潮,工作容易找到,政治气氛宽松和谐,某某家的二闺女还成了共青团团员……可惜人们无法预知这美好的情景不过是昙花一现的海市蜃楼,而潘多拉的盒子一旦打开是没有任何力量能够约束的,邪恶就像一个无底洞,没有底线,希望却被潘多拉关闭在盒子中。
后来的事实证明,从哈尔滨返乡的苏侨走向了一条不归路,等待他们的是一场看不到头的铁色长夜。前苏联最黑暗的历史时期,1935开始的大清洗运动扑面而至。
二、战栗
前苏联大清洗运动又称肃反运动,目的是肃清所谓潜伏在革命队伍中的反革命分子。从哈尔滨回国的侨胞只是这次运动中被打击的一个小群体,他们的经历大致相仿,都有过在中国东北生活的经历。而遭受的命运与其他受迫害的公民并无本质区别。运动中,除斯大林之外的所有苏联人,无人能置身事外,无人能摆脱命运的安排。每个人都像是一颗螺丝钉,或是被拧在国家机器上,或是被随意丢弃,包括斯大林的帮凶。
从哈尔滨归国的侨民命运之所以让人感到尤为悲惨,首先是因为他们的人生本是另外的样子。就像《哈尔滨档案》作者十分不解她的曾外祖父一家为什么要回到苏联,为什么不去上海,甚至于可以像她的外祖父母一样赖在哈尔滨不走。她当然找不到答案,她能找到的只有前克格勃封存的血色档案。她的先辈一家五口人在大清洗运动中悉数被捕,其中两人被迅速处死,一人在监狱被折磨致死,另外两人被关入劳改营,并有幸活到了赫鲁晓夫时代,五十年代中期被平反。其次,这些回国侨胞的命运更类似于集体乘坐了一架失事客机,没有一名乘客可以置身事外。如果说普通的苏联公民还可以心怀侥幸地躲过浩劫,那么,“哈尔滨人”所能奢求的只有活下去,就像电影《芙蓉镇》中的那句经典台词,“像狗一样活下去。”
所谓“哈尔滨人”,是当时苏联内务部命名的概念,范围包括苏联成立后流亡到哈尔滨的俄国人,包括在满洲里、海拉尔等中国边境城市居住过,哪怕只呆过几天的人,也包括撤退到苏联境内的中国抗联战士,如赵尚志烈士,甚至还包括更早之前,苏联刚刚成立时从哈尔滨等地投身祖国的侨民。这些早期回国的侨民并非是“红萝卜”,他们确实心系苏维埃,向往红彤彤的世界,但是他们和后来者有一条共同的属性,曾经在哈尔滨生活过。
这起针对哈尔滨人的清洗行动,是苏联肃反运动中的一条枝蔓,官方代号为“00593号命令”,领导者是苏共内务部及秘密警察领导人叶若夫,据不完全统计,“00593号命令”导致近五万名“哈尔滨人”被捕,其中30992人被镇压。
身高1.51米的叶若夫也有一个属性,就像人们暗地里送给他的绰号,“血腥的侏儒”。而00593号命令不过是他罄竹难书罪行中的几枚竹叶。当叶若夫干掉了相对保守的前任格里赫·雅戈达;干掉了百分之七十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干掉了百分之八十的高级军官,包括苏军15位集团军司令中的13人,85位军长中的57人,159位师长中的110人;并逮捕了半数党员,大约120万人,还把10万5千名神父还给了上帝。当他超额完成斯大林旨意后,他的使命也就到了结束的时刻。1938年11月,随着第三位恐怖金刚,拉甫连季·贝利亚登场,叶若夫随即被捕,和他的前任一样,在一间地下室中被秘密处决。
之后的情节就像我们看过了无数遍的大戏,罪恶由叶若夫承担,伟大的斯大林同志被蒙蔽了。但是肃反运动的方向是正确的,也是必要的,还要进行到底。随后苏德战争爆发,肃反对象暂时得以解脱,其中三百三十多万劳改犯得以从全国各地集中营中释放,以补充临阵掉转枪口的“俄奸”所造成的战力缺口。但是战争结束后,肃反运动再掀高潮。1948年,仅古拉格群岛劳改营就新增罪犯230万人,创历史新高。
苏联肃反运动造成的死亡人数现已无法查实,其中档案显示,斯大林在1937—1938年的时间里亲笔签署的处决名单就有681692人。他当然不会像中国皇帝那般在每个名字上朱笔画勾,否则他再夜以继日的工作也难以在一年多时间里勾掉68万条性命。大约像他批准屠杀波兰战俘,即卡廷惨案那样,一纸命令就干掉了两万多名波兰精英。另外有一个间接数字大致可以反映肃反运动的规模。据俄罗斯联邦90年代公布的数据显示,1921—1954年,前苏联有四百多万人因“反革命罪”遭枪决、监禁和流放。其中半数发生在大清洗期间。不知道“反革命罪”是笼统的说法,还是具体罪行。比如被处决的苏军高级将领的罪行是叛国罪和谋杀罪。而近五万名“哈尔滨人”,可以组建成两个日本师团的归国侨胞属于日本间谍罪。
布哈林在被捕前几天给苏共几位领导人写过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我就要离开人间了,我不是在无产阶级的斧钺下低下了我的头,无产阶级斧钺虽然是无情的,但也应该是纯洁的。我在万恶的机器面前是无能为力的,这台机器居然使用了中世纪的方法,拥有无比强大的力量,大量地炮制有组织的造谣、诽谤。这些万能的机构能把任何中央委员,任何党员磨成粉末,把他变成叛徒,恐怖分子,暗害分子,间谍。如果斯大林对自己产生怀疑的话,那这个机构也会立即找到证据的。”
更令人无助的是,斯大林创造的“反革命罪”模式、清洗模式在赫鲁晓夫上台后并没有终结。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影响深远,波及到了半个地球,直至苏联解体。
三、红与白
用不同的颜色代表不同的意识形态,现在看来是一种有趣的比喻。几十年前,却意味着如不共戴天,你死我活,是革命与反革命的原则性问题。
哈尔滨开发的第一个二十年间,侨居在哈尔滨的俄国人不存在温饱问题,加之主流势力都是沙俄政策的既得利益者,对苏维埃政权也就谈不上有好感。十月革命后,流亡到哈尔滨的赤贫俄侨增多,苏维埃的意识形态逐步在产业工人中产生了影响。红白之争开始浮现水面。对于大多数忙于生计的小市民阶层,属性却很难界定,每一次风吹草动就可能改变阵营。这很正常,谁能解决大家吃饭问题,大家就会拥护谁。所以在意识形态的世界里,大多数人都是墙头草。1925年以前,多数人心系旧政权,哈尔滨也被称为“白俄之都”。苏俄重掌中东路后,颁布命令,中东铁路只录用中苏两国国籍的员工。命令下达的第二年,八万名白俄有三万人变成了苏联人,其中部分人回到苏联垦荒。另外的五万人坚持原来身份,成为无国籍白俄。这些人除部分南下天津和上海,大多数仍滞留在哈尔滨。日军入侵后,中东铁路易主,又有部分白俄改换门庭,随苏侨回国。至此,只有一万五千名俄侨居住在哈尔滨。1945年苏军进入东北,大多数人领取了苏联护照并回国垦荒,而知识分子一般还可以从事原来的职业,如创办哈尔滨“荷花”艺术学校的著名画家基齐金,他是从上海携妻子返回苏联的。从当事人的回忆录看,大清洗运动后回国的俄侨,虽然在哈尔滨生活的经历不再意味着反革命,但是仍属于一个不光彩的烙印,因而回国后都碌碌无为、郁郁寡欢。至于在日军占领期间反对过苏联或是与日本当局关系密切的白俄则遭到清算和镇压,如哈尔滨巨商斯基德尔斯基兄弟。
俄侨或苏侨最后离开哈尔滨的时间是50年代。当时的苏联是赫鲁晓夫执政,他否定斯大林的做法得到了包括哈尔滨侨胞们的拥护,因而大多数人最终还是回到了苏联,少部分聪明人移居其他国家,如作者的父母。
四、价值和价值观
《哈尔滨档案》的人文价值在于作者通过对其家族显微镜般的观察,深刻地展示了前苏联大清洗运动的真相,令人触目惊心。透过冰山的一角,我们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罪恶和悲剧其实并不遥远,更非谎言和故事,而是活生生的现实。唯一不同的是当代人更幸运,没降生到那个黑色的年代。而罪恶一旦降临,悲剧拉开序幕,普通人就只能随波逐流,就像风暴中的一叶扁舟。
对于通过文字走进这段历史的后人来说,除了震惊,大概还会有一种无能为力的感觉。就像索尔仁尼琴在其著作《古拉格群岛》写下的献辞:“献给没有生存下来的诸君,要叙述此事他们已无能为力。但愿他们原谅我,没有看到一切,没有想起一切,没有猜到一切。”
至于本书所要弘扬的价值观,即如何避免悲剧重演,可以引用前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对大清洗运动的总结。
2007 年底,普京在莫斯科南郊“布托沃射击场”的大清洗纪念地发表了演讲,他说:“这样的悲剧曾在人类历史上反复上演,其原因是那些看似吸引人的空洞理想被置于人类的基本价值观——珍视生命、人权和自由之上。”
当我读罢《哈尔滨档案》一书的最后一个文字,一股异样的情绪紧紧地裹住了我,不完全是震撼和悲悯,更近似于被掏空了的感觉,情感和灵魂正在离我而去。如同一尊木乃伊,人世间的喜怒哀乐都不再和我有关;亦或是变成了祖国的陌生人,站在熟悉的街道上却找不到回家的路,想要打听下却发不出任何声音。
奇怪的是我毫无恐惧,就像看清楚了自己的未来而无惧死亡一样。或许本文开头引用的王蒙的评语正是我想说的。
“正视历史也如正视现实,要能战栗,能不战栗。至少不能转过脸去。正视至少能让人记住哪怕是前进一小步。遗忘与躲避只能是无可救药地走向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