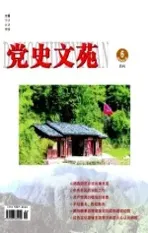我父亲周伯勋的银幕前后
2011-08-10周治平口述王岚整理
周治平 口述 王岚 整理

2009年3月,在纪念“左联”成立80周年座谈会上,笔者有幸见到了周扬、夏衍、冯雪峰、丁玲、周文等“左联”人士的子女,其中还有周伯勋的儿子周治平先生。周治平先生的叙述,让《一江春水向东流》中的庞浩公、《武训传》中的张举人、《鸡毛信》中的“猫眼”司令等角色,再次活生生地出现在笔者眼前。而这些角色的塑造者周伯勋,是一名杰出的演员。我国早期无声电影《玉堂春》中就有他的角色,那是他正式踏进影坛的第一部作品。此后几十年,他在几十部电影中扮演了许多令人难忘的角色。但他不仅仅是一名演员,早年即在文艺界领导人阳翰笙直接领导下,积极投身抗日,与田汉、聂耳等在战斗中结下深厚的友谊;他还根据党的指示,活跃在电影界、戏剧界,并把获取的一些情报通过弟弟周伯涛快速交给我党高层领导,是一名潜伏在影幕后的红色蝶报;解放后,他一度担任过国泰电影制片厂厂长,在周扬、夏衍等领导下工作。此后一直在上海电影制片厂担任演员兼制片主任,相继拍摄了《武训传》《聂耳》《尤三姐》《望江亭》等影片。因为周伯勋曾经拒绝过江青当基本演员和任主角的要求及了解她的一些丑史,“文化大革命”中遭到政治迫害。去世后,海内外许多主要媒体发了消息,给予他很高的评价。周伯勋一生丰富曲折的经历,随着时代的发展,已经成为历史了。我们只能掀起历史的盖头,借助他儿子的回忆探寻这位历史人物。
结识田汉,在阳翰笙直接领导下工作
我的父亲周伯勋,1911年4月22日生于古都西安。1929年他来到上海,经同乡郑伯奇介绍,考入创造社主办的上海艺术大学中文系学习,次年即加入田汉主办的南国社。田汉是我国杰出的话剧、戏曲、歌词作家,电影剧本作家,小说家,诗人,文艺批评家,社会活动家,中国现代戏剧的奠基人,更是一位卓越的文艺工作领导者。他早年留学日本,成立创造社,1920年代开始戏剧活动。我父亲参加南国社不久,经田汉、郑伯奇介绍,又加入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从此走上为革命为艺术献身之路。
1931年,我父亲和田汉等一起创办大道剧社,任演员兼总务组长。“九一八”前后,在上海、杭州、苏州等地,演出了《火的洗礼》《SOS》《乱钟》和《暴风雨中的七个女性》等进步戏剧,颇受大、中学生和爱国知识分子的欢迎。当年共产国际的刊物上也专门发文介绍,赞扬他们为积极抗日所做的演出。大道剧社成员还积极推动上海各大学及部分中学的爱国戏剧活动,组织学生抗日示威游行。此后,引起上海租界巡捕房的注意,剧社活动越来越困难了。
20世纪30年代初,为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共产党派大批干部深入到各个电影制片公司。1933年,我父亲周伯勋协助田汉、阳翰笙创办艺华影业公司。阳翰笙是我国著名的编剧、戏剧家、作家,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之一,原名欧阳本义,字继修,四川高县人,1927年年底参加创造社。1928年初起陆续发表小说,并撰写宣传马克思主义和革命文艺理论的文章。1933年起创作电影剧本 《铁板红泪录》《中国海的怒潮》《逃亡》《生之哀歌》《生死同心》《夜奔》和《草莽英雄》等。抗战期间曾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主任秘书、文化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电影制片厂编导委员会主任等职。在艺华影业公司,我父亲任总顾问室秘书兼演员,在阳翰笙直接领导下工作。
1936年西安抗日风起云涌,我父亲应邀返西安,任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宣传部副部长、西安实验剧团副团长兼导演和演员,他导演了话剧《春风秋雨》《未登记的同志》《日出》和《雷雨》等,为我党领导的抗日统一战线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当时演出就在我祖父开的阿房宫大戏院上演,票价很低,为的是让更多百姓都能来看。期间,我父亲多次受到周恩来的接见。
1938年10月,根据阳翰笙的要求,我父亲离开西安到重庆,参加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领导下的中国电影制片厂,任演员兼剧务科长。他还担任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文艺组副组长,受到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的多次接见和指导。
1940年初,中国制片厂拍摄阳翰笙编剧的《塞上风云》时,剧务主任是我父亲,他和导演应云卫率领摄影队去内蒙拍外景。离开西安后,西北王胡宗南派人装扮成绿林好汉,多次恐吓威胁他们,意欲阻止他们去延安。但他们多次粉碎了胡宗南的阻挠和破坏,快速而坚定地踏上了去延安的道路。其实,临行前,周恩来给他们开了介绍信并叮嘱他们:去延安后,一个都不许留在延安,以免给国民党顽固派落下话柄。当我父亲他们特意绕道延安后,受到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的接见和招待。冼星海亲自为他们指挥演唱了《黄河大合唱》。我父亲和应云卫在延安的欢迎会上,作为国统区电影界代表发言致谢。此行对他一生产生了重要影响。
与田汉、聂耳的友谊

1933年周伯勋在自家弄堂为聂耳学溜冰留下的影像
从1932年初到1935年聂耳去日本,是我父亲和聂耳往来最密切的时期,那时他们都是爱好文艺的热血青年。
聂耳(1912—1935),原名聂守信,字子义(亦作紫艺),汉族,云南玉溪人。他从小家境贫寒,对劳苦大众有深厚的感情。他在有限的生命中创作了数十首革命歌曲,他的一系列作品,反映了底层劳动人民的声音。聂耳开辟了中国新音乐的道路,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音乐先驱,天才的人民艺术家。
1931年,我父亲在电通影业公司除了负责剧务、演员,还是《电通画报》编辑,常约聂耳写稿。聂耳则是黎锦晖主办的明月歌舞团的练习员,黎锦晖对他有知遇之恩,因为在聂耳最落泊时,是黎锦晖接纳了他,让他能够有一份收入,不至于流浪街头。但聂耳对明月歌舞团出于经济考虑,经常演出迎合社会小市民的靡靡之音很反感,就以“黑天使”的笔名写批评文章,不惜得罪老板黎锦晖。聂耳的大胆举动,在明月的人看来无疑是吃里扒外,甚至是忘恩负义。有人当面责骂他,也有人暗地里劝他,聂耳很苦闷,但他已然将生死抛于脑后,后来更是主动请辞。但这样一来,生计就成了问题。于是,他来找挚友、我的父亲周伯勋,希望老朋友能帮助他走出困境。我父亲那时刚从西安到上海,自己借住在青年会宾馆,见好友空怀一腔报国心和满腹才华而无用武之地,就诚恳地对他说:“上海我不熟,但我可以介绍你去西安,那里有我许多朋友,而且那里很缺音乐老师。”
聂耳知道我父亲认识文艺界风云人物田汉,自己也非常仰慕,就请我父亲介绍和田汉认识。我父亲马上答应并很快安排他们在一个朋友家里见面。这次见面,让聂耳看清了人生的方向。后来聂耳离开了 “明月歌舞剧社”,虽然没去西安,但他到了距离抗日前线较近的北平。1932年11月,聂耳从北平又回到上海,先后在联华影业公司一厂、百代唱片公司、联华影业公司二厂为电影配音和作曲。1933年,聂耳由田汉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可以说,是我父亲促成了中国音乐史上两位伟大的音乐家的携手合作,之后田汉很多电影音乐都找聂耳来作曲。聂耳为田汉的歌剧《扬子江的暴风雨》创作了《打砖歌》《打桩歌》《码头工人歌》《前进歌》,为电影《桃李劫》谱写了主题歌《毕业歌》,为电影《大路》谱写了主题歌《大路歌》和插曲《开路先锋》,等等。聂耳作曲的《卖报歌》,让人记住了那个卖报的小女孩杨碧君。聂耳之所以能成为伟大的音乐家,除了他的天分外,还得益于他和普通劳动人民的广泛接触,并能聆听他们内心的真诚呼唤。写《卖报歌》时,他常常去街头观察那些小孩,好几次,他还拉上我父亲周伯勋一起去,并征求他的意见。当年田汉写完《风云儿女》的主题歌词《义勇军进行曲》,还没来得及交给聂耳,就被国民党抓走。聂耳得知夏衍拿到了歌词,就主动要求夏衍让他来作曲。聂耳在上海只用两天时间就写成了草稿,因受国民党追捕,便逃往日本。在异国,他怀着对祖国的无限思念完成了作曲,并托人寄回了祖国。1935年7月17日,年仅23岁的聂耳在日本藤泽市游泳时不幸溺水身亡,作词者和作曲者倾心完成的作品从此成了绝唱。
聂耳工作之余喜欢运动,他常常去我父亲家。有时候在家里坐不长时间,他就会拿根绳子到弄堂里去跳绳,或者到弄堂里打篮球、溜冰。大多数时候,酷爱摄影的我的父亲就会拿着照相机跟在后面,给聂耳拍下许多生动的照片,让后人看到了一个立体的、年轻的、伟大的音乐家。
这些事,在聂耳的日记中都有所记载。但我父亲却从没和人讲过,而是一个研究聂耳的日本专家通过聂耳的日记发现后,来向我父亲求证。我父亲告诉那位日本朋友确有其事,同时也告诉他,这样两位优秀的人物在那样的时代就算没有他介绍,也会有人给他们介绍,他们总要相遇,总会合作,创作出传世之作的。
活跃影界,拍了许多进步电影
1934年春,在党的领导下,我父亲周伯勋参与“电通影业公司”的创办,任演员组长兼总务、剧务发行、宣传及《电通画报》编辑等职,并和田汉、阳翰笙、司徒慧敏等成为我党领导下的“电通影业公司”业务骨干,电通因此成为左翼电影的大本营。但电通因为拍了一系列宣传抗日的进步电影,比如风靡一时的《桃李劫》《自由神》《都市风光》和《风云儿女》等,被国民党视为“赤色大本营”。
1935年下半年,国民党政府逮捕了田汉和阳翰笙,“电通影业公司”被迫停止活动,创作人员被迫转移。我父亲周伯勋协助地下党组织,以上海影剧社名义,组织演员到南京等地演出了具有革命内容和宣传我党团结抗日内容的话剧,有《回春之曲》《洪水》《黎明之前》等,将抗日戏剧演到国民党的心脏,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周伯勋1934年为聂耳(右一)、金焰、王人美拍的照片

《一江春水向东流》剧照
抗战胜利前夕,受党指示,我父亲和司徒慧敏、徐韬等参加了凤凰影业公司的筹建,后改为昆仑影业公司,是当时进步电影的中心,也遭到了国民党的破坏。
日本投降后,我父亲到上海主持拍摄了《八千里路云和月》和《一江春水向东流》等电影,他分别担任制片主任和重要角色,上映后轰动整个影坛,《一江春水向东流》当年曾获南京国民政府“中正电影艺术奖”。解放后,该片又获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优秀电影奖”。
为了扩大我党对电影事业的领导和影响,1947年底按照阳翰笙的指示,我父亲离开昆仑到了国泰影业公司,担任艺术厂长和艺术委员会主任,对改变公司亲国民党拍摄方向起了很大作用,并通过自己的工作,主动邀请田汉、夏衍、于伶创作进步影片,迎接上海解放。
生于西安,根落在上海
我的祖父出身很苦,从小到盐庄去当小工,但他聪明、勤奋、努力,很快就由小工升为主管,后来又接收了老板的盐庄。从盐庄开始又搞药房,开戏院,做地产,从此富甲一方,被选为西安市商会会长。我祖父一心要把来之不易的家产传给两个儿子,但他万万没想到他的两个儿子却不恋优越的家庭生活,都跑到上海参加了进步影剧活动,还经常遭到国民党的追捕。为了把两个喜欢唱戏演剧的儿子留在家里,他不惜拿出全部家产集资建造了阿房宫大戏院——西安第一家无柱子戏院,既可以唱戏,又可以放电影。它的建成,可以说是西安文化设施建设方面的一个重大成就,当年曾轰动一时。解放后,我父亲周伯勋和我叔叔周伯涛兄弟俩商量:“我们革命半辈子,不能当资本家,还是交给国家吧。”就这样他俩不拿一分钱,就把阿房宫大戏院交给了国家。现在阿房宫大戏院有9个放映厅,还是西安较大的剧院。
我父亲和叔叔离开了西安老家,但却一辈子没有离开过心爱的艺术世界,虽然在这个世界中他们的人生跌宕起伏,走着不同寻常的坎坷路。
《塞上风云》拍完后,皖南事变发生了。我父亲请示阳翰笙后,离开中国电影制片厂去了昆仑电影制片厂的前身凤凰电影公司,那是爱国商人夏云湖办的公司。夏云湖有三个电影院,我父亲被任命为主管影院业务的负责人。我父亲协助贯彻党的意图,争取夏云湖,为抗战后与夏云湖的合作做准备。抗战期间我父亲还被任命为军委会文艺组副组长,具体工作就是安排蒋介石等高级将领看戏。这一有利条件让我父亲如鱼得水,一旦知道蒋介石的任何行动消息,就马上通知弟弟周伯涛,周伯涛再报告给地下党。

《一江春水向东流》剧照
有人说我叔叔周伯涛没出息,只能靠哥哥演一些小角色,其实他也是一名中共地下党员,只不过是以一个普通演员的身份出现在公众视野中,但事实上他在哥哥的影响下,参与了很多抗日工作。解放后一直在文化系统工作。在和苏联合拍的记录电影《中国人民的胜利》和《解放了的新中国》2部片子中担任中方导演,获得斯大林文艺一等奖。为了抗美援朝,他代表剧组把全部奖金10万卢布捐给志愿军买了飞机大炮。1957年,他离开上海电影制片厂,被组织派到苏联和民主德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去学习管理知识。学成回来后,他参与筹办上海电视台并担任副台长兼总导演。“文化大革命”中历经磨难,造反派把他打得浑身是伤,连扁担都打断了,因为他去过苏联,就被诬蔑为“苏修特务”。直到粉碎“四人帮”后才恢复工作。改革开放后,我叔叔曾经担任上海广电局副局长。20世纪80年代中期离休,享受厅局级待遇。上海电视台有意把影坛周氏两兄弟的坎坷人生拍成电影,有编剧连剧本都写好了,但最终被我叔叔阻止了。他一直对子女说:我是党的文化干部,党叫干啥就干啥,个人没有什么值得宣传的。
当年电通影业公司的《风云儿女》即将完成时,蓝萍经人介绍进入了“电通”,她曾经演过话剧《娜拉》,那时也已小有名气。此时“电通”正在筹拍由夏衍编剧的《自由神》,安排她在片中演女兵余月英,此外主演还有王莹、周伯勋、吴湄等。因为我父亲是剧务主任,分配角色有一定权威,还掌管着所有演职员的薪水发放,蓝萍便向他提出做主演,还要求做一名有固定月薪的基本演员,我父亲感到为难,就婉拒了她。不料“文化大革命”中成为我父亲被整的一个不是理由的理由,他的问题被无端拔高,竟然与陈丕显、曹荻秋等一同被“监护”在一起。
1952年起我父亲任上海电影制片厂演员兼制片主任。其实,他本来有机会去北京出任文化部门的厅、局长的,但他选择留在了上海,在上海电影制片厂成立后的第一部故事片 《鸡毛信》中扮演日军“猫眼司令”。随后又主演了《球场风波》及《三年》《球迷》《红色种子》,主持拍摄了《聂耳》和《望江亭》等影片。十年“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四人帮”的残酷迫害。粉碎“四人帮”后,我父亲恢复了名誉,还被选为代表出席了全国第四届文代会,受到邓小平等中央领导的接见。此后,我父亲遵从阳翰笙等老友、老领导的意见,积极从事写作。在上海《文汇报》、北京《大众电影》《电影画报》、西安《电影之窗》《西安晚报》和《山城电影》《羊城晚报》等全国多家著名报刊上发表了150余篇文章,以亲身经历,记述了中国电影事业的发展历程,给后人留下许多宝贵的历史资料。在粉碎“四人帮”的前一天,他揭露江青的一篇文章就刊发在《羊城晚报》的头版报眼上。作为经历过新旧两个时代的中国老一辈电影人,他还发掘培养了一批演员,例如《一江春水向东流》里的主角陶金、《羊城暗哨》主角冯喆等。他还多次接受海内外媒体、专家的报导和访问。
我父亲在他一生近40年的电影、舞台生涯中,共饰演了几十个经历不同、身份各异的反面人物。他力主反派正演,是中国影坛上以擅演反派角色的老演员之一。他还曾是中国电影工作者联谊会理事。

第三次文代会上周伯勋受周总理接见
1987年8月30日,我父亲在上海因病去世。他去世后,上海的 《解放日报》 《文汇报》 《新民晚报》等主流媒体以及中国台湾、香港和美国等国家 (地区)的许多报刊发文哀悼。如果他只是一名演员,那真是超规格了。关键是,我父亲周伯勋不仅仅是一名演员。父亲去世后,我们给著名作家、时任中国文学艺术家联合会副主席的阳翰笙写了封信。当时他正在烟台休养,知道我父亲去世后特意发来电报,电文如下:“惊闻周伯勋同志病逝,不胜哀悼。伯勋同志是左翼戏剧电影运动早期的积极的参加者,他是一个优秀的表演艺术家,几十年来,在党的领导下,为中国革命戏剧和电影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谨向伯勋同志的亲属表示亲切的慰问。我同意做周伯勋同志治丧委员会委员。”我父亲的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是吴贻弓,治丧委员会委员除了阳翰笙外,还有于伶、夏衍、夏征农、陈沂、袁文殊、巴金、石方禹、张骏祥、白杨、徐桑楚和秦怡等30位各级领导和文学艺术界知名人士,出席追悼会的有各界人士共300余人。悼念活动是很隆重的。
题图 周伯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