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之树》:叙事电影的反叙事化
2011-08-02刘小磊
刘小磊
刘小磊: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讲师
“正是生命之树的枝桠伸展的地方。我们看到无从探源的光芒,广阔的星云,移动的星辰,成形前的星球,太阳和月亮被黑风暴所阻挡,给予生命能量的一道道闪电,汩汩地悸动着的原始湖泊,史前植物、动物,缓缓舞蹈的水母,双髻鲨,栖身河岸的恐龙,一个胎儿的眼睛,以及最重要的,初生的孩子。”
——《生命之树》独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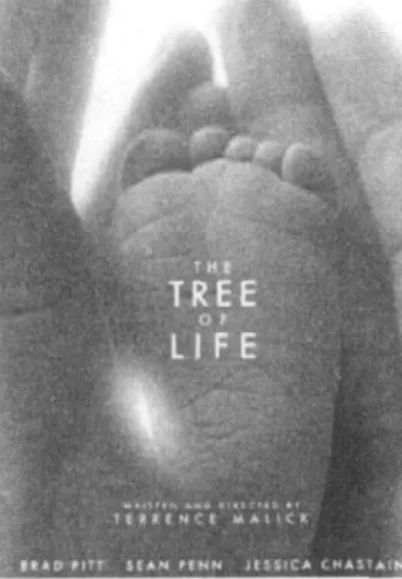


2011年10月6日,瑞典文学院宣布将2011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瑞典诗人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给予他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词是:“经过他那简练、透通的意象,让我们用崭新的方式来体验现实世界”。这句颁奖词或许也可以送给获得今年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大奖的影片《生命之树》。
但泰伦斯·马利克(Terrence Malick)的《生命之树》自获奖以来一直引发巨大的争议,有人认为这是一部博大精深、精致美妙的史诗佳作,也有人认为这只是一部矫揉造作、故弄玄虚的意识流之作。分歧的争议点聚焦在“美轮美奂的画面镜头、悲天悯人的宗教命题和支离破碎的叙事内容”三者的无法对接。一部139分钟的影片带给观众的是一次费解又意犹未尽的观影体验。然而,如果对影片进行剥丝抽茧似的解析,我们会惊讶地发现:这部貌似打破叙事规则的影片恰恰是最大限度地遵从了好莱坞最传统的叙事法则。
一、叙事法则——一个泛家庭化的故事
《生命之树》从表面看没有条分缕析的故事线索,也没有深刻集中的人物刻画。但将支离破碎的细节进行重新整合后又会发现,这是一个最好莱坞式的泛家庭化故事,遵从了一切传统的人物塑造和叙事法则。
影片以《约伯记》开篇。这既是一个宗教背景,也是一个哲学背景。《圣经》中的约伯正直、敬神,从不做不义之事。他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妻子为他生了七个儿子三个女儿,他还有7000只羊、3000只骆驼、500头牛和500头驴,以及成群的奴仆,上帝认为他是最正直敬神的人。有一天,撒旦混在天使中对上帝说“约伯怎么会敬神?因为你保护他的一切。要是你毁了他的一切,他还会敬奉你吗?”上帝对撒旦说“好吧,我现在把他的一切都交给你。”于是,约伯失去了一切。但约伯仍然一如既往地信仰上帝,上帝非常开心,还给了约伯14000只羊、6000只骆驼、2000头牛和1000头驴。妻子为他生了七个儿子三个女儿。约伯又活了140年,得见幸福。
《生命之树》以这样的开篇提出了好莱坞惯常表现的两个主题:家庭与信仰,故事在美国一家五口人的平凡家庭琐事中展开。布拉德·皮特(Brad Pitt)饰演的父亲是个事业无成的中年男人,年轻时的他极具音乐天赋却放弃理想,做了一名普通的工程师。但是他发明的专利无人问津,尽管他工作勤奋、从不请假,“甚至连星期天都没有休息”,但他为之奉献了大半辈子的工厂依然面临倒闭的命运。他将自己所有未实现的理想和对于成功的判断标准都强加在三个儿子身上:逼儿子学钢琴,在家中实施近乎苛刻的家教,教他们打架,教育他们不能对人仁慈、不能被他人利用。父亲的所有行为都是在“美国梦”破灭后对美国普世价值的一种变相反抗和消解。杰西卡·查斯坦(Jessica Chastain)饰演的母亲则带有强烈的符号性,她是基督教信仰的化身,带有着圣母玛利亚般的光晕。母亲宽容、感恩,用爱来教育孩子,并保护孩子远离父亲的家暴。
电影的节奏是由三个儿子从出生到成长的整个过程控制和切分的,以大儿子杰克为视点和主轴,以小儿子的死亡为重要的转折点。儿子刚出生时的画面纯净无暇,充满着童趣和快乐,随着年龄的增长,当他们开始有了自我意识、认知和辨析能力后,生活也开始从纯粹简单向复杂而充满未知和危机的状态转变。杰克在目睹了饥饿、贫穷和死亡后,开始对世界感到恐惧;父亲的严苛教育让他学会了被迫的迎合和顺从。母亲施予的“爱”在面对强权和暴力时则带有着太多的无力感。于是,“俄狄浦斯情结”再次出现。《生命之树》在展现杰克成长时有两次重要的“俄狄浦斯再现”:
第一次是父亲在车底修车,杰克慢慢走向支撑汽车的千斤顶,他沉默地徘徊在周围,嘴里小声嘟囔着“上帝啊,让他死吧;上帝啊,让他死吧”。儿子必须要透过杀死父亲才能够确立一个独立的“我”,才能作为一个真正的主体而存在。
第二次是处于性启蒙时期的杰克满脸通红、鬼鬼祟祟地闯入邻居的卧室,翻找女主人的内衣。一缕阳光射进来,杰克迎着阳光,仿佛捧起一件圣袍般地举起那件女主人的睡袍仔细观看,然后把它偷走,让它随着河流飘走。杰克表现出的是一个男孩子在青春期对“性”图腾般的膜拜。
一直以来,“俄狄浦斯情结”是好莱坞叙事电影的重要法则,在宣扬“自由、平等、博爱”的信仰教义的美国最注重的就是作为“个体”的成长。这个成长的过程必然是混沌中的破旧立新,父亲也成为阻碍个人成长的重要符号。从经典好莱坞时期希区柯克的电影,到新好莱坞时期的《毕业生》、《教父》甚至最近的《贝奥武夫》、《猩球崛起》……好莱坞电影大多呈现出一种凸显个人成长的“泛家庭化”倾向,这符合了美国对电影一直以来所强调的“信仰教义”,电影希望观众直面的是《约伯记》中所提出的问题:“假如撒旦拿走上帝的恩赐,你该如何面对?”
《生命之树》给出的答案是多年后的杰克(西恩·潘[Sean Penn]饰演)还是被父亲的潜移默化所影响,置身于现代的社会机器之中,多个仰拍镜头和低机位跟进的镜头凸显出杰克身心的疲惫与压抑,他与父亲实现了和解,更使得所有人最后在天堂相聚。
如果给《生命之树》脱去耀眼夺目的华丽外衣,它讲述的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故事:从一家人单纯快乐的生活,到逐渐加深的隔阂与矛盾,再到最后的化解和体谅。这是一个典型的“泛家庭化”好莱坞叙事,但是泰伦斯·马利克用反叙事化的表现手段给一则叙事故事加上了哲学的注解。
二、反叙事化——一首生命起源的赞美诗
泰伦斯·马利克是一位诗性导演,他习惯于用一种反叙事化的方式去讲一个通俗的故事,这在他为数不多的作品《天堂之日》、《不毛之地》和《新世界》等都有所表现。但是和其他习惯于碎片叙事的导演不同,马利克基于的最根本的表达立场是源于生命之初的“新道德价值观”,这也是在他所有作品中一以贯之的。
新道德价值观是哲学家尼采对于道德自然主义的重构,尼采认为“我制定一个原则:道德中的每一种自然主义,也就是每一种健康的道德,都是受生命本能支配的……相反,反自然的道德,也就是几乎每一种迄今为止被倡导、推崇、鼓吹的道德,都是反对生命本能的,它们是对生命本能的隐蔽的或公开的、肆无忌惮的谴责”。尼采明确地把他所倡导的新道德价值称为以生命本能为基础的道德。他肯定个人生命应该从自然欲望出发,强调个人生命本能的正当性,鼓励个人的自爱、创造和强大。
泰伦斯·马利克是尼采“新道德价值观”的忠实拥护者,《天堂之日》中男主角让自己的女友委身嫁给所剩时日不多的农场主,从而引发了一场灾祸;《不毛之地》中少女与青年垃圾工人相爱,他们因为犯了一件谋杀案而各自逃亡;《生命之树》中则是父亲强迫性地在儿子身上加诸属于自己的梦想……但是因为导演肯定生命的自然欲望,所以他对主人公的行为是不做出任何价值判断的。换句话讲,一切遵从生命个体欲望的行为都是符合新道德价值观的。在新价值道德观的表达立场下,泰伦斯·马利克以“宇宙、生命和家庭”为关键词,用一系列美轮美奂的镜头进行反叙事化的组接,试图将“泛家庭化”的故事上升至对生命起源的探讨。
从影片结构上看,导演是将地球生命、人类生命与家庭琐事三条线索进行穿插式的并置叙述:第一条线索是展现从宇宙大爆炸到寒武纪、侏罗纪乃至白垩纪的宇宙演变,观众目睹了岩浆喷发、地球改变、植被生长、恐龙灭绝,直至人类诞生;第二条线索是展现作为个体的“人”的孕育过程:从放大的显像细胞到细菌乃至胚胎的形成。地球的起源与人类小生命的诞生是相同相通的,随着地球的变幻,人类也在代代繁衍;第三条线索则是展现一个普通家庭的平凡琐事:从快乐、到矛盾、争吵直至原谅。正因为是三条线索的并置叙述,让每一个镜头都成了导演诗意化的画面展示:阳光、海洋、树木、火山……自然界的神秘奇妙,残酷和谐,动荡平静都通过影像的魅力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宛若一首生命起源的赞美诗。
但是观影争议也因此出现了。精美画面与叙事故事之间那微妙的前因后果究竟应该如何地体现?影片中那充斥着大量的隐喻性符号与镜头语言蕴藏的驳杂繁复的生命奥义究竟有何关联?导演很努力地用各种画面充当隐喻性的符号,从而实现对“新道德价值观”的表述,但是却因为过于细碎和繁复,最后给观众留下的难免只是一种模棱两可又欲言又止的感受,以至于忽视了导演原本想要讲述的是一个再通俗不过的叙事故事。
影片的结尾还是非常撼人心魄的:成年后的杰克走向海边,跟随着儿时的自己,回忆父亲和母亲,回忆那早逝的弟弟,思考着生命的缘起。这时,他跟年轻时的父母走到了,终于接近了天空,感受到了生命的意义,正如母亲一直教育他们的:There are two ways through life — The way of nature ,and the way of grace(人生有两种生活方式:一种是自然之道,一种是感恩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