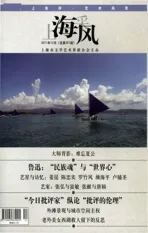“今日批评家”纵论“批评的伦理”
2011-06-22采编
采编/红 菱
不可否认,批评是一门衰老得很快的艺术和学问,这也就出现了所谓的“前日批评家”、“昨日批评家”、“今日批评家”的划分。今日批评家即70后、80后青年批评家已然成长为批评界中坚力量。为了聚集这些年轻的文学批评家,让他们更好地发出自己的声音,上海市作家协会、中国现代文学馆、《南方文坛》杂志社联合主办了“今日批评家”论坛。近日,第二届论坛在上海举行,主题设为“批评的语境与伦理”。

论坛上,作为“昨日批评家”的《南方文坛》主编张燕玲、中国现代文学馆常务副馆长吴义勤等率先表达了期望与提醒。张燕玲表示,在审稿过程中,她发现年轻一代的批评家出现一个问题,经常对自己所感兴趣的批评对象先入为主,她希望青年批评家在今后的文学批评中能够站在深厚的中国文学土壤里面,冷静地回应这个世界,并且思考,“在今天媒体津津乐道于发行量时,批评家尤其青年批评家是否还有勇气谈论美学风格,是否还有勇气谈论我们所评论的作品对当代文学、这个时代贡献了什么。批评实践必须以具体的作品为中心,要从文本出发,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做一些及物的、扎实的作家作品评论。”吴义勤也提醒青年批评家,不要片面地迎合媒体而否定一个作家作品,“从大众心理角度来说,对我们的期待是发出否定的声音,会认为一个人否定这个时代某一个作家,或者是大作家,或者比较受关注的作品,这个批评家就是敢于讲真话,有正义,有勇气。但实际上否定也不一定就是真话,肯定的东西不一定是假话,要发出自己真实的声音,你代表自己比代表什么都重要。今天很多批评家可能更乐意做代言人,反而忘了自己真实的艺术修养、艺术判断、艺术感觉是什么。其实做一个批评家,对一个作品正面的阐释比什么都重要。”接下来,近三十位“今日批评家”展开了激烈的讨论,真实地袒露了自己的困惑,以及对当下批评现状的反思,有力地回应了论坛主题。正如巴金研究会副秘书长周立民所言,发出自己真实的声音,这也应该成为我们这个论坛的目的和动机,也应该是批评伦理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回归“自我”与尊重感觉
刘志荣(复旦大学副教授):刚才强调批评家要读书,感觉这是一个讽刺性的说法,因为这是最基本的。我觉得做一个业余的批评家有一个好处,读过的东西有感觉时才会说话。我对自己的定位是一个业余批评家,但是如果能够配得上“批评家”这三个字,无论如何应该要有一个专业读者的素养,专业读者的素养应该包括他自己在这方面的各种经验方法,包括他独到的眼光。当然最好的方法是专业的读者能够重新做一个普通读者,把他的那些心得和专业眼光里面的判断,用大家都听得懂的话讲出来。讲到批评的伦理,实际是蛮严重的问题,这个严重的问题其实也是大家和社会对一个人提出的要求。我们现在看到如果这个人没有这方面的想法,外部的要求经常是失效的,更多的应该是自己对自己的要求,至少不说一些很空的话,一些很夸张的话等等。批评要说真话,首先真相我们是不是能看出来。第二个,看出来之后是否能够做一个很好的表达,所有这些都是问题。
严锋(复旦大学副教授):刚才志荣讲的过程中有一个词我非常有共鸣,就是“感觉”,我们要尊重自己的感觉。现在很多脑科学对感觉、直觉的研究发现,其实它的正确性往往会超过知性、理性的分析。以前批评界其实也经历过一个从感觉向知性和理论发展的过程,八十年代开始架构理论,九十年代登峰造极。这个步骤都很对,批评的感觉泛滥,本身就是缺少一种客观的标准。但是我们是不是应该反思,我们走到另外一个极端。我们要思考,怎么把握一种平衡,就是在感性和知性、感觉和理论、个人的偏爱和相对客观的标准之间的平衡。之前我感觉出现了某种失衡,我们现在为了这种平衡也应该作出自己的努力,尊重自己的感觉、感受。从这个出发,达到一种相对的客观。
岳雯(中国作协创研部副研究员):当一个话题不断出现自反性讨论的时候,很显然出现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不是外面强加出现的,而是自己本身已经对它产生怀疑,我们就要问问题到底出在哪儿?我有时候会觉得最大的问题是我们个人的缺席。我们真的热爱这个职业吗?我们真的愿意做这个事情吗?有可能是这种自我的缺席导致了今天批评面临的困境,因为自我不在了,所以我们不敢对任何一个作品下斩钉截铁的判断,我们甚至不相信我们的判断是对还是错的。一个成熟作家的作品出来了,我们可能会诚惶诚恐,读的时候觉得不是特别好,可能会想是不是没读懂。我们并没有建立以我为主的评价体系,所以我们根本不在意文本,不在意问题是什么样,我们只要说我们表达了,至于表达得漂不漂亮,我们不在意。因为自我缺席了,我们也会拒绝情感的介入。说到底文学是情感化的,当我们拒绝情感在里面渗透的时候,最后面临的只能是概念,是逻辑,是很冷冰冰的,甚至很枯燥的、不愿意为人所读的东西。
梁鸿(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你的内心是什么,你的感觉是什么,你的感觉来自于哪里,这可能对我们来说很重要。如果一定要强调批评的语境和伦理,首先要回到自身,要审视一下自我的知识架构,自我的审美感觉,自我在小说、文学文化长河里的基点。我们批评家应该要有一个整体的意识,才可能对某个个案做一个批判。这几年我有一个感觉,这一代批评者因为整个教育的原因,对自身的文化、自身的生活不太了解,我们不知道身处何方,我们学了一大套各种理论,都是生吞活剥、囫囵吞枣的,我们对自己也处于一种否定和批判的状态。如果今后要说我们自己的伦理,一定要首先回到中国生活内部,回到我们自身的文化内部,从这里出发,然后再去结合曾经学习的西方理论,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好的批评起点。
房伟(山东师范大学副教授):说真话的问题,首先也是对自我自身修养的提高,否定性的批评不一定是真话,来源于你自身的修养能不能看到这个问题。现在批评家有时候急于下判断,自己的理论修养,对于作品的阅读量是不是合格呢,这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是忠于自己内心的体验,有时候作品看不懂就老老实实地说看不懂,有时候觉得这个作品好在哪里,就老老实实地把好的东西展示给大家,即使表述过程中有不到位的地方,但是是忠于内心的体验。我认为,目前文坛批评伦理有两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一是封闭的保守性,因为我在高校,这种感触比较深,课题化的生存和项目化的生存很大程度上遏制了作为批评家敢于创新的勇气,在课题化、项目化生存的情况下,大家都在求大、求理论、求深度,对于具体作品扎实的解读往往不够。二是批评没有个性,没有血性,没有自我,没有自己独立的价值判断。记得谢有顺老师曾经谈到,他认为批评很大的问题就是“无心”,自己没有自己心灵的存在,变成这种虚假或者僵化、腐朽的批评,这对于目前批评界的伤害是非常大的。
“说真话”问题上的困惑
毛尖(华东师范大学对外汉语学院副教授):前面很多都说到批评要说真话的问题,我的困惑是应该说哪些真话,或者有时候真话是不是应该说,这也是经常困扰我的事情,包括前一段时间网上看到钱理群2010回顾,他是我很尊重的老师,但他的文章让我有些困惑,也有不少质疑。在这个时代真话在多大程度上是有建设性的,在更大的批评语境中这些真话有效吗,或者应该说吗?比如就一部电影《情》来说,有很多可以质疑的地方,但是它的倾向非常好,那么在稚嫩的阶段,我们应该怎么说话,这是一个真话的限度问题。
另外一个困惑,前面朋友谈到要发自内心,说出自己的感受。有时候我在想我个人的感受是不是靠得住,在多大程度上我可以信赖我的感受,这也是因为我自己这两年在教电影的关系,我以前一直教世界电影,很受同学欢迎,这两年我觉得我应该教中国电影,很多时候学生觉得很难看,我有时候强行让他们看,把自己的想法推给他们,这可能有一种博弈,真实的情况和自己的感受在不断互相平衡和博弈的过程。
霍俊明(北京教育学院副教授):作为一个中国人来说仍然有一个悖论,我们说现在已经进入一个自由阅读写作的时代,有了博客,有了微博,我们进入“自媒体”的时代,一切都开放了,我觉得不是如此,今天无论是写作、阅读,还是评论作品,仍然有很多的限制。包括刚才说能不能说真话,或者最想说的话能不能说出来,我觉得作为批评家而言还是要自由的证明,如果没有自由说话的权利就谈不上批评,也失去了批评家的身份。当下批评遭受很多挑战,这种挑战包括来自所谓的自媒体对文学写作和阅读甚至批评家话语权的冲激。
李东华(中国作协创研部副研究员):我只讲我自己的两点困惑。第一点,在网络化时代,面对那么海量的创作,你个人的阅读经验总是非常有限的。你会发现今天形成的一种自信满满的判断,到了明天随着阅读量稍微增加,今天的判断无非是建立在孤陋寡闻基础上的偏见,有时候人也不是不想说真话,最痛苦的是今天觉得说的是真话,第二天发现不过是个偏见而已。第二点,在这个网络化的时代会发现文本的互动非常活跃,人人都可以参与批评,这种批评的泛化和传统批评的精英化形成鲜明的对比,怎么能避免你的批评不是在一个非常小的圈子里的自说自话,怎么避免你的批评不过是一种学问的展示而已,你如何能够让你的批评真正富有自己生命的感悟,真正具有精神的洞察力,来面对当下的文学现实和生存的现实。有一次我去理发,给我理发的小男生也就20多岁,他谈起网上的很多文学作品,当时我觉得很羞愧,我觉得我的思想也未必比这些普通读者更能提供什么有力的东西。
张莉(天津师范大学副教授):我记得蒋光慈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理论:冰心,好一朵温室的花儿,我们让她走吧,让她走到美国吧,要不然她就哭着回到她妈妈的怀抱里去了,我们不需要冰心这样的女人。我觉得他的评论出了问题。张天翼对冰心也有一个评论,他说冰心的文章好,我看了冰心的文章就感觉像是在旧世缠了足的女人又放了脚也有好看的。当时很多人觉得他说得特别好,我们对好女人的形象就是按规矩裹脚,但是又放了。我看到这两个评论的时候想到一个问题,这个文学趣味里面有性别的趣味。这个层面上做的很好的就是鲁迅,鲁迅也评论过两个女作家,他超越了一种非常浅层次的个人趣味,而且是一个恶趣味,建立了自己个人文学品位的趣味。
批评的伦理首先是对自我的反思,说真话,但是你真话的限度在哪里?我们知道蒋光慈也在说真话,但是我看的时候就想,哥们,你怎么啦。今天回想我们如何做批评家的时候,我当年的那些阅读经验给予我启发,我认为批评应该是形象生动的,是用人的感情来传达的,并且是有实践的,有见识的,跟别人不一样。作为一个批评家应该能把人人心中有人人笔下无的东西传达出来,哪怕就是几个字的精髓,把它传达出来了。
金理(复旦大学中文系讲师):今天我们面临的新东西太多了,是不是我们必须为它们发言。批评家有时候有点可怜,好像我们必须跟着那些人跑,跟着现代传媒跑,那些被我们追捕的对象时不时要求我们给出一些判断,这些判断越直接越好。那些能够给出判断的批评家肯定是食量非常惊人的批评家,他们开各种各样的会,迅速进入状态,每个人都给出非常多的理由、判断。我非常佩服这样的专家,但是有时候我也疑惑,是不是我们真的可以对每个问题都发言,有时候觉得在今天这样传媒的时代,或者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是不是应该承认甚至保持一种必要的无知和选择的尊严。
批评的伦理体系与标准
邵燕君(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当代的批评不知不觉走入一个人情的怪圈,我们无法坚持自己,太得罪人,如果我们想重建批评,必须重新建立伦理体系——我们俩是非常好的朋友,但是我真的不觉得你这个作品能够当选这个奖项,并不意味着我不承认你的文学成就。这应该成为一个伦理,大家都能接受,而不是这次不评你肯定是把你得罪惨了。茅盾文学奖是一个挺好的事,从此我们可能就要建立这个伦理体系。包括我参加你的研讨会,你给我掏钱买飞机票,你招待我了,并不意味着我一定按你的意思说你好。在我的文学体系里,如果我给你写了文章就挺对得起良心了,这个伦理体系我们得建立起来,否则我们就无法说话了。
甫跃辉(《上海文学》编辑):我是一个编辑,负责小说、理论两块,我自己又写小说,我碰到很多编辑也在写东西,有可能之前我向他投过稿,他把文章发了,这时候他给我投稿,我就很尴尬了。所以有时候我知道这个编辑在写东西我就不投稿,换一个编辑投。同时我又是理论版块的编辑,经常有朋友把他们的作品寄给我,让我写评论的文章,我就不得不写,所以就导致我很混乱。我同时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我写的理论文章可能被我退过的批评家觉得很好笑,你自己写成这样子,还把我的东西毙掉了。这样就存在一个问题,标准在哪儿,这个标准很混杂,有很多人情的东西在里面。刚才邵燕君老师说到茅奖,那是更复杂的大的环境,我觉得这个小环境已经够混沌了。有的批评家给我写过评论我小说的文章,他给我一个稿子我就很难弄,所以可能需要稍微理清一点规则,把标准变得稍微简单一点。
张念(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副教授):在我们这个人情大国,到处存在伦理陷阱和伦理绑架的现象,这可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中国传统文化就是人与人之间相互纠缠、亏欠、付出的利益网络,不仅是文学圈,艺术圈更是这样。我发现有很多很年轻的80后在这里,如果要做批评,其实要解决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做减法,就是我要放弃什么。批评工作不是商务局或者质检总局,不要搞得我是产品检验员一样,说它是一等品还是二等品。第二点,要提升问题的品质,应该有新的提问方式出来,这是我自己对自己的定位,也是我自己的一个原则。在这个时代,网络生产使得文学已经成为一种文学劳工了,我们很羞于说因为伦理是什么,要为自己立法。我们能做的工作是更前一步的,我觉得不单单是文学批评,还有我们批评的本性,和当代文学史交融的过程方面,能不能建立起自己的思想纬度。
刘颋(《文艺报》评论部主任):这届茅盾文学奖打破了原来的伦理,建立了新的伦理,我想,每个人如果能公开表明自己的态度,这可能已经是比较健康的生态了。因为我处于网络后台,所以能看到很多网友的留言,很多网友对这个实名制是一致认同的。另外,我觉得是否一定要那么在意我们现在的批评生态,就是大生态,和我们现在大的批评伦理。我的感觉是,其实每个批评家都有自己的批评生态和批评伦理,每个批评家如果是本着对自己负责的态度,把自己的生态、自己的伦理秩序建立好了,从个体入手,这个大的环境才会有改善。关于文学批评的问题,就像一个人举着手术刀给别人做手术,你首先要检查你的手术刀是否干净。
李云雷(文艺理论与批评杂志副主编):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变化的语境之中,这个语境可以包括几个方面,比如说文学批评的语境,文学的语境,包括整个中国的语境,也都在发生变化。在变化的过程中我们怎么坚持批评的伦理,这是很重要的事情,批评的伦理又包括什么,也是值得探讨的事情。我们平时说评论最简单的是好事说好,坏事说坏,这也应该是批评该坚持的原则。但是后面也涉及到很多问题,我们怎样批评一个作品是好还是坏,这就涉及到批评的标准问题,并且批评标准在不同的时代也在发生变化,我们怎么在变化的时代中发现一些新的审美元素和美学经验,这也应该是批评家应该做的。我们不应该固守旧有的标准,应该具有前瞻性和探索性,在这些新的美学元素和经验出现的过程中应该敏锐地捕捉住它们,这也是批评家应该具备的素质。
黄轶(苏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这些年来,我们一直对文学创作、文学批评有一些沮丧的评价,我们是不是可以冷静下来重新建立一种批评的信念,如果对批评和创作的不满很泛滥,可能会使乏力的批评更加乏力。第二点,批评的道德哲学最重要的是有助于促成一个时代的审美理想的建立。很大程度上批评确实是脱离了创作的现象,我们在批评的时候不仅不能脱离文本,而且应该像生态批评一样更多地注意到中国生态危机发生的很多个案的因素,这样的批评才能使批评达到批评的功能,实现它审美理想的建立。第三点,在批评的过程中,我们是要强调批评的审美方面,当然也应该强调批评的思想本位,另外是审美围绕下到达实际的能力,这才能符合批评伦理的想象力。批评的伦理一定不等同于伦理的批评,批评本身是一种富有理性精神的科学研究,不能拿简单的伦理批评粗暴取代。但是批评伦理确实也是伦理的行为,对批评家自身也有一种参与和构成的功能,我们是在批评的过程中实现了反省和自律。
批评需要更宽广的视野
刘铁群(广西师范大学副教授):不少人认为,似乎对一个作家说好话就不真诚,批判他就是真诚的。而有那么一部分人专门猛烈批判别人,这样一批批评家成名了。在这样一个荒谬的理论之下会把批评引入歧途。好的批评并不是看它是肯定还是否定,批评家有发现作家缺陷的职责,但更重要的是发现作家的创造性,发现作家值得肯定的地方。现代文学史上文学批评的重要开创者茅盾,其实他做出的重要成绩就是肯定赞赏扶持了一批当时的青年作家,茅盾也做过批判,没有猛烈的批判,而这个事情恰恰是他晚年后悔的事情。对于从事批评工作的人来说,我们更需要的是用真心去体会文学作品,用灵魂去跟作品对话。在这个情况下我们才能够对文学作出自己负责任的评价。我想起福轲说的一句话,我忍不住梦想一种批评,这种批评不会努力去评判,而是给一部作品,一本书,一个句子,一种思想带来生命。如果批评家能够努力用心去阅读,给一部作品,一本书,一个句子,或者一种思想带来生命,这就应该是批评的健康路子。
胡传吉(中山大学中文系讲师):我的疑问是,批评是不是只能面对当代呢?这个问题可能会涉及到学术的尊卑问题,好像批评跟当代发生关系就不是一个学问,或者不是一个研究。现代或者古代才是研究或者学术,到了当代就一定是批评的事件。另外,批评可不可以宽容一点。第一,是不是应该对青年人要宽容一点。比如一些青年的作家,像李娟、迪安啊,这些作家是不是可以多关注一下。回顾历史,很多作家都是很年轻的时候被发现,比如铁凝、苏童、张爱玲等。这个宽容不是一定要说好话,唱赞歌,重要的是发现他们。第二,针对作品本身来讲,其实也是一个格局的问题,我们能不能把宽容落脚到文学的多元层面,一个批评的格局里面是多种文学的样式,首先谈到小说,我们现在的眼光是不是对长篇小说关注得太多,对一些中短篇关注得不太够,这可能有市场的因素在里面。文学类型方面,学院派特别注重严肃文学,我觉得其实有多种文学题材,是不是都可以关注,包括科幻小说,侦探小说,还有散文等。第三,关于多样文学、多种文学的宽容,是不是要多关注一下体制外的作家。
郭艳(鲁迅文学院教学部副主任):当下一些中青年作家和批评家经常把传统过于笼统化,当下批评语境具体到语言、思想,甚至于文体的粗陋,就成为一种无可回避的尴尬,表现为思维的传统和当代批评话语的匮乏。另外,我觉得中国的批评语境和中国现代化是一体的,现在现代化的进程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很多元,批评也承载着来自整个社会的变化,文学自身也有一个演变的历史。文学到了这样一个时代,网络文学、80后青春写作等,他们呈现出很多新的东西,批评家要很敏锐地发现,而且找到批评主题自身对这些问题的看法。
邵燕君:之前我带着学生做文学期刊的点评,后来做不下去了。我带的那些小孩从70后到80后,他们的语境彻底变了,尤其是针对历史作品的长篇小说,而现在我们的作家也有一个特大的问题,他们不会比较如实地传达历史语境。以前作家有本事传达一个完整的语境,比如你可以完全不理解中国农民是怎么回事,但是你看赵树理的文章可以理解,可是现在的作家没这本事,他写一个文革可能是非常个人和偏移的,70后、80后阅读的时候可能也没有自己的解读。我有一个建议,对于专业的研究者而言,我们读文学作品的时候千万不要读选本,不要读单行本,最好读原始文学期刊原发的。因为只有当时的文学杂志才能呈现出当时周边的文学生态,这对于我们研究者尤其是“今日批评家”而言,是比较好的了解昨天的事情的方法。
黄平(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讲师):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勾连批评语境难度还是蛮大的。第一,我们需要像对待现代文学一样,还原当代文学的文学环境,这就是要做到把文学生产之语境文本化。难度比较大,也比较繁琐,但真正静下心来做,也不是没有可能做好。更加挑战的在于第二点,当我们把当代文学变得和现代文学一样,研究充满了材料、史料的时候,如何与我们所认为真正的、文学性的东西勾连,怎样做到问题意识不被材料淹没?批评语境化,能否把批评背后的历史语境真正打开,成为一个需要克服的难点。
金理:讲到历史语境,大家都认为应该重回历史语境。但我们说回去就能回去吗?特别在今天,大家都受到很多新历史主义的影响、洗礼,都会感受到在历史和叙事、在知识和真理之间关系非常复杂。有时候我们往历史研究对象投影的时候是不是应该警惕一些问题,我们是不是应该警惕因为今天的“无”,而到历史上投射一种“有”,由于今天匮乏了,我们生造了一些过去的繁荣和丰富出来。另外我们是不是应该警惕以一种后出的思想概念或者工具强求前人,而无视前人在特殊语境当中的关切。我们都是在事后做研究的,我们都占据时间的优势,都有后见之明,这种后见之明是不是应该谨慎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