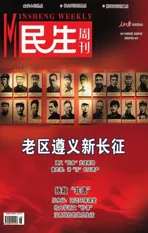天桥的褪色与坚守
2011-05-02
□ 本刊记者 周 旭
天桥的褪色与坚守
□ 本刊记者 周 旭

付文刚的中幡表演。图/傅若乔
天桥文化对于北京就如同胎记一般,虽是与生俱来,却在这座城市生长、壮大的过程中悄然褪色。然而,正如许多老北京所说的,“北京可以没有三大殿,不能没有老天桥”,天桥文化在北京的城市性格里留下了一块无法磨灭的印记。
寻迹老天桥
8岁学艺、15岁登台,付文刚从父亲付顺禄手中接过那柄4.4米的小中幡时,只记得父亲“不能把这门玩意儿丢了”的教诲。然而,耍了一辈子中幡的付顺禄不会想到,当年用于糊口的玩意儿竟然被儿子擎到了奥运会开幕式,更在60周年国庆庆典晚会上让天桥绝活又火了一把。
中幡起源于清代宫廷外事活动中的执事表演,清末年间,在天桥卖艺的王小辫向在宫中做大执事的哥哥学得该项技艺,由此将中幡带到民间。那时,付文刚的师爷宝三爷还是在天桥学摔跤的一个小孩,因为觉得中幡耍起来有意思,还对摔跤有帮助,便时常追着王小辫的表演凑个热闹,也私下学了几招。
一次,王小辫为一位王爷表演,宝三爷挤在人群里看热闹。突然,王小辫的中幡一歪,直直地向王爷家的一个孩童倒了过去。就在30多斤的中幡即将砸到孩童的时候,宝三爷用了摔跤的一个腿法将中幡挑起,王小辫顺势接住了中幡,观众以为是两人玩的一个技巧,掌声雷动,连声叫绝。
表演结束,王小辫找到了这个救了他一命的孩子,两人由此结缘。后来,王小辫收他为徒,天桥多了一个会耍中幡还能摔跤的宝三爷。上世纪50年代,大武生出身的付顺禄成为宝三爷的第三个徒弟,也是唯一一个完整继承了中幡和摔跤的人。
对于天桥,付文刚的记忆来自中幡、来自摔跤,也来自在天桥卖艺的父亲和师爷。早年间,民间杂耍艺人多是一些受压迫的穷苦人,卖艺为生,是不被尊重的“人下人”,还要被四霸天欺负。然而,这个劳苦大众的聚集地又是一个包容性极强的市场,只要有真本事,就能在这里表演、生存。在普通的卖艺人之间,也形成了一种惺惺相惜。
“您瞧,这说书的还真不赖,给您逗乐了,您也看看我们这玩意儿……每次表演前,我们都要点评一下上一场的表演,也是对前场的人的尊敬。表演完,还要介绍一下后面出场的人,不能让人家看完我们的就走。”对于天桥的规矩,付文刚烂熟于心。而当时,中幡的热闹场面也让他激动不已。
“在天桥,中幡一玩起来,炸场子!”付文刚回忆道,宝三爷的中幡一撂摊,摆了半圈的条凳都坐满了人,站着的更是里三层外三层。当时天桥没有什么高的建筑,最高的戏楼也只有两层。中幡9.9米,一抖起来,把人都吸引过来了。“宝三爷和我父亲都讲艺德,在这里卖艺的谁都不容易。为了不抢别人的生意,他们就等天桥快闭市的时候才抖中幡,即使这样,每个月下来,也能打300多块钱。”
在付文刚看来,父亲的卖艺生涯中,老天桥留给他最宝贵的财富并不是吃穿住用的着落,而是艺德。虽然,现在的天桥已经难寻当初的老天桥旧貌,但提到艺德,付文刚还是愿意说起老天桥,说自己是天桥技艺传承人。
卖艺人与文艺工作者
天桥作为老北京南城文化的标志,成了许多外地人甚至外国人一心向往的地方。然而,当他们来到天桥,却发现这里早已不是那个耳边回荡着叫卖声、街边聚集着卖艺人的杂耍集市,而是一条条干净的街道,一个个规整的社区,渗透着京味儿却散发着现代气息。
早在上世纪50年代,政府就对天桥进行了治理。筹建了杂技团,调整了娱乐场地,还盖起了居民住宅。杂耍的老艺人有机会给毛主席、周总理表演,“杂技”这个名字,就是周总理为这些绝活起的。从杂耍到杂技,别看仅有一字之差,却让艺人感到了尊重。
玩车技的金业勤,艺名“小老黑”,在旧社会卖艺让他吃尽了苦头也受尽了侮辱。新中国成立后,他考进了杂技团,成为新中国的文艺工作者。“以前卖艺总是受欺负,现在我们成了文艺工作者,还能坐飞机去苏联演出,我们愿意给新中国做贡献!”
从卖艺的到文艺工作者,民间艺人的地位提高了,生活也得到了改善。他们各自有了单位、发了工资,也分了房子。天桥这个自然形成的表演场消失了,老艺人分散在杂技团、戏院、艺术团到各地演出。虽然在之后的六七十年代,许多文艺工作者受到了牵连,但进入80年代,演出团体依然火爆。
曾经喧嚣的老天桥如今真的要销声匿迹了吗?那些玩意儿真的成了绝活,也真的只剩下遗产了吗?
付文刚清楚地记得,他们每天下午在钟鼓楼地区演出。表演吸引了许多外国朋友,他说出了平生学会的第一个单词“money(钱)”。而在那个平均月工资只有60元的年代,他们艺术团每个下午都能赚到30元钱。
2006年,经国务院批准,天桥中幡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付文刚也成为该文化遗产项目的传承人代表。
最初几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招牌确实给付文刚带来了许多机会。然而,不过两三年的时间,各门各派的中幡表演纷纷登台。“许多外行人只图热闹,请的都是一些只懂皮毛的杂耍人。这些人打着中幡继承人的旗号,只要给钱就去表演,其实他们连怎么绑中幡都不会。”就这样,付文刚的“正牌军”渐渐没了生意,市场混乱也坏了中幡的名声。
与此同时,随着人们文化生活日渐丰富,天桥文化这种源于劳苦大众糊口、消遣的艺术形式逐渐被人们所遗忘。老一辈艺人纷纷进入暮年,许多绝活面临着后继无人的窘境,第三代“八大怪”之后再无新人。
坚守金字招牌
2004年,文化部在全国启动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宣南地区因为坐拥天桥这块风水宝地成为北京市的两个试点之一。
主管街道文教工作的赵兴力是土生土长的南城人,从小浸润在南城的平民文化中。然而,启动非遗保护工作,却让赵兴力犯了难。走遍整个天桥地区,他没找到一个还在整场演出的民间艺术门类;问遍了身边的人,也没发现一个传承民间技艺的老艺人。
曾经喧嚣的老天桥如今真的要销声匿迹了吗?那些玩意儿真的成了绝活,也真的只剩下遗产了吗?
在工作岗位上,赵兴力主管文教,开展群众文化活动是他的主要工作。一次偶然的机会,一位居民果少卿找到赵兴力,说她会表演魔术,希望参与一个演出活动。赵兴力随口问了一句:“你还会什么?”得到的答案让他喜出望外,鼓曲!赵兴力找到了苦苦寻觅的鼓曲表演者,而果少卿又把赵兴力带到西直门的一个小院,赵兴力认识了圈子里更多的鼓曲艺术家。
这个发现让赵兴力既兴奋又担忧,十几位鼓曲艺术家都是年迈的老人,鼓曲真的要成为绝响了吗?赵兴力组织举办的“天桥杯”鼓曲赛,让他看到了鼓曲生存的高龄环境,却更坚定了他复兴天桥文化的决心。
2004年底,在盛金商城,天桥文化连续三个月在周末上演,吸引了大批观众也引来了众多媒体,更让许多民间艺人重回天桥。飞杠高手“飞飞飞”的传人曹华德从安徽回到北京已是80高龄,他带着身怀绝技的儿子、儿媳回到天桥,希望看到复兴的天桥文化。
2006年,天桥街道成立了曲艺茶社,为鼓曲爱好者搭建了一个免费表演和学习的平台。2009年底,天桥还办起了鼓曲培训班。通过一系列的表演和培训,赵兴力希望鼓曲活在民间,活在表演中,活在孩子的生活里。在他看来,保护天桥的民俗文化、民间技艺,最好的保护就是经常上演,而非简单申遗。

然而,现实却也让坚守天桥文化的人们感到一丝失望甚至无奈,赵兴力发现,关注、爱好鼓曲的还是一些年龄偏大的人。周边的许多演艺场所也开始慢慢转变态度,一个文化广场承担不起复兴天桥文化的任务。
付文刚用了七年才成立了宝三民俗文化艺术团,却连个固定剧场都没有。师徒、学生30余人,都只能在家练练基本功,10个都已是年过不惑的徒弟仅能掌握他2/3的技术。“以前都说师傅留一手,徒弟丢两手,我现在是想教都找不到人。早不是老年间徒弟找师傅的时候了,现在是师傅找徒弟。”
受过夹门(音,指懂规矩的拜师弟子)的付文刚也坦言,随着年龄增长,演出不固定、场次减少,自己的功夫也会逐渐退化。父亲那句“不能把这门玩意儿丢了”的教诲,不时敲打得他的心生疼生疼。
重回天桥的曹华德也不免有些失望,天桥早已不是印象中的模样。正如他四个儿子都学了他的技艺却只有一个还在靠演出吃饭外,天桥的许多绝活都面临着后继无人、也无人捧场的困境。
“天桥是老北京南城文化的发源地,更是平民娱乐的聚集地。无论时代如何发展,人们都需要一个休闲的空间,所以天桥文化永远不会过时。”如今,街道办事处的赵兴力作为政府的代表,成了众多民间艺人的“主心骨”:“每次举办活动,我就看到政府在坚守,老艺人们也在坚守,那些在舞台下面使劲拍巴掌的观众也在坚守,要守住天桥这块金字招牌,我也不敢有一丝松懈。”
□ 编辑 刘文婷 □ 美编 庞 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