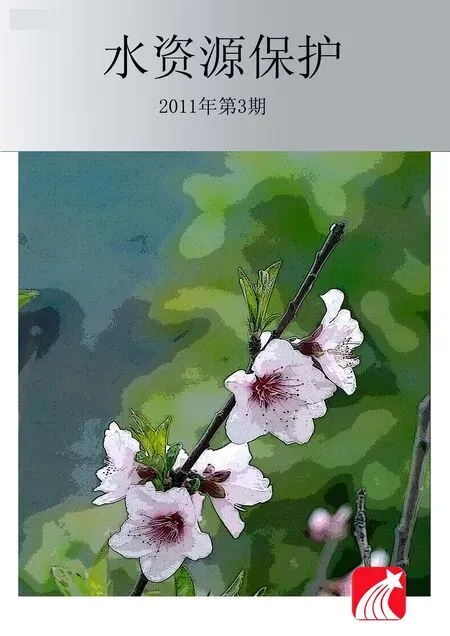可交易水权制度构建探析
——以澳大利亚水权制度改革为例
2011-04-14陈海嵩
陈海嵩
(浙江农林大学环境法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浙江临安 311300)
可交易水权制度构建探析
——以澳大利亚水权制度改革为例
陈海嵩
(浙江农林大学环境法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浙江临安 311300)
以澳大利亚水权制度改革为例,探析了可交易水权制度的构建。认为:澳大利亚可交易水权基本制度框架的缺陷是忽视了水权交易中的外部性问题;我国可交易水权制度的构建应以市场机制和协商机制弥补区域水权在排他性上的缺失,并制定取水权优先规则和取水权征收补偿制度。
水权交易;水权改革;第三方效应;法律规则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水资源危机的日益加深,如何通过市场机制配置水资源逐渐成为世界各国广为关注的课题。我国的水权交易包括地区之间水权交易(如东阳-义乌水权交易)、工业与农业部门之间水权转换(甘肃省、内蒙古自治区的省(自治区)内水权转移)、农户之间水权交易(甘肃省张掖市的水票交易)等形式。由于水权制度改革不仅是资源配置或生产力布局问题,更是涉及制度建设和国家管理体制演化的问题[1],因此,借鉴国外在水权交易与水市场建构上的先进经验,总结出相应法律规则的内在规律,成为急需完成的课题。本文以澳大利亚为例,对可交易水权制度进行剖析,以期对我国可交易水权制度的建构有所助益。
1 可交易水权的提出与发展
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全球水危机的加深,人们认识到水资源可持续利用与综合管理的重要性,水市场逐步成为水资源优化配置的重要手段,建构适于进行市场交易的水权制度成为各国学者探讨的前沿课题。在理论上,比较于政府管制,水市场机制能在用户自愿参与和多元协调的基础上更好地配置水资源[2]。正是在此背景下,保障水资源市场配置顺利实现的可交易水权制度应运而生,并在一些国家得到了初步实践。最早在法律上确认可交易水权制度的国家是智利。根据智利1981年颁布的《水法》,水是公共使用的国家资源,但可向个人授予永久和可交易的水使用权;现有的水使用者可以免费获取地面水和地下水的财产权,新的和未分配的水权通过拍卖向公众出售;水权和土地所有权完全分离,由私法加以规范,水和土地可以自由买卖、抵押和转让。作为首个实行自由水市场的国家,智利模式获得了广泛的肯定,但越来越多的学者指出,智利实行的可交易水权制度具有较大的缺陷,它忽视了水资源的综合管理,导致可交易水权制度实施20多年来,智利仍然面临着严重的水资源短缺和水污染问题[3]。这也正是智利在2005年对水法进行再次修订以及强调政府对水资源进行管理的原因。
目前可交易水权制度的发展较为领先的国家是澳大利亚。澳大利亚注重对水资源的可持续综合管理,并在这一框架下建立可交易水权制度。从地理情况上看,澳大利亚是全球最干旱的地区,由于降水分布不均,澳大利亚面临着严重的局部水资源短缺问题。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增长,单纯的行政性水权已经无法满足澳大利亚日益增长的用水需求。根据澳大利亚政治体制,水资源及相关事项属各州的管辖范围,但在水资源问题日益突出的大背景下,建立一套全国性的水资源法律与政策体系,以保障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就成为必需。1994年2月25日,澳大利亚政府间理事会(The Council of Australian Governments,CoAG)举行会议,批准了《1994年水事改革框架》,要求各州制定并实施综合性的水资源配置制度,由此揭开了澳大利亚水权制度改革的序幕。澳大利亚水权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是,要求各州实施综合性的水资源配置制度,明确界定水资源的财产权、数量、稳定性、可转让性和水质等。水权制度确立后,就可制定水权交易的相关制度。以《1994年水事改革框架》为基础,澳大利亚基本形成了全国统一的水资源政策。为了更加深入地实现水资源可持续综合管理,2003年起,澳大利亚政府间理事会开始对《1994年水事改革框架》进行修改。2004年,澳大利亚联邦与各州政府签订了《关于国家水资源行动计划的政府间协议》(Intergovernmental Agreement on a National Water Initiative,以下简称NWI),提出了可交易水权与水资源可持续综合管理的基本框架与要求,并规定了预期成果与各州应采取的行动措施。
2 澳大利亚可交易水权的制度构建
NWI是目前澳大利亚联邦与各州水资源政策的基本性法律文件,所有的涉水法规都必须与其相符。为了给水市场的形成和运作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澳大利亚对水权制度进行了重新构建,提供了以下几个方面的水权交易基本制度框架。
2.1 水权权利束的类型化
根据NWI,为形成有效的水市场,必须对水权权利束中的具体功能进行分类并加以特定化。具体而言,可交易水权被划分为3个部分[4]:①针对某一具体水资源的可消费量,确立一个与土地相分离的、永久或者是无期限的水资源份额权利;②根据特定水资源规划,分配特定水量;③对因某一目的而在特定地点用水的情况进行法律审批,并将其和一般性取水权相分离。根据这一规定,有学者[5]将澳大利亚的可交易水权划分为 3种类型:水获得权(water access entitlements)、水分配权(water allocations)和水使用权(water use approvals)。其中水获得权规定的是水权人的水资源份额;水分配权规定水权人在一定期间有效的取水量;水使用权授权水权人从事与水权有关的活动,并将前面两种权利转变为用益权。2007年,澳大利亚新颁布的《水法》即以这一划分确立不同的水权类型。
不难看出,澳大利亚可交易水权制度在区分水权与土地权利的基础上,进一步对水权权利束中的“水获得权”、“水分配权”和“水使用权”进行了分类。对水权权利束进行分类,目的在于提高水权体系每一部分的可流动性,减少交易成本,使水权市场运转更有效率。澳大利亚可交易水权制度的设计目的有:①使水权成为确定的财产权。根据NWI的规定,水权权利束中的水获得权是一种“永久或者是无期限的水资源份额权利”,该权利能够保证用户进行水资源交易、赠与、出租、分割或者合并,具有可抵押性和可强制执行性[4]。②保证水权的排他性。一般而言,因为水权的行使往往具有外部性,水权的排他性使用水主体具体实施水事活动时不可避免地受到很大的限制。这些限制涉及水工程的建设、运行、抽水、排水、转让等诸多内容,如此一来,水权的交易价值和转让范围大受影响。解决水权排他性限制与交易性之间冲突的方法,是将水资源份额利益与特定水资源的具体开发利用活动分离开来[6]。显然,针对水事活动的不同阶段而对可交易水权进行分类,可将对取水、蓄水、排水活动的限制安排在“水分配权”和“水使用权”阶段,而“水获得权”代表了特定水资源份额的利益,用水主体能够没有限制地转让份额内水资源,从而保证了水权的排他性。
可见,对水权权利束进行分类,既是建立可交易水权的基础,也是保证水市场和水权交易有效进行的前提,是减少水权交易成本的有效方法,代表了水权制度在利益分配规则上的发展趋势。
2.2 用水风险负担规则的明确化
水权的易变性和不确定性是阻碍水权市场交易的最大因素之一。水权制度不仅要关注水资源利益的分配,更要关注水资源风险的分配。风险是水权的固有性质[7],欲构建可交易水权制度,不仅需要在水资源分配方面进行权利的细分,更需要明确各用水主体在用水风险分配上的规则,以保障其用水预期,使水权具有可预期的确定性和安全性。澳大利亚水权制度在这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根据NWI的规定,相关水资源规划中应界定生态环境用水和其他公益用水,并给予法律上的承认,使之具有和消费性取水权同样程度的稳定性[4]。以相关水资源规划为基础,在可消费性水资源量确定的前提下,澳大利亚用水风险分配规则[4]为:①因季节性或者长期性气候变化和周期性的自然事件(如森林大火和干旱)引起的可消费性水资源量减少的风险,由取水权人承担。②因水系统维持知识的改进而引起的可消费性水资源量变化风险,2014年前由取水权人承担;2014年之后,由于实施或修改综合性水资源规划而产生水资源量变化风险,在每一个10年期间,按照下列方式分担:取水权人承担最先减少的3%水资源配置量的风险;减少的3%~6%水资源配置量的风险,由州政府和联邦政府分别承担1/3和2/3;超过6%的水资源配置量减少风险,由州政府和联邦政府平均分担。③对于前面没有规定的,由于政府政策变化(如新的环境目标)而产生的任何可消费性水资源配置量减少的风险,由联邦政府和州政府承担。④如果受影响各方自愿同意一种与以上3种方式不同的水资源配置量减少的风险分配模式,则这种风险分配模式是一种可以接受的替代性选择方案。
可见,澳大利亚建立了一种明显区别于原有行政水权制度的用水风险分配规则,其最大特点是:对水资源配置量减少风险的不同情况进行分类,并明确承担主体及其承担比例;同时,允许相关主体自愿协商进行风险分配,避免了制度的僵化。应该说,澳大利亚的水权制度第一次针对水资源风险的分配建立了相对明确的规则,初步摆脱了行政自由裁量权对水权确定性的影响,水权人可以通过公开、透明的规则,对水权的变化和风险的承担有相对稳定的预期,为水权的市场交易奠定了基础。
2.3 生态环境用水对水权交易的限制
随着污染程度的加深和人们环保意识的增强,生态环境用水的重要性日益被人们所认识。如何使生态环境用水与消耗性用水达到平衡,以保障流域的生态环境,成为水权制度建设中必须重视的问题。生态环境用水量要合理,过多分配生态环境用水将适得其反,造成不必要的经济损失和投资浪费,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就发生过类似事例[8]。为了合理确定生态环境用水量,1996年7月,澳大利亚、新西兰农业与环境部门部长理事会通过了《关于生态系统用水供应的国家原则》,目的是在水资源总体配置的层面上,妥善处理生态环境用水问题。该文件明确宣告“应当在法律上承认生态环境用水”,并提出,“在承认其他用水者既有权利的同时,应尽可能最大程度地满足维护水生态系统的用水需要”,“在因既有用水者导致生态环境用水需求不能得到满足的情况下,应采取行动以满足生态环境用水需求”。以该文件为基础,2004年NWI也对生态环境用水进行了规定,明确提出对生态环境用水和其他公益用水给予法律上的承认,使其具有与消费性水权同等程度的稳定性。NWI还明确规定,因取水权而持有的水,只有在不危害生态环境和其他公共利益,并且不与公共利益目标相冲突的情况下,才能在市场上进行交易。可见,生态环境用水与消费性用水具有同等法律地位,生态环境用水和其他公益用水构成了可交易水权的外在限制。
3 澳大利亚可交易水权制度的缺陷
从目前世界各国情况看,澳大利亚可交易水权制度对水权交易及水市场的建构起到了较好的促进和保障作用,具有典范意义。然而,以2004年NWI为核心的澳大利亚水权制度仍然存在一定的缺陷,其中最为显著的是对水权交易中“第三方效应”(third-party effects)的忽视。由于水具有独特的物理特质,当事人所进行的水权交易往往会对非当事人享有的水权产生影响,即产生外部性问题[9]。“第三方效应”指第三方的水权因水权交易受到影响,其中最具普遍性的是回流问题。回流是指由于水资源具有流动性,在消费中水资源未被完全使用而重新进入地表水和地下水,继续被其他用水者使用。如果水权交易对回流的水量或水质造成影响,就会使第三方利益受到损害,从而影响到水市场的运作效率。
显然,第三方效应及回流问题对水权交易及水市场构成了挑战,水市场的制度构建必须将水权交易中的外部成本内部化,并对第三方受到的损害进行必要的补偿。但在澳大利亚可交易水权的制度构建中,并未考虑回流问题。具体而言,根据可交易水权的类型,水权中的水分配权意味着权利人有从特定水资源总体中获取一定水资源的权利,但这不是基于其实际消费并返还的水量,这就使得依赖上游用水回流的下游用水者难以确立其实际可用的水量。换言之,由于水权被定义为对特定水资源总体的使用权利,上游用户就拥有某种隐含的权利,可以在不考虑下游用水者的情况下使用或交易回流的水量[10]。可见,根据NWI对可交易水权的制度设计,下游用水户的利益并未得到有效的保障。
针对这一制度构建上的缺失,澳大利亚政府2006年发布了关于NWI及水权交易的研究报告。该报告提出,为弥补对回流问题的忽视,应对水权制度进行一定的修订,具体有两种可供选择的方式:①为水体的“回流”创造一个独立权利;②改变水权的定义,将其从总体水量使用权变为净用水量使用权。目前,第二种方式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赞同。在该方案中,水权中的水分配权持有者享有消费一定净用水量的权利,其实际用水量的增加必须获得额外的许可,进行水权交易则意味着水权人可用水量的减少。显然,根据水市场的要求,可交易水权中分配水权的客体,是水权人的实际用水而非概括性的特定水量,这样就在制度构建上消除了水权交易所可能产生的外部性问题。
综合前文所述,以澳大利亚可交易水权相关制度为蓝本,可以归纳出可交易水权在制度构建上的几个基本要求:①可交易水权与生态环境水权具有同等地位,只有在不影响生态环境用水和公益用水的前提下,水权交易才能进行。推而广之,可交易水权在实践中有效运行的前提条件是政府的有效监管,水市场只能是一个“准市场”[11],必须以保证生态环境用水为前提;②在水资源利益分配上,应针对水事活动的不同阶段对水权进行分类,实现水权与土地权、水分配权与水使用权的相互分离,保障水权的排他性,减少水权交易中的交易成本;③在用水风险负担上,应摆脱行政自由裁量权对水权稳定性的影响,在对用水风险分类的基础上,建立相对明确的法规,以保障水权的确定性;④应对可交易水权的客体进行更为精确的界定,避免水权交易中的外部性问题。
4 我国可交易水权制度的构建
从世界范围看,可交易水权代表了水权制度的发展趋势。从构建可交易水权制度的视角,我国目前水权制度的最大缺陷在于用水风险负担规则。根据我国现有法律法规,我国水权制度主要存在两类用水风险负担规则:①按照规定的比例共同承担用水风险,如黄河流域各行政区域之间按照“同比例丰增枯减”的原则进行用水分配;②由政府进行直接管理,在必要时对用水权进行限制甚至取消。总体而言,我国水权制度的用水风险负担规则遵循行政主导的模式。我国政府在水权建设中具有重要地位[12],但过多的行政干预不可避免地影响水权制度自身的稳定性。有研究[13]指出,我国目前的水权制度缺乏安全性,当水权受到负面影响时,没有明确的条文规定如何应对发生的状况,现有的水资源管理体制强化了用水的不确定性[14]。这正是用水风险负担规则缺失造成的结果,需加以改变。笔者认为应该强化我国水权制度的稳定性,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市场预期,在此基础上逐步建立起适合我国国情的水权交易规则,最大限度地实现水资源的市场配置。主要措施应包括:以市场机制和协商机制弥补区域水权在排他性上的缺失;制定取水权优先规则;建立取水权征收补偿制度。
[1]陈敬德.可交易水权改革若干问题的思考[J].水资源保护,2006,22(5):32-35.
[2]CHONG H,SUNDING D.Water markets and trading[J].Annual Review of Environment and Resource,2006,31:239.
[3]CARL J B,SIREN S.Chilean water law as a model for international reform[M].Washington D C:RFF Press,2004.
[4]The Australia National Water Commission.Intergovernmental agreement on a national water initiative[M].Canberra:National Academies Press,2004.
[5]FISHER D E.Market,water right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J].The Journal of Water Law,2006,23(1):100-112.
[6]裴丽萍.可交易水权论[J].法学评论,2007(4):50-53.
[7]HEAR NE R R.The market alloca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transactions of water use rights in Chile[D].Minnesota:University of Minnesota,1995.
[8]尉永平.澳大利亚水改革的成功经验及启示[J].山西水利科技,2003(4):55-56.
[9]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Watertransfers in the west:efficiency,equity and the environment[M].Canberra:National Academies Press,1992.
[10]YOUNG M D,McCOLL J C.Robust reform:implementing robust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to achieve efficient water use in Australia[J].Journal of Land and Water,2003(3):43-47.
[11]胡鞍钢,王亚华.转型期水资源配置的第三种思路:准市场和政治民主协商[J].中国软科学,2000(5):12-16.
[12]李光丽,霍有光.政府在现代水权制度建设中的作用[J].水利经济,2006,24(2):58-61.
[13]高而坤.中国水权制度建设[M].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7.
[14]陈海嵩.水管理体制的法律思考[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6(3):35-39.
Study on institution construction of tradable water rights:a case study of reform of tradable water rights in Australia
CHEN Hai-song
(Environmental Law and Social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Zhejiang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University,Lin'an 311300,China)
The construction of tradable water rights was analyzed using the reform of tradable water rights in Australia as an example.It was found that the defect of basic frame of Australia water rights reform was the neglect of third-party effects in water rights trade.This provided a reference to the institution construction of tradable water rights in China,and the principle of water taking risk was the key in constructing the institution of tradable water rights in China.
water rights trade;water rights reform;third-party effects;legal rules
F407.9
A
1004-6933(2011)03-0091-04
10.3969/j.issn.1004-6933.2011.03.023
浙江省高等学校优秀青年教师资助项目(2010);浙江农林大学科研启动项目(2010FR082)
陈海嵩(1982—),男,湖北武汉人,讲师,博士,主要从事环境资源法学、水管理研究。E-mail:chshjf@yahoo.com.cn
(收稿日期:2010-11-03 编辑:彭桃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