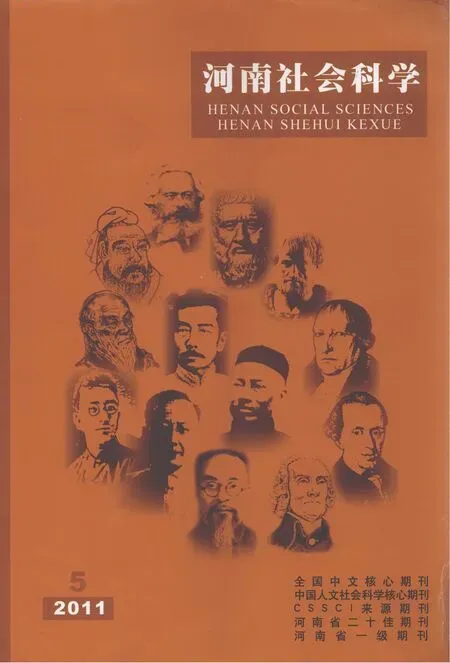国民幸福视角的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研究
2011-04-13邓先奇
邓先奇
(华中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4)
国民幸福视角的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研究
邓先奇
(华中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4)
消费主义生活方式的兴起对国民幸福造成不良影响,以GDP作为衡量经济社会发展的唯一指标无法如实反映国民幸福水平,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带来的社会问题冲击着国民幸福,这促使人们反思如何在经济社会发展中促进国民幸福水平的提升,而“不丹模式”下“国民幸福总值”的理念和实践则对我国提供了有益的借鉴。科学地构建和测评国民幸福指数,将国民幸福作为社会发展的终极价值取向,正确看待经济因素对国民幸福的影响,注意社会转型期提升国民幸福的关键,这是从国民幸福的视角思考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启示。
国民幸福;国民幸福总值;国民幸福指数;社会转型
当前,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国民收入的不断提高,“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不断得到贯彻和落实,国民幸福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人们既关注宏观的国民幸福研究,如GNH(国民幸福总值)提出的背景,GNH与GDP(国内生产总值)的关系,“不丹模式”的实践及启示,也关注微观的国民幸福研究,主要是指从微观个体的幸福体验来描述国民幸福,度量出“国民幸福指数”(NHI)来反映国民幸福状况,它成为社会发展评价的新尺度。
一、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引起人们对国民幸福的关注
(一)消费主义生活方式的兴起对国民幸福造成不良影响
从某种程度上说,如果没一定程度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得到满足,人就不会有满意和愉悦的状态,幸福也无从谈起,需求的满足需要消费,需要物质和能量的消耗,所以,消费的存在对幸福具有前提性的意义。
以美国为代表的、发源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则给社会幸福带来全面的不利影响,因为这种消费是通过大众传媒不断刺激人们的消费欲望,使人们沉迷于消费,追求高消费和消费的符号象征意义,消费的目的不再仅仅是为了满足实际需要。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的全球蔓延,一方面创造了需求,拉动了生产,但更多的是降低了国民幸福的水平。因为消费主义生活方式加速了全球资源的枯竭、环境的破坏和生态的恶化,而且会为了争夺资源和生存的空间引发国际矛盾与冲突;消费主义生活方式使人们公共活动空间和闲暇时间减少,过度饮食损害了身体健康,这必然导致国民幸福水平降低。更进一步地,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收入分配方式必然会产生人们之间的收入差距的扩大,在一个穷人和富人并存的社会里,消费主义生活方式必然会产生社会不安定的因素,因为高品质的、奢侈的消费毕竟只有小部分人才能实现,但它却激发了大多数人的与实际收入水平不相称的消费欲望,这种不合理的欲望轻则使人心理失衡,精神空虚,“仇富”心理产生,重则使社会贪污腐化滋生,违法犯罪横行,社会风气败坏。针对这一现象,美国学者杜宁指出:“消费与幸福之间的关系是微乎其微的。更糟糕的是,人类满足的两个主要源——社会关系与闲暇,似乎在奔向富有的过程中已经枯竭或停滞。这样在消费者社会中的许多人感觉到我们充足的世界莫名其妙地空虚……”[1]
西方消费主义生活方式已经在全球蔓延,我国也深受影响。消费主义生活方式给国民幸福带来的负面影响促使人们反思:物质财富的消费非但不是幸福的唯一来源,它反而降低了国民幸福水平。那么我们能否以一种全新的消费方式和发展模式来提升国民幸福水平?
(二)以GDP作为衡量经济社会发展的唯一指标无法如实反映国民幸福水平
人们一直都认为财富的增长与幸福的增长正相关,所以增加人们的财富一直被当做提高人们幸福水平的最有效的方式。在此观念的指引下,各国都以GDP作为衡量经济社会发展的唯一指标。但是,进一步发展的结果却表明,财富与幸福的关系并不呈显著正相关。对发展中国家而言,经济的增长确实可以提升人们的幸福水平,但经济发展到一定的水平以后,财富对幸福的贡献不那么大了。例如,美国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人均GDP翻了几番,但人们的幸福程度并没有多大的变化,压力反而增大了。中国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中国经济发展创造了世界经济奇迹,达到了年均增长9%的高速度,但是,Erasmus大学的Ruut Veenhoven教授对中国3次幸福调查却表明,1990—2002年间国民幸福指数并没有持续增加,1990年国民幸福指数是6.64(1—10标度),1995年为7.08,2002年为6.60[2]。这就不得不引起人们的反思:人们耗费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创造了巨额的社会财富,为什么没有相应地增加国民幸福水平?
实际上,国际经验表明,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非经济因素对幸福的影响会越来越大。当在人均收入达到1000美元之后,人们会更加关注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两个方面的非物质因素,这些也都是用经济指标无法衡量的影响人们幸福水平的重要因素。奚恺元则从四个方面指出GDP本身存在的缺陷使它无法如实反映国民幸福水平:“第一,一些对于人们幸福至关重要的因素以及经济发展所带来的非经济方面的负面影响并未被GDP指标体系所记录。第二,外部不经济没有被GDP指标完整记录。第三,非市场经济活动并未被纳入GDP的计算,从而夸大了经济增长对于幸福水平提高的贡献。第四,一些与国民幸福关系并不清晰甚至是体现国民幸福水平下降的经济增长被纳入GDP的计算。”[3]
当然,我们并不能就此否认财富对于幸福的重要性而放弃物质福利的发展,但是把GDP作为衡量经济社会发展的唯一指标是欠妥的,因为仅仅关注GDP并不必然提升国民幸福水平,我们需要以一种更科学更全面的方式来衡量经济社会的发展,从而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真正目的。
(三)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带来的社会问题冲击着国民幸福
2010年伊始,有几则新闻持续牵动着人们的神经,那就是国内发生了多起杀童案,富士康接连发生跳楼事件,还有其他种种令人匪夷所思的现象,例如毒奶粉、地沟油你方唱罢我登场,妙龄女孩扬言非“富二代”不嫁、丧失道德底线的女艺人高调做代言人……人们纷纷反思,为什么这些不正常的社会现象频发?2010年5月《国际先驱导报》上有一篇文章说,“ 告别了‘东亚病夫’的往事,体魄日渐强健的中国人心理却正在严重畸形化。杀人者被诊断为有精神病史,上访者可以被投入精神病院,社会失败者大都抑郁不堪,上班族为未来担惊受怕……我们大家,看来都病了”[4]。
“大家都病了”的社会绝对不是一个健康、幸福的社会。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些“社会病”的频发?人们纷纷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看法,比较一致的看法是,这是中国社会转型期的社会深层次矛盾所致。为什么社会转型会影响国民幸福?如何在社会转型期提高国民幸福水平?这些问题值得我们深思。
中国现在正处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的转变时期,而且这个转变是全方位的转变,“即包括经济增长在内的人民生活、科技教育、社会保障、医疗保健、社会秩序等方面在内的社会全面发展”[5]。在社会转型时期,人们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社会心态都会发生明显的变化。社会转型的最终目的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产生了巨大的成就,表现在政治民主、经济富强、精神文明、社会和谐等各个方面,这些成果极大地提高了人民生活质量、提升了社会幸福水平。但是,社会转型带来的问题也不容忽视,李维指出:“现代社会存在着的官僚腐败、政治商品化和消费主义风潮,极其容易造成道德失范、权利泛化和社会价值观念的冲突。在些背景下研究人们的主观幸福,是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6]
在当代中国,亟须一种全新的发展模式、发展观念和消费方式,来抵制消费主义生活方式对国民幸福带来的不良影响,缓解社会转型期的社会矛盾,防止“社会病”的发生,科学地衡量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从而实现国民幸福最大化的目标。
二、“不丹模式”下“国民幸福总值”的理念和实践
1972年,不丹国王吉格姆·辛格·旺楚克(Jim Singye Wangchuck)创造性地将“国民幸福总值”(GNH)引入治国理念,并作为不丹本国发展政策的基石。他认为,人生的基本问题是如何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之间保持平衡,国家在实现现代化的同时,不能失去精神生活和平和的心态,因此,不丹以GNH而不是GDP作为政府至高无上的社会经济发展目标,在国家治理的过程中兼顾公平和效率,从综合的、总体的角度衡量不丹的国民幸福,国家治理的目标并不是部分的国民幸福,而是让全体人民都过上幸福的生活,并且从经济增长(Sustainable and equitable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环境保护(Conservation of environment)、文化发展(Preservation and promotion of culture)、政府善治(Promotion of good governance)四个方面落实GNH国策[7]。
不丹以“国民幸福总值”(GNH)代替“国民生产总值”(GDP)来衡量国家发展,经过30多年的实践,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成效显著。在40年以前,不丹还处在物物交换的经济状态之下,但是,它现在却一直保持着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在南亚各国中是国民平均收入最多的国家。不丹有着丰富的旅游资源,但为了保护自然环境,不丹严格限制入境旅游的人数,而且还每天征收165—200美元的额外费用。目前,不丹王国的国土面积的74%被森林所覆盖,2005年10月,联合国环保署将“地球卫士”奖颁给了不丹。现在的不丹,人民生活虽简朴,但内心却充实宁静,整个国家社会秩序井然,犯罪率极低,去不丹旅游过的人都异口同声地说,来到这里好像回到了精神的家园。在海外留学的多数不丹人都会选择归国定居,尽管工资只有发达国家的一半甚至几十分之一。2006年,英国莱斯特大学公布的一份调查报告称,不丹在“全球快乐排行榜”中,紧随以高福利而著称的瑞士及北欧诸国之后,名列第8名[8],这说明,在重视GNH的理念和实践的发展政策指引下,在人均GDP为700多美元的不丹,人民生活得很幸福,“不丹模式”也引起了全球的瞩目。
在“不丹模式”的指引下,越来越多的国家及学者投身到国民幸福的研究中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通过实验心理学证明,快乐才是人类行为动机的本质和行为的终极目的,并提出了国民幸福指数的测度方法——日重现法(DRM),他由于研究快乐心理学的成果而获得2002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黄有光、奚恺元等一批行为经济学家,也提出了快乐是人类唯一的有理性的终极目标的思想。英国则创设了“国民发展指数”(MDP),把社会、环境成本以及自然成本都考虑了进去。而日本则抓住影响国民幸福的文化因素,大力发展“酷”文化产业,通过注重本国的GNC(Gross National Cool),不仅提升了本国的国民幸福水平,而且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
三、国民幸福指数的构建
国民幸福指数是衡量国民幸福程度的综合指标。对国民幸福进行系统的统计度量,科学地测评国民幸福水平的变化,不仅有利于落实国家的发展理念,而且可以为提升国民幸福水平提供政策依据和操作手段。在国际上,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最早提出了幸福指数的概念,在我国,钟永豪等(2001)提出“国民幸福指数”(NHI)的概念并设计了NHI指标体系。社会发展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方面因素协调进步的结果,NHI也是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中国科学院院士程国栋等人则建议,在国家层面上由政治自由、经济机会、社会机会、安全保障、文化价值观、环境保护六类构成要素组成我国的国民幸福核算指标体系,由幸福的建构性要素、工具性要素的划分及工具性要素的评价一起构成核算国民幸福的框架[9]。周四军等人则根据NHI已有的理论成果,从经济发展水平、人口与就业结构、人民生活水平和生活环境四个方面,选取了25个指标,构建了国民幸福指数评价指标评价体系,并利用变异系数法和距离综合评价法,对我国1998—2006年的国民幸福指数进行了测试和评价[10]。张韬认为,走出“路径依赖”、“资源依赖”和“政策依赖”,从而在根本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构建新型社会发展衡量方式的基础[11]。2004年奚恺元和《望东方周刊》对中国六大城市幸福指数进行了测试。2005年,中欧国际商学院完成了《2005年中国城市及生活幸福度调查报告》。2006年6月我国国家统计局负责人宣布正式启动国民幸福指数的研究和制定工作。
但是,“由于幸福属性的多样和评价的复杂,建立整体的、可行的幸福核算框架还有待时日”[9]。尽管如此,根据国内外目前已有的研究,对我国国民幸福指数的评价结果共同显示,虽然目前我国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都有了较大改善,但经济水平较低依然是影响我国国民幸福水平的主要因素,而且环境压力、收入分配的公平性也是影响国民幸福的重要因素。除此以外,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转型给人们带来的社会压力对国民幸福的影响也不容忽视。
四、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提升国民幸福水平的路径
(一)国民幸福应该作为社会发展的终极价值取向
对国民幸福的已有研究表明,将GDP作为衡量经济社会发展的唯一指标,无法如实反映国民幸福水平,反而会出现所谓的“幸福悖论”,因为“经济增长虽然与国民幸福的增加存在一定的关系,但是两者并不等价,一味以传统经济指标来指导社会发展会将人们引入歧途”[3],这种歧途就是为了发展生产而鼓励人们过度消费,使西方消费主义生活方式盛行,造成人心理的失衡和社会资源的浪费,在这种情况下人“被物所役”,以致在面对一个对象的时候会出现一处感觉,即“只有……在它被我们使用的时候,才是我们的……因此,一切肉体和精神的感觉都被这一切感觉的单纯异化即拥有的感觉所代替”[12]。人如果丧失了自我,即使在物质丰裕的条件下也找不到幸福的感觉。
社会是个人的集合体,社会发展本身不是目的,应当把社会发展当做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手段、实现国民幸福服务的工具,所以,要将社会的发展从一味地以GDP为中心转向以人的全面发展中心,要按照国民幸福的要求及其人们需要层次变化来修正与改革社会的方方面面。2006年10月,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开篇就指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保证,按照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原则构建和谐社会,就是一个以国民幸福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终极价值取向的社会。
(二)正确看待经济因素对国民幸福的影响
经济增长、收入增加是国民幸福的必要条件,因为经济增长增加了国民收入,收入增加会提升国民的消费水平,而消费需求的满足增进了国民幸福与快乐。从整体上看,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均收入越高,人们所感受到的幸福程度也越高,而且,收入与幸福之相关性在低收入群体中比在高收入群体中更显著。在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条件下,这种相关性更明显。“零点调查”发布的2005年中国居民生活质量指数研究报告显示,54.6%的城镇居民和66.4%的农村居民将贫穷列为感到不幸福的主要原因,所以,在人们基本生活需要还没有得到满足的条件下,想通过追求精神生活的方式来提升国民幸福水平是不现实的。
“不丹模式”也促使我们认识到,虽然我们不可忽视经济因素对幸福的影响,但经济因素并不是决定国民幸福的唯一因素,健康、亲情、生态、文化、社会公正、人际关系这些因素之间的协调发展对幸福也有决定性的影响,这些要素原本不需要耗费多少资源,却是快乐幸福的源泉。只是由于我们的社会片面地、过多地强调到物质消费、GDP对人们幸福的影响,才出现了既耗费大量资源,又使得幸福水平难以提高的后果。因此,借鉴“不丹模式”,关注国民幸福,以一种更加全面的、综合的指标衡量和指引经济社会发展,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实现每一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实现国民幸福最大化,尤其是像我国这样的人口、资源、环境矛盾突出的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导向和目标。
(三)处理好社会转型期的问题是提升国民幸福的关键
社会转型期的社会问题不容忽视。经济方面的贫富差距不断扩大、政治上的腐败横行、生态环境的破坏和生存资源的枯竭、社会心态的失衡和社会道德的失范,这些因素对进一步提升国民幸福的水平会产生负面影响。在这种情况下,需要通过健全社会制度来保障社会国民幸福,通过保护生态环境来维护国民幸福,通过关注文化发展来提升国民幸福。
制度能有效地化解社会矛盾,保持社会的稳定与有序,制度也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保证。我国的社会转型期既是发展的黄金期,也是矛盾的凸显期。如果一个国家公平正义出现严重的问题,社会成员、社会阶层、社会群体之间就会出现激烈的矛盾和冲突,社会和谐和社会稳定得不到保证,国民幸福也将难以实现。按照“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要求建立起来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必然是公正的社会制度,是能够实现国民幸福的制度,“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造福全体人民的伟大事业,其根本目的就是让人民群众在良善的社会制度安排中共享社会发展的成果,实现最大幸福”[13]。
人本身是一种对象性存在物,自然界就是人表现和确证人的生命的对象,如果没有自然界的存在,人的生命、人的本质就不会有存在的依据,人类的幸福也无从谈起。所以,保护生态环境、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是实现国民幸福的前提。我国目前已面临着巨大的生态环境压力,而且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也受到环境和资源的约束。由生态环境破坏引发的社会问题已严重影响了国民幸福。现阶段我国应建立以市场调节为手段,以法律保障为前提的生态环境补偿机制,从而改变我国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的趋势,这既是实现国民幸福的必然要求,也是“不丹模式”带给我们的启示。
社会文化直接影响人民的价值观,影响人们对事物的评价和对幸福的认识。在当前世界一体化的条件下,更要对外来文化和传统文化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尤其要注重吸收传统文化中对国民幸福有益的因素。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勤劳简朴、知足常乐能有效地抵制消费主义文化对国民幸福的不良影响,传统文化中的注重家庭、亲情、集体的思想也是提升幸福的重要手段,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思想更与现代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观念不谋而合。
[1][美]艾伦·杜宁.多少算够——消费社会与地球的未来[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
[2]WDH.World Database of Happiness,Continuous register of research on subjective appreciation of life,(version 2005)[EB/OL].Http://www.eur.nl/fsw/research/happiness.
[3]奚恺元,等.撬动幸福[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8.
[4]国际先驱导报.我们的社会病了[EB/OL].http://news.xinhuanet.com/herald/2010-05/24/content_13550195.htm.
[5]范燕宁.当前中国社会转型问题研究综述[J].哲学动态,1997,(1):18—21.
[6]李维.风险社会与主观幸福:主观幸福社会心理学研究[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
[7]Lyonpo Jigmi Y,Thinley.Gross.National Happiness and Human Development-Searching for Common Ground[R].Gross National Happiness Discussion Papers,Centre for Bhutan Studies,1999.
[8]淦家辉,王玲玲.从GDP到GNH——伦理学视野下人类发展考量的跃升[J].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4):72—76.
[9]程国栋,徐中民,徐进祥.建立中国国民幸福生活核算体系的构想[J].地理学报,2005,(6):883—893.
[10]周四军,庄成杰.基于距离综合评价法的我国国民幸福指数NHI测评[J].财经理论与实践,2008,(5):112—115.
[11]张韬.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走出“路径依赖”陷井[J].贵州社会科学,2010,(12):40—44.
[12]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13]罗建文.民生幸福与制度选择的哲学探索[J].哲学动态,2010,(1):91—95.
F27
A
1007-905X(2011)05-0086-04
2010-06-30
邓先奇(1978— ),女,湖北大悟人,华中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社会认识论、幸福论。
责任编辑 姚佐军
(E-mail:yuid@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