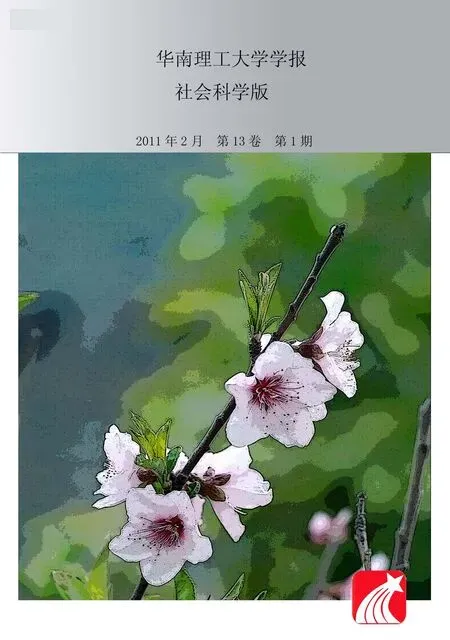战国语境下的“白马非马”新解
2011-04-13郭智勇
郭智勇
(电子科大中山学院 香山文化研究所,广东 中山 528400)
一
“白马非马”是中国名学史乃至中国思想史上一个著名的命题,同时也是一个久悬未决的公案。据说它是战国时期的名家公孙龙所提出和主张。传统上,主流学派都以《公孙龙子》中的有关论述作为正解。该书《白马论》说:
“白马非马,可乎: ”曰“可”。曰: “何哉?”曰: “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故曰白马非马。”
“马”所指的仅是物之“形”,而“白”所指的是物的“色”,“色”和“形”不是一码事,所以“白马”不等于“马”。不难知道,这是从比较抽象的理论思维角度所作的一个概念分析判断。
问题是,这一对“白马非马”的解释仅仅是《公孙龙子》一书的说法,在先秦其它的典籍中并无旁证。特别是,在刘向所辑的极为可靠的先秦典籍《战国策》中,本是有一段关于“白马非马”的话语的,只是二千年来这段话语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合理的解释。《赵策二·秦攻赵》有这么一段:
夫刑名之家皆曰“白马非马”也。已如白马实马,乃使有白马之为也。
这段话的上下文是这样的:
秦王曰: “寡人案兵息民,则天下必为从,将以逆秦。”苏子曰: “臣有以知天下之不能为从以逆秦也。臣以田单、如耳为大过也。岂独田单、如耳为大过哉?天下之主亦尽过矣!夫虑收亡齐、罢楚、敝魏与不可知之赵,欲以穷秦折韩,臣以为至愚也。夫齐威、宣,世之贤主也,德博而地广,国富而用民,将武而兵强。宣王用之,后富韩威魏,以南伐楚,西攻秦,为齐兵困于殽塞之上,十年攘地,秦人远迹不服,而齐为虚戾。夫齐兵之所以破,韩、魏之所以仅存者,何也?是则伐楚、攻秦而后受其殃也。今富非有齐威、宣之余也,精兵非有富韩劲魏之库也,而将非有田单、司马之虑也。收破齐、罢楚、弊魏、不可知之赵,欲以穷秦、折韩,臣以为至误。臣以从一不可成也。客有难者:今臣有患于世,夫刑名之家皆曰“白马非马”也。已如白马实马,乃使有白马之为也。此臣之所患也。昔者秦人下兵攻怀,服其人。三国从之,赵奢、鲍佞将,楚有四人起而从之,临怀而不救,秦人去而不从。不识三国之憎秦而爱怀邪?忘其憎怀而爱秦邪?夫攻而不救,去而不从,是以三国之兵困,而赵奢、鲍佞之能也,故裂地以败于齐。田单将齐之良,以兵横行于中十四年,终身不敢设兵以攻秦折韩也,而驰于封内,不识从之一成恶存也。”于是秦王解兵不出于境,诸侯休,天下安,二十九年不相攻。《赵策二·秦攻赵》
这段话二千年来都被置于一种扭曲的状态。归笼一下,传统的解释大约有三种,但都未能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第一种理解可说是不知所谓,如鲍彪所注: “如使白马实马,必有白马之为,而天下之马不皆为白马,故曰非马。”[1]这种解释与文章的语境毫无关联。第二种理解是似是而非,如戴文光所注: “白马原非马,六国原不纵。使名之为白马,实有白马,则六国言纵,实成其纵,今都不然。”[1]1037这种理解好似与上下文有些关系,但仍然过于模糊,没有给出古人讲这些话的理由。第三种认为这一段是错简,完全不予理睬。这种理解不是解决问题,而是取消问题。
总之,过往的注解对这一段文字实质上并没有作任何真正意义上能符合上下文语境的解释,也就是说对这一段文字的研究几乎是空白。这使得我们对战国时代的著名命题“白马非马”的原意扑朔迷离,也使得我们对《公孙龙子》有关“白马非马”的理解是否真的出自战国名家心存疑虑。
笔者2006年曾对《吕氏春秋》中“藏三牙”作过研究,得出了与过往的理解完全不同的认识。笔者认为,《吕氏春秋》中的“藏三牙”并非《公孙龙子》的“藏三”命题,它其实是一个日常意义的文字诡辩。因为人们日常所知的常识是“藏两牙”(古“藏”通“臧”,“臧”是小孩的常用称呼,“臧两牙”是说“七八岁的小孩由于换牙常给人感觉只有两个牙。)“藏三牙”的说法是一种辩术,它从字型上来说“藏三牙”。“藏三牙”是说: “藏”字有三个“牙”型笔画。[2]在对《吕氏春秋》研究的过程中,笔者对战国时期以公孙龙为代表的名家的思想主旨有了一定的认识。战国时期的名家是建立在日常经验基础上的名学,它强调的是日常语言层面上的言意相符和名实一致。 它与《公孙龙子》中纯粹的概念分析和逻辑梳理有相当的学术距离。笔者因而怀疑《公孙龙子》对“白马非马”的论述未必是战国时期形名家公孙龙的原意。
为此,笔者对《战国策》和相关经典进行了充分的阅读和深入的理解,果然在《战国策》文本所提供的背景和线索中找到了战国年间的这个命题的真正含意。
问题的答案出在“白马”上,传统上由于过于受制于《公孙龙子》文本,总以为这是一个抽象的理论问题。实则从《战国策》文本出发,完全可以看出,“白马”指的是洹水边的一个地名,在战国年间是一个有名的渡口,秦国与东方六国的边界所在。这一点可以从《战国策》文本中体现:
然则是举赵则韩必亡,韩亡则荆、魏不能独立,荆、魏不能独立,则是一举而坏韩、蠹魏、挟荆,以东弱齐、燕,决白马之口以流魏氏。一举而三晋亡,从者败。大王拱手以须,天下遍随而伏,伯王之名可成也。(《秦策一张仪说秦王》)
张仪为秦连横说赵王曰: “弊邑秦王使臣敢献书于大王御史。大王收率天下以傧秦,秦兵不敢出函谷关十五年矣。大王之威行于天下山东,弊邑恐惧慑伏,缮甲厉兵,饰车骑,习驰射,力田积粟,守四封之内,愁居慑处,不敢动摇,唯大王有意督过之也。今秦以大王之力,西举巴蜀,并汉中,东收两周而西迁九鼎,守白马之津。秦虽辟远,然而心忿悁含怒之日久矣。今宣君有微甲钝兵,军于渑池,愿渡河逾漳,据番吾,迎战邯郸之下。愿以甲子之日合战,以正殷纣之事。敬使臣先以闻于左右。(《赵策二·张仪为秦连横说赵王》)
《战国策》中“白马非马”的“白马”是一个地名,而不是真正意义上哺乳动物“马”。“白马非马”这一话语在当时其实是一个非常生活化的言语,完全没有《公孙龙子》中概念分析和逻辑演绎的意味。
二
读者朋友也许会问,笔者凭什么要这样来理解?也就是说,为什么战国时的形名家要说“白马非马”这样的话?
只要我们不被《公孙龙子》所误导,而是从《战国策》所提供的背景和线索中去思考,这一段话的含意其实是非常明确的。
我们都知道,先秦时期的中国古人是非常重视盟誓的。在进行重大的合作行动之前都要举行隆重的结盟仪式,宰杀牲畜以牲血涂口并将牲血注于盟书之上,进行口头及文字上的发誓诅咒以神圣化。1965年山西侯马出土的战国时期盟誓遗址就是一个最好的实证,《吕氏春秋》中有杀牲结盟详尽的文字解说:
昔周之将兴也,有士二人,处于孤竹,曰伯夷、叔齐。二人相谓曰: “吾闻西方有偏伯焉,似将有道者,今吾奚为处乎此哉?”二子西行如周,至于岐阳,则文王已殁矣。武王即位,观周德,则王使叔旦就胶鬲于次四内,而与之盟曰: “加富三等,就官一列。”为三书,同辞,血之以牲,埋一于四内,皆以一归。又使保召公就微子开于共头之下,而与之盟曰: “世为长侯,守殷常祀,相奉桑林,宜私孟诸。”为三书,同辞,血之以牲,埋一于共头之下,皆以一归。伯夷、叔齐闻之,相视而笑曰: “嘻!异乎哉!此非吾所谓道也。……今周见殷之僻乱也,而遽为之正与治,上谋而行货,阻丘而保威也。割牲而盟以为信,因四内与共头以明行,扬梦以说众,杀伐以要利,以此绍殷,是以乱易暴也。……”二子北行,至首阳之下而饿焉。(《诚廉》)
所以宰杀牲畜从而进行“歃血”是结盟仪式中至为重要的一个环节。在古人看来,必须要“歃血”才能使结盟受到天地鬼神的约束,才能使结盟的各方尽心尽力履行自己的盟约义务。
从《史记》的有关内容来看,古代中国人确有宰杀白马来盟誓或敬神的习俗。*《史记》中有不少古人杀白马敬神的记载: 如《始皇本纪》载: 二世梦白虎齧其左骖马,杀之,心不乐,怪问占梦。卜曰: “泾水为祟。”二世乃斋於望夷宫,欲祠泾,沈四白马。又《河渠书》载: 於是天子已用事万里沙,则还自临决河,沈白马玉璧于河,令群臣从官自将军已下皆负薪窴决河。又《史记正义》载吴俗传云: 子胥亡后,越从松江北开渠至横山东北,筑城伐吴。子胥乃与越军梦,令从东南入破吴。越王即移向三江口岸立坛,杀白马祭子胥,杯动酒尽,越乃开渠。从《战国策》所提供的背景和线索中,可以看出,之所以当时的形名家要说“白马非马”,似乎是因为当时的合纵各国,并没有宰杀白马从而进行“歃血”的结盟仪式,只是准备在“白马”这个地方作一些象征性的结盟表示。这种象征性的作法本来就抺杀了盟誓的神圣性,对特别重视“名实相符”、“循名责实”的形名家来说,这也是与他们的行为规范完全不相容的,所以他们一针见血地指出: “白马非马”——你们这些象征性的行为是起不到作用的。
当我们明白到这层意思时,前述的那段难解的文字也就文从意顺了。
客有难者: “今臣有患于世,夫刑名之家皆曰‘白马非马’也。已如白马实马,乃使有白马之为也。此臣之所患也。”
这一段的意思用现代语文说应该是这样的: 有人提出了如下的质疑: 我现在感到疑惑不安,因为形名家指出说,你们的“白马”仅是指地名“白马”,并不是真的动物马(实马)。这是不行的。(如果要使盟约达到真正的效果,牲畜必须是是真正的动物),只有“白马”是真正的动物马时,才谈得上有真正的刑“白马”的“歃血盟誓”行为。(现在你们仅仅是象征性地在白马这个地方盟誓,而不是真的宰杀动物马。)我担心这样做的效果。
这里的“已如”即是“必如”的意思,“乃使”即是副词“才能”的意思。“已如白马实马,乃使有白马之为也”是说“白马一定要是真实的动物马,才谈得上有对白马的行为(所谓“刑白马”,所谓“歃血盟誓”)。
这样的理解并非来自笔者的想象,而是有充分的史料依据的。从《战国策》的有关文本看,当时的合纵各国确实准备在白马这个地方作一个“刑白马”的象征性仪式,而不是要真的宰杀白马从而完成真正意义上的盟誓: 《赵策二》说:
故窃大王计,莫如一韩、魏、齐、楚、燕、赵六国从亲以傧畔秦,令天下之将相相与会于洹水之上,通质刑白马以盟之,约曰: ‘秦攻楚,齐、魏各出锐师以佐之,韩绝食道,赵涉河、漳,燕守常山之北。……秦攻赵,则韩军宜阳,楚军武关,魏军河外,齐涉渤海,燕出锐师以佐之。诸侯有先背约者,五国共伐之。六国从亲以摈秦,秦必不敢出兵于函谷关以害山东矣!如是则伯业成矣!”(《苏秦从燕之赵》)
“相与会于洹水之上,通质刑白马以盟之。”问题是,这里要“刑”的似乎不是真正的动物白马,而是在“白马”这个地方作一个的象征性“刑”的仪式而已。或许“白马”这一地名就是因为该处有一石头景观极似“白色之马”,它能够满足人们“歃血盟誓”的联想要求。《战国策》的另一处也有类似的记载,隐约可见“刑白马”仅是一个在“白马”这一景观上举行的象征性仪式而已:
且夫诸侯之为从者,以安社稷、尊主、强兵、显名也。合从者一天下,约为兄弟,刑白马以盟于洹水之上,以相坚也。夫亲昆弟同父母,尚有争钱财,而欲恃诈伪反覆苏秦之余谋,其不可以成亦明矣。(《魏策一·张仪为秦连横说魏王》)
“白马非马”所在的《赵策二·秦攻赵》,所载的内容是苏子(应是苏秦)对秦王的对话。苏子想解除秦国对东方六国的戒备之心,从方方面面解说此时的东方六国不可能结成合纵的同盟来对付秦。而其中的“白马非马”一段借形名家的观点指出,由于合纵各国不是按传统的正规仪式来“歃血盟誓”,所以他们的合纵,主观上来看,表明他们没有诚心,客观上也就不会有效果了。古人是非常强调天人合一、主客互渗的。可以看出,这样的理解是与上下文紧密相关的。
至此,我们似乎可以认定,战国期间的公孙龙辈所说的“白马非马”仅是一个日常经验意义上的话语。它的本意是: “白马”指的是“白马”这个地方而不是真正的马。
三
如果认定《战国策》的“白马非马”是一个日常经验意义上的话语,那《公孙龙子》中的“白马非马”则是一个完全不同层面上的命题,有着完全不同的的内涵和意趣。纵观整个《公孙龙子》的内容,虽然有不少部分到现在还没有得到充分的理解,但它们的高度思辨性和纯概念分析的风格与《战国策》和《吕氏春秋》所反映的时代特征是完全不同的。这一点,只要我们仔细品味《战国策》和《公孙龙子》,是完全可以感受到的。
战国时期名家的着重点是日常经验意义上有“名实相符”,所谓“循名责实”,这一点可以从另一成书年代非常清楚的先秦典策《吕氏春秋》中得到证实。该书《正名》篇说:
名正则治,名丧则乱。使名丧者,淫说也。说淫则可不可而然不然,是不是而非不非。故君子之说也,足以言贤者之实、不肖者之充而已矣,足以喻治之所悖、乱之所由起而已矣,足以知物之情、人之所获以生而已矣。凡乱者,刑名不当也。人主虽不肖,犹若用贤,犹若听善,犹若为可者。其患在乎所谓贤从不肖也,所为善而从邪辟,所谓可从悖逆也。是刑名异充,而声实异谓也。
该书《审应》篇中的故事很能代表战国年间真正的公孙龙的思想状况:
赵惠王谓公孙龙曰: “寡人事偃兵十余年矣而不成,兵不可偃乎?”公孙龙对曰: “偃兵之意,兼爱天下之心也。兼爱天下,不可以虚名为也,必有其实。今蔺、离石入秦,而王缟素总布;东攻齐得城,而王加膳置洒。秦得地而王布总,齐亡地而王加膳,所非兼爱天下之心也。此偃兵之所以不成也。”
《审分》的意趣同样:
今有人于此,求牛则名马,求马则名牛,所求必不得矣,而因用威怒,有司必诽怨矣,牛马必扰乱矣。百官,众有司也;万物,群牛马也。不正其名,不分其职,而数用刑罚,乱莫大焉。夫说以智通,而实以过悗;誉以高贤,而充以卑下; 赞以洁白,而随以污德;任以公法,而处以贪枉;用以勇敢,而堙以罢怯。此五者,皆以牛为马、以马为牛,名不正也。故名不正,则人主忧劳勤苦,而官职烦乱悖逆矣。国之亡也,名之伤也,从此生矣。白之顾益黑,求之愈不得者,其此义邪!故至治之务,在于正名。名正则人主不忧劳矣,不忧劳则不伤其耳目之主。问而不诏,知而不为,和而不矜,成而不处,止者不行,行者不止,因刑而任之,不制于物,无肯为使,清静以公,神通乎六合,德耀乎海外,意观乎无穷,誉流乎无止。此之谓定性于大湫,命之曰无有。
同一个“白马非马”的表述,它的内涵却有着根本的不同,它无疑反映了两个根本不同的思维趣味。从学术发展史上看,应该代表着完全不同的历史阶段(很难想象,同一个公孙龙既会说“白马是地名不是马”; 又会说“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故曰白马非马。”)章学诚曾精辟指出: “古人未尝离事言理。”(《文史通义·易教上》) 与《吕氏春秋》一样,《战国策》名家所表现的正是一种在日常经验层面的朴素思想,反映的是战国时期中国名学的发展阶段。与之不同,《公孙龙子》则是一种建构在概念分析和逻辑演绎基础上的有相当深度的作品,是一种纯粹的理论著作②。笔者认为,把《公孙龙子》和《战国策》、《吕氏春秋》浑为一谈是一种缺乏发展观的表现。《公孙龙子》应该是后人托付的作品。
参考文献:
[1] 范祥雍. 战国策笺证[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1037.
[2] 郭智勇. 藏三牙新解及其他[J]. 船山学刊,2007(4): 94-96.
②《公孙龙子》之费解其来有自,以至于以东晋谢安这样的旷世才俊,阮裕犹有“非但能言人不可得,正索解人亦不可得”之叹。详见《世说新语· 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