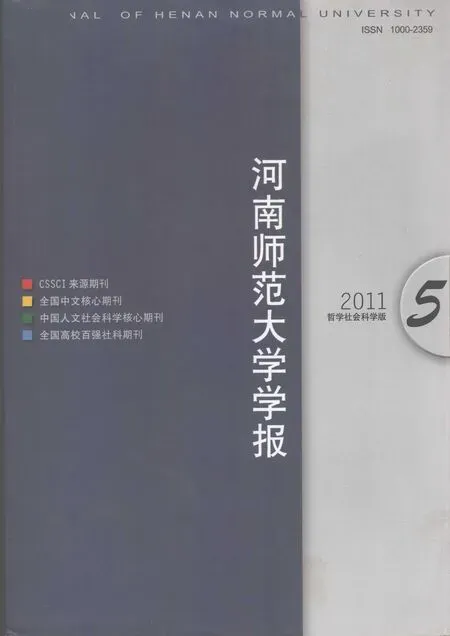去恶成性及其内在困境
——张载的人性论探析
2011-04-12金银润
金 银 润
(北京师范大学 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哲学与社会学学院,北京 100875)
去恶成性及其内在困境
——张载的人性论探析
金 银 润
(北京师范大学 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哲学与社会学学院,北京 100875)
张载所言之性包括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天地之性至清、至善,是人性善的来源;气质之性善恶相混,乃恶之发端。气质之恶可变而为善。变化气质,须有立本、学礼、善反等涵养工夫。其人性理论为从根本上阐释道德善恶问题提供了新颖的方法和视角,有力地推进了传统哲学及伦理道德思想的发展。但在从天地之性到气质之性,又从气质之性反归天地之性的跨越中,他缺乏有力的逻辑推演,从而使得变化气质反归天地之性在理论上也面临着一定的困境。
张载;天地之性;气质之性;变化气质;困境
关于人性的讨论由来已久。在伦理学史上,有孟子的“性善”论、荀子的“性恶”论、董仲舒的“性三品”论、扬雄的“性善恶混”论、韩愈的“性情三品”论、李翱的“性善情恶”论等等。它们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道德善恶问题,但另一方面又没有完全从理论深层解释清楚:从最本源的层面言,人性到底源于何物,是善是恶?如果说人性为善,为什么有的却表现为恶的品质?如果说人性为恶,为什么会有如此众多道德芬芳、境界高远的圣贤?为了彻底解答人性善恶问题,张载提出了天地之性、气质之性及变化气质等观点。
一
说到人性,须谈“性”,谈性,须讲“气”。在张载的语义中,“太虚即气”[1]8,“虚空即气”[1]8,从本质而言,太虚也就是气。具体而言,气有两种。其一,是“湛一无形”[1]10的气,即“太虚”,也叫“太虚之气”,是“气之本体”,也是万物之本体。此时的“气”,是指物质存在性。其二,是“感而生”[1]10之气。其有阴阳之变化。前者是后者的本体,后者是前者的聚化。归根结底,它们只是一气:“太虚之气,阴阳一物也。”[1]231
由气可导出“性”。张载对“性”有自己独特的理解。他说:“由太虚,有天之名;由气化,有道之名;合虚与气,有性之名;合性与知觉,有心之名。”[1]9对“合虚与气,有性之名”中“虚”与“气”的理解比较复杂。陈来先生指出:“这里所说的‘虚与气’分别指太虚之气的本性与气的属性。”[2]51牟宗三先生对此处的解释为:“横渠说此语时,似以为‘至静无感,性之渊源’,虽无感,而并非无感之性能,而感之性能即气也,神即气之质性也,故云‘合虚与气有性之名’矣。”[3]424而气的属性就是“神”。张载说:“神化者,天之良能。”[1]17“神者,太虚妙应之目。”[1]9王夫之也认为:“神者,气之灵。”[4]8天即是太虚、太虚之气。但“神”是指气的潜在性能,不是指外在功效。“神,天德,化,天道。德,其体,道,其用”[1]15。王夫之认为:“变者,化之体;化之体,神也。”[4]67所以,性就是合本原与性能而言:“天能谓性。”[1]21
基于此,可以说,“性者万物之一源”[1]21,“有无虚实通为一物者,性也;不能为一,非尽性也”[1]63。性是万物之本源,也是体:“未尝无之谓体,体之谓性。”[1]21
此性也是天性、天地之性,是至清、至善的:“太虚为清。”[1]9“天地以虚为德,至善者虚也。”[1]326“天地之性纯粹至善。”[5]695它也是不亡的:“聚亦吾体,散亦吾体,知死之不亡者,可与言性矣。”[1]7它于人皆是善的:“性于人无不善。”[1]22
对于人性而言,除了至清的天性,还有不纯、不清的性——气质之性。何谓气质之性?“形而后有气质之性,善反之则天地之性存焉”[1]23。气质之性,是人的形体形成之时,由于禀气的清浊的不同而形成的性。它来源于阴阳之气。阴阳之气,在天为道,在人则为性:“阴阳者,天之气也,亦可谓道。刚柔缓速,人之气也,亦可谓性。”[1]324此性是“人之气”,也是气质之性。当气质之性没有成就天性时,是善恶相混的:“性未成则善恶混。”[1]23“气质之性有善恶也。”[5]694所以君子不以它为本源之性。对人而言,气质之性是与生俱来的,并且是被气所决定的:“人之气质美恶与贵贱夭寿之理,皆是所受定分。”[1]266
虽然气质之性来自“感而生”之气,但是从终极来看,它也来自天性:“性者万物之一源。”[1]21正因如此,它可以反归于天地之性。不过,它的反归,不是简单的返回,需要一系列复杂的改造程序。这就需要变化气质。
二
张载认为气质是可以变化的:“气质恶者学即能移,今人所以多为气所使而不得为贤者,盖为不知学。”[1]266气质为恶的人,只要肯学便能使气质转移,成就天地之性。现在的人为气所禀,不能为圣贤,是因为他们不懂得要去学习、改造。变化气质的过程,就是不断地进行内在和外在修为的过程。
(一)立本
变化气质之始,是立本:“学者先须立本。”[1]324“学者当须立人之性。”[1]321立本,也就是弘心,志于天性,立天性于心。心弘则阔大平旷,虚净纯然,万物皆通,不为物欲所诱导:“盖心弘则是,不弘则不是,心大则百物皆通,心小则百物皆病。悟后心常弘……常不为物所牵引去。”[1]269常存此心,以此为本,心便立得正,学习、行动就不会迷失方向、误入歧途。为此,他极力批评时人的不当之处:“若今学者之心出入无时,记得时存,记不得时即休,如此则道义从何而生!”[1]267此心丧失,或不稳、不定,时有时无,都是无法复性、成性的,道义何以可得?
本立,心弘,虚静平旷,学者便可温和、谦恭。“则学者先须温柔,温柔则可以进于学,《诗》曰:‘温温恭人,惟德之基’,盖其所益之多”[1]268—269。温柔,乃温和、谦恭之义。温和、谦恭之后,心平气和,抛却高傲自大、狂躁不安之态,可进于学。
(二)学“礼”
学习,首先和主要的是学“礼”。“礼”,一般而言,包括《周礼》、《仪礼》、《礼记》三部。而张载尤重《周礼》。张载在《经学理窟》中专有一篇讲解《周礼》。《经学理窟·礼乐》中的“礼”,也尤重《周礼》。比如他说:“酌必是周公七年之后制礼作乐时于大武有增添也。”[1]261“《周礼》言‘乐六变而致物各异’,此恐非周公之制作本意。”[1]262这些都直接说明,张载此处所言之“礼”是尤指《周礼》的。另外,《宋元学案·横渠学案上》中说张载:“至于好古之切,谓《周礼》必可行于后世,此亦不能使人无疑。”[5]665“先生法三代,宜不在《周礼》。是又不可不知也。”[5]665这些进一步佐证了他对《周礼》的偏重。
“礼”还包蕴着另一种“礼”——“天地之礼”。所谓“天地之礼”,也就是理、天理。他说:“礼亦有不须变者,如天叙天秩,如何可变!礼不必皆出于人,至如无人,天地之礼自然而有,何假于人?”[1]264它不出于任何人之手,是一种宇宙中本然就存在的、永远不变的、定分天地秩序的“礼”,此便是天之理。
两“礼”虽形态不一,但有着紧密的联系。天地之礼是圣人制定之礼的本体、来源,而后者是天地之礼在人身上的体现。他说:“礼所以持性,盖本出于性,持性,反本也。”[1]264“礼即天地之德也。”[1]264所以,学习、领悟圣人之礼,是在悟天之理,能“持性反本”,除去恶质,复归太虚之性。
学礼须诚意:“故成就其身者须在礼,而成就礼则须至诚也。”[1]266但学礼与诚意并无先后,两者须兼修:“诚意与行礼无有先后,须兼修之。”[1]266诚意可以使人专心于学礼,而学礼又可以去除杂念,守定于性、理。两者互为条件,相互依存,相辅相成。
同时,学礼要谨防四弊:“学者四失:为人则失多,好高则失寡,不察则易,苦难则止。”[1]30王夫之对此的解释是:“为人,求诸人也,失多者,闻见杂而不精;好高者,自困而不能取益于众;易于为者,不察而为之则妄;知其难者,惮难而置之则怠;四者,才之偏于刚柔者也。”[4]156如果自己不认真思考、体悟,老是依赖于别人的说解和见识,自己的知识见闻可能多而杂,但不可能精深;高傲自大,自我封闭,不虚心向别人学习,就不能博取众长;不深入体察,学到的东西则会很浅薄,很空;见难而退,无益于进步。学礼的过程中,要尽量避免以上的情况发生。
(三)善反与不善反
学礼,不一定就能通达天地之性,还须看其善反与否。张子云:“性于人无不善,系其善反不善反而已。”[1]22“善反之则天地之性存焉。”[1]23性于任何人,都是善的。要成就天性,在于其善反与不善反。“反”,来自《中庸》与《孟子》。《中庸》云:“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诸正鹄,反求诸其身。’”[6]779孟子也说过:“反身而诚,乐莫大焉。”[7]302张子借之而来,用它指要由末归于本,由善恶混的气质之性反归于至善的天地之性。
要做到善反,从反面来说,就不能“过”:“过天地之化,不善反者也。”[1]22“化,天道”[1]15,是天地的运行法则。它并不仅仅指天地的自然运行规律,还包含有天地的道德运行法则。因为天乃“至善”之太虚。过,有超过与不及之义,总之都不与天道相统一,皆不适宜。从正面而言,即是要“无意为善,性之也,由之也”[1]28。即是说,不要以私力强行而为,也不要抱有某种心机故意为了善而行善,这些都是在伤害天道。要顺应天道本性而为,与天道相和谐。此便是“所谓圣者,不勉不思而至焉者也”[1]28的道理。
当然,圣人可以“不思”而为,而常人则须“思”:“天资美不足为功,惟矫恶为善,矫惰为勤,方是为功。人必不能便无是心,须使思虑,但使常游心于义理之间。”[1]271人的天资好,并没有什么值得耀扬的。能改惰为勤,化恶为善,这才值得去做、称赞。而要改恶为善,必须要运用人的思虑功能。
思的过程,包含着“心悟”:“学贵心悟,守旧无功。”[1]274此“悟”有两层含义:其一,要悟得其中的深义、精髓。学礼,不能停留于字面的认识,要深深体悟其中深邃的道理,在思想、精神上与圣人相交游、相通联。其二,学礼,要有自己的创新发现。守旧无创见则无益。破旧立新,需要有疑。“于不疑处有疑,方是进矣”[1]275。敢于存疑,尤其是要在别人无疑之处,产生疑问,才会有进步。
运用思虑也不能过甚,要简易而为:“夫求心不得其要,钻研太甚则惑。心之要只是欲平旷,熟后无心如天,简易不已。”[1]269“简易不已”,在方法上就是中庸之道。保持中道,切勿太过,太甚则不正,不正则会被迷惑。
善反,还需合内外之道:“修持之道,既须虚心,又须得礼,内外发明,此合内外之道也。”[1]270修持,既要虚其心,让心保持平旷、自然,又要“得礼”。这就需要学习、践行礼,即是“复性”,“复性便是行仁义”[1]341。将虚心与学习、践行相结合,才能反归天性。
三
张载的人性论,成一家之言,发前人之未发,意义甚大。简言之,有以下几点。
(一)其人性论,既以物质本原性为基础,也强调了善恶的矛盾运动性
“太虚即气”[1]8,“合虚与气,有性之名”[1]9,强调了性的物质本原性。“由气化,有道之名”[1]9,显示了气的阴阳变化性。而“变化气质”,演绎了由气质之性反归天地之性的矛盾运动性。“性善”并非“空”“无”的,其存在的本体是至善的太虚。恶由禀气而成,但能变化为善。性的物质本原性批驳了释、老“空”、“无”的本体论;其矛盾运动性突破了董仲舒认为“人受命于天,有善善恶恶之性,可养而不可改,可豫而不可去”[8]34的“恶不可去”的思维定式,也超越了韩愈认为的“然则性之上下者,其终不可移乎”[9]6429的“善恶不移”论。在很大程度上,张载人性的物质本原性和矛盾运动性既批判了虚无和唯心的人性本体论,也生动演示了道德善恶的辩证运动规律。
(二)能将道德属性和自然属性看成是人性的来源,是人性论史上的一大进步
孟子的“性善”论,荀子的“性恶”论,董仲舒的“性三品”论,扬雄的“性善恶混”论,韩愈的“性情三品”论,李翱的“性善情恶”论等,要么以道德属性为人性,要么以自然属性为人性,而没有将两者共同看作是人性之来源。
张载有综合孟、荀之意图,在理论上也作出了极大的努力。他认为,人性之善源于天地之性,人性之恶源于气质之性。而天地之性,是“至善”的,是道德属性;气质之性则包含了“人之刚柔、缓急、有才与不才”的自然属性。虽然在价值导向上,他不以气质之性为性。但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的介入,已将道德属性和自然属性统统纳入人性的范围之中。这在人性论史上是一大进步和启迪,对后来提出“性者生理也”[10]55的王夫之及主张“血气心知,性之实体”[11]21的戴震有着深刻的影响。
(三)在传统伦理的视野中,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提出,能较好地解决人性善恶问题
董仲舒的“性三品”论认为:“圣人之性不可以名性,斗筲之性又不可以名性,名性者,中民之性。”[8]311—312但董子并未言明为什么会有三种人性。扬雄的“性善恶混”论主张:“人之性也,善恶混。修其善则为善人,修其恶则为恶人。”[12]85扬雄只是在后天修为的层面言人性可以为善为恶,但并不曾言性为何是善恶混的。韩愈认为,性是人先天就有的:“性也者,与生俱生也。”[9]6428而情是“接于物而生也”[9]6428。还说:“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导而上下也;下焉者,恶焉而已矣。”[9]6428那么,摆在韩愈面前的难题与董子的极其相似:同为人,为什么性有上中下三品呢?李翱认为性是善的,情是恶的。他说,“性无不善”[13]7194,“情由性而生”[13]7192,且“情者性之动也”[13]7192。既然性是善的,而情乃性所生,又是性之动,那么,为什么“善”的“性”却生出了“恶”的“情”?这也是他必须迎接的挑战。以上诸多理论难题,用张载的“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都可以得到一个较好的阐释。人性本善,而由于气禀的不同而形成了“性三品”、“性善恶混”、“性善情恶”等不同的状态。但只要变化气质之恶,皆能成就善性。
其天地之性、气质之性及变化气质理论的提出,意义非凡。对此,后人给出了很高的评价:“学至气质变化,方是有功。”[5]694“自孟子言性善,而荀卿言性恶,扬雄言善恶混,韩文公言三品。及至横渠,分为天地之性、气质之性,然后诸子之说始定。”[5]694可见,后之学者对张载人性理论价值的认可。也可看出,它对后来学术影响之大。
四
张载关于人性的学说,在前人的基础上,进行了大胆的创新,对解决当时理学中遇到的某些问题,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发挥了积极的影响。与此同时,它也很难摆脱自身的局限性。
(一)从“至善”到“有善有恶”
在张载的两种气中,未聚无形的“太虚之气”,是“气之本体”,是万物之本体;太虚“感而生”之气有阴阳之变化,形成万物。前者是“至静无感”、“湛一”的,也是至清、至善的;后者有阴阳之变化,有清有浊,有善有恶。那么,至清、至善的“太虚之气”怎么会生出有清浊、善恶之别的阴阳之气呢?由此,也引出另一个问题:如果太虚之气不能生出清浊相混的阴阳之气,那人又怎能禀得此气而形成善恶混的气质之性?
(二)气质之性:先天抑或后天
气质之性是不是人天生就具有的?他言“形而后有气质之性,善反之则天地之性存焉”。这就表明,气质之性是人有了形体之时就产生的。既然如此,它也是人生来就具有的。若它是人先天固有的属性,那么它就很难变。但是,他认为气质之恶是能够改变的。并且,由气质之恶向天性之善的转变,不仅仅是一个量变的过程,更是一个经历了质的蜕变和境界升华的过程。如此,就不能视其为先天的“定分”。因为,若一事物能够发生彻底的质变,就很难说其性质是先天就被决定的。所以,在张载的语境中,人性便存在着内在的紧张:气质之性既是先天的,又不是先天的。
(三)气质之性反归天地之性的困境
如果气质之性是道德属性,是先天的,那么这种先天的道德属性是有善有恶的。同时他也认为,人性的最终本原是至清至善的天地之性。于是,人性便有两个来源,一个是至善的,一个为有善有恶的。问题由此而来:其一,如前所言,至善的天地之性,如何能生出有善有恶的气质之性?其二,说人性的来源既是至善的,又是有善有恶的,这本身就是相互抵牾的,虽然两个来源的性质、地位并不一样。
有的学者倾向于认为,气质之性是人的自然生理属性。这样说,似乎更能表明恶来自“攻取之欲”,而非道德本性为恶。如牟宗三先生就认为:“气质之性,依横渠说此词之意,是就人的气质之偏或杂,即气质之特殊性,而说一种性。在中国思想传统中,自‘生之谓性’一路下来而说的气性、才性之类,都是说的这种性,宋儒即综括之于气质之性。西方所说的人性(人的自然)亦即是这种性。康德所说之性脾、性好、性向、人性之特殊构造、人之特殊的自然特征等,亦是指的这种性。但这种性实在是形而下的,实只是心理、生理、生物三串现象之结聚。”[3]435
也有学者持这种观点,认为气质之性是生理的性:“这种本性是和他的生理条件、身体特点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张载把这种具体的每个人的本性叫做气质之性。”[14]217这种自然属性,也是张载所言的“攻取之性”:“湛一,气之本;攻取,气之欲。口腹于饮食,鼻舌于臭味,皆攻取之性也。”[1]22如果说气质之性是一种自然属性,也意味着它是人的生理属性,并不具有先天的道德属性,那么,它何来善恶相混的特质?又如何能与道德属性的天地之性牵上必然的联系?
还有的学者认为:“张载思想中的气质之性主要是指性格而言,而不是指决定欲望的自然属性。”[2]53—54气质之性即使是主指性格,也未必能与道德属性的天地之性产生直接的关联。如,有性格刚毅的人,也有性格柔和的人;有天生性急之人,也有天生性缓的人。但并不能说,刚毅的人就是善的,柔和的人就是恶的;性急之人就善,性缓之人就不善。反之亦然。改变“人之刚柔、缓急、有才与不才”等性质,就能反归善性?即使调控气质之性,那也是自然限度的改变,并非道德性质的转移。比如,性格太刚毅之人,可以柔和来调之,这也只是自然生理属性的改变,与道德善恶的变迁没有直接关联。
也许现实中的确存在着这样的现象:性格刚毅的人可能道德德性很好——正直,敢于扬善惩恶;性格柔和的人可能不正直,奸诈。但是,并不是所有刚毅的人都正直,也不是所有柔和的人都奸诈。因为从根本处言,刚毅与善、柔和与恶等无必然的逻辑联系。
或许有人会说,气质之性是道德属性与自然属性相混的。此部分第一段已讲,道德属性不能为恶,若为恶,便有矛盾。那只有自然属性为恶。但自然属性本身并无善恶,只有当其被某种力量所利用,与某种对象发生是否符合一定法度的关系时,才能产生道德的善恶问题。如,人有智愚,但其本身并无善恶可言。只有当它们被不正当地运用时,才能产生恶。故不能直接言,自然属性的强弱就是善恶,改变自然属性的“刚柔、缓急、有才与不才”就一定能与道德的善发生必然的联系。
所以,无论气质之性是道德属性,还是自然属性,还是道德属性和自然属性相混的,在理论上,想要说明,变化气质之性,就能反归至善的天地之性,是有一定困难的。
张载力图运用其成性理论从本原的向度来深层解答人性善恶难题。此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诠释了善恶的生成与互动问题。毋庸置疑,在古代的哲学和伦理学视域中,它取得了巨大的创新和突破,价值自不可小视。同时,其理论本身也面临着一些不可回避的难题。
[1]张载.张载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8.
[2]陈来.宋明理学[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3]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上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4]王夫之.张子正蒙注[M].北京:中华书局,1975.
[5]黄宗羲.宋元学案:第1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6.
[6]王文锦.礼记译解:下册[M].北京:中华书局,2001.
[7]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60.
[8]苏舆.春秋繁露义证[M].北京:中华书局,1992.
[9]韩愈.原性[C]//全唐文新编:第10册.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
[10]王夫之.尚书引义[M].北京:中华书局,1962.
[11]戴震.孟子字义疏证[M].北京:中华书局,1961.
[12]汪荣宝.法言义疏:上[M].北京:中华书局,1987.
[13]李翱.复性书[C]//全唐文新编:第11册.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
[14]任继愈.中国哲学史:第3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责任编辑张家鹿]
B82-09
A
1000-2359(2011)05-0015-05
金银润(1978—),男,湖北鄂州人,北京师范大学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哲学与社会学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伦理学史的研究。
2011-06-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