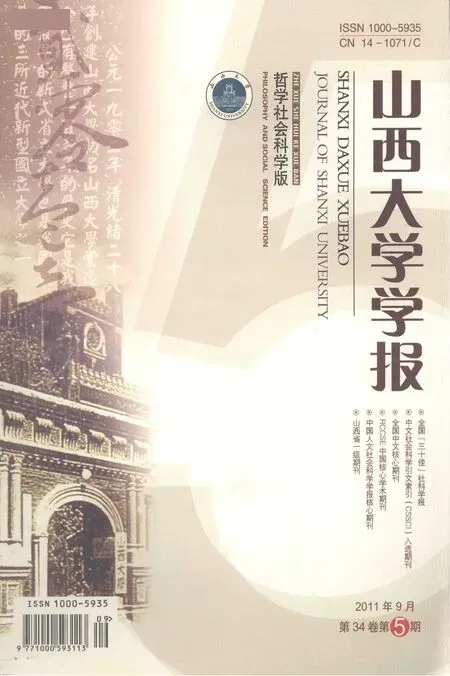从解释学视角看辩证法在中国的语境化(对话)——有感于读《中国辩证法》及其他
2011-04-12桂起权柳海涛
桂起权,柳海涛
(1.武汉大学 哲学学院,湖北武汉 430072;2.重庆大学 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重庆 400030)
从解释学视角看辩证法在中国的语境化(对话)
——有感于读《中国辩证法》及其他
桂起权1,柳海涛2
(1.武汉大学 哲学学院,湖北武汉 430072;2.重庆大学 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重庆 400030)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逐步中国化的过程,是哲学意义的再生产、再创作、再阐释过程。瞿秋白、李达、艾思奇等人起了重要的中介作用,最终在毛泽东那里才达到成熟形态。在语言转换过程中,汉语负载着提供汉字特有的意象簇的丰富类比关系,承载着中国人的世界观和思维模式。汉文字所特有的联想机制和汉文化独特的“阴阳、通变”风格思维模式发挥作用。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文本与作为解读者的中国人特有思维模式之间实现一种“视界融合”。毛泽东的辩证法的中国特色比瞿秋白和艾思奇更为强烈,更为鲜明,也更为娴熟。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中国化;解释学视角;汉文化独特的思维模式;毛泽东
柳:桂老师,您是在科学哲学队伍中有很深“辩证法情结”的学者,这并不多见,而我则是马克思主义教员队伍中的一个新兵。我俩上次讨论了如何《以更加开放的心态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1],表明了我俩对形态各异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积极成分的肯定。今天,就接着讨论辩证法在中国语境化的过程吧。我觉得,从田辰山的《中国辩证法》[2]13一书谈起,更容易展开思路。
桂:我也有同感。田辰山在夏威夷大学跟随安乐哲教授做“东西方文化、哲学的比较研究”,他对中西方差异有切肤之感,这是国内学者很难感受到的。这种相互对比的视角特别好,它能够使人们加深对“中国辩证法”的独特性的理解,并且能够触发对马克思主义如何在中国内在化的历史进程的一种微妙的感悟。那么,今天还是请您先谈谈阅读心得吧。
一 从东西方文化比较研究的视角看
柳:好的。田辰山于1980年代初到美国求学,每每发现,在中国所学西方术语含义与英语对应词的原意其实相去甚远,比如“Dialectics”一词,在苏格拉底、柏拉图那里,更多包含“对话”、“论辩”的含义,相比较,中国人所说的“辩证法”则更多具有“相反相成”的含义等。那么,中国人心目中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又如何呢?正在疑虑之际,两位比较哲学家出现了,于是他就拜安乐哲教授为师,而郝大维教授则成为其课程老师。他终于弄明白了中西方思想传统存在结构性差异——两种宇宙观、思维方式乃至两种语言结构的差别。西方人心灵深处——超绝主宰体的宇宙、两极决然对立、单向因果性思维结构;东方人心灵深处——道和万物的自然世界、通变式互系性思维结构。麻烦在于,这些理念好像“文化基因”那样潜移默化地几乎渗透到民族的潜意识中了,各自反而感觉不到。
桂:说得对!换句话说,一些根本性的理念是渗透到罗蒂所说的“文化共同体”、“语言共同体”的“集体无意识”(荣格语)中去了,在自觉意识层次上往往显示不出来。
柳:田辰山发现,一般西方学者的根本错误在于,把中国语境下的“辩证法”与欧洲语境下的“Dialectics”不假思索地视为完全同一概念,忽视其间结构性的差异。
桂:是啊,中国学者何尝不是这样,不知不觉地会把两者简单地画等号。既然中国人所理解的“马克思的辩证法”与作为欧洲文化遗产的“马克思的辩证法”,实际上在内涵和外延上都有差别。于是,问题来了:“中国式的辩证法究竟是什么?”
柳:田辰山的研究结果是:(1)中国式的辩证法,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现了一种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清晰的、有鲜明特色的思想风格;(2)它从中国哲学传统中汲取了丰厚的营养;(3)有意思的是,它体现在瞿秋白、李达、艾思奇和毛泽东等人的作品之中,并且反映出中国古代哲学线索的强大影响;(4)虽然苏俄标准教程中的“马克思主义”(桂插话:原先,田辰山把“苏联马克思主义”说成“西方马克思主义”,那是不确切的),也是根植于恩格斯的思想,然而他们的解读与中国人的解读模式具有相异的特征。
桂:说起中国式的辩证法,田辰山喜欢概括为“通变式互系性思维”,而我更喜欢采用“阴阳(格式的)辩证法”这个更通俗的说法。这里我联想起一件事,有一位加拿大记者路易斯·麦克劳德在《摄影师在中国》(1972年2月)一文中说:“中国人崇拜马克思和列宁,他们在几千年以前就以阴和阳的格式懂得了辩证法。”美国易经学会会长钟启禄在《易经·黑格尔·休姆及佛学中的辩证与因果概念》一文中说:“易经这部古典,在方法论上,是体用辩证逻辑。”[3]
柳:为了追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及其与中国版的差别,田辰山是这样展开自己的思路的:首先,对中国独特的宇宙观的若干重要特征进行分析。通过对《易经》的考查,力图表明“通变”思维=中国哲人的一种炉火纯青的思维方式。接着分析马克思主义东渐中国的历史背景。分析西方思想借道日本而传入中国,“通变”因素被包含于这一解读辩证法最初阶段的情况。再接下来分析“辩证法”、“唯物论”进入中国后,瞿秋白、艾思奇等前卫知识分子的回应。到最后,考察中国式的辩证法在毛泽东思想中的成熟,看看辩证法如何呈现一种特有的中国形式。
桂:比较哲学家郝大维、安乐哲在《通过孔子而思》(1987)一书中概括出中国传统哲学有三个特点:(1)一个内在性宇宙;(2)概念偶对性;(3)把传统作为阐释的语境。儒家对事物内部关系的“偶对两分性”,其核心就是对宇宙的情景化解释。田辰山作出推广并且认为,在中国人建构和阐释“辩证唯物主义”的过程中,传统“通变”式的哲学思维起了重要作用,它为中国理解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提供了概念框架,在其中,“阴-阳模式”关于同一事物两个基本方面相反相成的作用,构成一切变化发生的动力来源。而“辩证唯物主义”这个词,则是苏俄马克思主义者在阐释恩格斯《反杜林论》时所创造的(普列汉诺夫,1891,1908;列宁,1908)。
柳:根据成中英教授的分析,作为反衬,与中国式通变思维模式不同,主流的、典型的西方思维模式是“单线因果性思维”:(1)分隔性原理:物质=互相分隔的实体。(2)外部性原理:由因至果的法则为外部性支配法则。(3)外部动力源原理。追溯终极原因结果会得到一个“不被推动的动者”。[2]73
桂:西方的辩证法版本在输入中国时,也就是与中国人建立在“道”、“易”、“阴阳”和“通变”等概念的互系思维方式进行对话之时,就必然经历一个解释学的重新阐释过程。以我之见,可以采用伽达默尔的观点,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思维互为文本与解读者。换句话说,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中国化,应当看做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原始文本与中国解读者所带有的中国传统思维眼光两者之间的“视界融合”的自然结果。
二 “Dialectics”的传入并被释译为“辩证法”
柳:清朝末年,梁启超使用汉语的有、无、成、则、象等词对西方哲学进行解读,一旦西方术语被译成汉语,这些汉语用词同时带进了中国人特定的宇宙观和思维方式。留日学者汪荣宝、叶澜所合编的辞书《新尔雅》(1903年,上海明权社),则更具有标志性意味。它表明用日文汉字翻译的西方术语,已经密集地出现在中国文人学者的著作之中。“Dialectics”一词被释译为“辩证法”等等,不免都要带上其古汉语相关的意义。
桂:我注意到,蔡元培先生可以说是黑格尔辩证法在我国最早的传播者,他的译文是当时对黑格尔辩证法最系统的介绍。
柳:蔡元培的译文意味着一种再创作,哲学意义的再生产。日文译文借用汉字“正题”、“反题”和“摄论”(今译“合题”),来翻译 thesis,antithesis和synthesis这三个概念,用以解读黑格尔的正、反、合思想,这已经是一种创造性的建构。然而,它们难以承载黑格尔的三段式,因为中国思想传统中不存在“绝对精神”自我运动的理念。蔡元培则更进了一步,他有一段译文用“太极”来描述黑格尔的“合题”。黑格尔的正、反、合,几乎被解释为,中国人所熟悉的“阴-阳”之间永无休止的对立、结合而达到“无极”,从而实现最大和谐的过程。[2]77看来,在这黑格尔辩证法的传播过程中,分析哲学家奎因所说的“翻译的不确定性”开始起作用了。
桂:值得赞扬的是,田辰山已经认识到,作为汉语文章,汉字所特有的联想机制和汉文化独特的思维模式发挥作用。中国习惯模式=“阴阳、通变”风格的思维方式,而西方主流模式=先验力量支配的宇宙论和严格秩序;而黑格尔哲学的焦点=把事物的必然性归因于一个先验模式,其辩证法的拓展源于西方柏拉图传统。我认为,蔡元培的译文所达成的,可以看作黑格尔辩证法的文本与中国传统思维模式的一种“视界融合”。对解释学的“视界融合”还可以有更深一层次的理解。我的一个关门弟子当时是英语系副教授,她的博士论文所做的就是,用戴维森的语言哲学(尤其是戴维森的“三角测量”理论)去解读翻译理论。[4]
柳:请您用最简洁的语言说说其中的要点吧。
桂:按照戴维森的看法:我们、他人、世界这三者之间存在因果互动关系。所谓三角测量是指:言说者、解释者与世界的对象原事件这三者的关系,这是采用地质测量作隐喻,好像我们经常在马路上看到过的,测量员用两个望远镜从不同角度去测定同一个目标客体那样。语言交流=语言使用者、其他使用者及其共享世界的对象或事件之间的三角测量。翻译=跨语言文化的交流,有作者、文本、译者这些因素共同参与并且相互作用,显然构成三角测量模式。读者对于文本原作者意图的把握,必须还原到相应的社会历史情景以及作者对此的内心体验。存在着(1)三类主体:作者、译者、读者。(2)三对主客二元关系:作者-文本、译者-文本、读者-文本。(3)三种理论(各占有部分真理):文本中心论——意义由“文本”(如《红楼梦》)本身所完全决定;作者中心论——意义由作者(如曹雪芹)的意图决定;读者中心论——意义由解读者的理解所决定(如红学家俞平伯或政治家毛泽东有全然不同的解读)。整体论式的全面考虑应当是:只有对这互动的三个方面进行整合,才能达到最佳的理解和理想的效果。
柳:这么说来,对于辩证法的中国化过程,文本意义的转译、理解、再解释的过程,也应当采用戴维森模式,即运用三角测量式的语言交流模式,即作者、文本、解读者三者互动沟通的模式来理解。
桂:完全正确,不过在细节上你可以回头再去进一步专门研究它。在眼前的问题上,田辰山的结论是,黑格尔的“Dialectics”经由蔡元培的汉语再生产,被转化成了我们所能理解的“辩证法”。经过这种再哲学化,“Dialectics”变成了一种新程序、新境域、新焦点和新视野。换句话说,从解释学观点看,蔡元培的这一翻译,给出了一条线索,就是黑格尔的辩证法与中国人的“阴阳、通变”思维彼此之间是可以实现“视界融合”的。
柳:不过,差异还是客观存在的。
桂:那当然。我记得1994年我们武汉大学哲学系所举办的“哲学茶座”(沙龙)。邓晓芒教授在解读黑格尔辩证法时说,从本来意义上说,“矛盾”一词,在中国人心目中是真刀真枪的“矛和盾”,具有本体论的意味;然而在德文中,Widerspruch则是“相反的话语”,因为从构词法上讲,Wider-是相反,-spruch是语言、话语,它是属于语言层次的并且具有认识论的意味。邓晓芒认为,黑格尔辩证法的本质在于“自否定”,可以归于一,而“二”(对立面)则是从“一”(统一体)内部通过自否定产生出来的;相比之下,在中国辩证法中,“二”(阴阳)是终极性的,不可归约的,如此等等。[5]因此依我看,在蔡元培的译文出现的与黑格尔辩证法相左的差异,并不令人惊异。相反,这是随着汉字的使用而即刻自然发生的事情。语言是思想的载体,特别重要的是,汉语负载着提供汉字特有的意象簇的丰富类比关系,承载着中国人的世界观和思维模式。于是,蔡元培在解读黑格尔辩证法的过程中,伽达默尔所说的“视界融合”就发生了:它直接发生于用汉字语义簇或汉字搭配,对黑格尔原使用语言的哲学概念,进行转译和再阐释的过程之中,并且随着汉语句式结构和语法的使用而得到强化。
柳:接下来,让我们更深入地讨论中国版本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形成。
三 中国版本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形成之初:瞿秋白
桂:人们发现,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如果以中国特色的语汇来表达,它与中国传统的“阴阳、通变”思想之间,至少在表象层次上是可能兼容的。这就像蔡元培在解读黑格尔时所启示的那样。于是,通过中国进步知识分子几代人的努力,“最终的结果是,崭新的西方语汇融会在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之中,产生出一个中国版本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2]81
柳:应当说,中国对马克思主义的认真研究与传播,始于1917年十月革命之后,正所谓“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我想,给大家印象最深的应当是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在《新青年》上的文章,不过他们的重点是放在唯物史观与马克思经济学说。
桂:瞿秋白可说是在中国系统讲解“辩证唯物主义”的第一人,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早期传播作出了巨大贡献。鉴于当时历史背景,他主要依据俄文著作,包括普列汉诺夫的著作,是受苏联马克思主义的强烈影响。1923-1924年间,在上海,用自编教材讲授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内容,在他充满创见的演讲中,渗透着他博大精深的智慧。为了便于理解,他大量使用古汉语词汇。在瞿秋白的“辩证唯物主义”讲演里,可以看到的是与中国传统的“阴阳、通变”哲学类似的思想。在这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思想的对话中,一个马克思主义非常中国化的版本开始发展起来。[2]85
柳:看来瞿秋白对“西马”,也就是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各派之争,全然不感兴趣。可是我们年轻人对“西马”具有浓厚的兴趣
桂:那是因为时代背景不同。“西马”不能解决那时中国革命的当务之急。
柳:在我印象中,瞿秋白读的中国古书特别多,文学功底好,对哲学著作情有独钟。像普列汉诺夫一样,文学艺术方面修养很高,才华横溢。显然,他是通过中国人的经验、中国人的文化传统和中国人的眼光来思考马克思主义的。
桂:是啊,瞿秋白在进行研究的一开始,就有意无意地阐述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十分中国化的版本。他讨论辩证唯物主义时所用的很多重要术语,皆诉诸“阴阳、通变”这一互系性思维模式。我对田辰山特别欣赏的是,他分析“中国化”的转换机制极有特色。他指出,与瞿秋白的论说息息相关的汉语语汇其实可以看作是一个相系相通的组合机制,它显示类比关系,也同时按含义的性质或特点,而产生出汉字特有的意象簇或观念簇的联想。中国古代思想家正是在相反相成的作用观念上,在这些互系性偶对物事的观念上,来认识变化的本质的。[2]89他还说过相当精彩的一句话:中国人的通变、相反相成的观念模式,渗透在哲学家和普通人平日的思维和生活中,并且结晶于格言名句之中。
柳:我觉得,瞿秋白对辩证法的理解已经带有中国古代“以阴阳为格式”的辩证法的明显的印记,并对后人富有启发性。瞿秋白相信,辩证唯物主义的实质就在于“正反相成,矛盾互变”,他说:“物的矛盾及事的互变便是最根本的原理”。他所频繁使用的用语有,互变法唯物论、正反相成、互变律、互动律、矛盾性等等。当 Контрадикция(Contradiction)被翻译为“矛盾”时,也就嵌入了中国思维模式(如阴阳、刚柔等一系列偶对范畴)。瞿秋白所采用的现代辩证唯物主义话语,反映了中国传统中的将一切变化解释为阴阳的通变的思想。[2]90瞿秋白把“辩证唯物主义”解释为这样一种世界观,宇宙间包括社会中一切都在变易和互动之中,天下没有固定的形态,一切都是历程。瞿秋白提出:“无一处不是矛盾”,这与阴阳偶对模式相吻合。[2]112
桂:瞿秋白对“矛盾”概念的重视,使人不禁联想起毛泽东《矛盾论》中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的名句。瞿秋白用“正反相成,矛盾互变”来解读辩证唯物主义,可是说已经初步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中国版本的最有特色性的方面。毛泽东在《矛盾论》中说过:“中国人常说‘相反相成’。就是说相反的东西具有同一性。这句话是辩证法的,是违背形而上学的。”[6]308-309这说明,瞿秋白已经敏锐地接触到了按中国传统思维模式来理解辩证法的最主要之点。
四 中国辩证法通俗化运动的杰出代表:艾思奇
柳:接下来,也许两个最重要人物应当是艾思奇和李达了吧。
桂:是啊。现在,我们的中心议题是:艾思奇是掌握用白话文体来解释复杂哲学问题技能的高手,他在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语境中通俗化的历程中发挥了十分巨大的作用。艾思奇是1927-1932年间在日本留学的。1932年回到上海。创办《正路》月刊,1934年11月又协助李公朴创办《读书生活》半月刊,并且负责编辑“哲学讲话”专栏。艾思奇下决心通过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生动活泼方式来讲解哲学,把唯物辩证法变为人们晓畅明白的道理。
柳:我就曾经读过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真是有趣非凡。印象最深的是,“雷峰塔是怎样倒的?”,答案是:老百姓一块一块地抽掉砖头,日长时久,“量变到质变”,大风一吹就倒了。用现在说法,还得加上“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当然,现在这些都已经成为妇孺皆知的常识了。但不能忘记,马克思、恩格斯深奥的哲学思想在刚刚传播到中国来的时候,理解起来有多么困难啊!
桂:你这么说,就使我联想起一件有趣的事:在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的延安版本中,我发现原先竟有过这样一段话,说的是,让十七八岁的毛孩子读《反杜林论》是读不懂的。但在《毛泽东选集》正式版本中它被删除掉了,因为对现在的大学生读起来应当没有太大问题。
柳:真是闻所未闻啊!显然,现在的青年越来越聪明,能理解更深更新的知识,毕竟时代不同了嘛。
桂:艾思奇确实不简单,他所做成的事,绝非一般人所能做到!在这个问题上,哲学像自然科学一样,对于一个深奥的道理,如果没有透彻的理解,那么怎么可能作出通俗而不失真的解释呢?!精辟而微妙的深入浅出解释,是只有大师级人物才能做出来的!当年艾思奇的论著确实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成为唯物辩证法在中国传播运动的重要里程碑。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化和中国化的杰出推动者,艾思奇表现出极大的智慧,我至今仍保持对他的深深的敬意。可惜,这样的人物如凤毛麟角,恐怕已经难以寻觅了!
柳:我知道,艾思奇是1937年10月到延安,实际上成为毛泽东身边最重要的哲学理论家和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家。此前不久,毛泽东认真阅读艾思奇《哲学与生活》(论文集),在读书笔记中成段摘录其观点并且加以点评,表明在其哲学思想上的强烈共鸣!我还知道,翻译是艾思奇将马哲通俗化的另一项重要工作,如《马恩书信选集》(1934)等等。
桂:但是,也许你不知道,新中国成立后艾思奇著有《辩证唯物主义讲课提纲》(1957),1958年的修订版取名为《辩证唯物主义纲要》。它为日后辩证唯物主义的中国化“范式”奠定了基础,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它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教科书。这是一部有国际影响力的著作,我至今仍保存着它的“俄文译本”呢。苏俄学者非常重视艾思奇这一位中共主要理论家。
柳:我觉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过程,也是一个解释学所关注的阐释过程。我很喜欢解释学和语言哲学。在中国哲学史上,朱熹将儒家精义通俗化为四书经典,就是一种语言转换过程,一种再解释过程,它成为实现哲学经典的通俗化工程的一个典范。[2]117同样道理,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过程中,很多西方概念关键词的汉化,都曾经过语言转换的翻译历程,其结果是,西方术语变成了汉语词汇,而这些已被汉化的词汇,则来源于中国环境特有的具体意象和事物的特征,也就是在前面讨论蔡元培时如你所说的“汉语负载着提供汉字特有的意象簇的丰富类比关系,承载着中国人的世界观和思维模式”。
桂:说得对!在艾思奇的通俗化过程中,原始的西方概念通过在中国语境下的更有具体意象的事物和更为新鲜、特定的历史环境,得到了创造性的再解释。这样,唯物辩证法就获得了丰富的中国意义。
柳:艾思奇与瞿秋白一样,精通外语并且懂得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基本内涵。从资料来源上来看,艾思奇的唯物辩证法思想,也是源于恩格斯和俄文文献。但是他的解读则采取了与俄国人迥然不同的另外一种路径,这是通过中国革命的经验和中国文化的视角来解读外语文献的。经过艾思奇运用中国哲学用语的再阐释,汉字所特有的联想机制和汉文化独特的“阴阳、通变”风格思维模式发挥了主导作用。[2]117-118
桂:艾思奇的“唯物辩证法”,在表现形式上,与恩格斯和苏联马克思主义都有不同。他主张,运用马克思主义来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并要熟悉中国传统思想。讲到辩证唯物论的实际应用,他主张要对中国固有哲学进行研究,对中国自己的过去哲学史上的唯物论和辩证法的因素(或遗产)加以发扬。比如老子《道德经》、墨家的《墨经》等。
柳:请你把艾思奇所做的阐释的独特之处,再说得更明白一些。
桂:艾思奇并没有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物质主义、还原论简单地等同起来。他过滤掉了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内部各派之争(包括欧洲哲学史上的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他属于苏联马克思主义的“多数派”(布尔什维克)这一边,深受恩格斯《反杜林论》的影响。艾思奇完全赞同恩格斯关于自然与社会的一切事物都是辩证的、相互联系的观点,不过经过他的解读,就与中国传统哲学的“阴阳、通变”思想相一致,换句话说,他把恩格斯的“辩证”更当成是那种根植于阴阳式类比偶对范畴的意思。诸如有无相生,难易相成,“一阴一阳之谓道”。[2]122我觉得最有趣的是,他用中国人所熟悉的“天晓得”态度来解读“不可知论”。艾思奇讨论辩证法三定律的次序与恩格斯也有所不同,对立统一变成了第一条。原因在于,他是用中国哲学传统的“通变”、“阴阳”模式来解读辩证法的,“相反相成”自然就成为辩证法的核心。毛泽东也十分赞赏这一点。
五 中国辩证法成熟形态的缔造者:毛泽东
柳:毛泽东思想无疑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成熟形态。我想,也许我俩可以从比较哲学与解释学的特定视角作出自己的解读。
桂:说得不错,毛泽东使中国传统辩证思想发展到现代思想形态,也就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中国版”。与众不同的是,毛泽东不仅是一种新哲学理论的主创者,而且是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伟大实践者。
柳:一般人的困惑在于,如果仅仅从信息渠道来讲,毛泽东的哲学资料大部分源于俄文文献。人们很可能以为,其观点想必会受到“苏联马克思主义”严重影响。为什么事实情况恰恰相反呢?
桂:毛泽东对唯物辩证法的解读,是大量使用中国典故和古汉语用语的。他所认同的唯物辩证法的许多方面,都借助于中国传统的阴阳、通变思维的转换和“视界融合”而实现的。田辰山说得对,由于毛泽东对中国历史更为精通又在哲学上更能高瞻远瞩,因此毛泽东的辩证法的中国特色比瞿秋白和艾思奇更为强烈,更为鲜明,也更为娴熟。
柳:这样的解释是非常合乎情理的。但是,我们决不满足于田辰山对毛泽东的解读,我们要走得更远更远。
桂:这是毫无疑问的。
柳:我注意到,毛泽东在成年前所学主要是“四书五经”,他尤其对中国传统辩证思想有浓厚的兴趣,深谙从孔孟、老庄、朱熹直到王夫之的古代辩证法,深受古代思想熏陶,从而形成了自己早年的辩证思想还将它运用于写作之中。1914-1918年在湖南第一师范期间,把《黑格尔一元论哲学》(马君武译)作为重要的研究著作。有趣的是,即使在他的《体育之研究》(1919)之中,也包含明显的朴素辩证法的因素。
桂:在延安时期,毛泽东更多阅读苏俄哲学书籍(译著)。1932年读过德布林的《欧洲哲学史》。1936年,苏联开展批判德布林学派的思想运动,在相关文献中大量援引了能够刻画列宁辩证法思想的主要特征的语录(来自刚出版的列宁《哲学笔记》),它们被及时翻译为中文,毛泽东有机会阅读到它。1936年到1937年间,毛泽东还反复阅读希洛可夫、爱森堡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李达等译,1935年版),并做了详细批注。看来,他是把希洛可夫关于主要矛盾的观点,看作进一步研究的一个较高的起点。这些思想也反映在延安讲稿《辩证唯物论讲授提纲》中,并且构成了《矛盾论》《实践论》的雏形。[2]131-132
柳:可是,这样的话,也许有人会提出这样的疑问,人们究竟应当如何看待希洛可夫的启示以及毛泽东的独创性?
桂:希洛可夫的书对毛泽东的思绪的作用只能算作一个重要的触发因子,启动了多米诺骨牌,让毛泽东灵感突发,像泉水一样涌现出来。然而,毛泽东《矛盾论》中的系统化观点则高超得多,毕竟他开创性地确立了矛盾辩证法的一种全新的范式。
柳:为什么这样说呢?您是如何看待矛盾论的?
桂:这里我并不想全面评价《矛盾论》。你可能从《矛盾论》主张“矛盾即是事物,即是过程,也即是思想”的角度来看,辩证法、认识论与逻辑实际上是三位一体的。不过,本人进入辩证逻辑学术圈已经好几十年了,也许我可以从辩证逻辑视角谈些感想:毛泽东的《矛盾论》[6]274-312和《论持久战》具有直接关联性,都应当看做是极为重要的辩证逻辑著作。尤其引人注意的是,毛泽东本人也肯定了《矛盾论》的辩证逻辑性质。
柳:此话怎讲?
桂:最直接的证据是,毛泽东在1958年9月2日写的《对工业类文件的意见》中说:“所谓不大懂辩证逻辑,就工业来说,就是不大懂工业中的对立统一,内部联系,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的分别。”[7]可见,在毛泽东心目中的辩证逻辑,其主要内容不外乎《矛盾论》所讨论的。毛泽东在延安哲学讲稿《辩证法唯物论提纲》中曾反复强调,辩证法、逻辑、认识论三者是同一的。在他看来,作为逻辑的辩证法就是辩证逻辑(当时他采取日文译名“辩证法论理学”)。
柳:我知道毛泽东一直很关心逻辑,可是还真不知道,毛泽东更关注辩证逻辑。
桂:我还没有说完呢!进一步说,本人强烈地感觉到,毛泽东晚年关于“分析与综合”的两次哲学讲话(1964年8月18日和1965年12月21日),[8]292-293,129-131这是货真价实的辩证逻辑的讲话,可以说是他对列宁《哲学笔记》中“分析与综合”思想的全新的解读,是对辩证逻辑方法极为重要的新贡献。
柳:为什么您会有这么强烈的感觉?
桂:因为在1962年,我曾经认真读过罗森塔尔的《辩证逻辑原理》的中译本(马兵等译)以及莫斯科大学教授阿历克山耶夫的《辩证逻辑》(俄文版)。可是,让我失望的是,罗森塔尔说来说去也只是形式逻辑层次的“部分与整体”的关系,阿历克山耶夫所讨论的只是几何学解题时用的分析法与综合法。很遗憾,苏俄在辩证逻辑方面的这两位权威学者,就“分析与综合”而言,都还未能突破形式逻辑的眼界。然而,读了毛泽东关于“分析与综合”的两次哲学讲话,却有顿开茅塞之感!毛泽东用深入浅出的方式所解释的正是许多哲学家很想讲清楚又未能讲清楚的问题。关键在于,毛泽东深刻地认识到,辩证逻辑意义上的“分析与综合”,所处理的已经不是普通逻辑意义上的“整体与部分”,如今,整体——是综合成“矛盾统一体”的整体;部分——是在矛盾总体中占有各不相同的特定地位的“诸矛盾部分和方面”。
柳:我想,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人,几乎没有人不熟悉《矛盾论》中的矛盾分析方法的。只不过各人理解的深度大不相同而已。
桂:今天,从逻辑、科学方法论的角度讲,博弈论已经得到科学界的公认。博弈论是一种研究冲突局势下最优策略的形式理论,它为分析竞争与协同之间的矛盾提供了一种普遍的可操作的结构模式。它的优点就在于能用简明而严谨的形式结构来刻画相对复杂的逻辑思想。我发现,从某种意义上说,毛泽东的矛盾分析法可说是“不用形式语言表述的博弈论”,它对分析矛盾特殊性提供了清晰的启发式程序,像人工智能研究的启发式程序那样,具有可操作性,当然它不是机械的、固定不变的算法。这是希洛可夫们所望尘莫及的。整本《矛盾论》以及《论持久战》所讨论的无非是这种“矛盾分析法”,也就是“分析与综合”相结合的辩证逻辑方法。毛泽东的那两次哲学讲话,对《矛盾论》和《论持久战》的这一深刻的辩证逻辑内涵则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8]292
柳:在讨论“分析与综合”时,当然离不开《矛盾论》的矛盾分析法,可是为什么又要和《论持久战》联系起来考察?
桂:毛泽东关于“分析与综合”的两次讲话,表面上看,举例是关于国共两党的矛盾分析,而不是抗战时期中日两国的细致矛盾分析,但是明眼人一眼就可以看出,基本思路与分析方法与《论持久战》如出一辙。《论持久战》可以说是用军事辩证法语言所表述的《矛盾论》。我记得1964年时,当时有一位西德的评论家,对毛泽东的军事辩证法和辩证逻辑思想评价甚高,列举、展开了《论持久战》中一系列军事辩证法的对偶范畴,并将毛泽东恰当定位于“军事战略家”。
柳:您的观点对我有很大启发。您不仅用解释学观点,而且用辩证逻辑观点来解读毛泽东的辩证法,确实很有新意。我忽然想起,当年徐寅生有个关于《如何打好乒乓球》的讲话,他是从国家队教练的高度具体分析了打好乒乓球的战略战术。当时我感到困惑的是,毛泽东批示说,全文充满辩证唯物论,是小将向身经百战的老帅们挑战了!现在,我明白了,原来毛泽东的头脑中所装备的是《孙子兵法》《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等,他作为军事战略家是从军事辩证法的高度来解读打乒乓球,这样才会使得徐寅生的文本显示出作者本人未能充分意识到的全新的意义。是不是这样呢?
桂:说得好!这是实践中的辩证法在毛泽东那里得到提升的一个典型案例。辩证法的中国化进程并没有终止。毛泽东之后,邓小平可说是注重应用、讲究实效的辩证法大师。
柳:在我印象中,你曾经解读过邓小平“南巡”讲话中的辩证法思想,并且概括出邓小平的“政治-经济不等式”和“两重性逻辑”。不过,我记不得“两重性逻辑”的确切表述了。
桂:所谓“两重性逻辑”的原则是指,把表象上应该互相排斥的两个对立的原则或概念联结起来,因为它们实际上是不可分割的和对于理解同一实在是缺一不可的。邓小平高瞻远瞩,提出“计划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这两个著名不等式,把目标与手段分开,一下子解构了长期禁锢人们思想的两大经济学教条。在实践中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邓小平在这两个政治—经济不等式基础上,借助于两重性逻辑,通过辩证综合产生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概念。这是把“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这两个在表象上似乎应该互相排斥的对立原则或概念联结了起来,整合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名之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就像马克思、恩格斯对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与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所做的艰辛而深刻的批判改造工作那样。这就使得两个深刻的、对立的局部真理整合成一个更深刻、更精辟、更完善的真理。[9][10]
柳:也许,从逻辑观点看,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念,是可以与毛泽东早年的“新民主主义”理念既合理又顺畅对接起来的。
桂:这就有待于理论工作者做进一步的精细研究了。
[1]桂起权,柳海涛.以更加开放的心态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J].河北学刊,2011(3):1 -6.
[2]田辰山.中国辩证法:从《易经》到马克思主义[M].萧延中,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3]钟启禄.易经·黑格尔·休姆及佛学中的辩证与因果概念[M]//刘大钧.大易集成.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300.
[4]方 兴.基于戴维森意义理论的翻译问题研究[D].武汉大学博士论文,2008.
[5]邓晓芒.辩证逻辑本质之我见[J].逻辑与智慧,1994(6):4-8.
[6]毛泽东选集:一卷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7:308-309.
[7]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367 -368.
[8]雍 涛.毛泽东哲学的历史发展[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
[9]桂起权.马克思《资本论》的辩证逻辑与邓小平的“两重性逻辑”[M]//《中国经济哲学评论》2006·资本哲学专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399-407.
[10]桂起权.关于邓小平“经济学不等式”的哲学思考——兼谈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逻辑协调性[J].东南大学学报,2006(6):5 -9,126.
(责任编辑 李雪枫)
The Contextualization of Dialectics in China form the Perspective of Hermeneutic(dialogue)——Reactions toChinese Dialecticsand Others
GUI Qi- quan1,LIU Hai- tao2
(1.The School of Philosophy,Wuhan University,Wuhan430072,China;2.The College of Marxism,Chongqing University,Chongqing400030,China)
The Marxist Dialectics’Chinization is a step-by-step reproductive,regenerative,re-creative and reinterpretative process of philosophical meaning,during which QU Qiu - bai,LI Da and AI Si- qi played important medium roles.And it reached maturity through MAO zedong’s work.In the process of linguistic transformation,Chinese characters have offered unique image clusters of the rich analogy relations,carrying the Chinese people’s world view and way of thinking and Chinese character’s unique associational mechanism,and the“Yin Yang,Tong Bian”style of thinking in Chinese culture have taken a key role.The texts from western Marxist dialectics and the unique mode of thinking of Chinese people,who acted as interpretationers,achieved“the fusion of horizons”.The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of MAO’s dialectics are more brilliant,more distinct,and more skilled than Qu Qiu - bai’s and Ai Si- qi’s.
Marxist dialectics;Chinization;perpective of Hermeneutic;unique thinking mode of Chinese culture;MAO Zedong
B024
A
1000-5935(2011)05-0006-08
2011-04-12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经济逻辑研究”(06BZX050);教育部青年基金项目“当代西方心灵哲学中的集体意向性问题研究”(10JYC720026);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CDJRC10010001)
桂起权(1940-),男,浙江宁波人,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科学哲学和自然辩证法研究;
柳海涛(1977-),男,河南南阳人,哲学博士,重庆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讲师,主要从事心灵哲学和社会科学哲学研究。
book=13,ebook=2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