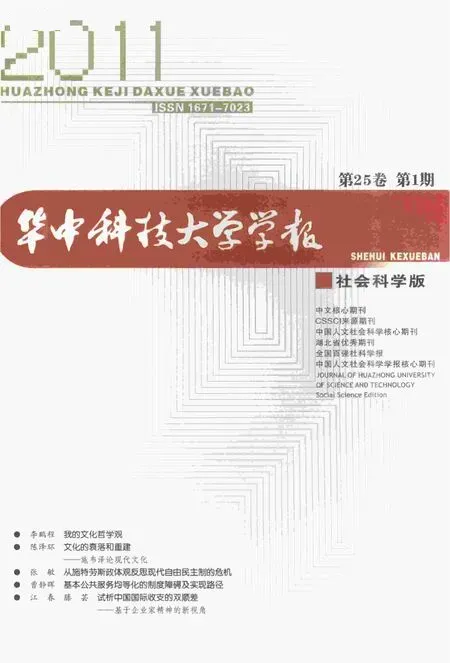农村仪式性人情的功能异化
2011-04-08陈柏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湖北武汉430074
陈柏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湖北武汉 430074
农村仪式性人情的功能异化
陈柏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湖北武汉 430074
仪式性人情在传统村庄社会中有着经济互助和维护社会团结的重要功能。在江汉平原农村,这些功能日渐发生异化,其本质在于名实分离。人情的互助功能正在丧失,越来越多的村民正借人情的互助之名而行聚敛财富之实,人情维护社会团结的功能也日趋弱化。农村仪式性人情的异化,与当前江汉平原的村庄社会变迁密切相关,因为村庄生活越来越缺乏长远预期,人们越来越看重眼前的经济利益,且村庄人际关系日趋离散,村庄中已不存在结构化的制约力量。
仪式性人情;互助;社会团结;功能异化
“人情”有着非常广泛的内涵。在关系层次上,它是指人际交往中的“给予”与“亏欠”。在这种“给予”与“亏欠”机制的作用下,村庄熟人社会被整合成了对内纷争较少、对外团结一致的亲密社群[1]。这种“给予”与“亏欠”机制主要体现在中国农村广泛存在的“行人情”上。“行人情”的场合可以分为两类:“仪式性人情”和“日常性人情”[2]。前者是指仪式性场合的表达性馈赠,后者则是指非仪式性场合的表达性馈赠。这里的“表达性”与“工具性”相对,指人情具有感情表达的性质,受长期互惠机制的约束,而并非达到某一功利目的的手段。当前中国农村正在发生剧烈的变迁,开始摆脱土地束缚的农民,其生活面向日益城市化,人际关系日益理性化。因此,“行人情”也发生了种种变化,“日常性人情”主要表现为大幅度减少[3],“仪式性人情”则发生了种种异化。
目前对人情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本土社会心理学和人类学两个领域。以黄光国、翟学伟等为代表的本土社会心理学家,侧重于从文化意义上理解人情、关系、面子等,进而探究中国人在人际交往中的行为逻辑和心理特征[4][5]。在莫斯看来,互惠是礼物流动的灵魂,礼物的“物”性和“灵”性构成了社会得以可能的必要条件[6]。以阎云翔、杨美惠等为代表的人类学家,沿着莫斯所开创的路子,从“礼物”的社会整合意义出发展开研究,开创了中国的人情研究传统,探讨了人情在中国社会中的作用和意义[7][8]。这些研究有着重要启发作用,构成了展开进一步研究的基础。
然而,本土社会心理学方面的研究较多地从个体之间的关系上来讨论,尤其是个体之间的利益交换关系,一些研究甚至局限于语词和个体生活体验,较为缺乏社会实证,对社会变迁关注不够。人类学方向的研究关注了社会变迁,但其经验研究容易局限于个案村庄,调研范围有限,未能意识到中国的区域性差异。近来,已有一些学者注意到了农村人情现象发生的各种变化[9][10]。笔者所在的研究机构,几年前即开始关注面子、人情等本土社会现象,并将其与转型期农村社会性质和乡村治理联系起来,关注了本土社会现象的区域差异,已有一批成果发表[11][12][13][14][15][16]①陈柏峰:“仪式性人情与村庄经济分层的社会确认”,《广东社会科学》2011年即将刊出。。本文将在这一研究传统下继续深入展开研究。文章将以江汉平原的调研材料为基础,讨论农村“仪式性人情”的功能异化。2005年以来,笔者多次到江汉平原农村调研,如沙洋、洪湖、京山、江陵等县市农村,通过深度访谈获得相关质性材料。在人情现象上,这些农村地区有着很大的共性。
一、人情的经济功能与社会功能
“仪式性人情”主要发生在村民“办事”的场合,包括婚礼、葬礼、盖房、生孩子、上大学、生日等庆典仪式场合。在不同的农村地区,“办事”的场合稍有不同。在这些场合中,与“办事”的主家有社会关系的人要前去“送人情”,这些人可以分为三类:亲戚、庄邻和朋友。在村庄中,“仪式性人情”是一个重要的场合,是一个家庭社会关系的集中展示。对于一个家庭来说,“办事”(发起“仪式性人情”并用酒席招待客人)的场合往往数年才有一次,甚至上十年才有一次。但是,一个家庭去参与别人所办事的场合(“送人情”)一年至少有数次,甚至数十次。参与的次数多少,反映了家庭社会关系的广泛程度,社会关系多的,参与“送人情”的场合自然就多。人情是一个“互惠”的过程,社会关系多,参与“送人情”的场合多,等到自己家庭“办事”时,来“送人情”的客人自然就多。在三种主要的社会关系中,亲戚虽说是由血缘关系确定的,但也有自我选择的空间,因为血缘关系远的亲戚是否在人情上继续走往,取决于人们的选择;庄邻也有可供选择的空间,有的村民在村里人缘关系好,办事时邻居来得就多,反之,来得就少;朋友的多少更是由家庭交往的范围所决定的。
从经济功能的角度看,作为习俗,“人情”是一种互助机制。“送人情”和“收人情”是互惠的,因此从长期来看是平衡的。“人情”的支出和收取实际上类似于储蓄和取款的过程。当别人“办事”时,村民前去送人情,这等于在别人那里储蓄了一小笔钱;日常生活中,村民的社会关系范围内,不断有人办事,因此不断送出的人情,就相当于在不同的地方做小额储蓄。当村民自己“办事”时,他社会关系范围内的村民都会来“回人情”,这等于村民从以前的储蓄对象那里取回了自己的小额存款。这些小额存款积少成多,就可以办大事。办事中收取的人情,来自村民的各种具体社会关系,也就是村民过去在日常生活中不定期存入的,虽然每笔不是很多,但汇集起来却不是小数目。
在传统社会中,“人情”作为一种互助机制是不可或缺的。传统农耕社会的经济条件非常落后,人们的收入来源极为有限,为儿子完婚、安葬老人等“大事”往往要消耗一个家庭十年甚至大半辈子的积蓄,甚至花掉这些积蓄也不够办事。而且,人们也很难将财物专门为办事而积累所有所需。因此,在“办事”的时候往往需要求助于他人,借钱当然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方法,“人情”则是另外一种方法。借助于“人情”,村民收回过去的储蓄,或者向社会关系中的人们广泛进行“小额借贷”,积少成多,渡过难关,办成大事。
在“人情”的互助机制下,人们可以将伴随着生命周期变化而来的办大事的压力,较为均匀地分布到日常生活中去。而“人情”之所以可以成为一种互助机制,原因在于村民的生命周期有所差异。一个年轻的家庭,很可能劳动力多而负担轻,没有为小孩成婚的压力,父母还可以帮助打理,家里不断有收入而支出不多。而另外一个老龄化的家庭,很可能劳动力少而负担重,如家里高龄的老人体弱多病,一旦去世就需要支出一大笔送终费用;年轻的孩子成婚的压力迫在眉睫,这是家庭压力最大的时候。如此一来,第一个家庭在十年之内可能不会办任何大事,没有收取人情的机会,而不断地支出人情;而第二个家庭却可能在较为集中的几年内办理好几场红事和白事,不断地在收取人情。不过,再过十年,这两个家庭的状况可能正好颠倒过来。这样一来,在家庭的生活周期内,当压力较大时,人们可以通过收取人情来分散压力;而当没有压力时,则可以通过“送人情”来帮助其他家庭分担压力;等到家庭的生活周期阶段发生变化,不同家庭的角色也会发生变化。
当客人来“送人情”时,办事的人家需要用酒席招待来客。在不同的地区,招待的餐数从一餐到三天不等,酒席的档次也不太一致。在传统农村社会,酒席比日常生活中的伙食要好一些,这主要是办事的农户为了表示自己的热情。但这种好伙食是有限度的,其成本花费会远远低于客人的人情金额。否则,人情的互助功能就无法体现出来。一般来说,办事的人家对客人的“人情”会有专门的“人情单”记载,这种记载是公开进行的。记载的目的主要是为了避免遗忘。在传统农村社会,送人情和收取人情的时间间隔往往数年甚至十数年,因此以“人情单”的方式保留“储蓄信息”就非常必要。送人情与还人情的时间间隔长,这表明人情的经济互助功能是在人们生活预期较为长远的条件下发生作用的。人们的生活预期长,才会在村民中进行长期的储蓄,才不会想着将已进行的储蓄即刻兑现。这样,人情的经济互助功能才可能实现。
从社会功能的角度看,“人情”是一种维护社会团结的机制。人情对于村庄社会秩序的生产和维护有着重要意义。在村庄社会中,存在亲人、熟人和陌生人三个不同层面的社会关系。在秩序生产上,最重要的是熟人之间的整合。理想状态下,熟人社会内部不但有先赋性的地缘与血缘关系,更重要是每个人与其他人之间都有着“人情”上的“给予”与“亏欠”关系①现实情况与理想状态有所差异。一般来说,南方村庄更加接近理想状态,而北方村庄往往以小亲族为单位,形成了几个“人情圈”,这构成了贺雪峰所说的“农民认同与行动单位”。中部村庄的情形更为复杂,“人情圈”相对较为松散。参见贺雪峰:《村治的逻辑:农民行动单位的视角》,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年版。。因为这种“给予”与“亏欠”关系,熟人社会构成了一个“自己人”的社会,熟人社会因此才是一个“亲密社群”。正如费孝通所说:“亲密的共同生活中各人互相依赖的地方是多方面和长期的,因之在授受之间无法分一笔一笔的清算往回。亲密社群的团结性就倚赖于各分子间都相互的拖欠着未了的人情。”“欠了别人的人情就得找一个机会加重一些去回个礼,加重一些就在使对方反欠了自己一笔人情。来来往往,维持着人和人之间的互助合作。亲密社群中既无法不互欠人情,也最怕‘算账’。‘算账’‘清算’等于绝交之谓,因为如果相互不欠人情,也就无需往来了。”[17]72
人情“亏欠”是村庄熟人社会的重要特征,每个人都亏欠其他人的,每个人又被其他人亏欠。因为这种“亏欠”,互相之间才有了“情分”;因为这种网络式的“亏欠”,村庄熟人社会才构成了“自己人”的社会。没有这种“亏欠”,作为亲密社群的熟人社会也就不复存在。这也是乡土熟人社会与城市里的“熟人”团体(如车友会)的重要差别。后者的成员尽管也是“熟人”,内部信息透明,但互相之间并没有深厚的网络式“亏欠”。熟人社会中,人情“亏欠”的范围非常广泛,既包括仪式性人情场合中的表达性馈赠,如生育庆典、婚礼、拜寿、盖房、丧礼等;也包括非仪式性情境中的表达性馈赠,如日常互访、拜年、探望病人等[7]50;还与日常生活中的合作、互助等非仪式性的人情密切相关。总之,人情“亏欠”镶嵌在村庄熟人社会之中。
在维护社会团结上,所有的人情都能发挥作用,但仪式性人情的作用更加突出。它具有村庄公共性,往往能将整个村落都调动起来,虽然频度不太大,有很强的间歇性,但比日常性人情有更高的强度和更深的含义。因为仪式性人情在村庄中是一个公共事件,具有公开性和公示性,是村庄社会关系的集中展示,也是社会支持的具体体现。经由仪式性场合的人情表达,社会关系得以公开性地展示,人们对“办事”村民的社会支持就得以表现出来。通过这种社会支持,村庄社会团结就得以维护。
在仪式性场合,来客的多少及客人的具体表现可以展示办事村民在乡村社会的地位。前来“送人情”参加仪式的人越多,呆的时间越长,态度越尊重,办事村民的社会声望和面子就越大。在这种仪式性场合,帮忙的人越多,甚至看热闹的人越多,也能表示办事村民的人缘关系好,能增加仪式的重要性。这就是俗话中所说的“捧场”。办事村民需要别人来“捧场”,但别人的捧场不是没有条件的,前提是办事村民过去或将来也给他人“捧场”。也就是说,办事村民要获得更多的面子,需要别人来“捧场”,这会激励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去给别人“捧场”,积极参与人情仪式中。这样,人情仪式就成了具有了维护和增进村庄社会团结的功能。
费孝通讲:“在传统结构中,每一家以自己的地位作中心,周围划出一个圈子,这个圈子是‘街坊’。有喜事要请酒,生了孩子要送红蛋,有丧事要出来助殓,抬棺材,是生活上的互助机构。可是这不是一个固定的团体,而是一个范围。范围的大小也要依着中心的势力厚薄而定。有势力的人家的街坊遍及全村,穷苦人家的街坊只是比邻的两三家。”[17]27这也许是以江南的市镇为经验基础的,而江南市镇已经逐渐与理想状态的传统农村社会有所不同。其实,在传统农村社会,贫穷或富裕确实会影响家庭人情圈的大小,但这种影响并不是绝对的。在有家族等结构性力量存在的村庄,人情圈是有一个基础性范围的。比如同一房份或五服范围内的村民办事,其他村民都要去“送人情”;在一些小的村庄,更是全村村民基本都要参与。
当然,并不是说传统农村社会的人情圈不存在社会排斥。不过,在村庄社会中,这种社会排斥主要不是经济上的 (虽然不能否认村民也有趋炎附势的倾向),而是一种基于道德评价的排斥。村庄道德的越轨者常常会被排斥在人情圈之外。人们在仪式性人情和非仪式性人情的场合来远离道德越轨者,而尤其是仪式性人情由于具有公开性而更让道德越轨者尴尬。阎云翔在调研中就发现,村里不孝敬老人的农户在办白事时,村民会通过不去人情仪式现场或只作短暂停留等方式来表达他们的不满[7]91。
在仪式性人情场合下,对道德越轨者的社会排斥,与通常情况下对一般村民的社会支持,其实是一体两面的。社会排斥是社会支持的反向表现,正因为存在社会排斥,社会支持的功能才能够更好地体现出来。通过社会支持和社会排斥的有机结合,仪式性人情维护社会团结的社会功能才可以落实在现实生活中。
二、财富聚敛:人情的经济功能异化
在江汉平原农村,当前人情越来越多,几乎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到了农闲时间,农村便几乎是家家办酒席,户户送人情,村民常常因为一天有几个人情仪式需要参加,而不能亲自赴宴,只好请人带人情。江汉平原的农民很忙,除了忙农活,就是在忙着人情走往。与以前相比,江汉平原农村的仪式性人情的场合明显有所扩大,内容越来越多。20世纪 80年代以前,人们只是按传统的仪式送人情,不过就是做房子、结婚、小孩满月、老人去世。一个家庭一辈子也才办有限的几次人情仪式。
而现在越来越多的场合成为仪式性人情场合,需要摆酒席收人情,除了传统的人情仪式,增添了小孩每个整数的周岁都要办,更有逢五也要办的仪式。不只是生日要办酒席收人情,人们还有很多办酒席收人情的理由。小孩考学也要办,考上大学要办,考上高中、中专也要办;考上学校的要办,花钱上学的也要办。参军的要办,店铺开业要办酒席,新房落成要办酒席。
在仪式性人情场合,前去送人情的人包括亲戚、朋友和庄邻。每家都有亲戚,父亲一辈的老亲、儿子一辈的新亲,舅亲姑亲表亲,加起来总得有 20家,每家来 2个人就是 40人。每个人都有朋友,包括小学中学同学,生意场上或一起打工的伙伴,关系好的同龄人等,30人不算多。一个村子有好几百户,关系好的庄邻少说也有 40户,尤其是同一个村民组的,基本是比较稳定的人情圈。这样算下来,不算那些帮忙打杂的人,就有一百多人的规模,一次就得摆十几桌酒席。在红白事酒席规模较大的场合,一般都有几十桌,少的人家也有二十多桌。这样一次酒席至少要花费几千元,不过这些花费可以在收取的人情中收回。送人情的数目因关系远近及仪式性人情的场合不同,而有很大不同。本村庄邻一般 50-100元,朋友 100元以上,一般亲友 100元以上,特别的亲友比如舅舅参加外甥的婚礼,没有 500百元恐怕很难拿出手。办酒席花的钱虽然也多,但收的人情钱总是更多,这样,办一次酒席实际上就是一次赚取收入的机会。
由于办酒席可以赚钱,人们办的场次越来越多,吃酒席送人情越来越成为负担,人人惧之却无法摆脱。在江汉平原农村,现在每个家庭几乎每两年就要办一次酒席,一个村民每年送给庄邻的人情就至少有二三十次。一个村民参加亲戚朋友办的酒席,至少又是二三十次。这样算下来,一年每户总共得出席约五六十次酒席,送五六十次人情。现在每个家庭一年的人情开支至少一万元左右,人际交往广的必定超过万元。洪湖桥头村的村支书每年花在人情方面的开支是两万多元。人情开支已经成为人们日常开支中最重要的部分,绝大多数家庭的人情开支超过了一个大学生一年的教育花费,几年的人情开支加起来就可以做一栋房子。如此一来,吃酒席、送人情,几乎成了人们沉重的负担和苦不堪言的麻烦事。在访谈中,对现在的仪式性人情往来人人叹气。有老人说:“现在的人情往来是陋习、是歪风。毛主席那会,大家不搞这一套。大家是个集体,有事情相互帮忙。”村民都说,别人给你送了人情你不去人家那里还,就是没有道德,就是一万个不对。因为人情往来讲究互惠,“来而不往非礼也”。而现在人情又重,还人情成了一笔沉重的负担。
人情是互惠的,以礼尚往来为原则的。在村庄中,因为自己的人情付出多了,找机会办事将人情赚回来,也算是有正当的理由。村民对此也比较理解,大家都默许这样,不会有太多的议论,这样下次其他人也就有了如此做的依据。
随着仪式性人情逐渐成为回收钱财的工具,一些摆酒本来就多的人更加频繁地请客,他们不仅要回收人情,还要聚敛财富。只要对人们突破过去的一般做法来回收人情的做法保持宽容,就会有更多的人想着突破过去的做法。这样,人们最终对借仪式性人情来聚敛财富的做法也毫无办法,于是就有了许多啼笑皆非的例子,一些人巧立名目来请客赚取人情。桥头村一个农户建两层的房子,建成第一层时请客办了一次酒席,过了一段时间建成了第二层,又请客办了一次酒席。
一起更极端的个案是“杀人请客”。村里有八个小孩卷入一场人命案,他们的家长希望在二审中将初审判决的死刑改为轻判,决定花钱去“走后门”。由于筹集不到更多的钱,八个小孩的家长先后请了客,他们说“收点人情筹点钱”。村里的人都觉得好笑,那些与之有人情关系的村民却也只得送人情去。在访谈时,他们说:“没有办法,他家杀人了都敢请客,你还不好意思去?”
更糟糕的是,为了聚敛财富,欺诈请客的现象开始出现。在桥头村,最早是村里一对夫妇,他们没有生养小孩。生小孩、小孩生日以及日后的订婚、结婚都是仪式性人情场合,可以有大笔收入进账的。他们没有小孩就没有机会收取这种人情,因此在人情来往中这些场合只出不进,颇感吃亏。后来他们对村民说抱养了一个小孩,于是请客收了一次人情。事后,人们发现他们把小孩送走了,根本就没有抱养小孩这回事,原来是“借鸡生蛋”。此事过后,村里马上有个年轻人说找了个对象,还照了结婚照,以订婚的名义告知亲友和邻居说要办订婚仪式。但请完客收完人情后,他的“对象”就拿着两百元“租金”走了。原来女孩是雇来的,村里一片哗然。大家说,下次上人情可要擦亮眼睛防止欺诈了。可下次有类似的情形,大家明知是欺诈,却还是“自愿”地去接受“欺诈”。桥头村一带,好几个村的书记都在城里买了房子,请客收人情后不久就将房子卖出去,这么一个倒手的过程就可以赚四五万的人情收入。这种欺诈的请客越演越烈,那些老实的农民支出的人情越来越多了。
三、财富聚敛:人情的社会功能弱化
在当前江汉平原农村,人情的互助功能正在丧失,越来越多的村民正借人情的互助之名而行聚敛财富之实。尽管一些老实的农民对此非常看不惯,背地里咒骂这些聚敛财富的村民“不要脸”,但他们毕竟抵抗不了潮流。他们可能一面在背地里咒骂,一面却“热情”地出现在人家的仪式性人情的现场。老实的农民也似乎越来越口是心非。
取消农业税前,村民们就开玩笑说:“大家都敢拖欠农业税费,但从来没有人敢拖欠人情。”“低头不见抬头见的,欠了人情以后怎么打招呼?”即使明知道是人情欺诈,大家也只敢背地咒骂,与对方有人情往来就必须去。因为别人欺诈是别人的问题,你不去就首先是你的道德有问题,要被人笑话“小气”,因此没有人敢先拉下面子说不去。这活脱脱是一个现代农村版的“皇帝的新装”,明明是财富聚敛的不道德过程,大家却都小心翼翼地将之演绎成人情的温暖场景。生活在村庄中的村民没有办法,只能被动地被裹胁进这种场景中。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聚敛财富的仪式性人情真的有温暖,它不过是借用了传统仪式性人情的外壳,而越来越缺乏传统仪式性人情的实质内容。
在传统社会中,仪式性人情毫无疑问是一个增加感情、巩固关系的场合。正是通过发展感情联系、培养私人关系,人情往来在村庄中具有了重要意义,成为增进社会团结的重要机制。
当前,人情在作为人际关系的润滑剂、维护社会团结方面出现了严重的功能弱化。仪式性人情场合送人情的金额日益重要,送人情的行为及其它附属的重要行为日趋不重要。仪式性人情场合的其他重要内容都逐渐丧失了,只剩下送人情一项实质内容了。人情本来是为了在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在经济上互相帮助,进而增强人际关系的互动。但这种经济互助功能日益丧失,逐渐沦为赤裸裸的剥夺和反剥夺的互动。其增强人际关系互动的目的不但没有实现,反而成了所有人提及都恐惧却又不得不“热情”参与其中的活动。
前文已提及,传统农村社会的人情也存在社会排斥,这种社会排斥主要是一种基于道德评价的排斥,村庄道德的越轨者常常会被排斥在人情圈之外。人们通过拒绝参与道德越轨者的家庭主办的仪式性人情场合,而让他们在经济上不能得到更多的帮助,在社会名誉上受到羞辱和孤立。由于存在这种社会排斥机制,村庄社会的主流道德得以维护,村庄社会团结才能得以有力维护。可以说,人情的道德排斥机制是其维护村庄社会团结的重要手段。
但是,当前江汉平原农村,仪式性人情中已经几乎不存在道德排斥机制,其中已经没有任何道德标准,甚至道德和不道德发生了相当的逆转。对于那些以欺诈形式办事的村民,村民虽然在背地里有鄙视和非议,但没有人会以自己的行动在人情中去予以抵制,因为其中已经没有道德的位置,不存在一个明确的所谓的正当性。
没有所谓的正当性,就不会再有传统乡村社会中的那种道德排斥。大家都只会将现有怪异的人情做法当作既定的格局,并在这一格局下进行理性算计。在既定的格局下,你没钱了就办酒席收人情,或者为了聚敛财富而办酒席收人情,刮走了我的钱;我没钱了也要办酒席收人情,来赚一次你的钱。在传统社会,人情越多,人际交往就密切;人情收入还可以成为互助性的资金,解决生产生活中的现实困难。但是,当前的情形发生了很大变化。恶性循环的人情博弈里,人们频繁地支出与收回。赚到的一点人情钱还没来不及投入生产,就又要支出了。而且摆酒席必定要花钱,由此农民的钱最终其实是被消费掉了。这样,农民除了在吃上“天天像过年”外,心情并不舒畅,仪式性人情场合也不能通过聚集力量来解决生产和生活上的问题。
在这种状况下,人情的互惠,人情联系起来的互助,以及人情作为社会关系运作的润滑剂,在欺诈性的人情博弈中丧失殆尽,剩下的是绞尽脑汁的不劳而获。人情之中的感情联系,及其维护社会团结的功能,尤其是其中的道德因素和道德排斥机制,已经被无情地剥离。老实的村民被人情负担压得透不过气来,而那些不怕他人在背后议论,不要脸面甘愿被人笑话缺德的人,则有了十足的空间,他们可以“摸脑壳”请客,并将人情作为一种聚敛财富的方式。
四、人情功能异化的逻辑
在调研中的江汉平原农村,人情的互助功能正在丧失,越来越多的村民正借人情的互助之名而行聚敛财富之实,人情维护社会团结的功能也日趋弱化。农民根本无法抵制仪式性人情的异化,只能随波逐流。农村仪式性人情的异化,显然与当前的社会变迁密切相关。然而,社会变迁是如何具体导致了仪式性人情的异化,其背后的具体逻辑如何?这需要仔细分析和细致梳理。
如果从发生学上考察,仪式性人情的异化,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先是有人发现自己在人情交往中总是吃亏,于是想办法找各种机会来实现人情的来往平衡。在这一阶段,人们对那些找机会实现人情来往平衡的村民保持了充分理解,没有太多的非议。第二阶段,当人们发现可以通过在传统之外找机会实现人情的来往平衡时,有人便通过找同样的机会来实现财富聚敛。在这一阶段,人们对通过人情来实现财富聚敛的村民非常鄙视,却不敢公开指责。在这两个阶段中,有以下几个问题值得注意:第一,为什么人们会突然发现自己在人情交往中吃亏,并会急切地想重新实现平衡?第二,为什么想办法实现人情平衡的做法不会遇到抵制?第三,为什么人们在明知是人情欺诈的情形下还会“热情”地去受骗?厘清这些问题,显然有助于理解人情异化的逻辑。
对第一个问题可以这么解释,在传统时代,本来就是因生命周期变化所导致的家庭宽裕与困难,而有必要、也能够通过人情建构一种经济互助机制。而生命周期的变化是以一辈子为单位的,因此,人情交往的平衡是长时段的,而不是一两次的计算,那时人们的生活预期非常长。人们常常不只是为当下着想,还为遥远的未来着想;不但为自己的今天着想,还会为子孙后代的明天着想。因此,当下的吃亏可以从遥远的未来获得补偿,甚至父辈的吃亏可以在子辈那里得以补偿。生活预期长,使得人们就不仅生活在一个物质的世界,而且生活在一个道义的世界。村民不仅看重物质的好处,而且更加看重道义的好处。那时,人们在人情交往中也可能有不平衡感,但很少有人敢公开讲出来,因为这种不平衡感在村庄生活中没有任何合法性,讲出来意味着目光短浅、不好相处,会导致相当消极的后果。人情交往中即使有争议,人们争论的也多是“礼数”,是基于价值收益而不是经济收益的争论。
当前,江汉平原的村庄生活中,人们越来越对未来生活没有长远预期,村庄精英不断从乡土社会流出,每个人都在期待往外的流动。没有人会在意将来自己的儿子生活在哪里,甚至自己下半辈子生活在哪里,还与不与其他村民打交道都不敢肯定。这种情况下,人们不会看重道义的好处,而越来越看重眼前的经济利益,甚至为了经济利益不惜把事情做绝。正是在这种境况下,人们会“突然发现”自己在人情交往中吃亏,而且期望尽快实现人情交往的平衡;而为了实现这种平衡,甚至在传统的仪式性人情场合之外想出种种方式办酒席收人情。也正是在这种境况下,种种突破传统的做法才能获得人们的理解,越来越多的仪式性人情场合才能获得人们的支持。
对第二、第三个问题可以做如下解释:因为当前村庄中已经不存在结构化的制约力量。当前江汉平原农村,人际关系日趋离散和原子化,在核心家庭之外不再有认同与行动单位[18]。每个村民都几乎是独立的个体,人们缺乏组织起来对抗越轨者的足够力量和可能性。由于不存在有组织性的结构性力量,村庄内部也不可能有强劲的地方性规范存在;即使有,也难以得到有效的执行。因此,各种突破传统的仪式性人情场合被不断制造出来,而村民根本没有能力抵制。一旦没有结构化的制约力量,单个村民的理性做法就是不出来公开指责和抵制,因为公开指责和抵制也难以得到其他村民的结构性支持。所有的村民都按这种理性做法行事,村庄最终就丧失了道德排斥能力。这就是所有的村民在人情诈骗的场合“热情”地去受骗的原因。最终,不讲脸面的人就能在人情交往中取得胜利,通过人情谋取利益,而在这种没有结构化制约力量、缺乏长远生活预期的村庄中,脸面本身也并不重要。
在缺乏结构性力量制约的村庄中,由于缺乏稳定的结构性社会关系,人情就成为了建构社会关系的重要手段[14][16]。因此,积极参与仪式性人情场合就是单个村民的理性做法,这也是江汉平原村庄丧失道德排斥能力的原因。在有结构性力量存在 (如宗族或小亲族力量强大)的村庄中,人们的社会关系处在村庄社会结构中,是人情关系运作较难以改变的,因此人情不会成为建构个人社会关系的有力手段。相反,由于村庄中存在结构性力量,仪式性人情场合就不仅仅是一个小家庭的事情,而可能成为全宗族、小亲族的公共性的事情。这样,小家庭就不能公开地计算人情交往的平衡账,而要顾及村庄的道德评价。人际关系原子化、不存在结构性力量的村庄中,情况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尽管人情的花费非常大,给农民带来了很重的负担,但所有的村民都无可奈何而又不得不卷入其中。人情给人们带来了强大的压力,每个村民只要不想被边缘化就必须去赶人情,借以维系自己在村庄中的位置。
仪式性人情的异化其实是当前乡村社会剧烈变迁时期发生的,一种名义与实质相分离的现象。“名实分离”是社会转型时期的普遍现象。费孝通曾指出,在一个变动缓慢的社会结构里,传统的形式是不准反对的,但是只要表面上承认这形式,内容却可以经注释而改变。对不能反对而又不切实用的教条或命令只有加以歪曲,只留一个面子。面子就是表面的无违。结果不免口是心非,滋生虚伪和歪曲,但这不可避免。名实之间的距离跟着社会变迁速率而增加。当社会加速变动时,注释式歪曲原意的办法无法避免,因此会发生位与权,名与实,言与行,话与事,理论与现实,全趋向于分离[17]80。人情异化中的“名实分离”,与费孝通所说的还不完全是一回事。人情异化中并不是传统的形式不准反对,而是指仪式性人情中新出现的各种事物和现象,它们借用了传统事物的形式,从而使得仪式性人情的表面与内核、形式与实质发生了分离。在一个完全固定的社会结构里,人情的表面与内核、形式与实质是不会发生分离的,但是完全固定的社会事实上并不存在。在变化缓慢的传统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村庄长老权力不会容忍这种分离。当前社会发生了剧烈变迁,人情的表面与内核、形式与实质发生分离,这也就可以理解了。
[1]陈柏峰:《论熟人社会》,载《社会》2011年第 1期。
[2]杨华:《人情的性质及其变化》,载《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研究生学报》2008年第 1期。
[3]陈柏峰:《纠纷解决与国家权力构成》,载《民间法:第8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
[4]黄光国:《面子——中国人的权力游戏》,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年版;
[5]翟学伟:《面子?人情?关系网》,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4年版。
[6]马塞尔·莫斯:《礼物》,汲喆译,陈瑞桦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年版。
[7]阎云翔:《礼物的流动》,李放春、刘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年版。
[8]杨美惠:《礼物、关系学与国家》,赵旭东、孙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
[9]朱晓莹:《人情的泛化及其负功能》,载《社会》2003年第 9期。
[10]黄玉琴:《礼物、生命仪礼和人情圈》,载《社会学研究》2002年第 4期。
[11]陈柏峰、郭俊霞:《也论面子——村庄生活的视角》,载《华中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 1期。
[12]杨华:《湘南宗族性村里的面子观》,载《华中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 1期。
[13]陈柏峰:《村庄生活中的面子及其三层结构》,载《广东社会科学》2009年第 1期。
[14]贺雪峰:《熟人社会的治理》,载《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 2期。
[15]陈柏峰:《乡村干部的人情与工作》,载《中国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 2期。
[16]宋丽娜:《河南农村的仪式性人情及其村庄社会基础》,载《民俗研究》2010年第 2期。
[17]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年版。
[18]贺雪峰:《村治的逻辑:农民行动单位的视角》,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年版。
责任编辑 丘斯迈
Function Distortion of Ritual Favors in Rural China
CHEN Bai-feng
(law school,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Wuhan 430074,China)
The mutual economic assistance and social solidarity maintenance are important functions of ritual favors in traditional rural China,which are distorted in Rural Lianghu Plain now.The name and essence of ritual favors are detached.The function of mutual economic assistance is disappearing,and the function of social solidarity maintenance is weakening.More and more villagers a mass wealth in the name of ritual favors. The function distortion of ritual favors is closely related with the social change in Rural Lianghu Plain.As villagers′lack of long-term expectations,they care of immediate economic interests;and the village has no power of structural constraints,village relationships become dispersed day by day.
ritual favors;mutual economic assistance;social solidarity;functions distortion
陈柏峰 (1980-),男,湖北咸宁人,法学博士,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人员,研究方向为农村社会学和法律社会学。
2010-10-25
C912.82
A
1671-7023(2011)01-0106-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