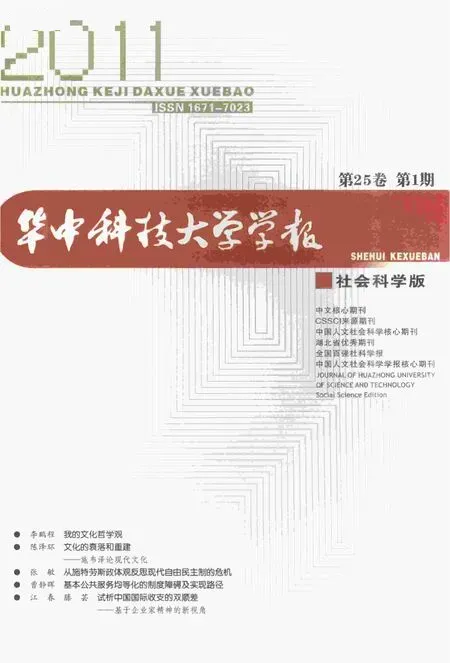都市研究中的空间视角
——一种都市社会学理论视野的探索
2011-04-08吴娅丹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湖北武汉430079
吴娅丹,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湖北武汉 430079
都市研究中的空间视角
——一种都市社会学理论视野的探索
吴娅丹,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湖北武汉 430079
社会学中空间视野的运用及发展与都市研究的演进脉络有着紧密的交织。以都市研究中的空间视角为主轴,对现代都市社会学的发展历程及问题进行的梳理与反思表明:对都市社会学来说,空间视角的引入与挖掘是推动都市研究理论及方法论创新的一种重要途径和有效方法,应受到学界重视并得到进一步推广。
都市研究;都市社会学;空间;理论探索
长久以来,空间与时间一起,被哲学视作是人类存在的基本范畴加以研究,但直到最近三四十年,作为一种重要社会事实的“空间”才逐渐在社会学领域引起重视。越来越多的社会学家开始把空间作为一种专门的研究类别进行系统和深入地研讨,“以空间思维审视社会”的研究路径得以发掘和发展,并且逐渐在“历史主义”长期占据主导的社会认知与理论意识体系中争得了一席之地,掀起了社会理论的某种“空间转向”。本文想在此基础上提出注意的是,“空间”在社会学中的发现与崛起,实际上与“都市研究”主题密切相关:都市是空间进入社会学论域的重要切入点和主要实验场,而都市研究中如何“安置”空间的问题,更是与社会学的重要分支——都市社会学的理论发展脉络紧密纠缠在一起。因此,本文试图以都市研究中的空间视角为线索和主轴,对现代都市社会学演进历程及发展问题进行梳理与反思,并以此阐明空间之纬对都市研究的特殊意义。
一、都市空间视角的发端——古典社会学的空间思想遗产
都市社会学通常被认为是以 20世纪一二十年代芝加哥学派的兴起为创立标志,然而这并不是说在此之前的社会学就没有关于都市问题的探索。实际上,对都市及都市生活的思考早在马克思、恩格斯、腾尼斯、齐美尔等古典社会学家的作品中就有所体现,它们构成了都市社会学最终成型的有益铺垫和根本基础。更为重要的是,其中的很多分析及讨论都显示出社会学初始阶段大家对空间向度的某种直觉和领悟,表明他们已经有意无意地触及空间意识或方法在都市研究中的运用与实践,这正是空间视角在社会学中的最初闪现。
将城市看作是一种异于传统村社的特殊的社会生活的空间形式,是早期都市空间视角的主要表达。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城市与资本主义”议题的分析对此进行了粗略地呈现。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城市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重要环境条件,他们在阐明了以“时间消灭空间”的资本扩张逻辑以及有关劳动的空间分工思想的基础上,对资本主义工业化时期城镇与乡村的对立以及城市内部的贫富分化与阶级斗争状况进行了经典的论述和总结[1],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空间表象与社会关系之间存在着联系的基本事实。尽管对这种关系的讨论仅是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分析的附属而存在,比较间接和隐晦,也明显缺乏理论性和系统性,但这些内容仍应该被视为空间分析融入城市政治经济学的思想先驱,它同时也是我们在后文将看到的 1970年以后都市社会学进入新发展阶段的启发性源泉。
继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后,更为专注地表达出早期空间思维方式的,是腾尼斯藉由《共同体与社会》一书对城市—乡村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空间组织形式及由它们所导致的社会生活形式所进行的探讨。在此书中,以乡村为特征的礼俗社会和以城市为特征的法理社会被腾尼斯归纳为人类共同生活基本结构的两种主要类型,它们受到不同的规则系统与运行逻辑的主导和支配。通过与传统乡村生活的比较,集中表现空间原则的城市形式以及唯我独尊、分崩离析、肆无忌惮的个人主义等城市生活特征。相应地,城市这种独特空间形式的研究价值也在腾尼斯的这一学术巨著中得到了最早的阐明和深刻的体现。
而齐美尔显然是古典社会学家中最出色地发挥了空间想象力的一位。他在《社会学——关于社会化形式的研究》中列出单章讨论“社会的空间和空间的秩序”问题,极力表达了空间是社会形式得以成立的条件,也是人们之间发生互动的方式的主导思想。他对空间的排他性、分割性、社会互动的空间局部化、邻近/距离以及空间的变动性这五种基本品质的概括与分析,则进一步表明了空间不仅具有物理形态和“行动布景”的意义,更是与社会行为与社会关系有着深层次的联系。值得注意的是,齐美尔对“社会性”空间思想的贯彻仍然选择了大都市作为展开论述的阵地,其关注焦点在于这个高密度刺激和高频率互动的都市空间如何对居民人格的塑造产生影响[2]19-31,从而开创了城市居民社会心理特征研究的先河。可以说,齐美尔的这些极富创造性的研究,其背后的动力正是对都市研究中空间视角的发掘与把握,他首次正面揭示出空间维度对都市社会的重大意义,使得空间第一次在都市分析中成为一个重要的“显性”研究参数。
二、形式主义空间的运用——芝加哥学派的兴起
当都市空间想象力在欧洲大陆启蒙并零星闪现时,大西洋对岸的芝加哥学派却真正做到了令其大放异彩——当然,他们所采取的方式明显混合了美国专业管理主义和实用主义理想色彩。但不管怎样,被誉为现代都市社会学创立标志的芝加哥学派还是给都市研究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在一批当时最有创新能力的社会学家帕克(R.E.Park)、伯吉斯(E.W.Bu rgess)、沃斯(L.W irth)、麦肯齐 (R.M cKenzie)等人的带领下,芝加哥学派的研究者们将都市研究与社会达尔文主义连结起来,开创了都市社会学中长期占据主流的人文生态学 (hum an eco logy),无形中促发了“空间”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至少是在形式上较为明朗和普遍地登上了都市研究的舞台。
将城市空间看作一个由人群的依赖共生与相互竞争所决定的生物有机体的基本认识,显著地塑造了新兴的芝加哥学派的都市意识,他们认为城市有机体的可见表面是最重要的,因此主张扎根于都市环境表层的空间结构及相互秩序,着重探讨人类组织形式和行为与空间区位之间的关联。他们的研究创立了一种著名的都市研究范式——对城市的社会和空间形态模型化,现在已为所有都市社会学的研究者们熟悉。其中最持久的模式是伯吉斯提出的分区理论和同心圆理论,用以描述不同的城市社会区域进化的过程。伯吉斯指出,城市趋向于形成一系列同心圆地带,而城市扩张分化的动力则适于用入侵、继替和隔离等生态学的词汇加以描述和解释。其他规划师用不同的模型回应了伯吉斯的观点。土地经济学家霍默·霍伊特(H.Hoyt)描绘了城市结构的扇区理论,他注意到城市不是按照同心圆趋势发展,而是沿着高速公路呈星状扩展开。不同的扇面常常会从中心商业区延伸出去,沿着高速公路主干线确立起来。影响扇面结构的主要因素是城市土地的利用、住房市场的运作和交通系统的规划,但“非理性因素”也可能改变城市的外观形式。后来的芝加哥都市地理学家 C·哈里斯和他的同事 E·乌尔曼则在《城市的本质》中打破了城市空间的单一模型,用多核理论阐明了城市发展中的多重核心和复杂进程。他们提出,在城市细胞结构中,土地利用围绕着都市中的多种生长核子而发展,而每一个核心都在有规律地塑造着它们周围的有序城市空间。这些规律基本上由更广泛的经济和社会力量决定,同时也受到历史和国际社会的影响[3]13-15,[4]109。
芝加哥学派的城市分区模型对 20世纪特别是上半叶的城市研究产生了导向性的影响,多数城市研究计划都基于同心圆和扇面规则以及城市结构的多核理论而提出。虽然这些总体表面模式在多大程度上能精确地描绘出城市发展与扩张的实际状况受到了广泛的质疑,但它们却清晰地表达了城市及城市生活普遍存在的空间性特征,并使它成为在社会科学的理论建设、经验获得和实践应用上能够得以施展的研究焦点。芝加哥学派无疑推动了都市研究中空间维度的导入,可是他们的运用方法过于简单和形式化,与一种专门的空间科学的理论需求之间仍然存在差距。不仅空间被简化为仅仅是物质性的知觉空间,因而空间的解释被局限在表层外观与行为的描述之上,无法涉及空间形构背后的深层动力;而且过分强调自然的 (有机的)进程以及依附于经济分析手段,也导致了都市生活中同样重要的社会和历史维度的掩蔽。社会维度的情况还略微好一些,芝加哥学派提供的城市发展模型至少使族群和阶级的影响在城市空间区域隔离的问题上得以部分地凸显;但我们始终难以在芝加哥学派的研究中看到纵深的时间维度与横向的空间维度间的具体联系,城市地方生态只是被一幅幅缺少辩证、相对静态的场景所表达着,人类行动与空间环境之间、社会历史(资本主义工业化)与都市地理(都市化)之间的动态相互作用基本被忽略了。
三、嵌入社会与历史的空间——新都市社会学的复苏
进入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世界范围内爆发的都市危机把芝加哥学派定义的城市理论与实践方法逼入窘境:面对来自各方的挑战——世界经济的急剧下降、大规模郊区化与内城的衰落、强迫集中居住的种族隔离、大都市的政治分裂、福特主义 -凯恩斯式国家中改变的劳资关系、社会运动的兴起等等,传统城市社会学企图通过适应与竞争而自动实现社会平衡的生态学方案似乎失去了效力,它围绕着“社会整合”而发展出的中心议题被正在激烈上升的社会冲突与协商所取代,旧有的思考与行动方式亟待从根本上被解构和重组,这正是为什么在 70年代都市研究领域一股富于批判的“新都市社会学”顽强地复苏。新学派的“新”意对“旧”的芝加哥学派的学术传统的摒弃与反思,其代表人物之一的马克·戈特德纳 (M.Go ttd iener)将其阐释为:1)转向资本主义和大都会的全球视角;2)将空间、阶级、性别与种族歧视等元素包含在都市发展研究之中;3)尽可能整合经济、政治和文化因素;4)关注房地产发展和政府干预的推力;5)城市和郊区发展的多中心区域视角[5]2。这些新的学术旨趣的概括与表达,再次把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到曾被芝加哥学派频繁使用的概念——“空间”上;然而,新学派的策略并不是抛弃空间以表明与芝加哥学派的决裂,恰恰相反,他们是通过超越形式主义空间、深化与空间的本质联系来体现自身的批判价值,这正是新都市社会学区别于芝加哥学派的生态学范式的核心所在。
实际上,奠定新学派理论基础的是朝着两个方向前进的亨利·列斐伏尔 (Henri Lefebvre)和曼纽尔·卡斯特尔 (Manuel Castells)。在他们的带动下,新学派在法国兴起,并围绕四个主题建构起来:前两个主题由列斐伏尔介入,而后在美国为戴维·哈维 (David Harvey)和爱德华·索亚(Edward Soja)出色地发挥,他们关注的是空间的生产和对城市的权利;而后两个主题是集体消费和都市社会运动,主要由卡斯特尔担当。尽管存在着知识来源和研究重点的差异,但他们不仅展现出对空间的共同兴趣,更是在空间视角的运用上,殊途同归地将资本、阶级与空间联系起来,把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看成是理解都市经验的重要手段。
在第一个发展方向上,列斐伏尔被公认为是一位旗手般的人物,其首要贡献在于藉由《空间的生产》一书建立了经典的空间理论及分析体系[6],为新都市社会学的空间想象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根基和扩展动力。列斐伏尔明确地提出了空间的本体论,指出社会现实不是偶然成为空间的,而是在先决条件和本体论上就是空间的;而且,空间从来就不是空洞的,它往往蕴含着某种意义,而这种意义存在于空间性、社会性与历史性的三维辩证中;列斐伏尔还运用“空间实践”、“空间的再现”、“再现的空间”这一三元概念组合,构建出一套由感知的物质空间、构想的抽象空间和实际的生活空间所组成的空间分析框架;①“空间实践”对应着感知的物质空间,可以通过观察、实验等经验手段,对其“外部形态”予以描绘与分析;“空间的再现”对应艺术家、规划师、人类学家等空间研究者们构想的抽象空间,因此借助被他们主观构想出的并按照一定规则概念化的空间术语和知识,可映射出空间的另一种面向;“再现的空间”则对应居住者和使用者活生生的社会生活空间,需要我们对日常生活世界中复杂的符号体系予以关注,从社会与空间两者间的实际运作过程和互动效果中探索空间的社会逻辑。并在马克思生产理论的启发下提出了著名的空间之生产理论,强调空间不仅是社会的产品,也是一种生产方式,因此要把以往人类对“空间中的生产”的考察转移到分析“空间自身的生产”上来。
斐伏尔并没有满足于宏大抽象的理论探讨,他也将空间生产理论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剖析中。在他看来,空间的占有和重组是战后资本主义化解内在矛盾、取得显著成就的重要手段之一,因此空间的生产理应被视为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的核心问题加以对待。而“都市”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尤其具有决定意义,因为城市空间的形成与快速发展是资本主义空间生产最典型的先决条件和产物,作为“人造环境”的城市空间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粗暴浓缩,而且城市规划师对城市空间展开的规划和设置也往往代表着特定阶级利益,事实上发挥了捍卫资本主义的功能。不难看出,列斐伏尔在以空间为视角探索城市化及城市发展问题方面做出了积极的尝试与努力,尤其是他将都市化理解为“现代性的空间化隐喻”的思维模式[7],为后世都市研究的空间视域带来了宝贵的灵感和深刻的影响。
追随着列斐伏尔的最杰出的两位都市研究专家当属哈维和索亚。哈维坚决贯彻着列斐伏尔“空间是一个生产过程”的观点,并极大地推动了从“社会正义”与“城市权利”的角度解读都市重构与危机的研究。他在《社会公正与城市》中提出,资本主义城市是一个在其本质上产生不平等的机器,而资本权利与逻辑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运用资本运动“三级环程”理论②初级环程指资本向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利润性生产的投入,次级环程指资本向城市物质结构和基础设施的投入,第三级环程是资本向科教、卫生福利事业等的投入。,哈维探讨了资本运动与城市空间生产的关系,指出资本以何种方式向哪个环程流动,与相伴而生的阶级斗争一起,决定着城市空间结构形态的规模与本质;而这种“建成的环境”又将重新构成资本进入新一轮循环的基本条件[8]。此外,哈维还对地租理论以及城市、地区与国际空间发展不平衡等问题做出了详细的探讨,进一步揭示出资本投入与空间形式之间复杂微妙的相互作用,凸显了争取都市空间规制权的重要意义[9]。在其更晚近的作品《后现代状况》中,空间重组成为了后现代时期的关键议题,哈维以“时空压缩”③哈维对时空压缩的理解是:“资本主义的历史具有在生活步伐方面加速的特征,而同时又克服了空间上的各种障碍,以至世界有时显得是内在地朝向我们崩溃了。”参见戴维·哈维:《后现代状况》,阎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4年版,第 300页。来说明当代资本主义的空间特征及存续动力,并展示出它所引起的文化实践与政治—经济实践的剧烈变化[10],启示人们调整空间观念以理解全新的都市面貌和对都市的体验。
索亚则通过阐述“第三空间”概念旗帜鲜明地巩固了列斐伏尔空间性—历史性—社会性三元辩证的空间本体论与方法论,并引人入胜地重构了包括洛杉矶、巴黎、奥兰治郡和阿姆斯特丹在内的后现代主义城市,完成了这种空间分析的实践[11]。“第三空间”具备了列斐伏尔倾其全部热情想赋予社会空间的那些复杂的含义,既不同于物质空间(第一空间)和精神空间(第二空间),又包容、超越这两种空间;而透过“第三空间”所洞悉的“后大都市”,既反映出越来越灵活、无组织的资本主义积累,又呈现了被权力与权威、新的文化与意识形态所塑造和重组的日常生活世界,在这一过程中,虽然索亚对城市的分析几乎不涉及社会运动和阶级斗争,但他对城市规划以及政府在资本主义城市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仍有反复地考量,实际上隐射出对“城市权利”议题的部分思考。
至于在另一个发展方向上,早期的卡斯特尔深受阿尔都塞的结构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他在《城市问题》中指出,城市空间是社会结构的表现,社会结构由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三大系统组成,而经济系统起着决定作用。在他看来,都市空间内在于经济活动的四个层面:生产——等同于“生产手段的空间表达”、消费——相当于“劳动能力的空间表达”、交换——起源于“生产和消费之间转换的空间化以及管理”、分配——这是“政治和制度系统与空间的结合”,于是这四个层面依次体现在工业区位、住房和公共娱乐、交通设施及商业、都市规划与管理这四个不同的纬度中[12]126-127。紧接着,卡斯特尔把特别的关注给予了消费领域。在资本主义语境下,城市被界定为“集体消费”的空间,是国家而不是个人成为公共事业和集体消费资料的提供者与管理者,于是国家得以成为一支凌驾于社会生产方式之上的独立力量,不仅调控着工业生产,而且直接介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强有力地执行着统治阶级的利益;而“社会运动”则表达了与国家倡导的城市规划对立、来自于都市居住地和相邻社区的反抗,他们既为向国家争取集体商品与服务以提高整体的消费水平而联合,也为保护自己的居所、维护社区的共同利益而斗争,显示出挑战由国家主导的空间结构的意义并试图重组城市空间的力量。卡斯特尔正是通过“集体消费”和“城市社会运动”的讨论,清晰地将空间置于资本主义运行方式与社会关系的分析中,使围绕着都市空间及其形塑而展开的利益胶着与斗争得以再现,这正是资本主义的特征、矛盾与动力所在。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新都市社会学的成功,得益于普遍性都市危机所提供的现实机遇,也得益于出现得十分及时的空间研究范式的理论进展。二者相互碰撞而产生的新的都市空间想象,构成了新都市社会学挑战芝加哥学派的利器和促进自身发展的动力。到这时,空间本身不再只是芝加哥学派生态学模式中的静止的、形式的空间,它由内而外地被社会意涵与历史意涵充盈起来,并与社会关系及社会变迁的整体过程紧密融合在一起。
四、由空间主导的新转型——21世纪都市社会学的反思
然而,新都市社会学的经验与成果就能一直受用吗?在度过了较为沉寂的 20世纪的最后几年,新都市社会学以缺乏斗志与新意的状态迎来了 21世纪的挑战。面对崭新的都市发展脉络和瞬息变化的都市现实生活,“新都市社会学”已经显出过时与疲惫之态,它一方面太直接地联系着西方先进资本主义都市化的经验,另一方面太依赖马克思主义的架构而不能吻合当今都市全球变动的现实。而此时都市社会学危机的根源与化解途径仍迫切需要透过“空间”去发现。敏锐的都市研究者已经把一些新涌现出的重要的空间现象与问题置于理论架构与经验观察的案头,并把它们理解为重振21世纪的都市社会学的关键。
威廉·米切尔 (William Mitchell)用《比特之城》(1995)一书阐明了他对进入一个新时代——信息时代的城市的新特质的洞悉,这被看作是最早尝试全面解析 21世纪城市出现的新变化的努力之一。米切尔相信,在 21世纪我们将不仅居住在由钢筋混泥土构造的“现实”城市中,同时也栖身于由数字通信网络组建的“软城市”里。正是数字化电信革命、方兴未艾的微电子化,比特的商业化以及软件日益主宰的物质形式,勾画出了新兴的 21世纪城市的轮廓。米切尔在此强调的是在政治和经济因素之外,技术变迁对城市结构和空间组合的强大形塑力,它将对传统的城市概念发起挑战。正因为意识到这种城市空间的颠覆力量会“深刻地影响我们享受经济机会和公共服务的权利、公共对话的性质和内容、文化活动的形式、权力的实施以及由表及里的日常生活体验”[13]4,因此,米切尔最终把研究落脚于重新思考和阐释城市规划的问题上,意图表明它们应该是新世纪都市研究的重要任务和工作。
同年出版的《数字化生存》也十分巧合地表达出与米切尔相似的时代判断,作者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 (Nicholas Negroponte)同样为我们描绘了一个数字化时代的到来,不过他采取了与米切尔不同的方式。尼葛洛庞帝从生活、工作、教育、娱乐等点滴入手,对数字时代带给人类生活方式的冲击作出了生动而详尽的阐明,指出信息时代中特定时空与经济和生活的相关性减弱了,这必将改变我们的生存方式、交往方式和生存观念,既体现出他对数字化生存方式的乐观积极的应对态度,也表达出他对其黑暗面的认知与警示[14]。《数字化生存》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所运用的空间视角远离了宏观社会分析的惯性思维,转而深深扎根于普遍的、琐碎的生活世界,揭示了空间与日常生活的紧密联系,有效拓展了空间视角的应用范围与解释潜力,这无疑是对都市社会学的空间方法论的最具价值的启示。
在捕捉 21世纪都市社会学需要面对的新的研究环境方面,卡斯特尔再次占据了一个显著的位置,可以说,他近年来从空间视域对“步入一个新的社会的都市社会学”的发展方向所进行的思考比任何一位学者都要引人注目和具有启发性。比米切尔和尼葛洛庞帝更早,卡斯特尔就在《信息化城市:信息技术发展与城市空间结构的互动》(1989)中探讨了由信息技术所带来的空间变迁对城市经济体系演变的影响,后来他又通过著名的信息时代三部曲——《网络社会的兴起》(1996)、《认同的力量》(1997)、《千年的终结》(1998)——向我们展示了一幅瑰丽壮阔的全球网络社会图景,完成了对米切尔和尼葛洛庞帝的深化与超越,因为卡斯特尔的研究,正如我们即将看到的那样,既观照到现实社会出现的本质变化,也将都市社会学的经典议题、理论以及研究优势融入其中。
卡斯特尔的基本立场是,在信息技术革命、全球化以及新的主导性社会组织形态之网络的出现这三种力量的交织推动下,现代社会正走向一个以新型的社会结构为依托的“网络社会”,而“空间转型”正是理解这种新型社会结构的根本性维度[15]。基于这一论断,卡斯特尔展开了对 21世纪的都市社会学应该紧紧围绕的都市空间趋势及议题的讨论,主要包括[16]4-8:1)大都市地带的兴起:它是一种被先进的远程通讯、互联网和快速交通体系创造出来的新的网络地理学和跨国家跨世界的城市化聚落和城市节点;2)社会过程及社会关系的转变:包括由新的空间模式和在线 -离线互动创造出交往性(sociability)的杂交模式;以高度去中心化和新型协作管理模式为特征的网络企业的出现;全世界都市区域的多族群和多文化的增长;以及全球犯罪经济植根于都市织理中; 3)城市公共空间特征的改变:是指城市公共空间日益成为地方生活的关键性表达,它们被商业化,并被“卷入跨区域网络”和“受到地点的空间分化所排斥”这样一种双重运动所主宰; 4)网络国家的浮现:网络国家成为了新的情境里管理城市和区域的实际机构,它在一种整合了由各国政府、民族国家、国际机构、区域政府、地方政府和非政府组织构成的超国家机制下运行。此外,卡斯特尔还在试图建构关于网络社会的更具分析性的理论框架的意义上,从功能、意义与形态入手,依次用地方—全球、个体性—社区共同性、地点空间—流动空间这三条二元对立轴线,来描述与分析网络社会的城市转型,把面临着一个新情境的“社会整合”议题重新拉回到都市研究的核心。
还有一些学者的研究显示出晚近都市空间分析的另一种面向,它们旨在把文化、经济与空间的内在关系凸显出来。斯科特·拉什 (Scott Lash)和约翰·厄里 (John U rry)通过《符号经济与空间经济》一书集中探讨了旅游、时装、服务业、影视文化等产业价值由符号意义决定的现象,以及城市贫困区、人口迁徙、空间化时间观念等空间经济现象,揭示了符号系统和空间系统如何相互作用与影响,最终构成了晚近现代社会的重要经济动因。他们的一个基本观点是,在一个由符号网络构筑的社会时空结构中,“经济过程和象征符号过程前所未有地相互交融,相互表达;换言之,经济日益向文化弯折,而文化也越来越向经济弯折”[17]91。沙朗·佐京(Sharon Zukin)也在同样的方向上作出了尝试和努力并产生了广泛影响。她在《城市文化》中明确表达了“文化同样是控制城市空间的一种有力手段”的观点,具体而言,一方面,作为一系列的建筑主题,文化在基于历史保护或地方传统的城市再发展策略中起着重要作用,“(对艺术、食物、时装、音乐、旅游的)文化消费与满足这种消费的工业的发展,给城市的象征经济,即它生产象征与空间的可见能力,提供了动力”[18]1;另一方面,作为意象与记忆的来源,文化象征着“谁属于”特定的区域,因此日益明显地成为社会差别和城市恐惧引起冲突的场所,而“谁占据公共空间,是经常由关于人身安全,文化认同、社会与地理社区的协商决定的”[18]20。至此,以上研究实际上传达出这样的立场:不被芝加哥学派和新都市社会学所强调的“空间的意义”,同样应当作为发掘都市空间视角的重要一环进入研究视野,以往被忽视的文化因素就应该更深入地融入到都市空间的分析中。
从社会学对都市研究理论的探索过程,不难看出在其每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上,空间视角都如影随形,并且逐步丰富和深入。尽管尚未被更多的人发现和重视,但都市社会学研究中不能缺失空间向度的观点已经明晰地显现,离开空间分析将难以理解都市结构形态、都市社会关系和生活以及都市文化危机与重构的本质,给城市发展、规划与治理问题的有效审视和妥善解决带来损失。
这样的认识,对于理解中国的都市化现象与问题显得尤为必要和富于意义。中国正不可避免地成为一个充斥着典型空间特征的新的都市世界中的一员,它不仅被逐步嵌入到全球“网络社会”的运行逻辑中,其加速都市化进程还将激烈地改变中国社会的物质结构及关系形态,使得都市空间的规模扩张、都市区域的功能分化、阶层的空间聚集与隔离等现象成为更显著的“都市问题”。然而,立足于中国经验的种种都市空间问题,正是基于西方情境的都市社会学无法准确解答,而本土的都市研究也没能给予有效开发和充分思考的问题。这就需要我们更主动地借鉴、发挥甚至是创造都市空间视角去推进中国社会“空间模式与都市发展过程”的研究,它将是发现新的都市研究理论与方法论工具的关键领域,是未来都市社会学尤其是中国的都市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的重要机会与动力。
[1]中共中央文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年版。
[2]孙逊、杨剑龙:《阅读城市: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都市生活》,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07年版。
[3]蔡禾:《城市社会学:理论与视野》,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 2003年版。
[4](美)Edward W.So ja.《后大都市:城市和区域的批判性研究》,李钧等译.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6年版。
[5]何雪松:《新城市社会学的空间转向》,载《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 1期。
[6]Lefebvre,H.The Production of Space.Oxford,UK and Cam bridge:MA:Blackwell,1991.
[7]Lefebvre,H.Writings on Cities.Oxford,UK and Cambridge,MA:Blackwell,1996.
[8]Harvey,David.Social Justice and the City.Oxford: Basil Blackwell Publishers,1993.
[9]Harvey,David.The L im its to Capital.Oxford:Basil Blackwell Ltd,1982.
[10]戴维·哈维:《后现代状况》,阎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4年版。
[11](美)Edward W.So ja.《第三空间——去往洛杉矶和其他真实和想象地方的旅程》,陆扬译.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5年版。
[12]Castells,M.The Urban Question.Cam bridge:M IT Press.1977.
[13]威廉·J·米切尔:《比特之城》,范海燕等译.北京:三联书店 1999年版。
[14]尼葛洛庞帝:《数字化生存》,胡泳等译.海南:海南出版社 1996年版。
[15]Castells,M.《网络社会的崛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年版。
[16]许纪霖:《帝国、都市与现代性》,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6年版。
[17]斯科特·拉什、约翰·厄里:《符号经济与空间经济》,王之光、商正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6年版。
[18]Sharon Zukin.《城市文化》,张廷全等译,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6年版。
责任编辑 丘斯迈
Spatial Perspective in Urban Study——An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of Urban Sociology
WU Ya-dan
(School of sociology,Huazhong Normal University,Wuhan 430079,China)
The progress of spatial perspective in sociology has a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urban study′s evolution.This paper makes effort to systematical review and reflection on modern urban sociology′s history and its involved problems according to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spatial perspective. It argues that the spatial perspective could be a significant way to inspire the innovation of theory and methodology of urban study, which is therefore worthy of concern in academic circles.
urban study;urban socio logy;theoretical exploration
吴娅丹 (1981-),女,湖北武汉人,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社会学理论及应用、城市社会学。
2010-11-23
C912.81
A
1671-7023(2011)01-009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