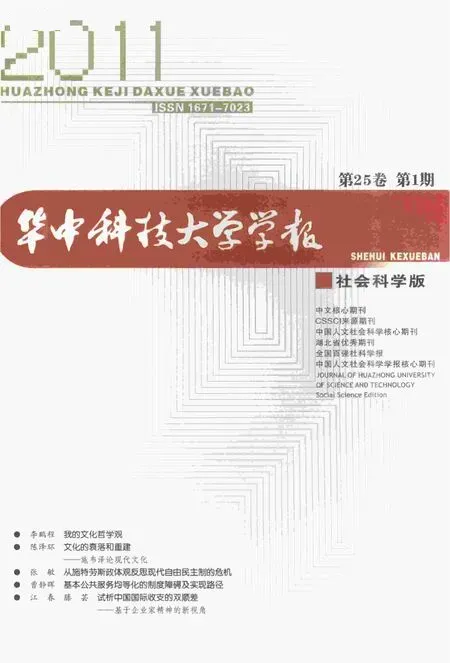浅议宗教的文学艺术功能
2011-04-08段德智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湖北武汉430072
段德智,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湖北武汉 430072
浅议宗教的文学艺术功能
段德智,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湖北武汉 430072
宗教与文学艺术由于其均偏重于“形象思维”方式,而在其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一直保持着一种特别亲密的关系,大体经历了一个从相互混融到两相分化、互存互动的演进过程。宗教对文学艺术的影响不仅历史悠久和极其广泛,而且相当深刻。宗教的文学艺术功能不仅表现在其对文学艺术精品的催生方面,而且还表现在其对文学艺术人才的塑造方面。宗教对文学艺术精品的催生在人类文学艺术史上是一种相当普遍的文化现象,无论是在古代希腊悲剧和莎士比亚戏剧作品中,还是在我国的古典名著中,我们都不难找到其浓重的宗教酵素。宗教对文学艺术人才的塑造功能也是同样显而易见的。可以说,离开了基督宗教的陶铸,就没有莎士比亚,而离开了中国宗教的陶铸,就没有曹雪芹。
宗教;文学艺术;催生功能;塑造功能
爱因斯坦在谈到宗教与科学的辩证关系时,曾道出了一句脍炙人口的名言:“科学若没有宗教就像瘸子,宗教没有科学就像瞎子。”[1]182如果说爱因斯坦的这句话的后半句强调的是宗教对作为文化形态之一的科学的依赖性的话,所昭示的则是宗教对作为文化形态之一的科学的助推功能。那么,宗教的文化功能是否仅仅限于科学这样一种文化形态呢?它对其他文化形态,譬如对文学艺术形态,是否也同样有其积极的助推功能呢?下面就扼要地谈一点自己的看法。
一、宗教与文学艺术关系的历史演绎:其互存与互动
在宗教与其他意识形态和文化形态的关系中,宗教同文学艺术的关系非常特殊,尤为密切。这主要的并不是由于宗教和文学艺术的同源性(即归根到底都来自社会生活)的缘故,也不是由于宗教在人类文化体系中的特殊地位的缘故,而是由于宗教和文学艺术把握世界的方式的一致性或相似性的缘故。人们把握世界的方式固然千差万别,但从根本上讲无非是两种思维方式,一种为所谓“逻辑思维”方式,另一种为“形象思维”方式。而形象思维方式的特征不是别的,正在于它的“形象化”,即它的“感性化”或“具象化”。很显然,这也正是文学艺术思维方式的本质特征。可以说,正是宗教同文学艺术把握世界的思维方式的这样一种“一致性”或“共性”把宗教同文学艺术特别紧密地联系到了一起。
宗教借形象思维的方式来把握世界不是偶然的,而是由宗教自身的本质规定性所决定的。宗教既然是一种由广大信徒组成的社会群体,它就不能不借助于形象思维的方式来宣传信徒和组织信徒。不仅如此,宗教观念的特殊性质也要求形象思维这样一种表达方式。因为既然宗教信仰的本质特征在于它的超越性,在于它是一种不可借抽象概念言说的奥秘,则宗教信仰在寻求表达方式时便势必内蕴着一种似是而非的悖论,即寻求一种对不可言说者加以言说的方式,而形象思维或文学艺术手法无疑是它不得不采取的一种比较妥当的表达方式。而这也是凡宗教都有一个神话故事系统的根本缘由[2]408-411。正如犹太教和基督宗教关于上帝全能、全知、全善的观念是通过上帝六天创世的神话故事、亚当和夏娃贪吃禁果的原罪故事、诺亚方舟故事、亚伯拉罕杀子献祭的故事以及耶稣受难的故事等一系列神话故事彰显出来,佛教关于“悟即是佛道”的观念是通过佛陀出家苦修和菩提树下悟道成佛等神话故事彰显出来的一样,其他宗教的基本教义或基本观念也往往是借这样那样的神话故事呈现给普通信众的。
宗教与文学艺术的关系同宗教与其他意识形态和文化形态的关系也大体相似:如果对这种关系作一番历时性考察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看到,宗教同文学艺术之间大体经历了一个从相互混融到两相分化、互存互动的演进过程。在远古时代,原始宗教同原始文学艺术差不多是浑然一体的。不仅原始艺术的绘画、音乐、舞蹈等形态往往同原始宗教 (包括原生巫教)的宗教观念、宗教仪式有这样那样的关联,而且作为原始宗教观念的载体的神话故事本身即是人类最初形态的民间文学或口头文学。在后来的历史发展中,原始宗教 (包括原生巫教和原生神话)同原始文学艺术的这种浑然一体的状况发生了变化,一方面从这种统一体中分化出了种种系统宗教,产生了种种神学体系,另一方面又从这种统一体中滋生出了种种早期文学和早期艺术形态,滋生出了种种世俗文学和种种世俗艺术。尽管,在整个前现代的历史时期,世俗文学和世俗艺术,总的来说依然处于宗教或宗教文学和宗教艺术的影响和支配之下,但是,无论如何,它们毕竟获得了某种相对独立的地位,并且在文艺复兴运动之后,逐步构成了文学艺术的主流,开始同宗教或宗教文学和宗教艺术建立起一种良性的互存互动的关系。
当我们对宗教与文学艺术的关系作逻辑的或同时性的考察的时候,我们同样也可以看到这种关系同宗教与其他意识形态或文化形态的关系的相似性。也就是说,存在于宗教与文学艺术之间的同样是一种既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相互贯通、相互推动的关系。宗教同 (世俗)文学艺术之间的对立最根本的就在于宗教的本质特征在于它本质上是人的神圣化,是一种以神为中心的文化,而 (世俗)文学艺术的本质特征则在于它本质上是自然和社会的人性化或人格化,是一种以人为中心的文化。而它们之间的相互依存、相互贯通和相互推动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即一方面是宗教的文学化和艺术化,另一方面是文学的宗教化和艺术的宗教化。具体地说,这种互存互动的关系一方面通过宗教文学和宗教艺术表现出来,另一方面又通过以宗教观念和神话故事为题材和思想背景的准宗教文学和准宗教艺术表现出来。宗教文学和宗教艺术,如基督宗教的圣经故事 (包括“雅歌”)和著名的圣彼得堡大教堂、我国的云冈石窟和敦煌壁画等无一不是以人格神或非人格神为中心的文学艺术,因而归根到底都是宗教文学化和艺术化的产物。相反,以宗教观念和宗教故事为题材和思想背景的准宗教文学和准宗教艺术则是文学和艺术的宗教化的产物。而作为文学和艺术宗教化的产物的所谓准宗教文学和准宗教艺术则明显地具有两重性品格。这就是:一方面,它既然以宗教观念和神话故事为题材和思想背景,则它就属于广义的宗教文学和宗教艺术的范畴,而有别于狭义的世俗文学和世俗艺术;另一方面这种文学和艺术尽管以宗教观念和神话故事为题材和思想背景,但就整部作品的宗旨来看,却分明具有世俗文学和世俗艺术的性质。例如,古希腊著名的“悲剧之父”埃斯库罗斯 (前 525—前 456)的名剧《被缚的普罗米修斯》虽然以古代希腊神话中的普罗米修斯的故事为题材,但是,整部戏剧所要弘扬的却是普罗米修斯不畏强暴、不屈不挠为人类的生存和进步而斗争的精神,它真正要颂扬的乃是当时雅典民主派反对寡头政治的斗争。再如,英国的近代诗人弥尔顿 (1608—1674)的《失乐园》和《复乐园》,虽然是以《旧约》的《创世记》卷和《新约》的《路加福音》卷中的神话故事为题材,但是,它们真正要颂扬的却是代表新兴资产阶级的革命者反抗王室贵族的斗争,是清教徒反抗长老派的斗争。我国著名的戏剧《目莲救母》虽然直接取材于佛教经典《佛说盂兰盆经》,但它真正要颂扬的却是我国世俗伦理道德中一个最根本的信条,即“孝道”。事实上,宗教与文学艺术,宗教文学和宗教艺术与世俗文学和世俗艺术也就是在这种既相互对立又互存互动的辩证关联中一步步向前发展的[3]158。
宗教对文学艺术的影响是极其广泛的。就艺术而言,可以说差不多所有的艺术形式都打上了宗教观念的烙印。例如,在绘画和雕塑方面,比较典型的有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拉斐尔的圣母像、古埃及的人面狮身雕塑,我国的敦煌壁画和永乐宫壁画以及龙门石窟、莫高窟、云冈石窟及泉州老子石雕坐像等;在舞蹈和音乐方面,在西方比较典型的有罗马教皇格里高利的“格里高利圣咏”、亨德尔的《弥赛亚》和贝多芬的《庄严弥撒曲》,在我国则有道教的“布罡踏斗”的“禹步”、《敦煌曲子词·谒金门》中的《仙境美》、茅山道士李会元的《大罗天曲》以及唐玄宗李隆基的《霓裳羽衣曲》和《紫微八卦舞》等;在建筑艺术方面,在西方比较典型的除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堂之一圣彼得堡大教堂外,哥特式建筑巴黎圣母院也别具一格,我国的佛教四大建筑群 (五台山、普陀山、峨眉山和九华山)更是中华民族为世界文明留下的宝贵的艺术遗产;在戏剧方面,除前面已经提到的《被缚的普罗米修斯》和《目莲救母》外,比较典型的还有古希腊悲剧作家索福克勒斯 (前 496—前 406)的《俄狄浦斯王》、古代印度著名戏剧家迦梨陀娑 (约公元 4—5世纪)的《沙恭达罗》、我国元代著名戏曲家马致远的《吕洞宾三醉岳阳楼》和《邯郸道醒悟黄粱梦》等。宗教对文学的发展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就诗歌来说,在西方,不仅《荷马史诗》受到了宗教的深刻影响,而且后来法国的英雄史诗《罗兰之歌》(1080年)、德国的英雄史诗《尼伯龙根之歌》(1200年)、意大利诗人但丁的《神曲》(约 1307年)也都是以宗教观念为思想背景的诗歌精品。在我国,古代诗歌集《诗经》中就有不少的祭祀诗歌和富于神话意味的诗歌;两汉以后,随着道教和中国佛教的出现和发展,道教的“游仙诗”和中国佛教的“禅意诗”都在诗歌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不仅涌现了一批像葛玄、吴猛、王梵志、寒山、拾得等著名的道士诗人和以偈为诗的诗僧,而且还涌现了一批像曹操、曹植、阮籍、嵇康、郭璞、李白、苏轼、王维等深受道教和佛教思想影响的在我国诗歌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诗人。宗教对小说的影响也同样是显而易见的。如所周知,西方的许多小说,如雨果的《悲惨世界》、托尔斯泰的《复活》等,都以这样那样的方式接受了宗教观念的深刻影响。在我国,魏晋时期曹丕(一说张华)的《列异传》和干宝的《搜神记》、明代吴承恩的《西游记》和陆西星道士的《封神演义》、清代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和曹雪芹的《红楼梦》(约 1790年)等都明显地渗透有道教、佛教和民间宗教信仰的内容。尽管宗教观念在许多时候对文学艺术的发展也起到了限制和压抑的消极作用,但是,总的来说宗教同文学艺术、宗教文学和宗教艺术同世俗文学和世俗艺术是伴生共长、互存互动的。宗教对文学艺术的影响是始终存在着的。
二、宗教对文学艺术精品的催生功能
宗教的文学艺术功能突出地表现在宗教对文学艺术精品的催生功能方面。在人类文学艺术史上,有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这就是,相当一部分文学艺术精品是由宗教催生出来的。
这一点在西方悲剧史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在谈到“何谓悲剧”这个话题时,英国文学评论家海伦·加德纳曾经给出了如下一个“定义”,开出了如下一个清单:“悲剧就是《俄狄浦斯王》、《安提戈涅》、《哈姆雷特》、《李尔王》或《费德尔》。”[3]7她接着解释说:“我们随即可以补充说,这样一个名单表明:‘悲剧’与其说是对某一文学种类的描述,不如说是一种尊称。在列这样一个名单时,我们只是在列举艺术杰作。‘伟大的悲剧’一说,其实是同义语反复,不‘伟大’的悲剧便不是悲剧,而只是‘失败了的悲剧’。”[3]7-8尽管我们可以对她的这个悲剧定义持保留意见,但是,无论如何还是不能否认,她所列举的这些悲剧是“艺术杰作”这个说法。然而,这些“艺术杰作”究竟是一种什么类型的“艺术杰作”呢?给出的答案是“宗教悲剧”(至少其中四部被她明确地界定为“宗教悲剧”)。索福克勒斯 (公元前 496?—406)的《俄狄浦斯王》(公元前 431年)被亚里士多德称作希腊悲剧的“典范”。这出悲剧讲的是俄狄浦斯一生都在反抗自己的命运,但是最终还是逃不脱自己弑父娶母的宿命。因此,它的主题是“命运”,是“事在神为”而不是“事在人为”,它所弘扬的是典型的希腊宗教精神。《安提戈涅》(公元前 441年)是索福克勒斯的另一部杰作。虽然其情节涉及的是俄狄浦斯的女儿安提戈涅反抗暴君这件事,但其主题却在于刻画宗教伦理(天法)与世俗法律(民法)的冲突。《哈姆雷特》(1601)是莎士比亚 (1564—1616)最重要的悲剧之一。该剧虽然从表面上看是一部“复仇剧”,但从其深层看则旨在昭示人的“原罪”。《李尔王》(1605年)的中心事件虽然看起来是围绕着“诚”与“伪”这样一种世俗道德展开的,但作者真正关心的则是“事物的神秘性,即‘这一不可知的世界所承受的所有沉重疲惫的负担’”[3]90。正因为如此,加德纳将《俄狄浦斯王》、《安提戈涅》、《哈姆雷特》和《李尔王》统称作“宗教悲剧”。它们之间的区别仅仅在于《俄狄浦斯王》和《安提戈涅》被她称作“希腊宗教悲剧”、“古代悲剧”或“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的悲剧”,《哈姆雷特》和《李尔王》则被她称作“莎士比亚悲剧”、“伊丽莎白时代的悲剧”或“17世纪的伦敦的悲剧”。无论如何,就其为“宗教悲剧”而言,一也。宗教悲剧在悲剧杰作中占有如此大的比例,不能不说是一个值得关注、值得深思的文学现象[3]136。
加德纳的难能之处在于:她不仅窥到了宗教悲剧在悲剧中的突出地位,而且还进一步深入地探究了宗教的悲剧功能,努力把宗教信仰、宗教观念和宗教情感理解为悲剧产生的重要动因。在她看来,希腊悲剧之所以能够产生出来,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 (如“社会状况”等),但是,古典时期“负罪文化”对荷马时期“羞耻文化”的取代,“负罪感”因此而“变成主要的宗教情感”无论如何是一项内在的原因[3]108。同样,“伊丽莎白时代的悲剧背后也有中世纪后期的宗教想象以及宗教思想和宗教信仰对罪孽、死亡和审判的日益增长的执着,它提供了龚布里奇(E.H.Gom b rich)教授所谓的‘先验图式’,伟大的艺术家们通过修正这个图式而探索着这个世界”。他还进一步解释说:“悲剧诗人的灵感,来自于对人类有能力理解历史经验之世界的信心,这和试图通过假说和实验来发现物质世界规律的精神是一致的。诗人的假说就是支配着他的时代的想象力的宗教观念。它们使他的想象力集中在他所处理的题材上并协助他编织情节。”[3]112她的这些判断至少可以在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中得到佐证。《哈姆雷特》虽然是一出典型的“复仇剧”,但却不是简单地以哈姆雷特的叔父为反方、以哈姆雷特为正方并且以正方最后战胜反方作为结局。《哈姆雷特》中没有魔鬼,但是自始自终都在展示“罪”、“恶”和“罚”,不仅双方在精心安排的情节中同归于尽,而且到最后把《圣经》中的“原罪”观念展现得淋漓尽致:随着剧情的展开,哈姆雷特不仅发现了他人的邪恶,而且发现并“揭露出他自己隐藏着的罪行”。离开了基督宗教的“负罪意识”,这样的剧情是永远不可能编织出来的。
宗教不仅对外国文学艺术精品有催生功能,而且对我国的文学艺术精品也同样有催生功能。众所周知,我国素有四大古典文学名著的说法。然而,这四大古典文学名著没有不以这样那样的形式与宗教有某种关联的。《西游记》的宗教性自不必言,即使其他三部古典文学名著也无不如此。就《红楼梦》而言,它的宗教色彩是相当鲜明的。人们常常拿《金瓶梅》与《红楼梦》作比,其实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言情小说。因为《红楼梦》的思想性和宗教性不仅为《金瓶梅》所缺乏,而且也为我国相当一部分文学作品所缺乏。《红楼梦》的宗教色彩不仅表现在剧中有作为癞和尚的跛足道人、亦道亦佛的空空道人、身在栊翠庵的妙玉和佛在嘴边的刘姥姥,也不仅仅表现在其中有一首《好了歌》,更重要的是在于它的根本旨趣和基本结构都是奠放在宗教观念和宗教情感上面的。只有从后面这个角度来思考问题,作者对《红楼梦》全书情节的处理以及其对众多人物命运的安排才能够得到合理的解释,读者才能透过“满纸荒唐言”觉解作者对人生和社会的深层思考和内心的“辛酸”,进而觉解作品的巧妙构思和真实“意味”,才能成为曹雪芹心中的合格读者。换言之,《红楼梦》自清代乾隆年间问世以来,差不多一直是最受读者欢迎的中国古典文学著作,其根本的原因也正在于它的这样一种思想性和宗教性。《水浒传》和《三国演义》的情况虽然有别于《红楼梦》和《西游记》,但是,宗教对于它们的影响也还是存在的。例如,《水浒传》虽然写的主要是农民起义,但是既然其第一回的标题为“张天师祈禳瘟疫,洪太尉误走妖魔”,而最后一回的标题为“宋公明神聚蓼儿洼,徽宗帝梦游梁山泊”,它的整个故事情节也就被置放进了“神魔小说”的框架之中了。更何况它的“三十六员天罡下临凡世,七十二座地煞星降在人间,哄动宋国乾坤,闹遍赵家社稷”的说法以及梁山起义的主题口号“替天行道”等,都具有浓厚的宗教意蕴。至于《三国演义》,虽然属于较为纯粹的历史演义小说类型,但是既然在第一回里就提到了“太平道人”张角领导的农民起义,我们就不能说它一点宗教气息也没有。更何况“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既是《三国演义》的卷首语 (第一回第一节),又是《三国演义》的结束语(第一百二十回最后一节),这与我们在希腊宗教悲剧《俄狄浦斯王》中所看到的“事在神为”或“命运”观几乎毫无二致。由此看来,宗教对文学艺术精品的催生在人类文学艺术史上是一种较为普遍的文化现象。
三、宗教对文学艺术人才的塑造功能
宗教的文学艺术功能还表现在宗教对文学艺术人才的塑造方面。
莎士比亚有“人类文学奥林匹斯山上的宙斯”之称,无疑是人类文学史上最伟大的文学天才之一,但是,莎士比亚同时也是一个宗教情结很重的文学家。我们这样说并不只是因为他出生在一个宗教家庭,出生后即在家乡斯特拉福镇的圣三一教堂受洗入教,死后又葬在其家乡教堂的墓地之中,而是因为他的作品到处流露出来的宗教内容、宗教情绪和宗教气氛。人们曾根据其作品中“具有大量《圣经》引证和语录”这一点断言:莎士比亚对《圣经》“了如指掌”,“比他同时代的大多数剧作家对《圣经》都精通得多”。人们甚至吃惊地发现,莎士比亚不仅熟悉英语版《圣经》,而且对日内瓦版本的《圣经》也很熟悉。而后者是“人们在家里阅读而不是在教堂里被指定阅读的那种版本”。据说,“一位神学家在仔细考察了剧中出现的明显的神学隐喻之后”宣称,“莎士比亚对当时的神学概念很熟悉,因为不管他是严肃地或是戏谑地引用某个神学概念时,他都对之理解得十分正确”。据此,《莎士比亚与基督宗教教义》的作者费赖 (Ro land M ushat Frye)称莎士比亚不仅熟悉《圣经》,而且还“精通神学”[3]71。如果说我们从莎士比亚的作品中看到的是莎士比亚对《圣经》的“熟悉”和对基督宗教神学的“精通”,则在对莎士比亚的作品的进一步考察中,我们就将发现正是莎士比亚对《圣经》的“熟悉”和对基督宗教神学的“精通”不仅铸就了他的作品的伟大,而且也铸就了他之作为作家的伟大。加德纳曾结合《哈姆雷特》非常中肯地写到:“莎士比亚戏剧的确以最为优美动人的形式表现了显然是基督宗教的观念,而在我看来,伊丽莎白时代的其他剧作家都没有做到这一点。”[1]73她还结合《哈姆雷特》的剧情具体而深入地指出:“我认为,除了他,没有任何一个剧作家对宽恕这一基督宗教基本观念有如此充满想象力的理解并如此令人难忘地表现了这一主题。……莎士比亚是描写人类本性的最伟大的诗人,因而我只能这样说:如果他的剧中需要一个以基督宗教徒身份说话的人物,那他就会以其独特的理解力和同情心富有想象力地进入基督宗教徒的体验和情感之中”[3]73。
如果说是基督宗教铸就了莎士比亚的话,则曹雪芹便是由中国宗教铸造出来的。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对曹雪芹如何修习佛学的事迹,除了他的朋友张宜泉留下的《和曹雪芹 <西郊信步憩废寺 >原韵》表明他曾游过广泉寺外,我们几乎一无所知,但是,既然他在《红楼梦》中以“情僧”自许,称《石头记》为《情僧录》,既然他以“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为《红楼梦》的主要旨趣,既然他强调他之所以在《红楼梦》中“用‘梦’用‘幻’等字”,“是提醒阅者眼目,亦是此书立意本旨”(《红楼梦》第一回),则佛教观念、佛教情感和佛教意境对于他的内在性和实存性,就是一件不言而喻的事情了。离开了佛教观念和佛教情感,不仅作为《情僧录》的《红楼梦》不可设想,而且作为“情僧”的曹雪芹也同样不可设想[4]132-133。
宗教对于文学艺术家之所以如此重要,最根本的就在于宗教具有提升文学艺术家人生境界和文学艺术境界的特殊功能。文学艺术作品固然要来于社会生活,但是文学艺术作品之为文学艺术作品,最根本的乃在于它之高于社会生活。因此,一个文学家艺术家要创造出文学艺术精品,除学养外,最根本的就是要具有超越社会生活的人生境界和文学艺术境界。中国近代文学家王国维 (1877-1927)在其《人间词话》中曾提出过著名的“境界说”,断言:“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5]1这是很有见地的。他还进而将境界区分为两种:“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而所谓“无我之境”,其实是一种“以物观物”之境,一种“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物我两忘”或“物我浑然一体”之境,一种“出乎其外”之境,一种舍之作品即不可能“宏壮”、“雅量高致”之境,一种舍之作品即便有“貌”也不可能有“神”之境,一种“豪杰之士能自树立”之境[5]2、3、29、37。然而,不难看出,王国维所说的这种“无我之境”,说到底,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宗教之境”。王国维非常欣赏苏轼,说苏轼的作品“雅量高致”,“有伯夷、柳下惠之风”[5]29,可见他所欣赏的正是苏轼的“超然物外”的宗教意境,亦即苏轼所说的那样一种“身在山外”或青原惟信所说的“山还是山”的禅境。一个文学艺术家一旦有了这样一种人生境界和文学艺术境界,他就势必具有一种超乎寻常的“宗教想象力”,他的作品也就势必因此而“自成高格”,“跌宕昭彰,独超众类”。我国宋代诗人苏轼如此,英国剧作家莎士比亚如此,清代小说家曹雪芹亦复如此。
在讨论宗教的文学艺术功能时,下面几点是需要特别注意的。首先,我们这里所说的“宗教”,所意指的并非是一种偏执的宗教信仰和神学理论,而是一种宗教精神和人生境界,一种宗教想象力。我们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强调宗教文学艺术功能的普适性的。一如加德纳在《宗教与文学》一书的结尾处所说:“在每个时代之中,诗人们都根据那个时代的力量和局限,在人生的众多形象之中,展示了人作为一种能进行宗教崇拜的动物的形象,从而找到了种种方式来丰富我们的想象。”[3]219其次,偏执的宗教信仰和神学理论非但不能铸就文学艺术精品,反而使文学家和艺术家常常处于一种“带着镣铐写作”的状态[3]147,从而即使有所成就,也只能生产出一些二流,乃至末流的作品。第三,尽管在许多时候,在许多领域,宗教都发挥了积极的铸就文学艺术精品和文学艺术人才的功能,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从整体上讲,在文学艺术史上,宗教的推动作用和铸造功能还是第二位的。根本否认宗教的文学艺术功能是片面的和不可取的,无限夸大宗教的文学艺术功能也同样是片面的和不可取的。
[1]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文集》第 3卷,许良英、赵中立、张宣三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77年版。
[2]约翰·希克:《宗教之解释——人类对超越者的回应》,王志成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8年版。
[3]伦·加德纳:《宗教与文学》,沈弘、江先春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1年版。
[4]吴恩裕:《有关曹雪芹十种》,北京:中华书局 1963年版。
[5]王国维:《人间词话》,徐调孚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
责任编辑 吴兰丽
On the Function s of Religion s to Literature and Art
DUAN De-zhi
(School of Philosophy,Wuhan University,Wuhan 430072,China)
Proceeding with the affinity of religion with literature and art,and making historical expositions of their in ter-dependence,this paper interprets stressfully the function of midwifery to the excellent products of literature and art,and the function of shaping to the talents of literature and art.
religion;literature and art;function of midwifery;function of shaping
段德智(1945-),男,河南辉县人,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西方哲学和宗教学。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 (09JZD 0004)
2010-12-06
B925
A
1671-7023(2011)01-0016-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