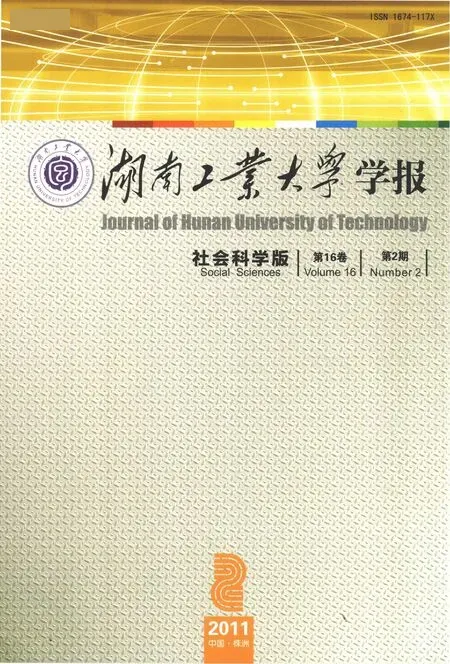烟尘弥漫的精神寻根之旅*
——关于肖仁福的长篇历史小说《汉人》
2011-04-07李红霞
李红霞
(绍兴文理学院教育学院,浙江绍兴312000)
烟尘弥漫的精神寻根之旅*
——关于肖仁福的长篇历史小说《汉人》
李红霞
(绍兴文理学院教育学院,浙江绍兴312000)
《汉人》是湘籍作家肖仁福的最新力作,作品寄托了作者向历史更深处追溯民族精神之根的愿望,流露出悠远沧桑感,是更深入地贯彻其“民间”立场的一种尝试。作品除对官场文化予以富有在场感的辛辣描摹,同时,其写作初衷与文本实况的背离、历史记忆和文学书写的分寸把握等,都体现出以“民间”为精神资源的当代官场、历史小说写作的某种实存状态。
肖仁福;《汉人》;历史小说;民间立场;官场文化
Abstract:Han Ren is the latest masterpiece of Hunan writer XIAO Renfu.It not only reflects the writer’s hope of seeking the root of national spirit deep into the history,but also reveals the his expectation of enhancing the level of his works with the form of historical novels which are full of vicissitudes,and it’s also an attempt to carry out his folk standpoint.The novel gives a vivid description of officialdom with bitter sarcasm.At the same time,the deviation between its writing intention and text,the uncertainty of historical memory and literature writing,both reflect the true status of modern officialdom novels and historical novels,which take“folk”as its spiritual resource .
Key words:XIAO Renfu;Han Ren;historical novel;folk standpoint;officialdom
《汉人》是湘籍作家肖仁福的最新力作,小说出版后引起了读者的广泛关注,人们对其中表现出的民间立场与官场文化的交融有着浓厚的兴趣。本文试图对《汉人》所表现的精神寻根进行探究,从而廓清此前关于作品的种种争论。
一 “民间”的尴尬:写作意图与文本实况的背离
《汉人》改写自《汉书·霍光传》,勾勒一代“明相”霍光的人生历程,在保持《霍光传》整体结构框架和主要事件的前提下于细部上辅以相当的虚构,一定程度上属于“故事新编”。“新编”往往天生反骨,证明了文学并非“被动诠释、反映特殊时空的意识形态”,相反,是“冲突和差异的发生地,价值和概念、信念和偏见、知识和社会结构的寓所”,而“所有这些可以清楚阐述历史自身的意识形态的复杂构成物,会在其中产生且最后被改变”。[1]所以,揭示、强化这些饱含内心欲望的冲突和差异是“新编”的重要价值所在,由此对构成“历史自身的意识形态性的复杂构成物”予以一定的破解和改变。肖仁福本身也是怀着类似抱负的——他张扬起“民间”的旗帜,对曾在国内批评界引起巨大争议的“民间立场”进行了个人化诠释:“说到作家的民间立场,我觉得不仅跟创作题材有关,更重要的还在于作家对生活的理解。……我描写了几股力量的抗衡:民与官,小与大,弱与强,贫与富。抗衡的结果是不言而喻的,更是宿命的,我无能为力。我唯一能做的就是通过对这几股力量的叙述,给读者呈现一幅复杂的世态图,供人思考。”[2]揭示将个体裹挟其中的类似漩涡的潜在规则或无意识运作模式,即所谓无人能从其遏制下幸免的“宿命”力量,叙述各力量间的对峙,呈现“复杂的世态图”,彰显“新编”的价值。
湖湘文化中始终弥漫着忠君爱国、忧国忧民情结,同时楚文化的浪漫激昂又赋予湘人以世代绵延的血性和激情。两种精神特质一旦结合,即催生出近代湘人浓厚的入世心态,突出体现为强烈的政治情结,进而拓展演化为一种社会心理,使其文化气质中焕发“敢为天下先”、“舍我其谁”的激情、豪情,从而与儒家文化在经世致用方面有其一致之处,却又独具特色。肖仁福的上述“民间”立场里显然是渗透着这种浩然正气和理想主义色彩的。他将笔触伸向历史,书写汉人之魂,是更深入地贯彻他的“民间”立场的一种努力。这种对民间力量的期待并非抽象的理想,而是来自他作为湘籍作家对湘人强悍野性、勇武雄强的地域性格的自觉意识以及酣畅表达的愿望。
从作家拓展创作视域、寻求更广袤的文化伸展空间这一角度看,《汉人》寄托了作者一种向历史更深处追溯民族精神之根的愿望,一种以浸润着古韵和悠远沧桑之感的历史小说形式提升自己作品层次的期待。这对于一位作家的成长成熟而言当然是顺理成章的,处理得好的话,会成为其创作历程的里程碑或者转折点,更何况肖仁福是怀着精神上的焦灼不安进行这种拓展的——他心怀着一种“做不牢”汉人的惶恐不安来写《汉人》:“霍光创造了昭宣辉煌,让咱们昂首挺胸。做定了汉人,做牢了汉人,霍光家族却再没机会做汉人,这是件多么让人惶恐不安的事情!我就是因为惶恐,因为不安,才走近霍光,走进历史深处,着手写这部历史小说”,“认准自己是汉人,咱们也就全盘接受了汉朝,一劳永逸地享用着汉朝设定的伦理规范、道德标准、政治理念、经济形态、生活方式,乃至一切行为准则。从此咱们的思维习惯再没改变过方向,心智和心理渐成定势。从此咱们便没法也没想过要走出汉朝,……汉朝没有远去,汉朝如影随行,跟咱们一路走来,咱们从前是汉人,现在是汉人,今后还会继续是汉人。”[3]从肖仁福的以往作品(如《官运》)来看,他对儒家正统的价值理念、行为规范、内在矛盾等已心生幻灭感,读者自然以为在《汉人》中即将看到对汉代所奠定的儒家主流价值观、行为规范等进行的深邃反思,一场宏阔的精神寻根之旅即将展开,要表现的“世态图”该有多么复杂、微妙和曲折!这种猜想与期待颇振奋人心。
令人始料不及的是,这次寻根之旅却最终落得枝杈分出,烟尘迷离,不知所踪。作家个体性情与写作对象间存在互相制约的关系,需要具有某种内在的精神契合,才能一荣俱荣,而以与儒家文化气质有别的湖湘文化激情、豪情去描写齐鲁文化背景下的政治人情物态,不免有点一厢情愿、理念先行,抛错了媚眼,表错了情——《霍光传》做为故事原型与勾勒“复杂的世态图”这一写作初衷间显然存在着内在冲突,因做为头号正面人物的霍光大权独揽处于绝对优势地位,“官与民”等几股力量的对峙在这个故事中基本无法获得展开和表现,削弱了文本的张力,“世态图”的复杂性因此减弱。霍光做为市井百姓却能凭借才干和机遇打破尊卑界限,闯入宫廷指点江山。为了坐稳位置,他的不少思想言行恰恰体现了中国文化中官民思维的某种同构性,而与肖仁福逐渐产生的对官场所需清新“侠义之气”[4]的期待其实并不切合。这些因素使得《汉人》的写作意图与文本面貌形成了巨大背离,生发出强烈的反讽意味,硬生生把两者之间的裂缝予以弥合,并未能使得“民间”立场获得更为深广的体现,反而流露出某种游移。
且不说做为群像的百姓在《汉人》中的出场只是惊鸿一瞥,而且似乎并非“看到了自身的价值,胆敢与命运抗争,胆敢颠覆不公平的社会和制度”,他们中的少数像《官运》中郭三、郭宝田那样具有血气和正义感,但这种正义感和血性在为魏相请愿的过程中却遭到被遛狗一般耍得团团转的命运,悲剧性地成为被无意识地煽动的愚民。伴随“民间”的彻底溃败,民间理想主义也无从寄身。至于官场各色人等在权力欲、虚荣心的驱使下前恭后据、蝇营狗苟的言行更是毫不足以做为精神归宿。真正能将其打破的是新的气质,而非“明相”的个人英雄主义悲壮坚守,更何况事实已证明“明相”并不靠谱——对霍光形象正面性格的塑造基本较为模式化。该人物真正引人深思和哂笑的,是作者以一贯擅长的嘲讽视角斜睨着官场心态描写——勾心斗角的老辣,才干过人而无法摆脱光宗耀祖思想的束缚以及身为将相,子弟封侯的传统。但作者嘲讽归嘲讽,整体上依然给予赞誉有加的待遇,他“神态安详,从容镇定。目光温和慈善,却分明透露着坚毅果敢”。[5]肖仁福以往作品中遭到质疑、嘲讽乃至幻灭的儒生形象在这里似乎又重新获得了推崇,但这种推崇终究因作品营造出的官场内外恶性循环式的人性溃烂而底气不足。
鲁迅曾把中国语境分为“坐稳了奴隶的时代”和“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6]霍氏家族最终遭到灭族而无法平安做“汉人”不假,但仍有很多人继续其一代代的卑微生存,所以引起肖仁福“坐不稳汉人”的“惶恐不安”到底源自何处?做“汉人”的标准是什么?复杂的世态图在作品中已不知不觉演变成为官场内部的倾轧实况展示,打破恶劣文化生态的愿望消融在世世代代以做明相、愚民、顺民来捍卫“汉人”地位的梦想中。肖仁福在这里所说的“咱们”又到底是谁?而“咱们”若坐稳了“汉人”真就那么荣光?“坐不稳“汉人”真就至于让人寝食难安?放弃个性化的独立审视思考,缺乏对民族精神的反省与提升,错失了以文学进行文化批判的可能性,而对出身百姓并回馈百姓的“明相”寄托理想,或对本不足以撑起精神归宿局面的所谓“民间”怀抱期待,都只能获得“宿命”的溃败吧!这次寻根之旅于是最终不了了之。
二 一地鸡毛:“民间”视野下的“汉人”生活
《汉人》封面上提及该著具有“文学笔法、史家深度”,做为历史小说,历史记忆和文学书写的分寸处理确实是需要面对的大问题。
《汉人》系以今人心叙古人事,其“新”首先体现在淡化历史事件而重在描写人性人心——虽意在写霍光,但除对几次君主更替经过详写外,对霍光那些名垂史册的政绩多用套话空话泛泛带过,如“对外进一步密切与周边国家的联系,创造良好国际环境;对内继续采取休养生息政策,发展生产力,富国强民”等,而重在描写活动于其中的人物,尤其重在描写驱使他们上蹿下跳的权利欲上。其次,以现代俏皮语言讲述故事,在基本不损毁霍光冷静、端庄、老辣性格特征的前提下以庄谐并出的情节打通尊卑贵贱、古今时空的隔阂,使严肃正经的名臣名将拥有了平常人的喜怒哀乐,又使端庄矜持的历史人物具有了普通人的世俗欲望。比如霍光在朝廷安危的关键时刻,冷静、果断地帮助昭帝粉碎了上官桀等人政变的阴谋,保持了西汉王朝的稳定和政策的连续性。作品给这段实有其事的历史添加了颇富戏谑色彩的虚构,平定叛乱后任用无德无才的王欣得以升任御史大夫,只因他会揣摩领导心思,为年迈的霍光送去了壮阳药,尤其令人哭笑不得。
《霍光传》的故事原型和呈现“复杂世态图”的创作初衷间存在冲突,从而妨碍了对世态复杂性的深入描摹,而从文学立场而言,“民间”立场本身也妨碍了《汉人》的写作境界的拓展。“所谓‘民间立场’的提出,实际上体现了当今学术界这样一种深层意识:在文学理论和批评中,人们总是试图寻找一种群体观念形态的支持,也许这种观念形态过去称之为‘人民大众’或‘革命’,如今变成了‘民间立场’。当然,有了这种群体意识的保护,文学自然安全多了,但它的个性却被一种无形的意识形态吞没了。”就创作者的精神立场而言,背后有几亿人做为“民间”为之撑腰,凭借这种安全感,作者获得了被大多数人承认的道德优越感,但文学本身不买道德的账,它追求的是站在自己的位置,以勾魂摄魄、玲珑通透的文字描摹深邃的人性。就创作结果而言,融入并依峙“民间”往往就意味着文学自身独立性的幻灭,从而导致写作境界的停滞,突出体现在对人性人情表现上的粗疏和叙事上的某些遗憾。
《汉人》过于注重“以古讽今”、古今对话,从而不惜对人物心灵予以较逼仄的表现,因此充满峻急的气息,而少了回味。这种逼仄突出表现在人物灵魂的缺失和整体情怀上悲悯意味的淡薄。首先,人性深度尚待发掘,体现出灵魂的缺失。作品最富意趣、最出彩处其实并不体现在对“汉人”精神传统的勾勒,也不是对史书所载霍光生平的文学化润色,更非有意于文体实验,而是作者对自己以往写作擅长处的继续发扬,即从细部上对各色人等之权力欲以及奴性心理的描摹,从而构成了一幅“乱纷纷你方唱罢我登场”的群丑图。人物完全被进行了扁平化处理,而非拥有多种性格侧面的立体性个体,他们人生的主轴似乎就是权力欲,为此不惜一切。而官场中人特别容易遭遇的个人道德、主观愿望和实际行为之间的剧烈冲撞未能获得深入表现。霍光这一“光彩照人”的中心人物形象,似乎没有任何个人化的内心事件,比如他没有标志性的小动作、对事物的偏好,他的精神没有成长转变的过程,没有回忆、也不期待,而基本上是一个权力运作和世俗功利性思维的工具、官场理念的载体,一台毫无情趣的政治机器。其次,因温情和悲悯感的淡薄而洋溢着虚无气息。牵引故事演进的线索基本依史书所载对霍光身世的顺时序叙述,且篇幅较长,叙事因而显得有些松散冗长。作品里所有的男女都沉溺于暗无天日的一滩泥沼之中庸庸碌碌地来去,对置身其中的荒诞氛围都没有反省。他们的退场或死亡基本上不具任何悲怆色彩和反省意味,而只是为另一人物登上权力斗争舞台做铺垫。人物生命中最富有魅力的爱欲生死在作品中的表现都乏善可陈,具有一种中国式的世俗和无聊感。为使霍光形象有点人情味而增加了对他私生活的描写,但这些情景不过更突显了他精神世界完全受功利欲望驱使而情趣索然的政治动物面目。话说对当下的批判再辛辣再入骨,倘没有一个理想的远景、一种温情的抚触,那批判就找不到归宿,陷入虚无之境。而倘若汉代政通人和、人民安居乐业,但是没有灵魂,缺乏温情和意趣,成为躯体活动而精神僵死的躯壳,这样的“汉人”做着还有什么意思?!
不妨大胆揣测,霍光、“汉人”、“民间”立场几者之间似乎需要某种更形象有力的衔接或者分离:倘若要以民族主义视角写汉人精神,就将他们作为特定文化社会人的各种人格侧面予以血肉丰满的描摹,表现其“伦理规范、道德标准、政治理念、经济形态、生活方式,乃至一切行为准则”;倘要写霍光,就写他作为一介儒生的心灵活动乃至挣扎,而无须让这么单薄的人物担当“汉人”代表,因为作为政治人物的才干并不意味着他的内心深度适合做为长篇小说的主人公,而作品又没有要打破史书框架另起炉灶完全“新编”的意思。结果,摒除了汉代历史文化特征的具体事物的描摹,人物生活处于一种真空背景状态,勾勒各个朝代普遍存在的血雨腥风的权力斗争一景获得了,但汉代人特有的文化心理基本未能获得表现。以一出戏剧来比喻的话,布景宏阔无比,但道具准备并不充分,上场人物仿佛临时拉来凑数的群众演员,举手投足充满寒酸味道,且出语莽撞,在当代题材作品中本显得较机智俏皮的语言等用在此处,被削弱了遥望历史所感觉到的悲怆感,与时代氛围不符,难以胜任追溯“民族集体记忆”或精神之根的能指重任。作家的创作性情与创作对象之间存在的相互制约关系,再一次发出自己的声音,而“民间”立场在文学创作中的限度也得以呈现。
[1]吴秀明,尹 凡.“新故事新编”:当代历史题材小说的另类写作[J].学习与探索,2006(6).
[2]聂 茂,肖仁福.民间立场的书写理由[J].芙蓉,2007(3).
[3]肖仁福.汉人[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281.
[4]龙其林.侠义文化精神与肖仁福小说[J].当代文坛,2010(2).
[5]鲁 迅.华盖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40.
[6]汤奇云.质疑“民间立场”[J].文艺争鸣,2000(2).
责任编辑:李 珂
A Tour Seeking Spiritual Root——On XIAO Renfu’s Long Historical Novel Han Ren
LI Hongxia
(Education College,Shaoxing University,Shaoxing,Zhejiang 312000)
I206.7
A
1674-117X(2011)02-0079-04
2010-10-10
李红霞(1978-),女,河北保定人,绍兴文理学院教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