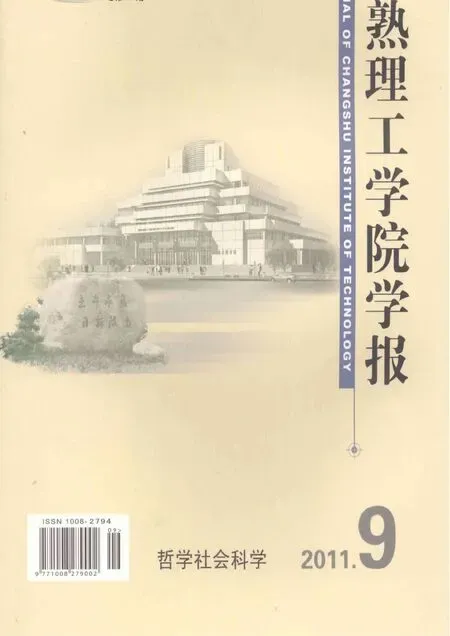殷次伊与清末常熟新学界
2011-04-02沈潜
沈潜
(常熟理工学院人文学院,江苏常熟 215500)
殷次伊与清末常熟新学界
沈潜
(常熟理工学院人文学院,江苏常熟 215500)
生逢20世纪初社会急剧变革时代的殷次伊,怀抱济世宏图,从追求新知新学、投身家乡教育的革新事业,到不惜舍身一死以图唤醒同胞,充任了除旧布新的时代吹鼓手,自觉肩负起历史赋予的责任担当。以殷次伊为代表的清末常熟新学界所表现出的“新机怒发”,与故乡毗邻上海的地缘优势及地域人文传统有着重要的关联。
殷次伊;辛亥革命;南洋公学;爱国学社;常熟新学界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历史转型期,以上海为中心的东南地区爱国民主运动蔚然勃兴。在此特定的历史舞台上,来自古城常熟的一批学界中人,以交相推引、各有声光的努力,演绎了一幅光彩夺目的生动画面,留下了一组光彩照人的生动形象。青年才俊殷次伊(1878-1903),就是其中一位充满悲情色彩的佼佼者。也是迄今记录人文常熟的读本中几乎被遗忘了的人物。本文缀合相关资料敷演成篇,以补史之阙。通过勾勒其生平事略,以期从一个侧面窥探辛亥革命时期常熟学界“新机怒发”[1]的历史动向和现实场景。
一
殷次伊,字潜溪,号同甫,又名崇亮,①参见《常昭学界之实况》,载《时报》第79期,1904年8月29日。另按:蔡元培在《记三十六年以前之南洋公学特班》有“殷祖同,字志伊”的说法,概为回忆有误。参阅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7集,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66页。1878年(清同治四年)出生于常熟城区。时代与环境的剧变冲击,使少年时的殷次伊就慷慨以天下为己任,有着独立不羁的性格。1894年(光绪二十四年)甲午战争前后,殷次伊曾游学燕蓟一带,因为目击时艰,愤世嫉俗,于是奋发自勉,一度东渡日本学习文理法政。戊戌变法期间,他与邑中名士丁祖荫(1871-1930)、徐念慈(1875-1908)、曾朴(1872-1935)、张鸿(1867-1941)等人声气相通,引为志趣相投的挚友。这些处于历史转型期的文人士子,为维新思潮所激荡,热心教育、鼓吹革新,成为常熟一地颇有声光的新派人物。
1897年,为追慕时尚,倡导新知新学,殷次伊和丁祖荫、徐念慈、张鸿等一起,冲破地方守旧势力的阻挠,在塔前别峰庵创立中西学社,首开常熟学界办学之新风。第二年学社迁入学爱精庐,改名为中西蒙学堂,又在原有基础上加以扩充,两年后改为中西学堂,1902年改称常昭公立高等小学堂,扩充别峰庵、武庙园址为校舍。面对办学经费上的匮乏,“种种改良之事业,集于数经理之身。”[2]殷次伊不遗余力,“疏其财,急公益,所得泽资,悉投学界恐不足。”有人为此戏语相问:“子之施债,无还期乎?”他却慨然相答:“不,吾国独立之日,即吾债偿还之日也。”[1]从殷次伊热心桑梓教育事业的追求中,不难看出他爱乡爱国的深厚情感。
据1903年《江苏》杂志第4期刊登的《常熟学界调查报告》称:这一年的公立小学校,经逐年扩张改良,已分为甲、乙、丙、丁班授课,另设师范班,程度在中学、小学之间,并附设女学校一所。一时前来报名学习的接踵而至,全校学生以公德相激励,教师以扶植自由、养成国民资格为义务。体育部则为培养学生尚武精神,开始实行早晚训练。[2]据1904年7月6日《时报》第25号所载《常熟学界之现状》记述,当时该校有教师5人、经理2人,监起居1人,学生20多人。学制分寻常、高等班,设伦理、国文、历史、地理、体操、习字、画图、算学、政治、经济、生理等课程。[3]8月29日《时报》第79号又有《常昭学界之实况》称公立小学校为常熟学界“最完全”的学校[4]。虽说当时学校规模不大、学生不多,女孩子上学更是凤毛麟角;但有办学新风的率先倡导,从书院到学堂的递嬗,使言子故里呈现出了新陈代谢的历史性转换。来自古城小巷里的朗朗书声,正隐含着求变趋新的应时转向,预示了一代新型学生群的应运化育。
1901年,“鉴于学界纷呶,非合群不足以谋公益”的考虑,常熟新学界人士组织教学同盟会,创教育救国、群治进化之说,[5]参加者皆邑内开明士绅,宗旨在于“组织学界同盟,为国民同盟之基础。”[1]会员分名誉会员和通常会员二种,并由会员公举总理、常议员、干事员等。据1903年3月23日《苏报》所刊《常熟敎学同盟会会员题名单》,该组织中,徐念慈任总理,曾朴为副部理,殷次伊与丁祖荫、朱积熙、张鸿兼任常议员。[6]身为常议员的殷次伊积极参与领导和组织工作,使“会律井井,秩序巩固,俨然一国会之具体。”丁祖荫事后回忆:“吾虞教育之机关,自此嚆矢”,一时隶名入会者达百余人。[5]1903年2月,教学同盟会还在寺前街的海虞图书馆创立了城西小学校,作为“普及教育之起点”,学校设有藏书楼和阅报处;同时倡办师范研究讲习会、开智会、通学会、体育会,以研究教育、开启民智,实行改革为宗旨。当年教学同盟会有成员47人,其中7人后来成为江苏教育总会的第一年入会会员。当然,这一吐纳时代精神的举动,与地方因循守旧人士适成鲜明对比,新旧抵牾势所难免:“常熟社会之现状,止有此点,而同志冲突当事压制之恶现象,且日现于会场中”[2]。新旧较量的抗衡中,他们依旧坚守着自己的决心、耐心,成为引领近代常熟新学界的先驱。诚如论者指出:围绕自戊戌开办的塔后小学的改良,逐渐形成了一个以曾朴、丁祖荫、殷次伊、徐念慈、徐宗鉴等新式士绅为中心的地方教育界。[7]211
1902年春,蔡元培和上海一批教育界进步人士,如黄宗仰、蒋智由、叶瀚、林獬、王季同、汪德渊等共同发起成立了中国教育会,认为“革命精神所在,无论其为男为女,均应提倡,而以教育为根本。”[8]7昭示了旨在教育救国、昌言革命的新型社会力量之崛起。为响应新成立的中国教育会,殷次伊、丁祖荫、徐念慈等人将此前的教学同盟会及时改组为中国教育会常熟支部,以此扩大影响。公立小学校的教育改革实践,也随之贯彻了中国教育会造就爱国思想、尚武精神等新国民教育的办学理念。殷次伊胞兄殷崇宽在事隔三十年后曾经追忆:“忆当庚子、辛丑间,海上始昌言革命,吾弟次伊从蔡君鹤卿(笔者按:蔡元培)、章君太炎及山僧(笔者按:宗仰上人)游,亦以贯输革命思想为己任,创设敎学同盟会于吾邑,与海上诸志士声气相应求,常往来苏沪间。”[9]
二
1901年初秋,在家人的资助下,意气风发的殷次伊考入了南洋公学(今上海交通大学前身)特班学习。
南洋公学,位于上海徐家汇虹桥路东端(今广元西路)、海格路(今华山路)的交叉口。原是1896年由清末政治实业家盛宣怀创办的大学,先后开设师范院(师范学堂)、上院(大学堂)、中院(中学堂)和外院(附属小学堂)四部。1901年9月增设特班,录取擅长古文、具有旧学素养又有志西学的学生。特班课程分前后两期:初级功课为英文、算学、格致化学;高等功课除进一步学习格致化学外,兼习地志、史学、政治学、理财学、名学,同时要求学生博览有关中外政治书籍,旨在培养通达中外时务的新式从政人才。当年5月特班举行招生考试,考试分初试、复试,每个阶段包括笔试和口试。笔试考国文,既有出自《四库全书》的晦涩试题,也有应世之策的时事考题。殷次伊在顺利通过招考的各个环节后被录取。
蔡元培当时兼任特班总教习(班主任),他倡导学生自由阅读,重视师生之间的切磋交流。在具体教学上,由他先召集每个学生面谈,然后开列可供选学门类和每门必读书目,每人选一、二门,参照书目次序借阅。学生必须每天写读书札记交给他,隔一、二天经他阅后写上批语发还。每月有一次命题作文,题材不限,让学生各抒己见。晚间轮流约见二三位学生谈话,此外还鼓励学生成立“演说会”学习日语等。蔡元培在课堂教学、课外谈话和作业评语中向学生灌输爱国思想和民主理念,要求学生关心国内外形势,学习西方新知识,并以此引导社会、唤醒民众。这一忧国忧民的情怀、谦和亲切的态度,无疑有助于特班学生成为新知新学新思想的带头人。
在特班招收的42名学生①另有学者据《南洋公学特班学生月课积分表》认为特班生有35名。参见张学继著《出版巨擘:张元济传》,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中,殷次伊与来自上海川沙的黄炎培、四川乐至的谢无量、福建福州的王世澂、江苏苏州的贝寿同、天津的李叔同、浙江绍兴的邵力子、吴兴的胡仁源、慈溪的洪允祥、瑞安的项骧等同窗,他们无疑都是蔡元培眼里的高才生。据蔡元培当年日记手稿中的一份特班生月课表,殷次伊的成绩位居第12名。蔡元培称他“富革命思想,善为文。”②参见蔡元培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1902年2月7日)的日记手稿。转引自蔡建国《蔡元培与近代中国》,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第52页。在校一年半的时间,殷次伊深受爱国热力的启发和鼓励,他积极运动教习,组织以爱国为宗旨的演说会,要求广大学生“惟现在之国不必爱,而未来之国良可爱也;老大帝国奚足爱,新中国则必爱”。[10]倡导自由民权,持论激烈,成为政治宣传的积极分子,也促进了学校青年学生中革命思想的滋长。
但是,由于学校自开办以后,管理上素来专制,对待学生毫无民主可言,“以压制缚束为威力,以用人派事为市恩,以排斥新书匿己短,以艰深旧学炫己长;以苛责细故为讲求实际,以管束学生为门面排场”[10]的种种腐败现象,在趋新求变的学生中早已积怨至深。至1902年11月爆发了因校方压迫学生而引起的200多名学生集体退学风潮(即墨水瓶风潮),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事后,殷次伊与何靡施、穆藕初、胡敦复、俞子夷、贝寿同等被推举为全校退学生代表,与校方交涉。1902年《新民丛报》第21号上刊有一篇《南洋公学学生出学始末汇记》的文章,就署名为“代表人:贝寿同、殷崇亮等公启”。文章在详细说明了此次学潮始末后写道:“夫我国学校专制之轭,实我学生社会之公敌,曾无有起反动之抵抗者。大陆专制国,唯我与露西亚。近世露国酷待学生之事,实为一部惨谈之历史。而学生至于流无限之鲜血以争之,将龂龂造成他日共和之新露国。呜呼,我同学之担负,岂不重哉?今日之事,为我学生脱离专制学校之新纪元。我同学之前途,之奋勉,当如何也?谨次第其事,公布于本邦一般之国民。”[11]在退学生一时无所适从的情况下,身为退学生代表的殷次伊等人及时请求中国教育会给予帮助。“首鸣之于总理,事决裂,建议于张园,集退学生而吸合其团体,与之组织爱国学社,苦志筹画,不日成立。”[1]可见,在罢课风潮的前前后后,殷次伊自始至终是一个有力的参与者,发挥了独到的作用。
此后,中国教育会、爱国学社和《苏报》馆三位一体,成为“上海革命的大本营”,[12]154倡导了世纪初高涨的学界风潮,推动了以上海为中心的爱国民主运动在更广泛意义上的蓬勃开展。
新成立的爱国学社,一开始就明确仿效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倡导变革的吉田松荫、西乡隆盛等维新志士的教育活动,把灌输爱国、民主思想作为己任。学社成立初期,社员求知欲旺盛,醉心新学,对时事政治的兴趣愈益浓厚,民族意识也日趋增强。除一般文化科目外,有哲学、政治学、革命的佛学等。其中,蔡元培讲授伦理学;章太炎、蒋维乔讲授高低年级的国文;吴丹初讲授历史地理;担任寻常班中文教员的吴稚晖,干脆以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做教本。学社每周还安排一次佛学讲座,由常熟籍佛界奇士黄宗仰主讲,内容都是阐述平等、大同等佛理中包含的革命意义。殷次伊以新中国主人翁自居,厕身其间,表现了激越的民主主义觉悟。有人为此称颂:“学界主人翁之荣名,如次伊者殆无愧。”[1]
三
1903年6月,清政府查封《苏报》馆和爱国学社,章太炎、邹容相继入狱,酿成震惊中外的“苏报案”,一时激起社会公愤。正在上海的殷次伊感念故国陆沉,感怀:“牺牲一身保社会,伟男子事也。”[1]决计东渡日本,参加留日学生组织的拒俄义勇队。7月3日,殷次伊准备先乘船归里省亲,与父母双亲辞行,未料一时孤愤难抑,跳江致死,年仅26岁。
惊闻殷次伊英年早逝的噩耗,古城为之哗然,时人痛惜不已。蔡元培曾追述,说殷次伊“散学后未久,于归途中失足坠水卒。”[13]66不过,当时《中外日报》披露的一封“来函”,或许道出了其真正的死因:“次伊身死之日,正海上钩党事急之时,耗至吾邑,举邑哗然,讵谓次伊之死,必死于自尽。”[14]当年10月章太炎在给柳亚子的信中说:“自教育会分散以来,爱国诸君亦飘摇失所;常熟殷君复蹈水死,恐塔后亦少达者。”[15]据1904年《江苏》所刊《常昭调查一斑》,指出教育支部为教学同盟会改名而来,“开办时颇有起色,自殷次伊死后,会亦随之解散”。[16]可见殷次伊曾在教育会常熟支部发挥着重要的核心作用。
一时间,同乡好友丁祖荫、徐念慈、庞树柏等人纷纷以诗致哀。徐念慈称他“只身海上游学三数年,举今日教育问题社会问题政治国际问题,莫不解决有心得。”满含深情吟咏:“君我友兮亦我师,忝颜不肯生偷息,灵魂往兮精神存。”[17]庞树柏的《哭殷崇亮》写道:“天纵一身能殉国,楚虽三户尚亡秦。劝君泉下撑只眼,待看乾坤再转轮。”[18]因“苏报案”而避走日本的佛界奇士黄宗仰也有挽诗一首,其中有句:“生不自由毋宁死,国民资格原如此。他年新史招国魂,君兮归来享角黍。”诗句通篇寄予了对亡友的深切怀念,也为他以“尸作谏励同胞”的爱国豪情所感佩。[19]
与殷次伊相知最深的丁祖荫在1903年第4期的《江苏》撰有《常熟殷次伊传》一文,文末附诗曰:“铁血横飞荡九州,雄心不死贯全球。三千革命军声起,齐向长江日夜流。/东海风潮卷地来,无端党祸起邹枚。汨罗魂与灵胥泪,迸作春申浦上雷。/终宵倚剑瞰天衢,蒙难酣嬉悯众愚。气节动人惟一死,为民为国不为奴。/江山无主奈愁何,凄绝同胞爱国歌。虞岭魂归风雪夜,春寒犹禁自由花。[1]对于殷次伊“不自由毋宁死”的献身精神,不无欣慰地赞誉:“美丽哉!吾虞方百里锦峰琴水明媚之山川。瑰玮哉!吾虞三千年南方文学灵秀之历史。学界风潮日簸荡,自由钟声日震撼。一跃而登二十世纪之新舞台,演四万万同胞悲壮义愤之活剧,生为人豪,死为国雄,以振起一乡之社会,感奋全国之社会者,有之,自殷次伊始。”[1]殷次伊以满腔的爱国之情、忧国之心,以自己年轻的生命谱写了一曲慷慨悲歌。
证诸与殷次伊同窗的黄炎培、李叔同、谢无量等各自拓展的人生事业,①黄炎培(1878-1965),我国近代职业教育的创始者和理论家,现代卓越的爱国民主人士,曾发起成立中国民主政治同盟,1949年后在人民政府担任要职。李叔同(1880-1942),留学日本,著名诗人、艺术家、一代佛学大师。邵力子(1882-1967),留学日本,为国民党政府要员,1949年后在人民政府任要职。胡仁源(1883-?),先后留学日本、英国,曾任北京大学、交通大学校长,教育部总长等职。谢无量(1884-1964),留学日本,为近代著名学者、诗人、书法家,长期从事教育、文史研究工作。贝寿同(1875-1945年前后),留学德国,被誉为我国现代建筑学的先驱,先后执教北京大学和中央大学。王世澂(1877-?),福建福州人,留学英国,曾任北京大学法政科学长。洪允祥(1874-1933),留学日本,曾主持民初《天铎报》笔政,任北京大学、上海大夏大学教授。项骧(1880-1944),留学美国,获经济学硕士,担任国民政府财政要职。后人有理由设想,假如天借以年,作为古城走出的学界后起之秀,殷次伊自有不可限量的人生愿景令人期待。但身处国势日衰、列强环伺的局面,殷次伊不惜舍身一死以图唤醒同胞,奋起革新。这一义愤蹈江之举酿成的悲剧,与其说是个人的悲剧,无如说更是时代的悲剧。
四
可以说,以殷次伊、曾朴、丁祖荫、张鸿、徐念慈等为代表的20世纪初新一代常熟学人群体志同道合,以锐意革新的先行者姿态出现在江南乡村社会,充任了除旧布新的时代吹鼓手。为传播新学、开启民智,他们积极投身于游学海外、创办报刊、组织社团、新办学堂等一系列活动,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时人赞誉:“是时,东南学子咸知振兴学务为救国保种之为唯一途径,此唱彼和,盛极一时。”[20]119这些与时更化的活动,以渐趋渐深的波澜,打破了常熟学界一直以来的沉闷局面,推动了地方文化教育事业由传统向现代的历史转轨。
生逢清末社会变革的常熟新学界中坚人士,伴随西学东渐的鼓荡,怀抱济世救民的宏图,各自肩负起自觉的责任担当。循此进一步分析,这样的人生选择,与其故乡毗邻上海的地缘互动优势及地域人文传统同样有着重要的关联。
地处苏南的常熟,北枕长江与南通隔江相望,南接苏州通往杭嘉湖,西出无锡联接京杭大运河,东经太仓、嘉定至上海,两地相距近百公里。境内河道密布,水路交通便捷,地理区位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史载,1900年,由上海英商老公茂轮船局最早在常熟开通至上海的轮船航路,“始有木轮行驶,自后推及于苏州航路。沪轮由东唐市经昆山,苏轮由元和塘过吴塔出境”。[21]1051912年苏州招商局内河航运公司又在常熟设立分公司,辟有常熟到上海的客班。民国初年,境内河道水系中入长江而间接连通上海的有11条,经太仓过嘉定至上海的1条,经昆山去上海的1条。到1915年,常熟往来于上海的火轮航线已有4条,这样的水上航线,大大缩短了常熟联通上海的空间距离,也增强了上海对周边城镇的辐射能力。
有了与上海都市辐射效应互生相伴的区位优势,来自古城常熟学界新旧递嬗的现象,在当年上海的《申报》、《苏报》、《时报》、《警钟日报》和《国民日日报》等报刊上,均有不少相关的篇幅给予热切的关注、敏锐的捕捉。如1903年《苏报》4月5日、4月6日、6月18日、6月24日就先后刊有《记常昭公学》、《常熟敎学同盟分会章程》、《常熟敎学同盟会开智会特别演说以后情形》、《纪常昭塔后小学二则》等有关常熟地方学界情况。1904年,《时报》设“特别调查”专栏,同样刊有多篇介绍常熟学界的调查文字,如《时报》第25号刊登了《常熟学界之现状》一文,报道当时常熟有公立小学校一所,分设城乡的私立学校7所,并称:“以上学校,出于私立者7区,出于公立者1区,然尚未见成立。可知吾人欲图建树事业,当将倚官家性根铲除净尽。一学校然,其余一切改良社会各项事业,亦莫不然。盖谋群治之进化,于文明竞争之日,而欲舍地方自治之制,其道莫由。”[3]第79号又载《常昭学界之实况》一文。[4]据调查,当时常熟既有以士商官场为读者对象、日销数达320份的《新闻报》;有各销20至30份不等的《中外报》、《申报》、《同文报》等日报,读者对象或为官场士绅,或为学界。此外,还有《江苏》、《浙江潮》、《游学译编》、《湖北学生界》、《科学世界》、《新小说》、《新民丛报》、《女子世界》、《东方杂志》、《绣像小说》、《政法学报》、《女学报》、《中国白话报》和《潮州白话报》等旬刊,每期销售数多者30余份,少则10来份不等,读者对象大抵为学界中人。①参见1904年9月23日《时报》第140号针对古城当年报刊创办与销售的情况所作的调查。这些报刊发行与传播,使受众与传媒、乡镇与都市之间有效地进行信息交流和思想沟通,滋润并催化着古城市民在传统与新潮的交互激荡气象。
还要看到,以环太湖为中心腹地的苏松常地区,是人文底蕴深厚的吴文化区域,历来富有浓厚儒家经世传统,以及长于思辨、敏于判断、善于吐故纳新的人文风尚。这些地域风尚,以其特有的渗透作用润泽过代代学人的心灵,丰厚了他们的学养。恰如时人在创刊于1909年的《常昭月报》序中称:“夫常昭(笔者按:指常熟、昭文两县)地滨大江,波涛之声,兴于昼夜。里传文学,弦歌之声,不绝今古。人多俊秀,士知礼让,风气早开,甲于列郡。其故在闻声而先觉,亦因善以其声启人听也。”②参见1909年10月3日《常昭月报》第1期,常熟图书馆藏。
当时介入上海新学界的常熟人中,除了殷次伊、曾朴、丁祖荫、徐念慈等,还有黄宗仰、张鸿、庞树柏、徐天啸、徐枕亚、吴双热等好友,他们无疑聚集了一个不无地缘特征的新知识人共同体。这些同仁友好以趋时更新的姿态走出家乡,走向都市知识领域,既在上海从事文化事业,或供职学校执鞭任教,登台亮相,鼓吹革新;或投身编辑出版,从事翻译创作,成为清末民初都市空间职业文化人中的一时俊杰。[22]同时凭借上海海派文化边缘的地理优势,往来于城乡与都市之间,热心于革新家乡文教事业。以一个文化人应有的敏锐触觉和社会责任,在传统和新潮的交汇中走出家乡,以吐故纳新的姿态介入上海知识领域,各自表现出了不同程度的社会忧患意识和人文情怀。
[1]初我.常熟殷次伊传[J].江苏,1903(4).
[2]初我.常熟学界调查报告[J].江苏,1903(4).
[3]常熟学界之现状[N].时报,1904-07-06.
[4]常昭学界之实况[N].时报,1904-08-29.
[5]丁祖荫.徐念慈先生行述[J].小说林,1908(12).
[6]常熟敎学同盟会会员题名单[N].苏报,1903-03-23.
[7]赵利栋.清末新式学务团体和教育界的形成[M]//晚清国家与社会.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8]蔡元培.在爱国女学校之演说[M]//高平叔.蔡元培全集:第3集.北京:中华书局,1984.
[9]刘永昌.乌目山僧传·附识[J].人文月刊,1944(9).
[10]爱国青年(张继).教育界之风潮:卷4[M].[出版地不详]:[出版者不详],1903.
[11]南洋公学学生出学始末汇记[N].新民丛报,1902-11-30.
[12]柳亚子.自传年谱日记[G].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13]蔡元培.记三十六年以前之南洋公学特班[M]//高平叔.蔡元培全集:第7集.北京:中华书局,1984.
[14]来函[N].中外日报,1903-07-14.
[15]西狩.致□君书(癸卯九月)[J].复报,1906-10-12.
[16]钦成.常昭调查一斑[J].江苏,1904(5).
[17]觉我.哭殷君次伊[J].小说林,1907(5).
[18]剑门病侠.哭殷崇亮[M].国民日日报汇编:第3集.上海:上海东大陆译印所,1904.
[19]中央.挽殷次伊[M].国民日日报汇编:第3集.上海:上海东大陆译印所,1904.
[20]冯自由.中国教育会与爱国学社[M]//革命逸史:初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
[21]常熟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标校.重修常昭合志(上)[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
[22]沈潜.清末民初上海文化界中的常熟学人[M]//许霆.常熟文化论丛.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3:264-280.
YinCiyi and Chagshu New Academic Circle
SHEN Qian
(School of Humanities,Changsh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Changshu 215000,China)
Living in a rapidly changing society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YinCiyi had an aspiration of contributing to the society.He pursued new knowledge and was devoted to the educational innovation of his hometown.He even sacrificed himself to awaken his compatriot.He acted as the trumpeter in his time that removed the old in order to build the new and shouldered the responsibility given by history.The novel and energetic spirit of the Chagshu New Academic Circle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represented by YinCiyi had an important connection with the geographical advantage which was close to Shanghai and the humanity traditions of his hometown.
YinCiyi;The Revolution of 1911;Nanyang Public Elementary School;Patriotic Society;Chagshu New Academic Circle.
K257.2
A
1008-2794(2011)09-0035-06
(责任编辑:韩廷俊)
2011-09-05
沈潜(1965—),男,江苏昆山人,常熟理工学院人文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文化江南与社会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