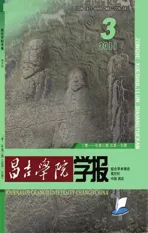华兹华斯《咏水仙》的真境界
2011-04-02房霞
房 霞
(临沂大学外国语学院 山东 临沂 276000)
一、诗学境界理论
诗歌是最古老的一种文学艺术形式,皆为感于事或物而作,是心灵的映现。其语义显明清晰,语言优美,情感丰富,经常运用奇特的形式与规则抒发朦胧情感,唤起情感与感觉的共鸣。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诗歌的表现手法很多,古有“赋、比、兴”,今有象征、夸张、复沓、重叠、跳跃等。西方诗歌的表现手法诸如半韵、头韵、拟声以及节奏等,节奏有时能达到美妙绚丽的效果。诗歌用词方面歧义、象征、讽刺以及其它文体方法使得诗歌有足够的空间而有多重的阐释。同样,隐喻、明喻、转喻在迥然不同的意象间创造一种共鸣。无论什么手法,皆离不开诗人丰富的想象。尤其是象征,在现代诗歌中又表现为心灵的直接意象。
东西方对于诗歌的认识基本是一致的。诗歌外在的特点即表现技巧与形式随社会生活方式与语言的变化而变化,诗歌那种直抒胸臆的特质永远是诗歌的灵魂。当然绝不能否认优秀诗歌应该具备其它的诸如高超的表现技巧以及完美的形式,但是“情真与不真”永远是鉴别诗歌优秀与否的最重要的标准,即是否有境界是衡量诗歌优劣的亘古不变的依据。那么对于境界理论东西方又有哪些相通的方面呢?
(一)王国维的境界理论
自古至今,中国的诗学理论基于对诗人诗歌本体的关注,以精气神为诗学鉴赏的最根本范畴,源远流长,无时不闪耀着生命神圣的光芒。从孔子的“思无邪”,到毛诗“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从钟嵘的“风骨滋味说”到司空图的“味外之味”;从严羽的“兴趣”到王士祯的“神韵”;从袁枚的“诗写性灵”到王国维的“境界说”,只有自王国维始才以“境界”为其诗学之本,即在于他抓住了“境界”这一最能体现汉语思想之“域性”特征的词语。因此王国维《人间词话》确乎是对中国传统诗学的有力总结,他理所当然地成为中国诗学的集大成者。
纵览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他的境界说有以下两个方面构成:
1.境界为其诗学理论的根本
王国维《人间词话》开篇宗义“词以境界为上。”[1]又云:“然沧浪所谓“兴趣”,阮亭所谓“神韵”,犹不过道其面目,不若鄙人拈出“境界”二字为探其本也。”[2]“能写真性情真景物者,谓之有境界。否则无境界。”[3]境界的核心为诗人赤子之心的所谓以血书者。
2.境界说的理论构成
王国维认为,有境界的诗词,必定有以下特点:生香真色的陶潜不隔境界;豪放雄浑的太白东坡气象;忧生忧世的屈原基督悲悯情怀;风人深致的《蒹葭》幽深情思;深美宏约的正中骨秀柔情;质朴天真的后主秀美精神;豪放沉着的永叔稼轩雅量胸襟;自由出入宇宙人生的东坡杜甫智慧情怀等。
(二)华兹华斯的诗学理论
古代西方诗学隶属美学,美学又隶属哲学。美学自成独立学科后,现代意义的西方诗学才浮出水面。亚里士多德认为诗歌是模仿技术,这种技术让一般呈现于个别,个别与一般的关系即为诗歌与真的关系。黑格尔认为诗歌是一艺术门类,而艺术与宗教、哲学并列为“绝对精神”展示自己的一种方式,即绝对精神的感性显现,也就是亚里士多德所谓的一般在个别中的显现。换言之,黑格尔“美学”中的诗论部分乃是古典诗学最为完备的哲学化样式,它的基本思路未出亚氏之右,即“诗-艺-理念”的入思模式。自启蒙运动到文艺复兴,从文艺复兴到现当代的各种文艺思潮,人的本性的展现成为文学的主题,诗歌也不例外。浪漫主义与意象诗学尤其注重自我真实情感的表达与展现。
华兹华斯作为英国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代表人物,他的诗学在继承批判基础上,加之个人的创作实践经验揉和而成。他的诗学观是西方浪漫主义灵魂,对以后的英美文学发展有着极为深刻的影响。
浪漫主义诗人寻找表现他们的内在情感的方法时,在自然界中找到了情感对应物,通过描绘自然把自己的感情客观化。这也是浪漫主义诗歌的一个重要特征。他在《抒情歌谣集》的再版序言中将诗歌看作“‘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4]他强调诗歌是情感的自然流露,包括语言也只有在情感的驾驭下,才会生动活泼,具有强烈的感染力,诗歌是大诗人满腔热情的语言。这句话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诗人是诗歌创作的主体;诗歌是诗人情感的表达;诗歌的价值是以情感人;情感是诗歌评判鉴赏的主要标准。”[5]
既然“一切景语皆情语”,诗歌就是“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华兹华斯情感表达所对应的自然界正是王国维的语语都在眼前所对应的“景语”、“情语”。既然东西方的诗歌理论在审美方面拥有如此相通的地方,因此借用东方的诗歌理论对华兹华斯的代表作《咏水仙》进行鉴赏尝试应该是科学的。
二、《咏水仙》的境界
华兹华斯的《咏水仙》以其流畅的韵律,优美的文辞,直抒胸臆的情感,征服了众多的中国读者。那么这首脍炙人口的名篇的魅力究竟何在?此诗生香真色,寄兴深微,最得风人深致,“语语都在眼前,妙在‘不隔’。”[6]优美的真景物,强烈的真情感,使得这首诗歌达到了绝妙的境界。
(一)《咏水仙》生香真色的不隔境界
1802年4月15日华兹华斯与妹妹多萝西访友归来。孤傲的诗人在高巴罗公园的林中首先看到了几株临湖的水仙花,接着又发现一大片金色的水仙,它们欢快地遍地开放。水仙很多,如天上的星星,都在闪烁。水仙似乎是动的,沿着弯屈的海岸线向前方伸展。诗人为有这样的旅伴而欢欣鼓舞、欢呼跳跃。“‘洛浦凌波女,临风倦眼开。……余生有花癖,对此日徘徊。’”[7]华兹华斯所描写的水仙与秋瑾笔下的水仙何其相似,开得那么美丽,让诗人如此动情,如此依依不舍。此时诗人所面对的不是花,而是一位颇解诗人心意的红颜知己吧。
1804年的某一天,诗人回忆起两年前所看到的水仙的情形用最美丽质朴的语言写道:
突然我看见一大片鲜花,是金色的水仙遍地开放;
它们开在湖畔,开在树下,它们随风嬉舞,随风波荡。
它们密集如银河的星星,象群星在闪烁一片晶莹;
它们沿着海湾向前伸展,通向远方仿佛无穷无尽;
一眼望去就有千朵万朵,万花摇首舞得多么高兴。
此情此景,华兹华斯的妹妹多萝西在她的日记中见证:他们访友归来,在高巴罗公园的林中看到了几株临湖的水仙花。往前走,水仙花越来越多;最后,在树木枝条下,看到沿湖一条长长的水仙花带,同乡间的小路差不多宽。我从没见过这么美丽的水仙花,他们长在青苔石头中间,长在石块周围,长在石块上面;有的把头靠在石块上休息,如同靠在枕头上消除疲劳;有的在摇摆,旋转,舞蹈,仿佛同湖面吹来的轻风一起欢笑;他们看上去那么快乐,总是在闪闪发光,变幻不停。
诗歌最大的魅力在于以真景物感发读者,以真性情触动他人。叶家莹在她的著述《唐宋词第十七讲》中这样写道:“王国维欣赏诗词的途径是直接的感发,所以他的《人间词话》主张‘不隔’,不能有隔膜,那个感发要直接表现出来。她理解的‘不隔’就是没有隔膜,情感的直接感发,‘隔’就是有隔膜,理性的雕琢痕迹太重,太过于明显,情感不是直接感发而来。”[8]
华兹华斯《咏水仙》没有任何的雕琢痕迹,以景语为情语,真切自然的不隔境界,蓬勃而出的真挚情感深深震撼读者的心灵,无怪乎百年来各国读者对于她如此偏爱,流传如此广泛。
(二)《咏水仙》风人深致的境界
“《诗·蒹葭》一篇,最得风人深致。晏同叔之‘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意颇近之。但一洒落,一悲壮耳。”[9]两首诗歌的意境非常相似,含有丰富的哲理,最富有风人情致。不过前者表现出了自然之美,而后者则为悲壮之美。
华兹华斯无愧于那个时代桂冠诗人的美誉,他在《咏水仙》中即有凄怆的心境表白:“我好似一朵孤独的流云,高高地飘游在山谷之上,”;又有自然洒脱的自然之美—“突然我看到一大片鲜花,是金色的水仙遍地开放/它们开在湖畔,开在树下/它们随风嬉舞,随风飘荡。”
以孤独悲怆之我观水仙,水仙花应该带有我的情感色彩。但是诗人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将富于自然之美水仙已经看做飘缈空灵的世外仙株,一种崇高的精神。诗人没有以自己的忧愤悲伤压抑自然精灵的化身水仙,而是借水仙美丽的光芒抚慰自己的灵魂。因此诗歌《咏水仙》也拥有风人深致的境界。
(三)《咏水仙》寄兴深微的境界
《咏水仙》这首诗写于华兹华斯从法国回来不久。诗人带着对自由的向往,参加了法国革命。但是法国革命并没有带来预期的效果,随之而来的是混乱。诗人的失望与所受的打击是可想而知的。诗人一下笔就写到:“我好似一朵孤独的流云,高高地飘游在山谷之上”;在诗歌最后一节则感叹“后来多少次我郁郁独卧,感到百无聊赖心灵空漠/这景象便在脑海中闪现,多少次安慰过我的寂寞/我的心又随水仙跳起舞来,我的心又重新充满了欢乐。”
华兹华斯在《抒情歌谣集》的再版序言中将诗歌看作“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这同时也是他的浪漫主义诗学观的宣言。当诗人对于宇宙人生即能入乎其内,又能出乎其外时。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能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入乎其内,方能有重视外物的气魄,故能与花鸟同忧乐;出乎其外,必能有轻视外物的胸襟,故能以奴仆命风月。可见,诗人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笔写情,故能写得如此真切感人。因此,诗人的对于自然寄予了多么深的情思啊。正如王国维先生所言:真正了解诗人的情怀,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因为诗歌中包含的诗人太多的期盼与情感,没有诗人的赤子之心,就无法对他们的诗歌做出确切的评价。
《咏水仙》应该是诗人在理想与追求遭受重创后,寄情于邂逅的水仙花。庞德在1919年给门罗的信中,曾这样说:“诗歌就是当你在某种环境中,受情感压力而说出的言辞。”[10]庞德的诗学观点深得华兹华斯的精义。诗歌所有的语言都是情感的产物,是“受情感压力而说出的言辞”,这语言是精确的,客观的,也是自然的。归根结底,诗歌是情感的产物。
《咏水仙》这首诗,读来千遍也不厌倦,或许就在于它寄兴深微,言有尽而意无穷,境界超然。
总之,凡“‘大家之作,其言情也比沁人心脾,其写景也比豁人耳目,其辞脱口而出,无娇柔装束之态。以其所见者真,所知者深也。’”[11]可见华兹华斯这首《咏水仙》自然真切,味外之味无穷,哲理丰幽,境界高潮,无愧于桂冠诗人的代表作之一。
结语
王国维一贯主张鉴别诗歌境界的高低主要依据是否有真景物、真性情。因此,有格调的思想意蕴风貌修缈的诗歌,为直致所得,为直寻所得。诗歌是情感的自然流露,受情感压力而说出的言辞,“即兴当场之悬词”[12]。虽然西方诗学(华兹华斯与庞德)的观点与东方诗学(王国维、叶家莹及钱钟书)措辞表达不同,但是他们对于诗歌本质境界的理解是一致的。
诗词者,物之不得其平耳鸣者。“无论是钟嵘在《诗品》所提到的风骨,严羽在《沧浪诗话》中论及的兴趣与王士祯在《花草拾蒙》中所论及的神韵,皆是“境界”的启蒙与雏形,是对于诗歌本质的探索与追求。”[13]应用境界这一诗学理论,在鉴赏《咏水仙》方面重视从诗人生命主体上整体把握诗歌的魅力,与新批评派的文学批评方法有些近似,避免了西方现当代理论对于诗歌肢解式的所谓学术研究分析,无疑是对文学批评的一个有益的补充。
参考文献:
[1][2][3][6][9][11]王国维.人间词话[M].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4.
[4]JohnPurks.APrefacetoWordsworth[M].Beijing:BeijingUniversityPress,2005.
[5]苏文菁.华兹华斯诗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7]张正义.历代咏水仙花诗词选[EB/OL].http://club.eladies.sina.com.cn/thread-48,2011-04-16.
[8]余福智.美在生命[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
[10]CleamthBrooks.UnderstandingPoetry[M].Beijing:ForeignLanguageTeachingandResearchPress,2004.
[12]钱钟书.管锥编[M].北京:三联出版社,2008.
[13]杨存昌.中国美学三十年[M].济南:济南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