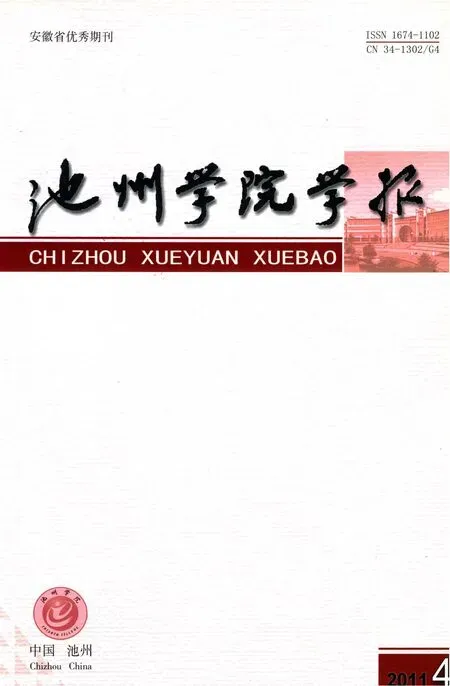近代大众传媒与灾害救济
——以1935年水旱灾害为例
2011-04-02孙语圣徐元德
孙语圣,徐元德
(安徽大学 社会与政治学院,安徽 合肥 230039)
近代大众传媒与灾害救济
——以1935年水旱灾害为例
孙语圣,徐元德
(安徽大学 社会与政治学院,安徽 合肥 230039)
近代中国自然灾害频繁,以报纸为主体的大众传媒对此给予高度关注,从各个方面及时、准确地报道了各个时期频发的灾害及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媒体还直接参与历次抗灾和赈济灾民的社会活动,表现出大众传媒关注社会、关注民生的强烈责任感,显示出大众传媒干预社会生活的强大功能。
近代中国;大众传媒;自然灾害;救灾
近代大众传媒的迅速发展,为人们了解灾害及参与灾害救助提供了物质基础。近代大众传媒主要是报纸、刊物、广播、电影等,就信息量、受众面、影响力而言,报纸则位居首位。大众传媒的发展,有利于全社会对公共事务或突发事件的及时了解,以便作出相应的反映和行动。
1 大众传媒与灾害信息传递
在救灾活动中,信息是关键。灾害信息包括灾害发生时间、地点、范围、程度、灾害后果(如人员受灾情况、人员伤亡数量、紧急转移安置人员数量、农作物受灾情况、房屋倒塌、损坏情况及直接经济损失等)、灾区的需求和已采取的救灾措施等。大众传媒以新闻报道的形式将灾害信息传播开来,形成舆论强势,引起社会关注,唤起社会各界帮助报道对象渡过难关。
1.1 灾害信息的来源
1.1.1 政府的渠道 民众获得报告内容的途径唯有通过广播与报纸等大众媒介,尤其是报纸对各地灾情报告与治水报告相继转登刊载,成为大众媒介与灾害救助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报刊对政府组织的调查团高度重视,关注政府调查团的建立过程、调查人员、调查范围等问题。如1935年7月17日始国民政府救灾委员会委员长许世英勘察水灾呈报中央报告,包括《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四省水灾查勘报告书》,报刊转录其全文《四省水灾总报告》并附标题“灾民一千四百万人,公私损失五万万元”[1]。
报刊媒介不仅引用调查团向政府发来的最终统计报告,在政府进行调查时,也注重调查的进展。本年水灾,政府曾多次派遣负责人员前往灾区调查,报纸记者在采访时也询问关于灾区一些问题,如对朱庆澜、章元善、许世英的访谈。在政府工作上,主要询问政府政策、纲领文件,在引用调查结果时注重政府的最终方针政策。如对政府各水利相关部门关于水利治理、防汛堵口等诸多报告,报纸也大多原文转载。
1.1.2 社会的渠道 社会渠道不像官方那样清晰简明,往往交错纷杂。如同乡会、慈善团体、受灾地自行组织宣传团以及各大报馆等新闻媒体,其目的为了多方筹集资金,征募救灾物资,向社会各界公布灾害信息。如何使灾情公之于众,引起普遍同情,大众传媒尤其是报纸的宣传广告作用无疑是最佳选择。各大报馆引用民间赈灾机构信息的同时,利用电报、通信与实地调查等手段收集新闻信息。
1.1.3 媒体自身的采编 在利用各机构的调查材料外,大众传媒通过自主渠道收集第一手灾情信息,从根本上了解灾情。消息全面快捷得益于广布各地的通讯员网络优势。1935年水灾时,以报刊为主体的大众传媒发动记者赴灾区实地调查并连载其见闻报告,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申报》记者陈庚雅《江河水灾之观感》的15篇系列报道和《大公报》特派调查员萧乾的《鲁西流民图》等8篇视察报告。他们用细腻的笔触,详细的描述了灾情发生后墙倒屋塌、田园冲没、牛马不存、家破人亡的惨剧。1935年,记者庚雅实地调查长江灾情,从上海到汉口,途径张公堤、汉口、岳阳等地,后又赴黄河灾区途径河南、山东、江苏等灾情最严重区域,一路访谈当地灾民与赈灾官员,用日记形式细致刻画了灾区点滴。《大公报》记者萧乾第一次独立旅行采访,用手中的笔为我们留下了山东难民与死神搏斗、逃离家园的人间惨景,配以画家赵望云素描写真与《每日画报》专栏水灾摄影照片,从视觉上为读者呈现灾后悲惨的场景。
著名记者范长江的“旅行通信”也是1935年灾害信息来源的一个亮点。1935年5月1日起,他以天津《大公报》特约通讯员名义离津南下,经烟台、青岛到上海,再沿长江西行,赴重庆、成都,沿途写“旅行通信”,5月10日起在该报发表;7月14日,范长江又从成都出发,开始了西北之行,至1936年6月结束,历时10个月。此外,报社记者身临灾区收集信息,也不乏其人其作。记者沿途所见有感而发,将一幅幅水灾写照图呈现于读者。
1.2 对灾害过程的报道
1935年灾害的消息,最先通过报刊的登载而为人所知。面对灾情,大众传媒纷纷关注社会民生,以当时媒介主要报刊 《大公报》、《申报》、《民国日报》为例,面对灾难几乎每日追踪报道,广为传布,及时向社会反映灾害信息,以引起社会和政府的重视,发挥信息传播媒介的作用。如以《大公报》为例,此次水灾报道占有大幅的版面,第三版是以国内新闻为主,从6月中旬开始,头条新闻几乎都是水灾进程的消息,一直到“华北事变”中日矛盾的激化。第五版专门报道社会,水灾的报道也经常占到版面的一半甚至四分之三。在新闻中,最多的是对灾情的报道,信息来源于各地发来的专电,连续不断的新闻内容并配以醒目的大标题,详细记载了灾害的全过程,水旱迫急、江河同难之声跃然纸上。为引起大家对江河水势进程更直观的了解,《大公报》特每日设一专栏转登水利会发布的《沿江各地水位(中央社电)》报告。各大报刊相继传递灾害预警信息,向社会发出警示。
1.3 对灾害损失的报道
灾害损失数据是衡量灾害大小重要的量化指标,对外及时、真实的发表有利于大众给予关注投以支援。1935年水旱灾害后,大众传媒将各地灾害的各种损失及时详细的登载,或转载各级政府的调
2.1 大众传媒宣传救灾的内容
1.4 对灾害影响的报道
查报告,或亲派调查员深入灾区,各方报告虽有出入,但大体上可概括1935年灾害程度。
除全国和重灾区湖北、安徽、河南、山东等灾害损失报道详细外,其他各省市县受灾损失报刊媒介也均详细转引,毫无遗漏,不吝版面,意在客观真实的反映灾情,唤起社会同情之心。
1.4.1 报道灾民的疫疠与死亡情形 《大公报》1935年5月6日、7月5日、7月15日、7月22日、7月 26日、8月 9日、8月 19日、9月 17日、9月 19日、10月23日、11月25日,《中央日报》1935年7月31日、8月 4日、8月9日、8月30日,《时事新报》1935年8月29、8月30日等众多版面报道1935年部分地区先旱后雨、水旱交乘,使受灾地区灾民得不到片刻喘息,不死于旱即亡于水的悲惨景象,各报刊杂志媒介的报道的伤亡数字惊人,令人动容。
1.4.2 报道灾荒与农民社会生活、农村经济 《申报》1935年7月18日、8月3日、9月5日,《国衡》1935年第4期,《中国实业杂志》,1935年第7至12期,《大公报》1935年 8月 22日、8月 29日,《农声》1936年第207期等报刊等用较多版面报道1935年灾后农民生活情形,报纸媒介用文字刻画更能扣人心弦,令读者动容不忍多想。此次水灾对交通方面的损失特别重大,如浙赣铁路杭江段,损坏路轨桥梁五六处;南洋断损失约十万余元,钱江大桥工程被冲毁,损失百余万元;湘赣公路、浙皖公路及平汉铁路、陇海铁路,冲毁路基、铁桥;广韶铁路被淹停车,平粤航空因水灾停航。1935年水旱交乘,长江黄河水灾,灾民流离者尤众,形成一副颠沛流离的流民图。《大公报》记者萧亁和画家赵望云同时被《大公报》派去水灾现场进行实地采访,一写一画,踏访鲁西灾区,并陆续在该报上发表《鲁西流民图》,描述了当时山东灾民外逃谋生的悲惨图景。
2 大众传媒与救灾宣传
遇到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时,运用大众媒介迅速报道政府和社会组织救灾决策、赈灾措施等信息,能够鼓舞大众根据形势进一步采取行动,推动救灾工作的进程。在1935年水灾救治中,大众传媒劳苦功高,发挥无以替代的作用,各地求赈报告、纷呈的救灾建议、政府的临灾措施、社会各界火热的筹赈活动,都是通过新闻喉舌在全社会传布流转的。
大众传媒参与灾害救助的过程,不仅在于向公众传播灾害信息本身,更重要的是宣传灾后社会回应,直接利用传媒动员与激励优势参与救灾的过程。1935年水旱灾后,各级政府与社会各界的救灾活动情形,透过大众媒介的宣传公之于众,起到传递信息、舆论监督、稳定社会的作用。
2.1.1 救灾主体 大众传媒对政府与民间慈善团体等救灾主体进行跟踪报道,通过报刊媒介的宣传使社会化救灾场景得以向公众全方位展现。大众媒介尤其是报刊对社会救灾主体的纪实报道为读者提供了可视平台,社会各界纷呈的救灾宣传活动透过报纸的寸方世界一览无余。
救灾主体包括政府即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社会力量及个人、家庭或企事业单位,或某一社会团体或社会团体的集合。在大众传媒宣传视野下的救灾主体名目繁多,如百花纷呈,数不胜数。形成中央和地方、政府和社会、国内和国外之间的协同合作,而一定程度上调节了利益矛盾、缓解了社会压力。
以《申报》、《大公报》为例,1935年灾害前后,宣传政府救灾的篇幅不下百篇,涉及政府机关包括国府水灾会、行政院、中政会、立法院、经委会全国水利委员会、黄灾救济会等政府机构,政府要员如蒋介石、汪精卫、孔祥熙、许世英、陆伯鸿、朱庆澜、冯玉祥等参与救灾行动言论,地方政府如湖北、山东、河北、徐州、湖南、河南、江西等,这些机构、个人、地区有关救灾活动均成为报刊新闻的热点问题,报纸一般在显要位置配以黑色醒目标题。对以上地方政府具体针对性的特色救灾予以专题报道,起到推广宣传作用。
以上海筹备各省水灾义赈会、天津水灾救济联合会、华洋义赈会为代表的民间社会救灾主体更是受到了媒体的垂青,中华慈幼总会、红卍字会、天津市黄十字、慈善团体联合会等民间慈善团体的活动也不乏篇幅。同乡会、宗教界、军界、妇女界、体育界、文艺界、教育界、海外华侨和众多个人等各领域的救灾主体更是媒体报道和关注的重点。
2.1.2 救灾方式 近代传播媒介如电报、电话的出现,有效发挥了信息传导、组织民众等方面的功能,大大提高了救灾效率,使救灾手段愈加灵活。
首先是宣传联合救灾。天津救灾联合会联合新闻界、教育界、实业界等联合救灾堪称本年灾后救助活动的典范。新闻界则扮演着中介力量。《大公报》作为水灾联合会募款经募人之一,通过新闻媒介优势为该会进行赈灾宣传,对该会动态以超出常规字体,大版面的报道,并配以渲染式的黑体标题以达到震动人心、唤起同情的效果。
其次是开辟赈款来源。救灾经费的来源渠道是多元的,大众媒介对救灾资金的来源高度关注,一方面身体力行发动各界广募善款,一方面对政府赈灾款项瞩望有期。各项救灾款项的来源都在媒介的注视下呼之欲出:水灾工赈公债、借垫赈款、实物助赈、游艺助赈、童子军“普捐”、捐俸助赈、节约助赈等多种助赈方式,经《申报》、《大公报》等多次报道而被人们所熟悉。
再次是拓展救灾空间。由于大众媒体的强力宣传和政府的对外及时播报,引起了外国政府与社会及海外华侨的关注,救灾空间不断拓展,不再局限于一地一域,而是横跨多省救灾,不仅国内各省之间相互支持,而且救灾活动有了国外的参与。救灾空间的拓展与大众传媒的强力宣传密不可分,如非灾区省市的互助、国外捐助等。
2.1.3 救灾机制 救灾机构和制度从临时性向规范性转变,这是大众媒介宣传的重点内容。就1935年来看,大众传媒宣传救灾机制的转变主要有:
救灾准备金。1935年7月1日财政部实行救灾准备金列入预算,此可视为政府救灾工作切实负责的重要步骤。《申报》、《东方杂志》等媒体对救灾准备金的讨论议程、拨放分配进行详尽刊报。
江河标本兼治案。自9月3日行政院通过《标本兼治办法提案》,各大报刊对此项提议高度关注,并不惜版面刊载财政部长孔祥熙提议标本兼治办法两项的具体内容。以《申报》《大公报》为例,地方政府救灾机制的规定也日益规范化。7月10日报道湖北省政府制定的《防水救灾办法》九项[2],11月15日报道湖北省政府确定改进水政计划八项[3]。河北省灾后制定了各县《查放赈款办法》[4],《大公报》中央社徐州十日电徐州专员公署规定《救灾步骤》[5],湖南省于灾后制定了《湖南省乙亥年水灾救济计划纲要》[6]。这些地方性的救灾制度通过大众传媒的宣传告之于众,起到了稳定人心的作用。
2.2 大众传媒报道救灾的方式
大众媒介尤其是报纸作为沟通宣传的利器,以启事、文告、社评、报道等形式,信息量大,经大众传媒传送,速度快捷,广布于众,披被众深。以报纸为代表的大众媒介不仅作为一种新闻传媒,同时也作为一种社会力量而存在,在灾害救助过程中利用传播优势发挥多种社会职能,弥补了当时政府在社会动员职能方面的缺陷,积极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救灾。
灾情急迫,资财匮乏,灾民待赈孔殷,为筹集救灾款物,社会救灾团体为唤起同情心,往往发布乞赈文告或求赈启事,向社会通告灾害的严重和救灾的紧迫性,以急切的心情、哀婉的用词、敦促的口吻,号召全社会捐钱献物、出资纳财。1935年,大众传媒运用符号资本进行救灾筹赈的宣传。
2.2.1 刊登赈电 报纸刊登各地乞赈电文既是对灾情信息的报道同时也是呼吁社会积极参与救济目的之所在。1935年灾害发生后各大报刊媒体即转发各地报灾乞赈文告及相关电文。这些电文包括下级政府向上级政府的救灾呼吁,如《大公报》1935年7月11日刊登湖北省电中央及蒋委员长等呼赈,7月17日刊登山东省主席韩复榘通电全国呼愿,7月23日河南水灾救济会电铁道交通财政三部,7月24日刊登韩复榘通电林森等关注鲁灾,7月25日刊登张群电中央请赈,8月7日刊登甘肃省通电呼愿赈济,8月14日商震通电各方请赈冀灾,8月15日刊登湖南水灾会电中央请赈等。这些赈电一般置于报纸第一张第一版“国内新闻”栏内,关注之情由此可见。
2.2.2 乞赈启事 民间团体叠量的乞赈启事也通过报刊媒介向社会呼吁赈济,或请求政府救灾,或呼吁社会各界救助灾民。如华洋义赈会在《申报》、《大公报》连载乞赈呼吁:“黄河之水天上来,天将此奇灾,遭难者千万,啼饿震野,哀抢彻天,敬求世界仁人,大慈大悲,速赐一臂之助”[7]。
社会团体的叠量的乞赈呼吁迭见报端,大众媒介作为社会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救灾济民义不容辞,各大报刊纷纷发表启事,作为筹募赈款的主体之一。天津《大公报》于1935年8月29日发表特别启事:本市救济各省水灾联合会现已成立。本报亦经加入作为经募人之一,兹定于8月24日起所有本报代收赈灾捐款,概行交由中交两行归入救灾会账内汇灾区,其各界捐款指定区域者仍由本报遵照捐款人意旨通知该会照办决不有误。并且应华洋义赈会之请代收该会捐款[8]。各杂志也在报纸刊登救灾征文启事,开辟救灾专栏,救灾相关文章多达数十篇,竭力呼愿,阐述灾情。
2.2.3 植入救灾公益广告 民国时期报纸广告日益成熟,应其商业性质既为赢利计,同时也是大众媒介关注社会民生与时事使然。劝募赈灾广告成为这一时期的特色,因其具有广泛的读者受众,图文并茂的赈灾广告宣传效果比一般宣传方式更加直观,字里行间充满了情真意切,体现大众传媒对于灾区民众的殷殷关切之情。
《申报》馆于灾后即打出筹募广告语代灾民乞赈“救灾即救命:多捐一文钱,多救一条命!”并与1935年7月至1936年1月每日于版面中央显著位置加以粗体黑体字配上边框,连载此句广告语。相比 《申报》,《大公报》的乞赈广告语更加别具用心,从8月19日到10月11日广告语每日更新,多方呼愿,号召全国同胞速起输将,充分体现了道德人文关怀,倾注了大公报人满腔热忱和全身心的投入。其版面、字体、标题的独特设计和运用,也起到了一般文章无法替代的作用。广告居于版面中央,配以边框与超出常规的黑体字在显著位置连续刊登,起到了为活动造势的作用。
《大公报》的广告用语利用文字渲染深入读者内心,为筹赈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超常规字体让人们从冲击力极强的文字和一个个惊叹号中,感受到被灾大地广大民众的痛苦呐喊及救灾的刻不容缓,这些无疑为募赈活动的成功奠下了基础。
2.3 传输灾情图画场景
媒在充分利用文字表达多样性的同时,借助摄影与电影技术传输灾情图画场景,相比文字而言更能生动反映灾区生活现状更能起到震动人心、劝募输将的效果。1935年全国21省水旱交煎,多灾并发,《申报》、《新闻报》、《司法日报》和一些英文报刊相继刊登募捐宣传,并附一张张漫画,画面场景同样极为凄惨:眼前是一片汪洋,不少灾民尚于水中拼命挣扎求生。
以报刊为主体的大众媒介发动各地记者实地调查将灾区受灾情景通过摄影记录下来传达于民众。7月17日《武汉大水速写》、《沿江水报》刊登了记者拍摄的武汉“房屋树木,尽没于水中,江流湍急,漂过树木、房屋、人口、牲畜、什物无数,其上且有往往有未淹死之人,皆以流急,无从施救”的画面。画家赵望云的素描写真与《每日画报》专栏水灾摄影照片,从视觉上为读者呈现灾后悲惨的场景,素描与照片都有文字注释。《大公报》《每日画刊》专栏《丰沛灾区踏查记》刊登七组灾区摄影图片,直观的记录了灾民啼饥号寒、堤坝露宿无家可归、灾童满身泥沙嗷嗷待哺、救济院与临时收容所灾民的惨状。
《大公报》特派员在实地调查苏鲁灾情,真实相片记录《苏鲁水灾踏查记》[9]的九组灾情图画,也有以书画写生方式的《苏鲁灾区写生》[10]。摄影技术的运用,为大众直观呈现了灾区情形,相比文字更能说明灾情的真实性。
以灾害题材的电影也成为1935年救灾宣传的方式。通过光影的动感传播,立体式的画面,为大众传送了一幅幅洪水横流、灾民逃避、老弱死亡、少壮离散的灾民苦状,观者无不为之悲怆,于是“赈饥援溺、义举仁心,尤令观者奋起”。
3 大众传媒与救灾舆论
就灾荒而言,以报刊、杂志为主体的大众媒介既传递灾害信息、宣传灾赈,而且引导社会舆论,成为社会公众舆论的代言人,担负着“社会守望者”的重要职责,实施社会赋予它的舆论监督功能。各种灾害的言论汇集于此,掀起了一股股救灾救国的舆论潮流。其中,《大公报》、《申报》等报刊的救灾社评、短评与《中国实业杂志》、《东方杂志》等的灾荒论文专栏最具代表性。
3.1 对灾害原因的讨论
大众传媒对1935年灾害致因进行了深层次的分析,从自然地理与社会经济方面给予了揭示。首先,《申报》1935年7月7日、7月 15日、9月 6日、10月 10日,《大公报》1935年7月16日、7月19日、7月20日,《社会科学杂志》1935年第卷第1期、《中国实业杂志》1935年第9期、1935年《申报年鉴》“水利及灾害”部分等,从1935年气象特点、河道湖泊状况等自然地理方面报道该年灾害原因,分析十分客观、中肯。
其次,对1935年灾害的社会政治原因,报刊的社评、短评,杂志的灾荒专栏以及社会各界精英分子和政府机构的相关专员通过媒体,对灾情予以极大地关注,进行了积极的思考和审问。《申报》1935年7月28日、《当代杂志》1934年第1卷第1期、《社会经济月报》1935年第2卷第9期、《史地社会论文摘要》1935年第1卷第10期等,帝国主义侵略与封建势力的剥削,使得农民日益贫困无力整理水利事业,以至灾害频繁。
《中国实业杂志》1935年第9期,《中国实业杂志》1935年第7至12期,《申报》1935年3月3日、3月 25日、6月 18日、7月 11日、7月 14日、7月17日、7月 24日、7月 25日、7月 26日、7月 28日、7月 30日、8月 6日、8月 31日、9月 4日,《大公报》1935年8月 1日、8月 6日、8月 20日、8月31日,《大晚报》1935年 4月 7日、4月 18日、9月1日,《益世报》1935年9月30日等报刊诸多版面,刊登大量文章论证水利失修与水政紊乱是防灾不力、水利失治、水利机关组织不全、水利财政缺乏以及水利工程腐败等是酿成灾荒的根源,言论谓鞭辟入里、切中肯綮。
《大公报》1935年7月16日、7月 22日、7月23日、8月 31日,《申报》1935年 7月 14日、7月27日、8月6日等日期的版面,刊登许多文论,指出沿河平民与水争地现象严重、蓄水量减少也是导致灾害的原因之一,认为应对自然灾害能力的弱化会形成和积淀一些消极的社会行为,甚至成为与社会发展相随始终的“灾害性”流弊。
3.2 对防灾减灾的讨论
大众媒介除了引导时人对灾害原因提出思考外,对政府防灾减灾的荒政也给以积极地献计献策,新闻媒体通过一系列的灾害评论文章,激起人们对这一议题的关注,并逐渐形成关于如何防灾减灾的社会舆论,希望集思广益为政府献言献策,挽救灾民于洪流之中。
3.2.1 兴修水利论 “防止水灾之治本工作当为水利事业”[11],兴修水利是时人讨论如何防止水旱灾害的焦点,各新闻媒介设置专栏阐释自己的观点。
《大公报》社评对救治水灾的对策颇具针对性,认为通过三种方式可治理长江水患,方法一“测量全江,通盘计划,彻底疏浚”;方法二“择定湘赣山间,多筑水坝,建造蓄水池,随时启闭,调节水量”;方法三“考察沿江民圩,权其利害轻重,若有妨碍,励行制止”。同时谈到近年治江积习有碍治标工作,“水害到来之时,一味加高堤岸,苟保一隅,而不知水高过岸,在有洪流倒灌祸自天来之危机,就治标言,亦决非得计”[12]。
1935年黄祸又袭,治理黄河问题一直是难点。著名水利专家李仪祉在 《大公报》1935年8月31日发表文章,从水利专业角度分析了治理黄灾的办法[13]。灾害治理除方法得当,人力因素也很关键。《大公报》在社评《治河亟务中之亟务》中阐述了当今治理黄河问题中涉及的机构设置和人事安排问题,主张“改良统制水利机构、调整技术意见,在行政院长直接管辖下设一治河督办,以怀抱爱国爱民之热忱,任用进贤用能之雅量人物,编制兵工之权,以监督地方之任,事权划一,责任分明。同时设技术部,广罗专门人才以学识经验两具宏富又能勤苦耐劳躬自督工之人才。总揽工务计划,统一专家意见,使为督办之辅”[14]。
《申报》记者庚雅在《江河水灾之观感》中综合时人治水言论,提出了关于治水根本办法,按“江河天时地理水性关系”,对症下药,成为当时新闻媒体治水言论的代表,他从四方面提出对策其中关于水利治理方面首先要“加固堤防”,并以1935年长江黄河大水为例举证。
外籍水利专家对中国水旱灾害相当关注,并对预防水灾方法也给以建议,各大新闻媒介予以刊录。外籍水利专家贝克谈到根本预防水灾办法,“不再防堤之增高而在于水利建设”,主张“筹备巨数款项,购办水利机件,以资进行”。并希望“中国各省当局能督率勤劳著世之国人,利用其锄与犁等万能农具,在河流两岸,开辟支流,同时水利机关放弃增高防堤工作,而注重于水道之疏浚,则既可避免水患,又可以引江水灌溉田禾,一举数得”[15]。《中国实业杂志》刊登了余受之翻译华洋义赈会总工程师塔德文章《洪水与饥荒》一文,提及中国洪水治理办法应“发挥中国河道的潜在利益”。
3.2.2 植树造林论 植树造林足以防灾理论在民国时期历年水旱灾害袭击后盛行,各种关于造林防灾言论多见于报刊杂志,主旨一致但侧重不同。如《东方杂志》刊登皮作琼文章的《森林与水灾》,金陵大学农林科的《设公林议》,美人李佳白的《治水琐言》等文章,《中国建设》上孟舒撰文《造林为拯救中国水灾唯一方法》,均从理论上说明造林对于防灾的重要,并建议颁布造林法规、设立林业学校等措施。这些属于相对较早的造林讨论。1935年中国经历“五岁四荒”,这一理论仍是热议的焦点问题。
3.3 对灾后救济的讨论
关于灾因、防灾的舆论通过媒介晓谕,传达与大众。除此之外,各种原因交织,灾象仍在1935年呈现,灾后救济问题成为最迫切研究的议题,大众媒介通过报刊杂志的舆论喉舌,掀起又一轮舆论热潮。
3.3.1 政府救灾职责与国民赈灾义务 监督政府是新闻媒介舆论监督的天职。对灾害救济而言,政府与民间社会处在何种位置,舆论的监督起着导向作用。1935年灾患已成,各省向国民频发乞赈电报,国民政府召开一系列救灾治水机关会议,并派许世英前往灾区调查。以《大公报》为代表的媒介为灾民困于洪水中苟延残喘的情形焦虑万分,希望政府当局以“速速救命”为先,对于救灾危机时刻政府却迟迟未见具体救灾措施,媒介此时以激发民众态度,给国民政府施加舆论压力,以影响政府决策为目的,掀起一轮“政府与救灾”问题的言论波澜。以《大公报》为例,发表了《政府与救灾》、《政府应努力筹赈》、《政府救灾宜快》等诸多时评、短评,劝诫与呼吁,批评与献策,字里行间表达对政府尽快出台救灾政策的殷切期望。
救灾也是国民应尽的义务。报纸媒介直接面对的是广大读者受众,以《大公报》为代表的报界发起“请求全国读者助赈”的号召,晓之以情动之以理,句句直指读者心扉,奉告全国各界人士,在社会愈穷,国家愈危的世事艰难情势下,更应表现中国人互救自救的精神!
3.3.2 灾后救济方法讨论 灾后救济可分为消极和积极两方面,历年赈灾都为惯例。1935年灾后救济也包括以上内容,除上述救灾方式外,各种灾后救济的言论通过新闻媒介发布于众,形式多样。
节约拯灾。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源远流长。马相伯先生劝告国人节约拯灾文章并委托报界刊载,以唤起全国民众一致努力开展节约运动以赈灾民,“节约其衣食住行之所糜费,以赈彼灾黎,夫减吾人物质上无谓之享受,而救彼无量数灾黎之生命”。救济不能空言,精神上的怜惜,是无补于事的,必须付诸于实际上的救助“节约服用,慷慨解囊”[16]。《大公报》发出家庭节约救灾倡议,“节省一点费用,就可救活灾民”。
挪移他款。1935年灾情惨重、灾区广阔、灾民众多,而国民政府财政枯竭,社会同样枯窘不堪,如何筹集巨款赈灾成为各界议论的焦点问题。各种筹募方式也通过新闻媒介传达于大众。《大公报》通过短评建议:各省先挪移部分军政费,同时尽可能地实行扣捐薪俸,以便提垫。灾重各省共同要求政府,举办一种特别赈灾附加税专充救灾之需。社会方面募捐,各慈善团体联合,共同负责劝募,所得之款,由联合总机关分发各灾区应用。
政府救灾款项不足只有移挪他款,《大公报》又提出三种建议:一是由国府通令全国京内外各机关,停止一切公物建设,一律告其缓办;二是由中央党部自动提议,在全国党务费五百八十七万零八百元经费内撙节半数或三分之一拨充赈灾;三是采纳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建议以铁路或邮电附加税作抵,要求银行垫借若干万[17]。
发行公债。发行救灾公债是一种筹募方式,针对是否发行,社会各界也颇有异议。部分人士认为“此种公债,名目虽属救济灾害,实则无意用于生产建设”,加大政府财政负担,但多数人士还是主张政府发行救灾公债从事工赈、农赈,“一方面既可开发产业,一方面又可容纳灾民,未始不是于民穷财尽中的一种筹划赈款办法”[18]。
募赈宣传。1935年大灾,中国民族重大灾祸,全国各大小城市,做普遍宣传呼吁,使全国人民皆知同胞在苦痛悲惨中生活,发救护同胞同情心。救灾之外,对国民教育也有重要意义。新闻界提出“实行”宣传方式。报章刊登善团鸣谢捐款广告外,详细收支内容,用徵信报告公之于众。全国各大小城市通过标语形式进行筹募宣传,由社会各界自动组织救灾团体,在城市中心各处,悬挂标语及壁报等,报告灾情,劝告捐款。各地电影院,每日附映灾情影片,并在荧幕上报告收款机关所在。各级学校有组织进行赈灾宣传。
防疫。灾后防疫与赈济同等重要,灾后引起的各种传染病也是引起灾民大量死亡的重要原因。7月23日《大公报》刊登了署名素端的《水灾区域宜及早注意防疫工作》一文,希望引起各方注意。
1935年水旱灾害之年,大众传媒在灾害救助过程中客观真实的传递了灾害信息,有效的宣传了社会各界救灾活动并积极引导救灾言论,动员社会整合救灾资源,体现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成为救灾中重要的社会力量,其积极作用对于当代大众传媒参与灾害救助仍有借鉴意义。
[1]大公报[N].1935-08-12.
[2]申报[N].1935-07-10.
[3]申报[N].1935-11-15.
[4]大公报[N].1935-09-15.
[5]大公报[N].1935-09-12.
[6]大公报[N].1935-08-23.
[7]申报[N].1935-08-22.
[8]大公报[N].1935-08-29.
[9]大公报[N].1935-10-17.
[10]大公报[N].1935-10-19.
[11]贝克.防灾与赶办水利事业[N].申报,1935-07-03.
[12]水害痛言[N].大公报,1935-07-22.
[13]李仪祉.纵论河患[N].大公报,1935-08-31.
[14]孙起烜.最近水灾之状况及其救治[J].中国实业杂志,1935(7-12):1858.
[15]根本预防水灾办法[N].申报,1935-01-13.
[16]劝告国人节约拯灾书[N].申报,1935-07-20.
[17]政府应努力筹赈[N].大公报,1935-08-28.
[18]作舟.关于救灾[J].东方杂志·东方论坛,1935(17):3.
Modern Mass Media and Disaster Relief——A Case Study of Flood and Drought in 1935
Sun Yusheng,Xu Yuande
(Institute of Society and Politics,Anhui University,Hefei,Anhui 230039)
The frequent natural cala mities in modern China attract high attention of mass media,mainly including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With accurate and timely news reports,the mass media records the frequent natural calamities of various periods and their impact on Chinese society.The mass media also directly joins the social activities of disaster precaution and victim relief,and shows a strong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for the society and people's livelihood,and display its function of social interaction.
Modern China;Mass Media;Natural Calamities;Disaster Relief
K03
A
1674-1102(2011)04-0017-07
2011-04-18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09YJA840001)。
孙语圣(1967-),男,安徽肥东人,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社会经济史。
[责任编辑:胡惠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