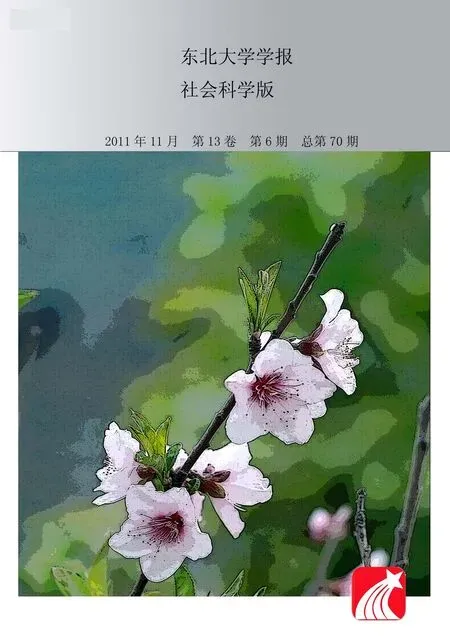技术理性在中国
----一种对技术理性的后现代解读
2011-03-31吕乃基
吕乃基
(东南大学STS研究中心,江苏南京 210096)
目前,学术界的主流对技术理性大体持批判立场,也有为数不多持肯定意见者[1],“技术理性是一种追求合理性、规范性、有效性、功能性、理想性和条件性的人类智慧和能力。当前中国需要大力弘扬、推进技术理性”[2]等等。本文基本上不涉及这些批判本身,而是试图以博弈论对技术理性形成和运行的语境及技术理性的主体作进一步分析,并由此考察一般意义上的技术理性在中国的特殊样态。鉴于本文是对抽象的技术理性作一般和特殊的语境分析,并揭示其与主体的关系,因而也就成为一种对技术理性的后现代解读。
一、 问题的提出
有人问,为什么早在公元前就有哲学家、文学家、科学家,而迟至18世纪才出现经济学家?理由是,其一在于亚当·斯密本人的修为,特别是接受近代科学精神和方法的熏陶,从而能够如科学家那样由纷繁的现象揭示本质。其二,经历由传统社会、中世纪、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漫长岁月,社会,在某种程度上如同自然界那样,终于(至少在相当程度上)排除了王公贵族、教会僧侣等各种利益集团的控制和干扰,在经济领域提供了在相当长的时间(几十到上百年)和广阔的空间(西欧)范围内相对一致和稳定的经济上的案例[3]。
同样,韦伯和马尔库塞等人之所以得以从近现代的科学技术中抽象出工具理性和技术理性也是由于这样的两个前提:其一:提出者具有必要的抽象概括能力;其二,西方社会语境----市场经济和工业革命----提供了在相当长的时间和广阔的空间范围内相对一致和稳定的相关案例。这样的语境可以归结为:工业革命和博弈,前者表明技术的应用和发展的广度和深度,后者的要义是,博弈在空间上的广泛性和时间上的长期性,也就是重复博弈,以及博弈规则的有限和相对稳定。前者较易达到,且各国差异不大,而后者却会有很大障碍并千差万别;本文以考察后者为主。正是这种在广泛时空中的一致和稳定,提供了类似于自然界那样普遍的现象,由此方可能抽象出工具理性和技术理性。既然只有在这样的语境下才能抽象得到工具理性和技术理性,那么反过来说,正是在工具理性、技术理性,以及科学理性的共同作用下,才有如此一致和稳定的社会,才有科学和技术的发展,以及内生型国家的现代化。
韦伯和马尔库塞等提出的工具理性和技术理性具有以下根本特点:其一,蕴涵了人的本性:以最小代价或成本获得最大收益。也就是亚当·斯密的“经济人假设”,实际上与自然界的“最小作用量原理”一致。技术理性可以说是自然界的普遍规律在人类社会的表现。其二,是对“经济人假设”的限定,或者说是经济人假设在以人和自然的关系为基础的实践活动中的表现形式。工具理性和技术理性,顾名思义,前者意在使用工具,主要旨在应对自然。以人与自然的实践关系为基础,其关键在于自然对于各色人等的一致性和持续性。其三,这样的一致性和持续性延伸到围绕着人与自然关系的人际关系和人与自身的关系,排除后二者的特殊性对前者的影响和干扰。上述三方面----人与自然、人际,以及人与自身关系----的一致和延续,构成了类似于自然界那样的客观对象,这是技术理性之所以在实际上存在,在认识上得以被韦伯等人所抽象的前提。
由此可以进而探讨中国语境下的技术理性。中国不仅没有科学理性,而且也不存在技术理性。技术理性是西方语境下的产物。因而学界对技术理性的批判,大致是跟在西方学界后面人云亦云。
二、 博弈:技术理性的要义
粗略地说,博弈,包括博弈的内外因素,前者包括局中人、博弈的次数以及博弈的规则等;后者指博弈所处的环境[4]。局中人也就是博弈者,是存在直接利害关系的决策者,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独立决策,承担风险,以及由此得到的利与弊。
规则的要义是,得到所有各方的参与或认同;各方之间的平权,以保证博弈的公平以及规则的有限和可操作。有限方可操作并有效,可操作意味着便于自身遵守和对其他博弈者的监督。规则的无限等于没有规则。规则应公平、普遍适用和稳定有效,以有助于博弈者在胜负中汲取经验教训、积累知识,以及培育信用(亚当·斯密早就作了论述),从而减少社会运行成本。反过来说,正是在长期和普遍的博弈中,才可能形成这样的规则。局部和临时的规则将多次博弈转为一次博弈,可能导致失信、背叛和人性的堕落。
技术理性主要涉及到三大博弈:人与自然界博弈、与他人(主要是竞争者和消费者)博弈,以及与自身博弈。
1. 人与自然博弈
人与自然的博弈是西方文化的起点与核心。技术理性开门见山的要义即有效和可控。生产方在生产中面对自然界需要有效和可控,消费者在使用商品----自然性与社会性的统一----时同样要求有效与可控。
自然界是这样一个对手:对于所有的博弈者一视同仁(一些研究者可能因对某地所特有的对象如地质和生物的“近水楼台”,而有“先得月”之利);是这样一个对手:在一定范围内,可以说“道不变,天亦不变”,因而是“有限规则”和“重复博弈”;是这样一个对手:一旦超过范围,或者人类变招,自然一定会出新招应对,奉陪到底,由此导致演进博弈。正是面对这样一个普遍、持续以及不可穷尽的对手,人类才得以在各项博弈中不断成长、进步,同时也认识到,永远不可能彻底认识和战胜自然,必须尊重对手,进而与对手和谐共处。
虽然其他活动如艺术等也会有所涉及,但人类主要通过科学技术与自然界博弈,科学重在认识,技术重在实践。虽然各民族都有自己特殊的技术,有过辉煌的成就,但大多基于难以重复和积累的经验,难以共享和传承。唯有近代之后西方的技术,得到来自科学的强大支撑,方能在与自然的博弈中步步为营,有所前进。科学活动育成科学理性,技术活动则提炼出技术理性。
除了技术,对技术理性的贯彻、体现与落实,能达到如此之精湛和充分的领域,就是体育了,甚至或许可以用体育理性来代替争议不断的技术理性*如果真是如此,学界不知是否会以同样的热情和力度批判“体育理性”乃至体育本身。。
体育,首先是要完成某项运动,无论是个人锻炼身体,还是人与人之间的竞技,同样需要有效与可控。失控,意味着失败甚至伤害。除了某些几乎完全是自娱自乐也就是没有博弈的项目,都会考虑投入产出比,即使投入的只是时间。举国体制,即把资源集中到少数人身上,寄希望于以较少投入迅速培养出世界冠军。最后,也是可持续。反例是服用兴奋剂,结果不可持续。在貌似非理性*非理性的典型当属这句话:“足球是圆的”,意味着偶然性----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的体育背后,实际上是深刻的理性----技术理性。
为什么在人的所有实践活动中,科技与体育如此相似,以至可以提出所谓“体育理性”?这是因为,无论是科技还是体育,在博弈的各方中都有一个共同的参与者----自然。科技自不待言;体育,在人与人竞技的背后同样有一个虽未直接参与,却时时处处在场的角色:自然界,包括外部因素,如时间、万有引力、摩擦力、阻力等,以及人自身的生理和心理局限。可以说,体育运动与技术理性有着先天的血缘关系。希腊,作为西方文化的源头,同时也是奥运的发祥地,并非偶然。现代奥运精神的“更快、更高、更强”,正与摩尔定律所提倡的“更快、更小、更便宜”不谋而合,在现代意义上印证了体育与科技在与自然博弈中的一致性。
2. 人与他人博弈
人际博弈会在相当程度甚至根本上影响人与自然的博弈,改变其胜负的结果。如果说,自然界对与之博弈的人一视同仁,因而对于所有人都是公平的话,那么人际博弈就千差万别。技术理性没有出现在地球的其他地方和其他时间,而是发生在近代西欧,发生在启蒙运动之后,发生在市场经济萌生的地方,这是因为市场经济,意味着围绕着人与自然博弈的人际博弈和人己博弈的普遍和一致。技术理性孕育于特定的社会背景之中。
如果说,在人与自然的博弈中的人可以泛指人类,那么在人际博弈中,就须分出你我,在博弈论看来就是“局中人”或博弈者。
局中人,就是技术理性的主体。韦伯和马尔库塞在抽象出技术理性之时,便舍弃了技术理性的主体。后人的批判,即使不是所有的话,绝大部分也都舍弃了实实在在的个体,所涉及的主体大致是人类,稍加限定,是浸染乃至深陷于现代性的人类,再进一步限定,则为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或者干脆就是----资本。一句话,不是“此在”,此时此地此情此景中的人。实际上,正是千千万万个个体----个人、形形色色的公司----的实践活动孕育并实践着技术理性。什么样的主体(以及主体间的关系),对于人和自然的博弈,对于技术理性能否、在多大程度,以及由什么途径得以贯彻,至关重要。所谓对技术理性的后现代解读,其一为语境相关,其二即主体相关。
例如,有效,对谁有效?可控,由谁控制?经由什么手段实现控制?
投入产出比或/和功能价格比,谁来投入,产出归谁?由谁出价,谁享用功能,谁承担后果?等等。技术理性的主体须参与竞争并享受成功的果实或承担失利的后果。显然,这里涉及主体的独立性,主体之间的平权。主体的独立性指产权清晰,拥有自主的决策权。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自中世纪后期西方社会经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科学革命和启蒙运动的一系列变化,所有的发展都是为了摆脱传统社会,不论是血缘宗法还是强权,不论来自教会还是世俗,对社会资源,在当时主要是土地和劳动力的垄断和控制,去除来自市场外权力等的干涉,搬开一切障碍,扫除束缚,让资源自由流动,主体自由选择。到了亚当·斯密的时代,摆脱了束缚的个体,终于可以在公平的规则下,独立自主地展开与自然的博弈。只有这样的个体,才是技术理性的主体;同时,也只有统一、开放、竞争和有序的市场,才会培育出这样的个体。统一,意味着所有的局中人面对所有的生产力要素自由选择;开放,表明市场在空间和时间上没有边界,符合资格者可以随意进入、继续,以及发展;竞争,是发展的动力;有序,意味着规则,而规则,是博弈的核心。市场的要义是交换,规则即保证交换在自愿和平等的原则下进行。由此再次说明,技术理性并不仅仅是技术活动的抽象,而是特定社会在特定时期的产物。
主体的独立和平权已经涉及生产方之间的博弈。
必须指出,技术理性的主体或局中人还包括公司的员工。正是他们和工会所具有的强大的谈判力量参与博弈,迫使公司不能只是靠压榨工人,而是把主要精力集中到与自然的博弈上来。后者即意味着科技的进步。
局中人不可或缺的一环是消费者。技术理性中的投入产出比和功能价格比,前者是生产方的计算,后者是消费者的计算,关键在于这两项计算的联动。生产方不能只顾自己的投入产出比,必须顾及,实际上是取决于消费者是否对其产品和服务买账,而消费者的功能价格比是否如愿,又依赖于生产方能否满足其需求。生产方与消费者的博弈,一方面保证消费建立于人与自然博弈的基础之上,另一方面保证人与自然博弈的目的和方向。
3. 人与自身博弈
人与自身博弈大致有三种情况,对财富的追求、挑战自然,以及激发和满足更高的需求。在市场经济兴起之初,新教伦理提供了这样的动力。关于这一点已经有大量论证。现代与自身博弈的典型当属乔布斯(本文写作和投稿时乔布斯尚在世,刊出之前已去世……)。
这就是西方文化“意欲向前”的精神,梁漱溟在其“文化三路向”说阐述了这一点[5]。
在与自身的博弈中还有极其重要的一环:遵守规则还是违规。要是违规可以以较小的代价----成本、可能的惩罚,以及良心的谴责,后者即在于与自身的博弈----获取博弈的胜利,那么违规就会大量发生,最终瓦解所有的博弈。西方文化的“人之初性本恶”引向法治的惩罚,天国、地狱和骑士的荣誉通往内心的守护。
技术理性,是特定文化也就是西方文化的产物。
人与自身博弈,与他人博弈,以及与自然博弈,这三大博弈构成了技术理性的基础。个体间以与自然的博弈为基础,以与消费者的博弈为导向而展开的博弈,在这样的博弈中形成技术理性。其中,与自然的博弈具有第一性的地位。自然界不仅作为博弈中的“局中人”,而且在相当程度上是规则的制定者。这是因为自然界对所有人的一视同仁,以及对于所有遵纪守法者的回报和违规者的报复。与他人特别是消费者的博弈赋予技术理性以价值和方向。与自然的博弈和与消费者的博弈规定了个体在市场中的“输赢”之含义。输赢,不是权力的此消彼长,也不是意识形态的好恶[6]。由此保证了规则的稳定、透明、普遍和公平。与自身的博弈在于意欲向前和遵守规则。正是在技术理性的“河床”(维特根斯坦语)中,在科学技术的基础上,社会沿着马斯洛需求层次的方向提升。
技术理性不是抽象的概念,与特定的语境特别是博弈规则相关,与博弈的主体相关。
三、 中国语境下的技术理性
主要考察古代和现今两个阶段。前者自古至鸦片战争,后者主要是1949年后,中间的百余年处于动荡之中,故不涉及。
1. 古代
中国古代技术发达,为何没有提出技术理性?
(1) 人与自然的博弈
在梁漱溟提出的人的三大关系上(人与自然、人际、人己),中国以人际关系为核心。在天人合一的文化中,在自然经济的环境中,人与自然主要是伦理和审美的关系,如风花雪月,无关乎博弈;即使实用技术,往往也附加了太多的文化色彩,掩盖乃至于淹没了人与自然的博弈功能。而真正涉及与自然博弈的技术则被贬为雕虫小技,以及主要靠经验积累和偶然性,得不到来自科学的支撑,难以共享、传承,往往失传,更谈不上改进。
至于与体育相关的武功,或者每每来自机缘或秘籍,或者神乎其神违背自然规律,自己一不小心还会走火入魔。兵器,本来实实在在属于人与自然博弈的产物,然而,或者在飞花摘叶和比拼内功时边缘化,或者依靠“玄铁”之类而陷入神秘主义。
(2) 人与他人的博弈
在古代中国,主要是没有交换或很少交换的自然经济,因而不构成生产者与消费者,以及生产者之间的博弈。人际博弈的主渠道是围绕官本位展开的科举考试和在朝廷展开的权力倾轧。在文人墨客,比拼的是琴棋书画。在必须考虑到人与自然博弈的场合如战争,在天时地利人和中,把“人和”放在首位。这固然没有错。然而若是极端夸大,再加上“兵不厌诈”这样在博弈中的无限策略,把人的计谋在战争中的作用发挥到极致,大大降低了自然作为幕后参与者的地位。
有趣的是,中国人在人际博弈中同样有对于有效、可控和投入产出比的精妙算计。在某种意义上说,其对人性的测度,分寸的拿捏,以及时机的把握,令世人叹为观止。令人遗憾的是,古代中国基本上不发生人际之间就人与自然的关系展开的博弈。人际博弈和人与自然的博弈无关,与技术理性无缘。后文还将述及“送礼文化”的影响。
(3) 人与自身博弈
梁漱溟认为,中国文化“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随遇而安*中国并非没有“向前”的“意欲”,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此处说的是主流。,求中庸之道,不求奋斗,知足常乐。重义轻利,对财富和创新的追求不强烈。
无论从何种角度看,中国古代社会与技术理性都相去甚远。
2. 现代
(1) 人与自然博弈
在新中国建立初期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口号中,包含了人与自然的博弈。然而其一,除了两弹一星等少数领域外,这种博弈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意愿,违背自然规律,结果只能适得其反;其二,即使如此,还是不断受到“中国特色”人际博弈的冲击,运动不断,“以阶级斗争为纲”。在与自然的博弈中担任主角的科技人员或靠边站,或接受再教育。他们的知识,被代之以与古代中国工匠一脉相承的工人农民的经验。有道是,“高贵者最卑贱,卑贱者最聪明”。
改革开放以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唯GDP论,从根本上说,与计划经济年代的现代化并无二致,但是少了阶级斗争和乌托邦类型人际和人己博弈的干扰。
体育同样是有趣的事例。改革开放前后,体育基本上是一脉相承,也就是举国体制。这样的博弈对于他国的参赛者不公平,对于本国公民不公平;前者不可能享受举国之力,后者则因此而被剥夺或至少减少了参与的机会。
(2) 人与他人博弈
上述有限的人与自然的博弈依然受到人际博弈的深刻影响。
在计划经济岁月,一切按照计划,不存在彼此的博弈,因而也就不存在独立的局中人。在集权以强调效率的国度,国家是否成了技术理性的主体?看来“15年超过英国”好像是国与国的博弈,其实不然。封闭的中国基本上没有在全球市场上发生什么交换。可以认为两弹一星是博弈的产物,但这不是商品,不涉及功能价格比。
不存在作为局中人的生产方,也不存在作为局中人的消费者,当然更不存在生产方与消费者的博弈了,凭票配给,消费者无选择和讨价的余地。提供产品的国家和使用产品的百姓之间不是博弈,而是恩惠和感恩的关系。至于工人,则由意识形态置换博弈关系。实际上,在计划经济年代,全部人际博弈就是以意识形态的对错来确定当事人的出局与否。
改革开放以来,上述状况发生了深刻变化。
民营经济的崛起意味着在经历了历史上的曲折和断续后,中国再度有了博弈的局中人,也就是技术理性的主体。然而情况并不简单。
影响当代中国博弈的首要因素当属政府所握有的巨大权力。其一,权力在于支配大量的资源,主要是土地、石油等自然资源,以及金融;其二,权力在于制定政策和披露消息。国企,作为共和国的长子*笔者曾有幸与“五矿”的一名小职员对话,称其为“国企”。他拉长了声调说,我们是央----企----。,自然享有所有的优惠。在国企的势力范围,民企难以与之博弈,即使在看似充分竞争的领域如房地产市场,共和国长子照样攻城略地,所向披靡。国进民退,“央企凶猛”(《南方周末》的通栏标题)。民企若要有所作为,往往不得不拜倒在权力的脚下。国企不必博弈,民企没法博弈。在这样的人际博弈中,与自然的博弈无关紧要,而掠夺、挥霍和污染却随处可见。与此相关的是,在强大的官本位中,公务员炙手可热,且越来越热,“下海”,已是遥远的上世纪的“传说”。
与此同时,消费者处于弱势地位。面对垄断,面对高油价、高通胀、高房价,消费者很少甚至没有选择余地,社会的“自愿性”渐次隐去。在消费者弱势的情况下,所冀望的扩大内需难以实现,更重要的是,技术理性得不到来自消费者在博弈中的均衡、拉动和引导。譬如,在事故频出的铁路部门,乃至发生追尾坠桥重大事故,消费者究竟有多大选择权和追诉权?不顾消费者意愿的高铁要把中国带向何方?
其次,在中国盛行数千年的送礼文化在眼下得到进一步“发扬光大”。古代的典型是郑和下西洋,泱泱大国,泽被天下。在国内则是处处时时的“皇恩浩荡”,民间的规范是礼尚往来,以及来而不往非礼也,等等。现如今,国家层面依然延续恩惠与感恩,民间的送礼也愈演愈烈。送礼,作为人的一种社会行为,并无不可,然而过度蔓延,甚至取代正常的交往,就不利于科技发展和社会进步(在西方,送礼被限制在十分有限的范围)。因为,无论在国家还是个人层面,送礼打断了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博弈关系。在送礼的关系链中,购买商品的人不使用商品,而使用者不买。因而,前者不在意商品的功能价格比,有档次,有气派(过度包装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送礼文化的结果),足矣;后者不在乎商品的价格:不要钱,还说什么?实在无用,送到街头巷尾的“礼品回收”处。简言之,就是送方出价格,收方用功能,功能价格比断裂。维修也成问题,买主持发票去报销,用者手上无发票。这样,生产方不知消费者的需求,后者也无从向生产方反馈使用的意见。在技术理性中,消费者的引导作用断裂,对生产方起作用的是购买者对奢华的追求,以及由此对技术理性的扭曲,偏离与自然博弈的正途。
与送礼文化相映成趣的是“献礼”文化。恩惠受的多了,就要回报,有多种途径,其中之一就是献礼,其后果就是违背规律。最新的事例即事故频发的高铁,一再返修的南京南站。献礼而违规的影响一直深入到社会的每一个毛孔。在中小学数学的应用题中,有相当多的题目是:原计划如何,现在提前了。技术理性被踩在脚下。如果说还有什么理性的话,那就是政治理性。
第三,规则的制定和实施。
没有规则,这既是中国数千年来的特色也是痼疾。传统社会尚有伦理道德,计划经济岁月有意识形态,现在是伦理道德世风日下,意识形态退避三舍,再嘹亮的红歌也代替不了规则刚性的制约。
当前,中国的“规则”(如果还称得上是规则的话)大致有三个特点。其一,数千年传统的影响,从兵不厌诈到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其二,压倒一切的权力。行政力量各行其是,官员随心所欲干预,下不为例,个案处理,比比皆是。官员往往既制定规则,又入场竞技,规则不具备对于局中人的超越性。其三,规则的模糊和“原则”在规则内留下“广阔天地”,而执行不力,可以在规则外自由“穿越”。剩下的只能是一次性交易,市场的“重复性”几乎荡然无存,而后者是博弈走向合作并演进的必要条件。正因为此,亚当·斯密预期的道德规范难以形成,必然导致信用缺失。在如此这般的“规则”下,在一次性博弈中,遵纪守法者必然输给形形色色的违规者。博弈走上了逆向的“演进”之路,那就是劣币驱逐良币。
世界工厂是个特殊案例。加入WTO,本以为中国的企业会面临世界舞台的博弈,其实不然。中国随即被纳入全球产业链,成为世界工厂,当然也为GDP作了巨大贡献。然而作为世界工厂,一手拿着图纸,在上游无需介入与自然的博弈,别人已经做过,“有效”与“可控”已经成熟,只需依样画葫芦开动流水线即可;一手接过订单,在下游无需与消费者博弈。剩下要做的只是使用,使用自然资源,使用人力资源。前者有地方政府的种种优惠,后者除了开胸验肺和以死抗争几乎没有谈判能力,同样还有地方政府撑腰。如果说还有同行间博弈的话,那就是在“使用”上的拼比:谁掠夺得更狠,以及地方政府间的博弈:谁的条件更优厚。只有一点与技术理性有关,那就是还讲点规则。遗憾的是,那只是对外。
(3) 人与自身博弈
现代中国的人与自身的博弈同样深刻影响人与自然的博弈,以及人际博弈。
在计划经济岁月,或者狠斗私字一闪念和割资本主义尾巴,排除任何逐利之举,或者违背规律“15年超过英国”,当然无技术理性可言。改革开放后,中国一度走上正轨。然而眼下是,投资领域投机成风,消费领域奢侈品独领风骚,垄断行业不思进取,竞争领域假冒伪劣。还有政绩工程和献礼工程对规律的违背。遵纪守法、开拓创新、营造品牌,扎扎实实展开竞争者步履维艰。
应该看到,进入现代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不过除了少数情况外,从这些成就本身和获得的过程中确实难以看到技术理性。权力对资源的控制使得局中人不能按自己意愿选择,局中人的主体地位或被扭曲、或处于弱势,彼此不平等和不均衡。规则或随意、缺失、不透明,或形同虚设。局中人,如果不是说所有的话,大多不想或至少没有按规则博弈。
总体而言,中国没有技术理性。以前从未有过,现在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没有。既没有这样的语境,也少有合格的技术理性的主体。既然如此,笔者不明白的是,我们在批什么技术理性?
参考文献:
[1] 王树松. 论技术合理性[D]. 沈阳:东北大学文法学院, 2006:11.
[2] 张明国,张恒力. 追问技术理性----技术哲学论坛研讨会综述[J]. 哲学动态, 2006(5):71-72.
[3] 海尔布罗纳. 几位著名经济思想家的生平、时代和思想[M]. 蔡受百,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4:9.
[4] 龙游宇. 信用的博弈演化研究[D]. 成都: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2007.
[5] 卢艳霄,张丛林. 梁漱溟“中国社会结构特殊论”及其现代价值[J]. 广西社会科学, 2008(4):47-50.
[6] 赵鼎新. 战争催生欧洲现代化?[N]. 南方周末, 2008-10-08(D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