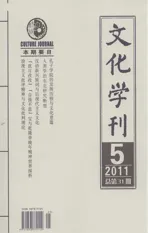人类学的东北研究断想
2011-03-20吴世旭
吴世旭
(沈阳师范大学社会学学院,辽宁 沈阳 110034)
人类学的中国研究曾经有过世界性的声誉,并在东南研究和西南研究方面形成了具有“范式”特征的学术传统,但对东北却很少加以关注。如果说地方经验是人类学思考的源泉,那么,东北的地方经验同样蕴涵着广阔的理论空间。本文主要探讨如何通过东北的地方经验展开人类学的研究,并以片断的思考求教于方家,希望能够以此推动人类学东北研究的延展与深化。
一、人类学东北研究的学术背景
所有的人类学想象都源于地方经验,这与人类学生成的历史、政治背景紧密相关。在现代世界体系形成的过程中,主导这一历史进程的欧洲人“发现”了西方以外他者,而正是对他者的研究促成了人类学的诞生。在古典人类学时代,地方经验通过传教士和殖民地官员等的异域记述进入摇椅上的人类学家建构的宏大叙事之中,成为进化论与传播论的基本素材。现代人类学兴起之后,研究者走出书斋进入到地方之中,通过直接的体验与观察所获得的地方经验,来建构不同人类学理论。
尽管中国的地方经验也得到了古典人类学的关注,但相对于西方的汉学研究,这种关注是微乎其微的。直到现代人类学的兴起,人类学的中国研究才喷涌而出,其动力则主要来自本土人类学者在特定时代的学术追求和社会使命。然而,与太平洋上的岛屿和非洲、美洲大陆不同,中国不仅地域广阔,而且有着悠久的文明史。这表明人类学的中国研究既具有空间意义上的“再地方化”的学术潜能,也具有时间意义上的“历史化”的学术前景。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虽然受限于西式“社会”与“文化”概念之处甚多,人类学的中国研究仍然在上述两种进路上收获颇丰,不管是早期的社区研究,还是随后的宗族研究、区系研究和民间宗教研究,乃至近十几年来涌现出的族群研究、区域研究和文明研究。遗憾的是,这些研究及其反思大都基于中国东南和西南的地方经验而展开,中国东北的地方经验则几乎无人问津。这种“偏向”固然有其特定的历史原因,但显然并不意味着东北的地方经验无足轻重。尽管可以在东北找到东南 “汉人社会”、西南“族群”的影子,也可以把东北的山林和草原比作东南的海洋、把东北的“边地”比作西南的“藏彝走廊”,但是东北毕竟是东北,和所有的地方经验一样,它对于人类学研究的价值在于其“地方性”。
在中国的语境中,“东北”最初意指一个地理方位,随后又逐渐演变为一个区域概念,二者都是“从混沌到秩序”的具体表现。东北的地方经验便寓于这种地方化的历史进程之中。“东北”之名很早便见诸史籍,如《周礼》有“东北曰幽州,其镇山曰医巫闾”的记载。幽州之设与镇山之封,表明中国东北方向的人与地已经被纳入到以“天下”为核心观念的政治治理之中。这里的“东北”主是一个方位概念,而作为一个区域概念的“东北”最迟到辽代便已出现。在这个过程中,政治与行政力量对东北区域概念的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如今所言之“东北”就是这种作用不断延续的产物,其具体所指包括今天的辽吉黑三省和内蒙古东部地区。在从“幽州”到“东北”的漫长历史进程中,对东北之地的称呼此起彼伏,暗含其中的则是政治力量的进退与交锋、文化观念的交融与碰撞和社会形态的延展与变迁。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东北作为一个地方得到了不断的营造,并形成了具有丰富内涵的“地方性”。
东北的 “地方性”无疑蕴涵着广阔的理论空间,思考如何以东北的地方经验展开人类学的研究,在人类学的中国研究日益兴盛的今天,显得尤为必要。这种思考不仅需要在学术史的脉络中对人类学的东北研究加以回溯,而且需要结合人类学中国研究的不同“范式”乃至其他学科的相关研究,在比较之中寻找人类学东北研究的进路,并在具体的经验研究中不断探索。
二、人类学东北研究的学术遗产
在人类学的中国研究中,东南研究和西南研究成果显著,分别以汉人社会研究和族群研究形成了具有“范式”特征的学术积累,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人类学进入中国之后本土学者的 “社区研究”和相继而起的不同理论及其反思。实际上,早在中国“社会学学派”兴起前后,已经有人类学家进入东北展开研究,其中包括鸟居龙藏、史禄国和凌纯声,他们的学术出身各不相同,关涉东北的研究成果也各具特色。
鸟居龙藏是个自学成才的人类学家,其学术成就主要表现为,融考古学人类学于一体,结合实地调查和历史文献,在重视考察古迹文物的同时,对不同族群的历史、体质、语言、宗教和习俗进行综合性的研究。从1895年开始,这位具有古典气质的人类学家先后在东北进行了十余次的实地调查,著有《南满洲调查报告》、《蒙古与满洲》、《史前满蒙》、《从人类学及民族学看东北亚》、《满蒙古迹考》、《辽代画像石墓》和《黑龙江和萨哈林岛北部》等大量相关作品。鸟居龙藏在理论上并无太大建树,但作为人类学东北研究的拓荒者,他对东北古迹与文化的记述却是细致而详实的。如何从这些记述中挖掘理论建构的潜能,是从事东北研究的人类学者必须深入思考的问题之一。
如果说鸟居龙藏以其全面的记述为人类学的东北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民族志素材,那么,史禄国在东北及其周边进行的人类学研究不仅在民族志记述方面成就显著,而且在理论建构上为后人留下了值得深究的学术遗产。这位处于古典与现代之间的人类学家在法国巴黎大学人类学院受过正规的教育,随后在圣彼得堡大学和帝国科学院从事研究,“十月革命”之后流亡我国。1915年到1918年之间,他数次在东北进行实地调查,后来出版了 《通古斯人的社会组织》、《满族的社会组织》和《通古斯人的心智丛结》等著作。史禄国以通古斯人的研究闻名于世,并且早在族群研究兴起的几十年前便提出了民族性和心智丛结的概念和理论,来解释族群认同问题和不同文化间的历史互动。尽管多年在中国生活并从事研究,但他的人类学研究却迟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如何重新审视史禄国的东北研究及其贡献,并从中吸取理论养分,是人类学的东北研究不可回避的基本任务。
凌纯声是本土人类学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他毕业于国立东南大学教育系,后来留学于法国巴黎大学,师从莫斯等人,归国后进入“中央研究院”,在社科学研究所民族学组任研究员。1930年,他和商承祖在赫哲族聚居的松花江下游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实地调查,并于1934年出版了《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这个研究“被认为是中国第一次正式的科学民族田野调查”,其成果也有“一本极其完整的科学民族志”的学术声誉。在这本专著中,凌纯声结合历史分析和田野调查,对赫哲族的历史源流及其与周边民族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论述,并分别从物质、精神、家庭和社会四个方面对赫哲族的社会与文化展开了详细的描述,同时也对赫哲族的语言和民间故事加以专门的整理与记述。对实证研究和历史分析的重视,在凌纯声的赫哲族研究中表现的尤为突出,这不仅得益于欧陆民族学传统的影响,也代表了中国“南派”人类学的研究取向。本土人类学最初的经典著作以东北的地方经验为对象,本身就耐人寻味,其在研究方法上的继承与融合更是值得后辈学者深思。
对于人类学的东北研究来说,上述三位学者的研究构成了不可多得的学术遗产,1930年代末之后人类学研究在东北近乎缺席,则使这些遗产显得尤为珍贵。值得一提的是,1980年代末以来也有少数人类学者以东北的田野经验展开研究,阎云翔是其中的佼佼者,但他的研究并未太多地关注东北的“地方性”,而更像是中国人类学早期“社区研究”的一种延续,不管是研究方法还是理论兴趣。
三、人类学东北研究的学术进路
尽管前辈学者的研究并未使东北成为像东南和西南那样备受关注的“学术区”,但这个人类学“边疆”所具有的学术潜力却非常值得期待。通过东北的地方经验展开人类学研究,需要在东北的“地方性”中挖掘学术想象力,这在以往的研究中已经有所体现,而人类学的东南研究和西南研究乃至其他学科的东北研究同样有助于这种想象力的激发。
从研究方法的角度来看,以往的人类学东北研究不仅注重经验性的实地调查,而且对历史文献也比较倚重;既有区域性的研究,也有以社区为单位的研究。如何将实地调查与历史文献更好地结合起来,对东北的社会与文化进行更充分的记述,是人类学东北研究面临的首要任务。在具体实践的层面上,由于东北内部同样有着“再地方化”的历史,可以按照不同的分类标准做不同类型的民族志研究。比如,以人文地理为标准,既可做医巫闾山或长白山的区域民族志,也可做辽河或黑龙江的流域民族志;以经济方式为标准,既可做村庄民族志,也可做都市民族志;以民族划分为标准,既可做汉族民族志,也可做满族等其他民族的民族志。
不管是做何种层次的民族志,其目的都是为了使特定的社会与文化得到完整的呈现,正是通过这种多重的整体呈现,才可能窥见特定的“地方性”并从中发现不同的研究主题。以往的人类学东北研究在物质文化和族群研究方面已有积累,其中鸟居龙藏的石棚、满蒙古迹、辽代石墓研究和史禄国的通古斯人研究尤为突出。如何在继承并深化这些研究的同时,不断开拓新的研究主题和理论取向,是人类学东北研究的关键所在。在东北的地方经验中,物质文化范畴的石棚、红山文化、辽塔辽墓、清代皇宫;经济范畴的牧耕渔猎、明清马市、貂参贸易、工业生产;社会范畴的部落组织、八旗制度、清帝东巡、移民浪潮、殖民侵略;宗教范畴的萨满信仰、镇庙佛庙等,都是其“地方性”的具体表现。对这些主题进行人类学的研究,可以采取不同的理论取向,而历史的眼光是不可或缺的,因为不同的主题并非截然分立,而是在历史的进程中相互关联。比如,红山文化中的玉器具有宗教的性质,进入文明社会后成为礼器之一和鉴赏收藏之物,明清以来又作为贡品和礼物被编织到不同的生产与消费的链条之中,如今甚至成为特定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并在不同的社会条件和文化环境中支配着相关群体和个人的命运。
研究主题和理论取向可以在区域研究内部加以继承与深化,也需要在不同区域研究的比较中相互激荡。东南研究对宗族和汉人宗教的长期关注,使国家与社会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形成了神—祖先—鬼的结构性理论;西南研究对族群理论的引入则不仅使国家与社会理论得到了深化,而且把人类学的中国研究推向了文明研究的脉络之中,近年来“华夏边缘”、“藏彝走廊”等研究和“中心与边缘”、“中间圈”等理论的提出是其突出表现。较之东南,东北地方经验中的宗族力量较弱,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更为复杂;宗教经由不同族群的历史互动中,也呈现为更复杂的状貌。较之西南,东北地方经验中的族群虽然多元,但却并非是简单的“中心与边缘”的关系,而是在历史的进程中形成了以二元关系为主、容纳了多重阶序关系的等级结构;东北虽然处于拉铁摩尔所言的“亚洲内陆边疆”,但却不像“藏彝走廊”那样存在于周边文明的包围之中。以东北的地方经验与东南和西南研究形成理论对话,无疑有助于人类学东北研究的不断拓展,同时也将使人类学的中国研究更加深入。
学科内部的继承与对话顺理成章,学科之间的互惠同样有助于人类学东北研究的进取。诸如考古学、历史学和地理学等学科对东北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众多的成果,这不仅为人类学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经验素材,同时也有助于理论思考的相互激发。以辽西的考古学研究为例,红山文化的发现与探究表明,东北构成了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这既有助于东北物质文化研究的展开,同时也对重新思考 “中心与边缘”理论具有很大的启发。再如,深受人类学影响的“新清史”对清王朝的研究,在近年来的清史学界激起了热烈的讨论,“汉化论”与“满族性”的争论至今未平,这同样为人类学的东北研究提供了富有弹性的理论对话空间。
总之,民族志记述是人类学东北研究之基,研究主题和理论取向的开拓则是其学术生命之本。这种生命力的维持与延续,不仅需要在人类学内部展开继承与比较,也需要和邻近学科的相关研究进行充分的学术互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