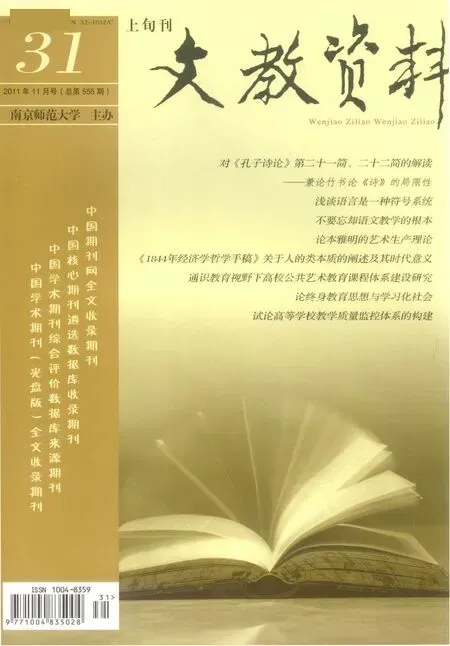一个百折不挠的奋斗者———试析路遥笔下的孙少平形象
2011-03-20白晓玲
白晓玲
(甘南藏族综合专业学校,甘肃 合作 747000)
在路遥为数并不多的文学作品中,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以其场面的恢弘、气势的阔大、人物的鲜明生动、事件的纷繁复杂和概括历史的深度与广度,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这部小说全景式反映了中国近十年间城乡社会生活的巨大历史性变迁。较之《人生》而言,小说在反映一个时代人们所赖以生存的曲折景况时,确实要来得深刻、通透,同时也更富有感人至深的哲学思考和人性阐释。作品塑造了一系列个性鲜活而棱角分明的人物形象。孙少安、田福军这两条交汇流动,稳居于农村改革的上层和下层的河流自不待说,即使像田晓霞、秀莲、惠英嫂那样作为陪衬,推动主体河流流动的人物,也都写得血肉丰满、深入人心。这中间,孙少平性格的发展运行和命运起伏是小说最光彩的亮点,他的喜怒哀乐、孜孜以求,甚至那种达到自虐程度的身心磨砺,都是负载着中华民族传统美质和独特道德范式的特殊象征。通过他近十年跌宕起伏的生命历程,我们会深深地感受到一代中国农村青年人生追求的艰难、命运奋斗的辛劳和取得每一步成功时的欣悦。
一、学生时代艰苦的精神磨炼,是他硬汉性格的雏形。
孙少平求学的时间,按推测,应该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当时的一切尚在困难的阵痛中徘徊,经济的几近崩溃,导致物质的极度匮乏。那时的孙少平正处在身体发育的特殊年龄,特别能吃与生活特别困难的客观矛盾使他异常痛苦。作者这样写道:“每天的劳动可是雷打不动的,从下午两点一直要干到吃晚饭。这一段时间是孙少平最难熬的。每当他从校门外的坡底下挑一担垃圾土,往学校后面山里送的时候,只感到两眼冒花,天旋地转,思维完全不存在了,只是吃力而机械地蠕动着两条打战的腿一步步在山路上爬蜒。”(《平凡的世界》第一部第6页)可以说,从这个时期开始,他已经初尝了人世的艰难与困苦。
由于贫困,他的自尊心忍受着难以言说的煎熬,他渴望穿一身体面的衣裳站在女同学的面前,满足他青春的萌动;他希望自己每天排在买饭队伍里,也能和别人一样领一份乙菜,并且每顿饭能搭配一个白馍或黄馍。但是,贫困的家境连他这点可怜的愿望都满足不了。于是,他无形中产生了自卑心理,在自卑心理的支配下,他比别人更加自尊。自卑和自尊,交互地影响着他成长的性格。
生活的艰辛,使孙少平分外珍重身边的亲情。当润叶姐交给他五十斤粮票和三十元钱时,他首先想到的是祖母、小外甥和哥哥,最后的那一份才是留给自己的。当洪水即将淹没曾经对他冷嘲热讽惯了的侯玉英的时候,孙少平丝毫也没有考虑到自身的安危,奋力救起了在危机中挣扎的侯玉英,让对方感到无地自容。成长的磨砺使他具有了比同龄人更为宽广的胸怀。正因为如此,连一向和他们家不合的金光明都禁不住大声地赞叹他:“人才,双水村的人才!”
当孙少平经历了以上零零碎碎的少年成长之烦恼以后,他终于在心里开始酝酿起自己的前景,他屡经磨炼的思想也插上了更为坚韧的翅膀,在一个更为广大的天地里恣意翱翔,他已经不甘心在贫瘠、沉闷的农村度过自己的一生,哪怕这仅仅是出于一腔青春的激情。
二、悲喜交集、起伏跌宕的两次爱情生活,是孙少平硬汉性格的催化剂。
如果从数量上计算,加上与郝红梅的爱情,孙少平的恋爱经历应该有三次。但与郝红梅短暂的爱情生活才刚刚揭开朦胧的面纱,即迅速面临夭折的命运。当一切结束之后,孙少平甚至感到一种解脱的喜悦。不仅如此,他也认识到,自己是一个普通人,一个来自农村的“乡里娃”,应该按照普通人的模式生活,“乡下人”的标准追求,而不是做太多的非分之想。
此后不久,在最自然的状态下,另一个女性,敢说敢干,颇有思想,又是地委书记女儿的田晓霞走进了孙少平的生活。这段爱情,是他俩在不知不觉间自然而然形成的,甚至直到很久以后,双方都不敢承认。在交往中,田晓霞那种大胆泼辣的作风和风风火火的性格令孙少平感到讶异,加上田晓霞非同一般的见解,更让孙少平感到在同性朋友之外,有了一个可以一抒胸怀、寄托衷肠的异性朋友。
然而,生活并非处处都是诗意的浪漫和玫瑰的温馨,当一场突然而来的灾难夺去他心爱的人年轻的生命后,孙少平青春期最为动人的爱情之火也随之熄灭。带着失去亲人的巨大痛苦和难以填补的情感“空洞”,孙少平回到了煤矿,他要用牛马般的体力劳动来医治如此深重的精神创伤。没有那里的劳动,他很难想象自己还能在这个世界上继续生存下去。
这一次,与孙少平不期而遇的是惠英嫂,一个勤劳、善良、温柔而美丽的矿工之妻。最初的接触十分偶然,却使他深深地感觉到,再也没有什么东西能比得上温暖的人情更为珍贵。在长期与这一家人的交往中,孙少平很快融入了这家人的生活,以至于“每次走向这个院落,他都有一种按捺不住的激动,这里是他心灵获得亲切抚慰的所在,也是他对生活深沉厚重的寄托”。他们即将迎来的结合,较之孙少平与田晓霞的爱情,要来得更为平和、安谧。
三、在城市边缘苦行僧般的劳动生活,最终造就了一个卓尔不群的铁骨硬汉。
出身于农民家庭的孙少平,从小就备受煎熬,他对劳动是不陌生的。一踏入社会,他便想利用自己勤劳的双手,为自己挣一个前途。逐渐觉醒并且明朗的个性意识,促使他走出苦难深重的土地,在更宽广的天地里追求自己的人生价值。
于是,他提着自己那份简单的行李,来到了黄原城,加入到众多拼命挣扎的“揽工汉”行列。在这里,他曾为无处过夜而踌躇徘徊,曾为了住宿而受尽远房亲戚的冷遇白眼,他曾忍受着超强度、满负荷的劳苦和役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他曾用战争年代的人们可能丧失宝贵的生命聊以自慰,他知道“出门”本来就不是享福的。几经周折,他从一座城市的边缘转移到了另一个城市的边缘,作为提升,他变成了最底层的“公家人”,劳动更加艰辛。长期的地下生活,使他和他的同事倍感阳光般的亲近。
平凡的世界从来就不乏感情和人性,孙少平在这样的艰难境遇中没有泯灭自己的天性。他正直善良。在煤矿,他以自己一天也不缺勤的成绩换来了大把的金钱,也赢得了工友们的尊敬和拥戴,劳动使他感受到了做人的尊严,品尝到了奋斗的乐趣。
在艰苦的劳动生活中,他天性依然,出于一腔正义,他勇敢地救下了遭受百般欺凌的小翠,而自己却失业了。即使小翠后来的遭遇令他深深地反思,他也没有心生悔意。为了报答师傅王世才对自己的知遇之恩,他果断地承担起照顾惠英嫂母子的责任,并且做得深沉厚道。在工友处于危险的千钧一发之际,他舍身抢救,以致给自己留下了终身难以愈合的心理的阴影。那种对壮烈的献身精神的强烈渴望,在此刻得到最集中的展现和深化,昭示了他非同一般的个性意识,最终给人留下难以磨灭的深刻印象。
纵观孙少平近十年的奋斗历程,我们深深地感到:存在于他身上的,是勇往直前的恒心和不懈追求的毅力。在他的面前,几乎不存在克服不了的艰难险阻。生活的艰辛、情感的跌宕、命运的一波三折他都能坦然面对。正因为这样,他的形象才会给人造成强烈的视觉冲击力,读者才会在掩卷沉思中获得心灵的震撼和审美的愉悦,从而也使孙少平这样一个普通的农村青年成为了当代文学作品中熠熠生辉的一个典型形象,感动了一代又一代的文学人。
[1]路遥.平凡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