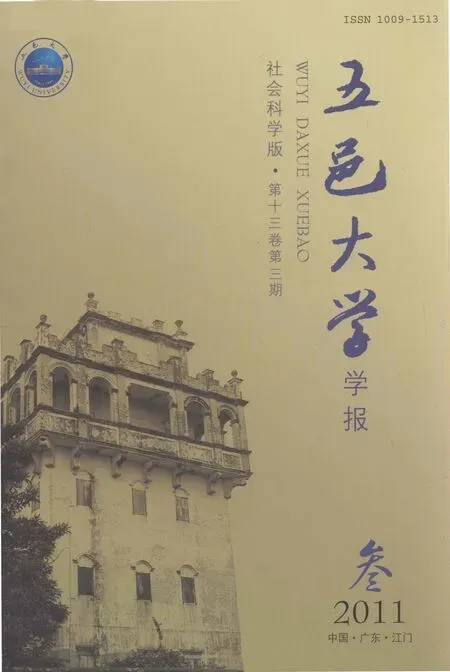梁启超清学史研究斠评
2011-03-19雷平
雷 平
(湖北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湖北 武汉 430062)
梁启超清学史研究斠评
雷 平
(湖北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湖北 武汉 430062)
梁启超是清代学术史研究的重镇。他注重对时代思潮的考察,又初步尝试中西比较,对清学的缘起、流派、方法等均有创见性诠释。但梁氏的研究也有不少缺陷,主要是中西比较有简单比附的嫌疑,“理学反动说”割断了清代学术与宋明理学的关系;同时文献准备不足,论证有空疏、浅薄之处。
梁启超;清代;学术史
梁启超是清代学术史研究的重镇。从1904年的《近世之学术》,到1920年的《清代学术概论》及1923年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梁氏逐步建构起关于清代学术的论说体系。他注重对时代思潮的考察,又初步尝试中西比较,这既使得他能够发覆创新,又使他因失之于比附而出现不够周密甚至疏漏的地方。
一、梁启超对清代学术的总体认知
在论述清代学术时,梁启超注意时代思潮的变化,注重宏观考量和总体认知,主要表现如下:
(一)学术主潮的考量:“实事求是”与“科学精神”
1904年,梁启超在续写《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第八章《近世之学术》时,说明论述的范围是“起明亡以迄今日”,实际上就是清代学术。梁启超认为中国传统学术可以划分为7个时代,而近250年为“衰弱时代”,他说:“综举有清一代之学术,大抵述而无作,学而不思,故可谓之为思想最衰时代。虽然,剥与复相倚,其更化之机,章章然次第进行。通二百六十年间观察之,有不可思议之一理趣出焉,非人力所能为也。……由此观之,本朝二百年之学术,实取前此二千年之学术,倒影而缫演之,如剥春笋,愈剥而愈近里,如啖甘蔗,愈啖而愈有味,不可谓非一奇异之现象也。”[1]130同时,梁启超又认为清代学术的主潮是“实事求是”,他指出:“本朝学者以实事求是为学鹄,颇有科学精神,而更辅以分业的组织,惜乎其用不广,而仅寄诸琐碎之考据。”[1]113论述清初学术时,梁启超注重对经世之学的表彰,他将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颜元、刘继庄等合称为“五先生”,认为他们“以经世致用为学统相同也”,“五先生之著述,可覆按也,彼其经世,非宋干、淳间永嘉派之言也。”[1]109在关于乾嘉学术的论述中,他注重惠栋与戴震之学,视之为“乾嘉正统派”。而在论述“最近世”也就是嘉道以降的清代学术时,梁启超则将论述重心聚焦到今文经学的复兴上,并疏理了自庄存经龚自珍、魏源迄于康有为的学术发展脉络。
(二)时代意义的确诂:“中国之文艺复兴”
1920年,蒋方震写成《欧洲文艺复兴史》一书,邀梁启超为之作序。梁氏认为:“泛泛为一序,无以益其善美,计不如取吾史中类似之时代相印证焉,庶可以校彼我之短长而自淬厉也。”[2]1他将清代学术思想与欧洲文艺复兴相比拟,不料“下笔不能自休,遂成数万言”,其篇幅几与蒋氏原书相当,不宜再作书序,只好独立成篇,于1921年出版,这就是《清代学术概论》。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梁启超开篇即论述“时代思潮”:
今之恒言,曰“时代思潮”。此语最妙于形容。凡文化发展之国家,其国民于一时期中,因环境之变迁,与夫心理之感召,不期而思想之进路,同趋于一方向,于是相与呼应汹涌,如潮然。始焉其势甚微,几莫之觉;假而*收稿日期:2011-04-13
在写作《清代学术概论》时,正值“五四”新文化运动后“科学”与“民主”观念大为流行的阶段。以胡适为发端,学术界掀起了一场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的运动。梁启超对这场运动也是认可和接受的,他积极致力于在中国传统文化与西学之间构筑一条可以有效沟通的途径,故着重强调乾嘉汉学的“科学性质”,并将其在世纪初提出的认为清代学术具有科学精神的观点进一步深化。梁启超认为清代学术“以复古为解放”,由王学返程朱、汉唐、西汉最后达致先秦诸子学,而其变迁的动力则在“科学的研究精神实启之”[2]4。从形式上看,清代学术的“复古”确实与西方文艺复兴比较类似,这也是梁启超为什么会特地表彰清代学术的原因。梁启超将“考证学”视为清代学术的“正统派”,并以考证学的发展为标准来梳理所谓“清学”的“生”、“住”、“异”、“灭”。因研究精神和环境的作用,清代学术所趋方向有四种,其中第三项即由“西学”的传入与影响生发出来:“自明之末叶,利玛窦输入当时所谓的西学者于中国,而学问研究方法上生出一种外来的变化,其初惟治天算者宗之,后则渐用于他学。”[2]27在梁启超看来,此种研究法即以归纳法为代表的科学方法。
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梁启超明确说:“吾常言:‘清代学派之运动’,乃‘研究法的运动’,非‘主义的运动’。”[2]43梁启超对清代学者的表彰最为有力的当数戴震,瞩目的正是戴震的治学方法。他说:“故苟无戴震,则清学能否卓然独立,盖未可知也。”梁启超将戴震比为“清学全盛期”“正统派”的代表人物,认为“戴氏学术之出发点,实可以代表清学派时代之精神之全部”,“此种研究精神,实近世科学赖以成立耳”[2]34。凌廷堪为戴震作《事略状》,称赞戴震治学讲求“实事求是”,梁启超则进一步评价说:“此其言绝似实证哲学之口吻,而戴震之精神见焉,清学派之精神见焉。”[2]38梁启超甚至倾向于称戴震为“科学家”。
(三)研究时段的设定:“近三百年”的贯通
1923年梁启超在清华大学讲清代学术,第二年整理出版讲义,即《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这部著作与《清代学术概论》一样,都以清理明末清初至清末民初近三百年中国学术思想发展线索为内容,可说是“五四”后学术史研究思潮中重要的产物。关于《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梁启超说:“这部讲义,是要说明清朝一代学术变迁之大势及其在文化上所贡献的分量和价值。为什么题目不叫做清代学术呢?晚明的二十多年,已经开‘清学’的先河,民国的十来年,也可算‘清学’的结束和蜕化。把最近三百年认做学术史上一个时代的单位,似还适当。”[3]1也就是大致将17、18、19这3个世纪的中国学术、思想的发展视为一个特定历史进程,称之为“近三百年学术”。他认为:“凡研究一个时代思潮,必须把前头的时代略为认清,才能知道那来龙去脉。”[3]1孟祥才评曰:“《清代学术概论》篇幅较少,言简意赅,是此期学术的鸟瞰图,重点侧重于‘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篇幅较多,内容充实,是此期学术的展览馆,重点侧重于‘史’。前者高屋建瓴,气势非凡,论锋慑人;后者侃侃而谈,循循善诱,学识服人。二书虽然风格不同,但确各有千秋,都显示了梁启超渊博的学识和高超的手笔”, “都是梁启超学术论著中的佳品。”[4]344可见,《清代学术概论》与《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以“论”见长,一以“史”见长,二者相得益彰,完善了梁启超的清学史论述。
梁启超的研究不以王朝为限,将清代学术史纳入“近三百年”这样一个较长的时间范围内来讨论,把握住“时代思潮”分析学术的盛衰兴替,同时又从东西比较的角度来论述清代学术,高屋建瓴,显示出博大的胸怀和广阔的学术视野。
二、梁对清代学术发展规律的总结
在宏观把握清代学术特征的同时,梁启超还注意揭示有清一代的学术规律:
(一)关于清学的缘起
在清学的缘起上,梁启超既表彰顾炎武的开创性地位,也积极肯定阎若璩、胡渭的作用。梁启超认为:“开创新学风的大学者,其造诣不必极精深,更重要的在于规定研究之范围,创革研究之方法,而以新锐之精神贯注之。”[2]11-12他认为顾炎武的“经学即理学”一语开出了有清一代的学风,这主要在于顾炎武创造了一套独特的研究方法:一曰“贵创”,著书必须是“古人未及就,后世之所不可无,而后为之”;二曰“博证”,即顾氏所谓的“每一事必举证,尤不以孤证自足,必取之甚博,证备然后自表其所信”;三曰“致用”。[2]11-12
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胡渭《易图明辨》均“漏略芜杂,为后人所纠者不少”,阮元辑《学海堂经解》“两书皆摈不录”。[2]13-16但这两部书在清代学术史上又确实发生了重要影响,原因何在呢?梁启超认为《古文尚书》作为儒家经典具有宗教性,阎若璩的考证则打破了其神秘意味,将其转化为学术研究的对象;胡渭的《易图明辨》则厘清了宋儒以己见加入《周易》的成分,恢复了经典原貌。这两书对于确立“清学”的怀疑精神具有重要意义,因此,阎、胡也就有了其特定的地位。[2]13-16
(二)关于清学的分派
在清学的分派中,梁启超继承章太炎的吴、皖二分说,又进一步揭橥吴皖两派的不同学风。章太炎在成书于1902年左右的《清儒》中提出了“吴派”和“皖派”的划分法,也指出了两派的特点:“(清学)成学著系统者,自乾隆朝始。一自吴,一自皖。吴始惠栋,其学好博而尊闻。皖南始戴震,综形名,任裁断。”[5]梁启超继承了章太炎的吴、皖分派说。他认为,惠栋为吴派的代表人物,治学以“尊闻好博”为特点,又以“凡古必真”定是非,“凡学出于汉儒必当遵守”,所以他既确立“汉学”的地位,又有“胶固、盲从、褊狭、好排斥异己的弊端”,故可称为“纯粹的汉学”;[2]33戴震为皖派的代表人物,治学以“深刻断制”为特色,其最得力处,在于“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推断务求精审,破除迷信,“巨细必究,本末必察”,其《孟子字义疏证》“随处发挥科学家求真求是之精神,实三百年间最有价值之奇书。”[2]42
(三)关于清学的裂变与转进
在清学的裂变与转进中,梁启超注意到今文经学的兴起,并梳理出晚清今文经学的学脉。早在1904年刊刻的《近世之学术》中,梁启超就已经梳理出以庄存与为发端、中经刘逢禄、魏源、龚自珍以至康有为的今文经学发展线索。他指出:“数新思想之萌孽,其因缘故不得不远溯龚、魏。”“今文之学,对于有清一代学术之中坚而怀疑者也。龚、魏及祖述龚、魏之徒,则近于诡辩者也,而我思想界亦自兹一变矣。”[1]127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梁启超不仅进一步明确了今文经学的发展线索,更对身处其中的康有为和他本人作出了较客观的评价。他肯定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和《新学伪经考》实为“思想界之一大飓风也。”但同时也指出:“有为以好博好异之故,往往不惜抹杀证据或曲解证据,以犯科学家之大忌,此其短也。”又说:“有为之为人也,万事纯任主观,自信力极强,而持之极毅。其对于客观的事实,或竟蔑视,或必欲强之以从我。其在事业上也有然,其在学问上也亦有然。”[2]78对于自己,梁启超评价说“可谓新思想界之陈涉”,在思想界“破坏力确不小,而建设则未有闻”。他勇于解剖自己“太无成见”,认为“晚清思想界之粗率浅薄,启超其有罪焉”。[2]89
(四)关于清学的方法论
在清学的方法论上,梁启超既从整体上总结了清代朴学的治学方法,又对具体的校勘学、辨伪学方法进行了探讨。梁启超认为“清儒之学,纯用归纳法,纯用科学精神”,其具体实施有四步,即:“第一步,必先留心观察事务,觑出某点有应特别注意之价值;第二步,既注意于一事项,则凡与此事项同类者或相关者,皆罗列比较以研究;第三步,比较研究的结果,立出自己一种意见;第四步,根据此意见,更从正面旁面反面博求证据,证据备则为定说,遇有力之反证则弃之。凡今世一切科学之成立,皆循此步骤,而清考证家之每立一说,亦必训此不昼也。”[2]62在论证了科学方法的四大步骤后,梁启超又将朴学方法概括为十类,即:一,凡立一义,必凭证据,无证据而以臆度者,在所必摈;二,选择证据,以古为尚;三,孤证不为定说;四,隐匿证据或曲解证据,皆为不德;五,最喜罗列事项之同类者,为比较的研究;六,凡采用旧说,必明引之,剿说认为大不德;七,所见不合,则相辨诘,虽弟子驳难本师,亦所不避,受之者从不以为忤;八,辨诘以本问题为范围,词旨务笃实温厚;九,喜专治一业,为“窄而深”的研究;十,六体贵朴实简,最忌“言有枝叶”。[2]62这实际上是梁启超以科学为标准而总结出来的方法。这些方法的实际运用效果又如何呢?梁启超又引入了西方学术的真谛之一——“凡真学者之态度,皆当为学问而治学问来加以判定,根据梁启超的说法,就纯粹的学者之见地论之,只当问成学不成学,不必问有用无用。”[2]47-48如此看来,清代学术因精于考订而成为“学”,其在学术史上必有相当价值。
除对清代“朴学”治学方法的总结以外,梁启超还对校勘学、辨伪学的方法进行了总结。他认为校勘学方法有四种:第一种,是拿两本对照,或根据前人所征引,记其异同,择善而从;第二种,是根据本书或他书的旁证反证校正文句之原始的讹误;第三种,是发现著书人的原定体例,根据它来刊正全部通有的讹误;第四种,根据别的资料,校正原著之错误或遗漏。[4]220-222关于辨伪学,梁启超也归纳出六种方法:第一,从著录传授上检查;第二,从本书所载事迹、制度或引书上检查;第三,从文体及字句上检查;第四,从思想渊源上检查;第五,从作伪家所凭借的原料上检查;第六,从原书佚文佚说的反证上检查。[4]220-222
这些方法的总结虽非尽善尽美,但是对方法的重视显示了梁启超治学的博大胸怀,对于后学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五)关于“学术史”写作典范的确立
通过对清代学术的研究,梁启超确立了“学术史”写作的典范。梁启超对学术思想的重要意义有独到的体会和深刻的认识。早在20世纪初他就曾指出:“天地间独一无二之大势力何在乎?曰智慧而已矣,学术而已矣。”[6]《文集》之六:101不仅如此,他还对“学术”的观念进行了探讨。在1911年所写的《学与术》中,他说:“学也者,观察事物而发明其真理者也。术也者,取所发明之真理而致诸用也。”[6]《文集》之二五:121他对“学术史”本身的问题,诸如起源、范围、考察重点等也进行了深入的考察,并自觉地从事“学术史”的研究。梁启超在20世纪初完成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在现代学术的形成中具有重要地位。胡适在《四十自述》中说他最喜欢这篇文章,因为“这是第一次用历史眼光来整理中国旧有学术思想,第一次给我们一个‘学术史’的见解”[7]。
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梁启超曾说:“大抵清代经学之祖推炎武,其史学之祖当推宗羲,所著《明儒学案》,中国之有学术史者,自此始也。”[2]17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梁启超也表达过类似的意思。但是,正如有的论者所指出:梁启超表彰黄宗羲的《明儒学案》为中国有学术史的开端,实际上是要有意消解刘师培对自己的影响。[8]刘师培所著《周末学术史序》第一次以现代意义上的“学术”作为考察单位,对周末学术史进行了整理。但是,刘著影响甚微,真正使现代意义上的“学术史”张大的要数梁启超。梁启超以“学术”作为考察单位,为20世纪的“学术史”著述确立了典范。他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是近代学术史上较早直接以“学术史”为名称的著作。在全书的最后4章,梁启超以“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为名,探讨了清代学者在经学、小学、音韵学、校勘学、辨伪学、辑佚学、史学、方志学、地理学、谱牒学、历算学、乐曲学等方面的成就。相对于章太炎和刘师培等人专论经学、钱穆主要论述理学的著作而言,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更具有“学术史”的味道。正是在梁启超“学术史”典范的影响下,才会有众多学者来认真关注学术史的研究和写作。虽然梁启超关于清代学术史的研究存在不少缺点,但毕竟第一次以“完整”的形式将清代学术的面貌展示在世人面前,其学术创新意义绝不容忽视。
此外,梁启超还非常关注地理环境对于学术风气的塑造。地理环境对于学者学养的培育和时代学术风气的转移具有重要影响,因而论学术不可不关注地理因素。梁启超在这一点上做得较好。在《清代学术概论》的最后,梁启超提出希望未来的学术“分地发展”的主张。1923年,他又写成《近代学风之地理分布》一文,“专以研究清代学者产地为主,于各家学术内容多不能论列”,“侪一切活动随其所引以为进展,听其所制以为适应,其含一部分真理,无少遗也”。[6]《文集》之四一:65
三、梁启超清代学术史研究的缺憾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史研究中做出了卓越贡献,但也留下了一些缺憾,值得后来者警醒与反思。
首先,中西对比的尝试为梁启超认识清代学术提供了参照系,但过于强烈的个人倾向导致了简单的比附。比如他将“清学”比为“中国之文艺复兴”,实在并非贴切之论。文艺复兴是西方文化由传统走向近代的重要转型阶段,“人文主义”是其打破中世纪教会神学迷信的旗帜。清代学者的“复古”、治学的“科学性”、戴震等人对“理学杀人”的指责,这些因素具有西方“文艺复兴”的某些表征。但是,在“复古”这种形式下,西方追求的是人的解放,而清代学者则是要“以经学济理学之穷”。西方的科学以实验和实证为特征,主要指称范围为自然科学,对于人文学科是否是“科学”的性质历来争议较大。清代学者虽然也讲“实证”,但主要是经学研究中的“例证”,而非西方意义上建立在实验基础上的“实证”。戴震虽然对理学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但后继乏人,“在当时除了章学诚了解外,并未成为支配的学说,没有起着社会影响。”[9]因而,梁启超将清代学术称为“文艺复兴”,在很大程度上是与“取吾史中类似时代相印证”的主观目的密切相关的,学理上的依据则不是太充分。这实际上也表明梁启超受到西方文化观的影响,由于时代的局限,他无法深谙其中的况味,更无法避免其缺陷。
其次,梁启超在清学起源上提出的“理学反动说”割断了清代学术与宋明理学的关系。梁启超认为,从明末清初以来,在学术界兴起了五种反理学的潮流:王学自身的反动、自然界探索的反动、欧洲历算学的输入、藏书及刻书的风气渐盛、宗教的反动。他认为“后来清朝各方面的学术,都从此(按:指对理学的反动)中孕育出来的。”[3]9胡适也指出:“约略说来,当日反‘玄学’的运动,在坏的方面有两个趋势:一是攻破那谈心说性的玄学;一是攻击那先天象数的玄学。”[10]实际上,梁启超和胡适的这种观点是从乾嘉学者溯源而来的。乾嘉汉学兴起后,汉宋之争随之展开①,持汉学观点者大多反对宋明理学。江藩将汉学与宋学截然分开,他在所著《汉学师承记》中说:“明象数制度之原,声音训诂之学,乃知经术一坏于东、西晋之清谈,再坏于南、北之道学,元明以来,此道益晦。至本朝三惠之学盛于吴中,江永、戴震诸君继起于歙,从此汉学昌明。”梁启超、胡适的观点显然与江藩有些相似,这也反映梁、胡更接近于汉学立场。但是,任何一种学术都不可能完全与前代脱离,“理学反动说”割断了清代学术与宋明理学的联系,忽视了学术发展的延续性特征。
最后,梁启超在进行清代学术史研究时,有现实的刺激和感触,但由于文献准备不足,论证有空疏、浅薄之处。朱维铮曾经对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进行校勘,指出梁启超曲引或误引前贤的地方有近百条。清代学术包罗万象,梁启超虽然涉猎极广,但并非对每一门学术都素有研究,比如对天算学,梁启超即承认“吾于此学绝无所知,万不敢强作解事”,但由于“本书体例”,梁启超又自认不能“自藏其拙”,勉强而为之。[3]320这种勇气虽然可嘉,但他“论清代历算学的文字主要来自阮元的《畴人传》,并无多少创见”[11]。其他如乐曲学,梁启超也承认自己没有多少心得。对于堪称清代校史代表作的《十七史商榷》、《廿二史考异》、《廿二史札记》,梁启超则主要依据自序、缀言来加以品评,显然不够深入。又如《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在总结清代史学成就时,提到章学诚时说“吾别有专篇论之”,但事实上直至终篇却未能再专论章学诚。
注释:
①汉宋之争的真实内涵目前还存在很多争议,有学者认为汉宋之争的真正意义不是汉学和宋学的争论,而是汉学家的义理与宋明义理的争端。笔者以为,这一说法很显然是今人的说法,当时学者大多还是将考据与义理之争看作是汉宋之争的内涵所在。
[1]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 [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2]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 [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3]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M].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1.
[4]孟祥才.梁启超传 [M].北京:北京出版社,1980.
[5]章太炎.章太炎全集:第三册 [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157.
[6]梁启超.饮冰室合集 [M].北京:中华书局,1989.
[7]胡适.胡适文集:第1册 [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73.
[8]周国栋.两种不同的史学范式 [J].史学月刊,2000(4):110-117.
[9]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五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462.
[10]胡适.胡适文集:第7册 [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239.
[11]吴铭能.梁启超研究丛稿 [M].台北:台湾学生书局,2000:218.
A Review of Liang Qichao’s Research into Qing Academic History
(by LEI Ping )
Liang Qichao is an important figure in the research on Qing academic history. He paid great attention to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ethos of the times , made an attempt to compare and cont rast it with the history of western learning , and made original interpretations of the origin , schools , and methods of the Qing learning. But Liang’s research also has many shortcomings , mainly in his simplistic comparison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learning and his cutting of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Qing learning and the neo-Confucianism of the Song and Ming dynasties. Also , lack of document preparation leads to emptiness and shallowness in his argumentation.
Liang Qchao ; the Qing Dynasty ; academic history
K092
A
1009-1513(2011)03-0007-05
雷 平 (1979—),男,湖北松滋人,博士,副教授,主要从事清代学术史研究。涨——涨——涨,而达于满度;过时焉则然,以渐至于蟀熄。凡“思”非皆能成“潮”;能成“潮”者,则其“思”必有相当之价值,而又适合于其时代之要求者也。[2]1
[责任编辑 文 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