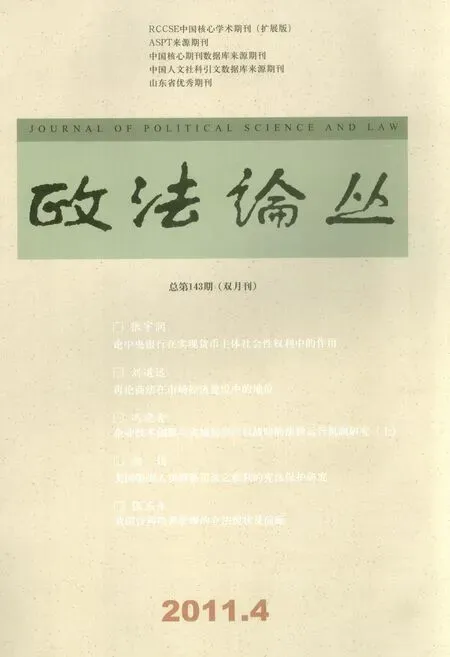法治语境下我国秘密侦查制度的现实困境和出路
2011-02-19丁延松
丁延松
(山东政法学院刑事司法学院,山东 济南 250014)
法治语境下我国秘密侦查制度的现实困境和出路
丁延松
(山东政法学院刑事司法学院,山东 济南 250014)
秘密侦查作为一种打击追诉犯罪的特殊侦查手段,在现代各国侦查实践中被普遍应用。我国立法对秘密侦查缺乏明确而详尽的规定,这与国外的立法规定相差甚远,也不符合建设法治国家对人权保障的要求。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语境下,基于程序正义理念的要求,亟需实现我国秘密侦查的法治化,以限制公权力对私权利的侵犯,确保在惩治犯罪和保障人权之间达到必要的平衡。
秘密侦查 立法比较 现实困境 法治化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更新和社会的飞速发展,在刑事犯罪领域不仅涌现出黑社会犯罪、恐怖活动犯罪、跨国犯罪等新类型的犯罪,而且毒品犯罪、职务犯罪、经济犯罪等传统型犯罪也日趋高组织化、强隐秘化、高智能化。这些犯罪所具有的极强隐蔽性和反侦查功能,对侦查工作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传统的侦查措施在侦破现代犯罪上就表现出日益明显的局限性。为了应对犯罪形势出现的新变化,秘密侦查作为打击追诉犯罪的特殊侦查手段便在各国的侦查实践中得到广泛使用。然而,鉴于秘密侦查所具有的强隐蔽性和易侵权性,我们又不得不面对秘密侦查的“双刃剑”功效,其在给侦查机关带来执法利益的同时,也就天然地蕴涵着侵犯公民权利和滥用的风险。为此,现代法治国家从保障公民个人权益出发,对刑事司法中秘密侦查措施的运用都进行了全面规范和控制。在我国的刑事司法实践中,秘密侦查也得到比较广泛的应用,但立法鲜有规定,这不仅使我国司法实践中秘密侦查措施的采取无法受到法律的有效规制,更为严重的是妨碍了我国侦查法治化建设的进程,这极不符合建设法治国家对人权保障的要求。因此,我国亟需对秘密侦查实行有效的法律控制, 实现秘密侦查的法治化,以限制公权力对私权利的侵犯,确保在惩治犯罪和保障人权之间达到必要的平衡。
一、我国秘密侦查的立法现状及现实困境
我国关于秘密侦查的立法依然是个空白,既没有专门规制秘密侦查的单行法,也没有在刑事诉讼法典及相关的司法解释中对秘密侦查手段予以规定。只有极少数原则性的规定涉及到秘密侦查措施,或者是侦查机关的一些内部规定来规范秘密侦查措施,致使秘密侦查的使用置于“隐形法”的调整之下,各地侦查机关在使用秘密侦查措施上也存在一定程度的随意性。目前,我国侦查机关使用秘密侦查手段的法律依据主要来源于两个:一是1993年颁布的《国家安全法》第10条规定:“国家安全机关因侦察危害国家安全行为的需要,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用技术侦察措施。”二是1995年通过的《人民警察法》第16条规定:“公安机关因侦查犯罪的需要,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用技术侦察措施。”除此之外,我国法律再无片言只语予以规范。对公民权利影响如此重大的措施,仅仅由国家的部门规制来调整,在全世界都极为少见,称之为“法外立法”并不为过。至于1984年公安部制定的《刑事特情工作细则》和2000年通过的《公安部关于技术侦察手段的规定》,只是公安(国安)机关内部通行的办案规则,导致所谓的“国家有关规定”、“严格的批准手续”究竟为何物,不足为外人道也。这显然与现代刑事诉讼基本价值和法治国家的要求相违背。可见,我国关于秘密侦查的立法极不完备,在司法实践中很容易陷入困境。
1.立法的缺失导致秘密侦查在实践中的适用不规范。在实践中,公安机关为了保护卧底侦查人员和特情,在向检察机关移送有关卧底侦查员或特情参与案件的事实材料时,对卧底侦查员以同案犯或重要证人的形式出现,并以“在逃”或“另案处理”为由,不移送材料。而检察机关在起诉此类案件时,因无明文的法律规定,存在一种盲目性和无奈性。法院在审理这类案件时,由于法律没有对因秘密侦查手段获取的证据的可采性予以规定,存在着一种不确定性和无序性。[1]P101这种做法很不规范,是无奈的变通之举。现行法律对秘密侦查规定的神秘化倾向,严重影响了国家法律的统一实施和国家司法机关公正的形象。
2.秘密侦查行为的合法性受到质疑。由于没有明确的法律授权,仅仅依照部门规章、政策行事,我国采取秘密侦查办案的侦查人员要承受着合法与非法的质疑。这也导致了侦查人员心里没底,加之具体的界限不明,秘密侦查人员本身就处于一种合法与非法的边界地带。
3.容易造成对公民权利的侵犯。秘密侦查本身就具有易侵权性,再加上法律没有对秘密侦查的适用程序进行完善的规定,导致秘密侦查措施的滥用。如果随意采用秘密侦查手段,会产生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的严重后果,即这种方法的使用往往会侵犯有关人员的合法权利,如隐私权、通讯自由权等。
4.缺乏外部的有效监督。目前,秘密侦查并未纳入刑事诉讼法调整的范围内,而是由公安(国安)机关内部的操作规则予以规范和实施,实行的是自我约束、内部审查、同体监督,具有不透明性,无法在外部形成有效的监督机制,其实质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黑箱操作”。这种制度设计很容易导致侦查机关在无任何外部监督制约的情况下行使秘密侦查权,为了快速有效侦破案件,动辄采用秘密侦查手段,产生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的严重后果。
5.秘密侦查获取的证据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由于法律没有明确授权侦查机关采取秘密侦查措施的权力,法律对特殊手段获取的证据的可采性问题也没有任何的规定,因此,通过这些侦查手段获取的证据,不能直接进入审判程序,必须经过“证据转换”,即对秘密侦查的结果必须通过刑事诉讼程序予以“公开化”,否则无法确保诉讼的公正性和效率。秘密侦查获取的资料“只能在分析案情时使用,不能在审判中直接作为证据使用。如果要在法庭上作为证据使用,需要在此前一定时间内告知有关案件各方秘密取证之信息,将其公开化后方能作为合法的证据使用”。[2]P306但“证据转换”的法律依据以及经转换的证据的合法性却有待考证,况且有些证据也是无法“转换”的。可见,秘密侦查有必要进行法治化。
二、秘密侦查立法的域外考察
由于秘密侦查措施的适用时常发生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利益冲突,现代各国为了保持两者之间的平衡,都十分重视对秘密侦查的立法,对其适用做出了明确规定。不仅可以使秘密侦查获得有效的授权,保证侦查手段的理性选择与行使,而且能够将可能发生的对公民权利的侵害降至最低。大陆法系国家采用诉讼法律模式,在其刑事诉讼法中对秘密侦查做出规定。联邦德国在1975年修正《刑事诉讼法》时增加了关于“监视电信通讯”的规定;1992年9月23日正式生效实施的《对抗组织犯罪法案》新增了关于“卧底侦查”规定;1998年修订的《德国的刑事诉讼法典》在第110a-110e条对卧底侦查做了详尽的规定,[3]P27在第100条对监听、录音的适用对象、条件做出了明确规定。[4]P453法国于1991年在《刑事诉讼法典》中增加了“电讯的截留”一节,对秘密监听的程序问题做出了详细规定。[5]P1242001年修订的《俄罗斯联邦刑事诉讼法典》第186条对监听做了规定:“如果有足够的理由认为,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和其他人的电话和其他谈话可能含有对刑事案件有意义的内容,则在严重犯罪和特别严重犯罪案件中允许监听和录音,监听和录音根据法院依照本法典第165条做出的决定进行。”该法还对监听和录音的申请、期限和使用等问题做出了具体明确的规定。[6]P145-147
英美法系国家采取综合法律模式对监听、乔装侦查等秘密侦查方法进行规定。美国国会1968年通过《综合犯罪控制与街道安全法》对秘密监听、录音做出了具体规定。美国联邦调查局于1981年颁布了《乔装侦查行动准则》,以加强对乔装侦查行动的内部控制与责任约束机制,其后又分别在1992年、2002年两度修改此准则。[7]英国议会1985年通过的《电讯截获法》,一方面将非法截获通讯规定为犯罪,同时也赋予了警察和情报部门在一定条件下截获通讯的权力。
纵观德、法、俄、美、英等国家有关秘密侦查的立法,无论采取何种模式,都是通过明确的制定法对秘密侦查进行规范,使秘密侦查的进行均处于一种有法可依的状态。可见这些国家的秘密侦查正在实现法治化,都是力求在“控制犯罪”和“保障人权”间求得平衡。尽管各国的秘密侦查立法问题在具体规定方面不尽一致,但是均涉及以下五个方面:
1.适用的犯罪范围。秘密侦查作为一种极易因侵犯公民权利而成为非法侦查的特殊侦查行为,必须严格限制其适用范围,这也是法治国家的共识。总的来说,秘密侦查主要适用于两类犯罪:一是重罪,即处罚较重的犯罪,如美国1968年《综合犯罪控制与街道安全条例》规定秘密侦查适用以下犯罪:间谍罪、叛国罪、谋杀罪、抢劫罪、贿赂政府官员罪、贩毒罪、敲诈勒索罪等12种犯罪。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第266条规定“在下列有关的刑事诉讼中允许对谈话、电话和其他形式的电讯联系进行窃听:(1)依照第4条的规定依法应判处无期徒刑或者5年以上有期徒刑的非过失犯罪;(2)依照第4条的规定应判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妨害公共管理的犯罪……”针对这类犯罪采用秘密侦查措施足以抵消因侵害公民隐私权而带来的负面影响。二是组织化、智能化、隐秘化的特殊类型的犯罪。由于其犯罪行为的特点,给侦查机关的侦查带来重重困难,侦查机关不采用秘密侦查,实难发现并侦破犯罪。
2.适用的必要性。德国《刑事诉讼法》第100条a规定,只有在以其他方式不能或难以查明案情、侦查被控制的住所的条件下,才允许命令监视、录制电讯往来。[3]P31美国《综合犯罪控制与街道安全法》规定,只有在常规侦查措施已经失败或不可能成功或过于危险时才能采用秘密监听手段。[8]P356由此可见,秘密侦查只有在常规性侦查措施难以查清案情时才能采用。这是基于秘密侦查措施是非公开进行的,难以受到外部有效监控,并且该措施往往直接触及公民个人的隐私权利的考虑。
3.秘密侦查的对象要具有相关性。即秘密侦查的采取只用来针对被指控人员及相关事实。为防止国家权力的过度扩张,这就要求秘密侦查只能针对犯罪嫌疑人及其犯罪事实才能使用。德国《刑事诉讼法》第100条a第5款规定,进行监听原则上只能针对犯罪嫌疑人而采用,只有在例外情况下才适用与案件有关联的其他人员。[3]P31
4.秘密侦查必须经过司法审查方能适用。由于秘密侦查措施是无需取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同意的强制性侦查措施,为了防止侦查机关在实施过程中侵犯公民的个人权利,西方各国均规定秘密侦查措施的适用,须经侦查机关提出申请、法官审查批准才能适用。如德国《刑事诉讼法》第100条b第1款规定,对电讯来往是否监视、录制,只允许由法官决定,在延误有危险时也可以由检察院决定。[3]P33
5.权利的司法救济。为实现国家秘密侦查权与公民隐私权对抗中的平衡,各国立法一般规定广泛的司法救济措施以对不当秘密侦查行为进行合理地抗辩。如侦查对象对秘密侦查所获得的信息有审查和提出异议权。对秘密侦查所获得的非法证据享有请求排除权。辩护方享有秘密侦查所获得信息的使用权和对非法秘密侦查行为的民事求偿权。美国《综合犯罪控制与街道安全法》规定,通讯被非法监听、泄露及非法使用者有权对非法行为实施者提起民事诉讼。[8]P360
三、实现我国秘密侦查法治化的出路
当今的中国社会正在由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变,传统的以道德教化和行政命令为手段的治国理念已经不适应现代治国的需要,于是我国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现代法治国家的基本治国方略。“法治意味着政府除非实施众所周知的规则以外不得对个人实施强制,所以它构成了对政府机关的一切权力的限制”。[9]P260可见,现代法治的基本原则绝对不是旨在对公民施行法律压制,而应该是一种限制政府权力的控制手段和保护公民权利的保障措施。所以“作为法治来说,其所治的关键在于治权”。[10]P92由于我国目前并没有形成符合法治原则的秘密侦查制度,而这有可能导致权力的恣意和对人权的威胁。所以,秘密侦查法治化的问题,从本质上来说就是如何对秘密侦查权进行有效控制,从而维护公民合法权利的问题。正如德国历史学家迈内克所说:“一个被授予权力的人,总是面临着滥用权力的诱惑、面临着逾越正义与道德界线的诱惑。人们可以将它比作附在权力上的一种咒语——它是不可抵抗的。”[11]P362针对秘密侦查措施在我国司法实践中运用所存在的问题,我们应在现代法治和人权保障的观念下,本着学习和发展的精神,充分考虑我国的实际情况,合理借鉴国外的合理立法经验,将秘密侦查纳入刑事诉讼法的统一调整范畴,从而实现秘密侦查措施的法治化。
(一)明确秘密侦查的性质定位
现代刑事诉讼行为理论认为,侦查行为属于刑事诉讼行为的范畴。秘密侦查作为行使侦查权的一种方式,自然是诉讼行为、侦查行为,理应受到刑事诉讼法的调整。何况任何国家行为的实施都需要有法律上的依据,秘密侦查也只有处于法律的控制之下,才能符合法治国家的本质要求。否则,权力一旦失去了约束,其所具有的天然扩张属性必然导致其被滥用。
(二)完善秘密侦查立法
秘密侦查行为由于其方式的隐蔽性,手段的技术性,视角的穿透性,如果不从法律上严加规范,容易陷入权力滥用及非法取证,并导致对被侦查者合法权利的侵犯,也不利于制约侦查人员的秘密取证行为。因此应加紧对秘密侦查手段立法,规范秘密侦查行为。关于立法模式的选择,国外有诉讼法律模式和综合法律模式,而考虑到我国的法律传统,应该在刑事诉讼法再修改时对秘密侦查有所规定,其具体内容应包括适用主体、对象、案件范围、方式、审批程序等等。
1.关于秘密侦查的适用主体。秘密侦查权应当来源于法律的授权。我国目前只有《人民警察法》和《国家安全法》有秘密侦查措施的简单规定,因而当前实施秘密侦查的主体还只限于公安机关和国家安全机关。但是在我国现行侦查体制下,享有侦查权的机关还包括人民检察院、军队保卫部门、监狱、海关缉私局,它们在侦查各自管辖的刑事案件过程中,难免会遇到没有被害人且隐蔽性较强的案件,当运用常规侦查方法难以侦破的时候,应当赋予其秘密侦查权。由于侦查主体的本质特征在于有侦查权,即根据法律授权,为追诉犯罪有权采取专门的调查活动,并有权采取限制或剥夺公民的自由等权利的强制措施,所以其他任何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公司企业和公民个人都无权进行秘密侦查。
2.秘密侦查的适用对象。如果秘密侦查被滥用,很容易造成对公民权利的侵害。而造成秘密侦查措施可能的滥用来源于两个方面,一个是案件范围的滥用,另一个是侦查对象的滥用。因此,秘密侦查手段的适用对象只能限于犯罪嫌疑人及与案件侦破相关的人员。对与案件无关的人员,包括证人和被害人是不能采用秘密侦查措施的,以避免借秘密侦查之名对无关人员的合法权益进行侵犯。
3.秘密侦查适用的案件范围。秘密侦查作为一种对现代刑事司法制度与公民权利保障存在巨大潜在威胁的侦查行为,必须严格限制其适用范围,这是法治国家的共识。我们可以借鉴国外关于秘密侦查的立法范围,以列举式和法定刑相结合的方式来明确规定我国秘密侦查适用的案件范围。一方面通过列举的方式对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杀人、抢劫等严重侵犯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的暴力犯罪、毒品犯罪、有组织犯罪、黑社会犯罪、恐怖犯罪等案件可以适用秘密侦查措施;另一方面则根据我国《刑法》的量刑幅度,对可能判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刑罚的案件适用秘密侦查措施。
4.进行秘密侦查的手段。秘密侦查的手段应当是在根据掌握的证据能够相对确定被侦查对象实施可疑的犯罪行为,在使用常规侦查手段无法查明犯罪事实的情况下才能适用。从国外的立法来看,秘密侦查的手段可以分为乔装侦查和秘密监控两大类。结合我国侦查机关在司法实践中的具体做法,可以在法律中明确规定进行秘密侦查所能采取的手段可以分为技术侦查(具体包括电子侦听、电话监听、电子监控、秘密拍照或录像、秘密获取某些证据、邮件检查等专门技术手段)和非技术侦查(具体包括卧底侦查、诱惑侦查、化装侦查和秘密拘捕等)。
5.秘密侦查适用的审批程序。秘密侦查是一种单方面的强制性措施,各国为将其纳入诉讼的轨道中去,相应地建立了司法审查机制,由法院审批并签发秘密侦查的令状。 考虑到我国目前尚未建立司法审查制度,而检察院是宪法授权的法律监督机关,所以可以参照审批逮捕程序将秘密侦查的审批权交由检察院行使为妥。检察院在接到侦查机关报请进行秘密侦查的案件后,应对以下内容进行审查:案件的性质;秘密侦查措施适用的对象及其可能犯有的罪行;秘密侦查措施适用的类型、范围、地点;使用的器材和适用的期限等相关问题。审查结束后对于符合法律规定的,检察院批准并签发令状,通知侦查机关在规定时限内使用秘密侦查措施。特殊情况下,确因案件紧急有秘密侦查需要,侦查机关可以先行秘密侦查,但事后应在24小时内补办相关审批手续。
6.秘密侦查的期限。为了有效地避免不当的长期进行某项秘密侦查对当事人造成精神和经济上的不必要损失,必须明确我国秘密侦查措施实施的期限。如法国《刑事诉讼法》第100条之2规定:“此项决定规定的截留期限最长为四个月。”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100条b第2项规定:“监视电讯往来的期限应当限制在三个月内,如果实施监视通讯的前提条件继续存在,准许对期限的延长,每次不超过三个月。[12]结合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笔者认为我国秘密侦查的期限一般应由案件性质加以确定,但最长期限一般不得超过3个月。
7.明确秘密侦查所获证据的采信问题。我国刑事诉讼法对证据的规定比较笼统,但坚持证据合法原则的规定还是较为规范的。对于秘密侦查所获取证据采信问题,一方面要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未经法定程序使用秘密侦查措施所取得的材料,法庭审理时应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另一方面确立合法证据采信规则,通过合法程序使用的秘密侦查行为取得的证据应当允许作为证据使用,不必再经历复杂的“转换”过程。
8.秘密侦查所获取信息的使用和处理。秘密侦查所获得的证据材料在案件审理中由法院负责保管,并且只能限于在本案中使用。这是由于秘密侦查手段是建立在损害被侦查人隐私权的基础之上,如此一来便可以防止被侦查人隐私的过分扩散。如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第276条规定窃听所得的材料不得在其他诉讼中使用,除非对于查明某些必须实行当场逮捕犯罪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至于对于秘密侦查所取得的证据材料如何处理的问题,美国《综合犯罪控制与街道安全法》规定秘密监听的记录以及有关文件必须要妥善保管,非经签发令状之法官的许可,不得销毁,而且保管期限一般为10年以上。我们可以借鉴国外的做法, 根据具体案情处理:对确有必要留存的要妥善保存,对获知的信息要严禁泄露;对与案件情况无关的材料案件审理结束后要在法官的监督下予以销毁。
(三)建立对秘密侦查的监督机制
秘密侦查如果适用不当,不仅容易危害公民正常权利,更容易诱发国家权力膨胀、滥用,失去制约。从逻辑上讲,这种权力比一般性国家权力更需要制约和监督。美国法学家博登海默认为:“在法律统治的地方,权力的自由行使受到了规则的阻碍,这些规则使掌权者受到一定的行为方式的约束。” “一个发达的法律制度经常试图阻碍压制性权力结构的出现。”[11]P358秘密侦查由于其保密性特点,知情面极小,很难由当事人及社会大众进行监督,只能由国家机关进行监督。域外关于秘密侦查的监督模式主要有行政机关监督模式、法院监督模式、检察院监督模式三种。那么,我国又该如何设计秘密侦查的监督模式呢?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秘密侦查手段的行使,是公安机关及国家安全机关自我授权、自我监督的模式,缺乏外部监督,明显不合理。一方面,内部监督带有暗箱操作的特点,在我国侦查法治化程度较低的情况下,很难防止权力不被滥用,毕竟“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13]P154另一方面,公安机关对秘密侦查的自我监督,明显架空了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者定位,不利于维护宪法权威,不利于完善我国的法律监督体系。如果建立由法院进行监督的司法审查机制是否合理呢?笔者认为也不妥。理由有三:首先,法院监督将会削弱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其次,由法院为主体进行的司法审查的物质基础并不具备;再次,我国并没有实行西方国家那样的司法独立体制。我国《宪法》明确将检察机关定位为法律监督机关,监督国家权力的依法行使,防止国家权力的膨胀、滥用是检察机关的应有职责。据此,由检察机关以法律监督者的身份对秘密侦查权进行监督当属法律监督权题中应有之义,同时,这种监督也有利于丰富和完善法律监督权的内涵,使法律监督权名实相符。另外,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37条也明确规定检察院审查起诉时必须查明“侦查活动是否合法”,逻辑上自然涵盖对秘密侦查活动进行法律监督。所以,笔者认为,我国应建立检察机关对秘密侦查进行法律监督的监督模式。
(四)建立秘密侦查的司法救济途径
只有得到救济的权利才是真正的权利。在秘密侦查的过程中,相对人始终处于毫不知情的弱势地位。为了弱化秘密侦查活动的超职权主义色彩,应该赋予被侦查人有效防御的能力,使其享有基本的自由选择权。
1.赋予侦查对象知悉、异议权。由于秘密侦查行为是在被侦查者未察觉的情形下进行的,且通常没有第三者在场为证,所以应当规定被侦查者有权获知秘密侦查结果的内容,以保证秘密侦查行为的真实性。如果被侦查者认为秘密侦查措施不当,有权提出异议,并向上一级检察机关要求复议。
2.非法证据请求排除权。许多国家的法律都规定,非法侦听获得的证据材料须予以排除,不得用作犯罪嫌疑人及被告人不利的证据,以此来有效遏制非法侦查行为。如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第271条规定:“如果窃听是在法律允许的情况以外进行的或未遵守法律规定的程序,所获得的材料不得加以使用。”因此,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如果有证据证明侦查机关在使用秘密侦查措施过程中,违反了法律规定的程序和要求,对于获取的证据,法院在审理中应予以排除,不予采信。
3.赋予受害人对非法秘密侦查措施的求偿权。秘密侦查属于职务行为,如果当事人认为侦查机关的秘密侦查行为侵犯了自己的合法权益,就有权依照规定请求赔偿。一方面,法律应明文规定被害人可以从违法侦查者处获得损害赔偿,包括财产性和非财产性的损失;另一方面,法律应明确规定被害人可以要求非法实施秘密侦查的机关或者审批机关承担国家赔偿责任。
[1] 詹复亮等.当前特情侦查的问题及其法律规制[A].刑事法判解:第3卷[C].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
[2] 何家弘.证据调查[M].北京:法律出版社, 1997.
[3] 李昌珂译.德国刑事诉讼法典[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5.
[4] 何家弘,张卫平.外国证据法选译(上卷)[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3.
[5] 陈光中.刑事诉讼法实施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0.
[6] 黄道秀译.俄罗斯联邦刑事诉讼法典[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3.
[7] 陈光中.诉讼法论丛(第11卷)[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
[8] John N. Ferdico. J. D.CriminalProcedure[M].WestPublishing Co.
[9] [英]冯·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M].邓正来译.北京:三联书店, 1997.
[10] 卓泽渊.法治国家论[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1.
[11] [美]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M].邓正来等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
[12] 唐磊,赵爱华.论刑事司法中的秘密侦查措施[J].社会科学研究,2004,1.
[13] [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M].张雁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
TheRealDilemmasandOutletoftheSystemofChina’sSecretInvestigationintheContextofLaw
DingYan-song
(Criminal and Judicial Law Shool of Shandong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Jinan Shandong 250014)
The secret investigation as a kind of special investigative method to attacking and looking into crimes is generally applied in investigative practice of modern countries. The legislation about secret investigation in China is short of concret and detailed regulation, which is quite different from the legislative regulation in foreign countries and does not conform to the requirements of constructing the rule-by-law country for human rights protection. In this linguistic environment of governing country by law and constructing the socialist country, on the basis of the request for a justice idea in procedure, it is urgent to realize the legalization in the secret investigation of China so as to limit the violation from the public power for the private right, to ensure to keep a necessary balance between punishing crime and safeguarding human rights.
secret investigation; legislative comparison; practical difficulties; legalization
DF73
A
(责任编辑:张保芬)
1002—6274(2011)04—117—06
丁延松(1979-),男,山东枣庄人,山东政法学院刑事司法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刑法、刑事诉讼法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