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土简帛在我国早期图书馆研究中的地位
2011-02-14傅荣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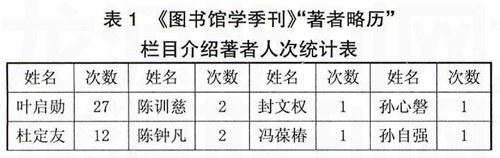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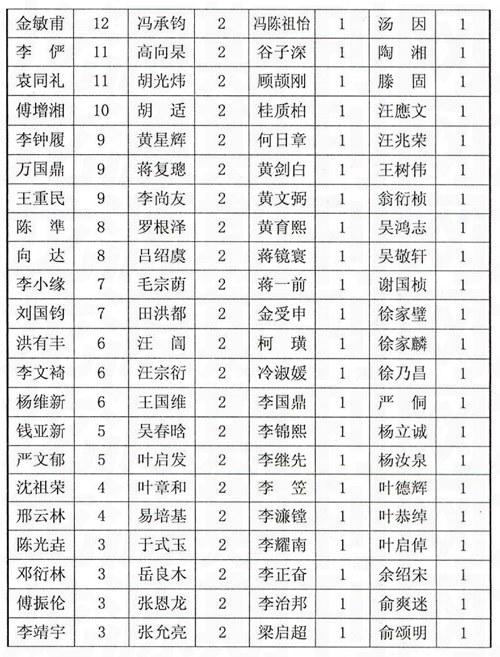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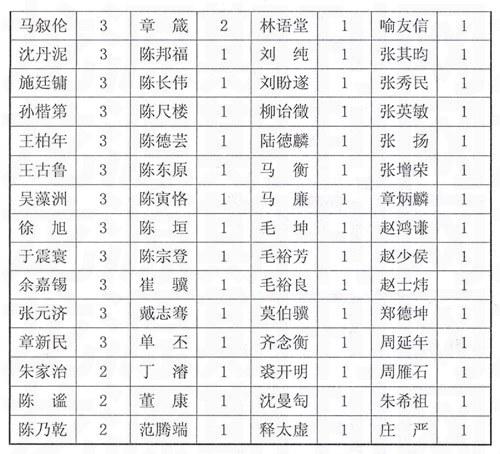
摘 要:出土简帛以文献实物的形式,"实证"了我国早期图书馆的基本面貌,有助于纠偏基于传世文献而得出的关于古代图书馆的集藏对象、知识结构和图书分类、图书目录和篇题的形制等诸多定论。但是,简帛文献的出土有很大的偶然性和不确定性,迄今为止的出土文献研究尚处于文本复原的早期阶段,文字释读和今译、帛片的拼接和竹简的排列等等都存在很多问题。因此,出土简帛本身并不能构成早期图书馆研究的自足材料,王国维先生倡导的"二重证据法"依然是我们需要持守的根本方法。
关键词:出土简帛 早期图书馆 图书
中图分类号: G259.29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938(2011)01-0135-04
Unearthed Bamboosilk Position in the Early Library Science Research in China
Fu Rongxian (The Information Management Research Center of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erbin, Heilongjiang, 150080)
Abstract:The features of the early libraries in China was evidenced by unearthed bamboo and silk in the form of literature object which was helpful in correcting many final conclusions in connection with the collective object, knowledge structure, classification of books, library catalog and structure of subjects of ancient library based on the literature be handed down from ancient times. However, there was a great chanciness and uncertainty on unearthed bamboo and silk. So far unearthed literature's research was still in the early stage of returning to original documents state. There are so many problems in explaining and translating manuscripts, splicing silk and arranging bamboo and so on. Therefore, unearthed bamboo and silk themselves cannot constitute sufficient material in the research of early library. "Double Evidence Method" initiate by Wang Guowei is still the fundamental method we need to hold on.
Key words:unearthed bamboosilk; early library; books
CLC number: G259.29 Document code: AArticle ID: 1003-6938(2011)01-0135-04
自1901年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在新疆尼雅故城发现第一批汉晋木简以来,中华大地屡有成批的简帛文献出土。这些出土的简帛实物最早是战国初期的,最晚则是魏晋时期的遗物。因此,本文所谓我国“早期”图书馆,主要断限在战国早期至魏晋时期约900年的时间跨度(公元前475—公元420)。目前,有关该课题的研究,主要是从文献学意义上的“图书”——而不是从文献收集、整理、保存和利用意义上的“图书馆”——立说的。例如,谢灼华主编的《中国图书和图书馆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是全国高等学校图书馆学核心课教材,实际上包括图书史和图书馆史两大部分,但该书有关简帛部分的内容都是放在“图书史”下论述的。可以说,出土简帛只是为图书史的研究拓展了新的领域,增添了新的视角,并引发了史料的重新评估和排列,但尚未得到图书馆学意义上的学科认读,更没有达成与图书馆学学科视界的有机融合。
总体上,利用出土简帛研究我国早期图书馆,所涉议题广泛,端绪堪称繁夥,本文仅就出土简帛在我国早期图书馆研究中的地位问题,提出一些初步看法。
1 出土简帛在我国早期图书馆研究中的价值
首先,简帛是我国早期图书的主要载体,早期作为“图书的馆”的图书馆是“简帛的馆”。
作为和传世文献相对的文献学概念,出土文献主要是指从地下发掘的甲骨、金石、陶泥、简帛乃至写本等古代文献材料。这其中,“刻于甲骨、金石,印于陶泥者,皆不能称之为‘书。书籍的起源,当追溯至竹简木牍,编以书绳,聚简成编,如同今日的书籍册叶一般。” [1 ]例如,“刘向为孝成皇帝典校书籍二十余年,皆先书竹,改易刊定,可缮写者以上素也”, [2 ]说明西汉刘向典校中秘的工作对象都是书写在简帛上的文献。从这一意义上说,简帛(尤其是竹简木牍)是我国古代图书的主要载体,我国早期作为“图书的馆”的图书馆应该是“简帛的馆”。
放眼世界,各国古文献多可分为纪念性的(monumental)和记录性的(record)两种,它们在书写材料、内容和目的上区别甚严。如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分两种,一般记录商务和政务的文字,是用削尖的木棍和芦苇书于泥版;而纪念性的文字,则是用刀凿刻于石头、象牙、金属和玻璃等坚硬材料上。古埃及,它的圣书体是宗教礼仪性的文字,主要用于庙堂或陵墓,也是刻在石头上(或刻在陶器上),字体比较规整(或译‘碑铭体);而僧侣体和人民体,多用于政务、商务或私人通信,以及科学讨论、文学创作,则主要是用毛笔或芦苇做成的笔,蘸黑墨或红墨钞在纸草上,字体比较潦草。玛雅文字,也是分为两类,一类是碑铭,一类是用毛笔写在树皮纸上。” [3 ]迄今已知最早的国外图书馆也是以收藏记录性的“软”材料文献为主。例如,公元前三千年前的埃及图书馆所藏多为写在纸草(Papyrus) 上的文本;公元前七世纪巴比伦尼尼微图书馆的资料则是刻在泥片(Clay Tablet)上的纪录;公元前四世纪印度图书馆所藏乃是书写在贝叶(Pattra)上的文献。
因此,商代窖藏甲骨不是我国图书馆的起源。至少就目前的考古成就而言,可能见到的我国最早图书馆只能是战国早期的遗留。当然,正如王国维先生指出:“书契之用自刻画始,金石也,甲骨也,竹木也,三者不知孰为后先,而以竹木之用为最广。” [4 ]由于简帛不像金石、甲骨等“硬材料”易于保存,所以我们可能见到的“最早”图书馆并不一定是历史上真正“最早”的图书馆。
然而,目前关于我国早期图书馆的研究成果,基本都是以传世的纸本文献为依据、“以文献证文献”而得出的。古谚云:“山川而能语,葬师食无所。肺腑而能语,医师色如土。”(方回《山经》引《相冢书》,明杨慎《古今谚》收录)。它深刻地揭明:山川的本来面目也许并不如葬师所云,肺腑的真实情况可能与医师的认识相去甚远。同样,关于我国古代早期图书馆的基本面貌,也是由类似“葬师”和“医师”的学者们代言的,他们的研究成果往往并不完全符合实际。因此,只有充分利用出土简帛,才能真正揭示我国早期图书馆的真实情况。
其次,大量简帛文书档案的出土表明,同以简帛为载体的文献又有图书与档案之别。
我国早期图书馆是“简帛的馆”,但这并不是说所有的简帛都是图书馆的集藏对象。总体上,迄今出土的简帛材料仍以书檄、律令、案录、符券、簿籍、检楬等档案文书为主,古人称为“艺文”或“经籍”的典籍图书并非出土简帛的主流。例如,尹湾汉简、走马楼三国时期吴简、里耶秦简等所出文献全部是文书档案,不包括图书。其中,“1996年10月在长沙走马楼发现的三国吴简,数量达15万枚之多,超过了以往所发现简牍的总和。” [5 ]而这批简牍的内容全部是档案文书。正是看到了文书档案类文献的大量出土,学者们才认识到:“过去研究简帛,大家是把档案和典籍放在一起研究,学界只有笼统的‘简牍研究或‘简帛研究。现在,由于材料山积,已经到了不得不分开的地步……文书档案,数量很大,特别是走马楼三国简和里耶秦简,数量动以万计,现在必须辟为专门领域。”[6 ]
这一区别,改变了长期以来图书、档案不分,从而图书馆与档案混同的认识现状,意义十分重大。例如,结合睡虎地秦简、青川木牍、龙岗秦墓竹简、周家台秦简的出土发现,我们认为秦朝的官府藏书有两大系统:一是博士官出于“通古今”之需而以“诗书、百家语”为主体的图书;二是文法吏出于具体行政公干之需而掌有大量文书档案,此为秦官府藏书的重点。相应地,秦朝官方文献整理也主要聚焦于文书档案。由此可以进一步证知,秦王朝的行政运作是建立在对官府藏书的收藏和利用上的,通过秦人对图书和档案的不同态度可以折射出博士官和文法吏政治地位的消长,并可考见秦王朝“以法治国”的行政本质。[7 ]与此相反,西汉刘向典校中秘,则完全以图书为对象,不包括文书档案。正如余嘉锡先生指出:“国家法制,专官典守,不入校雠也。《礼乐志》曰:‘今叔孙通所撰礼仪,与律令同录,臧于理官,法家又复不传,汉典寝而不著,民臣莫有言者。夫礼仪律令,既臧于理官,则不与他书‘外则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则有延阁、广内、祕室之府者同。” [8 ]也就是说,档案性质的法、律、令,以及同样具有档案性质的礼法一体背景下的礼典,并不在刘氏的文献整理范围之内。宋儒王应麟亦云:“愚按:律令藏于理官,故《志》不著录。” [9 ]它反映了汉朝与秦朝“以吏为师”迥不相侔的、以“独尊儒术”为取向的另一种政制气象。
图书与档案的分野,还可以进一步证明:萧何所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是文书档案,与今天的“图书”概念无涉,因而与图书馆关系不大;《汉志·兵书略·权谋》虽著录“《韩信》三篇”,但它是讲军事谋略的图书,与韩信参与汉初定制形成的“三十五家”军事律令档案文献《兵法》不是一回事;杨仆《兵录》承绪韩信《兵法》,也是军事律令的汇编或结集,而不是“我国最早的军事专科目录”;先秦古籍中的盟府、故府、周室、府库、大府等应该是兼收图书但以档案为主的档案馆。“当时只有档案馆,没有图书馆,典籍、档案和地图是收于一处”;[10 ]“尚书有青丝编目录”中的“尚书”不是儒家经典之一的《尚书》,而是司职文书收发或上传下达的官署机构“尚书台”,因此,“尚书有青丝编目录”不是我国一书目录(和群书目录相对)称名之所由。[11 ]我国文献目录有档案目录和图书目录两大体系,档案乃原始办事记录,图书具有思想上“盘根究底”或文采上“踵事增华”的超越内涵,因而档案目录只有“条其篇目”的“目”,而图书目录还有“撮其旨意”的“录”;刘向典校的“中秘”是我国目前可以确知的图书馆的真正开端。
再次,出土简帛有助于我们从宏观上认识当时的知识体系和知识分类,并进一步认识当时的图书分类。
中国古代图书散佚严重,古人所谓“五厄”、“十厄”,今人所谓“典籍聚散”,都是研究这类问题的著述。而迄今出土的简帛图书,多为失传有年的文献。作为传世文献的重要补充,出土简帛让我们看到了更多的古籍品类和数量,因而也有助于我们从宏观上认识当时的知识体系、知识结构和知识分类。总体上,诚如上文所述,当时以简帛为载体的文献包括图书和文书两大类。文书是档案学史研究的对象,可粗分为官文书和私文书两大类。就图书而言,《七略》、《汉书·艺文志》将当时的主要图书区别为六略(大类)、三十八种(小类),反映了秦汉之际的总体学术面貌。然而,“过去我们把关注的重点放在精英阶层文化,即《汉书·艺文志》中前三类——六艺、诸子、诗赋,而忽略了后三类——兵书、术数、方技。出土的简牍、帛书文献却有相当大的部分恰恰是‘兵书、‘术数、‘方技,天象星占、择日龟卜、医方养生、兵家阴阳的知识在古代随葬文献中的数量,表明它在实际生活中占了很大的分量,也常常是古代思想的背景。” [12 ]李零的《中国方术考》和《中国方术续考》(东方出版社2000年版和2001年版)、刘乐贤的《简帛数术文献探论》(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等文献,都是针对后三类文献的大量出土而撰写的著作,这无疑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后三类文献在秦汉社会文化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当时的图书在六略、三十八种的基础上还区别为两大部类——我们称之为“学”部和“术”部。事实上,秦始皇焚书正是首先区别文书与图书,再行对图书作两大部类的划分。总体而言,文书档案不在焚烧之列,图书类中的后三略(“术”部)也不在焚烧之列。如果说,文书档案主要由“吏”掌管,那么图书则主要由“士”所职掌。秦朝官僚结构中,和博士相对的是狱吏,也就是文法吏。《史记·秦始皇本纪》曰:“(始皇)专任狱吏,狱吏得亲幸,博士虽七十人,特备员弗用。”从字源上讲,士和吏都是由“史”分化而来,在甲骨文中,士、史、吏、使为一字。[13 ]这也说明了图书与档案文书在早期渊源甚密,只是在战国或春秋才出现分化。进一步说,“士”又分为文学士和方术士,简称学士和术士,《史记》、《汉书》中多有之。如《史记·秦始皇本纪》:“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这两类“士”分别掌管学部图书和术部图书。众所周知,章学诚“《校雠通义》的内容百分之九十以上是讨论《汉书·艺文志》的”, [14 ]其提出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中的“学术”,正是从这一意义上立说的。魏晋以降,尤其是《隋书·经籍志》以后,古代图书以经史子集四部分类为主,作为“术”的兵书、数术、方技皆入“子”部,反映了我国古代总体知识结构由秦汉之际的“学”和“术”并重,向重“学”轻“术”或有“学”无“术”的转向。
出土简帛还有助于我们认识当时的一些具体知识分类的学术依据和学术动机。例如,《汉志·兵书略序》“省十家二百七十一篇重”,所省十家包括兵技巧类的《墨子》和兵权谋类的《管子》两种。换言之,《汉志》只将《墨子》、《管子》等十家文献分入诸子略;而刘歆《七略》则将《墨子》、《管子》等十种文献同时“互著”在诸子略和兵书略,以强调《墨子》、《管子》兼有兵书的性质。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一号西汉前期墓葬出土《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尉缭子》、《六韬》、《墨子》、《管子》、《晏子春秋》等典籍,[15 ]前四种都是兵书无疑,而《墨子》和《管子》同时随葬,亦可证其兵书性质。由此可见兵书类文献是银雀山汉墓墓主的主要收藏,并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刘歆《七略》将《墨子》、《管子》同时“互著”在诸子略和兵书略的基本依据和学术动机。再如,《汉志·诗序》语涉齐、鲁、韩、毛“四家诗”,但《汉志》著录“《诗》凡六家,四百一十六卷”。四家《诗》而云“六家”,是因为《齐诗》又有“后氏”、“孙氏”两家,可见当时之分“家”并不特别严格。而如果按照这一标准,仅从《汉书》来看,可以独立成“家”的就有很多。例如,《汉书·儒林传》载:“韦贤治《诗》,事博士大江公及许生,由是《鲁诗》有韦氏学。”《隶释·汉武荣碑》云:“荣,字含和,治《鲁诗经》韦君章句。”这是《汉志》所没有著录的《鲁诗》韦氏学。据《儒林传》,类似的还有《鲁诗》张、唐、褚氏之学,许氏学;《齐诗》翼匡、师伏之学;《韩诗》王食、长孙之学等,它们都没有为《汉志》所著录。然而传世文献中的上述记载,并没有引起人们对所谓“四家诗”的质疑。直到1977年安徽阜阳汉简《诗经》的出土才改变了这一局面。人们发现,该阜阳汉简《诗经》“既与《毛诗》有如此之多的异文,可以断定其绝非《毛诗》系统”,同时也“不会属于鲁、齐、韩三家中的任何一家”,从而认定“《汉志》并没有将汉初治《诗经》各家囊括”。 [16 ]
最后,出土简帛真实地反映了古代目录、篇题等方面的具体形制。
大量简帛古籍的发现,“等于给我们打开了一座丰富的地下图书馆”, [17 ]有助我们复原早期图书馆的真实面貌。例如,有学者认为:“从文献记载来看,秦代著名的私人藏书家当有四人,即吕不韦、孔鲋、孔腾、伏生。” [18 ]实际上,伏生只是在秦始皇焚书时“壁藏”了一本《尚书》。据考古发现,湖北睡虎地、湖北云梦龙冈、湖北周家台、甘肃放马滩、湖北王家台等地都有秦简出土,它们都是墓主的私人藏书,实际藏书规模并不亚于吕不韦、孔鲋、孔腾之伦,更在藏有“一本”《尚书》的伏生之上。
总体上,对地下简帛文献的“有意”发掘始自1901年,并且20世纪的“前50年,主要发现是文书;后50年,才有大批古书出土”。[19 ]因此,先贤讨论古籍的目录、篇题等问题,多为没有见到简帛古籍的推测之辞。幸运的是,我们今天能够从出土简帛中直接见到古籍形制的原生面貌。例如,古人所谓“篇题在后”的结论就是根据宋版书得出的。然而,张家山247号汉墓出土的8种典籍中,《历谱》和遣策无标题。其余6种皆有标题,其具体分布情况是:《二年律令》、《脉书》、《引书》的标题都书写于开篇第一枚简的背面,即篇题在前;《奏谳书》、《盖庐》的题目书写于全书最末一枚简的背面,即篇题在后;而《算数书》的书名写在第六枚简的背面,即篇题在中间。 [20 ]可见,古籍书名位置并无定准,“篇题在后”的结论是值得商榷的。又如,清人卢文弨《钟山札记》所谓“古书目录,往往置于末”的论断长期为学界所信奉,但长沙马王堆《五十二病方》的52种病症方剂之“目”却列在该书前面,即出现了置于书首的前置目录。再如,学者们相信《易经·序卦》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书目,“目录之作,莫古于斯”。但上海博物馆购藏的楚简《曲目》,以及银雀山汉简的《孙子兵法》、《守法守令十三篇》目录都要早于《序卦》。 [21 ]
2 出土简帛在研究我国早期图书馆中的局限
出土简帛对于我国早期图书馆研究的价值是不言而喻的,但这并不意味着简帛文献本身可以独立地构成相关研究的自足材料。
首先,简帛文献能否顺利“出土”有很大的偶然性,实际出土的简帛文献也是十分有限的。单纯从简帛出发,难免以偏概全。事实上,1901年以来的出土简帛主要集中在西北和中南地区,且主要是私人所藏,官方文献则主要以作为官方办事记录的档案为主,而官府藏书迄今尚无任何发现。另外,“现己发现的简牍帛书,有不少都是从墓藏中出土。特别是典籍类的古书,无论是写在简牍上,还是写在缣帛上,几乎都是墓葬所出。这给我们造成一个印象,好像墓藏不出,就是当时没有。”[22 ]而揆以常理,实际情况显然并非如此。
其次,由于简帛长期埋于地下或浸在水中,出土时多已残损、散乱、扭曲和变形,有些材料还受到过盗掘的干扰,并且,简帛出土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很难保证已出土的文献就是最有价值的材料。例如,银雀山1号汉墓出土了5件木牍,其中只有2片可断定分别是《守法守令十三篇》13篇的篇名目录和《孙子兵法》中《势》、《九地》、《虚实》、《用间》、《七势》等篇的篇名目录,而其余3片的目录形制已不可缀合还原。并且,简帛的文字及音韵释读、断句、简序排列等等完全依赖人工,因此从一开始,简帛的整理就充满了人的主观见解。[23 ]
再次,古代藏书情况十分复杂,有些涉及到古代的书殉笔葬制度,往往并不是墓主的主动收藏。“古代墓藏埋什么不埋什么,这要取决于当时的随葬制度和习惯,并不是活着用什么,死了就一定埋什么;或者这一时期埋了什么,下一时期也还埋什么”;[24 ]“在古代墓葬中,竹简帛书是比较特殊的随葬品,它们的种类和数量同墓主的身份地位没有直接关系,不像棺椁、衣衾和铜器、玉器,可以根据其等级对号入座”。[25 ]因此,墓葬所出简帛与墓主生前藏书之间并不能完全划上等号。
综上所述,虽然出土文献在我国早期图书馆研究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并不能改变传世文献在相关研究中的坚实地位和历史价值,因而不能踵武“出土文献将改写或重写中国学术”, [26 ]认为出土文献也将会改写或重写中国古代早期图书馆的研究。
3 结语
有关我国早期图书馆诸多问题的研究,具有明显的“史学”性质,严格考订历史资料乃一切研究的首要前提。这就需要在对文献精选识断和辨惑裁定的基础上进行历史的分析和逻辑的归纳,确保研究结论与史料之间具有直接的对应关系。传世文献和出土简帛各有短长,从这一意义上说,王国维先生倡导的“纸上材料”与“地下材料”相结合的“二重证据法”, [27 ]仍然是我们在从事具体研究时所应恪守的主要原则。
参考文献:
[1]钱存训.印刷发明前的中国书和文字记录[M].北京:印刷工业出版社,1988:55.
[2]吴树平.《风俗通义》校释[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409.
[3][6][10][19]李零.简帛古书与学术渊源[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43,46-47,46,6.
[4]王国维.简牍检署考[M].上虞罗氏云窗丛刻本,1914:1.
[5]周立耘.专家聚首读“吴简”[N].人民日报,2001-8-22.
[7]傅荣贤.论秦朝图书与档案的分野及其“以法治国”的行政取向[J].图书情报工作,2009,(8):142-145,97.
[8]余嘉锡.古书通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4.
[9](宋)王应麟.《汉书·艺文志》考证[A].文渊阁四库全书:675册 [Z].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69.
[11]傅荣贤.“尚书有青丝编目录”正诂[J].图书情报工作,2009,(21):139-141,145.
[12]沈颂金.二十世纪简帛学研究[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3:11.
[13]许兆昌.先秦史官的制度与文化[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5-6.
[14]王重民.《校雠通义》通解[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13.
[15]许荻.略谈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古代兵书残简[J].文物,1974,(2):27-31.
[16]胡平生,韩自强.阜阳汉简《诗经》简论[J].文物,1984,(8):13-21.
[17]李学勤.简帛佚籍与学术史[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15.
[18]徐凌志.中国历代藏书史[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4:45.
[20]张显成.简帛文献学通论[M].北京:中华书局,2004:169-170.
[21]傅荣贤.中国古代目录五题[J].大学图书馆学报,2007,(2):46-50.
[22][24][25]李零.简帛古书与学术渊源[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72-73,72,82.
[23]曹峰.出土文献可以改写思想史吗[J].文史哲,2007,(5):38-51.
[26]李学勤.重写学术史[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27]王国维.古史新证[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1-4.
作者简介:傅荣贤(1966—),男,黑龙江大学信息资源管理研究中心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