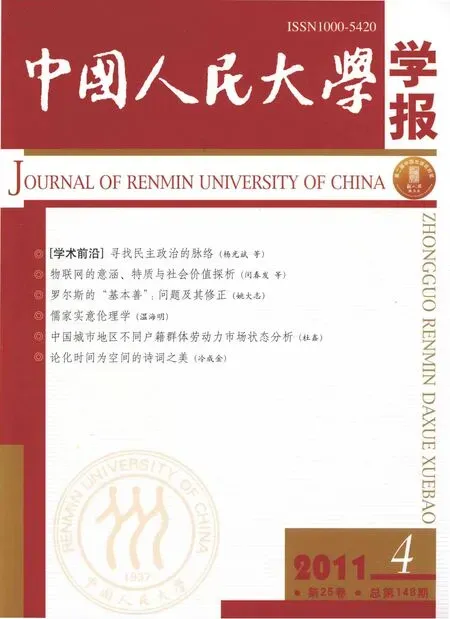日本近代“道德”、“伦理”概念的变迁
2011-02-10李萍
李 萍
本文所说的日本“近代”,指幕末至昭和初年,大体时间约为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30年代。日本在这一时期受到西学的影响,经历了重大的思想激荡,完成了一系列的社会变革。本文拟以“道德”、“伦理”两个概念的变迁为例,分析日本社会自身原有的伦理思想如何应对西方观念的冲击并进行了怎样的适应性调整。
一、近代初期译介西学过程中“道德”、“伦理”的变形
西方的“伦理”和“道德”概念分别产生于古代的希腊时期和罗马阶段,据说是亚里士多德最先将ēthos改造为ethic,并留下了人类第一部伦理学著作《尼科马可伦理学》,而西塞罗则将拉丁文的mores发展为moralis。“伦理”、“道德”的古义均为“风俗”、“惯例”,经思想家们提炼后开始指普遍、共有的行为规范。正如许多学者所指出的,西方古典时期伦理学的核心是探讨如何使一个人的生活变得有意义或幸福。这一问题通常又被归结为道德与幸福的关系问题。在哲学领域,“道德”、“伦理”的起源义均为“风俗”、“习惯”,所以“道德”、“伦理”并未被严格区分,只是个别思想家因关注点不同而偏重“道德”(如斯密、康德)或“伦理”(如黑格尔)。在西方伦理思想中,“道德”或“伦理”的最终根据大多诉诸永恒的信念或人类理性,这样的信念和理性可以为“道德”、“伦理”提供终极意义上的支撑。虽然在艺术审美、社会批判、文化构建等方面,近代西方都有彻底世俗化的转向,但在伦理思想领域,西方社会则或多或少保持了对信仰的敬重。在哲学上,这样的信念被不同的哲学家分别以“理性”、“知识”、“良心”、“自由意志”等概念加以表达。
在日本,大规模地接受西学(最早称兰学,后称洋学)始于享保元年(1716)德川幕府第八代将军德川吉宗所进行的“享保改革”。佐久间象山(1811—1864)虽然是当时非常有名的儒学家,但也十分关心兰学,并钻研了西方的自然科学、兵书、医书和制炮术。他以朱子学的“格物穷理”思想为基础来理解近代西方的科学,提出了“东洋道德、西洋艺术”的重要命题,将西方近代成就限制在技术这一范围。在他看来,虽然西学比传统“格物”更精致、更实用,但无非属于“艺术”或“技艺”之列,“道德”则只存在于东洋思想中。他所说的“道德”即儒家的道德规范、社会秩序观念,或者说未经改变的、恒常不变的传统价值观念,这样的纲常名教自然只能在传统的儒学体系中寻找。佐久间象山笃信只有“东洋道德”才能保证承认差别的身份秩序的存在(东洋社会结构的合理性),断定它优越于西方类似的东西,所以,完全不必学习或引入西方此方面的内容。可见,佐久间象山所说的“道德”并没有超出传统儒学的范畴。
1868年发生的明治维新改写了日本的历史,日本自此开始了富国强兵、殖产兴业等资本主义化过程。明治时代也是日本近代思想激荡、党派纷争的时期,在各种势力的综合作用下,日本近代社会的转型不仅是渐进的,也是几经反复和充满血腥的,思想界进步与复古、革新与保守的斗争始终没有停止,在“道德”、“伦理”问题上也不例外。
译介西方哲学最为热心者当推西周(1829—1897)。他曾进入幕府为翻译欧美科技方面的书籍而设立的“蕃书调所”学习。1862年。他为了完成购买军舰的手续和掌握军舰操纵技术,以海军留学生的名义被派到荷兰留学。西周利用这个机会,广泛涉猎了当时欧洲的社会科学及哲学研究成果,特别是当时十分盛行的密尔的功利主义和孔德的实证主义哲学。他最初把“philosophy”称为“西方的性理之学”,并认为“西方的性理之学”(类似于程朱理学)与经济学(类似于王政学)一样都是实学。他于回国后的第二年(1866)撰写了《百一新论》,这是一本试图把西方各种学问加以综合统一论述的书,也被认为是日本第一部哲学知识启蒙书。该书明确地把“philosophy”翻译成“哲学”,并认为哲学就是“通过参考物理、探明心理,确立用于揭示天道和人道的教之方法的学问”,它是统一“百教”的根本学问。“哲学”又被细分为致知学(logic)、性理学(psychology)、理体学(ontology)、名教学(ethics)、政理家之哲学(political philosophy)、佳趣学(aesthetics)、哲学历史(histo ry of philosophy)和实理上哲学(positive philosophy)。[1](P21-23)他还指出,儒学的一大弊端是“对政(政治学、法学)、教(道德学)的思考的确混乱”[2](P106),必须把外部的政治、法律的世界与内部的道德、价值的世界截然分开。需要指出的是,他对ethics的翻译并不一致,有时是“道德学”,有时是“名教学”。不过,他确实对“道德”与“伦理”做了不同的解释,认为“道德”(moral)与内在价值相关,“伦理”(ethics)则是关于道德的系统理论。这一解释对后世理解、使用“道德”、“伦理”概念产生了重要影响。①至今,在中国,为数不少的人认为“道德是关于善恶的观点”,“伦理是道德的系统理论”,又被称为“道德哲学”。
与西周把哲学看做是实学、是统一个别科学的方法论(实学式哲学观)不同,中江兆民(1847—1901)把哲学理解为探究更高级的(或者说次元的)形而上学诸问题的学问(理学式哲学观)。他于1886年撰写了《理学钩玄》,其中所设定的哲学体系包括“性理”(psychology)、“论理”(logic)、“法式”(mothod)、“原理学”(metaphysic)、“世界的害恶”(multi-monde)、“道德”(mo ral)。中江兆民也将mo ral翻译成“道德”,但认为“道德是以正当不正当的观念和这种自知的能力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3](P110)不同于西周将哲学的各个分支并列,中江兆民把“道德”看做哲学的最高阶段,是其他哲学内容如性理、法式、原理学等的运用。这种理解具有西方学问条分理析的特点。
新渡户稻造(1862—1933)曾游学欧洲多国,最后定居美国。他用英文著述来介绍自己祖国日本的思想文化,尤其注意到了日本人的道德与西方人的道德的差异。在欧美游历时,他经常被那些知道日本学校不进行宗教教育的欧美人问这样一个问题:不进行宗教教育又怎样实施道德教育呢?常常被这样的问题所困惑,总是不能马上作出回答,这促使他对此进行了长期的思考。后来他发现,自己被灌输的道德观念正是“武士道”,于是,他萌发了让自己的美籍妻子和更多的欧美人理解日本人道德的念头,从而用英文写下了《武士道:日本的精神》一书,通过对武士道的描述来说明日本传统道德的根基及特点。他在书中所理解的“道德”已经带有强烈的西方色彩,即生活方式、习俗、惯例,而非传统儒学的礼教内容。
进一步撇清“道德”的传统内容,为其加入近代元素的是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1834—1901)。他将“道德”与“富足”联系起来,认为道德与富足兼具才是“文明”的状态。他说:“所谓文明是指人的身体安乐、道德高尚,或者指衣食富足、品质高贵。”[4](P30)这里反映出与传统思想的重要区别:传统思想主张道德就是人生价值所在,也是评价、解释意义的根据,是目的本身;但福泽谕吉却将“道德”作为“文明”的一个构成要素,而且是体现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指标。这样,“道德”就被工具化了。此外,他不仅承认西方科学、技术的先进性,也肯定了西方道德的合理性,甚至指出西方道德的合理之处在于注重公德、兴公德。他明确且富有创意地将统一的道德一分为二,划分出私德和公德两个部分:“凡属于内心活动的,如笃实、纯洁、谦逊、严肃等叫做私德”;“与外界接触而表现于社交行为的,如廉耻、公平、正直、勇敢等叫做公德”。[5](P73-74)在文明社会,公德比私德重要,智慧比道德重要。日本传统道德“是专指个人的私德而言的”,只有将私德转化为公德,传统的“君子”才能转化为文明社会的“国民”。正是在福泽的大力传播下,“公德”以及“社会道德”的概念自明治中期以后在日本知识界普遍流传开来。其实,在西方伦理学中,并没有公德和私德的概念,也从未出现关于公德与私德的讨论,但福泽谕吉却把当时西方社会达到的社会道德状态理解为“公德”,这样,既可以为传统东方道德留下生存空间(作为个人心性修养),也提出了后起国家在资本主义化过程中加强社会道德普及和提升全民道德共识的问题。公德与私德的划分尽管在学理上仍存在不少问题,但现实意义非常重大,它甚至也影响了许多中国近代思想家如梁启超、孙中山、鲁迅等人。
二、明治中后期融合倾向的出现
明治10年代后半期至20年代后期,日本政府开始致力于确立近代国家和培育国民道德。1879年颁布的《修订教育令》把“修身科”首次提到所有教科的前列,成为“日本国民教育的核心”,日本的近代教育也由此从主知主义转为德育主义。中日战争的胜利(1895)进一步增强了日本人和日本政府的自信,以致出现了狂热的民族主义浪潮。在哲学领域,出现了与启蒙思想相对立的、以引导国民思想为目的而复活儒教思想的倾向。
元田永孚(1818—1891)于明治12年(1879)禀天皇之意撰写了《教学大旨》,明确提出:“自今之后,基于祖宗之训典,专以明仁义忠孝。道德之学,以孔子为主,人人尚诚实之品行。然此,各科之学随其才器,日益长进,道德才艺,本末具备。”[6](P137)他将道德、才艺分别置于本末的对阵之中,将接受西学的范围限定在技术领域,用儒教的“仁义忠孝”作为日本人精神的核心。因为儒家所强调的忠诚和孝的观念非常适合建立统一的君主立宪国家,在这样中必须保持一元意识形态的绝对统治。在他的倡导下,以教化为主的道德教育逐渐取代了明治初年建立在西方启蒙观念基础上的自主教育模式,以便减少西方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思想的负面影响;道德教育开始被看成强化国家的工具,道德的礼教内容及其教化功能等都受到推崇。元田永孚又从传统儒学德目中选出了20个作为《幼学纲要》(1882)的核心,认为这些德目是建立稳固的帝国而必须对国民进行的道德教育内容。这20个德目是孝行、忠节、和顺、友爱、信义、勤学、立志、诚实、仁慈、礼让、俭素、忍耐、贞操、廉洁、敏智、刚勇、公平、度量、识断、勉职。他的思想成为《教育敕语》(1890)的理论基础。但元田永孚毕竟是受到了近代思想洗礼的学者,他的复古仍然为西学的合理内容留下了少许空间,例如,在20个德目中,公平、勉职都是具有时代精神的,而且对一些传统德目也赋予了部分新的诠释,如信义、立志、俭素、识断等。
如果说元田永孚是复活旧道德的急先锋,那么,西村茂树(1828—1902)则温和同时也精巧了许多,他主张在折中东、西道德的基础上建立新的道德体系。西村茂树用“道德立国论”来批判西周的政教分离的观点,并于1887年出版了《日本道德论》一书。他认为依托国民道德实现了国内统一的日本,也可以凭借国民道德确保国际上和外交上的自立目标。但西村并没有简单地照搬传统儒教,而是增添了新内容。他把“道德之教”分成“世教”和“世外教”,前者包括东方的儒教和西方的哲学,后者包括佛教和基督教。他把后者作为“下等社会民众”的信仰而加以排斥,将前者作为“上等社会人物”的道德而奉为国民精神的支柱,换句话说,他力图将儒教和西方哲学加以综合,构成“日本道德的基础”。不过,他所说的西方哲学主要指孔德的实证主义哲学,为此,他舍弃了西方哲学的一般世界观和形而上学立场以及其他主流的哲学体系,而保留了在理论的精密性和方法论的有效性上具有明显优势的实证主义哲学流派。
井上哲次郎(1855—1944)最热衷融合东西方道德,他的思想以承认皇权、国体为前提,被称为国家主义的东洋道德之集大成者,但他的融合说表现出“命题之作”的局限性。他一生的学术目标就是融合东西方思想,将东方传统思想与西方哲学进行嫁接,用西方哲学的方法来挖掘、整理东方思想的内容。井上哲次郎与蟹江义丸编辑、校订了十卷本的《日本伦理汇编》,卷一至卷三为阳明学派,卷四至卷六为古学派,卷七、卷八为朱子学派,卷九为折中学派,卷十为独立学派和老庄学派。这套书在解释日本传统伦理思想资源时,力图将东西方的道德理论融为一体,例如,他们从日本古学派的思想中发现了类似于西方的“自由研究的精神”,认为日本朱子学所倡导的道德学说与德国观念主义伦理学说有异曲同工之处,等等。
即便在军国主义政治高压下,一些学者也受到西方自由主义和人道主义精神的鼓舞,坚持对“道德”、“伦理”的独立思考,反对单纯的复古或一味迎合政府教化的意图。大西祝(1864—1900)曾经尖锐地批判官方的《教育敕语》不是伦理学研究者自由讨论、学术交锋的产物,而是专制政治、君主意志的体现,它虽然部分反映了政府对国民特定道德德性的关注,但完全忽视了伦理学的理论争辩。大西祝表现出的自由主义精神在当时还有一些追随者,如桑木严翼、中岛德藏。相比于“国民道德论”的喧嚣,这种理性的、批判的声音却明显曲高和寡、应声了了。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这样的思想潜流一直存在于部分学院派学者身上,它日后成为日本知识界构建独立的伦理学体系的核心力量。
明治末年至大正的二十多年间,日本思想界出现了一个活跃期,教养主义、人格主义、观念主义、文化主义、日本主义等各种思潮或运动风起云涌。在1898—1901年间,日本学界主要围绕道德的作用问题展开了大讨论,起因是:当时的很多调查结果和民间的反映是,明治维新以来,法律侵入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但缺乏道德补充的法律并不能充分保证社会秩序和民众的凝聚力。人们开始怀念道德制约法律、引导法律的前现代社会环境,这进一步推动了强化德育主义的倾向。但学术界并未简单地抛弃法律,转向人伦道德,而是引入了一个西方概念“人格”(personality)。“道德”之所以优越于法律,没有道德的社会之所以令人不安,是因为道德是建构人格的重要力量,道德能够为人格提供内在支撑。中岛力造(1857—1918)是第一个翻译“人格”概念的人。人格概念的引入使日本近代的伦理学与心理学、法理学等现代学科之间建立起紧密的联系。由于人格概念对道德主体特征的揭示,有利于强调道德的精神性、内在性因素,这也使得道德可以摆脱传统的舆论、他人眼目、相互规劝式的外在作业或他律模式,使道德在世俗化世界中获得了有力支撑。
如果说福泽谕吉最先注意到道德的社会调节功能,涉泽荣一(1840—1931)则将道德的社会调节功能直接转化为经济发展的动力因。作为日本近代企业之父的涉泽荣一提出了著名的“《论语》和算盘一致论”。他说:“道德和经济如鸟之双翼,车之双轮,缺一不可,换言之,《论语》和算盘并不是对立之物,可以右手拿《论语》讲之,左手拿算盘计之,退则可利家和富国,进则可理天下之经济。”[7](P379)涉泽在经济界具有重要的影响力,他将营利与求道、经济与道德相融合的做法反映了当时日本社会的风潮,即力图用具有儒家色彩的道义来融合近代西方的功利意识、权利观念。
三、“道德”、“伦理”概念的确立
自19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就没有停止过对外的侵略、征服,但日本国内相对稳定,资本主义经济得到发展,资本主义政治目标也得以部分实现,因此,在思想界并没有完全关闭学习西方的大门,也没有停止对自身传统的思考。“日本知识分子当时如醉如痴地探讨的是在一个现代国家中道德的基础,以及道德与宗教、法律、科学理性的各种关系。”[8](P428)在此期间,日本出版了大量西方关于道德的撰述,并进行了初步的反思和综合的理论建构工作。例如:蟹江义丸和桑木严翼共同主编了《伦理学书解说》丛书(富山房出版),共12册,分别评述了杜威、斯蒂文等人的伦理学。阿部次郎(1883—1959)出版了专著《伦理学的根本问题》(岩波书店),这是一部系统探讨伦理学理论的著作,其中的问题意识和论证方式都借鉴了西方的思想。
在文学界和一般社会思潮中也体现了道德观念的变迁。有关“教养”、“理想”等问题的讨论、自然主义的盛行及对其的反思等都对当时日本人的道德观产生了深远影响。自然主义对当时的日本来说具有反叛性,因为它背离了集团主义的献身伦理和民族主义的团结道德,主张对自我本性的回溯,用自然而然的情绪、利益、感性来反对充满高压和一体化要求的社会道德氛围。评论家石川啄木在《时代闭塞的现状》一文中表达了对当时苦闷、忧郁的精神生活的感受,指出“自然主义”与其说是文艺上的一种思潮,毋宁说是在明治30年代中形成的新自我意识的根本支柱,年轻人的“私我主义”是社会“闭塞”的折射。在石川啄木的论述中,“道德”已经不再是传统的修身范畴,而是与现实生活相关的思虑。他曾这样追问:“每年数百公立和私立大学的毕业生,却有一半找不到工作,不得不借宿在贫民窟中……比他们要多几十倍、几百倍的年轻人却在半途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失去财产的同时也失去了道德心的贫民和卖淫妇激增说明了什么?”但从哲学层面上说,自然主义挣扎于进化论的唯物论和新康德派的观念论之间,是一种抱有理想主义却又不得不屈服于现实的威权主义伦理。不过,在当时的日本思想界,占据主流地位的还是主张伦理理想主义的德国新康德派思想、提倡人格说的唯心论和主张自我实现说的英国新理想主义。
在近代日本思想史上,在哲学和伦理学领域建树最为卓著的是西田几多郎和和辻哲郎。西田几多郎(1870—1945)的代表作《善的研究》(1911)确定了“西田哲学”,被认为是现代日本哲学的肇始。他将西方的“有”与东方的“无”作对比,“以回归后者的轨迹为论说的首要着力点,既可以在复兴东方文化的过程中,又可以在调和东西伦理的过程中,找到其各自的理论依据,所以西田的《善的研究》是明治日本的哲学、伦理学的归结,也可以理解为走向大正、昭和时期的转折点”。[9](P378)不过,构成西田哲学思维底色的仍然是东方的禅宗,贯穿西田众多著述的主线可以说是东方伦理高于西方伦理的优越感。
从“人格”和“自我”的探求出发所进行的“人格本位的实践主义”式伦理学探求,可以说是一种相对独立的伦理学体系,主要体现在《作为人间之学的伦理学》和《风土》的和辻哲郎伦理学之中。和辻伦理学的主体不是西方文化的“人”或传统儒学的“君子”,而是“人间”。“人间”是“人”的同时,也是“人世之中的人”,在此双重结构中的“人间存在的根本理法”被理解成这样一种辩证运动:它“通过个人(即对全体性的否定)进一步实现全体性(即否定之否定)”,即“绝对的全体性的自我实现的运动”。和辻深刻地指出,拥有各自历史的国民,只有在其特殊性中追求自身全体性的形成,真正意义上的inter-national的关系才成为可能。“国民道德”的问题只能在伦理学的终篇得出结论。在日本现代哲学史上,西田哲学、和辻伦理学都被视为日本化的哲学成就之重要代表。
在现代日本,哲学界鲜有讨论“日本人的道德”或“日本社会的伦理”之类的问题,与此相关的话题都被归入“日本人论”或日本国民性的讨论范围。在专业书籍和学术词典中,“道德”和“伦理”的解释已经非常具有现代性了。例如,在《现代哲学事典》中,对“道德”的解释是:“所谓道德,就是关于人应该像人一样行动的要求之探讨,一般认为它与伦理同义。”[10](P462)“伦理”则有两个条目:“伦理I”是对英语ethics的解释:“伦理与道德同义,都起源于风俗,伦理学或道德哲学在现代西方被分为规范伦理学和元伦理学两支。”而“伦理II”是对人伦的解释:“所谓伦理,就是关于人伦的理法,因为伦指人的小组和人的关系,理就是对这样的人的小组和人的关系所作出的条理规定……伦理这样的词汇揭示了中国思想的特色。”[11](P466)日本著名学者河合隼雄、鹤见俊辅主编的《伦理与道德》一书对道德和伦理的定义分别是:道德“就是关于善的事物和恶的事物的社会性共识”;伦理“是不依据外部参照系、有时还与外部参照系对抗的决断以及与个人选择深刻相关的、构成了善恶标准的思考”。[12](P279)不难看出,在今天,日本学术界对“伦理”、“道德”的解释几乎与西方同仁是同步的。虽然存在差异性认识,如对“伦理”另一层含义的说明,但其作为概念强调了个体独立意志的牵连,作为社会事项则主张通过说理、讨论、诉诸思想史来澄清。
[1]宫川透、荒川几男编:《日本近代哲学史》,东京,有斐阁,1976。
[2]日本名著全集刊行会编:《日本名著》,第34卷,东京,日本名著全集刊行会,1928。
[3]中江兆民:《一年有半,续一年有半》,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4][5]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6]《近代日本思想大系》,第30卷,《明治思想集》,东京,筑摩书房,1976。
[7]《涉泽荣一传记资料》,第41卷,东京,青木书店,1961。
[8][9]中村哲夫:《梁启超与“近代之超克”论》,载狭间直树编:《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10][11]山崎正一编:《现代哲学事典》,东京,讲谈社,2004。
[12]河合隼雄、鹤见俊辅主编:《伦理与道德》,东京,岩波书店,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