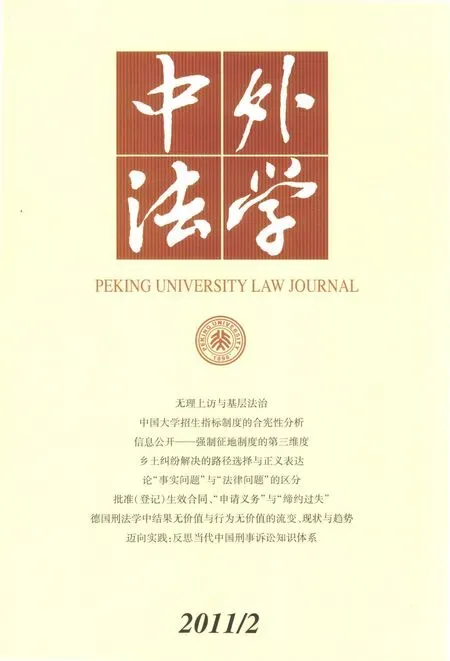“水和油”抑或“水与乳”:论英国普通法与制定法的关系
2011-02-09李红海
李红海
普通法和制定法是英国法中最主要的法律渊源,这二者之间的关系一直都是英美法律界的热点问题。理解这种关系不仅有助于理解普通法、英国法本身,而且对于理解司法和立法之关系等法理学问题也有帮助。因此,本文将通过梳理英美法学界在这一问题上的看法,来尝试对普通法和制定法的关系进行描述和分析。
众所周知,在英国实际上存在普通法、衡平法和制定法三种法律渊源——这是按照法律规则的来源加以分类的:即普通法来自于普通法法官,衡平法来自于衡平法法官,制定法来自于国王加议会(king in parliament)。但另一方面,如果从形式上来说,我们又可以将这里所说的普通法(狭义上的)和衡平法合称为“普通法”(广义上的)——而且事实上这二者在 1875年英国的司法改革之后就融合(无论是程序上还是实体上)在一起了〔1〕关于此,请参见 F.W.Maitland,Equity also the Fo rms of Action at Common Law,two coursesof lectures by F.W.Maitland,ed.byA.H.Chaytor andW.J.Whittaker,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09,pp.15-17。——从而以判例法的形式共同区别于体现为成文形式的制定法。亦如艾森伯格所言,普通法是法院自己建立起来的那部分法律;〔2〕参见(美)M.A.艾森伯格:《普通法的本质》,张曙光、张小平、张含光等译,法律出版社 2004年版,页 1。此处的引文为引者自译。或如杰克·彼特森 (Jack Beatson)所说,普通法是建立在判例基础上的法律,在这个意义上包含衡平法。〔3〕参见 Jack Beatson,“Has the Common Law a Future?”,Cam bridge Law Journal,Vol.56,(1997), p.295。如此,此处所谓普通法和制定法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指普通法、衡平法与议会制定法之间的关系,或曰法官法和议会立法之间的关系。
一、传统的观点:“水和油”
在英美法律界,传统的观点认为普通法和制定法是两种非常不同的法律渊源,因此根本不能等同视之。这些差别主要体现为:普通法是由法官在司法实践中“创制”或“发现”的,而制定法则是议会“制定”的;普通法源于民众的社会生活,是对其间规律的总结,体现的是规律性的内容,而制定法则根基于政策和人的意志,因此带有临时性、意志性,甚至是武断性;普通法更多体现的是整个法律体系中的基本原则,因此可以从此案类推到彼案——事实上普通法也主要是通过这种方式实现发展的,而制定法由于不是扎根于原则,因此不能将制定法条款类推适用于普通法,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不能类推适用于其他制定法条款;〔4〕参见 Jack Beatson,“The Role of Statute in the Development of Common Law Doctrine”,Law Quarterly Review,Vol.117,(2001),p.248。普通法并无明确的边界,而制定法的适用范围一般都由其自身的条款予以了明确的限定……〔5〕参见 Trevor R.S.Allan,Law,Liberty,and Justice——TheLegal Foundations of B ritish Constitutionalism,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pp.79、81。
这些似是而非的说法在我看来多少充斥着意识形态的色彩,因为其中的很多结论很难说是史实或事实。比如就法律作为社会运行的规律而言,你很难说法官的“发现”就不会或没有掺杂个人意志,而议会的“制定”就完全是个人意志作用的结果而没有建立在对社会规律的认识基础上;而某些普通法原则本身就来源于制定法的史实也反证了上述的很多结论……因此,〔6〕如后文提到的,普通法中的许多基础性制度实际上是来自于亨利二世和爱德华一世时期的制定法。如限嗣继承制度实际上来源于 1285年的《附条件赠与法》。英美法律界就普通法和制定法关系的这些传统观点,与其说是事实还不如说是信条、信仰,是这个共同体千百年来一直秉持和延续的基本信念和价值观。
也许正是由于这种信念和价值观,导致了很多法律家 (包括法官、律师和法学家等)对制定法采取了一种漠然置之的态度。庞德曾对此有如下描述:
……我们有着太多的立法,而法院和律师却对此漠不关心。法律教科书的编写者们仔细地、从最偏远的角落里收集来那些已遭废弃的判例并加以引用,却很少去引用制定法——除非是那些已经成为我们普通法一部分的、界碑式的制定法;即使引用制定法,也是通过司法判决来适用的。同样,法院倾向于对重要的制定法置之不理:不止是裁决其为宣示性的,而且有时候会悄无声息地认定其为宣示性的而不给出任何理由,他们只是引用先前的判例而并不提及相关的制定法。〔7〕这里庞德部分地引用了他人的看法,参见 Roscoe Pound,“Common Law and Legislation”,Harv.L. Rev.,vol.21,(1908),p.383。
虽然普通法在美国与英国的情况差别很大,虽然庞德为美国学者,但其对于普通法法律家对制定法之态度的这段描述,却与英国并无二致。
剑桥大学法律系的特雷弗·艾伦 (TrevorAllan)认为,制定法在出台时要考虑到既有的普通法规则的存在,在这个意义上制定法会受到普通法的影响;而普通法则有着更为深厚的法律原则基础,因此并不受制定法的影响。〔8〕Allan,见前注〔5〕,页 79、81。彼特森将艾伦的这种说法归纳为一种单向度的影响,“尽管普通法原则会注入制定法之中(除非后者明文排除之或明确与之相悖),但一般情况下制定法不应影响普通法”。〔9〕Beatson,见前注〔4〕,页 248。
类似的说法还有很多,其反映出来的 (在我看来)都是一种对于制定法的敌视和警惕态度,即普通法法律家们生怕议会通过制定法侵蚀自己的权力而慌不迭地要和制定法保持距离,甚至是划清界线。这被彼特森形象地比喻为“油和水”(oil and water)的关系,即制定法和普通法就像油和水,二者源出不同,并肩流淌,彼此独立。〔10〕Beatson,见前注〔3〕,页 300。
那么普通法法律家们为什么会对制定法采取这样一种心态呢?在我看来,这和普通法法律职业阶层的兴起和发展密切相关。普通法法律职业阶层的兴起大概可以定位于 13世纪的英格兰,作为其核心代表的是王室法官,其后又包括围绕在伦敦中央王室法院周围而出现的普通法律师。王室法官本来是国王的臣仆,是国王委以行使他固有司法权的王室官员,但一些机缘和因素使得他们逐渐趋于独立。〔11〕比如令状、格式诉讼所带来的法律技术化、专门化,实际上提高了诉讼的难度,为法律的专业化、职业化“创造”了前提。关于这一点可参见(英)保罗·布兰德:《英格兰律师职业阶层的起源》,李红海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年版,页 55-70。有关该独立过程经常提及的一个例子是,12世纪后半期格兰维尔〔12〕亨利二世 (1154-1189年在位)后期的王室法官,据说著有《论英格兰的法律与习惯》(1190年左右成书)一书,该书被誉为英国法律史上第一部有关英国法的重要著作。的著作中还引用了优士丁尼《法学阶梯》中的话“皇帝的命令就是法律”,而到13世纪中期布拉克顿〔13〕亨利三世 (1216-1271年在位)时期的王室法官,著有《论英格兰的法律与习惯》(1250年左右成书)一书,该书是继格兰维尔著作之后第二部英国法的重要著作。在他的著作中则提出,“国王不在任何人之下,但却在上帝和法律之下”。布兰德的研究也表明,法律的技术化和专业化使得普通法律师开始在 13世纪兴起,并且和王室法官一道形成了一个分享某种共同知识、遵循某些共同职业伦理规范的共同体或职业群体。从一定意义上说,正是这个群体阻止了罗马法在英格兰的复兴 (因而更不用说继受或接受了),〔14〕参见 F.W.Maitland,English Law and the Renaissanc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01,pp.23-26。并且在后来垄断了英格兰的法律事务和掌控了英格兰法律的发展。
但这个生发于国王后来却又竭力独立于国王的阶层,在 16、17世纪却面临了空前的生存危机。都铎和斯图亚特王朝的专制,衡平法庭、咨议会等特权法庭(作为行使国王【所保留之】司法权的机构)对普通法法庭管辖权的侵蚀以及这两类法庭之间的对立,王权的强大 (相对于以前任何时代,尤其是此前的约克和兰开斯特王朝),使得普通法法官和国王之间的关系必须得到重新明确。因为司法权本源自于国王,但普通法法律家们却总是力图主张自己的独立地位。这种紧张在 16世纪末 17世纪初就有过许多表现,但其顶点却是那场众所周知的、詹姆士一世国王和柯克之间面对面的冲突,〔15〕关于这场冲突的详情,请参见 Sir Edward Coke,12 Coke’s Reports,63,65.(注:这是引用柯克本作品的通用格式)。后来柯克被免职,普通法传统和普通法法律职业阶层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普通法法律家们才开始全面、集中、认真地论证普通法的基本理论问题,即普通法的本质,其正当性、合理性,普通法和制定法 (因而也是和主权者)之间的关系,等等,是为经典普通法理论。就和制定法的关系而言,经典普通法理论主要是通过说明普通法与制定法之间的不同、普通法自身的优点等,来与制定法划清界线的,这也是彼特森“油和水”关系说的实质。这些观点经过柯克、黑尔和布莱克斯通的论证、发展和完善,为英美的普通法法律家们所继承和接受,并成为了他们的基本信念。
彼特森用油和水来比喻制定法和普通法的关系,其主要强调的是这二者之间的相互独立,这在前文已有论述。除此之外,在我看来,为经典普通法理论同样强调 (至少是述及)但却并未为彼特森所明示的一点是,在普通法法律家那里,普通法是高于制定法的。恰如日常所见,油总是浮于水上,并且彼此相对分离。在这个意义上,彼特森的油和水的隐喻其实恰好完整地体现了经典普通法理论中关于普通法和制定法之关系的内涵:一方面,二者相互分离,彼此独立;另一方面,普通法还高于制定法,是制定法的基础,如水处于油之下 (因此为其基础)那样——尽管彼特森自己并未对这后一点予以明示。接下来我将集中讨论这后一点。
关于普通法高于制定法的观点,我们可以举出许多理论和实际的例子。
首先是实践方面。在普拉克内特对 13~14世纪中期英国制定法的解释问题进行的研究中,我们可以发现很多有关普通法高于制定法的“蛛丝马迹”。如,13世纪晚期和 14世纪早期,某些法官作为咨议会成员曾参与了某些法律的制定,而后来他们又在司法过程中来解释这些他们制定的法律。他们有时进行严格的字面解释,有时进行了很大的扩展,有时又大大缩小了制定法的适用范围,有时还会直接拒绝该法的适用——认为合适时会完全置制定法于不顾。〔16〕参见 T.F.T.Plucknett,Statutes and Their Interpretation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Four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22,pp.I-XXIX,20-34。因此,如普拉克内特所言,至少在这一时期,法官的司法并不规范,制定法之于法官只是他判案时的一种规范来源、一种资料而已,而这种来源或资料未必就比习惯、国王的令状等具有更高的神圣性、权威性。因此,此时法官对制定法的型塑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作用还很大:可以扩大、缩小之,也可以不适用之,甚至还可能宣布其为无效!在这样的背景下,法官高于制定法、普通法高于制定法的结论完全是可以被接受的。
实践方面的其他典型事例,还包括 17世纪的博纳姆 (Bonham)案和后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司法审查权。〔17〕关于此二者,参见(美)爱德华·S·考文:《美国宪法的“高级法”背景》,强世功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6年版。但关于博纳姆案的详情,可参见 T.F.T.Plucknett,“Bonham’s Case and Judicial Review”,Harvard Law Review,Vol.40,(1926-1927),pp.30-70。在博纳姆案中,柯克引用了 14世纪的先例说:“在很多情况下,普通法会审查议会的法令,有时会裁定这些法令完全无效,因为当一项议会的法令有悖于共同理性、权利或自相矛盾或不能实施时,普通法将对其审查并裁定无效。”〔18〕见上注,考文书,页 63。英国后来有些判例接受了这一理论,不过 18世纪时它又被平静地抛弃了,然而它却被美国接受了,形成了司法审查的制度。只要法官可以审查制定法的效力,只要遵循先例的原则还在起作用,我们就可以说普通法高于制定法的结论是有意义的。
再来看理论方面的支持。
经典普通法理论家之所以认为普通法高于或优于制定法,这和他们对法律概念的理解直接相关。经典普通法理论认为,法律并不是个人意志的反映,而是对社会生活规律和人们生活习惯、规则的揭示和体现;换言之,法律是被发现的,而不是被制定的。不仅普通法如此,制定法也一样,它们之间的不同仅在于揭示者(法官 v.立法者)和揭示之后果的体现形式不同(判例 v.制定法)。〔19〕参见 G.J.Postema,Bentham and the Common Law Tradition,Clarendon Press-Oxford,pp.3-13。
而问题恰恰在于,议会立法这种形式在完成揭示社会生活规律之任务时存在很多缺陷。如,与边沁完全相反,柯克和布莱克斯通都认为导致英国法混乱、不一致和不公正的唯一或至少主要事由,是议会立法而不是普通法。〔20〕同上注,页 15。而之所以如此,布莱克斯通认为这是因为议会立法存在某些内在而绝非偶然的缺陷。这主要体现在,作为议会立法之核心的人的意志具有临时性和武断性,而不是对现存社会秩序的理性反思,因此无法保证其合理性。更为糟糕的是,议员变动不居,无法保证其立法产品形成一个内在一致的合理体系;而不像普通法那样,法官必须从先前的资源(如判例)中寻找规则,并以此为出发点对手头案件所适用的规则予以重新表述,因而可以保持规范的一贯性和连续性。〔21〕同上注,页 15-16。更为严重的是,布莱克斯通认为,制定法威胁到了法律的性质及其所提供的自由。他说,制定法是最高权力之行使的显而易见的表征,但司法决定并非权力之行使而是对其所发现之既存秩序的报告。不过该秩序并不是创设的,也非从民众共同生活之外强加的,而是自发形成的,而法律毋宁是对这一生活秩序的表述而已,因此法律应使自由成为可能而非对自由的限制。〔22〕参见Blackstone,1 Comm.39-74(注:这是引用布莱克斯通《英格兰法释评》的通用格式)。在此意义上,普通法可以说来源于民众并建基于民众的同意之上,而这种同意要比代议制之同意深刻得多,因为它来自于这样一种认同感:规制其生活的规则是他自己的规则,它们限定其生活、赋予其生活以空间和含义,且早已施行并根深蒂固,以致对他来说完全是自然而然的。
因此,从传统的角度而言,制定法与经典普通法理论家们所认可的法并不一致,在他们看来制定法甚至不能算作法,因为它并没有符合经典普通法理论上述关于法的定义。但即使自17世纪以来,经典普通法理论的上述观念就已开始受到了挑战。人们发现,一些人可以通过行使其意志而创制法律,法律不仅被视为现存社会 (甚至是自然)秩序的正式和公开的表述,而且还是改变或重生这一秩序的工具。这样的现实让经典普通法理论不得不为制定法在其理论体系中重新寻找合适的位置。而在这方面,黑尔的说法更具有说服力。
黑尔认为,法要成其为法,或法是否为法,不在于其产生或引入既有法律体系的方式,而在于其现实的权威基础,即要为民众在社会生活的实践 (自然也包括司法实践)中使用、检验并接受。如果不能为民众所接受,那么无论这种“法”宣称自己有多高的权威、来自于何处,都只能是一纸具文。他解释说,今天的普通法有很大一部分实际上起初来自于制定法,但后来它们被吸收进了普通法,成为了普通法的一部分,从而成为了真正的法。今天英格兰的法律中有很多规则起初是来自于罗马法或教会法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认可了罗马或教会的权威;它们之所以能够成为我们的法律,是因为这些规则为我们的实践所接受从而融入到了我们的法律中。习惯或习惯法同样如此,并不是所有的习惯都成了普通法,它们也有一个被选择、被吸纳或被放弃的过程。如此,制定法也不例外,它也需要接受实践的检验并在既有的法律体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才能真正具有效力。〔23〕参见 SirMatthew Hale,The History of the Comm on Law of England,6th edition,London:Butterworth, 1820,ChapterV II-V III。
而所谓普通法,就是这些在民众社会生活中真正起作用的规则的总和。制定法要想真正成为法,就必须为社会实践、为普通法所接纳,在这个意义上,较之于制定法,普通法更具有基础性、权威性,因而也可以说是如自然法一般地高于制定法、实在法。
显然,与柯克和布莱克斯通比起来,黑尔的解释更为圆满也更能让人信服,它使得普通法高于制定法的观点在理论上得到了强有力的论证。
综上,在普通法和制定法的关系问题上,英美法律界传统上采取了彼特森所谓的“油 (制定法)和水(普通法)”的关系说,即普通法和制定法彼此分离,各自独立;而且普通法是制定法的基础,因此在一定意义上高于制定法。这种传统观点甚至还在主宰着今天的英美法律界,而其根源则在于普通法法律职业阶层为了自身的独立而“人为”地和制定法划清界线,在于以柯克为代表的经典普通法理论家们对于普通法立场的极力维护。
二、真实的谎言:对油水关系说的批判
但源自于经典普通法理论家们的这种“孤芳自赏”和“顾影自怜”,其实从一开始就遭到了质疑和反对。本着君主至上和实证主义法学的立场,霍布斯在 17世纪就对柯克的观点进行了批判。实证主义法学认为,只有主权者制定的法律才是真正的法律。霍布斯认为,创制法律的不是智慧,而是权威;除非一个人拥有立法权,否则他就不能够创制法律;使得法律具有效力的不是法律的文本,而是那个拥有国家之力量的人的权力。因此国王是我们的立法者——不仅是制定法的立法者,也是普通法的立法者。〔24〕参见(英)托马斯·霍布斯:《哲学家与英格兰法律家的对话》,姚中秋译,上海三联书店 2006年版,页 1-20。显然,霍布斯采取了一种和柯克完全不同的法律观:在这里,法律是权力和意志的结果,而不必然与智慧和对社会规律的揭示有关;法官也不再是任何法律的“发现者”或“创制者”,而只是一个执行国王意志的臣仆。在这种法律观主导下,作为国王意志主要体现方式的制定法自然要高于普通法,因为后者只是作为国王之臣仆的法官的意志,是国王意志的间接体现。用简单的公式表示即为:国王产生制定法;国王产生法官(国王之臣仆)产生普通法。
霍布斯对柯克的批判是致命的,它直接点中了经典普通法理论的要穴,因为他的理论更能够反映当时的社会、政治现实,更为实证;而柯克那些意识形态式的说教最多只是普通法法律家们的一厢情愿,是一个真实的谎言——它可以成为法律家们的理想和信念,但却很难说是事实!因此普拉科内特认为,普通法高于制定法的说法属于无稽之谈;〔25〕Plucknett,见前注〔16〕,页 26-29。贝克也认为,这只是法律家的观点而并非历史事实。〔26〕参见 Sir J.H.Baker,An Introduction to English Legal History,4thediti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p.195。尽管后来黑尔基于霍布斯对柯克的批判有一个回应,尽管黑尔的理论较之柯克更为缓和也更具说服力 (见上文末尾),但 17世纪以来在英格兰蓬勃发展的关于主权的政治观念还是改变了人们的法律观:中世纪的法学认为,制定法履行着与法官同样的职责——宣示、阐释和说明早已存在于民众实践中的法律,只是更为明确和概括;而到了17世纪,制定法则不仅被视为现存社会(甚至是自然)秩序的正式和公开的表述,而且还是改变或再生这一秩序的工具——因为人们发现,一些人竟然可以通过行使其意志而创制法律!〔27〕Postema,见前注〔19〕,页 15。再加上都铎王朝以来的专制和 17世纪初的政治斗争,最终使得以柯克为代表的普通法陷入了空前的生存危机——这一点前文已有论述。
不过令人惊异的是,普通法并未在 17世纪的危机中消亡或垮塌,而是有惊无险地渡过了难关。王权过度膨胀导致的结果是其自身受到了限制,而站在王权对立面的普通法反而巩固了自己作为英国民众自由之堡垒的地位。接下来的政治斗争主要发生在议会和国王之间,普通法没有再受到此二者的特别压制。同样,经典普通法理论也并未因霍布斯的批判就销声匿迹——毕竟,普通法法律家是法律界的主流;相反,这些观念还随着普通法延续了下来,并注入和主宰了普通法法律职业阶层,直至今天。
但经典普通法理论存续下来的事实,并不意味着其关于普通法与制定法关系之论述中所存在的问题就消弭了。我们还是从油水关系说的两个方面分别对之进行解构。
首先,所谓的普通法和制定法相互分离、彼此独立的状况,其实从一开始就不是事实,而且今天这种状况尤甚。这其中一个突出的例证是,早期普通法的很多内容其实都来源于制定法。比如贯穿整个中世纪最主要的一种不动产诉讼形式的新近侵占之诉,据说就来源于 1166年的《克拉伦敦法》(Assize of Clarendon);如果考虑到普通法中救济可以决定权利的特点,我们甚至可以说,普通法中对于不动产的占有从事实(如大陆法通常认为的那样,“占有”只是一种事实而非权利)上升为权利的过程也源于该法。而取消次级分封并代之以同级转让的《封地买卖法》、设立限嗣继承的《附条件赠与法》也都是普通法重要的规则来源。甚至像陪审这种最为典型的普通法制度的引入,其实在一定程度上也要归功于前述《克拉伦敦法》和 1176年的《北安普顿法》。〔28〕有关这几则制定法的情况,请参见(英)密尔松:《普通法的历史基础》,李显冬、高翔、刘智慧、马呈元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9年版,页 140-155。当然,站在普通法的立场上,我们也可以说这些里程碑式的制定法后来以黑尔所说的方式融入到了普通法中。但无论如何,我们这里所看到的是普通法和制定法紧密地交织在一起,难以区分和分离,而不是分立和互不干涉。而到了今天,二者的这种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的状况更为明显。比如,英国很多制定法的用语都来自于普通法 (比如 1925年的《财产法》),这样普通法就会通过法官对制定法的解释来影响到制定法的实际含义和运行。因此,普通法和制定法之间并非像传统的油水关系说所描述的那样,相互独立、互不干涉,而是从一开始就纠缠在一起,无法分离。
其次,所谓普通法高于制定法的说法也并不总是事实——司法审查表明有的时候也许是。一个最直接和明显的证据是,制定法可以取消或改变普通法。比如《封地买卖法》对次级分封的取消,1535年《用益权法》对受益人用益权的转化 (从衡平法权利转化为普通法权利),1873 -1875年的《司法法》对普通法诉讼格式的废除,1925年《财产法》对过去众多普通法地产权的取消,等等。
更为重要的是,不止是油水关系说本身受到了批评,越来越多的人已开始对其理论基础提出了怀疑和批判。早在 20世纪初,庞德就对经典普通法理论中的某些说法提出了质疑。如有人认为,制定法“没有根基”,而只是“草率和很不审慎地被采纳”;它们很粗糙,与其所将要适用的情形很不适合,因此几乎无法执行;制定法还是“导致诉讼的渊薮”,相反普通法并无这些缺陷,“而是奠基于公正的原则之上”,“是各种对立的利益长期斗争、协调的结果”。针对这些说法,庞德指出:
几乎无须认真考虑就可以断定这些经常提及的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戴雪已经告诉我们,已婚妇女法在关于分割财产的衡平法理论中拥有很深的根基。我们能说那些取消普通法关于不适格证人之规定的制定法、那些允许被告人作证和允许刑事案件上诉的制定法,都是没有根基的吗?难道任何普通法原理都要比这些制定法或坎贝尔勋爵法、莱昂纳多勋爵法及票据法,更为坚实地建基于公正的原则基础之上吗?衡平法的精致和大法官加于受托人身上的过于道德化的不可能,就一定比受托人救济法有更深厚的根基和更代表公正和正义吗?难道任何司法判决的制作都比统一州法专员委员会或国家统一离婚立法委员会所提出法律草案更为精细认真,或与其所将适用之情形更适合吗?哪个法庭在作出与工业有关之判决时能够 (甚至是假意)像立法委员会那样经常深入基层和生产第一线进行调查,并听取雇主、雇员、医生、社会工作者和经济学家关于工人和公众需求的证言?
还有人争辩说,因为普通法是习惯法而且建基于被统治者的同意,因此高于制定法。为此,庞德回应道:
今天我们看到,所谓的习惯只不过是司法裁决的习惯,而非公众行为的习惯。我们还看到,(国会)立法是一种真正、也更为民主的法律制定方式,在这里民众可以更为直接和明确地表达其意志。我们还被告知,未来的立法在于将民众的认可置于社会实验室生产出的东西之上,而很显然,法院是无法操控这种实验室的。〔29〕这两处均见 Pound,见前注〔7〕,页 404-407。
第三,自工业革命以来,英国的社会问题越来越复杂,这需要议会以制定法的形式来快速应对,并以带有普遍性的方式来推进和实现社会变革,而在这方面法官从个案到个案的缓慢演进式变革显然力不从心。因此整个 19世纪,英国的制定法呈爆炸式增长之势,其数量之巨决不亚于任何大陆法国家。而普通法代表的是农业社会的经验,〔30〕Pound,见前注〔7〕,页 404。当工业时代 (更不用说全球化时代了)到来时,它就无法适应更为复杂的社会形势了,因此它只能淹没在制定法的汪洋之中。
再者,彼特森曾指出,随着欧洲一体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欧盟的法律和指令等不断涌入英国,它们或者需要由英国的法官直接适用(如 1998年的《欧洲人权公约》),或者需要由英国议会通过制定法将之具体化后再由法官适用(如各种指令)。在第一种情况下,英国法官所需要解释的是一种以不同于英国之立法方式所起草的法律;即使在第二种情况下,英国议会在对欧盟的指令或立法进行转化时很多时候也是采取原文照抄的方式,其结果是法官面临的问题和第一种情况差不多。类似的问题在法官解释国际法规范时也会出现。大陆法性质的制定法进入英国的结果是,英国法官需要以一种不同于以往的方式 (也许是大陆法的解释方式)来面对和解释这些制定法,而在大陆法的传统中是不存在所谓的“油水关系说”的,大陆法法官并不会以普通法法官的眼光来审视制定法。在这些情况下,所谓的油水关系说早已不是事实,或者从来就不是事实;而面临彼特森所说的内外压力 (指国内制定法越来越多、作用越来越大、涉及的范围越来越广,国外或国际上大陆法性质的制定法不断涌入),普通法法律家必须重新定位他们看待制定法的视角,作为局外者的我们,也必须重新审视普通法和制定法的关系。
三、水乳交融:普通法和制定法关系的真谛
既然传统的油水关系说已经不再适合于 (也许从来就没有适合过)描述当下的普通法和制定法的关系,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来重新看待这个问题呢?我将这种关系定位为“水和乳”的关系,意思是普通法和制定法之间是水乳交融的关系:二者相互影响,彼此难以分开,因此也很难说谁高谁低。先来看制定法对普通法的影响。
1.制定法确立或转化为了普通法。这指的是如下的情形:因为该制定法确立了英格兰法律体系中的某些基本制度或者揭示(或发现)了英格兰社会生活中的某些基本规律,而成为了英格兰法中的基础性、根本性、恒久性的规范,从而转化为了普通法。典型者如 12、13世纪尤其是亨利二世和爱德华一世时期的那些里程碑式的制定法,具体如曾确立早期普通法多种基本诉讼格式和引入陪审制的《克拉伦敦法》、《北安普顿法》,取消次级分封制的《封地买卖法》,确立限嗣继承的《附条件赠与法》,1352年确立基本叛逆行为的《叛逆法》,1535年的《用益权法》,等等。我们可以在一种较弱的意义上说,这些制定法确立或创制了普通法;但更为准确的说法应该是,这些制定法因其内容(确立基本制度或揭示基本规律)的根本性而融入了这个社会、为英格兰社会所普遍接受和认可 (这正是普通法所要求的或对法律概念的界定),因此具备了普通法的特征,融入了普通法,成为了普通法、英格兰法的一部分。
2.从制定法的适用过程中衍生出普通法。这是基于制定法生发出普通法最常见、最普遍的方式。具体是指,普通法法官在将制定法适用于具体案件时,通过对该制定法的解释,将抽象的制定法规则(rule)与具体的案例场景相结合,从而产生出一个适合于本案的新的、具体的规则(ruling)或理论。这后一规则、理论显然来源于前述制定法,但又不同于该制定法,因为它是该制定法适用于本案的结果,属于法律的适用而非法律本身。当后来的法官碰到类似场景之时,他所依据的可能就不是前述的制定法本身,而是前述法官总结出的那一新的具体的规则或理论;而当后来的法律学生、律师、法官阅读该先例并试图总结出其中蕴含的规则、理论之时,他们总结出的也是后面的新的具体的规则和理论,而不是前述体现在制定法中的规则 (因为这个规则不需要总结和提炼而是现成的)。这集中体现了法律和法律的适用之间的不同,但更重要的是,它也揭示了普通法生命之树长青的原因所在:法律条文必然要付诸实施,因此法律条文和法律适用之间的距离必然存在;只要制定法还需要法官去适用和落实,只要遵循先例的做法或原则还存在或被认可,普通法就会从制定法中源源不断地吸取营养,普通法就有存在的空间和可能,就会永葆青春。
3.制定法改变或取消普通法。关于这一点,前文已经举过一些例子,如《封地买卖法》对次级分封的取消,1535年《用益权法》对受益人用益权性质的转化 (从衡平法权利转化为普通法权利),1873-1875年的《司法法》对普通法诉讼格式的废除,1925年《财产法》对过去众多普通法地产权的取消,等等。其实质是立法者对法官在司法实践中的某些做法不满而通过制定法改变或取缔之,是制定法影响或高于普通法最直接也是最激进的例子。
下面再来看普通法对制定法的影响。
1.普通法通过司法审查取消制定法条款。这是所谓普通法高于制定法的最典型和最激进的例证,但它带有更多宪政含义,因此并不是任何时期、任何英美法国家都具备的。从国别上来说,司法审查在美国最为典型,联邦最高法院不仅可以对政府的行政命令进行司法审查,而且还可以对国会通过的法律进行违宪性审查。从时间上来说,柯克在 17世纪时曾主张过法院具备这样的权力——这也被后人视为了司法审查权的理论和实践之源。但就英国而言,司法审查并未像美国那样发展成为宪政性的制度安排,法院最多只能对政府的行政命令进行审查,而对于议会的立法则因为戴雪所说的议会至上而一直不能予以评价。不过,自 1998年的《欧洲人权公约》进入英国之后,这方面也在发生变化。《公约》授权英国的法院可以审查国内的立法,并宣布某法与公约相悖而弃之不用。〔31〕Baker,见前注〔26〕,页 209-210,98。
2.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大小,决定着普通法对制定法影响的程度。既然制定法在适用过程中必须经过法官的解释,那么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大小,就会对制定法最终的含义产生重要影响。比如普拉科内特的研究就表明,14世纪中期以前,法官对于制定法的型塑作用非常大:他们可以扩大、缩小其含义,或者径直搁置不用,而不必解释说制定法因为违反什么更高位阶的法律而无效。到了 14世纪中期,法官司法时的这种随意态度开始消失,法官们开始严格解释制定法。制定法也不再被认为是宽泛的、法官可以在其间行使广泛裁量权的政策性建议;相反,它们被认为是应当予以精确执行的文本。接下来,在被剥夺裁量权之后,法官们遁入了逻辑之中,人们力图设计出一些规则供解释时遵循:句子的语法结构加上对制定法之性质的一般性考虑。立法和司法的分离达到了这样的地步,以至于法官认为自己所面对的是一个完全外来的文本,他只能通过其语词和文本来了解立法者的原意,也就是所谓的严格解释——这就到了近代的情况。
但伦敦经济学院的荣誉教授迈克尔·赞德 (Michael Zander)在其对近年来法律解释的研究中却发现,自 20世纪以来,英国法官在制定法解释方面的总体趋势是更加自由。这集中体现在以下几方面:法官在解释制定法过程中可以而且需要探寻立法者的本意或目的;法官不仅要落实议会所说(指字面反映出来的意思)而且还要落实其所指(指字面背后的意图);法官对制定法的解释应该反映时代和情势的变迁;欧盟成员的身份致使英国法官有时会采用欧陆法的方法对本国的制定法进行解释;而法官对制定法的解释甚至会被认为是一种立法。〔32〕参见 Michael Zander,The Law-M aking Process,6th editi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 pp.193-208。迪普拉克勋爵 (Lord Diplock)也曾举例说:法官在税法案件中经常会解释并实际上创制法律,因为现实生活中的很多情况都是立法者当时没有预料到的,而有的则是纳税人为了规避立法之规定而事后有针对性地设计出来的。〔33〕参见Lord Diplock,“The Courts as Legislators”,Holdsworth Club Lecture,1965,pp.5-6。转引自Zander,同上注,页 211-212。
当法官可以探寻立法者的原意时,当法官对法律的解释是为了落实议会所指而非其所说时,当法官对制定法的解释可以甚至是应该反映时代和情势的变迁时,司法和立法之间的关系就不再是简单的前者被后者所决定的关系,而是前者会对后者产生深刻的影响。而只要遵循先例的原则存在,后一个法官就会参考甚至是必须遵守前一个法官已对制定法作出的解释——此时制定法本身的重要性已经退居其次,真正重要的是法官对制定法作出的解释。正是通过遵循先例的原则,通过法官对制定法的解释,普通法在实际上强烈地影响甚至是控制了制定法的实际含义。
3.法官个人在解释法律时保守或自由的倾向,也会强烈地影响到制定法的含义。自 14世纪中期以来,普通法法官对于制定法的解释趋于严格,即特别强调对制定法的文义解释而不强调对其背后立法者意图的探寻。我们可以为这种现象找到很多的原因:诸如普拉科内特所提到的立法和司法在此时开始比较明显地分离——在今天分权的宪政体制下,这已成为一种要求对制定法进行严格解释的体制性的理由,否则就可能构成对立法权的“赤裸裸的侵犯”;又如,普通法法官为了排除制定法或立法的影响,也经常通过严格解释的方法将制定法限定在特定的 (比如制定法自身明确规定的)范围之内……但这并不排除某些持自由倾向的法官仍然可以在这样的传统之下对制定法予以较为积极的解释,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人物就是丹宁勋爵。
丹宁勋爵是 20世纪英国伟大的法官之一,他强调法官或司法在面对社会变革时应该秉持更为积极的态度和主动承担更多的责任,主张在法律缺失或不当之时法官应该发挥更多的自由裁量权,以更好地实现社会公正。这种积极主动应对社会变革的态度和传统的英国法官的保守倾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也是他后来从上议院重返上诉法院的原因所在。〔34〕参见刘庸安:《丹宁勋爵和他的法学思想》,载(英)丹宁勋爵:《法律的训诫》,“序言”,杨百揆、刘庸安、丁健译,法律出版社 1999年版。另外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是,相比之下,在面对制定法的解释、判例的推翻和发展等方面,美国的法官要比英国的法官总体上更为自由。这些例子表明,在英美的法律传统之下,法官 (个人)的思想倾向也会强烈地影响到制定法的含义和适用,影响到普通法对制定法的能动性作用。
4.此外,还存在许多促使普通法影响制定法的客观因素。比如,①近代以来的很多制定法都采用了传统的普通法的术语,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 1925年的《财产法》(Law of Property Act)。该法虽然废除了过去纷繁复杂的(普通法上的)封建地产权利,但却保留并大量使用了普通法的术语,这使得该法在解释、适用时必须采用普通法的进路,其受到普通法的影响在所难免。②近年来欧盟法开始大量涌入英国,但它们中的很多却使用了英国人并不熟悉的 (欧陆式的)术语和表述方式,而英国议会在通过国内的制定法落实这些欧盟法时也不假思索地直接采用了其原来的术语而未作任何解释和限定,这虽给英国法官解释这些欧盟的法律造成了困难,却也给他们恢复往日宽泛的自由裁量权、为普通法在新时代新的情势下影响制定法带来了客观上的机遇。〔35〕Beatson,见前注〔3〕,页 292。③制定法中有时所使用的宽泛和模糊的术语也给普通法发挥作用创造了条件,因为它们必然需要普通法法官予以解释和限定,并因此而形成一系列的判例,而判例是普通法影响制定法最直接和明显的方式。阿蒂亚就说过,其宽泛和模糊的语言意味着宪法问题在现代美国相当程度上是判例法问题。〔36〕参见W.M.C.Gummow,Change and Continuity:Statute,Equity and Federalism,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p.63。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前法官奥康纳 (O’Connor)也曾说过,国会希望法院能够通过借助普通法传统来型塑制定法的宽泛命令。〔37〕Gummow,同上注,页 8。④普通法汇集了整个英国法中的许多基础性原则,如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契约自由,未经正当程序任何人不得被剥夺生命、自由和财产,任何人不得从其违法行为中获利,等等。它们分布在各个部门法领域、贯穿于司法过程中,不仅包括实体性的,也包括程序性的,还包括一些基本的理念、共识和做法——如布莱克斯通就曾总结过关于法律解释的十大原则〔38〕Blackstone,1 Comm.87-92.。它们不仅构成了议会立法的前提和基础,而且也是司法过程中法官解释法律时所必须考虑的因素。如此,制定法在被解释之时也必然会受到这些普通法原则的影响。虽然制定法可以改变这些原则,但实际上它们很少这样做。⑤当制定法并无明确规定(即出现所谓的法律真空)之时,法官就不得不动用普通法来填补这样的规则空缺。而制定法无明确规定又分两种情况,一种是客观上尚未制定某方面的规范——这在一个传统上制定法只是起辅助和补充作用的国家是很常见的;另一种是立法者不愿意或很难就某些棘手的问题及时制定出法律——其实法院也不一定愿意处理这些问题,但他们却无法像议会那样回避或搁置之,而是不得不立即处理。后一种情况如,1989年之前英国并无关于对精神病人是否可以予以医学治疗的立法,但法院却必须立即处理就此发生的诉讼。类似的例子还有,1991年上议院决定婚内强奸为犯罪;1993年,上议院规定负责医生无义务为永久性植物人提供治疗,包括人工进食喂养;1991年,上议院承认不当得利原则。无论何种原因导致的规则空缺,法院都必须解决手头的案件,这是由这个机构的性质决定的——它不可能像议会那样,一个法案通不过可以撒手作罢。而普通法本身的优点,如它可以通过判例发展出新的规则,又为它在社会变革中承担积极的角色提供了可能性。如彼特森就认为,普通法的这种活力在法院对行政机关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司法审查时就体现得特别明显。〔39〕Beatson,见前注〔3〕,页 296-297。⑥遵循先例的判例法传统也为普通法影响制定法提供了必然性。一个新的制定法生效之后,必然会有第一个法官对其进行解释、适用,此时的解释和适用可能会采用文义解释、会探寻立法者的意图;但这之后会就此制定法 (准确来说是其中的某一条文)形成一个判例,后来者在解释该条文之时就不一定再重复原来的解释过程,而很可能是参照这第一个判例。如此,围绕这个条文就会形成越来越多的判例,而我们前面提到过,只要遵循先例的原则还在起作用,只要法律和法律的适用之间的差别还存在,制定法就必然无法逃脱普通法的影响。彼特森在谈到普通法对制定法的影响时说,普通法的技艺还将延续,判例还会堆积,而判例堆积越多,制定法就越失败。〔40〕Beatson,见前注〔3〕,页 302。
四、结论:未来属于谁?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大致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1.从过去到现在,普通法和制定法之间从来都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传统的油水关系说关于二者彼此分立、相互独立的说法从来都不是事实。
2.关于普通法高于制定法或制定法高于普通法的讨论没有太大意义,较为中肯的说法可能是,在某一历史时期、某种场合或某个具体的案件中,普通法或制定法占据了一定的优势。但这样的讨论对于理解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并无太多助益。
3.综合以上两点,我们与其将普通法和制定法的关系定位为油和水,还不如视之为水与乳的关系,以体现二者相互交融、难以分离、难分高下的关系。此外,我们还必须从司法和立法的对立、从司法过程和法律解释的角度去理解这二者间的关系。
4.从制定法的角度来看,历史上,它在整个英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的确无法和在大陆法系中相比:它不是整个社会或某个领域的基础性、基本性规范,而只是普通法的补充或修正;很多时候它只是例外,而不是常规;它不是某个领域法律发展的起点,而只是对该领域法律发展的调整……但今天,制定法的状况已大大发生了变化:不仅数量、篇幅有大幅增长,而且在社会问题、责任限定、劳动法、公司法、家事法、国际私法等领域意义重大,甚至在侵权、合同这些普通法的传统领域,其影响也在不断提升。况且,欧盟法和国际法的涌入也都是以制定法的形式出现,这都增大了制定法在英国法律生活中的影响。因此,对制定法来说,它在英国的法律体系中是一个地位不断上升、作用和影响不断增大的趋势,是一种朝阳式的法律渊源:过去它曾遭到普通法法官的“歧视”,后随着其地位的不断抬升而被普通法法律家策略性地“隔离”,但今天它早已是普通法所必须面对的对手,所以它的未来是光明的,未来属于制定法!
5.对普通法而言,我认为它经历了或正经历着一个和上述制定法相反的下降趋势。就管辖范围而言,如上所述,纯粹的普通法核心地带正在不断萎缩,其传统的领域正在不断遭到制定法的侵蚀。更为可怕的是,就法律适用而言,在普通法可以解决的问题中,英国法官也开始直接诉诸欧洲人权公约——这甚至是要摧毁作为整个普通法基础的判例制度!〔41〕Beatson,见前注〔3〕,页 293-294。彼特森在其就职演说中从国内制定法的扩张到国外欧盟法、国际法的涌入,描述了今天英国普通法所面临的严峻形势,甚至并非危言耸听地指出,背负普通法传统的英国有可能会沦为下一个路易斯安那、魁北克,而成为制定法汪洋中的普通法孤岛,并忧心忡忡地提出“普通法还有未来吗”的问题。但在我看来,普通法面临制定法 (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挤压并非今天才有的事,而是古已有之。制定法并不是今天才有,而是一直就存在于英国,外来规则 (如罗马法和教会法)的压力在16、17世纪也许不亚于今天,因为它还结合了国王的特权和专制。但普通法还是挺了过来,这其中虽然有一些偶然因素,如议会对国王的胜利使得普通法得以渡过难关,但它也从另一个侧面揭示了普通法所面临的真正威胁不是国内外的制定法,而是与普通法法治传统相违背的专制和特权,而这并不仅仅是普通法而且是任何法律都面临的最大的敌人。至于制定法、罗马法、教会法这些敌人,梅特兰强调了普通法的技术性因素的功效,如律师公会、年鉴等。〔42〕Maitland,见前注〔14〕,页 27-28。同样,面对今天汹涌澎湃的制定法大潮,我对普通法的前景并没有那么悲观。其原因在于,和梅特兰类似,我也强调的是普通法的技术性特点。在我看来,普通法是一种开放性的法律体系,它之所以能够历千年而不衰,而且扩及全球,就是因为它能够通过判例的机制将其他法律渊源的精华吸收到自身中来,从而使自己实现吐故纳新、与时俱进。而我们知道,在英国,制定法是必须经过普通法法官的解释才能适用,因此,只要立法和司法之间的差别还存在(而且今天还有扩大的迹象,2009年 10月 1日英国最高法院摆脱上议院而成立就是一例),只要法律和法律的适用之间还有不同,只要遵循先例的做法或原则还在延续,普通法就会存在下去。因此,普通法不仅不是一个夕阳式的法律体系,而且将永远是那艘充满活力的、从过去驶到今天并将继续驶向未来的“阿戈尔英雄的战舰”(黑尔语)!所不同的也许只是,它将以一种新的形式来和制定法保持关系。而维系它如此生命和活力的,正是那些作为法律职业共同体成员的、历代和今天的普通法法律家,是它的高度的技术性和专业性,是它永保开放的宽阔的胸怀!在这个意义上我说,未来不仅属于制定法,同样也属于普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