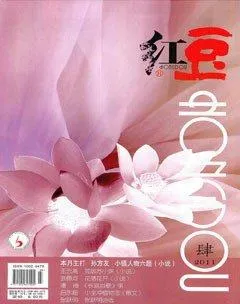小金冲植物志
2011-01-01吕永超
红豆 2011年4期
清涩皂荚
皂荚学名叫皂角树,是一种具有特殊诱惑力的存在。它是一个向往,—个可以停顿或者终结的场所。不论在任何方式的路上,我经常翘首守望肥皂荚。
皂荚是小金冲代表性的植物之一,它品字型站立在老屋旁边的空地上,互生的羽状复叶,摇曳着白色细花。成群的蜜蜂嗡嗡嘤嘤,逐渐肥硕的身子摇动了树枝。我搭上梯子,爬在肥皂荚的树杈上,身子在皂荚和叶子之间穿梭——青涩的皂荚果不断打中我的额头。
在乡村,8岁那年起,我就没有了偷懒的理由。到11岁,我喜欢—个人出门和劳作,即便是上学,也远远躲开那些穿红戴绿的女孩子一我们有过亲密的时光,在肥皂荚下,不设防的打闹,无忧无虑的欢笑,似乎在那一瞬间,突然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慌乱和羞怯,是远远地躲开。
劳作之余,我喜欢躺在竹床上,仰望弯弯的青涩皂果,想象它是藏在地里的花生、它是挂在夜空的一弯月亮。它还是,它还是拢住二妞头发的镯子。
二妞是小金冲最爱干净的女娃。前些天,我割草的时候,看见了放牛的她,胸脯竟然鼓胀起来了,我一阵心跳。急忙收回的目光,被她在无意中捉住,我的脸像番茄一样红。
很多次,光头佬私下对我说,二妞背地里说我不正经。我没有反驳,顺手拿棍子钩下一枚皂荚叶子,像羊一样嚼了几口,然后吐在地上。我爷爷不知道从哪儿听说了这件事情,十分严肃地教育了我。我很伤心,看一下就不正经了吗?我觉得二妞滥用了不正经这个短语。我应该找二妞解释一下。光头佬承诺搓和此事。
那个黄昏,光头佬带来了二妞等一帮小伙伴。他向我眨了眨眼睛。我心知肚明。光头佬故意说是来帮助二妞采摘皂角的,二妞说用皂角洗澡真好,能散发一种淡淡的肥皂香味。他脱下汗衫,噌噌噌,赤膊而上。其它伙伴都仰望着光头佬,二妞靠近我的竹床边。我闻到了她身上淡淡的肥皂味,就气馁了,整个腹腔空空的,勇气尽失。我第一次感到自己的虚弱。
光头佬肯定看到了我的表情,哧溜一声,从上面滑下来。他挠着青头皮,满脸疑惑地说:你爷爷在上面种了刺丁吧?我上不去了。
二妞横了我一眼,扭头就走。伙伴跟着都走了。我一下子瘫坐在竹床上,脸皮发烧,好像连骨头都升高了温度。
事实上,肥皂荚的树干上都长有这种坚硬的刺丁,都被我父亲折断了。光头佬是给我台阶下,才急中生智编了这个理由。
我爷爷信以为真,就准备好一排竹竿,留给伙伴们敲打皂荚果子。光头佬又把他们叫来。没有看到二妞,我陡然提升自己的地位,神气地给他们每人发一根竹竿,像将军给士兵发枪,大声吆喝:打皂果啊。竹竿晃动,乱打一通,地上掉下许多皂角。突然,二妞不知从什么地方钻进来,二话不说,蹲在地上捡皂角,抱都抱不下。我退到身后。爷爷拿出竹篮,递给二妞。爷爷说,你喜欢都拿去吧,再也不要说他不正经了。爷爷用眼睛看着我,二妞也在看我,露口一笑,一嘴白牙。
光头佬从二妞那儿抢来几只皂角,引领我们跳进池塘里,青蛙或者白鱼一样翻动着身体。然后,彼此用皂角搓洗着对方的前胸后背。学着二妞的样子,抬起小臂嗅了嗅,忘情地说,真香!二妞站在远处,肯定是生气了,抓起石头和土块,甩着膀子使劲朝我们丢——她的力气小了,石头还没有飞出一丈远,就坠落在地上。
二妞确实再也没有说我不正经。我爷爷心痛皂荚,再不允许我的伙伴们敲打皂角。可是,二妞还要。爷爷答应了,说二妞诚实,在晚饭后满足她的愿望。爷爷胃不好,吃饭很慢。光头佬、二妞他们,跟我捉了半天迷藏等爷爷。爷爷还在吃。我不敢催爷爷,躺在竹床E生闷气。我听见光头佬气喘吁吁的声音,他们一定看到我假寐了。—会儿,他们风风火火地跑走了。我心里想:等我爷爷开打皂角的时候,就去叫他们。
我没能去叫他们,睡着了。当我睁开眼睛,发现自己不是躺在皂荚下的竹床上,而是躺在家中木板床上,只有昏黄的灯光和两根青皂角陪伴着我。我翻身而起,探身望窗外,一片漆黑。我知道自己一不小心睡着了,不是有意的,而是一不小心,就与美好的东西失之交臂。在昏黄的灯光下,看着皂角发着清幽的光,觉得是那么不真实,如梦如幻。而实际上如梦如幻的却是真真确确,我的真实就是我睡着了,我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没有睡着,我睁开眼睛跑出去找到光头佬他们,得意地告诉他们:我爷爷在打皂角呢,你们上当了……
那一个晚上,我只轻轻地闭上眼睛,等我睁开眼睛时,一切都改变了。几年后,我是一个毛头小伙子的时候,在皂荚树下,也同样感觉只是闭眼的刹那,爷爷已经到了另外一个世界,光头佬初中毕业跟着他舅舅学木匠手艺,二妞学跟她姐姐学裁缝,还有下田种地的、穿上绿军装的……而继续读高中的我,剃光头发,呆坐在皂荚树下,苦等脑门上脓包成熟。一旦脓包露出黄嘴,就用皂角刺挑破。母亲心一横,四指卡住脓包,用力压挤,脓血倾出,而后敷上锤烂的嫩皂角刺,不几天,我青皮脑袋又光溜溜了。
多少年后的某一天,我回老家和光头佬、二妞相遇在皂荚下。光头佬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快要当外公了;二妞胖了,身体像皂荚腰身一般粗大,但穿着依然讲究。我们共同回望过去的岁月,仿佛就在睁眼闭眼之间。在我们不知不觉时,皂荚已经长高了二、三米,人世间的悲喜苦乐也一遍遍地上演、又一回回地落幕。我们没有机会去观看,也没有机会去亲历。当我们忽然想起再一次打下皂角时,竹竿已经挨不上边了,皂荚往上长高了好几寸,这时恰恰是我们怎么够也够不到的距离。这距离,就让彼此的世界成为两个不相交的圆。
光头佬和二妞都说,那个晚上,我们看到你躺在竹床上,我们我以为你真的睡着了。他们记忆中的那一刻都是:我睡着了。
我说,爷爷打皂荚的时候,我真的睡着了。爷爷在深夜咳嗽后,如果想起我,他一定以为我在熟睡,而那时我却醒了。我翻身而起,屋里灯光昏黄,皂荚闪着青光,外面一片漆黑。
我和光头佬、二妞彼此对望,似乎是在恍惚间我们都从不谙世事的小孩,长成中年人。许多次,我父亲都想砍倒皂荚树,给家里添上一把椅子,一张桌子,或者别的东西,可又止住了这个念头,是我的童年提醒了父亲。现如今,老家人又要求我砍倒皂荚树,我坚决地说不,因为皂荚树下还有我父亲、我爷爷的童年啊!
光头佬很赞赏我的举动,向手掌吐了几口唾沫,用力击打着皂荚树干,嗵嗵几声闷响,接下来是皂荚叶子震动后沙沙的声音。刚抬头,正好看见一片半枯的叶子从我头顶上悠悠地飘落在地上。我伸手捡起那片叶子,把它托在掌心上仔细端详:一片很普通的肥皂荚叶子,长椭圆型的,一半发黄、一半暗红,中间—个小洞。在我看来,这片肥皂荚叶子充满着禅机,的确和我有缘。人生不就是这样么:平凡普通,实实在在,而且最终百川归海,叶落归根。
我举起叶片透过上面的小洞看他们。光头佬大声地问:这是当年的皂荚吗?
二妞说,这就是生于小金冲、长于小金冲,最后又把生命奉还于这片土地的皂荚……
鱼腥草
这是小金冲最劣等的一块田地,靠近水库坝底,终年潮湿,种什么庄稼都歉收。但是,正是这块田地,吕三爹拄着锄头把子,眼里喷火,与自己嫡亲侄子狗蛋对骂。吕三爹把锄头把子敲得当当响,他的话也响当当,这地老子种了四、五年了,现在说给你就给你?除非你有胆子把俺卵子给骟了!
—位长辈用自己的隐私与下辈人赌咒,在小金冲是“封顶”的语言。自然,村里的调解、左邻右舍的好话,都无济于事。
事情很简单。前几年,狗蛋和小金冲其他年轻人一样,背着行囊,远赴东莞、广州、北京打工,把这块地无偿地送给牛三爹耕种,还签了一份为期八年的协议。现如今,狗蛋反悔了,想收回这块地。吕三爹死活不同意,他的意思是,无论如何也得把这块地种到第八个年头,协议就是这么写的。狗蛋寸步不让,说愿意承担全部违约责任,每年还额外补助三百元零花钱。按说,这样的条件对得起良心,但是吕三爹就是牛,固执溢于言表。说着说着,就蹲下来,摸着这块地上种的鱼腥草,潸然泪下。吕三爹说,他这一辈子只为一个人流泪,那是他过世的母亲。再就是这次了。他抠起—把泥土,紧握松开,松开又紧握,仿佛抓着老母亲的双手。
吕三爹这个举动,给我以强烈的震撼。我突然明白了跟我在城里居住了十年的老父老母,为什么毅然决然地返回老家,坚守着属于自己的两亩田地了。他春插稻禾、冬播小麦,周而复始,没有半点怨言。父母都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了,不缺钱花、不少衣穿,就怕天天见不到土地。在城市里,我曾托人寻找了一块边坡,慰藉他的心灵。父亲摇头叹气说,这不是俺的地。俺地的籍贯是小金冲;俺地的田坎上、疏林下长着不起眼的鱼腥草;俺的地是俺的本钱,是俺的手艺,知俺冷热。实际上,吕三爹如此不舍这块地,其想法应该和我父母的完全一致。这两年,打工返乡、重新耕田种地的人大有人在,狗蛋就是其中—个。现在没有“三提五统”,一亩地一年种两季,“干净钞票”大约是以前的三四倍数,如果种草莓、葡萄等经济作物,估计倍数过两位数。过去抛荒的田地现如今成为“金元宝”,村支书和村长笑得合不拢嘴——古老的土地上活跃的身影不再是上了年纪的老农、拖儿带女的婆姨,更有胸厚肩宽、走起路来踩得土路嗵嗵响的小伙,秀发飘拂、神态里带着一种乡里的蛮野和稚气的姑娘。
我居住的小区前面有一片上世纪五十年代建设的五层居民楼,拆旧房时,来了许多农民工。在毫无保险的情况下,有人站在楼上摔着大铁锤破碎预制板,有人挥舞洋镐钻倒红砖墙。瘦削的背影在坍塌声、尘烟里起伏。如此超负荷的劳动能换来承包头及时足额发放工资,再苦再累心也甜。但是,承包头用种种理由拖欠他们的血汗钱。我亲眼所见,临近中秋,承包头蒸发了。拼死拼活干了几个月,一个铜板都拿不到,他们显得多么的无助。那段时间,他们在工地上或蹲或站,一脸茫然,好像视觉、听觉和语言都是多余的,任秋风裹着枯叶在头顶上打旋。幸好媒体出面干预,有关部门趁热打铁,讨回了工钱。电视台为此事播发了一则新闻,记者还特地给观众—个特写:年轻的农民工点着工钱,一脸的微笑。看到这儿,我一点也高兴不起来,总觉得民工的笑容与有的述职报告上文字极其相仿。
现在,回到小金冲种地那些年轻人也是从前的民工,他们中就有人有类似的经历。只是年轻^爱面子,不愿提起那些失望和伤感的往事。在城里,农民工永远是弱势群体,只有回到乡村,他们才是真正的“爷们”,脚下的那块土地为他们支撑起挺直的脊梁。
吕三爹握着泥土直挺挺地站着,狗蛋也是。有人递上香烟,想缓和一下气氛。吕三爹没抽,夹在耳跟上,或许是说话太多,他的嘴唇干裂;狗蛋叼起香烟,从背后裤袋里抽出—个矿泉水瓶子,里面不是白水。他扭开瓶盖,说,三爹,你老喝一口?吕三爹从鼻孔里哼了一声,接过去就咕嘟起来。狗蛋把香烟弹在地上,又说,三爹,这是鱼腥草水,降火。围观的人一阵哄笑。吕三爹似乎明白了什么,呸地一声,满口水扇面喷出,大声说,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狗蛋抹了抹脸上水沫,说三爹,莫怪侄儿不客气了,那咱们在乡法庭上见。
吕三爹把矿泉水瓶子扔向八丈远,冲着狗蛋背影怒骂,你这个不孝的狗东西,你去告吧!老子就是不给你地,看法官把老子吃了?
看到村长也跟着狗蛋走了,吕三爹就不骂了,再次蹲了下来,不再说话。貌似平静的外表下,还是不能掩饰他内心的慌乱:他非常明显地用力一口一口咽下口水,好像他的喉咙全部被扼住了。
秋天的太阳不冷不热地朗照着。吕三爹种植的鱼腥草,温暖地匍匐在狗蛋那块地上,像红苕一样的叶子没有叶绒,不沾污一粒尘垢;心形的叶边没有芒刺,不染指外来之物。地下茎横走,有节。清廉的叶子沐浴和风雨露,吸纳天地之气,酿造成养分输送给自己的母体。圆融的主茎直立向上,接受八面来风。烈日下不萎黄,晨露里不浅褪。白色小花,漂亮,纯净,孤寂。老^挪动身子,慢慢地、轻轻地抚摸着鱼腥草,抚摸着土地……
狗蛋这块地吕三爹摸爬滚打两年,才摸清它的脾性,才有这碧绿的鱼腥草茁壮成长。—个农民对土地的依恋,就是在朝夕相处中产生的。这种感情一旦形成,就直接与农民的血液融为—体。土地成为他们的依靠,他们的根,他们的温暖之源,须臾离不得终身不背弃;土地也因为他们温暖而富有思想和灵性,总会铺出阳光大道开满鲜花予以回报。正是因为这种朴素的关系,要吕三爹离开这块土地,无异于抽取他的精血!当吕三爹的双脚踏上心爱的土地时候,浊气跑了出来,闷气也消散了。在一呼一吸之间,那些甜韵清新的元素徐徐注人心灵,人就踏实温暖了。鱼腥草在他眼中,并没有实在的意义,只是一个符号。但是通过它,使外人得以温暖——不是计算,而是温暖。在充满惊喜的温暖中,获得了新的踏实、新的温暖。
在乡村,其实许多纠纷,都起源于温暖的缺失。缺失温暖,就让人觉得像是母亲永远地离开自己。吕三爹曾因为母亲去了另一个世界而老泪纵横;土地也是他的母亲啊,狗蛋让他失去温暖,他当然毫无顾忌地再次掩面而泣。
这时,村长的声音从老远地方传来:三叔呀,你老别发愁了。好事好事。吕三爹吃力站了起来,还趔趄一下。这些村长都看在眼里,他知道,狗蛋要地,已使老人心力交瘁。他喘着粗气,关心地问,三叔,你没事吧?摸了摸老人的手,冰凉冰凉。村长又说,我不给你绕弯子了。狗蛋的工作我做通了,这地你老继续种。吕三爹浑浊的眼里突然放出逼人的光亮,你、你说的是人话?
村长肯定地说,是人话!我把你种鱼腥草的经历给狗蛋讲了,狗蛋十分感动。他打算把这片地采取股份的形式并拢过来,搞产业化经营。你呀,不但种这块地,还要种比这大得多的地。狗蛋和村支书商量细节问题,暂时来不了。他说,晚上请您老喝酒,陪不是……
村长后面的话吕三爹没听进去,他又蹲下身,把手尽量放慢、放轻去抚摸鱼腥草、抚摸土地,温暖火一样地从心底往上升腾……
八角刺
小金冲有处果园,就在村侧面的坡地上。季节一到,果园里桃红李白枣青,满园飘香,馋得我们直流口水。绕开园门,试图进去,总被一圈一人多高的八角刺篱笆挡在园外。
这儿的八角刺伴随果园长了上百年,粗细不一的杆儿撑着的叶片,终年青碧。沿儿上挺着刺,坚硬而锋利。还有或青或红的豆状果子,隐现于枝枝桠桠之间,常疑为躲闪着的眼睛朝外窥看。用手轻掰八角刺的时候,它微笑观望,相安无事;要想把重叠叶片的分开,趟出一条缝,须臾间它就强烈反弹,不动声色的叶片立即伸出几根硬刺,尖锐地戳破肌肤,惟恐避之不及。这就都是八角刺,挤压、针刺、忽高忽低、左冲右突……貌似平静的外表下隐藏着不平静,被世人看见,被嘻嘻哈哈走动的灵魂领略。
八角刺其实并不丑陋。对着它,我时常想象一幅这样的场景—一乐队指挥头扎碧绿八角巾,其舞台位置背向观众的身影在一种内敛的激情中曲折成一个音符,顶端扩大并具有3个大而尖硬刺齿,是一小处五线谱标示的调性符号。二胡——杆茎的二胡在它叶面底下。贫瘠土地深处根系的幽魂,宛如乐队中首席琵琶,低俯下身演奏出的乐曲音色的柔韧性,坚忍不拔。那是否是中国风格的民乐协奏曲《八角刺》?是《八角刺》开始部分的一段华彩?
可惜,民乐典章中没有八角刺,但丝毫不影响我用这样的形象来比喻八角刺。
八角刺用它的沉稳、坚韧,搭乘时光的流速,在阳光、雨水、草丛的山卯、地头、坡边去完成属于自己的四季。
记忆中有两件事与八角刺有关。从撕开的伤口中渗漏出的水分看,它可以酿酒,可以醉人,可以醒世,可以洗心。
小金冲吕姓高祖在靠近胡姓的一山岗上安睡了几百年。那山岗原来就是吕姓自留山,高祖完成了他手头上所有的事情,就与八角刺为伴,把这里作为恒久的居所。山岗因此更显美丽而温暖。每年清明节,吕姓子子孙孙,都要前往山岗,站在八角刺边沿看血红的夕阳,让一天最后的辉煌从身上慢慢滑落。
然而,胡姓一大户相中了高祖的安居之所。曲里拐弯地胡诌他家儿子被坟沟的八角刺工伤,扬言吕姓后人要么迁移祖坟,要么滚八角刺。
这山冈是小金冲人根脉所在,是小金冲吕姓子孙的精神家园。生活在清朝中期的长辈们扬起粗壮的胳膊手臂,响亮地回答:头可断,血可流,高祖坟墓不可移!但是,吕姓后人在几十年以前已经迁徙到小金冲,这山岗已经是划归胡姓管辖。恶龙难缠地头蛇。为了避免械斗,我的长辈作出了残酷选择:滚八角刺!
那是—个烈日当空的正午。在祖坟下的山坳平地上,我的长辈赤裸裸不着一线,被捆束在八角刺里面,眼睛都不眨一下地倒地打滚,一圈,两圈……胡姓头人则坐在一旁,冷笑,吸着一根水烟观看。围观的妇人吓得浑身筛糠,有的还哭出声。面对撕裂痂壳般锦心地疼痛,他毅然决然地滚了八圈,维护了尊严。他一直盯视着胡姓头人,森严的目光如八角刺,锥着胡姓头人。胡姓头人骇怕之极的声音是没有声音,张着大嘴,支棱着耳朵,跌跌撞撞地退却了。我可敬的长辈浑身鲜血淋漓,扎满了尖利的八角刺。乡人抬他回家,用银针一根根从他身E剜刺,整整剜了一夜……
我的高祖依然睡在那儿,陪伴他的八角刺不管是整齐的,还是散乱的,每一根枝条都尽可能地向上生长,姿势完全不同。即便是生命终止了,它的状态却不会终止,枝干屹立不倒,立体的死亡凝固了一段时光,展示着曾经发生的壮烈事情,令人震撼。
新世纪的月光像水一样泼洒下来,照耀着秋后的小金冲果园。桃李下架上市后,果园变成了公园。园门敞开,这里有永远的约会,有躲在树荫下的拥抱,有藏在篱笆背后的接吻。恰在这时,八角刺的果实也成熟了,它鲜红欲滴,泛着圣洁的光辉,袅散着香甜的气息,诱惑着怀春男女伸手采摘。爱,常让人忘记八角刺的厉害。伸出的手,总被锐利的八角刺或轻或重地啄一下,露出针眼大小的红点。接下来是最精彩的一幕:扎伤的手被抓了过去,含在口中轻轻吮吸。两腮鼓胀之间,情更浓意更切了。
哪个女娃不怀春,哪个后生不钟情?同是姓吕的一男一女,撇开父母视线,也在这里演绎山盟海誓。顿时,小金冲炸开了锅。按照族规,这种行为要滚八角刺。但是,女娃和后生性情刚烈,非他不嫁,非她不娶。女娃被父母反锁在房间,以泪洗面;后生被父母用八角刺抽打小腿之后,不是去抚摸灼痛的伤痕,而是昂起倔强的头,大声地说:我们恋爱,上不违法下不失礼,何错之有?
族中长者在鞋帮上磕下旱烟枪中烟屎,没有任何表情地答:错就错在你不认识过错,不滚八角刺你不知道什么叫族规!
这是无声的命令。祠堂大殿里铺上了八角刺,只等祭拜祖宗仪式结束,后生就要被人推倒在八角刺上,接受最严厉的惩罚。
女娃的父亲生性胆小,不敢看那场景,竟然在生产队一间破旧的碾子房里,拿着《圣经》唱道:“不计恶人的计谋,不站罪人的道路……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
女娃母亲不信那一套,从祠堂闪身溜回家,故意打开房门的铁锁。让女娃逃了出去。女娃一路跌跌撞撞,去了乡政府。女娃头发蓬乱,上面落满了土灰。秋天的影子一点也看不到,女娃的苹果脸都被土灰蒙盖,泪痕清晰可见。
法律战胜了族规,维护了公平正义。更可喜的是,因为这件事情,板结的族规有了松动,许多条款与时俱进……
这对有情人终成眷属。在婚后的第三天,他俩再去了趟小金冲果园,在当初彼此献出初吻的八角刺篱笆下,寻找一株躯干粗壮的八角刺,把两人的名字刻上去。
如今,几年过去了,他们的名字一直和八角刺一起生长,笔画之间已经结成了痂一样黑色。巧的是,后生已经是小金冲果园的主人。我问他,是否因为哪段经历,才承包小金冲果园?他点头称是,说八角刺在他心中,永远地有了意义。在八角刺的身体里,刻着的不仅仅是名字了。
抬头是稗子
我一直在回忆,是什么时候,父亲教我识别稗子的?
应该是在一个有梦的早晨。我在宽大的竹床上翻转着身子,不停地追着梦中提花篓的月亮姑姑,乐此不疲。突然,被父亲一声怒吼震醒了。我不知道犯了什么错,懵懵懂懂地下了床。父亲不满我的嘀咕,提溜着我的耳朵,一路揪到田埂上。这时候,我才明白,因贪睡,把昨天晚饭时与父亲达成薅秧识稗的承诺忘得一干二净。我揉搓着耳朵,在把委屈迁怒到小黑狗身上。土块过去,小黑狗汪汪几声跑远了。
我的老家小金冲,地处大别山余脉南麓,长江中游末段的北岸。千万年来,长江带冲积,构成了小金冲一半是丘陵一半是平原,水田里的稻谷油菜、山地里小麦高梁,养育了明朝万历年间从江西瑞昌迁来的吕姓人家。这里植物种类繁多,却没有哪一种像稗子这般受到小金冲大人的重视。农家孩子认识稗子是一门成长的必修课。如果连稗子都不知道,会被众人耻笑为“没熟透的苕”。
我就是在阳光熹微的早晨,被父亲拉到水田了开始认识稗子的。晨风徐徐,稻禾青碧。这个季节的稻禾与稗子,—样的享受着阳光和土地的滋润,一样的绿色。—个八、九岁的孩子,是很难一下子把它们分辨清楚的。我又一次把稻禾和稗子混淆了,拔出了稻秧留下了稗苗,屁股叠印了严厉父亲的严厉巴掌。我埋首稻禾中间,忍泣不止。
很长—段时间,我十分憎恨稗子。稗子让我挨打小腿上留下稗茎一般粗细的枝条印痕,稗子使我亲娘在大热天中暑脸成稗叶颜色……我见到被大人们摔到田埂上的稗子,连忙用石块把根砸烂,用瓦砾将茎斩断。如果适逢口袋有火柴,我一定会支起干草枯枝,把它葬身火海。
在小金冲,有一句几乎妇孺皆知的俗语:抬头是稗子,低头是稻谷。它既是识别稻稗的“方法论”,亦为蕴涵人生意味的辩证法。每年四月或九月,在稻子抽穗扬花时,农民又要下田拔稗子。此时节,稗子是好找的,它扬花灌浆比稻子早,又总是比稻子高出一头。老练的农民站在田埂上瞅田。是瞅,不是望,不是看,更不是瞭,是一目在旁,身边有禾,稗抢稻风头,心里上火,自然,稗子多半难逃上岸枯死的命运。没有枯死的,它就在田坎或旱地上,葱郁地生长,直至结出饱满晶莹的小稗子。当然,稻田中也有许多漏网的稗子,它们在隐与露之间,恰当地掌握了平衡点,巧妙地藏在稻穗之间,随同稻子,从碧青走向金黄,从娇柔走向成熟。在收割稻子的时候,我们也收割了稗子。即便此时农民把它清理出去,但稗子也很骄傲,毕竟它顺利完成了延续稗子种族的任务。
因此,多少年来,老人们坐在老樟树编制的树荫下,向孩子们讲述着稻稗“低头抬头”的辨证关系——人啊,要想抬头,首先要懂得低头。越成熟、越饱满的稻穗,头就垂得越低。而那些空空如也的稗子,却—个个很招摇地把头抬得老高,露出看似深沉,实则肤浅的目光。要知道,虚心竹有低头叶,傲骨梅无仰面花。说完,老人们总是得意地摩挲着山羊胡子,缺着牙朝我们笑。
我把听来的故事复述给父亲听。父亲抽完一袋烟,什么也没有说,拿来锄头。我以为父亲要去锄地,也吵着要去。父亲把锄头递了过来。我看见光滑的锄头杆上,有一些浅浅的裂纹,里面嵌满了黑色的汗垢。父亲示意我闻闻。我闻了,都是汗味——父亲的,母亲的,可能还有爷爷的,奶奶的。父亲反问,咋就没有你的稗子?黑色脸上的皱纹拧得紧紧的,像螺丝,似乎嵌入骨头中了。我在父亲的眼里是“稗子”,神情黯然,快乐灰飞烟灭,消失殆尽。
母亲亲呢地抚摸我的头颅,用眼睛横了父亲。说,父亲不是反对你听爷爷讲故事,关于稗子,我那会儿都听说了。你爷爷还不是骂你父亲是稗子?可是他是稗子吗?他要是稗子呀,俺才不嫁给他了。你父亲干什么事情都有自己的主见,自然,他希望自己的儿子别人云亦云,即便是对的,那也是抄剩饭。
少不经事,许多想法较为冲动。一冲而动,隐秘的欲望突然膨胀起来,立即左右人们的意识和行为,所以我“复印”着古老的故事,痛恨稗子。当我的胡子蓬勃得不可救药必须每天动用剃须刀的时候,我照样清除稗子,但是我佩服稗子是一种有着相当生存智慧的植物。
谁也不否定稻稗“低头抬头”蕴藏道理的正确性。但我更惊叹稗子的隐、露智慧。什么是稗子?稗从禾卑,说白了就是谷中之卑贱者。卑贱者稗子与高贵者稻谷,在争夺空间战的时候,从来就没有屈服,哪怕有人类帮忙,它们还能倔强地生存下来,一年又一年。这是一种异己的力量,根本原因并不在于异己的它者稻子,而在于它自己,自己就是它者。在农耕文明里,稻谷永远是高贵者,“根红苗正”;在稻谷的眼里,稗子,你算哪根苗?但是,稗子以自己的倒下,衬托了稻子的金贵;而稻子的倒下,扶起了人类的站起。这是一种死亡与新生的转换,数千年来不可或缺。所以稻子才叫稻子,稗子才叫稗子,一叫几千年。
我们的确要感谢稗子的存在。没有稗子很难说稻文化如此动人,念念不忘;或者说,正因为有稗子,稻文化无所恃,所以无所失;无所怙,所以无所瞑。盈虚相济,善建不拔,令人仰视。
想到这里,就把“抬头是稗子”作为“小金冲植物志”的开篇写了出来,没有卑怯,面目安详。《本草纲目》载:
稗子
【气味】辛甘苦微寒无毒
【主治】益气宜睥金疮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