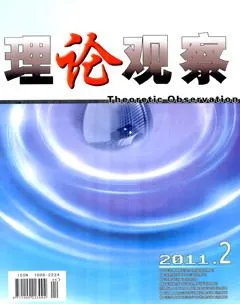政府规制失灵的激励机制
2011-01-01刘娟
理论观察 2011年2期
[摘要]随着现实问题的日益突出,政府规制已然成为学术界讨论的热点问题。基于政府规制理论框架,从信息收集、规制立法和行政裁决三个环节,全面审视郭京毅案中政府规制扭曲全过程,并在此基础上,探析政府规制失灵的内外部双重激励机制。
[关键词]郭京毅案;政府规制失灵;激励机制
[中图分类号]D63[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1)02 — 0025 — 02
一、引言
2010年5月21日,历时两年之久的郭京毅案终于落下帷幕。案件涉及国家商务部外资司、条法司,国家工商总局外商投资企业注册局和外汇管理局管理检查司、综合司;郭京毅、邓湛、刘伟等多位高官落马;河北廊坊新奥燃气集团、首创集团、国美电器等多家大型上市公司,北京思峰律师事务所、北京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涉及行贿。本文基于政府规制理论,审视郭京毅案所涉及规制政策的形成、执行及其调整全过程。
二、扭曲的政府规制过程
(一)政府规制含义及其过程
孙亚忠学者对政府规制做出以下定义,即“政府规制一般是政府依据一定的规则对微观经济主体的活动进行限制和规范的行为。”
政府规制涵盖了规制政策的形成、执行和调整全过程,其信息收集、法规制定和行政裁决三大阶段都不可避免的触及不同利益集团及其相互关系。
(二)郭京毅案中的政府规制扭曲
信息收集是政府规制行为的第一阶段。其首要任务即是向公众提供消费品及产业技术等方面的信息,尽量减轻信息不对称的程度,并且,相关机构应该根据收集到的信息了解市场和公意,以此确定规制的领域、方式及程度。商务部条法司的郭京毅几乎参与和主管了20多年来的外资法律法规的起草和修订。然而,在立法前的信息收集阶段,并未将相关企业信息公诸于众,只是立法官僚精英的内部商议。这一方面导致原本就处于信息弱势的公众更是无力行使其应有的监督权;另一方面,导致立法的相关人员在利益的驱动下为方便创租而进行片面的选择性的收集信息。
规制立法是政府规制行为的第二阶段,也是最为关键的阶段。规制立法将确定政府规制对象、范围、方式、程度等,因此其制定过程将很大程度决定规制立法能否反映社会公共利益。信息公开对于该阶段更是意义深远。美国建立了严格的规制立法程序,如对建议法规的听证、法规的发布、评价及修正等;我国的相关法律主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等。但从其具体规定中可以看出,我国对规制立法程序的规定较为宽泛,仅严格规定了立项、起草、审查、决定、公布、解释六个大体程序,对每个环节的细节规定较为模糊。如《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第十二条规定“起草行政法规,应当深入调查研究,总结实践经验,广泛听取有关机关、组织和公民的意见。听取意见可以采取召开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多种形式。”但对于“深入”“广泛”的界定模糊,这必然导致其流于形式。大量事实表明,政府规制立法与公众利益的错位是规制失灵的主要源头,郭京毅案正是其典型例证。郭京毅在参与起草《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暂行规定》《关于外商投资举办投资性公司的暂行规定》等法规及其补充修改时,有意对部分规定模糊化,表面上看是对并购等行为的进一步规范,实质上是赋予相关部门更大的审批权,为条法司解释法律开辟更大发挥空间,为企业寻租留下空间,是一种创租行为。
行政裁决是政府规制行为的最后一个阶段。由于规制机构掌握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因此行政裁决也是最可能直接产生政府规制失灵的阶段,这就更需要信息的公开与多方的监督。从我国商务部外商投资企业审批流程可以看出,条法司和外资司掌握了相当大的自由裁量权,并且所有相关信息仅在企业、条法司和外资司三者间流动。这期间存在很大的寻租空间,如,分批分期的向企业提出补充意见或者拒批,就为企业“活动”提供了时机和方向。而在此机制下,郭京毅利用人脉关系开创了自己的“村委会”, 扭曲行政裁决过程。外资企业将寻租意图连同相关资料一并报呈外资司;外资司原副司长邓湛与条法司巡视员郭京毅、处长杜宝忠合谋;一方面将思峰律师事务所推介给外资企业,暗示其收租意图,另一方面,将所谓“法律意见”,即如何逃避法律规制的信息传达给思峰律师事务所;外资企业将租金以“咨询费”的形式交给思峰律师事务所,并按照其指示改进材料,最后将补充完善的材料交给外资司;外资司与条法司对资料正式进行“会签”;最后两司审核同意后下发正式批文;而最终与思峰律师事务所分享租金。随着时间的推移,当“思峰村委会”成为一种潜规则后,整个扭曲的行政裁决过程便简化为外资企业直接联系思峰律师事务所,由其作为纽带与外资司和条法司沟通运作。
三、政府规制失灵的双重激励机制
(一)内部激励机制
1.理性经济人对“帕累托改进”的追求
这是最根本、最强劲的内部激励。“政府中的每个成员都首先是他自己本人,然后才是行政官,再然后才是公民” ①作为“他自己本人”,必然更多的表现为“经济人”的一面,而对“帕累托改进”的追求便是其自然之举。在规制者和企业家的范围内,寻租不失为一种“帕累托改进”,它通过对现有产权进行重新分配,获取体制内无法给予的高额利润。
郭京毅案中落马的司局级高官都曾被称“未来海阔天空”,然而在政府规制行为过程中,出于其“经济人”自身的利益考虑,遵循“趋利避害”和“利益最大化”的行动逻辑,利用知识和权力,通过立法创租、执法设租,获取了狭义范围内的所谓的“帕累托改进”。
2.政府规制成本的双向驱动
政府规制成本包括制定成本和游说成本。其中政府规制的制定成本包括直接成本(即由试试规制所耗费的人、财、物构成)和间接成本(即机会成本和其他规制引致的成本),其承担者是政府,因此,具有一定的硬约束性。政府规制的游说成本主要指各集团的组织费用和寻租费用,均由政府规制对象承担,并且其中的寻租成本可以转化为规制机构及其人员的收益。正如上述分析,具有“经济人”面相的规制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在降低制定成本和增加游说成本(进而增加收益)的双重驱动下,更倾向于做出创租、设租以及收租的选择。
3.非选票约束下的扭曲目标
据佩尔兹曼规制的立法模型,立法者作出规制决策的约束条件是使其所期望的选票数最大化,政治家所选择的规制政策,要满足选票数的最大化,同时还将使政治的边际替代率等于企业利润与消费者盈余之间的相互转移的边际替代率,从而达到一种均衡。但处于转型期的我国并不存在该规制模型,公众的选票无论是对于立法者,还是对于规制执行者都不存在约束作用。这就使得规制机构与规制对象的目标一致化,即利益最大化,并在此驱动下,被利益集团俘获。
(二)外部激励机制
1.政府规制需求偏好弱显示机制
西方的政府规制是基于成熟市场经济中出现的市场失灵,而我国正处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阶段,政府规制仍拖着“家长式”政府管制的影子。因此,我国至今都没形成真正独立的成熟的规制需求主体,与其相对应的偏好显示机制也未得到很好的建立。在此,本文将规制需求群体界定为企业和消费者。目前,我国中小型企业均没有能力依据自身偏好影响和制约政府规制行为,而即便是有一定议价能力的大型企业也大都与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能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独立”。而我国的众多消费者,由于自身缺乏偏好表达意识和能力,加之集体行动的“搭便车”效应,更是无法影响政府规制。这一切构成的政府规制需求偏好的弱显示机制,促使规制者更轻易的扭曲规制过程。
2.信息不对称
规制机构与被规制企业间的信息不对称。企业,作为政府的被监管对象,为追求其利润最大化,不会有将其信息完全告知政府的动机;规制机构方面,由于缺乏有效的激励,获取相关信息的积极性不足,而且,由于有限经济人的现实存在性,规制机构很难准确了解企业自身的成本、需求结构、发展现况等信息。正如斯蒂格利茨所言,“不完全信息和不完全市场作为市场失灵的一个来源在公共部门里是普遍存在的”。
公众与规制机构间的信息不对称。与国外的情况不同,镶嵌于我国社会的“委托-代理”结构,不是国会与政府的关系,而是公民与规制机构间的关系。由于政府规制决策本身具有很强的专业性,普通公民对此并不熟悉;而相关规制机构由于长期从事相关领域工作,对相关产业也有较为深入的了解。这就必然导致公众与规制机构间信息的不对称。郭京毅案中涉案人员正是利用自己对司法专业知识的了如指掌和公众对此领域的陌生,利用两者的信息鸿沟,滥用权威发生寻租行为的。
3.缺位的监督机制
政府的性质决定了政府规制监督的不易性。一方面,规制者也是垄断者,其行为是难以得到有效监督的。另一方面,作为一种公共管理行为的政府规制,既具有追求效率、效能和收益最大化的管理属性;又具有强调责任性和回应性的政治属性;同时仍具有致力于平等保护公民权利的法律属性。这使得规制者的行为效果难以测量,并且规制者可以利用自己的优势在多重属性间进行切换,从事自己有利可图的工作,产生所谓的“套利行为”。
行政立法程序封闭导致的部门利益法律化倾向,为政府规制者的趋利行为开辟了广阔的空间。政府规制立法过程本应是政府、企业、消费者全面互动的过程,但目前我国并未吸收各种利益主体的广泛参与,加之上述需求偏好弱显示现象,主导整个规制立法过程的往往是部门官员。缺乏完善的、透明的规制程序导致规制机构难以中立和独立,出现明显的部门利益法律化倾向,为政府规制者的趋利性提供可能性。
〔参考文献〕
〔1〕孙亚忠. 政府规制、寻租与政府信用的缺失〔J〕. 理论探讨, 2007,(01).
〔2〕卢梭. 社会契约论〔M〕. 北京:商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