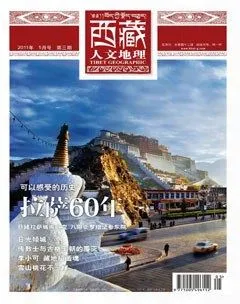八廓街罗增坚参东院
2011-01-01尹文涛
西藏人文地理 2011年3期




自大昭寺广场北侧向东步行5分钟,穿过熙熙攘攘的老街,就走到了我要寻找的一幢土石结构的老院,这里叫“罗增坚参东院”。它坐落在拉萨老城区繁华的中心地带,属于城关区鲁固社区。这个院子是1951年和平解放以后建造的,最初是土木结构的二层院落,大多一家人住在一个小房间里,主要解决进藏部队转业到地方工作的和从内地直接来西藏工作的政府机关职员的住房。1991年政府投资重新翻建了这个院子,建成土石结构的三层院落,分为东、中、南三个大院,每院大致有40户居民,解决了很多当时有困难的居民住房问题。后来在这个院子里生活的有在政府机关供职的人,有在八廓街做生意的人,也有从外地来拉萨打工的人等等。这几年,政又出资对八廓街周围的老屋进行了维修,改造了水电系统,在保护旧建筑的基础上,又改善了居民的生活条件。鲁固居委会主任强巴跺着脚下的天台说:“这就是阿嘎土,藏族人用它铺设屋面,又防水又结实,和水泥一样。”
强巴主任说,这个老院是一个藏、回、汉三个民族混居的院落,藏族人口占大多数。但相对来说东院汉族居民多一些,尽管各自的宗教信仰不同,风俗习惯不同,居民们团结友爱,相处和睦,生活和谐。的气氛浓厚,社会治安状况良好,成为了民族团结的典范。
一、烈士的后代
一进东院大门,是一个不大的天井小院,地上铺着不规则形状的青石板。四周是住房,二楼三楼各有一个小小的露天走廊,走廊边还竖着一排低矮的铁花护栏。这个小院的住户大多是里外两间,因为是不规则的格局也形成了一间和三间的住户。
一楼的一户人家,主人名叫黄强,生长在拉萨,古铜色的脸庞常常带着一幅墨镜,一年四季总是一身保安员的制服,当在广场执勤时手上时常拿着一部对讲机,一付公职人员的作派,凌然不宜接近的感觉。他是一位汉族人,更严格地说是半藏半汉的团结族。他的父亲叫黄克勤,革命烈士,生前曾任18军53师独立营的连长。黄克勤1951年随大军进藏,和平解放西藏后转业至刚成立的拉萨市公安局,1974年因公去世。黄强的母亲是藏族,名叫强巴,退休前也是一位公安干部。黄强是家里的长子,他十几岁时父亲去世,兄弟姊妹4个就在母亲的抚养下长大成人。黄强的妻子也是一位藏族人,如今已经从天路公司退休了。现在黄强的母亲和其他的兄弟姐妹都已经搬出去住了,只有他们一家人还留在老院居住。黄强和女儿都在广场一带上班,说来倒也方便。女儿在广场旁边的德克士餐厅已经工作了6年,近年当上了大堂班长。
除了过春节要比这里其他的藏族居民要重视一些之外,其他方面黄强一家和藏族百姓的生活几乎是完全一样的,他们已经彻底的融入了这里的生活。
二、坐飞机买菜的年代
老院中的东院现在还有43户人家,原有的住户还剩下不到一半了。由于自治区大力推进的城市安居房政策,大部分原有的住户已经迁出老院,搬入新居了。其中就有我的朋友次平和索玛米两家,他们也都是18军的后代。次平的父母都是汉族;索玛米的母亲是藏族。
次平从小就生长在拉萨,他回忆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拉萨生活说:当时在老院里谁家有青菜吃了,就能肯定他家来了内地的亲戚或朋友。因为当时西藏只有土豆和白菜,从内地来拉萨的亲朋多数是坐飞机过来的,一般都要买些青菜带进来,一些难得的绿叶菜和一些豇豆、青椒、茄子之类能长时间存放的菜类。有了青菜的人家会把青菜当作宝贝一样地送一些给亲朋好友,自己家里也有限度的改善一下生活。次平说,那时家里最好吃的一道菜是大白菜加粉条和红烧肉罐头一起炖。
次平说,当时家里买不到肉,因为拉萨那时是凭票供应。父亲就去打渔,在拉萨河里打渔。父亲每周都去,有一次带着次平一起去打渔。拿着渔网到一个浅滩,让次平站在一边,叫次平拉着网别放。父亲就淌水到河的另一边,过了一会,父亲喊:“收网!”次平手上感觉突然一沉,使劲往上拉,一看网里全是噼啪蹦跳的鱼。我爸把鱼放在自行车后座上,让次平坐在前面的大梁上,骑车回来。到家烧了一锅很香的鱼。那年次平才10岁。
三、名字中的历史烙印
虽然黄强和其他3个兄弟姊妹都生长在西藏,藏话说的很好,完全成了地道的藏族人,但由于父亲是汉族,他们最初取的都是汉族的名字。但是后来弟弟妹妹们还是把户口本上改成了藏族名字。至今,兄妹里只有黄强保留着汉族的身份,但他的儿女已经不愿意继续延用老爸的身份了,在填表格时,民族一栏里选择了藏族,大儿子名字叫次仁旺堆,二女儿叫央拉。他们觉得这样和朋友们相处才不会感觉别扭。
索玛米和哥哥不仅属于藏二代,很特别的是他们还带有藏回身份,即藏族信仰伊斯兰教的人。索玛米的哥哥叫哈桑,在文革时家里又分别给他们俩取名红胜和红卫。小时候父母把他们寄养在四川老家,老家人又给哥哥取名罗雪来,意思是从雪山上来的孩子;弟弟因为很瘦小被取名为罗川竹。长大后哥哥继续使用罗雪来的名字,身份证上的名字也是罗雪来;而弟弟身份证上用的名字是索玛米。索玛米是一位画家,在自己的绘画作品上常常签名川竹•索玛米。我认识的另一个藏族朋友名字叫卫东,是文革中起的名字,一直沿用到现在,而他藏族名字次丹,别人却很少提起。这种名字中包含的复杂意蕴可以说是一段民族融合的历史的烙印。
四、藏装的魅力和气势
藏族服装在我眼里是一道很有韵味的风景,但在拉萨的固定居民中已经很少能看见这道风景。这些在城里工作的人,平时都是西式的服装,只有到了过年过节才能包揽令人眩目的民族服饰风采。当黄强知道我对藏袍的喜爱后,很高兴得发出了邀请:“再过几天是藏历年了,你来小院看吧!准保让你看个够。”几日后,我如约而至。刚踏进小院迎面几个嬉笑玩耍的小姑娘一下吸引了我的眼球,她们穿着节日的藏装手挽手的正在玩耍。平时看惯了他们穿着蓝白相间的校服,只是感觉到她腼腆沉静尤其是上初中一年级的卓嘎,暗红的绸缎藏装,领口袖子露出浅粉的衬衫,乌黑的长发别着亮晶晶的发卡,高原少女特有的肤色显着可爱,一笑露出浅浅的酒窝和洁白的牙齿。
换上藏装的黄强与之前穿制服的他,可谓判若两人。那股 “气势”的改变的确不只是表面上的,而是由内而外透露出一种魅力。高大的皮帽让他身高陡增,厚重的皮靴让他步伐稳健,肥大的藏袍让他身形魁梧,宽阔的兽皮镶滚让他气派十足。我对黄强一下子从平视变成了仰视,并不由地从猎奇转为赞美。
服装的中西合璧在央拉身上显着一览无余,她穿一件咖啡色印花藏袍,外罩一件粉红色小夹克,显得既时尚又成熟。
五、等待安居房
现在老院里一部分房屋租给了外地来的生意人,这里租金便宜,交通方便。随着火车的开通,外来务工经商的人员越来越多,老院的房子也更加抢手,不断有外地客人到这里来求租。
与此同时,原有的本地住户不断外迁,老住户已经越来越少了。黄强家算是老住户之一。但随着大儿子的结婚,目前家里住房确实显着有些紧张了。他和妻子还有大儿子和儿媳妇再加小女儿,5个人住在两间屋中,每间各16平方米,平均每个人6平方米多一点,这远远低于城市安居工程人均面积最低标准。不过这个问题也即将得到圆满的解决。西藏城市安居工程建设采用“政府主导,公助民建”的方式,包括拉萨市补助资金,城关区补助资金,群众自筹资金和贷款金额政府贴息等政策,构成了一条龙解决方案。对于住户本身几乎不存在太大的经济压力。目前城市安居工程已经完成了第三批,黄强家有望在第四批中解决住房问题,搬出老院。他高兴地告诉我,街道已经叫他填写了各种住房表格和住房申请,已经办完了很多手续。在这之前因为大儿子结婚,他已经向街道申请廉租房,街道已经同意。这几天大儿子就可以先搬过去布置新房。可以说在内地最让人头疼的住房问题,在西藏基本不算太难的问题,没有几个人因为房子的事情太过愁苦。正如次平感慨地说:“现在拉萨本地的居民,哪家没有两套房子,哪家没有一辆汽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