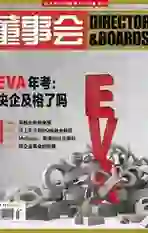为股东协议正名
2011-01-01章六红
董事会 2011年3期
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都只能关注常态——即所谓“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问题,而股东的个性化需求、应急管理以及一些未雨绸缪的事宜则应当交由股东协议负责
在公司治理实践中,股东协议大量存在,尽管其作用独特而巨大,但并未引起立法、监管等有关主体的应有关注。
常见的也是合理的
顾名思义,股东协议即股东之间的协议,其大量存在自有合理性,是现实的市场逻辑所致。显然,这个定义只是划定了一个大致的轮廓,其界限可以说比较模糊。然而,模糊正是股东协议的一个巨大优势。股东协议凭此能有效应对公司治理及市场交易的巨大复杂性与高度不确定性,也有效节省了日常治理实践中的交易成本。
公司股东人数众多、公司股权结构复杂以及公司经营范围的广泛等特征,都有赖于股东协议的登台献技。依照公司法的规定,尽管最为依赖股东协议的有限责任公司其股东人数并不算过多(50个以下股东出资设立),表面上看起来似乎不算复杂,但由于股权结构具有高度复杂性,而这两者之间近似于一种乘积关系(非简单叠加关系),因此股东规模的简洁优势瞬间荡然无存。以出资方式为例,按照公司法规定,股东可以货币、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等多种方式出资,而每一位股东的出资方式并不受限制,此其一;再者,伴随公司的存续,股权结构又会不断发生新的变动,譬如老股东的退出、新股东的加盟,再如出资额的增减、出资方式的变更、出资资产的价值评估等,都是这种复杂性的不断演绎。治理不断走向复杂,但这还远未到极致,我们还必须考虑到公司面临的市场竞争、来自消费者的影响以及宏观政策调控等。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影响因素的众多,而是这些因素的影响具有高度不确定性,比如环保政策对企业能源消耗的调节(拉闸限电),再如某一品牌的产品质量事件引发全行业品类的信任危机,这些不确定性在当前社会转型时期极易被触动诱发。联系到股东利益上,对这些问题仅依靠公司法、公司章程应对,毋庸置疑又力不从心。可以说,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都只能关注常态——即所谓“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问题,而股东的个性化需求、应急管理以及一些未雨绸缪的事宜则应当交由股东协议负责。
从交易成本看,股东协议与公司法、公司章程等都具有节省交易成本的作用。不过,公司法与章程可以有效节省企业事前的交易成本,而对事中及事后出现的一些问题却无法着力或者作用有限,股东协议由于具备高度的灵活机动性和股东的同心协力,不论是信息搜寻、谈判决策还是监督协议的执行都能保持良好效率,这是其独到之处。
灵活的治理工具
人们在谈及股东治理问题时多将注意力聚焦于限制大股东、保护中小股东利益方面,但中小股东尤其是上市公司的中小股东,其本身参与公司治理的积极性是存在疑问的。中小股东们更关注短期的投资收益,相形之下,部分大股东却更关心企业的长期价值。以利润分配协议为例说明,中小股东与大股东间可能会达成在任何经营情况下均要求分配红利的协议,但当公司处于亏损之时,这种协议就会损害大股东、企业的整体价值。因此,这种股东协议显然不具有正当性,这就需要立法的介入。
当然,股东协议更多地作用于有限责任公司治理领域。众所周知,有限责任公司更为注重人合性而非资合性,因此这里的大小股东之间的利益博弈更紧密地联系着企业的命运。上市公司的中小股东能保持“理性冷漠”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其可以“用脚投票”,而有限责任公司的退出机制在立法层面则困难得多。所以,尽管有股东派生诉讼等手段可以保证中小股东利益,但并不能解决在出现公司僵局、大股东主导控制却不违法等情况下中小股东的利益诉求问题,譬如优先购买权及利润分配问题等。而基于这些事项的复杂性以及可能的秘密特性,章程并不能发挥多大作用,可以依靠的便是股东协议了。以Clark v. Dodge案为例:双方约定少数股东可持续在公司